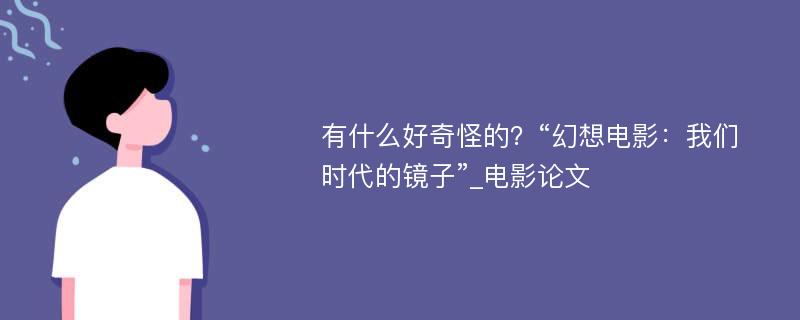
何奇之有?——质疑《奇幻电影:我们时代的镜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镜像论文,奇幻论文,时代论文,电影论文,何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持人导语
观看、鉴赏、研究电影可以有很多种方法,有所谓从社会、作者、观众出发的外部研究,也有从叙事、场景、人物出发的内部研究,所有这些都是借助影像来说话的。正是在此基点上,我们提倡电影研究的影像本位意识,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或提法上的标新立异,而是希望建立一种明确的批评意识,即无论影片与社会热点的远近如何,与人生的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如何,电影的本质是影像的,因此,关系影像的真假之辨其实是无意义的,影像就是影像,影像是批评的基础。本文对“奇幻电影”的驳论,从元语言的角度出发立论的。
黄文达(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
读《文艺研究》2007年第1期文章《奇幻电影:我们时代的镜像》(以下简称《奇幻》),觉得这是一篇书写相当规范的论文,从提出概念到论证概念外延、内涵直至新事物产生的社会原因,有条不紊、中规中矩值得称道。然而,对于这样一种完美形式之下所表述的内容则不能令人信服。下面我将按照原作的顺序对作者的观点提出质疑并表述自己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
关于奇幻电影概念的外延和内涵
《奇幻》作者将“奇幻电影”定义为一种新出现的电影类型,这种电影类型的外延和内涵均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
外延:1、与现实世界没有关系(比童话片复杂);2、形式上的中古世纪风格(以之区别于科幻片);3、幻想内容的写实表现(以之区别于宗教片、灵异片、神怪片等)。
内涵:1、表现的奇观化;2、历史的虚化;3、存在的无根性。
《奇幻》一文讨论奇幻电影概念外延的目的是要将这样一种电影类型与其他类型的影片相区别,只有这样才能够说明这一类型是“新社会”的产物,它与所有“旧社会”所产生的电影类型有所不同。我们姑且暂时认同这样的界定,然后在“旧社会”的影片库中找找看,是否有同时符合外延和内涵三个条件的影片,如果有,说明《奇幻》作者的界定不能成立,其认定的美学原则也将被彻底推翻。
这样的影片其实并不难找,因为《奇幻》一文对于外延和内涵的界定不可能将所谓的“奇幻电影”从传统的各种幻想类影片中区分出来。1926年由著名电影大师茂瑙拍摄的默片《浮士德》(Faust),便能够完全满足“奇幻电影”的所有要求。1、对于外延来说,这部影片是在摄影棚中拍摄的具有神话色彩的影片,与现实世界无关,也不属于简单的童话故事;2、形式上也能够满足中古世纪的风格,因为“浮士德是德国十六世纪民间传说中一个神秘性人物”,①影片的造型和细节都与故事中所表现的那个时代相关;3、影片内容有写实的细节表现,如浮士德与人决斗杀人、最后爬上已经点燃的火刑台,请求被自己遗弃的女人原谅等等。从内涵来说,1、影片中出现了许多天堂、魔鬼的画面,可以算是奇观化。尽管因为科技手段发展的原因,当时的制作水准不可能与今天的相提并论,但是影片在当时观众心自中所造成的奇观效果,一点也不会亚于今天的奇观大片之于今天的观众,甚至有可能超过;2、《浮士德》是一部根据民间传说改编的电影,自然是虚化的历史;3、“存在的无根性”要求“故事中人物的性格、行止不是由影片中切实的存在处境规定的,而由传奇化的剧情预先决定”。浮士德与魔鬼签约,从而能够保持永远年轻,这显然符合“传奇化的剧情预先决定”。如果孤证不能作数,还可以举出日本著名导演新藤兼人1968年拍摄的影片《黑猫》。这是一个有关某武士打完仗回家后,发现自己的妻子和母亲在战乱中被杀后已经变成了厉鬼,从而与之斗争的故事。故事发生在日本的战国时代(满足外延2和内涵2),在一片竹林中,林中的鬼屋时隐时现,美女时而人形,时而化作黑猫(满足外延1和内涵1),过往的武士往往遭到诱惑而被杀害(满足外延3),唯有这位武士得到了厉鬼的款待(满足内涵3)
……
诸如此类的电影,还可以找到许多。这一方面说明《奇幻》一文的界定并不能将“奇幻电影”从其他的幻想电影中分离出来成为具有独立意义的类型;一方面也说明作为一种以奇观为主要吸引观众手段的电影由来已久,并非在现代刚刚出现。
或许有人会说,这不是“奇幻电影”之过,而是《奇幻》作者没有将“奇幻电影”的概念梳理清楚。如果能够认同这一说法,那么我们便可以讨论问题的关键所在了,这就是“奇幻电影”究竟是不是一种新出现的类型或样式?如果是,一定能够从中找到不同于过去的特征;如果不是,便不可能找到具有独立意义的特征。《奇幻》作者之所以不能够给出明晰的定义,在于未能仔细考察电影的历史,特别是有关奇幻表现的电影的历史。强调奇幻作为当代电影新类型的说法,事实上是割断了我们的历史,仅从一个褊狭的角度来看待电影(包括文学)这种已经具有百年积累(对于文学来说也许是千年)的艺术样式。从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那些最主要的“奇幻电影”,如《指环王》、《哈利·波特》等,基本上脱不出传统科幻、②灵异、神魔电影的格局,至多是在某种程度上样式的混合或技术上的提升。
作为“奇幻电影”这样一种说法或称谓的存在,其实并没有值得特别批评的价值,因为语言上的“喜新厌旧”,如同更衣、换口味一样,也是人类的本能。清朝人把“湖”称“海”,南方人把“喝”说成“吃”、说成“饮”,都不能改变事物自身的属性。当我们坚持一个不同的称谓代表的是唯一独立存在的事物而不是某一事物的别称,便需要将这一事物与相类似的事物进行对比,以显示出其所特有的意义。文化历来都是传承的,而且世界上大部分地方的人群,都是以这种文化传承为荣的,因此,每当有人宣称与历史传承“一刀两断”的时候,我们都不得不小心求证。
关于消费时代
既然“奇幻电影”作为一种“新”电影类型不能成立,那么其产生于消费时代的论证自然也就不能成立。但是,《奇幻》作者给我们画出了一个环环相扣的因果链:首先是“奇幻电影”造就了各种“幻象效果”,然后是“幻象效果”营造出“游戏化”,“游戏化”释放出“游戏欲望”,“游戏欲望”使观赏主体专注于“自己的欲望”,最后达成了消费时代中所特有的“欲望消费”。因此,这种“欲望消费”可以用来解释“奇幻电影”的产生。需求刺激生产,这是常识。因此,如果我们不能指出这一因果链中的哪些环节出了问题,同样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质疑。
《奇幻》作者在文章中使用的是鲍德里亚的消费理论,这个理论告诉我们,当商品生产过剩的时候,它们就会成为带有文化性质的符号并从商品的本身漂移开去,此时的消费变成了一种“欲望消费”。对于一般商品来说这不难理解,购物的兴趣在于消费,而不是指向商品,所购商品或堆放在家里,或送人,或观赏,商品本身的价值被弃之不顾,真正被消费的是消费者的“欲望”。但是对于信息类的商品来说,一次欲望的消费和一次商品的消费并不能被完全区分清楚,过去的人去看电影是为了娱乐,今天的人也是为了娱乐。当然,在过去的电影娱乐消费中往往还能得到知识、教益、审美,也就是一般所谓的“意义”。而在今天,也就是在后现代的意义上,电影娱乐消费中不再含有过去的“意义”了吗?从理性上推理似乎应该是这样(我们确实也看到了这样的电影,如《杀死比尔》,但消解意义的大部分作品并不是奇幻大片),否则欲望的消费和非欲望的消费在电影来说就无法区分了。但是《奇幻》的作者做出了否定的回答,认为西方的“奇幻电影”并没有放弃意义的底线,放弃意义的是那些东方 (中国)的“奇幻电影”,并认为对于“欲望消费”“不能给予太高的评价”。这也就是说,产生于消费社会的文化产品未必都是后现代的,未必都是“欲望消费”。悖论由此而产生:《奇幻》作者坚持认为“奇幻电影”是消费时代的产物,但又不承认其对于意义的消解。——或者说只是在部分的意义上,在中国“奇幻电影”的范围内才认为是“欲望消费”。这样一来,“奇幻电影”作为消费社会产物一说的基础便不再是坚实的。
再来看作者对于东方“奇幻电影”的批判,也未必站得住脚。这也是当今社会的时髦,对中国娱乐大片一派“苦大仇深”的声讨。《奇幻》作者举国内影片为例,认为张艺谋、陈凯歌的影片“服从于欲望的消费逻辑”。换句话说,张、陈二人的电影被认为是消解意义的。如果《奇幻》作者的结论是正确的,那么,他们的电影应该受到年轻人的激赏,同时为年龄稍大的观众群体所拒绝,这才是正常的逻辑推理。但事实恰好相反,谙熟后现代“消费文化逻辑”表现的年轻一代不能接受张、陈两人的电影,能够接受他们电影的正是年龄稍长的、观念传统的一代(这可以从骂声一片和票房满满这两个极端现象中看出)。逻辑的推理应该是张艺谋、陈凯歌与消费社会的后现代表现无关。③——但不能说他们与“奇幻电影”无关,是《奇幻》作者将“奇幻电影”与消费社会的后现代性强行捆绑等同,才得出了如此自相矛盾的结论。
从《奇幻》作者所例举的西方奇幻大片来看,这些影片往往寓教于乐,对于主题意义的强调与传统的影片并无差异,因此《奇幻》作者也不得不承认,“按照传统的价值标准,奇幻电影有太多值得质疑之处”。尽管如此,《奇幻》作者依然坚持认为“从奇幻电影流行的强度和时间长度来说,我们得承认,它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电影类型”。我们不知道“电影流行的强度和时间长度”是否也能够作为一种区分电影类型的标准,至少迄今为止还从未听说有人使用这样的方法来区分电影的类型,《奇幻》作者也未在文章中做出定量、定性的分析。在一篇论文的结尾使用这样的判断,不仅推翻了作者文章中所有的推理和结论,而且也让人觉得作者对自己的研究所持的态度是不够严肃和轻率的,这也是某种后现代的游戏?
关于电影中的游戏
除了对“奇幻电影”是“欲望消费”之作品存疑之外,《奇幻》作者对于“游戏”一词的使用似乎也有问题。因为“欲望消费”之“欲望”被作者归之于游戏的欲望,于是我们不得不讨论有关游戏的问题。作者在这里使用的显然不是广义的游戏概念,因为广义的游戏概念“系指为娱乐所做任何的消遣和活动。包括玩玩具、参加体育活动和看电视等”。④简而言之,可以包括所有的艺术活动。类似的说法不但可以在字典中查到,同时也可以在康德、赫伊津哈、加达默尔等人有关游戏的论述中查到。⑤如果电影本身就是游戏,那么这个问题便无从讨论了,我们总不能说电影中的游戏是从1895年电影诞生的时候便开始了。因此,《奇幻》作者所讨论的游戏必然是狭义的游戏概念,狭义的“游戏”有一个公认的重要特征,这便是假定性。弗洛伊德说:“尽管孩子聚精会神地将他的全部热情付给他的游戏世界,但他很清楚地将它和现实区别开来。”⑥对于我们的讨论来说,一部电影中的游戏假定性必须是对元叙述的故事结构框架进行假定,而不是故事本身对于现实的假定。至于故事结构的框架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并不重要,游戏只是在某一个固定区域内的具体的行为,而不是形而上的判断。以这一标准来衡量,几乎所有的“奇幻电影”都不够游戏的资格,也就是说,这些影片并没有进行游戏,或者说没有出现真正的游戏的行为。什么是电影中的游戏?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有待讨论和研究的问题,但可以确信的是,游戏已经出现在电影之中,比如像《罗拉快跑》这样的影片,便是在游戏。影片内部所叙之事在同元叙事“开玩笑”,也就是相对元叙事的结构框架来说,其内部部分的叙事具有假定的成分,罗拉跑回去找钱这件事是假定的,并非在故事中真的发生,而只是可能发生,由此我们可以确认这里具有游戏的成分。相对于一般的“奇幻电影”来说,如果不能在它的元叙事框架之内找到假定的成分,我们便不能轻易说游戏。《无极》中满神的预言如果是假的,我们便可以说那是在游戏,但很遗憾,满神的预言一一兑现,元叙事紧紧地控制了每一个叙事的因素,没有任何松动。因此也就没有理由认为这部电影是在游戏。——有关游戏的问题不可能在这里全面展开,但我们可以确认,对于“奇幻电影”来说,说它是游戏显然还不够充分。
通过对于“奇幻电影”的讨论,我们倒是真的可以发现一些时代的镜像——这就是对历史和传统的遗忘(也有理论家称之为“断裂”)。这里说“时代的镜像”显然不是指某个人或某篇文章,而是应该反思我们的教育和信息提供系统为什么会造就一代人对整个传统的遗忘?西方社会早在几十年前便已经跨入了富足,也能够看到形形色色的“遗忘”,但是作为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它始终没有让“遗忘”成为一代人共同享有的事实(作为个例,德国青年曾“遗忘”过纳粹的历史,但他们后来做了“亡羊补牢”的工作)。对于需要讨论的电影类型来说,对于没有看过的电影、没有了解的电影史来说,我们显然不应该选择遗忘来创新,尽管遗忘可以使“创新”变得理直气壮和唾手可得。但历史并不会因为某些人的遗忘而不复存在,它总会在某个时刻以某种方式现身,使所谓的“创新”立现颓败——就如同发生在“奇幻电影”中的一幕。
至此,我想我已经把我的质疑说清楚了。显然,这仅仅是质疑,并没有花费太多的精力去建立“破坏”之后需要建设的东西,这是因为我想尽量把需要探讨的问题集中,同时也不希望将文章写得太长。建设的工作可以在另一个题目之下继续。
注释:
①[德]歌德《浮士德》,董问樵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7月版,译序第3页。
②请注意,科学幻想电影从来就不是讲科学的。参见拙著《类型电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3章。
③参见拙作《爱欲之沟和笼养鸡的童话——张艺谋、陈凯歌电影接受的社会学阐释》,载《当代电影》2006年第5期。
④《大美百科全书》,台北,光复书局1990年12月版。
⑤[德]康德《判断力批判》,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1月版;[荷]约翰·赫伊津哈《游戏的人》,多人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10月版;[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7月版。
⑥[奥]弗洛伊德《创作家与白日梦》,林骧华译,载伍蠡甫主编《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1月版,第13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