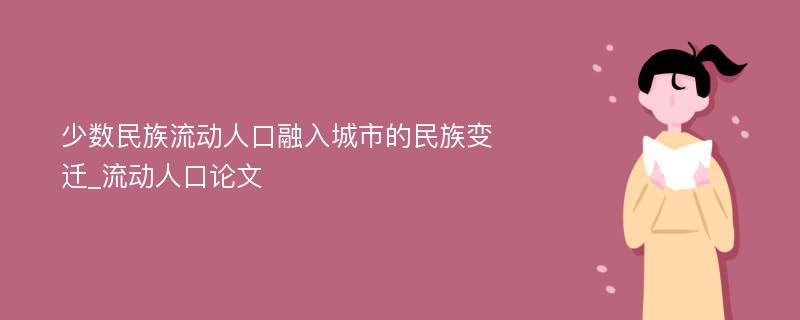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中的族性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流动人口论文,少数民族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65X(2015)04-0034-06 党的十八大以后,伴随着“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的不断深入,城市已逐渐成为族际交往的主场域。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4》中统计,当前我国流动人口的总量已达到2.45亿,超过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在此背景下,当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规模已达到3000万,其中大部分都流向了中西部大中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与此同时,由于中西部地区存在着较大的城镇化空间,中西部大量农村汉族人口也快速向中西部城镇涌入①。由此可见,各民族跨区域的族际流动和城市空间内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将成为当前和将来一段时间民族关系的重要特征。 在族际流动的城市背景下,虽然少数民族成员身份具有先赋性和稳定性,但少数民族成员的族性特征却可能随着城镇空间场域的不同而呈现出增强或削弱的态势。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过程伴随着族性的保留、维系与重新建构,呈现出很强的弹性机制,与当前多民族社会结构的失衡、紧张或稳定的不同状态密切相关。因此,研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过程中的族性变迁特征对于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空间融入、文化融入、情感融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中的族性及族性变迁 在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伴随着民族主义浪潮的不断席卷,族性(ethnicity)研究也提上日程。从理论上解释,族性既意味着族群实体,也意味着族群意识,具有双重含义。本文更强调族性的民族意识与民族认同,主要从族性产生的主观视角进行考察,更强调作为一定民族成员身份的人们的民族认同、民族责任和民族意识等主观因素。 基于族性的主观视角,分别有原生论和场景论两种理论基点。在原生论理论视域下,族性来自“既定禀赋”,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先赋性。如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z)认为族性是原生的,它是一种优先于其他的、符合逻辑和情感的核心认同形式。它根深蒂固,与心理需求甚至生存本能有着密切的关系②。而英国学者戴维·米勒(David Miller)对与族性相关的另一个词语民族性(nationality)进行了直接定义,他认为民族性具有五个要素,即由共享信念和相互承诺构成;在历史中绵延;在特征上积极的;与特定地域相联;通过其独特的公共文化与其他共同体相区分③。在米勒看来,民族性涉及民族认同,它意味着民族成员对民族团体的个人认同;民族性涉及有界限的伦理责任,它意味着民族成员对民族共同体负有伦理义务;民族性涉及民族政治主张,它意味着特定地区组成民族共同体的人刻意正当地主张民族自决(自治)④。 这些原生论的族性定义认为,族性具有区别自我和他者的主观特质,即不同民族身份的普通民众个体在社会交往进程中,感知到了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差别,隐约体会到了“自身”和“他者”之间的不同,但这种感知又难以说清楚,一般被理解为“族性”。在族际流动的背景下,由于族性认同具有原生性和稳定性,即使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跨地域、跨民族流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族性认同仍然根深蒂固。 在工具论理论视域下,不同民族身份的普通民众有可能也有能力根据场景的变化对族性认知和表达做出理性选择,此时族性是民族个体或群体在特定场景中的策略性反应,也是民族个体或群体在进行权益竞争过程的一种社会工具。对此,戴维·米勒在《论民族性》中曾认为“民族性观念是一群人有意识的创造,他们对它加以阐述和修正以理解他们的社会政治环境”⑤。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rth)对类似的族际流动过程中的族性内涵曾进行了较深入研究。他认为族群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于,它构成了一个联系与互动的范围,拥有自我认定和他者认定的成员资格,因此构成族群的最重要原因在于社会边界,不在于地理边界,也不在于语言、文化、血统等内涵⑥。费孝通也曾经说过:“生活在一个共同社区之内的人,如果不和外界接触不会自觉地认同。……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民族的认同。”⑦此时,虽然族性具有原生性和稳定性,但随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族际流动性的加大,这种蕴含着民族认同、民族责任和民族意识的族性内涵和特征在不同民族流迁过程中,在不同场景下可能被激发或强化。 基于以上两种理论基点,一般的理论逻辑认为,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过程中,不同民族共同体的人们在大致相同的区域中互相接触,形成了一个综合的社会实体。在这一社会实体中,不同民族成员之间尽管在社会、生活领域,特别是商业领域不断相互接触、相互影响和相互依赖,但由于族性的原生性,其文化差异、认同差异、民族身份差异将继续保留下来,构成一个多元族性社会。在这种族群混合的环境中,族群边界在当地的基层社区中愈加清晰,即以族性为核心的民族边界会通过特定的文化、语言、宗教等因素限定自身,排除他人。特别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员与当地居民之间存在着经济、文化、社会、传统习俗及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使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镇空间场域中对自身的族性认知随之凸显。这种理论逻辑意味着,在族际流动背景下,不同民族的普通民众对自身的族性认知将经历一个从不清晰到清晰的动态变迁过程。 然而,这种族性认知凸显的变迁过程是否就意味着族性变迁的全部历程呢?事实上并非如此,进一步探究,就会发现族性变迁不是一种趋于单一动态变迁的过程,它本质上是趋于多元动态的、复合变化的社会变迁现象。随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不断深入,族性既有可能趋于内嵌和交融,也有可能趋于表达和彰显,地域的流动性与族性的自我修正之间的关系复杂多变⑧。 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中的族性变迁路径一——内嵌和交融 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过程中,往往经历了从简单的熟人社会的人际信任模式到陌生社会的适应与融入的过程。即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城市化进程中,由于不同民族对城市生活社会适应性的提升,族性认知在最终可能呈现出内嵌和交融的趋向。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现代性背景下的文化同质性 在全球化、城镇化背景下,现代性对个人消费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日益加剧。不同城镇和村庄的建筑特征、媒体文化、消费模式拥有许多共同的特质。在民族地区,也难以见到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建筑、饮食、服饰、语言和风俗习惯。在现代性逻辑下,相同的媒体和书本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吃、穿和读,如何适应现代化生活。原来带有鲜明民族性的生活方式日益衰落,即使有意愿选择一种不同于他人的生活方式,也难以实现。在此背景下,族际之间的地理流动性并没有表露出强烈的民族差异性。不同民族的人们在不同地域所感受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似乎并没有多大的不同。再加上初入陌生的城市,即使具有强烈的相异族性特征。民族成员也往往优先考虑经济利益,更愿意努力去适应新的城市环境,试图规避自身的相异性和族性以求融入城市。此时族性往往呈现为一种边缘状态,更多地表现为文化的统一性。这种文化的统一性在很大程度上是民族成员个人意识统一性的体现。 (二)官方民族主义的影响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曾提出“官方民族主义”概念,用于定义民族与王朝制帝国的刻意融合⑨。而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快速崛起,也伴随着统一的民族建构——中华民族的崛起。这种官方民族主义虽借用了安德森的概念表述,但它与西方社会官方民族主义不同,并不是对蔓延欧洲的群众性民族主义的反动,也不是表达出民族与王朝之间的矛盾。相反,这种官方民族主义是一种国家层面的国族建构,是国家与民族的内在相容。 但不可否认的是,官方民族主义的存在,仍然有压制与此相关的民族认同和情感的潜意识。一方面,族性在当前中国政治文化环境中,总是作为一种高级政治呈现。族性中呈现出越来越多的政治情感。在政治压制之下,族性往往被疏离,民族成员甚至不愿意谈及这一情感(可能是压制在内心深处),认为内心深处受到挑衅或担心政治施压而回避。如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调研过程中,往往都难以洞察民族成员关于自身族性的真实态度。另一方面,官方民族主义更强调政治忠诚高于民族忠诚。政府对民族团结的展示,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民族团结景象,更强调和凸显出政治忠诚的价值和意义。在此背景下,族性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这种状态主要体现在民族成员个体对族性的隐形疏离。 (三)东西部地区社会相互依存性的加强 当前,我国东部城市中的生活方式、高额工资、社会服务设施吸引着西部的少数民族,而西部城市中的丰富自然资源、巨大的劳动力市场和发展机遇也吸引着内陆乡镇的农村人口,这些城镇都由于族际之间的人员流动而迅速发展起来,所有这些因素都滋长了各民族相互依存的新环境。在各民族相互依存的过程中,伴随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不断深入,各民族成员和群体之间的经济、社会交往非常频繁,会促使各民族之间族性差异性的减少、共同性的增多。 正如戴维·米勒所指出的,族性呈现为一种功能性的东西,即人们更关注什么状态的族性能满足现代社会的需要,如何安全地控制族性这种火山爆发式的力量⑩。从现实视角看,民族认同和忠诚性是现代社会的人类难以消解的既定状态,但是疏导民族主义情感和渴望,使其朝着对他人造成最小痛苦和苦难的方向发展仍然是政府的首要目标。 因此,在族际的不断流动过程中,族性认知从增强到内嵌和交融,对族际流动人口的有效治理是政府所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标。然而,达成这一目标的过程注定是艰难的。因为在族际流动过程中,不仅伴随着族性认知的内嵌和交融,还伴随着族性的表达和彰显。 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中的族性变迁路径二——表达和彰显 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过程中,民族成员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阶层的关注远超过对族性的关注。然而,在高度流动的自由社会中,虽然族性看上去似乎在人们的生活中起着边缘的作用,但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往往被直接激发,使族性得以高调表达和彰显。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族性认知内嵌和消解的过程是失去自我,接纳他者的过程,往往会引发反弹 第一,流动性、短期接触和信息交流的匮乏都使得族际流动过程中社会排斥过程的产生。当不同民族共同体的个体跨越边界流动时,即使与其他群体的成员之间产生认同,但民族标签仍然经常存在,这是族性的客观呈现。换句话说,在一定情形下,族性往往趋向于把一群特定的人联系起来,并使其成为一个排斥外来者的共同体。挪威学者弗雷德里克·巴斯就非常强调族群并非是在共同文化基础上形成的群体,而是在文化差异基础上的群体的建构过程(11)。 此时,在日常生活中对族性表现冷漠的人往往在感觉到民族集体命运和民族集体政策受到侵害时,更能将自身福祉与整个民族共同体的福祉紧密相连。从而引发对族性的反弹。从理论上看,东方民族主义更倾向于引发民族意识的反弹。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认为,西方民族主义是公民——领土的,它基于共享共同地域的人们的理念,受一套共同法则的约束,参与共同的公民文化:而东方民族主义则是族群——血缘家系的,由共同的祖先和共享的祖先文化联结在一切的人们的理念(12)。抛开当代西方国家的愈演愈烈的移民问题不提,西方国家大多是单一民族国家,族性与公民身份之间,与国家之间是积极相容的。然而东方民族主义的呈现状态则有所区别。各个民族之间的祖先文化的差异及权威主义文化的压制,国族建构在文化领域往往出现更多的族群相异性,反而容易造成族性的反弹。 第二,族性表达彰显往往与情感价值认同有关,难以通过经济手段遏制。按照集体行动的逻辑,在经济人的基本假设下,个人付出成本使共同体获得公共性收益,然而个人只能获得行动收益的极小的份额,集团其他成员通过“搭便车”坐享其成,因此一般情况下,经济人或理性人都不会为共同体的共同利益采取行动。然而,族性的表达和彰显往往考虑的并非经济利益,难以用成本收益来衡量,而更多的是情感价值和认同意识。因此,在一些特殊的社会排斥事件之下,基于情感表达的族性反弹极为常见。 (二)在更为严重的社会紧张和排斥状态下,族性成为民族成员的民族标签,成为与政府谈判的筹码 当前,伴随着全球化、现代化、城镇化的不断深入,从农村进入城市和从小城市进入大城市的城市人口流动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的新常态。其中大量少数民族人口也因为工作、经商、读书、旅游、探亲、从军等各种原因进入附近城市或内地城市。这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虽然大多在短期离家后会再次返回原居住地,但由于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语言及社会认知的差异,很容易在城市生活进程中产生带有民族标签式的各种情绪。再加上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群体的交往交流交融形态与其他群体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形态相比有着显著的特点,如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交往交流交融时间较短,又同时具有跨区域性、民族身份的敏感性等。在这些特点的影响下,如果带有民族标签式的负面情绪没能及时疏解,则很容易扩展至其他地域或更多的少数民族群体,造成社会不稳定状况,甚至成为民族群体性事件的催化剂。 在涉及民族性的群体性事件中,西部城镇中较多发生的是族群分层,其主导趋势在于生产资源竞争日益激烈的两极分化,部分人获得较高的经济收益,而另一部分人则依赖政策优惠,双方都有强烈的相对剥夺感,更突显出族性的差异。东部城镇中较多的是利用民族标签来进行维权,利用族性来向政府争取更多的自身权利,从而使族性得以提升。 此外,在现代性社会中,经济发达程度越高,对个人与社会之间身份关系的思考会越来越深入。在族际的社会紧张和排斥状态下,从心灵深处唤醒这种族性的可能性也逐渐增大。安德森曾经描述了一种知识分子阶层在民族主义意识中扮演核心角色的情形:“作为双语知识分子,尤其是作为20世纪初期的知识分子,他们能够在教室内外接触到从超过一个世纪的美洲和欧洲历史动荡、混乱经验中萃取出来的关于民族、民族属性和民族主义的模型”。(13)而当前随着双语教育的普及和全球网络的快速发展,精通双语的、具有民族身份的人们已不再局限于知识分子,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往往精通两种或多种语言,了解不同的文化特征,具有民族精英的基本特质。当社会生活的日常民族情感问题受到忽视后,一旦出现伤害少数民族感情的严重社会事件,使个别少数民族群体形成城市偏见后,就很难有机会再改变其刻板印象,澄清误会。这是因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流动具有短期性特征,其人员不会长期停留在城市中。这些人群带着自身对城市的记忆和改造后的民族认同、意识返回原居住地,所流散的不仅是民族紧张关系,还有民族的刻板印象,会形成更多民族群体的负面记忆与认同的连锁反应。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当前城市社区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接纳和包容不够。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特别是流动经商人员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础在于经济流动。这些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从农村或小城市到大城市的过程中,习惯通过熟人社会获取相关信息,习惯在单一少数群体圈子内进行交流,属于单独被隔离的孤立群体。其自身与城市社区居民之间的日常生活联系并不紧密。再加上当前涉及宗教因素的暴力恐怖事件频出,城市居民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态度往往比较微妙,对个别民族频查身份证,宾馆拒绝住宿登记,出租车拒载等社会问题高发,极易伤害少数民族情感(14)。此时,相同的社会方式、消费模式的趋同伴随着文化碎片化、政治认同的不一致和语言、宗教的高度区分,在社会紧张与排斥的状态下,民族成员对族性的的彰显显而易见。 总之,族性似乎具有一种天生的凝聚力量(15),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过程中,它构成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群体认同的基础,很容易通过“族性动员”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个体分散力量加以汇集,从而构成涉及民族因素的群体性事件。要试图将族性的负面动员力量降至最低,并发挥族性的正功能,就需要认真考察,在族际流动这一场域下族性的变迁特征。 事实上,真正良好的族性状态的达成,必须从“如何理解自身作为这个或那个民族的成员,因此我们彼此之间应该如何行为以及如何对待外人”(16)入手。多民族共同体是依赖于相互承认而存在的共同体,族性是一种体现历史延续性的、根深蒂固的民族认同。在多民族共同体中,族性的最佳状态并非是族性认知的内敛或表达、彰显,而是一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的相互嵌入。正如戴维·米勒所说,族性的未来状态需要展望一种更为复杂的嵌套认同,这种认同的稳定性依赖于较大单位给予较小单位的政治和文化要求适当的承认(17)。 注释: ①王云芳:《促进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三交”应重视社会情感因素》,《中国民族报》,2015年7月24日理论版。 ②[英]爱德华·莫迪默,罗伯特·法恩主编,刘泓,黄海慧译:《人民·民族·国家——族性与民族主义的含义》,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 ③[英]戴维·米勒著,刘曙辉译:《论民族性》,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27页。 ④[英]戴维·米勒著,刘曙辉译:《论民族性》,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10-12页。 ⑤[英]戴维·米勒著,刘曙辉译:《论民族性》,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6页。 ⑥[挪威]弗雷德里克·巴斯主编,李丽琴译:《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代译序,第11页。 ⑦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第9-10页。 ⑧[英]戴维·米勒著,刘曙辉译:《论民族性》,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6页。 ⑨[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84页。 ⑩[英]戴维·米勒著,刘曙辉译:《论民族性》,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7-8页。 (11)[挪威]弗雷德里克·巴斯主编,李丽琴译:《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代译序,第10页。 (12)[英]戴维·米勒著,刘曙辉译:《论民族性》,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9页。 (13)[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31页。 (14)王云芳:《促进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三交”应重视社会情感因素》,《中国民族报》,2015年7月24日理论版。 (15)严庆:《族性与族性政治动员——族类政治行为发生的内在机理管窥》,《黑龙江民族丛刊》,2013年第6期。 (16)[英]戴维·米勒著,刘曙辉译:《论民族性》,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8页。 (17)[英]戴维·米勒著,刘曙辉译:《论民族性》,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1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