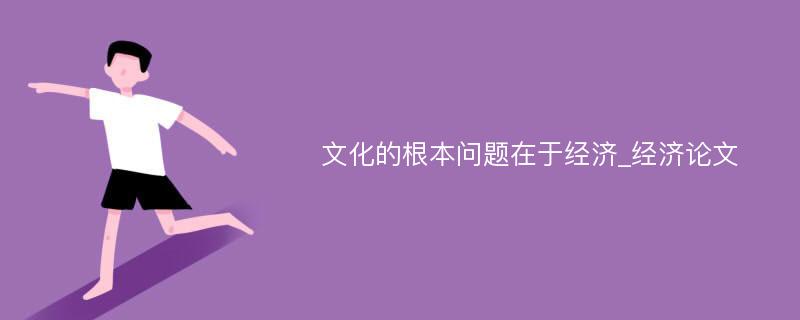
文化的根本问题在于经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是一个十分势利的东西。当你的国力蒸蒸日上时,其文化的光彩和热力也就欣欣向荣。当你的国力日见衰弱,其文化立即变得色彩黯然,热力减退。文化的背后是政治、经济力量的较量、角逐。文化内在的根本是经济。
人常说传统是一种可怕的力量,但传统也可以是一种巨大的文化资源却并未为许多人认识,多年来有一种把传统与现代化对立起来的思潮和倾向。要实现现代化,似乎非与传统决裂不可。而且这种批判传统、与传统决裂的思潮在近百年来的历史上时起时伏,有时还占有主导性的地位。然而,认真反思起来,也许正是这种过激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推迟了近百年来的现代化步伐,之所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指中国在较长时期中不能实现现代化,其中原因是很多的,而这种过激的反传统的思潮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但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导致了人们既不能客观清醒地认识传统,也不能科学深入地了解西方文化,使我们实现现代化的实践,缺乏来自传统文化资源的动力。
到现在为止,意识到不能割裂与抛弃传统的思想,大多不是从正面,比如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感到了传统的巨大深厚的影响所致,而往往是从反面,从不得不如此的角度得出的。因为传统竟然象一个沉重而古怪的大包袱,你越是想扔掉它,它却变得越沉重,越顽固,越抛不掉。你自以为抛弃了它,转过一个身去,它却在另一个出口处迎着你呢。于是人们埋怨、狂躁、过激而又无可奈何。然而,世界上不是所有的文化都遇上如我国传统文化那样的命运,时至20世纪末,有不少非西方的文化,都或先或后地走上了现代化之路,比如印度文化,希伯来文化,伊斯兰文化,日本文化,东亚文化等等。其中与我国文化有同样悠久历史的“舍离此世”(renunciation)价值观念和森严等级的印度文化,在经过相当的现代化的变迁之后,而依然保持着它们文化价值的中心系统,这种文化在现代化的挑战下,仍然发挥出了创造性的力量。再比如,与我国文化同宗同统的东亚四小龙的文化,都程度不同地发生了现代化的变迁,那么为什么独独在我国本土的传统文化会成为如此沉重的障碍、恼人的包袱呢?这里有着两种不同的对待传统的态度,或者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消化和开掘传统的途径,在有的国家,传统焕发了新生;而有的国家里,传统就如腐尸。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些现代化进展顺利的地方,传统也被消化得彻底,并且其被新生的程度也相应地提高;而越是现代化不发达的地区和民族,传统总是充满着陈腐的气息。传统与现代化之间,似乎分明地存在着相反与相成的两个方向的关系。当传统成为一种可怕的惰性力时,那末现代化的步伐将蹒跚不前;当传统成为一种巨大的文化资源时,那末现代化也就顺利而繁荣。那末,传统与现代化之间,什么情况下能相生相成,而又在何种情况下又相反相损呢?它们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内在联系呢?
要批判或决裂传统文化的观点是近百年逐渐高涨起来的思潮,是伴随着现代化而又不断遭受挫折的历史过程的产物。在这之前的很长一个时期里,我国的文化传统有过相当辉煌的历史。我国是个很早就以农业立国的国家。人们以土地为本,过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活。相互之间以血缘关系互相联结。经济上有比较稳定、可靠的来源,社会关系因为以天然亲情为纽带,因而也比较牢固。如果没有大的天灾人祸,即可形成和谐、安定的社会局面。
这种农业经济的文化,在唐朝时期曾经发展到四夷来朝的极盛阶段。当时的统治者和士大夫阶层在对待外来文化时,就象将彼俘来一样,丝毫没有被同化被压抑的惶恐。同化了不少外来文化的因素之后,很自然的是,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原有的文化传统的内涵。在这个阶段上,文化传统无疑是一种荣耀,是一个接纳、熔铸和改造他种文化的本体,是一种推动社会繁荣和发展的力量。但是,时隔不久,这种文化传统的光焰渐渐地不如昨日那么辉煌了。文化传统也象有生命周期的东西一样,走过了辉煌的顶峰,便慢慢地衰落下去。大宋皇朝被北方的金赶到了南方,连皇帝也被虏了过去,当了人家的儿皇帝。明朝最后被清——一个游牧民族灭掉了。然而所幸的是,这些骑在马上的民族到了京城之后,用以“化成天下”的文化还是汉文化系统,他们原有的文化被融了进来,渐渐地被汉文化系统同化了,因而使我国传统文化的血脉不致于中断。但要是细究起来,那气度到底受过数次打击,比起盛唐时期以来,要萎缩得多了。
受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欺压还是暂时的,使文化论者颇感安慰的是,它们无一例外地为我们灿烂的文化传统给同化了。但是,历史发展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时,事情变得有点不妙起来,从西方过来的一种依恃枪炮作先导的,以商品自由流通贸易为方式的文化,发散出强大的政治的压力和经济的辐射力,竟使这有5000余年传统的文化有溃不成军的态势。保持了几千年的文化优越感一朝而破,终于使有些人士感到中国文化反不如人,因此要抛弃传统的劳什子,要实行“全盘西化”。
要抛弃传统,实行西化,从我国民族所受的深重打击来看,在情绪的一面上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们的情绪为转移的。而且过分的情绪化,往往会造成理智的被蒙蔽,容易为偏见所左右,这也是有无数的事实可证明的,从我国文化发展的经历中可以领悟到,文化其实是一个十分势利的东西。当你的国力蒸蒸日上之时,你的文化的光彩和热力也就欣欣向荣,而当你的国力日见衰微,那末你的文化立即会变得色彩黯淡,热力减退。所以,文化若从狭义的角度去看,即仅从人文方面去看时,那末它仅是一种现象,是建基于经济、政治之上,经过某些复杂微妙的折射之后的表现。也就是说,文化的背后,是政治、经济力量的较量、角逐。若从广义的大文化的角度,那末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等精神文化仅是大文化中的外表部分,而其内在的核心是政治和经济,而最最根本的部分是经济。若这样去看问题的话,那末我国文化发展中的曲折也就能有较恰当的解释,并因此对我国文化传统在当今和将来文化中的衍变,也可以有一个较有说服力的预见。
在我国的盛唐时期,经过了较长时期的发展和积累,我国的农业经济体系由不成熟走向成熟,国力达到了相当强大的程度,它的政治和经济的优势远远高出于它周边的尚处于游牧经济时代的小国,所以,它的文化辐射力也超越国界,对周边民族的文化有极大的示范和导向的作用。这时,它不但不怕别的文化来同化它,相反,它确实象一个大熔炉一样,博采众长,把对方文化的优秀部分熔解到自己的内部来,化为自己血肉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这之后,我国的作为基础的农业经济虽然一如既往,但是它内部的固有矛盾,即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日甚一日。农业经济的主要依靠来源是土地,但土地的资源是可以穷尽的,而人口的发展速度却是没有限度的,这两者之间的不平衡日益加剧。再加上统治阶级的腐朽,造成社会矛盾尖锐。这时如果有较强的周边民族的入侵,便造成文化上的某些颠倒乱套——游牧文化入主中原,占主导地位。虽然这种颠倒乱套往往是暂时的。问题表现在文化上,内里还是因为经济实力衰弱所致。农业经济的发展走过了盛唐时期的高峰之后,便走向日渐的没落。从宋、元、明到清,实际上是一个缓慢、悠长的农业文化的衰落期。我国的可耕地本来就不多,东边是大海,农业经济时期无此能力去开发它、利用它;西边和北边是大片的荒漠和戈壁,农业经济的低下的生产力,不但无能为力去开掘它的价值,反而大受其害。而人口的增加代代相传。所以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上的法则是资源逆灭的原则。于是它的国力不可能再日渐增强,只有越来越削弱,而解决这种经济、政治矛盾的唯一方法是战争,是一次又一次的推翻统治者争夺权力的农民战争;一次又一次的统治者内部争权夺利,权力和资源重新再分配的战争;一次又一次的周边民族不堪受压、取而代之的边乱战争。每经过一次战争后,人口大量减少,土地的兼并和不均暂时受到抑制,各社会阶层的利益得到某种程度的重新分配,这样统治的实力得到某种程度的恢复。但是,它的衰弱的趋势是不可能改变的,只不过暂时延缓了它衰弱的速度罢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立足于农业经济的封建王朝到明、清之际,它所代表的文化,也只是在作苟延残喘罢了。
到了19世纪末,我国的5000余年传统的文化遇上了一个从未遇见的对手——西方文化,对于这种文化,它几乎没有招架之功,更谈不上还手之力了。这种文化之所以如此强大,关键的是,它的背后是一种新兴的经济基础,即现代工业基础。这种工业经济基础比起我国那已行将没落的农业经济基础来,一,它正处于如日中天的发展期;二,它与农业经济基础相比,是一种全新的异质的经济体系。西方世界从13、14世纪开始产生资本主义的萌芽,到16、17世纪逐渐走向成熟,到18、19世纪则正是它的腾飞时期。它的经济力量的发展,大到国内市场已远不能满足它的需要,因此急于到世界各地去寻找和开辟新的市场,并且它的实力确实足以辐射到全世界的范围里,因此,到20世纪初,整个世界在这种经济力量的辐射下被连成一体。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被认为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在力量的未经开发的市场,而被卷挟进了20世纪的资本主义经济统辖的轨道中,而两种经济力量对比的强弱是不言自明的。再说,为什么工业经济体系能焕发出如此巨大的力量,要认清这种经济基础的异质性。工业经济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单一的自然资源——土地,它在科学技术的层面上产生出机器,因而能在大得多的范围里利用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其次,这种经济所涉及的范围可以无限止地扩大。因为它的产物是商品,商品依赖的是市场。根据商品自由流通的原则,它可以在最大的范围里配置资源,可以在全世界的范围里把人力物力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使世界各地各国发挥优势互补,有无互通,从而产生出规模连动的生产效益。第三,这种经济体系在市场上遵循的是竞争的法则。各种商品的价值依赖于它在市场竞争中的活力,因此这种体系推动各地各国的企业,千方百计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数量,扩大市场的复盖率,以求在市场中获胜。并且不是一次性获胜,而是不断地获胜,“不进则退”的原则推动生产力不停地向前发展。所以这种经济有活跃的生命力,不象农业经济那样,是一种匮乏的死气沉沉的、穷途末路的经济。
因此,我们不能只看到西方文化的强大,它的来势汹汹,而给它冲昏了,弄懵了。有些人看到西方人的洋枪洋炮利害,就想用钱买过来,以为这样便可以制西方文化于臣伏的地位;有的人看到西方君主立宪制度比我们封建王朝开明,又想搬来中国;有的人又看到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比我国的发达,于是也想举起科学民主的旗帜。可是,为什么我们想学西方而终于不可得?反过来,为什么我们想扔掉那几千年留下来的传统劳什子,也终于不能够?这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一个病症的两种病相,传统与现代化依然血脉相连。根本之点在于,只注意于所谓文化的表相,而未注意或无能力改变我国的经济基础,治标而不能治本。如果我国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如果我国的经济内涵已成为工业经济占主导的地位,那末不仅传统可以继承,现代化也并不遥远。
也许事实更能说服人。让我们举例以说明之。比如关于我国传统文化中压灭个性的问题,以及与此有关的关于传统中的群体意识和家族意识问题。我国的一些先知先觉者在五四之前就提倡要发扬人的个性,主要的代表人物如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一代早期的留学生,他们在经过拿他国文化与本国文化比较参照之后得到这样的认识。他们认为在我国文化传统中的人民,并不是“人”,只是“父”“母”“弟”“哥”,各在一个固定的社会格局中,社会赋予他们的义务太重,压杀了他们的个性,因而,人人都萎萎缩缩,哪来国力的强盛和文化的高扬?因此必须要高扬人性,“人立而后生”。但先觉者们虽然倡导甚力,但用这种道理来改造我国的国民性,似乎并未收到多大的效果。五四之后不久发生的抗日战争,要求人们的是牺牲自己个人的爱国主义;新中国建立之后,新时代要求于人们的是,从建国初的克服个人主义,到文革时的“斗私批修”,“触及灵魂”,一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醒过来的知识分子再次提倡发扬个性。历史走了一条漫长的路,个性却始终没有得到相应的张扬。这当然并不能说先知先觉者们的这种提倡是错误的,但至少可以说明,这种努力并未抓到时代的实质。现在依然有不少人努力于批判传统文化中的群体意识,似乎群体意识就是传统的、落后的东西,但就是这种群体的或者说集团的意识,在日本乃至东亚的现代文化中却焕发出了现代的生命力。日本和东亚不少成功的企业采用家庭式的管理体制,日本式管理的核心是企业集团利益多于个人利益。在当今日本,对集团的忠心已经成为提高日本企业生产力的源泉。如日本的松下公司,明确规定以职工的幸福为目标,劳资双方努力合作,把人的价值与经济效率结合了起来。另外,企业与企业之间,也不仅仅是你死我活的竞争,也有相互间的协调和互补,也提倡一种合作精神。所以这种敬业的传统被凝聚成了一种新的活力。再比如关于孝悌这种传统道德,在五四以来遭受了猛烈的批判的炮火,但它在现今的台湾、新加坡等的现代文化中,不但不受批判,而且还发扬光大。如孝悌这种传统看似文化,但它的根子却植于经济。在新加坡这样现代化经济相当发达的社会里,人人都有较好的发展,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前辈提携后代,后代尊敬长者,前辈的开拓为后代打下基础,并不形成压制后代的力量,孝道与社会成同步发展形态。而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时期里,生产力低下,人们没有充分发展的机会,给了长者以机会,意味着夺去了后代的生机。
那么,被我国文化界经常批判的某些传统,为什么在另一些文化系统中产生了新的生命呢?因此,关于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必须有另外一种新的解答,这就是,文化问题的答案深埋在经济系统之中。在我国封建时代的匮乏的农业经济系统里,经济本身缺乏活力,各种因素都处在萎缩状态,因此不管你是来自于传统,还是来自于西方的,一进入这个系统,都有被吸干生命汗水和变味的危险。所以鲁迅愤而称这种文化为酱缸,东西南北而来的文化,一入此缸,统统被同化为酱缸文化,相反在欣欣向荣的工业经济体系内,这种经济力量不但能消化固有的传统,而且能吸收各类不同的文化精华。象日本、新加坡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就是这样,它们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化的;既具有民族个性,又是面向世界的。
到这里,我们可以回过头来说,传统有时是一种可怕的力量,有时又是一笔巨大的资源。问题的关键在于处在何种性质的经济体系内。时至20世纪末,我国的经济发展终于踏准了现代化的节拍,在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指导下,人们终于领会到,现代化最首要的是经济的现代化,然后在经济现代化的基础上,构建政治的现代化,上层建筑的现代化。有了这个现代化的基础,我们才能面对悠久的历史传统,才能面对人类共同创造的不同类型的优秀文化,开掘出丰富、深厚的文化传统资源,融中外古今优秀文化精萃于一炉,建设起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大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