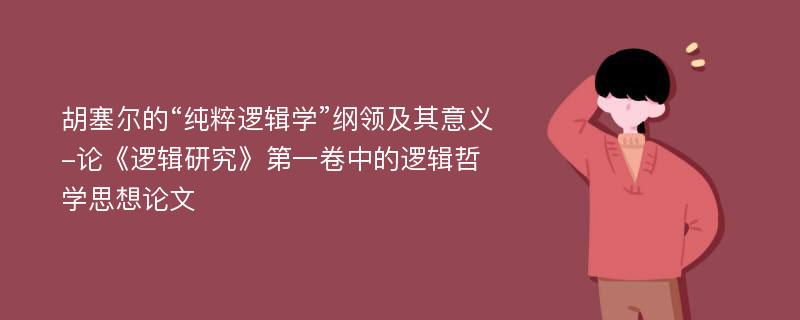
胡塞尔的“纯粹逻辑学”纲领及其意义
——论《逻辑研究》第一卷中的逻辑哲学思想
钱立卿
摘 要: 胡塞尔的《逻辑研究》第一卷不仅对于现象学的发展意义重大,同时也作为一部独立的逻辑哲学著作参与到20 世纪初的逻辑哲学发展中。胡塞尔基于对传统逻辑的反思,提出了“纯粹逻辑学”的构想,它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首先是重新确立逻辑学的纯粹性、独立性和非经验性,反对心理学主义的解读;其次,确定逻辑学处理的对象类型、对象间关系类型以及理想中的理论结构形态。这两方面平行于从弗雷格到希尔伯特的逻辑哲学发展过程,前者表明了新时代的逻辑学如何在根本上超越了传统的观点,后者则最终导向了现象学哲学。这也意味着20 世纪初的逻辑哲学与某种彻底的认识论研究之间存在着结合 点。
关键词: 逻辑学;科学论;流形论
在1900 年出版的《逻辑研究》第一卷前言里,胡塞尔言简意赅地表明了他对数学哲学和逻辑哲学的基本构想,也指出了这种思想的起源和方向。首先,这是一条逐级层进的思想线索:从数学基本概念的研究发展到对形式算术或形式数学的整体研究,最终提出关于数学、逻辑学,甚至一般理论科学的结构形态理论纲领,即“流形论”(Mannigfaltigkeitslehre)。其次,与这条线索相关联的是一个更具“传统”哲学意味的论题,即逻辑学与认识论的关系或者说逻辑学的认识论基础问题:它们是独立的理论性规范科学还是辅助性的实践性操作技艺?① 上述内容参见胡塞尔:《逻辑研究》 (第一卷),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年版,第1—2 页。 上述两点直接关系到逻辑学甚至是一般的纯粹理论科学的本质,可以合并为下述问题:关于一般理论的“元(形式)理论”是什么,它又如何得到辩护? 这个问题引导了整个《逻辑研究》的计划,胡塞尔正是由此展开论述,为当时的科学之基础或统一性的科学之纲领本身提供说明。在他的原初设想中,第一卷的工作着力于那个“什么”,第二卷的最终目标则是那个“辩 护”。
一、《逻辑研究》第一卷的定位
胡塞尔的论述表明了《逻辑研究》第一卷的基本方向,但这还不足以彻底说明这本书的真正目标。瑞士现象学家伯奈特认为,目标的事情在第一卷中并不那么清楚:一方面,这本书批判了心理主义并解放了形式的—逻辑的对象,它的目的就是让逻辑学及其对象获得独立的、观念性的意义;另一方面,它是为理解纯粹逻辑学与思维的具体现象学过程之间的关系——认识的观念性条件与思想在时间中的个别化行为之间的关联——所作的前期清理工作,而这种现象学过程会在第二卷中以各项具体研究的形式展开。① Rudolf Bernet et al.,An Introduction to Husserlian Phenomenology ,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93,p.27.如果把这两方面综合在一起看,似乎可以说第一卷虽然有自身的内在目的,但最终仍是为了给第二卷作铺 垫。
这个看法固然有道理,但并不完全正确,甚至可以说有些轻视了第一卷自身的独特意义。事实上,从数学和逻辑学的哲学反思走向普遍形态理论的进路,本身就蕴含着三个不同的导向。导向1:作为形式科学的基础或元科学 (元数学和元逻辑学)。无论是《算术哲学》中的某些初步讨论,还是1895—1986 年在哈勒的逻辑学讲座中的内容,或是1901—1902 年冬季学期的哥廷根数学哲学讲座等等,均属于这个方向。导向2:这是最具现象学特色的向度,即以《算术哲学》为标志的意向—构造的研究进路。这些初步工作也给《逻辑研究》两卷之间的过渡提供了理解的可能,它表明纯粹逻辑学的有效性根源在于意向性结构,或者说“‘意向行为’与‘意向相关项’之间的区别与平行关系”② 胡塞尔:《逻辑研究》 (第一卷),“前言”第10 页。译文有改动。 。对当时的胡塞尔来讲,作为系统的、追求奠基性与严格性的“纯粹逻辑学研究”,必须进一步上溯到现象学式的“描述心理学”上。导向3:对于形式数学一般化的合法性和意义的追问很自然地扩展到了对所有理论科学之基础、关于认识形式的本质的疑问。③ 同上书,“前言”第2 页。 它根本上指向了类似于笛卡尔与莱布尼茨设想过的普遍科学(mathesis universalis)。胡塞尔继承了波尔察诺以降的传统,把这种关于一般理论科学的形式理论称为“科学论”(Wissenschaftslehre)。
这三个导向都是《逻辑研究》第一卷的应有之义,而且可以分析出截然不同的指向性。A)在单纯的“逻辑学”视角下,导向1 和3 都具有独立意义,它们不仅与20 世纪初的逻辑学发展密切相关,而且本身就是新的逻辑哲学理论。B)按所谓的“描述现象学”视角,导向2 是终极基础,因为任何一种知识的形式与内容必然都完全出自我们的意识行为,是其内禀的相关物。所以,导向1 和3 都只是不同层次上的形式的理论的“科学形态”,最终的解释必须回溯到意向分析上——不论是早期的现象学心理学还是后来的纯粹或先验的现象学都以此为准绳。C)如果我们跟随胡塞尔把“认识论”或对纯粹认识之基础的哲学阐明视为原则问题,从而获得一种“现象学哲学”视角,那么真正关键的事情就是追问一切可能知识的根基能否及是否得到保证。如此一来,导向2 的目的是为导向3 奠基——现象学哲学是科学论的终极辩护,也是完成哲学最高目标的一个方法论标志——而只有导向3 才真正决定了哲学工作的目标区域的基本框 架。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道”如果可以用言语来表述,那它就是常“道”;“名”如果可以用文辞去命名,那它就是常“名”。“无”可以用来表述天地浑沌未开之际的状况;而“有”,则是宇宙万物产生之本原的命名。因此,要常从“无”中去观察领悟“道”的奥妙;要常从“有”中去观察体会“道”的端倪。无与有这两者,来源相同而名称相异,都可以称之为玄妙、深远。它不是一般的玄妙、深奥,而是玄妙又玄妙、深远又深远,是宇宙天地万物之奥妙的总门。
进一步讲,导向3 本身就给这个“能否”是“是否”的问题提供了两个层次的回答:一是在(第一卷)纯粹逻辑学自身的定位中批判性地阐明一切理论的、严格的科学的形式架构,亦即给出科学论的基本规划;二是通过逻辑学与意向成就的关系表明这种架构本身如何得到具体的阐述和辩护,它导向(第二卷)分析的和现象学的研究。也就是说,第一卷的立场就是在直接阐明前者的同时指出后者的必要性。对胡塞尔来讲,第一个层次是方法性的,它植根于知识本身的意向构造特性,探究科学论甚至一切知识的最终基础 ;而第二个层次涉及哲学研究的目的性,它指示着具体工作一步步通向现象学哲学的最高目的 。1913 年《逻辑研究》第二卷再版时,胡塞尔在引论部分谈到了逻辑学对于现象学哲学的基本意义:“因而我设定这样一个前提:人们不愿满足于将纯粹逻辑学仅仅建设成一种数学学科式的、具有素朴实事效用的命题系统,而是去追求与这些命题有关的哲学明晰性,即:明察在这些命题的观念可能的运用中起作用的认识方式本质以及随同它们一起构成的意义给予和客观有效性的本质。”① 胡塞尔:《逻辑研究》 (第二卷),乌尔苏拉·潘策尔编,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年版,第3—4 页。 他接着阐明了现象学的目的意义:“现象学打开了‘涌现出’纯粹逻辑学 的基本概念和观念规律的‘源泉’,只有在把握住这些基本概念和观念规律的来历的情况下,我们才能赋予它们以‘明晰性’,这是认识批判地理解纯粹逻辑学的前提。”② 同上书,第4—5 页。
3.2 非计划性拔管是临床护理安全管理的重要问题之一 非计划性拔管的发生,对高龄患者来说轻则造成患者局部损伤、使患者无形中延长住院天数并增加住院费用,重则可能危及生命安全,也是增加医疗纠纷的安全隐患。留置胃管被广泛应用于胃肠内营养支持治疗、胃肠减压、外科手术患者等,同时也是病情观察的重要窗口。胃管是所有非计划性拔管中发生率最高的一种[6]。
鉴于研究采用问卷法可能会导致共同方法偏差的问题,因此在收集数据时通过设定问卷项目的顺序,强调数据的保密性、匿名性等进行程序控制。在数据分析时,本研究进行了Harman 单因素检验。结果表明,在数据未旋转的情况下共13个因子的特征根值均大于1,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仅为24.16%,小于临界值40%。因此,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并不严重。
正是在上述视野中,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第一卷的标题“纯粹逻辑学导论”(以下简称“导论”)以及它所致力于的导向3。但事实上,整部著作只有到最后一章才开始正面谈论这个导向,因此不少学者或者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之前大篇幅的心理主义批判上,或者认为第一卷与第二卷之间衔接有严重问题,而第二卷又暗中回到了心理主义。其实胡塞尔的写作策略完全是由于批判研究(Kritik)本身的特性使然。从历史上看,“批判”意味着对在理论建立之前,先对引导理论的前提与问题做出区分与鉴别的工作。胡塞尔虽然没有直言《逻辑研究》的批判向度,但对他而言,这种做法本身就是正确而自然的,也很清楚地反映在具体的行文当中,并不需要靠康德或新康德主义来为其正名。在他看来,既然最终的立论要建立在驳论的基础上,而后者必须通过审查“时代的精神状况”实现,那么当时有关逻辑学、数学以及各种自然科学的哲学观点都必须在根本上得到批判性考 察。
二、逻辑学的系统性、理论性与观念性
理论科学不同于规范科学。规范性体系包含的目的性 不同于其表达的规范对象之间的关系性 。这种关系只涉及对象是否存在,而不涉及对象存在方式之间的比较,或者说,理论科学只讨论“客观联系的形式”而不关心“纳入规范的形式”。② 同上书,第40—41 页。 更重要的是,在任何一种规范的导向制定前必须先认识到某种真理形式,这些真理或是理论科学本身的内容,或是其实践运用后的派生物,前者构成了规范科学的根基与内核。无论如何,对真理形式的先行把握决定了规范性科学不可能是最终奠基性的知识,它总是派生于某种理论性活动。所以,尽管我们可以在不同意义上讨论逻辑学的性质,但如果要问的是最纯粹、最原初意义上的逻辑学,那么就必须注意不同性质之间的主次关系。在涉及具体科学的时候,胡塞尔并不反对把逻辑学视为一种规范体系或是方法论工具,他只是表明,这种规范的甚至是完全应用的视角总是需要纯粹理论性的基础来支 撑。
这一年,我一个人去大连看海,那是我们第一次相识的地方,也是我们,告别的地方。很多时候我在想,当时我们祈盼着的永远,竟是这样的永远。一个人从此就这样消失,无影无踪。死是很突然的事情,也是安详的,大痛大悲之后,终究要归于宁静。而我,也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尽量让自己能活得快乐一点,再快乐一点。
胡塞尔对科学基础问题的担忧与当时的欧洲科学前沿图景直接相关。狄尔泰与新康德主义者试图抵御自然科学方法对人文领域的入侵,力证整个精神科学的独立性和自我奠基性;希尔伯特素来关心数学的基础问题,无论是他所在的哥廷根学派还是罗素与怀特海等人的工作都指出,传统的数学观念面临着许多疑难,不适合用来理解当代的数学;汤姆逊对以太测量实验和黑体辐射中紫外灾难的忧虑随着量子论和相对论的出现而消除,但这却引起物理学基本观念与方法的革命——诸如此类的情况不胜枚 举。
胡塞尔当然知道当时思想界的基本格局,但在他看来,最根本也是最危急的事情发生在逻辑学那里:A)不仅仅因为各门应用的、实在的科学与理论的、观念的科学自身的规律体系全都是逻辑学的课题,更因为所有科学之概念及科学的真理性本身,特别是诸真理的统一性 本身必须建立在逻辑之上。B)同时,一些被认为具有高度严格性的科学(如数学)内部也存在着基本概念的合法性问题,它们同样要像其他学科一样得到辩护。这些概念的澄清工作就算不是完全立足于逻辑学,至少也是和逻辑学相关的。如果逻辑学遭受任何形式的相对主义危害,那么人类的整座知识大厦就像建在流沙上一样。如同康德面对休谟问题时的情形,胡塞尔也要解决同样的难 题。
(1) 他首先要处理的问题是:逻辑学到底有什么样的地位?它只是一门普通的科学,还是可以承担起基础的意义?对胡塞尔来讲,知识基础的角色受亚里士多德第一哲学传统的影响,始终是由形而上学承担的。但这个基础无法满足所有科学的完善性需求,因为存在着一部分不探讨实在对象的科学。尽管亚里士多德也注意到了数学的特殊性,将它与天文学一同放在第一和第二哲学之外,然而其本质依然未得到恰当把握。“关于科学的科学”或“科学论”的概念本身并不指向逻辑学,而只是表明了一个特殊的理论领域。其他知识的基础,无论是现有的还是仅仅可能的,都由这种元理论来解 释。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意味着语法层面的一致性尽管对纯粹逻辑学很重要,但在胡塞尔那里似乎还不足以单独拿出来讨论。一致性只不过是理论为真的必要条件,而(往往)不是充分条件;如果充分性未得到辩护,那么任何一种形式理论都不能绝对地确保真理。胡塞尔本人也并没有在前期发表的著作中详细谈过一致性问题,甚至“无矛盾性”都没有作为专题概念出现在第二项任务的描述中。因此也许会有人怀疑:胡塞尔是否未能真正看透这种性质的关键意义 呢?
因此“逻辑学的地位与使命”已经被转化为另一个问题:既然各种特殊的逻辑已经作为一个内在于一切学科的事实 ,而具有上述任务和内容的科学论又应当 是一门纯粹的、一般的逻辑学,那么这门科学应该如何让自己从当前的混乱观念中脱身呢?换言之,逻辑学如何做到一方面澄清自己的本性,另一方面又在摆脱具体、特殊的诸逻辑学以后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显然,这个新问题的两方面就是“导论”的两大基本任务,也是我们后面要具体阐释的内 容。
(2) 逻辑学的本性到底什么,它究竟是实践性的还是理论性的?是工具论还是某种规范科学?历史上往往把逻辑视为一种实践性和工具性的学科,是为了保证正确的判断而使用的系统技术理论。更重要的是,这里还隐含着一种目的论维度:不论逻辑学本身是否是理论性的,它都可以发展出实践性的技术科学,特别是当这种理论性被理解为规范性的时候。因此胡塞尔担心这样一种理解会强化逻辑的工具论倾向。但是,逻辑学的本性是什么和它能导出什么结果是两码事。反过来说,即使可以断言现实的逻辑学当中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实用性动机,这仍然不能说明逻辑学自身的特性就是实践的。所以,传统的工具论观点并没有充足理 由。
在上述第二项任务中,语法学在独立于语义学的意义上已经先行指明了理论形式可以仅仅在纯粹命题形式层面得到研究。在胡塞尔看来,这表明了理论本身确实可以从不同视角和不同层次上理解。在某种视角下,任何理论——无论是潜在地成立或现实地成立——都已经直接划定了包含着与其相关的可能理论全体的整个领域。也就是说,个别理论由于必然归于此领域而失去了自身的特殊性,它与别的可能理论都只是同一种理论形式“属”下的不同“种”。胡塞尔由此认为,这种高阶理论形式本身的形态与数学中的“流形”概念非常相似,所以建立纯粹逻辑学框架的第三个任务就是提出“流形论”纲领 。
胡塞尔对当时的哲学大环境的判断几乎和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序里讲的一模一样:前者认为以心理学观点看待逻辑学的人们在打一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① 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一卷》,第2 页。 ,后者则认为17 和18 世纪的形而上学家们全都身处“无休止争吵的战场”。②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一版序,第1 页(A VII)。 这种大乱斗的结果就是,真正有效的、关于具体事实及事态的知识理论或基础科学全都像空中楼阁一般,讲的再多也无济于事,人们照样可以理直气壮地怀疑科学知识。这样的科学显然离开它的理想状态太远 了。
另外,要学会保留证据,比如一些发票、小票等。如果自己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及时跟中国领事馆打电话,寻求帮助。如果是跟团游的话,旅行社也会出面帮助解决。
过片分换头与不换头两种,《卜算子》属于后者。对于《卜算子》这样的精简小令来说,过片于一首词的成败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该词调过片方式丰富多样,常以递进、承接、转折为主。
(3) 在胡塞尔看来,心理主义基本思路如下:既然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的感知、信念、判断和认识,那么无论是认识论还是反映思维规律的逻辑学甚至一般科学都要由心理学说明。这种思路的表现是以来自有限事实领域的经验科学去为一切更普遍的科学理论奠基。可是,就算存在完备的心理学知识体系,它所研究的规律性也都带有概然特征(因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规律),即便这种概然性可以通过大量的事实性而逼近确定性,但终究不是必然的。而逻辑学始终阐述普遍必然的规律,且有绝对的确定性。这个简单的事实已经表明心理学解释难以真正切中“逻辑性”的实 质。
不过,心理主义者也可以同意上述大部分断言,只不过工具性和规范性派生自人的心理活动,逻辑是心理产物,最基础的问题必须由心理学负责。胡塞尔当然不同意心理主义者的看法,因此最后的驳论就是关于科学论之理论层面的辩难,即如何批判心理主义。不过胡塞尔的这个反驳过于著名,相关研究也汗牛充栋,因此这里就只限于其思想的概 述。
但心理主义始终坚持客观法则与主观思想的相关性,正是在此必然的相关中,思想的规律或自然对象的规律才可被理解。这是一切认识论研究的基本事实和零点,无可置疑。可质疑的地方在于,客观规律、关系性以及纯粹理论科学的概念是直接与心理学事实或心理性的认识行为 相关,还是与作为观念性结构的认识成就 相关。换言之,要追问的是理论科学所解释的究竟是自然规律还是逻辑规则。胡塞尔通过一个思想实验来说明这个问题:如果有这么一个人,作为绝对准确的思维机器,一切推理都完全符合逻辑规则,即使如此,仍然不能认为他的思想行为规律与逻辑规律是一回事。当我们解释思维机器或计算机何以表达正确结果时,我们究竟是在问这种表达的意义是什么,还是在问实现这种表达需要凭借何种软硬件配置。思维过程如果有某种规律,其解释只能是物理层面的,但思维内容的律则性不具备任何物理意义,两者之间的解释层次不能互相替代。也就是说,“观念规律与实在规律之间、规范性与因果性之间、逻辑必然性与实在必然性之间、逻辑基础与实在基础之间”① 胡塞尔:《逻辑研究》 (第一卷),第59 页。 ,都存在无法消除且相互不可还原的差异,而心理主义者恰恰未能注意到这 点。
2月20日,水利部召开2012年预算执行管理工作会议。水利部部长陈雷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水利部副部长矫勇、周英出席会议并讲话,部总规划师周学文主持会议。
进而言之,心理主义坚持经验科学方法的优先性,导致了一种概然的立场,因此也就必然蕴含着关于逻辑真理的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观点。② 同上书,第98 页。 这又直接联系到另一事实,即特殊的人的实存性,因此还会很自然地通向逻辑人类学主义。③ 同上书,第102 页。 怀疑论的荒谬在于其自我否定的立场——假如同一命题内容仅是相对的真并且相对的假,那么“既真又假”本身就不符合真假的含义;而人类学主义没有注意到思维规律与逻辑规律、事实可能性与逻辑可能性之间的关键差别——人总是可以实行错误的推理过程,但推理规则本身是不存在对错问题的。总的来说,逻辑心理主义者们尽管观点不尽一致,但他们都没有意识到,把握逻辑学特性的关键在于区分作为实在过程的判断行为与作为观念对象的判断内容 。④ 同上书,第163—167 页。
不过心理主义也并非完全没有贡献,至少它表明了逻辑观念的给予性问题仍然是个问题,也必须成为某种彻底的逻辑科学之研究对象,尽管它自己给出的回答是错误的。问题既然存在就必须要回答,假如承认纯粹的逻辑规则具有必然性与规范性,那么一方面要指出这种必然的规则如何能规范主体的认识活动,另一方面也要指出逻辑观念是如何被认识和获得的,后者要求哲学家给出辩护的同时还不损害逻辑概念本身的观念性与客观性。这自然就是《逻辑研究》和一般的现象学认识论的任务 了。
70后的周耒是广西文坛近年来较为活跃的壮族青年作家,广西崇左人,现居崇左。崇左位于广西西南部,往西与越南接壤,散落居住着二十八个少数民族,周耒身处边境多民族杂居地带,在这样独特的地理风貌和文化影响下,他的文学创作为桂西北作家群主导的广西文坛,增添了一抹不一样的亮色。
综上所述,逻辑学是一种普遍科学(mathesis universalis)。就它自身而言,其必然性直接反映在推理规则当中;就它和各门科学的关联而言,其有效性是普适的。所以,尽管逻辑学本身是观念性和理论性的,但本质上就具备规范性和实用性。然而,逻辑观念的形成方式、必然性与有效性的根源等等,仍然需要某种哲学来解释,只是这种解释不能采取经验性视角,无论是心理学主义、物理主义还是广义上的自然主义都无法触及逻辑对象的本质——只有同样属于观念性理论的学说才能够为某种观念性科学的合法性作辩 护。
三、作为科学论的纯粹逻辑学
科学作为人的活动有外在的、经验性的统一,又反映了科学本身真理性的内在统一——后者既包含了事物的关联整体与思维体验的意向关系,又包含了事态之中的客观关系或真理。在最基本的意义上,两者都是同时被先天给予的,并且规定它们的仅仅是一种观念性的或纯粹可能的、普遍有效的关系结构,而非任何具体事实或事实科学。所谓的“科学论”就是关于上述两种关系的纯粹结构理论,由于关系性及其相属概念本身都是一些形式的、普遍的东西,因此关于它们的科学必然是一种纯理论的学科。科学论截然不同于规范逻辑学或逻辑技术,它只是关于概念和关系规则整体的结构形态的元逻辑学(meta-logic),胡塞尔称之为“纯粹逻辑 学”。
当然,仅仅是这样的概括还不足以让人明白纯粹逻辑学究竟要干什么。尽管含义本身的意向本质与对象本身的普遍构形(Gestalt)都被视为“观念上可能”的对象性(Gegenständlichkeit),并在“元科学”的层面得到研究,可我们还是难以理解这种高阶、普遍的、基础的科学是什么。胡塞尔认为,在具体进行科学论的研究之前,必须先完成几项任务来确定纯粹逻辑学的主题、基本构想以及总体框 架。
首要的任务是阐明逻辑学的对象域和对象类型 。① 胡塞尔:《逻辑研究》 (第一卷),第211—213 页。 这就意味着研究两个相互关联的环节:(A)由各种具体的概念导出的逻辑概念,后者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原子式的逻辑概念。具体的概念是各种科学的原材料,比如“光子”“DNA”“法人”,等等,它们本身的含义规定和处身概念体系中的位置各式各样。但纯粹逻辑学完全不考虑它们的实质含义,仅仅关注它们在形式上的意义,从各种具体概念中抽象出统一的逻辑特征,建立逻辑性的概念,诸如“概念”“句子”“真”等词项。这些词项是纯粹逻辑学的最底层要素。第二个层次是从这些要素彼此之间的关联方式而来的、构造出的基本联结形式的概念(die Begriffe der elementaren Verknüpfungsformen)——比如选言判断、联言判断、主语和谓语形式等——亦即被构造出的判断与句法的结构。胡塞尔称它们为“含义范畴”,因为它们表示概念与语句、语句与语句之间存在的一切可能结合关系或可能含义类型,而这些含义结构及其复合本身也构成新的含义范畴。(B)含义范畴是表达方式和意义结构的逻辑表征,它们蕴含了另一类逻辑学对象的存在,这些对象本身和表达方式无关,只是反映了一切可谈论的事物固有的逻辑特性。① 参见Edmund Husserl,Gesammelte Werke Band III/1 ,Ideen zu einer reinen Ph änomenologie und ph änomenologische Philosophie. Erstes Buch :Allgemeine Einf ührung in die reine Ph änomenologie ,Hrsg. von Karl Schuhmann,Den Haag:Martinus Nijhoff,1976,S.27。这就是诸如“对象”“事态”“关系”“数”“集合”等等纯粹形式性的对象范畴词项,它们可以从任何事物上得到,和事物的本体论意义或类型无关。对象范畴与含义范畴构成了一切可能的表达内容的逻辑表征。值得一提的是,把对象范畴纳入逻辑学视野,是19 世纪逻辑学与数学发展的深刻结果,它意味着逻辑学不再对逻辑关系和关系中的对象作朴素的区分,而是把逻辑关系本身也视为一种对象。在这个观点下,一切能够谈论到的、反思到的内容都可以在逻辑层面上被对象化,逻辑法则也获得了真正的绝对普遍 性。
四川省2012年起将在全省列入规划治理名录的325条中小河流上,建设3133个水文监测站点,编制325条河流的洪水预警预报方案,建设一个省级水文应急机动监测队,并用两年时间初步建立全面覆盖这些中小河流的水文监测体系。届时,这些中小河流的水情、雨情信息可以在10分钟内到达当地县级防汛抗旱指挥部门和省水文信息中心,从而为防洪抗旱减灾提供决策依据。据了解,四川省在中小河流水文监测系统建设中将全面提高水文自动化水平。其中,雨量站、水位站按“无人值守,有人看管”的无人自动站标准建设,全部实现雨量和水位信息自记、固态存储及远传。
这项任务最终导向了以现象学的、本质明察的方式研究概念与关系性在意识中的构造,同时也使得我们有可能从现象学的角度全面考察逻辑学的实质与限度。胡塞尔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考察过逻辑范畴的问题,比如在“导论”中着重强调作为概念的逻辑范畴,后来又从判断形式的角度重申了此事,并将这个层次上的纯粹形式理论之基本框架分为三个环节:纯粹含义范畴理论、基本的判断形式及其复合变化、以运算的视角研究形式变换。② 参见Edmund Husserl,Gesammelte Werke Band XVII ,Formale und transzendentale Logik ,Hrsg. von Paul Janssen,Den Haag:Martinus Nijhoff,1974,S.54—57。
第二个任务是确定上述对象与含义范畴之间的可能结合方式 。这种结合具备形式上的“真”或客观有效性,一切合法的组合都在其列,而不合法的组合被排除在外。初看起来,这项工作似乎已经包含在前一个任务里了,为什么还需要单独列出呢?对胡塞尔来讲,前一项任务通过指出含义范畴的复合操作仅仅预先规定了第二项任务的范围——正如它也预见了第三项任务一样——但我们还需要知道逻辑范畴构成的整体究竟具备哪些性 质。
理论科学的形式表现为单纯的演绎关系,也就是说,在任何一门理论中,命题和概念范畴之间都是由确定规律支配的。理论在其纯粹的逻辑层面表现为形式上客观有效的结构,通过一种从运算视角而来的演绎逻辑展现,它对一般对象与一般事态的存在与否作出推理,以此保证后继含义的客观有效性。① 胡塞尔:《逻辑研究》 (第一卷),第214 页。 不论是经典的三段论逻辑还是数学化的现代逻辑,都对理论科学有两项基本贡献:第一,推理性的联结模式保证了“每一门学说都是一个自身封闭的理论……与此有关的规律都导向有限数量上的一批原初的或基本的规律……这门理论将那些个别的理论作为相对封闭的组成部分包含在自身之中”② 同上书。 。第二,后承逻辑表明了科学的形式真理是句法意义上的“真”:它是个无矛盾的逻辑系统,亦即全体命题构成的理论具有一致性(consistency)。
初看起来,似乎最后这个条件已经从语法和语义两方面规定了形式系统的意义,但实际上这点不仅不显然,而且还遭到了弗雷格等人的挑战。④ 关于弗雷格、希尔伯特与胡塞尔在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以及后续讨论,参见钱立卿:《弗雷格与希尔伯特的几何学基础之争——兼论胡塞尔对几何学起源的分析》,载《世界哲学》2015 年第2 期。 从胡塞尔的角度来看,希尔伯特与弗雷格都只有一部分正确性。在较高层次的观点上,诸如形式算术或希尔伯特几何公理的对象仅仅是关系的承载者,真正的数学对象是关系性本身,为了将之变成唯一主题而获得一种普遍的结构,需要将初始概念的基本内涵或语义抽离掉。在此意义上,高观点下的形式数学只相当于一个纯形式的逻辑系统,里面存在的并非原初意义上的数学对象,而仅仅是一种纯语法结构。⑤ C. O. Hill & G. E. Rosando Haddock,Husserl or Frege?,Chicago:Open Court,2000,p.168. 既然对象范畴服务于关系或命题形式本身,那么句法学就是决定性的要素,它已经构成意义和真理的充分条件了。可是,高观点自身的合法性也是需要得到辩护的,它所依赖的表达手段以及表达出的观念从来就不是单纯的“自在之物”——无论我们是否能直接断言其本体论性质——而是从逐步观念化的活动中获得出的。如果说希尔伯特可以只谈论语法层面的公理体系,那仅仅是因为在观念化中,除了关系性本身之外的其他对象都被视为一种无差别的对象性了,因此才可能转化为形式对象的演绎系统。但是,要彻底理解这种纯粹语法性的真理,恰恰就需要初始的对象、关系性、构造方式本身都被明见地给予——尽管其内容与方式的现象学分析同样要遵循普遍的语法结构。因此,对作为基础科学的纯粹逻辑学来讲,单纯的句法学并不充分 ,它只是最重要、最基本的框架和导引。换言之,指向明见性研究的纯粹逻辑和诸如形式逻辑、形式数学这样的学科之间存在着一种基本距离,虽然前者在单纯的形式上可以与后者使用相同的表达结构并以类似的方式来解释,但两者背后的逻辑哲学基础完全不同——从现象学的视角来看,形式主义仅仅是一种观点或纲领,而不是能够自我辩护的、完整的哲学理 论。
但逻辑学是否及如何能承担此重任,还需要更多的资格审查。事实上,这个审查只有到全书最后才得以完成,而胡塞尔一开始的对科学“论证”(Begründung)的说明只能是初步与纲领性的。他的观点可以总结如下:第一,科学知识的论证本身具有固定构成的特性。① 胡塞尔:《逻辑研究》( 第一卷),第13 页。 也就是说,知识并不是直接来自偶然的经验给予物,而是遵循某种“刚性”的表达规则,用后来的话说即是出自本质法则 ,得到关于一般本质而非个别具体经验物的知识。相应的,科学论需要澄清规则本身及本质概念的特性。第二,论证表达之间的关联,或刚性规则之间的关系,本身也具有先天的规律性和确定性,这是真理线索的保证;相应的,科学论必须将本质规则整体作为一个关于论证形式的体系进行阐明,并显示其普遍有效性 。② 同上书,第14 页。 第三,也是极为关键的一个拓展,即从个别科学走向一般科学。每一种理性知识与构造它的认识方式一样,具有自身的“认识领域”,而不同知识的纯粹论证形式可以在一个更大的系统下被纯粹地研究。这个层面上的科学论研究也必须有如此形式和任务,要成为“探讨作为这种或那种系统统一性的科学 ”③ 同上书,第20 页。 。
事实上,关于一致性与真理性的问题虽然没有在胡塞尔早期的现象学哲学著述中专门讨论过,但是集中出现在他的数学和逻辑哲学研究里面。在哥廷根数学学会的两次演讲中,胡塞尔的核心论题就是关于19 世纪许多新出现的数学概念。这些新概念本身似乎没有什么“直观”内容可言,但却深刻地反映了当代数学不同于传统数学的特性,因而引发了一系列的哲学反思:新的数学关注的对象究竟如何理解,其含义是什么?更关键的是,“有”这种东西 吗?
对希尔伯特来讲,他就关心这样的问题:假如新的数学概念是有用的,那它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我们又如何断言其在数学上的存在?他的回答总体上是形式主义的:假如数学对象的构造不会导致矛盾,那就证明它是存在的。类似的看法亦被诸如康托尔等数学家认可。① Stefania Centrone,Logic and Philosophy of Mathematics in the Early Husserl,Heidelberg:Springer,2010,pp.153—154. 而胡塞尔讨论的是另一个密切相关的问题,即如何设想一种新的“数”的概念,数系在何种条件下可以合法地扩 张。
胡塞尔的回答与希尔伯特相去不远,他主张的条件可以简单概括如下:A)一种普遍算术、公理系统,甚至某种理论科学的概念整体,都可以在形式层面用算法或运算系统(Operationssystem)表征。② Edmund Husserl,Gesammelte Werke Band XII,Philosophie der Arithmetik,Hrsg. von Lothar Eley,Den Haag:Martinus Nijhoff,1970,S.444. 如果各算法系统之间构成一种依次扩张的关系,那么较大的系统必须有更多的公理或基本关系,但所有这些关系仅仅满足不矛盾性。B)这种扩张必须以保留原有系统的真理为前提。也就是说,不仅要保证旧系统内的全部命题在新系统内仍然可表达且为真,同时新系统中以旧系统语言表达的定理也得是旧系统的定理。③ Ibid.,S.438. 用现代逻辑的语言来讲,胡塞尔所要求的是一种保守扩张(conservative extension)。C)新系统必须能够基于它的公理系统与后承来确定地理解任何一个(用它的语言所表达的)命题,而且任何一个可能命题的真假也可以逻辑地确 定。
可是,从概念的范畴前进到作为关系形式与命题判断的句法系统,可以发现上述两项任务之间存在着极其密切的关联性:一致性推理必须体现在逻辑范畴的复合规律中才能表明这种纯粹逻辑学是有效的。在《逻辑研究》第二卷里,含义范畴之间的复合关系及其一致性规律即被统一在纯粹语法学的课题下,尽管没有充分展开。③ 胡塞尔:《逻辑研究》 (第二卷),第376—381 页。 同样,在《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中,关于范畴的形式本体论和关于判断的形式命题学(formale Apophatik)互相交织在一起成为纯粹形式逻辑的两大主题。④ Johanna Maria Tito,Logic in the Husserlian Context,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90,p.19.
四、纯粹逻辑学的“流形论”形态
胡塞尔论证自己观点的策略是:分别考察工具论和规范科学的目的论关联,同时注意理论科学与规范科学的异同关系,由此逻辑学即可获得自身的恰当定位。规范科学只要具有内在目的的可能性,它就可以生发出与之配套的技术操作,但由于规范科学自身已经意味着“应当是”,本质上就蕴含了一种进行价值认定与目的设定的可能。这样,规范科学与工具论就具有内在的或目的论上的统一性,区别仅仅在于后者是前者的特例,而规范性只是作为一般实践目标或技术目的的理论表述。① 胡塞尔:《逻辑研究》 (第一卷),第39 页。
19 世纪中叶,数学家黎曼在就职演讲中把一个变量在某种限制条件下取到的一切可能值的集合称为流形。后来许多数学家按各自想法延伸与扩展了黎曼的概念。胡塞尔亦然,他把任何一种现实或潜在的形式理论都称为流形,而最普遍、最一般的认识领域本身就是那种流形理论的对象。胡塞尔说:“一门流形论的最一般观念就是……确定地组织各种可能理论(或领域)的本质类型并研究它们相互间的规律性关系……如果在流形论中,有关的形式理论果真得到实施,那么为建立这种形式的所有现实理论而作的全部演绎性工作便也随之得到了完成。”① 胡塞尔:《逻辑研究》 (第一卷),第217 页。 简而言之,流形论实际上就是要把与特定质料 领域相关的纯粹科学统合到一些纯粹形式 的理论中,每个形式理论对应着一组“质料的”或实质性的纯粹科学,是它们的逻辑化或形式化的结 果。
比如说,最初关于空间特性的纯粹科学是欧氏几何,它的五个公设来自对实际空间的抽象,但并非纯形式理论,而是有其实质内容的(理想的空间元素)。在流形论观点下,希尔伯特的公理化方法是把原先的几何公设变为纯粹语法形式,让几何学成为完全按此形式规则演绎的形式系统。可是,这种纯形式理论还算是欧氏几何吗?在希尔伯特看来,如果认为欧氏几何的精髓就在于这些演绎关系和结构中,那么这种形式理论仍然保留了欧氏几何的核心,因此他有理由把自己的重构性著作命名为《几何基础》。而如果考虑到形式理论本身的意义、适用范围和几何学(geometria)的本质,那两者差别就极其明显,形式理论不带有几何学意义,也能够适用于任何一种满足其演绎关系的可能理论,欧氏几何只不过是其应用实例之 一。
既然流形论是关于一切可能理论的可能形式,那它就必然包含整个认识领域里一切可能的纯粹形式观念,也就是说,在第一个任务里展示出来的两种纯粹范畴与第二个任务所标示的后承逻辑学都作为理论形式的内容一并包含在流形论的框架内。可是,如果事情仅仅是如此,或许我们能够理解为何胡塞尔认为它具有最高的方法论意义,但真正说来这还无法展现其全部的内 涵。
近年来海上风电发展迅猛,装机容量已经超过 600 MW,单机容量由最初的2 MW 发展至现在的6 MW[1]。然而,伴随着风电渗透率的不断增加,其对电力系统稳定性的影响已经不容忽视。由于风能的随机性和不可控性,风电场的输出会有波动,因此对海上风电场进行建模与详细的可靠性分析至关重要。
胡塞尔在1900 年前后《观念I》 《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等著述中,都提到了“确定的流形”与“确定性”(完备性)概念。考虑到完备性,胡塞尔对形式系统的性质有更多的要求,如果以现代的方式总结,大致可以这么讲:如果一个理论T 是一致且语法完备的,那么T 的任何一个一致扩充都是保守的。① Stefania Centrone,Logic and Philosophy of Mathematics in the Early Husserl ,p.178.它蕴含了一个很自然的结论:数系的扩充与构造方式是正当 的。
服装造型是一个舞者的识别标志,在比赛中,一些优秀的舞者会选择一些特色装扮来增加自己的辨别度,如有些选手会选择标志性头饰、有些选手选择特色发型、有些选手会在衣服的款式或颜色上做变化。在表演中,舞者会根据剧情或角色的需要选择相应的服装造型以突出人物的表现力。
这里不用讨论胡塞尔的要求是否合理,只需要注意他强调数学系统或理论应当遵循的扩展方式。之所以选择保守扩张,因为我们希望理论与理论之间以及下层理论与上层理论之间始终保持着兼容关系。对于一切本体论概念,不论是形式的还是质料的,在流形论的视野下它们都必然构成一个整体:A)对于形式的概念和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相容关系,需要考虑的是对象范畴如何摆放到形式本体论的层级关系中。B)另一方面,质料本质并未作为一个专门概念出现在《逻辑研究》第一卷中,不过在第70 节里以自然世界空间的范畴为例说明了情况。② 胡塞尔:《逻辑研究》 (第一卷),第217 页。 简单说来,几何学处理的空间并非日常意义上的空间,而是范畴化和观念化了的空间。对于经典的欧氏几何来讲,它所处理的二维或三维空间是能够支持某种几何理论的最低层次上的、个别的空间范畴,在它之上还有更广义的空间范畴与一般空间概念本 身。
对胡塞尔来说,上述三个任务中,第二个任务表明了一致性 要求,第三个任务指向了完备性 与一致扩充,只有具备所有这些性质的理论才可能(但非必然)是基本的、严格的、表达真理的科学。流形论的真正目标是建立一种大全的理论形态 ,它既能够在自身内具有完备性,同时又能在面对特定对象领域的时候进行保守扩张。对于一般理论科学来讲,不同层次间的对象需要的研究方法和结果可能都不一样,而当我们从较小的认识领域转向更大领域的时候,之前的研究结果有可能因为种种遮蔽和限制而导致在更大范围和更全面的考虑下失效。为避免形式理论出现这种结果,我们希望小领域的研究结果在扩大研究范围后仍然成立,新的成果不会推翻过去的成就。这样,知识在扩展中还保持着严格性与确定性,变得越来越完 善。
结论:“纯粹逻辑学”的逻辑哲学意义
在胡塞尔看来,对传统逻辑学进行批判,重新确立逻辑学的性质与目标,具有重大的意义。首先,黑格尔之后的19 世纪哲学对于自身的目标、任务和进路都无所适从,陷入了比前两个世纪更混乱的争执之中。① 参见Frederick C. Beiser,After Hegel:German Philosophy 1840 —1900,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pp.15—18。 其次,新兴的人文科学与发展迅猛的自然科学在哲学基础方面和应用论域方面的大规模论战持续了近一个世纪,在深层次上质疑了人类现有知识的可靠性与发展的可能性。贯穿这两方面争执的一个方法论问题就是自然科学式进路何以有效,其适用范围又有多大。方法论问题的背后则是包括哲学在内的各种理论知识形态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分析,但无论是什么样的分析都会最终指向理论的某种形式理论。这正是逻辑学的基本内容,无论我们如何定义逻辑学,都必然要包含这部 分。
19 世纪的逻辑学发展奠基于密尔、弗雷格等人的重要工作上,对于逻辑对象的来源与本性都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在实际的数学与逻辑学研究中,人们逐渐认识到,这些学科处理的对象本身不具有经验实在性,而是有其独特的意义。同时,相应的研究工作的有效性与合法性也不能从经验科学的研究角度得到辩护。所以新时代的逻辑哲学与数学哲学基本任务,就是在肯定这些对象观念性与学科独立性的基础上,去解释这些性质的发生和理解问 题。
今天看来,胡塞尔的“纯粹逻辑学”纲领和康德的“先验逻辑”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逻辑学理论,而是逻辑哲学理论。纯粹逻辑学的基本构想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重新确立逻辑学的独立性和逻辑对象的观念,二是探讨逻辑学处理的对象类型、对象间关系类型以及最终形成的理论结构形态。作为理论形态的逻辑学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也能够作为“普遍科学”充当各种特殊科学的结构理论与形式理 论。
但上述基本构想并没有穷尽“纯粹逻辑学”的全部意义,因为逻辑学作为一般科学的形式理论,其有效性终究不是不证自明的,而是需要某种哲学来辩护。哲学必须对自身的概念以及概念之间的复合规律,连同一般的命题形式本身,都给出充分的解释,说明它们作为意识的行为结构与相关物是以何种方式、遵循何种规律给予我们的。胡塞尔认为,心理主义和柏拉图主义之间存在两难,一方面的令人信服立刻带来另一方面的牵强附会,而更完善的理论尚付阙如。因此,纯粹逻辑学所确立的观念性并不是哲学解释的完成,而仅仅是开启后续哲学研究的起点。在这个意义上,《逻辑研究》的发表意味着20 世纪初的逻辑哲学与某种彻底的认识论研究之间存在着某个结合 点。
本报讯10月30日,受国投新疆罗布泊钾肥有限公司邀请,中农控股参加了新疆和田地区和田县喀什塔什乡扶贫捐助活动,为当地捐款3万元。
最后必须指出,哲学虽然可以对逻辑做出某种“奠基性”的辩护,但这不意味着它本身可以在形式上超越逻辑的限制。科学论与流形论既然涵盖了一切理论的一般形式,自然也适用于哲学本身。这并不是说哲学研究要预设某种形式理论的前提,而是说它的探究成果既是对形式理论有效性的说明,同时也自身的形式也会满足形式理论的要求。可以说,《逻辑研究》第一卷不仅阐述了一种全新的逻辑学构想,而且确定了现象学和逻辑学的内在关联:现象学哲学 的规划必然要远远超出纯粹逻辑学或科学论范围,但无论它走多远,在基本形式与结构上也必然具有某种流形论 的形 态。
● Husserl’s Program of Pure Logic and Its Significances On the Philosophy of Logic in the First Volume of Logical Investigations
QIAN Liqing
Abstract: The first volume of Husserl’s Logical Investigations is very important to the development of phenomenology, and it also takes a role in the prosperity of philosophy of logic in the beginning of 20th century.Husserl’s conception of a pure logic has two aspects, the first of which has claimed independency and nonempiricality for logic, while the second elaborates on the type of logical objects and their relations as well as the complete form of the theoretical structure of logic. The second aspect finally leads to the scheme of a phenomenological study, thus it implies that there is a transition point from the philosophy of logic in question to a deeper and more radical epistemology.
Key words: logic; theory of science; theory of manifolds
中图分类号: B8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0047(2019)05-0066-15
作者简介: 钱立卿,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 员。
基金项目: 本文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当代数学哲学的现象学诠释”(项目编号:2018BZX011)资 助。
(责任编辑:肖志珂)
标签:逻辑学论文; 科学论论文; 流形论论文;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