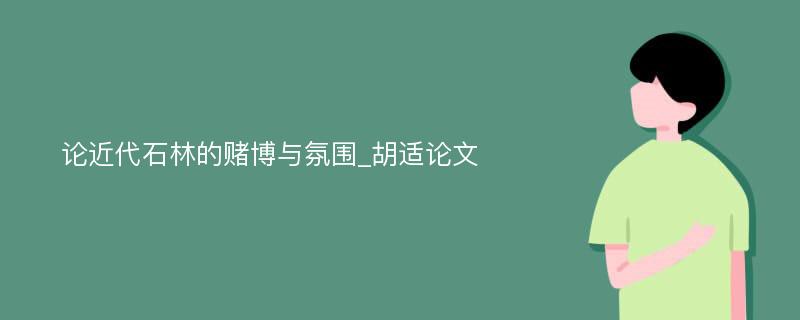
赌博与近代士林风气散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风气论文,近代论文,士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到赌博,人们总不免将其与市井中人、帮会无赖、商贾政客连在一起,很少想到清雅狷介的士大夫也会涉足赌界,甚至沉湎其中的。的确有不少文化人以卫道者自居认赌博为不耻,“考之于道艺,则非孔氏之门也;以变诈为务,则非忠信之事;以劫杀为名,则非仁者之意也。”[①a]因之“圣人不学,学者不览。”[②a]但殊不知文人们也并非桃园之人,方外逋客。士大夫中间以云博、格塞、棋弈为雅尚者不少,如果碰到责难或者有心理不平衡之时,就会搬出孔圣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平己”[③a]的箴言,或防人之口,或聊以自慰。于是,千百年来文人们参赌聚赌之事代有发生,不绝如缕。
传统士大夫参赌聚赌原因,除了普通人性因素以及文人们特有的“雅尚”外,似乎都与社会变动相关,在社会剧烈动荡的特殊时期,士子们参赌成风自然有特殊的内涵,对于他们来说,赌博或者是一种对于名教束缚的抗争与发泄;或者是一种对于社会变动、英雄末世的彷徨与无奈;或者干脆就是一种嗜好,一种中国传统士大夫于案牍劳形之余特有的消遣方式……
传统士大夫与赌博的关系格局对于近代知识分子有所影响。晚清以至民国的不少文化人介入赌博,在心理、态度、行为方式诸方面都与他们的前辈差别不大。但这并不等于社会与时代的变化没有对此施加任何影响,相反在某些参赌的近代知识分子身上所折射的时代特色还相当明显。如同是因消解苦闷而陷入赌博的泥沼,但其苦闷的内涵却与传统士大夫有所不同,因为消遣而作方城之戏,但消遣时的心态、意趣竟与旧时文人大相异趣……
先说晚清的两个例子。
龚自珍是近代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其学问道术、操行节守历来为世人称道。但此公却也有竹林之好,而且是赌场上一常败将军。据记载:
龚定庵嗜博,尤喜摇摊。尝于帐顶绘先天象卦,推究门道生死,自以为极精,而所博必负。
时杭州盐商家,每有宴会,名士巨贾毕集,酒阑,辄于屋后花园作樗蒲戏。有王某者,是日适后至,见龚独自拂水弄花,昂首观行云,有萧然出尘之概。王趋语云:“想君厌嚣,乃独至此,君真雅人深致哉!”龚笑曰:“陶靖节种菊看山,岂其本意,特无可奈何,始放情山水,以抒其忧郁耳。故其所作诗文愈旷达,实为愈不能志情于世情之征,亦犹余今日之拂水弄花,无以异也。”语此,复云:“今日宝路,吾本计算无讹,适以资罄,遂使英雄无用武之地,惜无豪杰之士假我金钱耳。”王本倾慕其文名者,乃解囊赠之。偕入局,每战辄北,不三五次,资复全没。龚甚怒,遂狂步出门去。[④a]
从上述文字可见,龚自珍对赌博是极认真的,每赌之前,都要精密推算一番。但其赌运与他的人生命运及时运、国运一样,极为不佳,可谓命乖运蹇、常输不胜。象定庵先生这样一位志行高远“萧萧然有出尘之概”的人为何会对赌博迷恋至此?这恐怕既非为了一博钱财,也不是官运亨通、志得意满后的潇洒和消遣,极有可能如他自己所暗示的与“抒其忧郁”有关。考之龚的身世及诗文,我们即可发现其言不虚。定庵先生的“忧郁”,既有类似于传统士大夫对怀才不遇,屡试不第个人遭际的不满,但更主要还是近代知识阶层对民族危机和社会更迭的一种忧患意识。在其诗文中就充斥着“幽恨满词笺”,“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之类的词句。他虽然曾经勾画过未来社会的蓝图,曾经提出过御敌防边的良策,也寄希望于“山中之民”起来推翻旧的社会,但都只是纸上议论,现实并没有按照他的议论而有所改变。于是只有忧郁,只有苦闷,只有沉湎于博场,去解脱,去沉醉。然而,定庵先生不是陶渊明,也不是谢安、李白、韩退之,其性情并不恬淡,手头也不阔绰,因此不能把输赢淡然处之,一旦赌输,便更加重其郁闷与不快。
与龚自珍相反,另一位文人赵菁衫倒是赌运亨通,常胜不负。《清稗类钞》载云:
赵菁衫观察清才硕学,为道、咸一代文宗。而嗜博成癖,术亦绝精,常胜不负,人至莫敢与角,则贷钱与之,负则再假,不责偿也。一日不博,若荷重负,自幼已然。太夫人忧之,恐将败行荡产,以孤幼,未忍峻责。或进曰:“若博而不废读,无妨纵之。久之术精,何患便毁家。设术疏而好笃,则为患烈矣。”因听其说,遂得博,读益愤,少年掇高第,产亦得无恙。自言博之道,通乎《诗》、《书》,其要义则在大《易》“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二语也。
赵氏之于博戏似乎可归于传统士大夫所说“雅尚”、“消闲”之类。有趣的是,他虽迷恋赌博,但既没荡产,亦没败行,更不废读。可说赌博功名两不误。这似乎不合于“行己有耻,博学于文”的古训,但两种极其对立的东西恰好在这位文人身上得到奇妙统一,这是否透露出近代知识分子一种新的道德修身观,尚待推测。但值得玩味的是,赵菁衫本人对赌博的看法,他之所以沉湎于斯,且毫不自渐,完全是出于他对博戏的一种文化理解与文化认同,他将博弈之道与《诗》《书》《易》贯通,从中体会出宇宙与人生“变动不居,周流六虚”的深刻意趣,俗不可耐的市井博技竞被其玩出一种清雅幽深的味道。这种境界岂是一般博徒所能轻易达到的。
象赵菁衫这样的文人大概属于“赌品”高尚之类。但并非所有参赌的近代文人都有赵氏那种“化腐朽为神奇”的悟性和才识的。在更多的文人那儿,赌博可能仍然还原为一种游戏,一种争胜。梁启超是一位道行较高的人,他有“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要打牌可以忘记读书”的名言传世,这充分说明赌博(这里指的是麻将)作为游戏对他的吸引力。梁实秋先生说:“读书兴趣浓厚,可以废寝忘食,还有功夫打牌?打牌兴亦不浅,上了牌桌全神贯注,焉能想到读书?二者的诱惑力、吸引力,有多么大,可以想见。”[①b]清末民初象梁任公这样对方城之戏有兴趣的知识分子不在少数,辜鸿铭闲来无事也是喜欢叉上几圈的,不过据说是一位“光绪(光输)皇帝”。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包天笑旅京,落脚于邵飘萍家,因无事可做,便与邵夫人邀潘公弼、徐凌霄在邵公馆经常打麻将。民国中期,也就是30年代,文人们闲暇之余或三两好友聚会之际,都有方城之战作为点缀,象徐志摩、萧军等都是其中干将。据说徐志摩的牌还打得相当漂亮,梁实秋说,麻将贵在临机应变,出手迅速,同时要手挥五弦目送飞鸿,有如谈笑用兵。徐志摩就是一把好手,牌去如飞,不加思索。麻将就怕“长考”。“一家长考,三家暴躁。”[②b]
然而,麻将并非只是消闲的工具,在清末民初知识阶层中,它更多的还充当着麻醉品的角色。以胡适为例,这两种功用就体现得十分明显。查胡适自传及《胡适的日记》,可发现胡适有两段时期与麻将发生过密切关系,一段为1910年一、二月间,胡适在上海中国新公学读书时。另一段为1922年前后,胡适任北京大学教授。前一段时期是借麻将解忧,后一段时期则是为了消闲。关于解忧,胡适《藏晖室日记》记云:“连日百无聊赖,仅有打牌以自遣。实则此间君墨、仲实诸人亦皆终日困于愁城恨海之中,只得呼卢喝雉为解愁之具云尔。”[①c]据统计,仅仅59天时间之内,胡适就打牌16次。究竟是什么不顺心的事导致胡适要自暴自弃?据胡适《四十自述》说是因为其“少年人的理想主义受打击之后”造成的。原来他曾参与上海中国公学要求学校民主的学潮,因校方拒绝学生要求而愤然集体退学,另组中国新公学,但新公学维持一年多后,因经济原因停办,胡适既不愿委曲求全重返旧校,又因家中经济困顿不想回家,于是“前途茫茫,毫无把握……在那个忧愁烦闷的时候,又遇着一班浪漫的朋友,我就跟着他们堕落了。”胡适及其他的这班少年朋友,这一时期沉醉于麻将,在当时的中国知识阶层中较具普遍性。1910年是黎明前的黑夜,知识分子中一部分人成为坚定的革命党人,在磨刀,在奋斗,而相当一部分人却消沉,却颓废。被磨蚀得光滑圆润的麻将,可作为近代文人软弱懦怯的见证;而哗啦哗啦的麻将声,似乎又是知识分子良知未泯,渴求民主新生活的心声在倾诉。
20年代胡适打麻将则又是一番心绪,这时他少年得意,26岁便成为北京大学教授,是饮誉海内外的知名学者。他在著书、执教之余,也不时搓上几圈,在这段时期的日记中,偶有“冬秀(胡适夫人——引者注)和几位女亲戚打牌,我也打了四圈”,“与芷舲、子慎、香谷打牌”[②c]之类的记载。胡适这时乃至到30年代中后期打牌,纯粹出于消遣:“近来太忙,每日做十几点钟的工,很想休息,又不得休息。我的天性是不能以无事为休息的;换一件好玩的事,便是休息。打球打牌,都是我的玩意儿。”[②c]由此可见,这时麻将桌上的胡适已没有旧日的愁苦,倒是多了几分得意,几分闲情。值得注意的是,在胡适所列诸类消闲方式中,胡适选择了麻将,这在近代知识分子中也颇具代表性,与前述梁启超之语暗合。这可能是麻将所特有的文化品性与知识分子的素养、性情、意趣存在潜在的沟通之处。说好一点,麻将的较智伐谋与文人善于用智重合,其流动的乐趣可补其终日枯坐书斋而造成头脑呆滞之不足。说不好的,就是麻将既可“深宵看竹”、“怡情养性”,“既可赌钱,又不十分现出赌钱的样子”(梁遇春语),这与中国文人伪善而又虚荣的心理最暗合不过的了。
因此,包括麻将在内的博戏在近代知识分子中间绝非仅仅是一消闲解闷角色,它仍然是有金钱财物输赢的赌博。在这一点上,近代知识分子与市井之辈没有两样。即使是象胡适这样十分注重自己名节的名人也难以免俗。好在胡适之先生输了钱,尚能从容应付,这当然与其身分和经济地位相关,一般小知识分子打牌输了钱,就不会如此潇洒。
近代知识分子除了涉足方城,小试身手之外,还有不少人到跑马场,回力球场,跑狗场一赌输赢的。被高楼与蜗居、文山与商海无情挤压的下层知识分子们参赌的动机、心态、意绪表现出直接、卑琐、茫然……与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以及自尊、清高、洒脱的风度毫无共同之处。近代(尤其是民国)士林的靡萎之风在这里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也就是在这靡萎之风遍被士林之际,仍然有许多知识分子没有同流合污,仍然维持着传统士大夫那种清廉自许、刚健自为的风范。这些知识分子对赌博的厌烦,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传统伦理的熏陶。巴金说是他的“父亲的板子从小就给我打掉了赌博的兴趣。因此,我对于那些整天把时间和金钱浪费在牌桌旁边、赌窟里面的人,就觉得有点不近人情了。”[①d]梁实秋的“家庭守旧,绝对禁赌,根本没有麻将牌。从小不知麻将为何物。”有一次他向父亲问起麻将的打法,遭到严辞训斥:“打麻将吗?到八大胡同去!”“吓得我再也不敢提起麻将二字,心里留下一个并不正确的印象,以为麻将与八大胡同有什么密切关联。”[②d]梁的父亲的教训是很有意味的,实际上是说赌博与士人身份不符。梁实秋后来坚决不受麻将的诱惑,大概便得益于自幼建立起来的这种身份观念:赌博无异于市井无赖狎妓嫖客的勾当,非清高儒雅的士大夫所能为。
如果说,巴金、梁实秋等拒赌尚属一种洁身自好的个人行为,那么,“五四”前后毛泽东、陈独秀、蔡元培、恽代英等通过舆论、社团等形式拒赌禁赌,则带有转移世风的鲜明历史自觉性。毛泽东组织的“新民学会”,其简章规定“以砥砺品行、研究学术为宗旨”。会规有“不懒惰、不赌博、不狎妓……”等条文,“含有一种实事求是、尚朴实、主诚实、禁浮华、戒骄躁等精神。”[③d]“少年中国学会”规约第十四条中有禁“嫖赌”等不道德行为,其目的在于“转移末世风气。本会信条,在积极方面,则有奋斗、实践、坚忍、俭仆之规定;在消极方面,则有第十四条概括规定之禁欲,实欲由少数青年身体力行,以造成一种善良之风气。”[④d]武昌利群书社等社团会规中都有不嫖赌的内容。“当时不少的青年学生是沉醉在极端个人主义的享乐腐败生活中:嫖、赌、烟、酒、鄙弃劳动、考试带夹带。代英同志针对这些时病,制定一种每日自省病,问本日是否做了利群助人的事,是否做到不嫖、不赌、不吸烟、不饮酒、不谎言、不带夹带等事。特别注意是否尚存留着这些意识与思想”[⑤d]。民国初年,蔡元培与李石曾、吴稚晖、宋教仁等人先后发起进德会、六不会和社会改良社等改良社会风气的社会团体。其主要戒约为:不狎妓、不赌博、不置妾、不吸烟、不饮酒等。但当时并无多少人实行。1918年1月19日,蔡元培又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北京大学之进德会旨趣书》,重新发起组织进德会。规定会员分为三种: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于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二戒;丙种会员:于前五戒外,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当时入会者不少,据记载教师76人,职员92人,学生301人。著名学者如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马寅初为甲种会员,蔡元培、范文澜、康白情、钱玄同为乙种会员,梁濑溟、张申府为丙种会员。由于不嫖、不赌、不娶妾为最基本的入会条件,因此,所有入会会员都是赞成戒除赌博的[⑥d]。“五四”时期进步知识分子的上述禁赌努力,给混浊卑琐的士林风气贯注了一股清新和煦的春风。尽管她在当时是那么微弱,但却代表了时代和社会的新潮流,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正是这批新型知识分子,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创造了一个使包括赌博在内的社会陋习全面、彻底禁止的新社会。诚如毛泽东所说,五四代表中国知识分子新方向,他们所努力提倡并身体力行的新风尚,才是近代士林风气的主流。
注释:
①a [魏]韦曜:《博弈论》。
②a [唐]李翰:《通典序》。
③a 《论语·阳货》。
④a 《清稗类钞·赌博》。
①b②b 梁实秋:《麻将》。
①c 《胡适的日记》(上),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②c 《胡适的日记》(下),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①d 巴金:《赌》、《旅途随笔》,生活分店1934年版。
②d 梁实秋:《麻将》。
③d 萧三:《毛泽东同志在“五四”时期》,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光辉的五四》。
④d 王光祈:《本会发起之旨趣及其经过情形》,《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三期,1919年5月1日。
⑤d 廖焕星:《武昌利群书社始末》、《五四时期的社团》(一),三联书店1979年版。
⑥d 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标签:胡适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读书论文; 历史论文; 梁实秋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