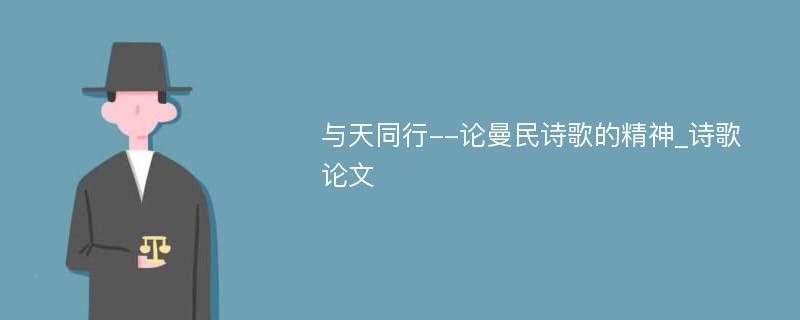
与天同游——罗门诗歌精神散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歌论文,精神论文,天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可能的天堂和实在的人世之间,千百年来,无论是用灵视还是用肉眼,我们所能企及的,永远只是那一片蔚蓝——虚茫而又深邃,混沌而又明澈;它存在着,即使驾驶着宇宙飞船,以光的速度前行,也无法穷尽它而它依然在你视野的前方辉耀着。它是这样的一种存在:我们既不能将它象玻璃一样敲下一块来做梳妆镜,又不能因它毫无实用价值而无视它的存在——抬起头,它就在我们眼前;低下头,它又在我们的心里。它唯一的功用在于提升和净化我们的目光,使之看到我们肉身的卑微与脆弱,同时也看到我们精神的宏阔与超迈。这是一种开启而非遮蔽,这是一种引领而非统治,这是人类的独自拥有的另一种目光——在人世之外,在自然之外,在实在的生活和笼子之外,照亮另一片风景——如另一只手,伸向你,伸向所有的人类,永不收回!
这便是艺术,是诗,是诗性/神性生命意识所拓殖的人类精神空间,是唯一可能握得着的“上帝之手”——诗人罗门则形象地将其命名为“第三自然”,便由此确定了他的诗歌立场,为其服役一生。
因了气质的不同,也因了文化境遇的不同,实际上,古今中外的诗人们,在对人类精神空间的拓殖中,一直存在着外向与内向两个向度的进发。一部分着眼于人的内宇宙,深潜于个体的生命体验之幽微曲回,以此揭示人类意识深处的本真存在,可称之为“微观诗人”;另一部分则放眼于人的外宇宙,高蹈于人类整体生存状态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之风云变幻,以此叩寻为历史和现实所遮蔽了的神性启示以洞见未来,可称之为“宏观诗人”。以此去看罗门,显然属于后者。虽然在他的诗之视域中,也不乏对现实人生及个体生命体验的探幽察微之观照,但更多的时候,诗人是以“高度鸟瞰的位置”(林耀德语)高视阔步在现世和永恒、存在与虚无之间,以其泼墨大写意般的诗之思,代神(诗神与艺术之神)立言,代永恒发问,以“将人类与一切提升到‘美’的颠峰世界”(罗门语)来完成他的“第三自然”之追寻。
与天同游以观照人世,以贯通天、地、人、神于“美的颠峰”——“双手如流”(罗门诗名句),诗人要推开的是一扇为尘世所一再遮掩起来的诗性/神性生命之窗,让我们在他的吁请中去叩寻“第三自然”的归所,对于这一超凡脱俗的诗人形象,罗门在其写于1989年的一首题为《与天同游的诗人》作品中,似乎作出了最恰当的自我写照:
你不是从那些烟囱里
制作出来的烟
也不是在低高度
走动的雾
你是以整座太阳的热能
从大地幅射
不断向上升华的
云
在一个主体人格普遍破碎猥琐的时代里,诗人罗门为我们所展示的这样“与天同游”的精神境界,确实令人感佩至深。无论诗人笔力所及,对其意欲追寻的这种境界表现了多少,仅就这种支撑其创造的精神源流之本身而言,在当代诗人中,也确是屈指可数的。也正是因了这一丰沛而宏阔精神源流的灌注,方使所有读到诗人作品的人们,无不为涌流在诗行中的那种“以整座太阳的热能”所迸发出来的“幅射”力所震撼!由此我们更看到,无论现代诗在其语言与形式上,发生和发展着怎样的实验与变革,其精神取向的深浅狭广,仍是第一位的因素。即或是身处后现代语境之下,诗,依然是精神的产物,而非工艺的制品。
二
在大陆诗学界,尤其在一些前卫/先锋诗歌理论与批评家那里,一直有一种先入为主的看法,即在缺乏全面深入的研读的情况下,就主观判定台湾现代诗只是在艺术上有一定价值,而在精神向度方面的开掘“肯定有限”,所谓:“小而美”、“堂庑不大”……等等。大陆有实力的前卫/先锋诗评家们多年来之所以一直鲜有人致力于台湾现代诗的研究,内中原因很多,但受这种人云亦云先入为主的观念之影响,也是其主要因素之一。
实则这确实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台湾现代诗从50年代初全面勃兴至今,经近半个世纪的深入拓展,实已在审美价值和意义价值两个方面,都已取得了历史性的丰硕成就。诚然,在大部分台湾诗人那里,我们确能感觉到,其对诗歌技艺的守望远远超过对诗歌精神的开掘,感情透支,诗思枯竭,唯剩下形式的重复,一些脱尽内涵的“空洞能指”。但声势浩大的台湾现代诗运,毕竟还造就了一批“重量级”的诗人,他们不仅以其各自独到的风格极大地丰富了现代诗的艺术殿堂,也同时以其不同凡响的诗之思之言说,极大地拓展了现代中国的精神天地——诗人罗门即是其中之一。
在台湾,罗门曾名列十大诗人之列。这十位大诗人各有千秋,而罗门的入围,依笔者所见恐怕主要见其诗歌精神的“堂庑”之大。这样说并非要贬低罗门在诗歌艺术上的成就,而是想指出,在对现代诗之精神向度的探求与拓殖方面,罗门是着力最重也最为持久的一位诗人,那份雄心和那种韧性以及圣徒般的虔诚与坚卓,是极为难得的。我想,大概每一位为罗门所吸引的读者,首先感动于心的,便是透过诗行所喷涌而出的、唯罗门所独具的那种精神的冲击波和震撼力,以及那不竭的生命激情和时时要穿透一切的敏锐目光。
何谓“堂庑之大”?细研罗门的作品,笔者发现,在罗门的诗歌精神构架中,几乎已涵纳了现代人类所面临的主要命题——
(一)对现代科技文明的反思与对现代人生存境况的质疑。
对这一主题的关注,在台湾,罗门是最早的开启者之一,也是最持久的拓殖者,故被评论者称为:“城市诗国的发言人。”我们仅从一系列罗门此类诗作的题目,便可见诗人在此向度的掘进之深广:长诗《都市之死》、《都市 你要到哪里去》、组诗《都市的五角亭》,以及《都市,方形的存在》、《迷你裙》、《咖啡厅》、《夜总会》、《床上录像》等一系列以都市生活为题材的短诗,其中《都市之死》等一批代表作,尤其为论者称道,影响甚大。应该说,罗门对这一类题材如此着力,显示了一位大诗人慧眼独到的超前性。现代人的主要麻烦是都市的麻烦,这里引诱的是欲望,追求的是流行,操作的是游戏,满足的是感官,造就的是“没有灵魂的享乐人”(马克斯·韦伯Marx Weber语)——在这里,在这些由水泥、钢铁与玻璃所拼凑的聚合物中,“脚步是不载运灵魂的”,而“神父以圣经遮目睡去”,“人们慌忙用影子播种,在天花板上收回自己”,并最终成为“一只裸兽 在最空无的原始”,而都市则化为“一具雕花的棺 装满了走动的死亡”——现代科技文明所造成的诸般负面效应,在诗人意象化的诗句里,得到了极为深刻凝重的揭示。
(二)对战争的反省和对死亡的透析。
诚如诗人所言:“战争是人类生命与文化数千年来所面对的一个含有伟大悲剧性的主题。”“是构成人类生存困境中,较重大的一个困境。”(《麦坚利堡》附注②)战争造成巨大的非正常的死亡,而人类更大的悲剧在于那些日常的、生来就必须面对的死亡之阴影。这是生命之根本性荒诞,并成为认知生命本质的基点。“……死亡带来时间的压力与空间的漠远感是强大的。逼使诗人里尔克说出‘死亡是生命的成熟’;也迫使我说出:‘生命最大的回声,是碰上死亡才响的’。”(《死亡之塔》题记)可以说,这些站在哲学高度所发出的理论认知,奠定了诗人对这一主题之诗性言说的坚实基础,由此成就的一批写战争与死亡的诗作,遂成为诗人为现代诗所做出的又一突出贡献。其中,长诗代表作《麦坚利堡》、《死亡之塔》、《板门店·38度线》等,更成为人们认识和领略罗门诗歌的标志之作。尤其是《麦坚利堡》一诗,无论就其审美价值来看,还是就其意义价值而言,都已抵达人类共识性的深度和广度,从而引起所有读者的强烈共鸣,为诗人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三)对现代人精神困境的揭示和对走出这种困境的诗性的探求。
这一命题实则已成为罗门诗歌精神的基石,亦即是他全部诗思的焦点所在。我们在诗人几乎所有的诗章中都可以找到这个焦点的闪光,而集中表现这一命题的,则以长诗《第九日的底流》《旷野》和短诗《窗》、《天空》、《流浪人》等为代表作。在这些作品中,诗人创造了许多令人触目惊心的典型意象,如“收割季后 希望与果物同是一支火柴燃熄的过程/许多焦虑的头低垂在时间的断柱上/一种刀尖也达不到的剧痛常起自不见面的损伤“(《第九日的底流》)“猛力一推,竟被反锁在走不出去/的透明里”(《窗》)“明天 当第一扇百叶窗/将太阳拉成一把梯子/他不知往上走 还是往下走”(《流浪人》)等。在这些可称之为“罗门式”的经典意象中,现代人焦虑、困窘和迷失的生存境遇,被揭示得入木三分,而在这种揭示的背后,我们更可感受到诗人那种超越个在体验,代人类觅良知、寻出路的阔大情怀——由大悲悯而生发的大关怀。
至此,我们似可以给罗门诗歌精神的“堂庑”,勾勒出一个大致的框架——这个框架由罗门诗中的主体意象和常用的关键词梳理组成并呈三个象限的展开——
第一象限:都市/人→在场的肉身/物化的生存样态→死亡;
第二象限:旷野/鸟→逃离的灵魂/失意的生存样态→悬置;
第三象限:天空/云→重返的家园/诗意的生存样态→永恒。
三个象限构成三维想象空间。互为指涉,互为印证,诗思贯通天、地、人、神,产生巨大的精神张力,呈现一派与天同游、与地共思的雄浑气象。应该特别指出的是,罗门对第三象限亦即其所称“第三自然”的指归,并未盲目而简单地落于“天堂”落于“上帝”,而是指向代“上帝”立言的“艺术与诗”。诗人曾尖刻地将天堂比喻为“洗衣机”,而“谁也不知道自己属于那一季/而天国只是一只无港可靠的船/当船缆解开 岸是不能跟着去的“(《死亡之塔》)由此诗人认为,人欲获救,于虚茫中找到永恒,必得“重返大自然的结构中,去重温风与鸟的自由”——这便是艺术的自由,诗意生存的自由。罗门是有宗教情怀的,无论是从他的诗作中还是其诗学理论中都可以感受到这种情怀的存在。只是诗人并未将这种情怀上升为虚妄的宗教狂热,归于单一的宗教维度。诗人明白,即或诗人真能将自己打磨成一把开启“天堂之门”的钥匙,可能否找到“门上的那把锁”呢?这是一个世纪性的悖论——而正是在这一悖论之中,诗人方获得他存在的特殊意义——“而你是唯一在落叶声中/坚持不下来的那片叶子/陪着天空”(《天空》)。这里的“天空”与“虚茫”“永恒”同构,而“那片叶子”、便是诗性的灵魂,是经由艺术与诗之导引,重返精神家园的本真生存样态。实际上,在哲学家们宣称“上帝死了”接着又宣称“人也死了”之后,艺术与诗,确已成为在这个世纪里依然觉醒着的人们的“私人宗教”——而这,正是罗门诗歌精神的宏关主旨之所在。
三
经由以上对罗门诗歌精神的粗略透析,我们便可进一步把握其诗歌艺术的基本品相。纵观罗门的作品,其主要的艺术特质,似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其超越性。罗门诗思灵动阔展,常有很大的时空跨度。无论处理那一类题材,都能自觉地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域之视点溶合在一起,放开去思、去言说,不拘泥于一己的情怀,或狭隘的历史观及狭隘的民族意识。表现在语言的运用和意象的营造上,也不拘一格,善于融化一些新的意识和新的审美情趣,创造出一些新语境。如此,便常常可以超越地域、时代与民族文化心理的差异,也便经得起时空的打磨,得到广披博及、长在长新的艺术魅力。
其二是其包容性。这主要来自于诗人创作中的大主题取向,无论长诗短诗,都能大处着眼,赋予较深广的底蕴。如屡为诗家称道的《窗》一诗,短短11行80余字,便营造出一派大气象,其开掘的精神空间已不亚于一首长诗的容量。这种包容性还表现在另一方面,即在罗门的诗思指向中,不仅有对现实犀利的批判,对存在深刻的质疑,同时也有对良知的呼唤和对理想的探寻,所谓“正负承载”,便具更大的震憾力。
其三是思想性。罗门本质上是一位偏于理念和知性的诗人,支撑其写作的,主要在于对意义价值的追寻而非浅近的审美需求。诗人大部分的作品,都可归为一种思性之诗,弥散着浓郁的哲学气息,且常有一种雄辩的气势和思辩之美让人着迷。实际上这也正是中外杰出诗人的一个优良传统,正如笛卡儿早就指出的那样:“有份量的意见往往在诗人的作品里,而不是在哲学家的作品里发现。”只不过当代汉语诗歌界里,罗门在此方面的探求,显得更为突出和执着。
而问题正由此提出——
细心研读过罗门所有作品的读者和批评家,或许都会发现这样的两个现象:一是其晚近作品与早期一大批成名之作(主要是集中在60年代的一批力作)相比,思想性更加突露而在审美价值上有所降低;一是就整体作品而言,在其创作主体所拓殖的精神空间与通过文本所凝定的艺术空间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落差。我们知道,罗门在60年代成名之后,便开始分力于对诗学理论的研究,至今已先后出版了《诗眼看世界》、《时空的回声》、《罗门论文集》等五部论集,用另一种文体来拓展和张扬他的精神立场和诗学主张。应该说,罗门在这一领域的贡献也是十分突出的,显示了一位杰出诗人的雄心和才具。然而,恐怕连诗人自己也未觉察到,当这一雄心发展到太过肯定,并急于使“可能”更多地转化为“现实”时,它对创作的负面影响就逐渐显露了出来——常为喷涌而生的观念的内驱力所推拥,急于言说而缺乏必要的控制,出现了一些人为的“预设框架”和“观念结石”,失去了原本自由而沉着的呼吸,过早地收缩于一个想象的中心。诸如后期的《文学新社区的开拓者》(1989年)、《有一条永远的路》(1990年)、《大峡谷奏鸣曲》(1993年)等一批作品,对观念的演绎愈发严重,对意象的经营缺乏创新,遂导致重复;不是主题的重复,而是说法的重复。语言也便渐趋滑于直陈式的,事象性的,只是组织得比较新颖机智,且依赖于一些奇崛之思的点染和出人意料的比喻作支撑,但整体上的语感显然已比从前有所弱化。
或许,以上的批评,并不尽切合诗人的创作实际,乃至仅只是笔者的一己之偏见。但作为一个诚实的批评家同时也作为一个诚实的读者,在研读完罗门的作品之后,确实从内心深处,更怀念起那个创作《麦坚利堡》、《第九日的底流》等作品时期的罗门。当然,返回是没有意义的,但超越是一份真诚的期许,而罗门正是属于那种具有超越意识和能力的诗人。其实他一直在做着这样的努力,只是好象有点错位。但对于罗门这样的诗人来说,奇迹可能是会随时发生的——不竭的激情,总是活跃敏感的思绪,似乎永远年轻着的心态,尤其是那份圣徒般的虔诚与坚卓,终会使他象在《旷野》一诗题记中所说的那样:“以原来的辽阔,守望到最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