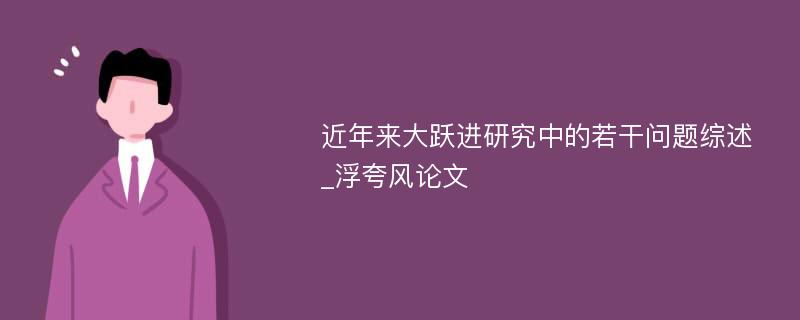
近几年“大跃进”研究若干问题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跃进论文,近几年论文,若干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10)01-0088-14
“大跃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仅就2006年以来发表的有关“大跃进”研究论文(包括当事人的回忆)作一概述,以期推动“大跃进”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对“大跃进”发动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
“大跃进”发动的原因是学术界一直探讨的老问题。任贵苓认为“大跃进”发生的原因有国际环境影响、社会历史原因、反右派斗争影响、毛泽东个人原因和体制上原因。[1]齐霁等认为有理论与实践方面、国际方面、国内社会历史条件、社会心理方面、中央体制及毛泽东个人方面的原因,以及反右派斗争影响的因素。[2]张明霞总结了国外学者对“大跃进”发动原因的探讨,主要有“一五”计划起因论、不断革命起因论、派系政治起因论等。[3]孙瑞华认为,快速发展生产力、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是“大跃进”发动的美好愿望;“左”倾错误逐步在党内占了上风是“大跃进”发动的主要原因;赶美超英浪潮是“大跃进”发动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国际背景;社会主义阵营蓬勃生机这一有利的国内国际环境是“大跃进”发动的条件。[4]张佩娟认为,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忽视客观经济规律是“大跃进”发动的首要原因;力图摆脱苏联发展模式的影响,探索本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是其发动的重要原因;中国的历史传统和中共的政治权威为其发动提供了现实可能;中共的领导体制和决策体制为其发动提供了组织保障。[5]陈燕考察了“大跃进”发动的经济体制原因。[6]李和平总结了“大跃进”发动的历史成因有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和全国人民急于求成、错误地批评“反冒进”、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存在弊端等。[7]
关于国际环境对“大跃进”发动的影响,韩金玲认为面对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快速发展的现实,中国必须超常规、高速度地发展——发动“大跃进”。[8]赵付科等认为,“大跃进”是由苏共二十大带来“思想解放”走向极端的“创造”;以苏联为首的国际共运中赶超战略和浪潮的影响,是“大跃进”发生的直接外在动力;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非正常化发展,又使毛泽东产生了率先进行“赶超”的想法。[9]柳绩等认为苏联因素的影响始终浮现于“大跃进”运动中。[10]张勇认为,毛泽东提出“赶超英国”,既与国内反“反冒进”思想一脉相承,也与第二次访苏期间受苏联影响有关。[11]韩钢认为,毛泽东在同西方国家竞赛的同时,也与苏联展开竞赛而且更看重这场竞赛,可从这一视角考察“大跃进”的由来。[12]
关于国内环境对“大跃进”发动的影响,唐正芒认为,1957年整风运动不仅在思想上为“大跃进”做好了舆论准备,而且因反保守而制订的高指标,又在事实上为“大跃进”的开展定下了目标。[13]罗重一等考察了“大跃进”发动之初的组织环境,认为南宁会议点燃了“大跃进”的导火索;成都会议确定了“大跃进”的高速度;八大二次会议确立了“大跃进”的指导思想;北戴河会议把“大跃进”全面推向高峰。[14]林蕴晖认为,“大跃进”的发动与当时党内形成的无法提出不同意见的政治氛围有密切关系。[15]邓昀考察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与农业“大跃进”发动的关系,认为它拉开了农业“大跃进”的序幕。[16]
关于体制和个人对“大跃进”发动的影响,余英认为,1958年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既是农村“大跃进”运动的产物,又进一步支撑了工农业“大跃进”。[17]方赛容认为,毛泽东“敢想敢说敢做”思想被片面渲染,成了发动“大跃进”的舆论基础。[18]高其荣等认为,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对“大跃进”的发动起了直接而又具体的推动作用。[19]
关于社会历史、心理方面的因素对“大跃进”发动的影响,杨奎松认为,“大跃进”是毛泽东的一个“强国梦”,也是当时举国上下成百上千万人想要创造人间奇迹的集体雄心的写照。[20]李朝军等认为,公众群体性运动的无意识、盲目性以及非理性等特性在运动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21]梁志敏认为广泛存在的“急于求成”、“骄傲自负”、“‘左’比右好”、“盲目攀比”、“崇拜权威”、“趋利从众”等特殊社会心理,对“大跃进”的发生、发展和持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2]
另外,邓进认为只有通过经济快速增长改变落后的局面,改善人民的生活,人民群众才会认同和支持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大跃进”成为选择。[23]黄宗华等从传播学的角度指出,“大跃进”的发生是政治传播中的思想政治教育、领袖传播、组织传播和媒介传播等合力作用的结果。[24]
除此之外,学者们还对与“大跃进”发生相关的其他问题进行了研究。关于“大跃进”的起点和发动标志,韩钢认为,如果不拘泥于口号,“大跃进”运动实际上是从1955年农业合作化速度加快开始的。[12]赵勋进考察了八大二次会议召开前后的情况,认为它的召开表明了“大跃进”的正式发动。[25]关于“大跃进”发动与赶超思想之间的关系。李守可总结了三种观点:毛泽东赶超思想的发生与发展是“大跃进”发生的重要原因;毛泽东赶超思想与“大跃进”运动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并不构成前因后果的关联;毛泽东赶超思想与“大跃进”的发动是一种双重互动关系。[26]罗平汉[27]、钱堂容[28]指出,赶超思潮与整个“大跃进”相伴始终。另外,刘家钦对“十五年赶超英国”口号进行了考证,认为这一口号在国内是1957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社论首先公布的。[29]姚润田也对“赶超”口号的演变进行了分析。[30]关于“大跃进”的指导思想,王治涛认为,“不断革命”论阐述了“大跃进”的前提、赶超目标和途径、领导和依靠力量、工作方法等问题,是“大跃进”的指导思想。[31]他还分析了“不断革命”论的意义与不足。[32]
二、对各行业、各地区“大跃进”的研究
农业“大跃进”是“大跃进”的先声,而农业“大跃进”又以农田水利建设为开头。吴志军认为,1957年冬1958年春的水利建设运动具备了“大跃进”的多种要件,标志着“大跃进”的正式启动。[33]陈惺回忆了“大跃进”时期河南水利建设的情况,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34]王瑞芳认为,这一时期的农田水利建设有得有失,得大于失;七分成绩,三分失误。[35]丁银高等从动员方式、运动模式、运动伦理、组织保障等方面,分析了政治运作对农业“大跃进”的推动。[36]张海博认为,大炼钢铁、大放“卫星”、大办公社、大办水利、大办民兵师,是农业“大跃进”的主要形式。[37]欧阳贻法则追忆了广东连县田北高产“卫星”一事。[38]
文教事业“大跃进”是“大跃进”的重要组成部分。杨凤城认为,文化建设“大跃进”的实现形式是“走群众路线”,从一般意义上讲具有合理性,然而在“走极端”、“一刀切”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下,却又走向荒唐,把普通民众的文化创造力、对文化的需要及对精神产品的评判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39]赵红峰、李涛分别考察了浙江高教“大跃进”的情况,认为付出了沉重代价,但同时也对突破苏联教育模式进行了有益尝试,并为后来高校的发展在专业及科研上奠定了初步基础。[40]刘洋记述了教育领域教学和科研“放卫星”,教育“大跃进”发展以及受损失的情况。[41]张烨分析了1958年高教“大跃进”发生发展的原因,认为其既有文化冲突的宏大背景,也有地方教育权力的中观诉求,还有受教育者及基层高校管理者的微观现实需求和动机。[42]邓进以广东省师资队伍为个案,研究了这一时期教师队伍的补充及培训问题。[43]近年来,对教育“大跃进”的回忆材料逐渐增多。王德彰[44]、施杰锋[45]、肖先治[46]、蔺德元[47]、赵俊贤[48]等分别回忆记述了自己所在中学、大学或自己在“大跃进”中参加深翻土地、大炼钢铁等运动的情况。曾任河南省教育厅负责人之一的王锡璋,回忆了河南教育“大跃进”的情况,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49]扫盲运动是文教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代天喜认为,党和政府颁布的一系列关于扫除文盲的文件,对于当时乃至当今的扫盲教育起到了历史性的奠基作用。[50]孟样才认为,“扫盲大跃进”不过是“大跃进”中一出小闹剧。[51]另外,贾艳敏对当时全民学哲学运动进行了分析。[52]对这一时期的扫盲运动应持一分为二的态度,进行客观分析。
对于科技工业方面“大跃进”的研究,也有一些成果。丁抒记述了大炼钢铁中“以钢为纲”的危害。[53]鲁戎[54]、靳承美[55]分别回忆了当时参加大炼钢铁的情况。杨小林记述了中国科学院受形势影响而采取的“跃进”措施。[56]罗平汉记述了“大跃进”的狂热让科学浮夸的事例。[57]邓进以广东省为案例,分析了当时技术革命运动的产生背景、展开阶段、具体做法以及对国民经济的影响。[58]孙烈考察了“蚂蚁啃骨头”的机械加工方法受到重视和推广的情况。[59]朱显灵等对“大跃进”时期农具改革运动进行了考察,认为农具改革运动不仅未能取得预期的成效,反而造成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浪费,影响了正常的农业生产,损害了广大农民的利益。[60]黄英等梳理了“大跃进”时期政治环境对国家技术观的影响,认为技术革新和创造成为政治任务,造成了技术的倒退和经济损失。[61]李杨记述了“大跃进”时期茅台酒产量跃进的情况。[62]
此外,美国学者大卫·兰普顿考察了“大跃进”时期的医疗政策,认为医疗“大跃进”失败的原因在于领导层政策缺乏一致性、决策权条块分割上面。[63]孔祥毅记述了中国人民银行在“大跃进”中的坎坷。[64]葛渭康记述了自己任公社粮管所副主任时从“大跃进”到饥饿的体会。[65]范眭回忆了当时有悖记者职业准则的亲历。[66]王幼辉[67]、尧山壁[68]分别记述了农业放“卫星”、大炼钢铁、深翻土地等方面的情况。
学者们还对各地“大跃进”情况进行了研究。石建国考察了东北“大跃进”及其对东北工业影响,认为从发展绩效的角度来衡量是失败的。[69]张文清分析了上海的“大跃进”与这一时期上海经济建设情况,认为应将两者区别开来,“大跃进”给上海造成了严重失误,但这一时期上海广大群众建设热情高涨,也取得了可贵的成果。[70]黄坚认为“大跃进”时期上海市政建设获得快速发展,但由于没有统筹兼顾好生产和生活,人民生活受到影响。[71]李君[72]、李伟[73]分别考察了山东“大跃进”和农业“大跃进”的情况,认为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同时也造成严重危害。另外,梁志远回忆了“大跃进”中安徽亳县党政群机关遭到冲击的情况。[74]何立波记述了徐水“大跃进”的情况,以及毛泽东对徐水经验否定的过程。[75]
三、对“大跃进”新民歌、壁画等文艺形式的研究
近年来,众多学者对“大跃进”中的新民歌运动、壁画运动等文艺形式进行了探讨。
关于新民歌运动的形成与发展,张育仁认为,“大跃进”民歌的发生发展与毛泽东青年时期钟情的“新村主义”有极深的政治伦理联系。[76]他认为,“大跃进”运动自始至终隐伏着民粹主义和“新村主义”诗化哲学的魂灵。[77]李丽琴认为,新民歌是由毛泽东直接提倡、组织,各党政部门与文艺部门的紧密配合,文艺家、诗人、群众的集体创作三者的推动下生成发展壮大的。[78]吴继金认为,毛泽东的政治理想主义左右着新民歌运动的发展,新民歌的夸张色彩受毛泽东浪漫主义气质的影响,而毛泽东强调政治性与艺术性统一的思想,直接导致了这场运动的终结。[79]董丽娜认为,民歌运动的发生不仅仅是主流意识形态单方面诉求的结果,它作为特殊文学样式的功能性因素同权力话语的时代要求实现的高度契合是导致这一运动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80]方涛认为,新民歌运动的发生与外部的权威导向密切相关,它的形成是集体主义膨胀的一个文学结果。[81]对于民歌运动的结束,江波认为,1960年这一运动渐渐偃旗息鼓。[82]罗平汉[83]、徐秋梅等[84]认为,1959年3月第二次郑州会议决定“诗歌”卫星通通取消,新民歌运动即停止,后一种说法比较符合实际。
关于新民歌反映的内容,张志慧等认为,新民歌隐含着诸多神话因素。[85]熊忠武认为,“大跃进”民歌因感情的缺位而导致了诗性的迷失。[86]李巧宁认为,新民歌中不乏豪情壮志,但更多的是浮夸虚假的应时之作,是主流话语的翻版。[87]韩金玲认为,新民歌存在一种悖论:一方面表达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意识,另一方面又使民众的自我意识无限膨胀。[88]盛瑞强认为,“大跃进”歌曲歌词沦为政治和政策的传声筒。[89]赖继年认为,新民歌反映了群众改变祖国面貌的迫切愿望,也直接间接地宣扬了“浮夸风”。[90]赫牧寰认为,新民歌把诗歌应具有的独特的意象创造、自由的情感表达和真诚的理想抒写完全消解于政治话语中,失去了民歌应有的魅力和文学应有的审美特质。作为政治话语,其也失去了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所应有的积极力量。[91]有的学者还对新民歌内容进行了个案和比较研究。何云贵以重庆的《跃进民歌》为个案指出,研究主要不是着重它的文学价值,而是把它作为一个历史文化现象来研究。[92]吴晓等以《红旗歌谣》为个案,认为特定权力意志的政治需要,造成了其中“民间”的意味丧失殆尽。[93]常帅也以《红旗歌谣》为例,认为新民歌运动是一场全民乌托邦的歌唱。[94]李静将“五四”时期的北大歌谣运动与新民歌运动作了比较,认为两者虽然都取面向民间之姿态,却各有倚重;前者旨在文艺创作思想的革新和中国现代民俗学学科研究领域的开创,后者则旨在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化革命诉求。[95]张凤渝指出,“大跃进”民歌艺术不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个性化创作,而是表现为艺术与生活的同一化。这样的美学追求,表达出对于西方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96]
关于新民歌的评价,郑祥安认为,新民歌违背了文艺创作规律,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艺术表现上并非一无是处。[97]鲍焕然认为,新民歌运动旨在建构优越于西方现代性的民族文化并真诚地借用“古典”和“民歌”的形式,结果却在规范与规训的双重作用下,于一体化认同建构过程中形成对世俗现代性的渴望与追求同审美现代性的极度缺失的强烈反差,从而走向对真正意义上的古典和民歌的自反性否定。[98]张凤渝认为,要重估新民歌在文学史上具有的承上启下意义,它是文艺大众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对于民间话语本身缺乏批判。[99]宋洁认为,“大跃进”民歌既是文学文本也是一种历史文本。“大跃进”民歌所透露出的群众的情感是真诚的,但是历史本身偏离了正确的轨道,由此这种情感也就成为一种被支配的情感。历史文本这时就仅仅成为了集体记忆,它不能等同于历史真实本身。[100]巫洪亮从工农“文化翻身”的视角来审视新民歌运动,认为新民歌运动中“文化翻身”既是真实可感的,又是在一定的限度内进行的。[101]此外,李兴濂指出,“大跃进”中绝大多数民谣现已散失、遗落,应加以抢救、收集和整理。[102]柯云记述了“大跃进”中开饭前做诗的情况。[103]
对于“大跃进”中兴起的壁画运动,吴继金认为,壁画运动对于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普及艺术知识、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起了积极作用。其不足之处在于:这种大规模的运动式的、一哄而上的突击式的、行政命令式的美术创作与宣传活动,导致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违背了艺术创作的客观规律,在艺术质量上差强人意。[104]刘志翼等认为,壁画以鲜明的政治立场和虔诚的态度为农村“大跃进”作了天真的图解。[105]他们还认为,壁画运动对美术教育界的浮夸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06]王先岳认为,新壁画运动是政治运动狂热催生的产物,是一场弘扬民族民间艺术、反驳民族虚无主义、解构专业话语权威的大众化艺术运动,同时也助长了艺术的公式化、概念化和庸俗化。[17]吴继金研究了当时的政治宣传画,认为其内容是“跃进画”,形式是“夸张法”,数量是“浮夸风”。[108]另外,吴继金还考察了美术“大跃进”的发生、发展及其带来的消极后果。[109]《美术学报》刊发了1958年有关广东美术“大跃进”的史料。[110]徐秋梅等记述了文艺“大跃进”的兴起、文艺“跃进”指标的制定、文艺“卫星”的升起及其结束情况。[111]阿庚回忆了“大跃进”中在河北上山下乡演出带有“左”的色彩的剧目的情况。[112]
四、对“大跃进”中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大跃进”运动是在全国范围内将各种资源重新进行配置的一次尝试。无论是调整中央和地方关系还是大办公共食堂的举措,或是造成环境破坏和人口非正常死亡的结果,都可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审视。
关于“大跃进”时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任志江认为其关系的演进和变迁,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收与放的两个极端,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进程。[113]张俊华考察了“大跃进”中“全国一盘棋”的思想,认为“大跃进”成于体制下放,终于体制上收。[114]他还对“大跃进”中的协作和经济协作区进行了研究,认为由于特殊环境的影响及对协作的错误理解,协作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115]此外,张森奉记述了“大跃进”时和朋友跑单帮的遭遇。[116]
邓进考察了“大跃进”时期的人力资源配置问题,认为毛泽东试图利用中国丰富的劳动力来替代资本短缺,但却没有创造出应有的效益。[117]张继久认为,农业“大跃进”本质上是对传统农业生产要素重新配置的过程,由于在此过程中存在大量不合理的做法,加之受农村生产关系急于过渡和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农业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118]
公共食堂是“大跃进”时期对资源进行重新配置的一次尝试。罗平汉对全国大办公共食堂始末作了详细的梳理。[119]李海滨等以徐水县为例,分析了农村公共食堂兴起的原因。[120]李春峰介绍了河北省公共食堂一哄而起、难以为继、强行恢复、彻底终结的情况。[121]他还对公共食堂的研究现状作了概述。[122]游国立等也综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公共食堂研究取得的成果、研究的主要问题、进展及不足等。[123]关于公共食堂的解散,罗平汉认为,朱德是党内较早提出解散公共食堂的领导人,并为其最终解散起了重要作用。[124]刘秉勋[125]、王健[126]、易奇勋[127]考察了毛泽东决定解散公共食堂的情况,认为韶山群众向毛泽东反应对公共食堂的意见是毛泽东最终解散食堂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党国英考察了河北省一个村庄的公共食堂运转情况。[128]周庆元[129]、亦斌[130]、陈海川[131]、马觐伯[132]、田家声[133]等都回忆了在农村吃公共食堂的情况。
关于“大跃进”引起的环境和人口问题,张同乐等考察了“大跃进”中因过度深翻土地、捕杀麻雀、“大炼钢铁”等造成河北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134]李若建研究了“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135]辛逸等考察了困难时期城乡饥荒差异性原因。[136]周律等以湖南溆浦县为例考察了人口非正常死亡情况,认为这与僵化的政治结构密切相关。[137]
五、对“大跃进”中浮夸风、“共产风”问题的研究
“大跃进”中,浮夸风、“共产风”盛行。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研究。
浮夸风的兴起与当时的大环境,如新闻宣传鼓动有很大关系。王惠超总结了报纸宣扬“三面红旗”的教训,并以主要篇幅介绍了“大跃进”中浮夸风情况。[138]罗平汉认为,大放农业高产“卫星”,与反保守、倡冒进的大环境有关。[139]袁鹰回忆了在“大跃进”中写浮夸文章的情况。[140]靖鸣等对广西环江县“水稻亩产十三万斤”的浮夸新闻作了考证。[141]当时有领导抵制浮夸风,田中玉记述了王震叫停“卫星田”的事迹。[142]
对于导致浮夸风泛滥的原因,赵付科等认为反右运动严重抑止了民主,窒息了不同声音的发表;忽视和不尊重科学,违背客观规律,造成了唯意志论的大肆张扬;统计工作为政治服务,无法可依,导致了统计数据的严重失真;不健全的干部制度,促使了大批干部造假;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盛行,偏离了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143]李若建认为,高指标是当时官员造假的基础。[144]许庆贺认为,“大跃进”前夕中国民众蕴藏着建设社会主义的急切心情、经济建设上对“反冒进”批判不断升级、思想领域中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盛行以及地方权力极度膨胀等,这些社会环境直接催生或助长了浮夸风的泛滥。[145]秦程节等认为,毛泽东对浮夸风的产生和蔓延起了鼓舞、推动作用,后来毛泽东开始纠偏,但未能从根本上纠正。[146]罗平汉分析了毛泽东对待粮食高产“卫星”的态度。[147]浮夸风的盛行,与信息失真、决策失误有直接关系,高心湛探究了“大跃进”时期的信息状况及其失真原因。[148]罗平汉对比了1958年8月上旬和10月中下旬毛泽东进行的两次农村调查。[149]
“五风”中以“共产风”危害最大。于继增记述了“徐水共产主义”试点轰轰烈烈兴起与草草收场的始末。[150]梁志远记述了安徽省亳县焦城区五马公社在“大跃进”刮“五风”所造成的严重后果。[151]周学雍记述了很多基层干群抵制“五风”的事例。[152]向海英分析了“共产风”产生的历史根源,认为与中国传统“大同”、“小康”、“均等”等思想有密切关系。[153]周震探讨了纠正“共产风”问题,认为直到八届十中全会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才从制度上堵住了共产风的根源。[154]
六、对“大跃进”中社会心理的研究
探讨“大跃进”运动社会心理成因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姚桂荣对该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155]有学者对这一时期国人的心理问题进行了研究。王立红等认为,批判反冒进以后,存在着全国性急于求成、自负、从众的社会心理。[156]冯庆芳分析了群众从众心理产生的原因。[157]王红等认为,“大跃进”中搞群众运动,排斥知识和知识分子,以及表现出的集体无意识,都反映出运动具有民粹主义的典型特征。[158]李军强考察了“大跃进”时期党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认为没能够切实解决好农民的思想问题。[159]冯鑫总结了这一时期社会心理发展和变化的原因:一是最高决策层的引领和导向作用;二是新闻媒体的宣传鼓动作用;三是意识形态的灌输教育作用;四是传统文化心理定势的影响;五是群体心理规律性驱动。[160]
除了分析群众的社会心理外,有学者还分析了毛泽东的心理。胡文超认为,赶超世界强国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思想根源;矛盾的不平衡性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认识根源。[161]王光银认为这一时期浪漫主义的空想与落后的现实的矛盾,坚持科学与破除迷信打破权威的矛盾,坚持民主与推行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的矛盾,纠正已经出现的“左”倾错误与肯定“三面红旗”正确性的矛盾交织,困扰着毛泽东,直接影响“大跃进”的进程。[162]
有学者还提出并论证“大跃进思维”这一概念及其内涵。张梦阳认为,“大跃进思维”具有悬空思维、表象思维、单向思维和专制思维的特征。[163]葛荃提出并考察了“大跃进思维定式”这一论题。他认为,“大跃进思维定式”指的是以这场运动为典型显现的一种模式化思维。[164]
七、对“大跃进”中人物与群体的研究
毛泽东与“大跃进”的关系,是学者们一直研究的重要问题。麦阳等以纪实的手法,叙述了毛泽东在1958年的活动,其中发动“大跃进”是一个重要方面。[165]杨俊考察了毛泽东重视钢铁产量思想的发展演变阶段,认为毛泽东在实践中不断调整钢铁产量指标使之越来越符合实际。[166]王小京考察了毛泽东的风险意识,认为在“大跃进”期间毛泽东的风险意识始终未放弃过,其抵御风险的意识被落实到了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制定上,在纠“左”的实践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为国民经济调整打下了思想基础。[167]张凤翱分析了“大跃进”前后毛泽东认识存在二重性的原因:一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长期性缺乏思想准备;二是党内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被破坏。[168]戚义明对1958年11月到1961年6月毛泽东在全党范围内四次提倡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学政治经济学的情况进行了考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在党内率先觉察并开始纠正“大跃进”中的错误所作的努力和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的探索。[169]宋海儆等考察了“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对经济建设的探索情况,认为这些探索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宝贵经验。[170]另外,宋海儆等还考察了这一时期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反思与实践。[171]另外,张家康等记述了庐山会议前毛泽东努力纠“左”的情况。[172]俞国记述了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言行及会议转向的情况。[173]唐正芒考察了1959年上半年毛泽东写的六篇《党内通信》内容,肯定了其对纠正“大跃进”错误所起的指导意义。[174]曾自记述了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毛泽东和读书小组成员在杭州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情况,反映出在“大跃进”挫折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进行的新思考。[175]
对于刘少奇与“大跃进”的关系,张志永认为,在酝酿和发动“大跃进”时期,刘少奇积极拥护和倡导;北戴河会议后,逐渐产生了疑虑;庐山会议后,对运动失望并最终放弃。[176]何立波也记述了刘少奇的认识转变过程。[177]
施亚利认为,“大跃进”中朱德强调按客观规律办事、主张实行“按劳分配”、强调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重要性,是最早认识“大跃进”错误的领导人之一。[178]董志凯研究了陈云在“大跃进”中对基本建设的贡献:对基本建设流程提出了“有先有后,轻重结合,先后结合”的观点;提出了“基本建设中要注重质量,防止片面节约”、“基本建设投资要保证重点和支援农业”等观点。[179]文苑也记述了陈云倡导理性、科学、求实精神的事迹。[180]
另外,高敬增等考察了“大跃进”发动到庐山会议期间李先念从紧跟到疑虑、反思的心路历程。[181]王素莉考察了张闻天在庐山会议后“新跃进”到调整时期实事求是的可贵言行。[182]李安峰探析了李富春对“大跃进”的曲折认识过程。[183]叶介甫记述了贺龙反对不顾质量的军工产品“跃进”做法。[184]穆欣记述了林枫对“大跃进”中教育改革的看法,及为纠正错误倾向、进行调整而做的贡献。[185]何立波考察了吴芝圃在河南“大跃进”中的表现。[186]李锐记述了“大跃进”期间他给毛泽东三次上书的情况。[187]陈彬记述了李达在哲学“大跃进”中的表现,指出李达支持过“大跃进”,但又对反常现象作了独立思考。[188]此外,阎明复等记述了赫鲁晓夫对“大跃进”由“沉默”到公开评论、批评的过程,认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斗争,成为后来两党、两国关系日益恶化以致最后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189]
“大跃进”是一场全民参加的运动,有学者注重研究其中群体的行为表现。佟屏亚考察了农业“大跃进”中农业科学家的表现,认为农业“大跃进”给几代科研人员烙下深刻的负面印痕。[190]郭省娟考察了“大跃进”中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的情况。[191]刘维芳认为,“大跃进”既写下了妇女思想解放史的新篇章,也表现了忽视妇女生理特点和缺乏对妇女的劳动保护、造成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以及妇女界在“妇女是否解放”等理论问题上的困惑和迷茫等不利影响。[192]台湾学者钟延麟认为军方在运动窒碍难行之时愈益吃重的驰援角色,以及其在克服本身困境上展现的能力、方式以及累计的声望,皆为军方在60年代地位的上扬和“文革”时对政治的全面参与,埋下了重要伏笔。[193]卢晖临探讨了基层乡村干部在“放卫星”中扮演的角色。[194]
八、对“大跃进”教训的探究
为发挥史学研究资政育人的功能,学者们注重总结“大跃进”的教训。孙晨纲认为,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抓经济建设,严重违背生产规律和实事求是的原则。[195]伊胜利认为,“大跃进”破坏了国民经济的正常比例协调关系;造成了资金、物力和资源的极大浪费;导致市场萧条、物价上涨、人民生活水平下降。[196]王也扬认为,“大跃进”的教训,根本的一条就是把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当作阶级斗争。[197]龚莹认为,“大跃进”的教训是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方针、政策,必须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相适应;必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尊重科学知识,遵循客观规律。[198]宋词认为如何对权力进行制约值得引起高度重视。[199]李杏指出,从科学发展观来看,“大跃进”违背了全面协调发展的要求,违背了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违背了以人为本的要求,也不符合科学正确政绩观的要求。[200]周汝柏通过回顾“大跃进”,反衬“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理念的正确。[201]李安峰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角度,审视“大跃进”教训,认为一要构筑和谐的干群关系,二要推进产业结构内部的和谐发展,三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202]黄一龙探讨了“大跃进”中非理智精神状态。[203]
关于“大跃进”与走自己的路(摆脱苏联模式)的关系问题,邢和明认为,“大跃进”想摆脱苏联模式,但并未成功。[204]林志友认为“大跃进”的基本思路,就是把战争中大搞群众运动的工作方法运用到经济建设上来。[205]郑谦认为,“大跃进”期间经历了对苏联模式认同——突破——复归的过程。[206]他还分析了解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及体制条件三个基本要素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207]林蕴晖指出,从“大跃进”时起,就播下了毛泽东与刘少奇对建设社会主义不同意见分歧的种子,直至“文革”发生。[208]
“大跃进”失误的造成,与工作方法和宣传动员方式有很大关系,这方面的教训也是深刻的。师连枝总结了当时错误的工作方法。[209]张昭国等认为,“大跃进”中领导人和地方干部并不缺乏调查研究,但这种调查是走马观花的考察,缺乏典型和一般相结合,缺乏民主气氛。[210]王佩连认为,在“大跃进”前期,政治动员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正效用功能;在中后期负效用占有绝对支配地位。[211]董芹总结了“大跃进”中《人民日报》传媒功能缺失造成的不良后果。[212]另外,双传学探讨了如何从方法论的角度科学总结“大跃进”的教训,认为只有把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统一起来,把价值判断建立在事实判断基础之上,把具体的认识和行为放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之中,才能形成科学的结论,把“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变成财富。[213]
对“大跃进”教训的总结,既有从研究中得出的理论思考,也有从亲历中得出的体验。李凯源记述了公社食堂要吃猴头、燕窝,评教授以产粮多少为标准等诸多事例,[214]乐朋记述了“红领巾钢铁厂”、沼气山药等事件,[215]刘武权回忆了“大跃进”所经历的大炼钢铁、吃公共食堂等方面的体验。[216]资中筠[217]、唐那碧[218]通过亲身体验,强调“民以食为天”是党和政府必须高度重视的大事。
九、对近年来“大跃进”研究的简评
通过对近年来“大跃进”研究成果的综述,可以看出一些新的研究动向。第一,“大跃进”研究仍是国史、党史研究的一个热点。本文搜集的有关研究论文(220余篇)数量大大超过写作《十年来“大跃进”研究若干问题综述》时搜集的论文(130多篇)数量,由此可见“大跃进”研究之热。第二,研究范围不断拓宽,研究人员逐渐多元化。范围不断拓宽主要表现在自然科学史研究的加入,如孙烈的《“大跃进”时期“蚂蚁啃骨头”的机械加工方法的兴起》[59];对社会政策的关注,如大卫·M·兰普顿的《“大跃进”时期的医疗政策》[63];对特殊群体的研究,如钟延麟的《大跃进运动中的军方活动》[193]等;比较方法的运用,如廖胜平的《“大跃进”与“洋冒进”之比较》,从社会经济环境、社会心理、造成的后果等方面比较了两者的异同。[219]研究人员多元化体现在现在“大跃进”研究的参与者既有史学工作者,也有各行业的专家;既有海内外学者,也有历史当事人。第三,当事人亲历的回忆材料明显增多。这些回忆材料对拓展“大跃进”研究范围,无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当然,如何科学地辨别使用这些材料也是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有学者提出把口述史研究方法与“大跃进”研究有机结合起来[220],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方向。
“大跃进”研究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是值得肯定的,但也要看到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第一,对有关问题的研究(如对“大跃进”发动原因的研究)结论大同小异,没有突破前人的认识;第二,有的观点难以服人,如有人认为:力图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积极探索本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促使“大跃进”运动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7]笔者认为,摆脱苏联模式,积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一定必然导致“大跃进”的发生。第三,有的基本史实、概念存在常识性错误。如有人认为,“大跃进”这场极“左”思潮的运动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的总演习”;认为“林彪、康生等人阴险地利用错误路线为其反革命服务,……使大跃进扩大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认为“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要求反冒进,但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最后刘少奇、邓小平等不得不向毛泽东道歉,承认错误,反冒进的正义潮流被压下去了”;“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基本上停止了大跃进运动”。[221]这样的研究,语言表述非客观,史实存在明显错误,观点也很成问题。还有人认为,毛泽东将反冒进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进行批判。[9]据笔者所知,毛泽东并未扣修正主义的帽子。有的研究从政党合法性的角度来审视“大跃进”的发动,角度虽新,但未必符合历史实际。[23]
由此可见,对“大跃进”研究还有很多工作可做,既有运用新材料、探索新领域、获得新成果的可能,也有对现有成果进行分析评价、去粗取精、消化吸收的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