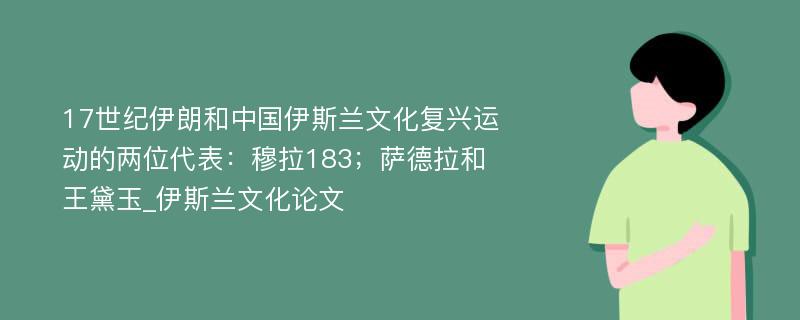
十七世纪伊朗与中国伊斯兰文化复兴运动的两位代表人物:穆拉#183;萨德拉与王岱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论文,伊朗论文,两位论文,中国论文,代表人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7世纪,什叶派教义学家、圣训学家与哲学家穆拉·萨德拉(1571~1640)成为伊朗伊斯兰文化复兴运动的杰出代表。几乎在同一时期,在中国也涌现出这样一位伊斯兰文化复兴运动的先驱者王岱舆(约1580~1660)。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王岱舆的研究日渐深入,发表了为数众多的论文。同时,随着中国与伊朗文化交流的发展,穆拉·萨德拉的经历和思想成就,也越来越多地被介绍给中国人民。近年来在中国出版的关于穆拉·萨德拉中文著作就有:1983年金宜久等编写的《什叶派》一书第6章“什叶派神学家及其著述”,1990 年金宜久主编的《伊斯兰教史》第3章“伊斯兰教在波斯和中亚”,1992 年马吉德·法赫里著的《伊斯兰哲学史》中文版第10章“关于穆拉·萨德拉及其继承者”,1994年宛耀宾主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中的辞条,1995年陈中耀著《阿拉伯哲学》第1章第2节“照明主义哲学”,至于论文尚未统计在内。随着中国人对穆拉·萨德拉了解的增多,他们对这样一件事很有兴趣:穆拉·萨德拉和他的同时代人王岱舆有什么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他们的学术思想有没有一定程度的联系?本篇文章的宗旨就准备对穆拉·萨德拉和王岱舆作这样的比较研究。
一、穆拉·萨德拉与王岱舆生活经历中的相同之处与区别
作为两位深受世人尊敬的伊斯兰学者,穆拉·萨德拉和王岱舆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但他们所以取得了成功,必然拥有适合的社会环境,丰富的人生阅历,崇高的献身精神和出色的工作成果,在这些方面,他们的经历有许多共同之处。
第一,他们同样出生于虔诚的穆斯林世家。穆拉·萨德拉全名穆拉·萨德鲁丁·穆罕默德·伊本·易卜拉欣,生于设拉子,出身于什叶派学者世家,幼承家学,接受了传统的伊斯兰教育。他一生7 次到麦加朝觐,并在最后一次朝觐回来时归真于巴士拉。王岱舆的祖先是西域穆斯林,14世纪中叶来中国从事天文工作,在南京定居300年。 他自幼开始接受伊斯兰宗教教育,曾拜经学大师胡登洲的弟子马君实为老师,在马君实指导下学完了穆斯林必修课程。
第二,他们同样在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中接受了历史使命。16世纪初,伊斯玛仪在伊朗建立沙法维王朝,为了巩固新的政权,沙法维王朝宣布什叶派为国教,并且开始了什叶派教义的宣传活动。到穆拉·萨德拉出生后,阿巴斯时期(1557~1629)的沙法维王朝更加重视扶植什叶派的力量,资助科学和文化。先是米尔·达马德承担起复兴哲学和教义学的历史使命。此后,穆拉·萨德拉把苏赫拉瓦迪的思想纳入自己的巨大学说体系之中,在苏赫拉瓦迪思想熏陶下登上历史舞台,但穆拉·萨德拉著作的重要性最终超过了他的前辈。王岱舆也生活在明朝灭亡清朝兴起的社会大转折时期。当时处于人口少数的穆斯林思想动荡,信仰受到冲击,为了唤醒穆斯林的宗教觉悟,营造适合穆斯林生存发展的思想氛围,调解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关系,改善中国穆斯林的社会地位,王岱舆担负起在中国宣传和解释伊斯兰教教义和哲学思想的重要责任。
第三,他们同样具有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创造精神。穆拉·萨德拉青年时期到伊斯法罕师从什叶派著名长老巴哈尔丁·阿米里和米尔·达马德学习。经过努力钻研,他通晓经训、教义、教法、哲学、文学,掌握了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取得了在法尔斯省省长创办的宗教学校教学的教师证书。虽然他遭到一些人的责难,但是仍然顽强地深入研究哲学理论,利用广泛的资料,提出了许多有创造性的观点。王岱舆长大后在熟读伊斯兰教典籍的基础上,一方面吸收国外优秀文化,另一方面攻读中国历史与哲学著作,被誉为通晓多种宗教(学通四教)与学问的学者(回儒)。他排除阻力,率先在中国用汉文来介绍和解释伊斯兰教教义及哲学理论,开创了用汉文著述伊斯兰教经典的新形式。
第四,他们同样具有足以自豪的代表性著作。穆拉·萨德拉除了对苏赫拉瓦迪、伊本·西那等人的著作作了大量的注释外,还写作了许多论文,如《复活》等。但引起世人关注的是他的主要著作《旅程》。有人认为这一著作是他许多论文的综合,也是他对自己哲学思想的总结,描写灵魂从创造到最高实在,再通过实在到另一种实在,然后从实在回到创造的四个旅程。王岱舆一生也留下了三部著作,但最著名的是《正教真诠》和《清真大学》,前者对伊斯兰教教义进行全面的介绍和解释,后者则讲解穆斯林在认主学方面必须具备的宗教知识。
由于伊朗和中国国情不同,他们二人的经历也有较大的差别。主要表现在穆拉·萨德拉生活在一个穆斯林占绝大多数的伊斯兰教国家,可以接触深厚的伊斯兰传统文化,可以获得著名伊斯兰学者的指导,可以获得政府的鼓励与支持,因此他有条件研究深奥的哲学理论,并进行系统的阐述;而王岱舆则生活在一个穆斯林占少数的中国,面对宗教知识缺乏的中国穆斯林兄弟,他的主要工作是向他们宣传和普及伊斯兰教教义,没有更多的精力去做系统深入的哲学研究。
虽然上述两人的经历有共同之处也有区别,但他们都深深地赢得后人的尊敬。穆拉·萨德拉曾被称作“伊斯法罕学派最重要的代表”、“17世纪伊朗文化复兴运动的代表人物和领导者”、“伊朗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伊斯兰最后一批百科全书式作家之一”。他的著作,至今仍是许多大学的宗教学科被讲授的重要教材。王岱舆则被称作“中国伊斯兰教学术研究的先驱者”、“中国回族穆斯林中最负盛名的四大伊斯兰学者的首席代表”。他“发人之所未发,言人之所不敢言”,伊斯兰教的光辉,因他而在中国得到昭著。
二、穆拉·萨德拉的哲学理论在王岱舆著作中得到反映
穆拉·萨德拉的哲学思想体系十分丰富,他的一些重要观点,不仅在伊朗什叶派穆斯林中广为传颂,也为其他国家的穆斯林学者所接受。在王岱舆的汉文伊斯兰教译著中,就表达了和穆拉·萨德拉相类似的一些思想。我们可以举出下面一些例子:
第一,穆拉·萨德拉作为伊斯法罕神秘哲学光照学派的代表,认为世界(包括自然和人类)是真主之光照的创造物,真主之光是万物的永恒根源,真主之光也是无限的,世界万物及其变化是真主无限光照的各种表现。有的学者把这种真主之光称作“真光”、“余光”。光在伊斯兰教中,被认为是真主的99种美名(或德性)之一。《古兰经》第24章第35节就谕示:“真主是天地的光明,他的光明象一座灯台,那座灯台上有一盏明灯,那盏明灯在一个玻璃罩里,那个玻璃罩仿佛一颗灿烂的明星,用吉祥的橄榄油燃着那盏明灯;它不是东方的,也不是西方的,它的油,即使没有点火也几乎发光——光上加光——真主引导他所意欲者走向他的光明”。在王岱舆著作中,也有对真主之光的阐述,如他在《清真大学》中说:“因其独一至尊,原有无对,自发普慈,要为万物,敕命有无,任其自便,此际始分体用。因其发于原有,是为能有,谓之余光。”他还说:“真主与创造宇宙万物的那种巨大力量之间的关系,好比光明的本体与光辉之间的关系(真—之于能有,比如光之本体与光之光辉)。”他在《正教真诠》一书中又写道:“未始有物之初,真主要造天仙神鬼,乾坤万物,自止一之余光显了万圣之元首即穆罕默德”,接着,他认为真主又用“灵觉之余光”,依次造化了列圣、贤人、良人、常人、迷人、天仙。随后,又用这种余光造化出神鬼、鱼鸟走兽、日月星辰、土水火风及草木金石。
第二,穆拉·萨德拉在解释自然界的起源时,认为“自然”是一切事物的实质,也是一切运动的原因,因此自然是永恒存在的真主与它所创造的物体之间的永久链节。这种思想,在王岱舆的著作也可以找到,不过王岱舆把这种“自然”称作“第一个数”(数一),认为“数一”是生成天地万物的种子,并且是天地万物的最高代理。他在《正教真诠》中提出:“诸所谓一,乃天地万物之一粒种子,并是数一。真一乃是数一之主也”,“真一同于数一,数一同于万有,不在万有,则万有消亡;若同于万有,则囿有万有矣”)。他在《清真大学》书中又认为:“所说的‘第一个数’,就是从真主这个根源生发出万般不同的事物,也就是真主巨大能力的出发点(所谓数一者,乃一本万殊,即以能有之首端)。”“第一个数”创造了万事万物,完全是秉承真主的命令而担任了“代理”的作用,是真主预设安排了一切物体的产生而且规划了万物发展的道理(名虽各异,其理本一。自能有之中承命而显)。
第三,穆拉·萨德拉认为人的灵魂借助精神升华,才能达到接近安拉。他在《旅程》这部巨著中提到了哲学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理论哲学,另一部分是能够使灵魂达到完美的实践哲学。实践哲学的目的是通过种种精神修炼的方式,使人的灵魂上升到崇高的境界,才能实现人主合一。王岱舆在《清真大学》一书中,也有类似的观点:“人们所说的最高级认识,就是竭力克服片面循私的个人意见,彻底回归到光明品德的源头,舍弃自己的私念,体会认识真主的独一无偶(所谓续认者,克尽偏私自见,复全明德之源,由无己而体认真主)。”他还在此书中说:“人通过视觉听觉产生的智慧和功能,虽然能做到深究事物的道理,但不能透彻了解真主的本来,必须把自己的私念与躯体完全舍弃不顾,才能了解最根本的机密,把自己的精神得到提升,使自己的所有见解符合真主的教导(因人之视听知能,虽能穷理格物,不能了彻原有,必须已有全熔,始得妙明,顿显本然动静,自此方明,然后知以主知,见以主见,言以主言)”。
第四,穆拉·萨德拉认为,真主之光赋予人以先天的灵知是最高层次的知识形式,它弥补人们后天产生的缺陷,使人成为“完人”。王岱舆也有相同的观点,但是他把这种真主之光赋予的灵知称为“真赐”,也就是“伊玛尼”。他在《正教真诠》一书中写道:“真主赐予的启示,在创造天地之前就预设安排为品行高超之人的为人准则,又规定其作为人们行事处世的要求。所以获得了真主赐予的伊玛尼,然后人们才能获得真正的见解(真赐先天地而为人极之宗师,处世法而为正道之枢纽。所以有真赐,然后有真知)”。
三、一种假设:王岱舆可能直接阅读过穆拉·萨德拉的著作
王岱舆的著作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和穆拉·萨德拉的思想十分相近,这不大可能是一种纯粹的巧合,而可能在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必然的联系。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地假设,穆拉·萨德拉的著作曾经和许多波斯文献一样传播到中国,从而被重视学习外来文化的王岱舆所读到,并且把穆拉·萨德拉的某些见解运用到自己的著作中去。
为了证明上面的假设有可能存在,我们列举一些事实作为依据:
第一,中国与伊朗之间一直有经济文化往来,早在公元前二世纪时中国与波斯就有了交往,以后,两国官方与民间的往来从来没有中断过。在成吉思汗时期,在大不里士坦和北京之间,每年都有定期的商队来往。中国的明代(1367~1644)时期,设拉子撒马尔罕和麦加的商队定期来到甘肃,有的还前往北京进谒明朝皇帝。比如1524年设拉子和邻近32个部落就向北京派出了使者,带去了马匹和特产,并从中国带回了磁器和丝绸。
第二,大量波斯语书籍曾流传到中国,王岱舆肯定见过不少波斯文伊斯兰教典籍,当然有可能从中见到穆拉·萨德拉的名著。如中国伊斯兰学者刘智(1660—1730)在他开列的67本参考书目中,就包括5 本波斯文著作。中国回族穆斯林经堂教育所使用的13种主要课本中,波斯文著作就有6种,包括波斯语语法著作、伊斯兰哲理诗集、 讲人生修养的哲学著作、圣训注释、神学著作。
第三,王岱舆的祖籍是西域,并世代从事天文历法事业,极有可能来自天文技术发达的波斯一带,因此他可能从小懂得一些波斯语。此外,中国穆斯林中一直袭用大量的波斯语词汇,包括对五次礼拜和星期的称谓,王岱舆必然会懂得这方面的词汇。同时,王岱舆从小在清真寺学习过伊斯兰教知识,当时一定要先掌握阿拉伯语、波斯语才能读懂原著。因此,根据王岱舆所处的社会环境,他应该具有较高的波斯语水平,有能力读懂穆拉·萨德拉的著作。
第四,王岱舆在1644年前后离开家乡前往人文荟萃的北京,当时穆拉·萨德拉虽已逝世,但他的著作早已闻名,王岱舆作为比他年轻的学者,在时间上有可能读到从波斯传播过来的穆拉·萨德拉的著作。同时,北京当时是中国穆斯林的著名聚居地区,文化信息交流比较方便,王岱舆来北京的目的之一是追求学问,因此,他找到一本穆拉·萨德拉的著作,并认真地加以阅读也许是十分自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