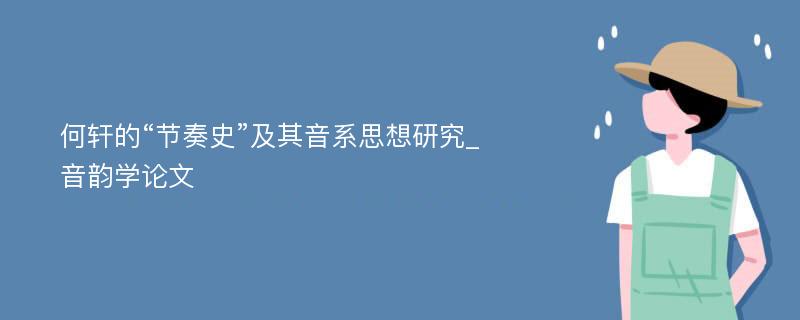
何萱《韵史》及其音韵学思想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音韵学论文,思想论文,韵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清何萱《韵史》欲综文字形音义三者一以贯之,与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同时而著书旨趣相近。限于时代,何萱对音韵学的理解可以补苴之处颇多。然何氏不墨守《说文》成规,在体例上“参用今音条贯”,对等韵、反切切及声调之发展均有其独特之见解。其音韵学体系并非元明以来之北音系统,而是“根源于泰兴方音”,因而对研究十八世纪之通泰方言及其历史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何萱 韵史 通泰方言
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清代是古音学、说文之学的鼎盛时期。名家辈出,述作蜂起。自顾炎武首破前人羁绊,离析唐韵,到段玉裁分古韵为十七部,本末分明,体例谨严,古韵分部大局遂定,在当时影响极大。研究《说文》的著作如林,知名的不下百种,段注自不必说,四大家之一的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亦无人不晓。而被罗常培先生誉为“体大功深,未尝不令人心折”、与朱书有同等价值的何萱《韵史》却鲜为人知。鉴于此,笔者拟对这部“沉埋里闾”百余年的音韵学、训诂学巨著的音韵体系作一系统的剖析。
一
何萱(1774—1841),字石闾,道光岁贡。由于家道中落,徙如皋石庄,蹴居汤氏废圃,老屋数椽。读书课子,寒暑不辍。馆谷所余,悉以置书,至数千卷。晚年归泰兴故里,更是摈弃举业,闭门撰述。所著《红露馆文集》十卷、《诗集》一卷《琴法指掌》二卷均未刊行。《韵史》八十卷几经周折,至一个世纪后,一九三六年才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共十四册,罗常培先生为之作跋。该书欲综文字的形音义三者而一以贯之。收字以《说文》为本,佐以《广韵》、《玉篇》,以前者为正编,后者为副编。每字之下,博引群书,详注出处,最后加按语,补其疏略,从音韵以治文字训诂,非奉旨虚应故事之作。
何氏完全打乱说文原本的编排次序,吸收时人的研究成果,“仿段懋堂先生十七部之说而扩之”,按十七部排列:一该部、二高部、三鸠部、四沟部、五姑部、六緪部、七金部、八甘部、九江部、十冈部、十一耕部、十二絙部、十三跟部、十四干部、十五几部、十六街部、十七柯部。平声71,上声66,去声70,入声74,共282韵。平上去入依传统四声相配,其中第一、六、九部同入,第五、十部同入,第十一、十二、十三部同入,第十四、十五部同入,第十六、十七部同入,实得252韵。显然,何萱将段氏的“异平同入”说稍加改造,即予采纳。每部皆列四呼表;四声表;音读,即音节表,该音韵地位无字者划圆圈;韵目,即同音字表,这为我们考察何萱的音韵学思想提供了条件。每呼以二十一字母次第为列字次第,同纽之中又以形近、谐声系联,不泥旧次。与同时代的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何其相似!朱书基本上承用段氏十七部,兼采戴震、王念孙诸家说,以古韵十八部为纲领,同部的按不同的谐声声旁分别排列。何朱二氏年相若(何氏大朱氏十四岁),同时闭门造出两辆相仿的“车”,实是有清一代音学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产物。打破东汉以来近十八个世纪的说文研究传统,代之以古韵部统领,已成为一种需要和时尚——段注附一谐声表而字未列,江沅谱其字而训诂不备,何朱二氏备其训诂,于是两书并成,可谓珠联壁合。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何书未谋付梓恐是主要原因,此二书的待遇却有天壤之别,正如罗常培先生在跋尾中所言:“并石闾同时而著书旨趣相近者,则有朱允倩《说文通训定声》。其与《韵史》当为闭门暗合,未尝丽泽相取也。以两书体例观之,朱则纯以谐声相统,何乃参用今音条贯,识见虽异,而功力实同。然百年以来,朱书则传诵士林,《韵史》则沉埋里闾,斯亦事之不平者已!”
二
清儒研究古音,精力集中在先秦韵语的整理,而对声母的研究,成绩远在韵母之下。谐声、假借等材料,只用作古韵语的佐证,所以他们的成就也就是古韵分部。在所谓古音之学鼎盛的时代,谈到古代声母问题的,唯钱大昕一人而已。声母系统远无定论,何氏不得不自己审定字母,认为见溪群疑等三十六母,有复有漏,未为精善,“非敷泥娘,皆一误为二,复矣。见端等母有阴无阳,明微等母有阳无阴,漏矣。知彻澄三母之字古音同于端透定,今音同于照穿床,不必另出,另出亦复矣。……故愚之《韵史》定为二十一字母,平声有阴阳,则以二十一为四十二也,旧时言字母者或云九音,或云七音,今细审之,只须言四音耳。见溪影晓喉音也(见溪不必言牙音),端透泥来舌音也(来不必言半舌),照穿日审精清疑心正齿齿头音也(日不必言半齿,疑乃鼻音,非牙音也,附齿头差近),帮滂明非微唇音也(重唇三轻唇二)。萱之所拟二十一字母曰见起影晓,端透乃赉,照穿耳审,井净我信,滂并命匪未。”对此,罗常培先生认为:何说本于潘耒《类音》,观其二十一字母,又本于方密之说而别出影母,是元明以来北音之声系。乍一看来,此评介有根有据,顺理成章,实则未道出症结所在。鲁国尧先生一语中的——“何氏的音韵学体系根源于泰兴方音”。
泰兴如皋方言今有声母二十一,古全浊上、浊去遇塞音,塞擦音不论平仄一律变送气清音,与何氏所记完全一致。何萱审定的二十一字母下,都注明和传统三十六母的对应关系,这种关系一直延续至今:见见、起溪群、影影喻、晓晓匣、短端、透透定、乃泥娘、赉来、照照知、助穿彻床澄、耳日、审审禅、井精、净清从、我疑、信心邪、谤邦、并滂并、命明、匪非敷奉、未微。
古人按发音部位,将声母分为唇、牙、舌、齿、喉、半舌、半齿等类,有五音、七音、九声之说。疑母——历来名曰牙音,而有相当的音韵学修养的何氏认为不妥,“其鼻音一字,前人未尝言及,萱以臆推求而得之。曾咨于深韵学者,不吾非也。缘向来误认疑母为牙音,故不知此音之出于鼻耳。”“疑乃鼻音、非牙音也”。由此可以看出何氏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和坚实的审音功夫。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语言学工作者特别是语音学者,无人不知古疑母是舌根鼻音——不必声学仪器显示,单凭一般的辨音能力就足够了。而于十八、十九世纪,时贤精于辨韵而疏于别声的情况下,在声母系统这一片“处女田野”上辛勤耕耘,有所开拓,发前人之未所发,何萱功不可没!
三
“音之有清浊也,为平声言之也。阴平为清,阳平为浊,不容淆也。上去声,各只一音,无阴阳清浊之可言也。强欲言之,亦姑曰上去相为阴阳而已,旧乃有上浊最浊之说,非自扰与?……入声每字皆含阴阳二声,视水土之轻重而判,轻则清矣,其出音也送之不足而为阴;重则浊矣,其出音也送之足而为阳。《韵史》内入声阴阳合并者此也。”何氏对声调的理解,显然是承元明以来五声之说,他的“四”声表实际包含五声: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明方密之《通雅·切韵声原》定为开、承、转、纵、合、(按即阴平、阳平、上、去、入)五声,清李汝珍《李氏音鉴》卷一:“敢问五声何谓也?对曰:阴阳上去入也。”何萱感觉到“入声每字皆含阴阳二声”而且明确指出二者的差别:阴入出音送之不足,阳入出音送之足。这是就发声的高度、响度而言,是对两个入声调值高低的具体描述:阴入调值低于阳入。这正是今通泰方言(按即江淮方言泰如片)的重大重点之一。汉语方言入声分阴阳的,只有通泰、赣、客及山西的几个方言点阴入调值低于阳入。鲁国尧先生把它作为一个重要依据,第一个提出了通泰、赣客方言同源的学说,为通泰方言史的研究打开了新的局面。
今通泰方言入声的喉塞韵尾显著,阴入调值为4,阳入调值为5。例如:设4——舌5,发4——伐5,八4——拔5,得4——特5,约4——药5,式4——食5,切4——侄5,两者壁垒分明。而何萱则囿于传统,拘执五声之说,不顾当时的语言事实,过而合之。这也是时代的局限。古无去声说、四声一贯说、五声说皆有一定影响,时人莫衷一是,而入声问题最令人头疼,江永在《四声切韵表·凡例》中也叹:“韵学谈及入声尤难,而入声之说最多岐,未有能细辨等列,细寻脉络,归于一说者也。”
四
等韵学与悉昙学关系密切,在西方语言学理论传入中国以前,一直是音韵家辨析音理、分析汉语语音系统的主要工具,在古音研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因其门法繁琐,深奥玄妙,又与术数学、易学等等多所牵联,后人颇觉晦涩。何氏为人实在,不喜空谈,对等韵之说嗤之以鼻。“等韵之说,蒙向所不晓,私以为可无用。故《韵史》只用四呼。开口合口两呼其音侈,侈则洪矣,齐齿撮口两呼其音敛,敛则纤矣。举洪纤而等摄尖团在其中,不知后人何以必言等韵也。”“萱雅不信等韵之说,平生未尝齿及也。有举此为问者,皆以不知谢之。既而问不已,余乃取四呼之法配此四等,用饷学者,殊觉易明而便于用也”。我们来看看何氏是如何配法的。“一等即开口呼,二等即合口呼,三等即齐齿呼,四等即撮口呼。”明清以来的四呼是中古两呼四等的发展,它们之间有联系,然而却不是一回事。粗略地说,中古的开口一二等是后来的开口呼,开口三四等是后来的齐齿呼,合口一二等是后来的合口呼,合口三四等是后来的撮撮呼。何氏误解等呼,不知二者交错为用之旨,因而出现了“以肴为合,以幽为撮,于宋于清,皆未为是”的情况。清代及其后持同样观点者大有人在,张文炜《音括》将开口作为一等,齐齿为二等,合口为三等,撮口为四等。此仅一例而已。
反切门法繁多,何萱只提及音和与类隔一对。音和指反切上字与被切字声母相同,下字与被切字韵母相同。类隔指反切上字与被切字发音部位相同,发音方法不同。这是语音的历时变化所致,与音和相比,多转了一个弯,加之等韵家对类隔的解释各有不同,元刘鉴的《门法玉钥匙》指“重唇轻唇、舌头舌上、齿头正齿三音中清浊者”,明释真空《直指玉钥匙门法》指“端透定泥一四为切,韵逢二、三,便切知等字”与《广韵》附记及《切韵指掌图·原序》不合。因此实用主义者何萱力避类隔,在书中全用音和。“后世必不能无,而有绝不可解者,则类隔是也。反切以双声为用,故曰音和;类隔则不和矣,何反切之有!反切上一字既用一定之母,其下一字纵使本韵本呼无字可用,亦岂无术以处此,而强立不甚通之法以惑后人乎?”、“切字之法,定在音和,而迂人乃有类隔之说。近世以来复淆以等韵之说,又纷以七音九音之说。夫欲使人真识字而转岐其途径。本近也而求诸远,本易也而求诸难。何异舍康庄大道而欲乘车入鼠穴乎?”何氏认为类隔是不甚通之法,运用它等于去钻老鼠洞,对之深恶痛绝。殊不知,钱大昕正是藉此考明古今音读的变化,他发现“伏羲”即“疱羲”、“扶服”即“匍匐”、“纷”读“豳”、“繁”念“婆”,得出了“古无轻唇”的结论;因为“直”读“特”、“竹”读“笃”等证明古无舌上音;以“舟”读如“雕”、“至”读如“疐”、“专”读如“端”,创“古人多舌音,后代多变齿音,不独知彻澄三母为然”之说。受钱氏启发和影响,章太炎有“古音娘日二母归泥说”,曾运乾有“喻三归匣”说,在古声母研究领域有所创获。而现代历史语言学家多人,也正是利用假借、谐声、异文等手段,研究上古音,考察汉语同某些周边语言、境外语言的亲属关系。
总括以上,何氏虽自称闭门造车,其音韵学体系可以补苴的地方亦多,如声准方音,韵拟周秦。然其不墨守说文成规,大胆改革编排方式,旁罗传注笺疏,以明字义正借之辨,改定字母,具体描写调值等等,为方音史、汉语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体现了时代风尚。他的务实精神,他的潜科学的审音方法,可以给治训诂、音韵者以很多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