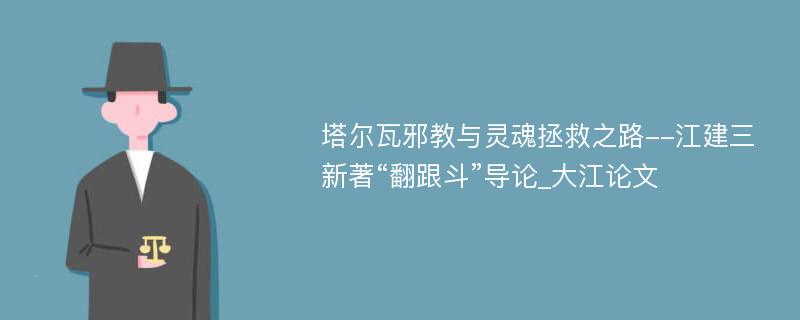
挞伐邪教,探索灵魂拯救之路——介绍大江健三郎的新作《空翻筋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空翻论文,筋斗论文,之路论文,邪教论文,新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空翻筋斗》,是亚洲惟一健在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宣布挂笔并沉寂5年之后的复出之作。应该说,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新作没有理由不受瞩目,所以去年6 月中旬《空翻筋斗》由讲谈社出版后在日本引起强大的冲击波,也便不足为奇了。先有签名售书的空前盛况,后有各大报章及文学艺术类杂志的书评推介, 再加上日本国家电视台NHK专访的呼应,使得该书在6至8 月间各大书店畅销榜上的排名一路攀升,由第10位9位直至第3位2位, 为日渐气短的纯文学书籍大大地提了一气。然而,除去这些客观的和炒作的因素,我们自然应该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作品本身,并从中探察作家的所思所想。这也正是介绍大江健三郎这部新作的旨趣所在。
这是一部上下两册、计约八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作者本人在封皮护带的宣传语中说:“深如渊薮的世纪末黑暗,激荡不休、渴求希望的年轻灵魂。但愿我能真实而痛畅地记下它们。”不错,这部小说正是从世纪末人们精神空虚、希望得到灵魂拯救的普遍态势着眼,通过描写一个新兴宗教团体的再生与幻灭来思考、探索现代日本人的灵魂拯救之路的。作家给它起了个一语多关的名字:《空翻筋斗》。
小说写的是一个小型宗教团体,它的主要领导人是两个年届四十的中年男子,一个被称作“师傅”,一个被唤作“向导”,师傅能在冥想世界中幻视到神的影像,并发出梦呓般的话语,而向导则负责将师傅的所视所云用常人的语言整理记录下来。这个宗教团体曾经有过一次溃灭的经历。在教团日益壮大之时,团体内部的一个高学历精英集团“技师团”为让社会感受“忏悔”,计划夺取核电站,策动恐怖事件,师傅和向导见局面难以控制,决定与警方、公安、传媒联手,阻止这一危险的发生。二人在电视上发表讲话,声称“以前在教团里跟信徒们宣讲的那些都是胡诌八扯,都是恶作剧”。这样,技师团的恐怖活动流于未遂,教团本身也趋于解散。教团首领自行放弃自己原创的教义,无异于杀了自己的回马枪。这一事件被传媒戏称为“空翻筋斗”,师傅和向导也像是在空中翻了一个大跟斗,落回原地,又跌进深不见底的地狱。小说取名“空翻筋斗”,缘由可见一斑。这也应了中国的一句俗语:题好一半文。
然而,小说是从距此次“空翻筋斗”事件10年以后、师傅和向导过着隐居般生活的东京开始写起的(从故事的中盘写起,在断续的倒叙中将故事向高潮推进,是大江健三郎一贯的叙事风格)。此时,二人正准备重整旗鼓再创新教,他们的麾下也正有一些人怀着对神的各自不同的希求聚拢而来。一是被称作舞者的年轻女子,她是个很出色的舞蹈演员,极具献身精神,专门在师傅和向导身边料理二人起居。一是奉财团法人会长之命来二人的事务所做文秘工作的青年荻。还有育雄和木津。育雄还是个少年的时候,参加过一次塑料片艺术制品大赛,木津当时是评委之一。在木津眼里,育雄实在是个令人难忘的奇怪少年——少女舞者撞到育雄,他偌大的作品一角插进少女舞者的裙裾时,他竟置比赛于不顾,把自己的精心之作捣了个稀巴烂。不久,木津就去了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后在美国的大学里谋到了终身教授职位,在一次回日本休假的时候,找到了让他魂牵梦萦的少年,并查知当年的少女舞者正在一家宗教事务所里供职。在他的促成下,三人得以再会。育雄自称听到过神的声音,神曾敦促他行动,要他“干起来!”可这声音后来就怎么也听不到了。育雄是祈望在与师傅的接触中重新听到神的声音,而木津却是要追随成了他同性恋伙伴的育雄,才决定进入师傅的宗教事务所的。
这样,这6个人构成了新教团的核心力量, 紧锣密鼓地筹划起重建教团的各类事宜。然而有一天,向导去说动原教团激进派“技师团”的时候,却被激进派关了禁闭,并被殴打致死。这是一个契机。师傅在向导的追悼会上郑重宣布重建教团。于是教团在一度“空翻”的教首带领下走上了复活再生之路。小说的上卷就在这里截止。
小说的下卷在一干人马移居四国山村的礼拜堂中开始。四国的森林村庄,一直都是大江健三郎的乌托邦、理想乡,他笔下的众多人物都是在这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寻找自我,开始新生活,实现再生的。那么这一次呢?
原教团解散后,仍有一些信徒组织各自为战继续活动,现在,它们——如静冈境内的“静女”小组,以宗教法人形式将原教团维持下来的关西支部,“技师团”——合入到了师傅的新教团中来,四国山间的村民们也在少年组织“童子之萤”领头人阿义的影响下和教团发生着联系,而渐渐地,教团的活动也和四国山村神话般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得到了奇妙的融合。这样,教团作为“新人的教会”在四国山间神话般的世界中获得了新生,小说也在这里进入了高潮——“新人的教会”召开全国大会,定名为“夏日集会”。作为此次大型活动的重要内容,师傅要在集会上进行说教,当初教团“燃烧的绿树”创始人点燃的巨树也要在集会上燃尽。然而,师傅在激昂的说教之后,却将自己也投入了火海,自焚而死。
大江健三郎在接受日本《读卖新闻》记者采访时说:“原本是打算只用5行左右来写师傅的死并结束全篇的, 但是在回家为母亲做一周忌的途中,我突然觉得应该写一写活下来的人们,这种想法非常强烈,促使我又写了终章。在这一章里体现了我新的出发点,我想我是超越了败北主义的。”可见,高潮之后的终章在全篇中举足轻重。那么终章又为我们展现了怎样的结局呢?
离开教团的荻回到教团所在地,知道为获得拯救而试图集体自杀的妇女们吃下的是被师傅偷换的泻药而不是青酸毒,结果一群人在树林里拉了个天昏地暗;木津已死,死前并未显露出对死的任何惧怕;育雄虽与舞者一起经营着教团,但是将经营与信仰分开来考虑的,而且育雄自己也打消了再次倾听神的声音的念头。最后,小说以育雄的这样一句话结束了全篇:“教会嘛,要我说,就是打造人灵魂的地方。”
这么平铺直叙地介绍小说的梗概恐怕是很惹作家生气的,因为作家的精心布局、巧妙设计都得不到展现。而大江健三郎在《空翻筋斗》中所表现出的技法的娴熟老到绝对是世界级水准。小说虽然用的是第三人称,但设定了木津和荻两个视点来推进全篇。通过这两个外围人物的眼睛耳朵和嘴巴,读者被引入到师傅的非凡世界,引入到四国乡间的神话世界。值得一提的是,作家在小说前段遍布悬念,把读者牢牢抓住,但进入中间段之后却有意放慢了故事发展进程,在让主人公们就认识和信仰问题作了大量思辨之后,又猛鼓一口气,三下五除二就把故事推向了高潮。正是在这松松紧紧收收放放之中,小说尽展魅力,加之作家一改过去冗长晦涩的翻译调文体,使小说更加便于阅读,这或许是这部新作广受青睐的原因吧。
大江健三郎是个追求“同时代性”的作家,他对现今日本社会有着极其敏锐的洞察力,也有着极其强烈的危机意识,这使得他的文学与时代紧密相关。稍早一点的《政治少年之死》描写了暗杀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的右翼少年;后来的《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等中期作品无一不涉及了1960年的反日美安保条约的斗争情况,《洪水涌上我灵魂》所描写的事件与几乎同时期发生的连合赤军事件极为相似;及至描写新兴宗教幻灭的超大长篇《燃烧的绿树》就更叫绝,在小说前两部出版、第三部正在创作的过程中,日本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奥姆真理教事件,等于是大江的小说走在了真实事件之前,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尽管大江曾宣布自己在完成《燃烧的绿树》后将停止小说写作,潜心哲学特别是斯宾诺莎研究,但面对日本社会的现状,他无论如何也是无法袖手旁观的。在大江复出一事上,1996年大江的挚友、音乐家武满彻的病故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武满彻的告别仪式上,大江发誓:“我要写一部长篇小说奉献给你,我必以一个小说家的身份恭立于你的灵前。”但是,不难设想,如果没有奥姆真理教事件的冲击,这部要献在武满灵前的小说也许就是别的什么题材,《空翻筋斗》扉页上“献给永恒的武满彻”的献词就也许会出现在别的什么新作的扉页上。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奥姆事件的冲击,促动了《空翻筋斗》的执笔和完成,也促动了大江的复出。在《空翻筋斗》里,大江除借主人公之口不止一次地提及奥姆真理教之外,还安排了一个师傅“空翻筋斗”后仍固守信仰的女信徒组织,使人不能不联想到麻原教祖被捕后依旧继续开展活动的奥姆真理教的新动向。“奥姆悲剧决不可以重演。为此,有必要在领导者和信徒双方的心中驱动想象力”。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采访时,大江如是说。这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读《空翻筋斗》的角度。
现在的大江健三郎几乎要被称作“宗教作家”了——“拯救”,“信仰”、“祈祷”、“神”之类的主题占了他小说的很大一部分。而《空翻筋斗》乍一看去也是一部宗教色彩极浓的小说——“忏悔”、“再生”、“奇迹”、“升天”一类字眼随处可见,《圣经·旧约》的《约拿书》、现代威尔士宗教诗人R.S.托马斯·曼、哲学家克尔恺郭尔等的引用也挂在主人公们的嘴边。的确,这部小说的中心内容是写一个一度放弃教义丢下信徒的教祖如何再度树立自己的信仰并再建教团的,而且围绕这个中心内容也的确牵涉到信仰和神的问题,然而追随者们在与师傅探讨宗教问题的过程中发现,师傅的宗教思想却是别有洞天,他其实真正追求的是一种无限远离宗教的宗教。小说中画家木津是惟一一个对神没有任何希求的人,他最终领悟到他自己所做的事情就是“一个站在宗教外面的人把一个站在宗教内部的人神圣化”,所以他才会在临终时感悟地说出:“育雄,你还是非要听到神的声音不可吗?……我呀,就是没有神,也会说rejoice(喜悦)的啊!还要什么神的声音哪,人, 还是自由些好啊!”在这里,“没有神”是十分重要的。就是说,一部看似以宗教为主题的小说,最后的落脚点却落在了“无神”、“无神的宗教”、“无神者的灵魂拯救”上,这的确是这部作品的大胆之处。师傅最后也死掉了,他的死与其说是殉教,不如说是与神的断绝。能够拯救人类的,不是什么神,而是人类自己。因为神没有自由,没有自由的东西与人之间不存在可以共生的时间和场所,也就无法给有自由的人以拯救,倒是没有神的世界里,人类更容易找到真正自由的根据。也就是说,没有神的宗教或许才有可能使人获得拯救,而这种大胆设想的根基则是人的想象力。小说在“新人”们要创造一个没有神也能打造人灵魂的地方的设定中结束,寓意恐怕就在于此。
大江曾就麻原教祖对待审判的态度做过两种设想:“一是在法庭上说‘我没有错!我敢作敢当!我接受死刑!’一是承认‘我错了,我失败了,我要放弃教团,希望信徒们也重新做人’,我在小说里写的是第二种方案,就是领导者‘转向’后的事情。可在法庭上,麻原的精神仿佛逃到了别的什么层面上,在他那里,审判并不成立。由于没有现实的答案出现,所以信徒们就又拾起了他们的信仰。这才是最危险的兆头!”(《达·芬奇》,1999年8月号,大江访谈)。 《空翻筋斗》正是在奥姆信徒们重建教团、世界各地邪教组织盛行、1999年7 月诺斯托拉达姆斯预言的世界末日迫近的大环境中问世的,它敏锐而大胆地传达着作家的这样一个理念:人的想象力才是超神的,才是自由的。而这,或许才是《空翻筋斗》赢得众多读者的根本所在。
大江健三郎去年6月12 日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采访时说:“我想反思包括自己在内的实现了‘转向’的日本人如何再生、新的日本人从何处产生的问题。”这里所谓的转向,指放弃原来的主义主张,改变立场方向。读大学的时候,大江就对诸如战争时期社会主义者的转向,战后天皇退神为人、发表“人间宣言”之类的转向问题产生了极大兴趣。他一直想就战后日本建设民主国家所不能回避的日本人的“转向”问题写一部小说,《空翻筋斗》的创作终于使大江实现了这个40年的夙愿(1999年6月21日,《读卖新闻》)。如此看来, 《空翻筋斗》这一题目本身的寓意就既深且广了。
大江一直认为文学应该是一种呼唤。奥姆真理教吸引了大批生活毫无忧虑的年轻信徒,他们在物质上能获得极大的满足,却仍然觉得缺点儿什么,觉得有什么不对劲,正因为如此,奥姆真理教才有可能乘虚而入,适时地满足了年轻人的精神需求,于是它便成了这些年轻人的绝对信仰。但是取缔奥姆真理教问题就解决了么?从奥姆那里寻找精神满足的年轻人向何处去?正是这些“激荡不休、渴求希望的年轻灵魂”让大江无法释怀,所以他才在探求“无神而获得拯救”的道路时呼唤“新人”的出现,呼唤“新人”的想象力,呼唤“新人”的行动。因为他认为,“如果年轻人不去做与‘旧人’想法相异的‘新人’,那么当今日本的痛苦现状将无法得以解脱”(《达·芬奇》,1999年8月号, 大江访谈)。无疑,《空翻筋斗》就是大江呼唤的载体。
“对文学也好,对政治构想也好,我是希望自己活着就能开垦耕耘一些荒芜地才好。”(大江健三郎《最后的小说》,1988)大江的这番话在《空翻筋斗》中又一次得到了印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