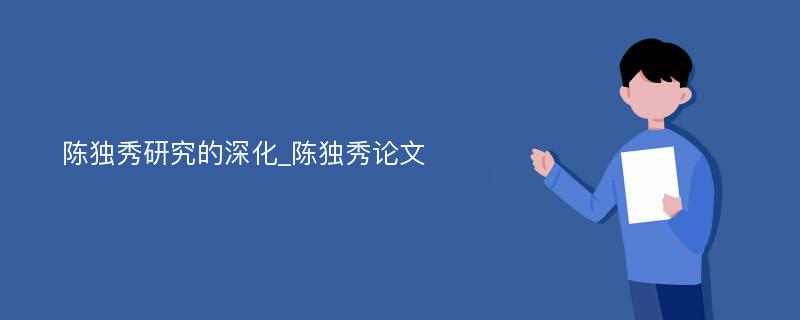
论陈独秀研究之深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陈独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一名对中国革命做出过巨大贡献,又有着种种是非的历史人物,陈独秀在中国现代史的舞台上具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对于这样一位历史人物进行客观而公正的评价与研究也一直是史学界关注的热点。但在八十年代以前,人们对陈独秀的研究基本上沿袭共产国际对他的批判,一直没能有所突破;进入八十年代后,特别是在九十年代,由于各种人为禁锢的解除,史学界对陈独秀研究的思维更加多样、视角更为广阔、途径更加宽泛,从而取得的成果也更加丰硕,对陈独秀的研究也随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本人才疏力浅,无法在宏观上对陈独秀进行整体的评判,只能挂一漏万,就我所知对一些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陈独秀研究现状的考察
长期以来,对陈独秀的研究一直局限于众所周知的几个方面:二次革命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问题、托派反党问题、对大革命失败应负责任问题等等。由于曾经存在的某种原因,人们对陈独秀的研究一直不能够做到真正的客观、公允。因而随着资料的进一步挖掘,考证的进一步深化,思考的进一步深入,原先的许多定论现在看来大都显得有些仓促与单薄。伴随着研究氛围的进一步宽松,研究成果的进一步积累与深化,有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的思维方式与论证手段对原先的诸多结论提出质疑与挑战,对陈独秀的评价也从“一边倒”呈现出“百花齐放”。
例如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传统的观点一直是陈独秀轻视工农,看重资产阶级的力量,导致右倾投降主义的产生,主动放弃了对革命的领导权特别是武装斗争的领导权,从而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但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有学者指出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确实有一段时间曾经看不起工农,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他的态度开始转变。又如“二次革命论”,原先的观点一直是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是其右倾投降主义的总根源,也是大革命失败的主因,但近期有人指出首先陈独秀有无“二次革命论”的思想值得进一步商榷,陈独秀在1923年左右形成的一系列观点只能认为是在革命领导权问题上的一些模糊认识,而在中共四大前后已经放弃,所以不能说陈已形成系统的“二次革命论”思想。退一步说即使他已形成“二次革命论”思想,也要对之进行全面的考察和认识,而不能断章取义只就某一句话就断定他是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的领导权。单就“二次革命论”而言,其中也不乏可圈可点之处。
再如关于托洛斯基主义者的问题,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后参与并领导了托派小集团是无可置疑的事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的深化,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他参与托派的动因提出了质疑,指出陈参与托派集团并不是因为二人有共同的思想和理论基础,而相当程度上只是因为感激托洛斯基在共产国际“六大”和其他一些公开场合为他在大革命失败责任上的辩解和开托。正因如此,才导致陈与托派组织后来公开的分道扬镳。
上述这些例证只是说明在陈独秀的研究过程中已经开始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但就整体而言,对陈独秀的研究还比较粗糙,还缺乏权威性、系统性与开拓性。
纵观近年来的陈独秀研究,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1)研究领域有所拓新。传统的陈独秀研究,其着眼点集中于他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研究、二次革命论思想扬弃、家长制问题批判、参与并组织托派问题动因考察等若干方面。近年来的陈独秀研究则突破了这一传统范畴,开始涉足一些新兴领域,例如他的经济思想研究、晚年民主政治思想初探、中西文化观的对比研究、阶级分析初论、抗战主张述评以及他与共产国际关系研究等。正是这些拓新,冲破了原有定式的束缚,使陈独秀研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也是这些拓新,使得人们得以拨开历史的迷雾,全面、立体、客观地对陈独秀加以评析。
在传统领域里,争鸣日益强烈,一些名家的定论遭受越来越强有力的挑战。例如在关于陈独秀在党内实行家长制问题研究上,张静如在《从陈独秀的封建家长制作风谈起》一文中坚持传统的观点认为:“陈独秀为人自信,常以长辈和先知者自居,他指导青年是认真的,却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做事很积极,但喜独断。”“为了推行他那条路线,他完全实行封建家长制统治,凡是与他不一致的认识、意见,他一律排斥,不予考虑,并且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采取组织措施……陈独秀既不要群众,也不要集体领导,唯我独尊,就完全破坏了党的建党原则。”(注:转引自赵国忠:《90年代陈独秀研究的新进展》,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1999年第2期,第142页。)有的学者对家长制说提出了严重挑战,指出:一、我们党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对此,陈独秀起了关键作用;二、陈独秀注意吸收新鲜血液进入领导层,不搞论资排辈;三、陈独秀允许并鼓励发表不同意见,从不搞一言堂;四、从客观上看,从党的建立到大革命失败短短6年中,我们党召开过5次全国代表大会,5次中央扩大会议,5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开得生动活泼,这一时期是我党历史上民主最充分的一个时期,毛泽东生前也承认这一点(注:张巨浩、林小兵:《关于陈独秀实行家长制统治问题的质疑》,《学术交流》,1992年第1期。)
在新涉足领域,有许多学者的角度之新、立意之深,让人不由赞叹。例如有人从中西文化的对比研究中发现“他那些对中国文化的尖刻批评,以致激烈的自我咒骂,都是‘怒其不争’的表现”。“在这激烈的言词后面,可以发现一颗忧国忧民、救亡图存的心在痛楚中震颤。”(注:张同乐:《论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的中西文化观》,《史学月刊》,1998年第2期。)对抗战的言论行动加以全面的考究分析,得出结论:第一,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审视,陈独秀始终坚持抗战的主张,保持了爱国主义者的晚节,但他曾对抗战的前途发生悲观,某些主张甚至出现倒退,违背了历史的发展规律,是错误的;第二,从理论信仰的角度来审视,陈独秀则始终没有放弃对科学、民主、社会主义的追求。(注:史远香:《陈独秀抗战主张述评》,《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2期。)因而从另一方面论证了“就是在生命最后15年里,在旧中国的泥潭里,陈独秀依然趔趄向前,尽管步履蹒跚,……但他毕竟没有当叛徒,没有做汉奸,没有做出丝毫有损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伟大国格和伟大人格的事来”。(注:胡绳玉:《中共党史人物传不能没有陈独秀》,《学术月刊》,1991年第11期。)
在这些有关陈独秀的最新研究成果里,有一点需特别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就是近年来的研究论著均有一个很大特点,那就是不论对陈独秀持肯定态度也好,否定态度也罢,但相较先前的一些研究成果而言都相对客观而冷静,审慎而公正。
(2)研究方法和手段有所更新。近年来,陈独秀的研究范围不但极大地得以拓展,从单纯的政治文化领域拓延到军事、教育、历史观、人性论、宗教观和文学价值论;另一方面在研究方法和手段上也不断推陈出新、有所突破。
传统的考证式研究虽然依旧在陈独秀研究甚或在整个历史学研究中占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与地位,因为历史学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它的首要任务就是察往而鉴今,资政而育人,而察往的首要途径就是对文献资料的考证与研究,离开了对文献的分析与研究,历史学就失去了存在之本,历史学研究也就成了无源之水。但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决不仅此一样,还有系统性研究、体系性研究、整体性研究、断代性研究、解析性研究、比较性研究、对比性研究、专题性研究、综合性研究等等。因而近期对陈独秀的研究方法日益呈现多样性,而又以比较性研究为主。通过比较,拓展了对陈独秀的研究范围,加深了对际独秀的思想认识,因而丰满了这一人物形象,使展现在人们面前的陈独秀更加真实可信。正是这些运用不同论证方法,采取不同思维方式的研究作品的出现,使人们能够从另一个角度去透视陈独秀的不同侧面,从而为我们准确把握在那个特定历史环境之下的陈独秀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参照系。
还必须指出的是,在研究方式和方法的多样性的同时,人们的态度愈来愈客观,力求用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把这样一位特定的历史人物放在他所处的具体时代中去,通过分析错综复杂的历史环境,展现他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从而揭示他内心思想的真实性,评估其理论的内涵和处延的正确性。
(3)独立的研究体系尚未建构完毕。从最一般意义讲,任何一个学术体系的建立,必须要有它自己特定的研究目的、对象、方法、内容、结构、意义和大量的专业人员。具体到陈独秀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将之划分为一个独立的研究体系的时机虽已成熟,但它却还远未达到一个成为一个专门学科的标准。它的体系框架尚未有人专门从理论上加以高度的概括与规范,研究它的目的与意义也未有人给以权威的阐释与界定,最重要的是到现在为止,还缺乏一批甘于寂寞、勇于奉献的学术人员,更不用说未来的学术梯队建设。
对陈独秀的研究与评价关系到如何正确看待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如何正确评价党在大革命时期的是非功过,怎样评析中国共产党在张扬个性的过程中所体现的对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扬弃。如果对陈独秀的研究我们不能正确看待与处理,我们就无法正视那一段历史,我们对党的历史的解说就缺乏一定的信服力。陈独秀作为一代伟人,他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民主的启蒙、文化的撞击,他带给我们的是以他为代表的那整整一个不能也不应该忘怀的时代。如果缺少他的存在,整个的中国近现代史就显得黯然而无光。
因而对陈独秀研究来说,构建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是必不可少而又迫在眉睫的事情。我们这一代学人应责无旁贷地担负起这一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
二、陈独秀研究展望
陈独秀研究从原先的禁锢式批判发展到今天的实证式评析,可以说已向前迈进了关键的一大步。但陈独秀研究的领域还有待于进一步拓展,视角还有待于进一步延伸,方法还有待于进一步更新,争论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思维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散。站在新千年的起点展望未来21世纪陈独秀研究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大胆作出如下预测:
(一)陈独秀研究体系必将最终建立并不断完善。作为一门学术体系的建立,当它适应了时代的发展并有了产生的基本基础之后,那么它的建立和完善就是一件必然的事情。陈独秀研究发展到今天,它的内容、对象、意义等已逐渐明晰,它的体系架构也已初现端倪、呼之欲出。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必将有更多的人认识到陈独秀研究的现实与历史意义,因而也必将有更多的人投入到它的建设者队伍之中去,所以预计将来的学术梯队建设也不成问题。这样,作为一门独立的学术体系的产生与存在,陈独秀研究都已完全具备最基本的条件。作为一门社会科学,陈独秀研究不可避免也要受到社会政治环境、学术氛围的制约与影响,随着思想解放的进展,我们的学术研究在党性与科学性的高度统一下,已基本不存在所谓的“禁区”问题,学术自由在当今中国已是不争的事实,因而亦不会有政治方面的顾虑与限制。
但我们也必须牢记,我们所有的研究都必须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进行,我们进行陈独秀研究,是为了更好地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这是我们所有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大前提。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我们既不能因伟人有过错误就抹杀其一切功绩,也不能因为是伟人就文过饰非,这是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的原则和准绳。只有这样,才能从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吸取经验教训,汲取丰富营养,更好地促进我们国家与民族的发展。未来的陈独秀研究也必须遵循这些指导原则,方才能有长足发展,成就其为一门真正成熟的科学。
(二)对陈独秀的评价与定位有所抬升。随着研究的深入,陈独秀研究涉及的领域将更为广泛,研究的方式与手段将更为宽广。以往的陈独秀研究大都从各个层面、各个角度、各个切入点对他分期分阶段地进行考察与探究,从而作出一定的剖析与评价。而今后的研究将更加倾向于整体性、系统性,从而对陈独秀的评价也将更为客观而科学。研究的着眼点也将从单纯地个人考察转为把他放在他所处时代和国际共运的大背景下进行综合解析与探索;研究的触角也将延伸到国外;研究的借鉴也将更多地考虑到全面、公正、客观;研究的力度也将适当加大;研究的手段也将更多地引进同时代最新的研究方式,从而使这门学科将更多地带有边缘性、时代性、前沿性的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国内外对陈独秀研究的不断深化,研究资料的进一步增多,对陈有利的论据也越来越多,从而使他对大革命失败的责任现在看来是越来越少。“1927年共产党的失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它无疑是由一系列复杂原因造成的,并非是陈独秀某种错误的直接结果。”(注:杨奎松:《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兼谈陈独秀的“右倾”问题》,《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总观陈独秀的一生,他的历史功绩是主要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确实有点像俄国革命中的普列汉诺夫。我们应当宣传陈独秀的历史功绩,确认他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永远纪念他,正如苏联人民永远纪念普列汉诺夫那样。”(注:廖盖隆:《陈独秀的评价问题》,见王学勤编著《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史学界存在的‘陈言皆右’、‘陈言必批’的习惯性做法,既是对陈独秀思想的歪曲,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幼年历史的否定。”(注:蔡文杰:《重评中共四大前陈独秀的阶级分析》,《安徽史学》,1998年第4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基本可以断言,未来的陈独秀评价问题肯定会有某种变动,他在中共党史中的地位将有某种程度的抬升。
综上所述,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对陈独秀的研究已取得了不少突破性的进展,许多长期以来存有争议性的问题在研究的不断深化中得以取得共识,人们对陈独秀的观感也越来越清晰,但任务远没有完成,陈独秀研究的领域还有待于进一步拓展,研究的视角有待于进一步延伸,研究的成果有待于进一步深化。总而言之,在我们面前还有诸多的未知领域,我们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