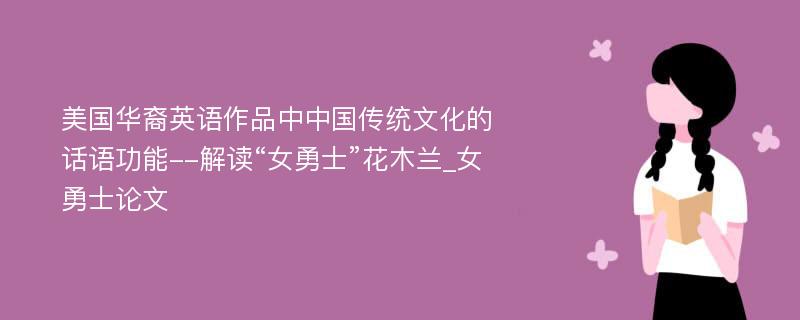
中国传统文化在美国华人英语作品中的话语功能——解读《女勇士》——花木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花木兰论文,英语论文,勇士论文,中国传统文化论文,话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华裔女作家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1940—)的《女勇士》(Woman Worrier,1976年)在美国当代文学占有重要位置, 是倍受关注的多元文化中的经典著作。本文以该书为例,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分析该书在美国倍受欢迎的种种原因,重点讨论该作品大量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符码,创造性地改写中国古老传说“花木兰”故事的现象,试图揭示美国华裔英语作家借助“误读”策略,树立自己既相异于中国文化又有别于美国文化的独特文化身份。
美国华裔英语文学走过了一段漫长的道路。一个半世纪前,美国西部淘金热吸引了最早的一批来自中国广东的数百名华人移民,他们把美国加洲称作金山,满怀希望挣够一笔积蓄和返家的路费便衣锦归乡。然而,他们所面临的是极端的种族歧视和残酷的生存条件,上万华人“苦力”对修建美国横跨东西海岸铁路长达6 年艰苦卓绝的贡献也丝毫没有改变他们的处境,1882年的“排华法案”将美国国门向中国移民关闭了60年之久,他们中大多数永久而孤单地留在了唐人街单身汉居住屋。直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移民仍处在美国社会的最低层,华人是劳资矛盾和经济危机的替罪羊和牺牲品,美国公众媒介充斥了丑化歪曲的华人形象,华人没有合法权益, 更谈不上用文字言说和捍卫自己的自由。 尽管100 余年前就出现了华人英语写作(最早的一本华人英语自传发表于1887年),(注:Amy Ling,"Reading Her / stories
Against His/stories in Early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in AmericanRealism and the Canon,edited by Tom Quirk and Gay Scharnhorst,p.72,New York: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1994.)但是,华人写作直到本世纪下半叶才引起了美国社会的广泛关注,甚至进入主流文化。本世纪60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兴起带动了整个美国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大变动,“女权运动”,“反越战”,“少数族权益”等运动随之而来,呈现一种反传统、反权威、文化寻根的思潮。华裔英语文学也从此开始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发展。
自60年代末,70年代初崛起的美国华裔英语文学,不仅在数量上比前70年有了成倍的增长(截止1990 年, 华人出版的英语文学作品约有70多本,在此之前,从50年代追溯到上世纪末的1887年,总共才有30余本,其中仅50年代就占了二分之一),(注: AmyLing, "Asian AmericanLiterature","Chinese American Woman Writers:TheTradition Behind Maxine Hong Kingston",in Redefining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edited by A.C.V.Brown Rueff and Jerry
W.Ward.Jr,New York: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1990.)而且在题材和类型上也有了很大的突破。50年代以前,约半数以上的华人英语作品是自传;到了五六十年代,除了一本诗歌,少量自传和纪实性作品外, (注:Amy Ling, "AsianAmerican Literature","Chinese American Woman Writers: The
Tradition Behind Maxine Hong Kingston", in Redefining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edited by A.C.V.Brown Rueff and Jerry W.Ward.Jr,New York: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1990.)小说成了主要的表现形式;从70年代开始,美国华人英语文学呈现五彩缤纷的局面,小说、诗歌、戏剧,及其它非小说类文体都有了长足发展,同时也涌现出了一批才华出众、锐意革新并拥有广泛读者市场的华裔英语作家。华裔小说作家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1940—)、谭恩美(Amy Tan,1952 —)和剧作家黄哲龙( David Henry Hwang,1957—)的名字在美国读者中,以及学术界、文艺界可谓无人不晓,他们的成名作《女勇士》(Woman Worrier,1976年)、 《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1989年)、《蝴蝶君》( M.Butterfly,1988年)深受美国大众的喜爱,后两部作品还被拍成电影。其中,汤亭亭的《女勇士》更是被盛赞为振兴美国华裔文学的开山力作。
汤亭亭属于第二代华人移民。她的父系家族很早就有人移民美国,她父亲年青时从广东去了纽约,她母亲到了40岁才得以去美国和丈夫团聚。汤亭亭1940年出生于加洲中部的斯托克顿,60年代的美国学潮中断了她在伯克莱大学的研究生学业,此后移居夏威夷教书谋生,10年后(1976年)发表了她的处女作《女勇士》。该书的出版可谓一鸣惊人,美国各大报刊好评如潮,(注: Amy
Ling, Between Worlds-Women Writers of Chinese Ancestry,Pergamon Press.Inc.1990,p.130.)并作为当年非小说类最佳书目而获得“全国图书批评界奖”。(注:Maxine
HongKingston, The Woman Warrior:Memories of AGirlhood Among Ghosts,New York:Vintage International,1989.)迄今为止,《女勇士》不仅接连不断获得奖项和拥有广阔的读者市场,而且赢得了美国学术界主流文化的认可。截止1991年,该书在美国的销售量高达450,000册,(注:Frank
Chin, "Come All Ye AsianAmerican Writers of the Real and the Fake",in The Big AllEEEEE-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merican Literature,edited by Jeffery Paul Chan,Frank Chin, Lawson Fusaolnada and Shawn Wong,New York:A Meridian Book,1991,pp.3-29.)《女勇士》自出版后就一直是美国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讨论最多的亚裔文本。美国语言学会计划发行一本《汤亭亭的〈女勇士〉教学入门》,把《女勇士》同乔叟、但丁、莎士比亚的作品并列在一起。(注: Amy Ling, "LiteratureandArt
in Comparative and Global Perspectives ' Emerging Canons' of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Art", in Asian Americans Comparative and Global Perspectives,edited by Shirley Hune,Hyung-chan Kim,Stephen S.Fugita and Amy Ling,Pullman,Washington: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1,p.192.)美国亚裔文学评论家Sau- LingCynthia Wong在一篇讨论该书的文章中这样说,“《女勇士》可能是美国当代亚裔文学中最有名的一部作品,……有良好的出版销量,它是许多大学课程规定的阅读书目,该书的某些章节是美国文学选集多元文化色彩的必选项目。可以说,许多读者或许对美国亚裔文学毫无所知,但却阅读过汤亭亭的《女勇士》。”(注: Sau- Ling Cynthia Wong,"Autography as Guided Chinatown Tour? Maxine Hong Kingston's The Woman Warrior and the Chinese- American Autobiographical Controversy",in Multicultural Autobiography:American Lives,edited by James Robert Payne, R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1992,pp.248-275.)
这本书在美国白人读者中反响热烈,同时也在美国华裔文学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论争,辩论双方的焦点在于:《女勇士》是一部沿袭了“东方话语”式的自传体写作,还是一部手法创新的小说;作者改写“花木兰”的传说,是否为了讨好白人而对中国文化遗产进行亵渎。一时间两军对垒,旗鼓相当。支持派认为,少数族作家并非少数族社区群体历史的代言人,要求华裔后代保持源远流长的传统市场是反历史的,《女勇士》不是自传,作者在尝试用一种新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什么是华裔美国人?”的思考, 改写“花木兰”是其艺术使然。 (注:
Sau-Ling Cynthia Wong, "Autography as Guided Chinatown Tour? Maxine Hong Kingston's The Woman Warrior and the
Chinese-American Autobiographical Controversy", inMulticultural Autobiography:American Lives,edited by James Robert Payne,Rnoxville: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1992,pp.248-275.)持反对意见的一派大都是男性,其主将即是被誉为美国华裔文学独立宣言《哎吔吔吔!
美国亚裔作家选集》( Aiiieeeee!
-AnAnthology of Asian American Writers, 1974 年, 并见注释(注:Frank Chin,"Come All Ye Asian American Writers of the
Real and the Fake",in The Big AllEEEEE-An Anthology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merican Literature,edited by Jeffery Paul Chan,Frank Chin,Lawson Fusaolnada and Shawn Wong,New
York: A Meridian Book,1991,pp.3-29.))作者之一的华裔文学宿将赵健秀(Frank Chin)。他认为,汤亭亭以及谭恩美、黄哲伦等受白人推崇的华裔作家的写作意识,属于美国主流文化长期熏陶下的“东方话语”的反映,他们追随传统华裔自传作家,以个人经验的写作,迎合和验证主流文化对中国文化和华人形象的种种歪曲描述。《女勇士》对“美国华裔小孩耳熟能详的真‘花木兰’故事”的篡改,表明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华人身份的“自我厌恶”,对中国文化“自卑”地否定。“花木兰”在《女勇士》中变成了“一个白人优越论创造出的中国式女人被禁锢在丑陋的中国文化中,并成为其牺牲品。”(注:Frank Chin,"Come All Ye Asian American Writers of the Real and the Fake",in The Big AllEEEEE-An Anthology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merican Literature,edited by Jeffery Paul Chan,Frank Chin,Lawson Fusaolnada and Shawn Wong,New York:A Meridian Book,1991,pp.3-29.)
《女勇士》究竟是怎样一本书?它为什么能获得如此之大的成功和引起华裔文人内部的大辩论?
《女勇士》(注:本文所用《女勇士》版本为New York: VintageInternational Edition,1989.)的全名是:《女勇士——一个鬼魂中长大的女孩的记忆》。全书分5个部分:1)无名女人,2)白虎山峰,3)巫医,4)西宫门外,5)羌笛之歌。前三部分作者“我”记述了几个儿时妈妈讲给她的故事:在中国老家,她的姑姑因为“私通”,分娩的当天被村里人抄了家,抱着婴儿跳进家中的水井,从此,不再有人提起她;作者想象自己成为“花木兰”,进白虎山修炼15年,然后带兵打仗报了国恨家仇,回到故乡成了英雄;母亲“勇兰”在中国学医和行医的经历,以及她能捉鬼和招魂的故事。后两部分是作者本人的讲述:“勇兰”得知妹妹“月兰”的丈夫在美国又结了婚,便把在香港的“月兰”“偷渡”来美去讨回她的权利,但“月兰”没有胆量面对丈夫,也不能适应美国的生活环境,最后病死在疯人院;作者的少年生活是在压抑和屈辱的沉默中渡过的,母亲曾挑过她的舌筋,让她讲话清楚和流利,终于,她像中国汉代被匈奴掳掠蛮地13年的蔡文姬,开口唱出了自己的歌。
从母亲的故事到自己的故事,读者可以粗略地看到书中的5 个部分是按作者年龄的增长排列的,但作者的叙述似乎混淆了母亲讲的故事与作者自己的感受、神话与幻想、美国的生活与中国的传统、历史与现实、听来的知识与事实真相之间的明确界限。单就写作手法看,《女勇士》亦非一本简单的书,叙述的多元视角,灵活的空间转换,多重的时间层面,现实与幻想的混杂,以及故事的互文性,令读者如进迷宫。《女勇士》一书所涉及的题材也极其广泛,我们很难给它的主题叙述下定义,这本书几乎包涵了关于移民处境,代沟矛盾,青少年的困惑和叛逆,女权主义,边缘文化,寻根意识,口头文学,家庭史诗,古老的民俗与神话,“东方话语”,“红色中国”,毛泽东,文化冲突,个人经验与历史叙述等使西方读者深感兴趣的种种成分。人们可以从各种角度阅读它,不同类型的读者可从中发现不同的可读性。这样的写作在70年代中的美国文坛可谓应运而生,与当时美国的人文环境十分贴切。即使今天来看,其风格也相当前卫,充满了五花八门的拼贴,前后矛盾的零乱叙述,以及随心所欲的神话改写,堪称为典型的后现代文本。
福克纳曾说优秀的作品必定是关于人的内心冲突的描写。 ( 注:William Faulkner,Speech for the Nobel Prize,1949.)《女勇士》中的“我”是一个思绪杂乱,充满反抗精神的愤怒女孩,她对华人的文化传统和美国的价值观都持质疑态度。她说母亲讲的故事前后矛盾,是胡编乱造。(202页)她怀疑好莱坞电影里的中国文化是否真实,(6页)常用“也许”否定自己的判断,(199 页)她憎恨“愚蠢的种族歧视者”白人老板使用“黄奴”的“字眼”,(48页)讨厌“华人女孩为使自己有美国女人味,把讲话声压得往往比美国人还要低”。(172 页)她感到回中国已无家可归,(106页)但“美国的生活令人沮丧”。 (45页)她不明白,为什么母亲说“我长大后会成人妻,给人当牛做马,但她又教我唱女勇士之歌‘花木兰’。我长大还得做女勇士”;(20页)为什么中国人守口如瓶,“却能保持五千年的文化亘古不变”? (185页)她要打破沉默,用文字向世人“报告怨恨”(她对中文“报仇”的字面解释),像“花木兰”一样为父老乡亲“报仇”。(53页)在书中,“我”站在其它叙述的对立面,不停地进行质疑或反驳,痛苦地寻求着关于“自我”(identity)的解答。《女勇士》所描述的正是现代人文化精神上普遍存在的那种“他人引导”社会里人们内心的困惑和焦虑,(注:杰姆逊(Fredric,Jameson):《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7—61页。)及范式权威缺乏导致的无归属感。
《女勇士》以第一人称“我”作为叙述者,使得多元叙述成为可能,“我”自由灵活地跳跃在传统叙述难以跨越的时空的界限之外,作品中的外在叙述与“我”的内在言说之间产生了张力,构成了巴赫金式的作品内部的多声部对话。这里的“我”显然是自传中的常规叙述主体所不能包涵的。在书中,当“我”使用中国式的英语,以华人的视角反观美国现象,或把华人的思维言行放置进美国文化背景中进行描述时;当“我”以不完全的知识解释中国和中国传统文化时;当“我”的美国主流文化视角下的“天真”(innocent)叙述,相悖于读者所认识的事实真相,或以美国式的轻松诙谐将神圣与俗常并置时,这种由反差或错位所产生的幽默和反讽的张力效用尤其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汤亭亭的《女勇士》中,我们看到了她的先驱者们的影子。在美国文学史上,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历险记》(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1884)和塞林格(J.D.Salinger)的《麦田里的守望者》(The CatcherIn the Rye,1951)都巧妙地运用了这种叙述错置策略,不仅更好地揭示了作品的主题思想,而且创造了极其幽默的喜剧特色。同样,《女勇士》也是一部充满幽默、可读性高的严肃作品。
毫无疑问,《女勇士》在70年代的美国文坛无愧是一本独特而入时的作品,而作者的华人女性身份在此也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从作者的创作主旨看,《女勇士》首先是一个女权主义的叙述。但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作品的实际支点在于两种文化的反差和冲突。作者兼备两种文化的身份使她的描述具有一定的客观性或可信性,对西方读者来说尤其如此。这点,作者在书中把它发挥到了极至。作者在描述5 个故事中的5位中国妇女形象的同时,穿插了许多发生在中国, 妇女遭受迫害的骇人听闻的故事,例如在“巫医”中,躲避日本飞机的村民看到同村的疯女人头上戴的首饰发出反光,怀疑她给飞机打信号,竟用乱石砸死了她。当然,作者的讲述也有漏出破绽的地方,“巫医”中作者的母亲完成学业归乡前到市场买女佣,模仿美国南方历史上买卖黑奴市场的做法,让女孩张大嘴查看她的牙齿,等等,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作者试图讲出比她的知识大得多的中国故事。
《女勇士》一书所罗列的中国传统文化符码之多令人叹为观止,从历史传说,神仙鬼怪,易经八卦,儒道佛教,到招魂祭祖,气功武术,裹足绞脸,听书看戏,到吃活猴脑,饮乌龟汤等古老而稀奇古怪的风俗民情比比皆是;书中提到了许多中国历史或传说中的人物,如花木兰,孟姜女,蔡文姬,岳飞,关公,孔子等;书中的各章节到处穿插着作者对“中国文化”自相矛盾的看法与评说。《女勇士》对“中国传统文化符码”的无节制的使用,反映了作者本人对中国文化有限而混乱,甚至片面的了解和认识。北京大学文化研究学者汤一介教授认为,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化是由两个相辅相成的因素构成的统一体,“就文化说,‘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传统文化’是指已成的文化,是过去文化的积存,它是凝固的,是有规定性的……;而‘文化传统’是指已成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的流向,是一种活动,是在不断变化之中,往往呈现为无规定性,”(注:汤一介:《在有墙与无墙之间》,见《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乐黛云、勒·比松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女勇士》的作者试图在书中把延续数千年之久的中国文化做共时性的呈现,割裂了外在符号与内在精神的联系,她笔下的中国文化只能是一大堆凝固的,非真实的图码。书中混杂而大量的中国文化现象,实际上不过是历史沉积下来的具象的文化符号而已,《女勇士》中描绘的许多东西,在今天的中国早已销声匿迹;它们有些虽然在形式上仍或多或少地存活在今天中国人的生活中,但它们所体现或包涵的实质意义却因历经沧桑流变,其所指功能已被大大地弱化和消解,现代中国人更乐意把它们当作一种有趣的民俗生活的点缀。《女勇士》是一本面向西方读者的书,中国文化的描述与该书叙述者的主体意识不无关系。《女勇士》的作者生长在与中国相异的美国文化氛围中,她对中国文化有着与我们本土人不同的视角。书中所描述的中国文化很大程度上,也是作者站在“他者”的立场对中国文化的“误读”。
我们看到作者虽然通过父母辈和唐人街的生活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的感性认识,但作者对中国文化所做的包罗万象,碎片堆砌式陈列,更多地说明了作者对中国文化的不甚了了。另一方面,也令人对她获取中国知识的认知途径产生疑问。作者本人在书中多次表示过她对中国文化的迷惑不解,甚至区分不了什么是真实的中国文化,什么是美国电影中的中国文化。可见,作者所理解的中国和中国文化深受其所处环境的制约和影响。
《女勇士》中描绘的中国文化既有西方文化猎奇心态的投影,又有“东方话语”式的对中国或中国文化的曲解。我们知道,几个世纪以来,中国或中国文化在西方人眼里的意象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变化。自13世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游记》在欧洲的传播,中国在欧洲几乎成了财富、高雅和神秘的代名词;到了16世纪末,以传教士利玛窦为代表的对中国的文化探险和交流,使得欧洲人对中国有了多元和较深层次的了解,17、18世纪的欧洲对中国的印象可谓毁誉掺半;19世纪,西方列强用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不再是具有永恒魅力的象征,西方人开始以征服者的眼光俯视中国文化,中国的形象与愚昧和贫穷联系在了一起。就在不远的过去,对大多数西方人来说,中国仍然是一个遥远的国度,“那儿到处是扇子和灯笼,长辫子和吊眼睛,筷子和燕窝汤,亭阁和宝塔,洋泾浜英语和裹小脚”。(注:Raymond Dawson (Fellow ofWadham College,Oxford),The Chinese Chameleon- an analysisof European concept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London: OxfordUniversity Press.1967.)本世纪推动美国强势文化全球化的急先锋好莱坞的电影,就充斥了关于中国或中国文化的许多不真实的描述和偏见,难怪乎《女勇士》的作者在书中数次提到电影与她的中国文化知识的不解之缘,生长在美国文化氛围中的作者难以摆脱来自美国主流文化的认知范式。
虽然《女勇士》写作的宏大目标是要对自己乃至所有美国华人的文化处境进行质疑或梳理,但文本所呈现的表层叙述的确为西方读者提供了他们喜闻乐见的异域传统文化的种种描述,满足了他们的猎奇心态。美国的普通读者更多看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神秘和趣味。一位白人评论家在《出版界周刊》(Publisher's Weekly)的一篇文章中,称赞《女勇士》“象中国织锦一般充满了富有变化的神话故事”,其文笔常常“达到了瓷器般的精巧”,在书中,“东方与西方相遇……获得了迷人的结果。”(注:Amy Ling,"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Chinese American Woman Writers:The TraditionBehind Maxine Hong Kingston",in Redefining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edited by A.C.V.Brown Rueff and Jerry W.Ward. Jr,
New York: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1990. Elaine Hikim,"Preface",in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An Introduction to the Writings And Their Social Context,Philadelphia:TempleUniversity Press,1982.)作者本人也在《美国文评家的文化误读》一文中表示,称赞她作品的评论家中约有三分之二的人并未超越他们自己已成定势的思维方式。(注:Deborah L.
Madsen(University
of Leicester),"(Dis)figuration:The Body as Icon in the WritingsOf Maxine Hong Kingston",pp.243,in Yearbook of English Studies,(4ES),London:24(1994).)并“强烈抗议把她的作品描述成神秘费解,充满东方异域色彩的写作。”(注:钱钟书:《钱钟书随笔》,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00页。 )作者企图颠覆美国主流文化中“东方话语”的初衷,似乎轻易地被掩盖在作品表层喧闹的中国文化符码之下。但同时,《女勇士》作者对中国文化的“误读”有意无意地契合了西方读者早已谙熟的关于中国文化的认知定势,在此,二者达到了阐释学意义上的“视域融合”。钱钟书先生在一篇论及文学革新的文章中这样说,“若是不顾民族的保守性,历史的连续性而把一个绝然新异的思想或作风介绍进来,这个革新定不会成功。”(注:钱钟书:《钱钟书随笔》,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00页。 )钱先生的观点从另个角度进一步说明了这一阐释学的现象。《女勇士》与以往美国华裔作品风格迥异,是一次突破性的写作,但它在形式上却与旧的叙述有着方方面面的联系,使读者在心理上能够认同和接受作者的表达,进而同情和理解作者所展示的华人的生存处境。
无可置疑,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描述,在客观上是《女勇士》赢得美国读者,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作者似乎对她的这些表层描述并不持赞扬态度,从她的叙述中,中国读者更多感到的是作者的对抗和批判。这一点,我们可在前面有关的讨论及作者本人的表述中得到验证。作者的本意是要从精神上同“中国文化”(即被误读的中国文化)划清界限,以颠覆美国媒介里华人的形象定势。遗憾的是,《女勇士》作者所抗争的正是她从美国主流文化认知范式里“下载”的中国文化。
如果我们把《女勇士》里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堆砌看成是作者对中国文化的“无意误读”,那么,在该书的第二章“白虎山峰”中,我们发现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了“有意误读”的策略。《女勇士》这个书名实际上就是指该书第二章“白虎山峰”里的女主人公“花木兰”。但作者笔下的“花木兰”与中国老幼皆知的花木兰传说大不相同。“花木兰”的故事最早源于南北朝时期(公元420—589年)的一首叙事性的乐府民歌《木兰诗》(也有系唐人所做之说(注:罗根泽:《乐府文学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28—131页。)),诗中刻画了一位替父从军,征战十年立下汗马功劳,辞去皇帝的册封,荣归故里的巾帼英雄;该诗文辞纯朴,活泼,琅琅上口,深受人们喜爱,千百年来在民间广泛流传,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与某些历史传说故事不同的是,“花木兰”故事自成型以后,除了仅有的两个其它版本外(明人徐渭的两幕杂剧《雌木兰替父从军》(注:王起主编《中国戏曲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658—671页。)和明人朱国桢《涌幢小品》里的《木兰将军》(注:王金盛编《历代微型小说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第351—353页。)),很少被改编,其情节也变化甚少。《木兰将军》仅在结尾处添加了皇帝欲纳木兰入宫,木兰不从,遂自尽,皇帝追赠孝烈将军,当地人立庙祭祀的情节;《雌木兰替父从军》主要情节与《木兰诗》基本一致,增添了未婚夫的角色(木兰的孝行感动了青年王郎,定要娶她为妻)以及军中将士之间的戏噱笑料。然而,《女勇士》中的“花木兰”不是替父从军,而是被鸟儿召唤进山修炼,师从一对神仙夫妇练功习武12年,学成后下山回家看望父母,临行前父母在她背上刺字,记下了所有要报的仇恨。花木兰出征后,军纪严明,爱兵如子,并同未婚夫在军营秘密成婚生子。凭借战神关公和法力的支持,她的军队所向无敌,一路劫富济贫,杀进京城,砍了皇帝的头,推举农民领袖做新皇帝,她被封为大将军,游览完长城返回家乡,杀恶霸,开诉苦会,砸碎祠堂供牌让乡亲们在里面听书看戏。最后,她跪在公婆面前许诺要操持农活做家务,生养更多的儿子,父母和亲戚靠她寄的钱生活幸福,她的忠孝有口皆碑。《女勇士》作者笔下的花木兰以“我”为叙述者,而故事的开头与结尾的“我”又是现实生活中的华人女孩。这里,花木兰的故事是发生在华人女孩头脑里的幻想,她把自己想象成花木兰,自编自演了一出中国英雄史诗。《女勇士》的改变与创造绝不仅限于上面所述,“白虎山峰”中的“花木兰”故事足有20余页,其中穿插了无数相关的细节。可以说,同原来中国版本的“花木兰”相比,《女勇士》里的“花木兰”已经面目全非。前者主要宣扬的是儒家的孝道,以及漠视功利,自强不息的精神。而后者则完全以一个自觉的革命者形象出现,她要造反,她要革命,她要报仇,她要建功立业。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女勇士》的作者通过“花木兰”来抒发自己的理想;她要用“花木兰”的豪迈气概抵御美国华人生活中的压抑;她要像“花木兰”那样为乡亲“报告怨仇”(如前所述)。作者对“花木兰”故事的刻意改变出自于她的精神需求,至少,“讲故事是对实际矛盾的虚构性解决。”(注:杰姆逊(Fredric,Jameson):《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7—61页。)通过改写,中国古代“花木兰”的传说变成了“我”的故事。借助“花木兰”作者创造了属于华人自己的神话。
美国人类学家马尔库斯和费彻尔在他们合著的《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书中如是说,“对异文化进行详尽的描述和分析时,……同时也隐含着对自身文化进行批评的目的。”(注:乔治.E.马尔库斯, 米开尔.M.J.费彻尔, 《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王铭铭、蓝达居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157页。 )中国传统文化构成了《女勇士》一书的文本质素,成为全书叙述工程的重要素材和参照背景。《女勇士》的作者借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描述和对中国历史传说的改写,深度地展现了华人在美国的生存状况和他们的文化心态,中国传统文化为美国华裔作家提供了言说的历史感和富有成效的隐喻功能。华裔作家离不开中国种族这个事实,他们的写作必然离不开华人的文化背景,中国文化遗产将是他们言说自己的有效工具。同时,华裔英语作家的双重文化身份迫使他们在两者之间保持中立,对两种文化既持批评态度又采取拿来主义,客观上起到了文化使者的作用。《女勇士》的作者在此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在该书出版后12年的今天,“花木兰”走上了好莱坞的银幕,已成为全世界家喻户晓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