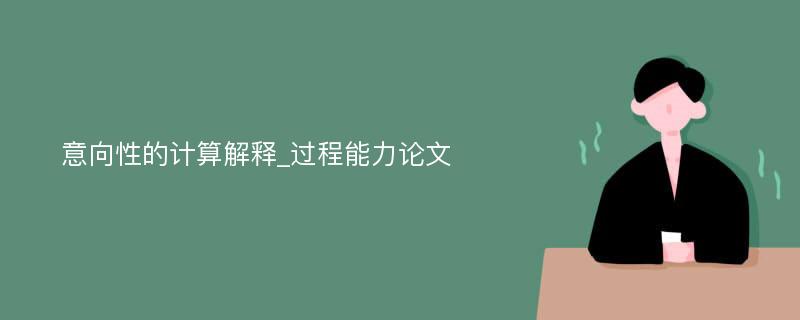
意向性的计算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向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心智哲学和认知科学中,意向性是颇受关注且又不断引发争论的中心概念之一。直观上,意向性系指心智状态或过程具有的“关于性”,即心智的内容是关于或表征某种东西的。许多哲学家认为,意向性是大多数(甚至所有)心智状态的标志。倘若意向性确是一种真实的现象,则以理解心智现象为己任的认知科学,就有责任用科学上合适的方式来解释心智状态的这一特质。
认知计算主义一直且依然在认知科学中处于主流地位。根据心智的计算理论,心智状态本质上是计算的,因此,意向性理应从计算的观点予以科学或自然的解释。但是,大量的论证似乎已表明,这种解释是不可能或不成功的。不过,有意思的是,尽管认知计算主义自产生起便不断受到来自各方的批评,但运用计算观点理解世界的研究范式却在这种氛围中大大超出了认知科学的范围,成功地扩展到当今物理学、生命科学乃至社会科学等的前沿领域。与此相应,人们对计算概念的把握也更加全面和深刻。于是便自然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以往那些反对认知计算主义的论证中所理解的计算概念,是否过于偏窄了,以致未能恰当地把握自然计算的实质,结果得出无法运用计算的观点解释意向性的结论?笔者认为,情况确实如此。为此,本文将基于心智哲学和认知科学等领域中关于计算的新理解,尝试对意向性给出自然的解释。
一、意向性问题
意向性是哲学中的一个技术性术语,不过如今亦已运用于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等领域,成为刻画心智状态的基本概念之一。辞源上,意向性(intentionality)出自中世纪的拉丁字——intendere,意为“瞄准”(to aim at)。不过,作为一个专门的哲学概念则始于19世纪末的哲学家布伦塔诺(F.Brentano),当然他本人并未直接使用这一名称。
在《从经验的观点看心理学》一书中,布伦塔诺认定心智状态与物理状态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具有指向某种对象的特性,即意向的心智状态是关于对象的,而这里的“对象”并非一定是真实的存在物。(Brentano,p.68)布伦塔诺关于意向性的论述中,有两个重要且相关的观点在当代心智哲学中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和争论:一是没有物理状态或现象具有意向性;二是所有且只有心智状态具有意向性,即意向性是心智现象的标志。(Crane,pp.229-233)
下面先从第二个观点出发来分析由意向性所引起的哲学争论。争论的焦点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个问题为:究竟是否所有心智状态都有意向性?显然,我们的信念是关于世界的状态或过程的,如“地球绕着太阳在转动”是我们关于地球状态的信念,所以信念具有意向性;类似地,如果我们有一个保护好地球生态系统的愿望,则这个愿望也有意向性。因此,意向性是信念和愿望等心智状态的基本特征。不过,除了这些具有明显内容的状态外,我们还有属于体感或情绪的心智状态,如疼痛和焦虑,它们则似乎并没有关于什么的内容。据此,有些哲学家认为,只有具有内容的心智状态才具有意向性。(Searle,p.1)按照这种看法,布伦塔诺的第二个观点就是不正确的。
另一个问题为:果真只有心智状态才具有意向性吗?图画、文字或现有计算机等的内容均可以是关于或表征某种对象的,而它们并不属于心智状态。倘若“关于性”确是对意向性概念的恰当刻画,则这些事物的状态应具有意向性。不过,解决这个问题似乎并不难。图画和文字等之所以看上去能表征另一事物,并不在于它们本身具有这种能力,而是在于第三方的存在:人不仅创造了它们,并且赋予它们意义,也就是说这种意向性仅仅是从人的意向性导出的。这样,一些哲学家便主张把意向性分成两类:内禀(或原始)的意向性和导出的意向性;并进而认为,前者是人(也许还有某些动物)的心智所特有和固有的属性,而人所创造的人工系统和符号则只有导出的意向性。(ibid,p.27)
结合以上两方面的分析,我们至少可以认为:人的一些心智状态具有意向性,而且导出的意向性可由人的意向性予以解释。假如将这个结论与布伦塔诺的第一个观点联系起来考虑,就会引起对心智意向性的来源的追问。如果心智现象具有意向性而物理现象没有,且意向性是一种真实的现象,则它究竟从何而来?一种方便的回答是:认定内禀的意向性是实在世界的一种自在的基本属性,其本身并非由其他属性所派生。这意味着我们所处的世界原本就存在着两类彼此独立的基本属性:物理的和意向的。然而,这种属性二元论的形而上学主张明显地与实在世界在物理上的闭合性相抵触,而且与现代科学的成就不相容。为了避免这些困难,我们就需要对意向性的来源予以自然的解释。正如福多(J.A.Fodor)明确表示的:“如果语义和意向性是事物的真实属性,那么就必须被确认为是同一(或许是随附)于本身既没有意向又没有语义的属性。如果关于性是真实的,它必须是某种别的实在的东西”。(Fodor,p.97)于是,理解意向性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原本非心智的事物何以能呈现出具有意向性的心智状态。
二、解释意向性的进路
当代大多数哲学家和认知科学家认为,既然意向性是真实的,而只有物理属性才是实在世界中事物的基本和不可归约的属性,那么,意向性就应该能“自然化”,或者说能还原为某种物理的东西。
沿着这条自然主义的解释进路,哲学家们已做了大量的探索。一个较早的、影响较大的进路是基于信息概念的因果共变假说。其基本观点为:如果一个事物的状态与另一个处于环境中的事物的某种物理状态之间存在着因果的共变关系,则该事物就携带关于对象的信息,结果便显现出意向性。(Stampe,pp.42-45; Dreske,pp.56-77)然而,这种解释存在着一些麻烦的问题。首先,心智意向性可以指向虚构的对象(如独角兽),或误表征外部对象。但依据因果的共变假说,意向状态由外部对象所引起,携带的是关于外部对象的信息,这样的话,就难以解释心智状态可表征并不存在的对象和误表征这些事实。其次,也许更为棘手的是,如果仅从两个事物之间存在因果的共变关系,就断定一个事物的状态携带另一事物的状态的信息从而具有意向性,那么自然界许多事物的状态就都会有意向性了(如树的年轮携带气候的信息);而如此一来,意向性的概念就变得不足道了。
鉴于存在这些问题,一些哲学家便试图从其他进路来还原意向性。一个较流行的做法是放弃因果概念,转而考虑生物的功能。这种进路的基本观点是:心智意向性可由生物功能来还原地解释,而后者又可从生物的进化获得自然的理解。既然心智现象由人(或某些动物)所例示,而人无疑也是一种生物,所以从生物功能的进路来解释意向性是一种自然和合理的选择。由于在生物学的概念框架中,胃具有消化的功能,但似乎胃并不是关于什么的,也就是说很难认定它的状态具有意向性,可见对于意向性而言,具有一些生物功能并不充分。因此,我们需要的是:要么生物功能加上其他一些必要条件,以致这些条件合起来成为产生意向性的充分条件;要么从生物功能中寻找一些特有功能,并认定它们才是意向性产生的充分条件。目前,一些哲学家选择后者,即认定能够解释意向性等心智现象的不是倾向于做什么的功能,而是为了什么而做的目的功能。这种目的功能是自然选择的产物,而选择过程也是设计过程,故自然的设计是心智内容和意向性的来源。(Millikan,pp.17-51)不过,究竟能否将意向性还原为生物的目的功能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主要原因在于:从概念上看,目的性的功能与心智意向性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裂缝。
还有一种进路由丹尼特(D.C.Dennet)提出。他认为,对于世界上存在的实体的行为,我们可采用三种不同的策略去预测和解释,即物理学立场、设计立场和意向立场。这三种策略在预测实体行为时复杂的程度和承担的风险各不相同。用物理学立场去预测对象的行为最可靠但也最复杂;而对于有些实体(像人或下棋的计算机)的行为,用意向立场去预测虽然失败的风险最高,但最简单也通常很有效。(Dennet,pp.42-68)在丹尼特看来,采用哪种立场取决于我们想达到的效果,因此不少人认为他的立场是工具主义的。
如果他的立场果真是工具主义的,那么意向性就可以认为是将一个实体看作意向系统的结果,因而对于心智意向性似乎也就不必进行还原解释。不过,倘若此处的“还原”并非指化归为某种非心智的东西,而是指将诸如人的意向性解释为某种更基本或更简单的意向性的产物,则仍可认为是还原的。丹尼特正是采用了这一还原策略。他承认书和计算机这些人工制品具有导出的意向性,却否认人的心智具有内禀的意向性,而是主张这种所谓“内禀”的意向性实际上也是通过自然选择从大自然的基本意向性中“导出”的。于是,他认为:“脑是一种人造物,它所获得的它的那些部分所拥有的意向性,来源于它们在它作为其中一分子的更大系统的生生不息的活动中的作用,换句话说,从它的创造者——大自然(或者人们所说的通过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的意图中得到意向性”。(丹尼特,第41页)
许多人不接受丹尼特对人的心智意向性的解释。反对的理由是多方面的,其中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这样一来就模糊了像计算机具有的导出的意向性与人所具有的意向性之间的区别,而单凭自然选择不足以“导出”心智的意向性。(Nanay,pp.57-71)笔者则认为问题在于:丹尼特从大自然中更基本的意向性来解释人的心智意向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对后者的理解,但意向性本身却成了一种隐藏在自然深处的神秘现象。当然,丹尼特可坚持工具主义的立场,认定意向性只是我们采用意向立场预测和解释实体行为的一种有效策略而已。但这样做并不能使我们理解为何采取意向立场去预测经常是成功的,也不能说明为什么我们常常能感受到心智处于真实的意向状态中。
对于一个实体行为的预测和解释,采用不同立场的策略无疑是需要和有效的,但并不一定要持工具主义的立场。实际上,如果借鉴丹尼特的这种策略,同时考虑上述几种还原意向性的尝试,我们就可找到运用计算的观点解释意向性的有效进路。
探究这种进路的基本出发点是假定只存在着一个实在世界,而对于它,概念化的方式却可以多样。这样,对于一个实体及其行为,我们就可以采用多种认识方式,这类似于丹尼特主张的多元立场。所不同的是,笔者认为,不同的概念化方式是对同一实在的刻画或描述,而保证它们之间相协调的约束条件就是随附(或实现)关系,故这并不是一种工具主义的立场。例如,面对一尊由泥团所塑成的塑像时,我们首先可认定有一个存在物;在此基础上,既可以将它看作有一定构型的物理系统(泥团),也可以将它看作一尊艺术品(塑像)。至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则是:塑像随附于泥团,或者说塑像由泥团所实现。这是两种概念化实体的方式,而本体论上却是只承诺一个存在物,因而每一种方式均是对实在的描述。在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对于同一个存在物,尤其是复杂的存在物,采用多种概念化的方式通常是必要而有用的。
与概念化泥团的方式相类似,我们可以对“脑”进行概念化。①首先需要认定脑是一个存在物,在此基础上,我们既可将它看作一个物理系统,这样就能在物理科学的概念框架中来考察它的物理的组成、属性和过程;也可将它看作一个心智(或认知)系统(简称为“心智”),于是便可以运用认知科学(或心理学)的概念框架来考察它的心智组成、属性和过程;至于心智系统与物理系统之间则是随附或实现的关系,也就是说,心智系统随附于物理系统,或者说物理系统实现心智系统。
由于意向性是一种心智现象,而基于上述分析,它的承担者是心智系统,这样,当试图对意向性进行解释时,就存在着两条基本进路:一条进路是从心智系统与物理系统之间的随附关系出发,去探寻心智现象的物理实现条件。当代认知神经科学所采用的正是这条进路,其任务就是发现心智现象与神经生理基础之间的关联(实现关系)。显然,这样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认知和实用价值,因为通过确定认知过程的物理实现,就有可能找到它们之间的关联模式,并借助这种模式来认定、改变或利用某种认知行为。然而,随附并不是还原,一旦将“脑”概念化为物理系统,我们就只能够描述或谈论物理现象,而归于心智系统的心智现象在物理实现的层面上就消失了。(Dietrich,pp.9-11)因此,要还原地解释意向性,这条进路似乎并不合适。
另一条进路是通过直接探索心智系统的本性和起源来解释意向性等心智现象。这样,首先需要阐明的是究竟什么样的一个系统可称为心智系统。对此,哲学界和认知科学界均没有公认的规定。不过,一般来说,心智系统是指处于环境中的这样一个存在物,它“在试图满足其目标的过程中运用信息”。(ibid,p.5)这表明,心智系统是一类信息系统,信息是其基本的构成单元。环境中,所有高等动物为了达到目标都运用环境提供的信息并采取相应的行动,故它们可看作是心智系统,简称“心智”;而我们目前所使用的计算机虽然也是信息系统,却由于不是为其本身的目标而运用信息,故并不是心智。特别地,人的心智是一个具有意向和意识等特性的系统。基于这样的认识,解释意向性的任务就须在属于心智的概念框架内展开。于是,问题便转化为:如何从构成心智的基本组元、属性和结构来解释意向现象的形成条件和机制。这样,笔者认为,第二条进路才是理解心智意向性的合适和自然的进路。
三、心智作为计算系统
基于上述对心智系统的规定和理解,就可以来描述它的特性。对于心智来说,运用反馈回路来达到对环境的控制或适应是其基本目标。而要达到这一目标,一个心智系统必须具有可用于比较来自环境的信息与预期的目标状态的内在状态;这意味着内在状态至少部分由来自环境的信息所构成,并通过信息变换和反馈的回路实现心智与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这样,当我们把计算规定为信息变换或动态变化时,就可以认定它是心智的基本特性之一;也就是说,心智是一类计算系统,具有计算性。②
作为一类计算系统,心智的第二个特性就是虚拟性。一个心智系统是实在的,但并非是物理意义上的实在,也就是说相对于物理系统而言,它是一种虚拟的实在。③如前所述,对于“脑”这样的存在物,我们至少可以采用两种概念化的方式,即将其看作物理系统和心智系统,而两者之间是随附关系。心智的这种虚拟性是其有别于物理系统的特性,同时是其具有能够模拟外部对象的能力的基本条件之一。基于这样的理解,心智系统也是虚拟机或虚拟系统。心智的第三个特性是表征性。因为心智的状态可以携带来自环境的信息,所以它能表征环境中的对象的状态和过程。心智的第四个特性是内禀的意向性。这种意向性一方面表现在心智能够表征外部对象,另一方面则在于它能够利用具有表征内容的心智状态去展开行动(包括心智行动),以便适应或控制环境。对于心智来说,初阶意向性表观上是关于并指向外部对象的,并由系统的内在状态与环境之间所形成的信息因果链来实现。
如果对人的心智进行考察,则我们可以发现,与其他心智相比,它不仅具有上述四种特性,而且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人的心智不仅是一种计算系统,而且它履行的计算具有通用性,即像通用的计算机那样,能够模拟其他事物的计算过程;它不仅是虚拟的,而且是一个由不同类型和多层级的虚拟机所构成的复杂虚拟系统;它不仅能表征环境中的对象,而且也能对表征进行再表征并具有不同类型的表征(如图像的和抽象的);相应地,它不仅具有初阶意向性,而且具有关于表征本身的高阶意向性。④
若认定人的心智具有上述四个特性,则会引发这样一个疑问:我们目前所普遍使用的计算机不仅是计算系统,而且同样具有计算的通用性、多层级的虚拟性和内容的多重表征性,那么它为何缺乏内禀的意向性?这表明虽然心智是计算系统,但并非具有通用计算性、多层虚拟性和多重表征性的计算系统都可以称为心智。
四、意向性的生成条件
于是,需要探索的是:一个计算系统能够具有内禀的意向性从而成为心智的条件是什么?据笔者的分析,要回答这个问题,塞尔提出的“中文屋”思想实验是一个恰当的切入口。
自1982年塞尔提出“中文屋”思想实验后,围绕其所展开的哲学和科学争论持续至今。塞尔设想自己对中文一窍不通,被关在一间屋子里。屋里放着一本包含中文字库和用英语写成的指令集的指南,这些指令的惟一作用是把一串中文字合乎规则地变换成另一串中文字。现在,假设屋外站着一群懂中文的人,他们通过一个小孔向屋内传人一些用中文写成的问题;塞尔则根据手头的那本指南决定向外界传出什么样的中文句子。由于他不懂中文,所以他并不知道传出的句子的意义。然而,对于屋外的人来说,从塞尔的行为可以判断他应该懂中文,虽然实际上他不懂。据此,塞尔作出了以下的论证:仅仅通过实现程序,一台计算机并不能具有真正的理解;一个真正的理解具有内禀的意向性,这样才有意义;人有理解能力,也就有内禀的意向性;所以,仅仅通过实现程序对于心智而言是不够的。(塞尔,第336-342页)
毋庸说,这个思想实验和所作出的论证不仅对强人工智能的主张作出了反驳,而且对认知计算主义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如果塞尔的论证是有效的,那么强人工智能者希望仅仅通过程序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的智能的梦想就将破灭;而对于认知计算主义者来说,就必须要能运用心智的计算理论来合理地解释人的理解能力和意向性。
既然“中文屋”系统因没有理解能力而不具备内禀的意向性,那么就须追问: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它与心智的差别?在思想实验中,对塞尔之所以不懂中文的一个似真解释是:语言本身并没有意向内容或仅仅只有导出的意向性,因而只有当塞尔的心智状态与懂中文的人的心智状态具有等价内容时,他才具有真正的意向性,而满足具有等价内容的必要条件是他的心智状态处于跟懂中文的人的心智状态一样的与环境对象的信息勾连之中,也就是说,心智的意向性的产生不仅需要对内部状态履行基于规则的计算,还需要恰当地表征来自环境的信息。由于当我们处于某个自然环境中时,进入感官(如眼睛)的环境信息通常是纷繁杂多的,因此,要识别环境中的某个对象就需要心智对信息进行有选择的表征。我们知道,目前使用的计算机(包括“中文屋”思想实验中的塞尔)所接受的信息是事先形式地表征好的,也就是说,它并没有选择地表征外部信息的能力。
那么,加上选择地表征外部信息的能力,从而实现计算系统内部状态与环境信息之间相勾连这个条件,是否能够断定系统本身就具有内禀的意向性?在反驳“中文屋”思想实验的各种策略中,被称作“机器人的回答”就采用了上述策略。(塞尔,第347-348页)不过,除了塞尔本人拒绝这一策略外,其他也有不少人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这个信息勾连条件加上基于规则的符号计算,对于内禀的意向性的产生同样是不充分的。一个颇具说服力的论证是:这种勾连是内部状态与环境中对象之间的对应关系,而对于一个认知主体来说,他是从第一人称视角来把握这种对应关系的;由于对应关系的一端并不属于其内部状态,而是属于外在于他的外部对象,因此这种性质本质上是一种外在的关系性质,而意向性是一种内禀现象,故并不足以说明心智状态的意向内容。(Bickhard,pp.65-75)事实上,仅仅通过这种信息勾连的对应关系,我们并不会认为勾连的一方就具有了内禀的意向性,不然的话,照相机甚至所有的测量仪器就都具有这种意向性了。对于心智来说,某种内部状态具有意向内容不仅取决于该状态与环境中的对象具有对应关系,更重要的是要确认该状态是关于对象的表征。由于环境中的对象并不处于心智内部而不可通达,所以,从第一人称的视角无法实现这种确认,故这种对应关系并不能成为内禀的意向性的构成条件。这表明,虽然来自环境中的信息对于形成“关于”外部对象的内容一般来说是必要的,但由于这种信息勾连是外在的联系,故其即使与基于规则的操作相联合,也不足以解释意向现象的内禀性或心智内容的意义。
由此看来,要确定一个计算系统成为心智的条件,从而实现对意向现象的还原解释,还需考察心智内部的基本属性和结构,从中找出内禀的意向性的构成条件。由上可见,只有在心智内部建构起关于外部对象的模型,而表征的内容涉指所建构模型中的“虚拟客体”时,才能形成意向现象的构成要素。也就是说,意向性或意义并不位于外在世界或外在世界与心智世界之间的交接处,而是位于所建构的模型之中。这意味着,假如一个计算系统具有建构关于环境中对象的模型的能力,并以这样的模型作为指向外部世界的“中介”,就能获得产生意向性的内部构成关系。这样,一个具有表征内容的心智状态其实是关于作为“中介”的模型中的“对象”,而这些“对象”则可通过信息回路与环境中的对象发生勾连;因此,直觉上,我们似乎能感知到心智的内容是关于或指向外部对象的。
只要一个建构的模型基于来自环境的信息,对外部世界的结构和过程作出模拟或预期,并借助行动与环境之间的信息回路建立起行动—知觉之环,就能够确认或修改模型。可以看出,虽然目前我们所使用的计算机也能通过模型表征和模拟外部世界对象的结构和过程,但这些模型却是使用者从外部“注入”的;也就是说,计算机并没有利用来自外部的信息建构模型的能力,而人(也许包括高等动物)作为认知者显然具有这种能力。⑤
基于上述分析并与计算机相比较,笔者认为,选择性地表征外部信息的能力和建构模型的能力是心智系统内禀的意向性的生成条件。
五、生成条件的计算解释
如果上述两个条件确实可以使得一个计算系统成为心智从而具有内禀的意向性,那么,意向现象的还原解释问题就转化为:如何从计算的属性、结构和过程来说明这两个条件,以致在计算概念的框架内合理地理解意向性的呈现。
对于表征外部信息的选择机制,运用计算的观点予以自然和恰当的解释从原理上说并不困难。就一个心智系统而言,知觉过程就是变换、选择和识别环境信息的过程,而根据我们对于计算的理解,这实质上就是一个由生物所履行的特殊类型的计算过程;也就是说,一个生物的知觉系统就是一个特定的计算系统。⑥事实上,当代认知科学、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学已经逐步解开了知觉的计算结构和过程,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由可以在自然环境中自主活动的机器人所实现。
既然一个具有选择和表征外部信息的功能的计算系统并不足以成为心智系统,那么,如何运用计算的观点解释建构模型能力的形成,便显得更为关键。要解释这种能力,一个基本的策略仍是从心智的功能着手,来探索一个心智究竟具备什么样的计算属性和计算结构才使得内部状态具有意向性。从计算的观点看,如同通用图灵机,人类的心智在计算上是普适的,即认知的计算能原则上模拟其他任何计算。这样,人的认知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模拟过程。⑦这个观点蕴涵着非常重要的科学和哲学意义。从它出发,至少原则上能很好地理解认识世界的过程如何进行:一方面,我们运用自然的感官或测量仪器获取关于认识对象的信息;另一方面,我们在大脑中建构模型或理论并将它们实现为可产生具体信息的计算结构和过程,借此来模拟认识对象的结构和过程。可见,我们之所以能够认识世界的基本前提,就在于拥有一种能模拟许多对象的能力。
这样,问题就转化为如何用计算的观点说明这种通过建构模型模拟认识对象的能力。由上可知,具有这种能力需要一种“模型生成器”,它的基本功能是能将环境中的无意义的信息转化为对心智而言有意义的信息。在计算的概念框架内,“模型生成器”就是一类能够实现其他虚拟机(模型)的基本虚拟机,而计算的一个基本属性可合理地说明“模型生成器”不仅本身是计算的,而且能够表征和模拟外部对象。这个属性就是计算的幂等性,即计算的计算也是计算。这样,“模型生成器”是一种基本的计算系统,而计算的幂等性又允许它通过计算去建构模型以表征认识对象的信息。由于每个具有一定功能的子计算系统(包括模型和“模型生成器”)均可看作虚拟机,故一个心智实际上是由多层虚拟机所构成的计算系统。这与目前使用的计算机相类似,差别在于心智具有运用外部信息建构模型的虚拟机——“模型生成器”。另一方面,由于大脑亦可看作一个具有不同层级和结构的子系统所构成的物理系统,这使得“模型生成器”的物理实现成为可能。事实上,自然界的复杂进化已经产生了“模型生成器”得以实现的物理结构和过程。
然而,为了解释心智的内禀的意向性或内容为何具有意义,具有“模型生成器”依然显得不够。这是因为,如今计算机或互联网中的一些软件似乎也具有生成模型和挖掘模式的能力,但我们仍然不认为这样的计算系统所获得的内容具有真实意义。那么,还需要什么因素才能使心智状态的信息变成有真实的意义?这里,关键是需要理解一种信息对一个由心智构成的认知主体本身而言,怎样才算有意义。显然,对于认知主体来说,如果一种信息与其生存和进化并不相关,则这种信息就没有什么意义。因此,确定一种信息是否具有意义需要与认知主体的约束相关联,而最基本的约束就是有利于维持其“活”的状态。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就可以明白:只有当由生成器所建构的模型不仅表征外部对象,而且通过与行动、环境和知觉形成一个信息的计算回路,从而使得认知主体在环境中成功地生存时,方可确认这种模型是对环境中对象的恰当表征,获得了有意义的信息。因此,心智内容的意义或意向性的产生是建构的模型在生存条件的约束下成功地对应于外部对象的结果。⑧由于这样的模型是基于来自环境的信息(通过知觉)而生成,并通过行动的成功与否来确认,所以,虽然意义居于模型内部,而意向性则仿佛是指向外部对象的。这种初阶意向性为所有认知主体所共有。
人类的心智系统不仅具有初阶意向性,而且具有关于初阶心智内容的高阶意向性。借助计算的幂等性,高阶计算成为产生高阶意向性的机制。这种高阶计算能够利用内部可用的信息,建构高阶模型来模拟低阶模型中的虚拟对象,而后者可以对应或不对应于外部对象。如果这些低阶的虚拟对象并没有对应的外部对象,那么这种高阶意向性就只是关于虚拟对象的。不过,这并不妨碍在心智系统内部建立起高阶模型与低阶模型之间的信息回路,从而使得前者获得某种意义。由于人的心智系统具有高阶意向性,因此,它可以指向非存在的对象。这就解释了人的心智的内容为什么能指向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的客体,而同时又是有意义的。关于高阶意向性的产生,一个基本而又关键的观念是:大脑不是单一的存在物,而是由多个子系统所构成的“超”系统,因此可以形成抽象程度和类型不同的表征,而表征、对表征的再表征就是形成高阶意向性的基础。
高阶模型的建构与具有初阶意向性的低阶模型之间的连接,同样可以看做是一个行动—认知之环;这里的行动就是心智活动,而这样的环路对于形成高阶认知和意识是必要的。⑨如果一个认知主体在解决问题或执行任务时,只依靠初阶意向性显得不够充分,那么拥有高阶意向性就会具有进化上的优势。因为一旦一个认知主体具备高阶意向性的能力,那么当碰到新情况时,就能够对自身初阶意向的内容和行动的模型(知识)进行评估,必要时作出修改,这样就能更好地处理新问题。
六、结论
本文的基本立场是:如果将计算理解为信息的变换或动态变化的过程,心智的意向性就能够在认知计算主义的理论框架内获得自然的理解。展开这种解释的基本进路是:首先,认定意向性是心智系统所具有的一种真实现象;然后,通过将心智看作计算系统,并基于对塞尔的“中文屋”思想实验的分析,确定一个计算系统能成为心智从而具有意向性的两个关键条件,即选择性地表征外部信息的能力和建构模型的能力;进而,进一步运用计算的观点解释这两种能力得以产生和实现的机制。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对能够产生意向性的两个条件的认定仅仅是基于理论的分析和论证,因此,这种认定严格意义上只是表明,如果两种能力得以实现,就有可能使得一个计算系统具有意向性。至于这两个条件实际上是否充分,尚需要经验的检验和确认。不过,基于上述分析和论证,可以提出如下猜想:假如一个人工的计算系统(如机器人)能选择性地表征来自自然环境的信息,能基于获得的信息建构关于对象的模型,并在环境中能成功地行动,则它就具备了类似于自然心智的内禀的意向性。当然,检验这一猜想将是具体科学的任务。
注释:
①心智现象显然不仅仅与脑相关,但为方便起见,这里只用“脑”来指代涉及心智的存在物。
②这里,计算与信息之间的关系是:“信息是静态的,而计算是动态的,计算变换信息”。(Rucker,p.5)
③这一特性与计算机和认知科学中已广泛使用的虚拟机概念密切相关。所谓虚拟机是在一台普适计算机上被模拟且运行的机器。从本质上看,一台虚拟机是由物理机器或其他虚拟机所实现的计算或信息系统。习惯上,之所以将这样的计算系统也叫做机器,很可能是为了强调它们亦是具有组元和结构的复杂系统。这些相互作用的组元的种类、数量和由此而形成的结构一起决定着整个系统的功能,从而能够实现一定的目标或完成特定的任务。另一方面,之所以强调这样的机器的虚拟性,是因为它们虽然与物理机器一样真实或实在,但本身并不是物理机器,其结构和功能需要由包括物理机器在内的更低层次的机器来实现。
④鉴于本文的主要兴趣是解释人的意向性,因此不仅需要考察一般心智的属性,而且更将关注人的心智的这些特性。
⑤事实上,在“中文屋”思想实验中,塞尔本人没有利用也无需利用这种能力。
⑥至于这个计算系统如何生成和运行,则是经验科学所研究的任务。
⑦在《用计算的观点看世界》中,笔者对此有较详细的阐述和论证。(郦全民,第151-153页)
⑧从进化的角度看,自然选择使得心智所建构的模型通常是可靠的。
⑨笔者认为,高阶意向性是人的高级意识形成的构成要素。不过,详细论证这一观点超出了本文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