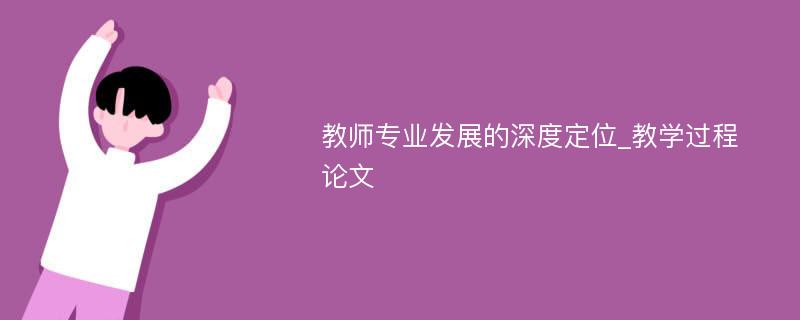
深度定位的教师专业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深度论文,教师论文,专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深层教育学与专业教育学的对立
今天,人们对教师专业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但如果我们能关注到教师专业化的历史,就不难发现:我们今天理解的教师专业发展,其实只是特定制度条件下相当特殊的一种社会建构,并非专业发展的唯一类型,更不是其本质特征,当然也不是教师发展的必然归宿。在传统社会,教育者维持很低的专业化水平,就可以很好地胜任其教育教学工作。一方面,具体的教育教学设计主要是在教学过程当中即兴完成的。就像孔子所说的那样:“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①P220苏格拉底(Socrates)的教育实践体现的也是这方面的特点:随时随地发生,没有事先的设计;每个人都参与教学的组织,每个人都是知识的源头;如果真的有什么知识,那也不是出现在教学活动之外,而是高度依赖于作为对话活动的教育教学实践本身,而且主要出现在这些活动的结尾部分。另一方面,很多时候,尤其是在个人之间的身份次序鲜明的东方社会,连这样的教育教学过程也不是经常可见的,即所谓“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①P174可见即便是我们今天广为推崇的启发,也不常见。这样,要想成为一位令人敬重的先生,需要的不是将一套科学的程式运用于教育教学实践的能力,而是培养一种尊重传统、沉醉于文化原典、借助自己的社会人格解决问题的态度。在这样一种社会中,教师专业化的痕迹是甚少的。如果有,那也主要只体现在或多或少存在的那样一些教育教学的经验上。但传统社会的教育教学说到底不是建立在这样一些教育教学的经验与技巧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人们的个人体悟/自求自得、教育者的地位身份及其所传授的文化元典的神圣性质的基础之上。②P126~130
中世纪的大学教师有严格的资格要求,但仍不要求我们今天所说的这种专业发展,而是基于一定期限的学术训练、对教师法团的认可以及教师法团对他的接纳与认可。这种学术训练按照哈斯金斯(Haskins,C.H.)的考证,一般都是针对一些重复使用的教材进行艰苦而细致的训练。由于书籍稀少、图书馆尚不存在、对经典的理解大量依赖于权威的阐发、学术自由的空间——除少数几个领域如哲学和神学外——相当大,学者们“有权说出自己所想而不需要去想自己说些什么”,知识本身与特定的教学/学术共同体之间就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正因为如此,经院主义,正如其历史学家反复提醒我们的那样,不是一个整体,而是有许多学派,各个学派之间的争论、各种观点之间的差异,与古希腊时期或我们当代一样尖锐和激烈。③P18~35与此相关联的是12世纪的那样一场伟大的学术复兴。在哈斯金斯看来,只要知识仅仅局限于中世纪早期的“文科七艺”,没有这样一场源自阿拉伯世界的学术复兴,中世纪的大学就不可能产生。③P3而根据涂尔干(Durkheim,E.)的研究,在中世纪,任何人如果想要授课,也都必须先跟从其他某位教师上课,并且必须达到一定的期限要求,大约五到七年不等。而且这位教师本身还必须获得应有的授权——“执教权”(主要来自教会,少部分来自王室授权),并且至少在他的学生的第一堂课上,为他举行某种授权仪式——“就职礼”。④P91~97这里的“执教权”是对一个人德性与才干的一种证明,而“就职礼”则是对他们师生关系的一种确认,而且更重要的是对教师法团本身的一种认可和尊重。因此,如果中世纪的大学教师也是一种专业教师的话,这一专业的基础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学术训练、经验积累和身份认同。而在我们今天所倡导的教师专业化实践中,教师培训不再建立在未来教师与大学教师之间的师徒关系以及他们对教师的接纳与认可的基础之上,他们未来的学生与他们之间也不再具有原来那种身份上的依赖关系,专业教育学而不是学术训练、经验积累和身份认同已经成了确保他们之间有效沟通和交往的手段。这始终是与大众教育的兴起连在一起的,完全是因为初等教育日渐普及,师生共同体开始瓦解,大众教育实践脱离了身份认同的传统轨道的缘故。
而一旦教师专业发展脱离身份认同的轨道,强调学术和实践取向的教师专业发展的路径也就走到了尽头。因为师生关系的建立不再以对教师本身的学识和德性的认可为基础,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再去展示个人的独特理解就已经不合时宜。事情又变得与中世纪早期相似,获得某种标准化的知识,像“文科七艺”那样的东西,而不是那种由教师个人所掌控的知识,就成了学习的主要目标。知识与教师本身的这种分离使得教学过程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问题的关键不再是在教师和学生之间建立某种学术或教学共同体,而是对人类现有的共同智慧尤其是近现代科学进行系统地传授,从而使得学习者最终成为合格的社会公共成员而不是忠诚但又非公共的师生关系共同体的一员。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实质性联系因而逐渐变得淡薄,技艺取向的专业发展路径由此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其目的不是把教师培养成一个学者、长辈或教育家,而是把他培养成一个在所教知识面前长袖善舞的教学法专家。这是一场与教育者天性作战的战斗,也是一场与知识天性作战的战斗。作为天生的教育者或者作为人,他们渴望生活在共同体中间,生活在与自己学生的亲密关系结构中间,将自己的生命与教育教学紧紧地连在一起。作为知识,它们根本就不可能以客观的形式被完整传授,它们总有自己的缄默维度,总是与某些人的生活或生命相关联,并在与别的知识共同体的对话或对抗中确认自身。但现在,教师必须切断与学生的情感联系,而且需要切断自己生命的鲜活内核与教育教学的联系。而他们的学生很多也已不可能与他们以及他们的教学活动乃至所学学科本身重建这种联系。他们天生就分属于不同的世界,都是这个世界中的“陌路人”。由于自己不再是学者,他们对知识也失去了应有的敏锐,已经不能展现知识的发现过程,也不能完全明白知识之于学术的意义,因而也避免对知识做个人化的阐述或理解。知识在这里被看成是特异化的东西。杜威(Dewey,J.)所说的“经验的连续不断的改造”在这里是不存在的。一种知识应对一种特定的情境,除此之外别无它用。教师的任务就是教现成的结论,实际上也就是培养作为技术工具的学生。这事实上就是现代学校教育的全部意义。在这里如果有教育创新,那也是因为有很多专业教育学,可以帮助教师应对更抽象、与情境分离更彻底的教学场景。
此前,教师的学识、德性和身份确保了教学过程的流畅性。教师们在这里借助的是一种深层的教育学。这种教育学与后世这种作为超情境的教育教学技巧的专业教育学完全不同。在那里,教育教学与教师生命之间有着更为深沉的联系。而现在,教师自己的生命经验完全独立存在于学科知识和教育教学过程之外。而在教育教学尚未展开之前,人们就已经在观念中建构出了教学过程的全部活动。这是教育基本结构的一项重大变化。它本身不是为了在教师、学生和知识之间形成某种互渗结构,而是致力于将教育教学与个体生命、课题和教学进程分离开来,将师生从前现代社会的那样一种关系结构中解脱出来。贯穿于其中的是一套应对更抽象、与情境分离更彻底的教学场景的教育学。杜威所强调的“教师不是简单地从事于训练一个人,而是从事于适当的社会生活的形成”⑤P17在这里完全失效。人们相信,专业的教育实践比起原来那种深层教育学支撑下的教育实践不但更有条理或计划性,而且还更有预见性。但正确的东西就简单地照着去做,这就是最大的失误。我们的最终目的也许是要培养学生的能动性,为了培养学生的能动性,我们也许确实有许多经验之谈或理论,但照搬这些经验之谈或理论只是避免了我们的明显失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否定了教师的主体性,当然也否定了学生的独特性。我们把学生当作某种抽象群体中的标准件看待,当作被解剖过的被试的同类看待,同时也把教师当成活动的理性执行者看待。如果任由教师和学生彼此借助情境性的对话或互动来探索,他们或许会走一些弯路。但什么是弯路?与最佳路径不同的也许可以说是弯路,但探索、对话和亲历的过程怎么是弯路?但近现代的教师专业化实践却满足于将专业教育学与那种深藏于这样一些过程之中的深层教育学对立起来。其实质,就是关注结果远远多过关注过程,关注教学的工具价值远远多过关注教学对人本身的发展价值,关注有理性能力的人远远多过关注那些试图进一步发展自身的理性能力的人。
二、对技术理性的专业化模式的批判
唐纳德·A.舍恩(Schǒn,D.A.)曾在宽泛的背景上,对这种基于技术理性的专业模式进行了揭露与批判,这种揭露与批判值得我们谨记并扪心自问:
“依据科技理性的模式——专业知识强而有力地塑造着我们对专业的看法,以及研究、教育和实践的体制化关系——专业活动存在于工具性的问题解决活动之中,这些活动因科学理论和技术的运用而有其严谨性。从这种观点来看,虽然所有行业都与从方法到目标的工具性调整有关,却只有‘专业’严格实践了基于专精科学知识的技术性的问题解决。”⑥P19
“如果科技理性的模式,仅出现在意图说明或对专业知识的系统描述之中,我们仍可能对科技理性模式的支配性存在一些疑问。但这个模式同时也镶嵌在专业生命的体制脉络(institutional context)中。在研究与实践的体制化关联之中,以及在专业教育的规范性课程之中,我们都可以明显地看见科技理性的模式。甚至当实践工作者、教育者及研究者在质疑科技理性模式时,他们仍身处那些维持着科技理性的体制之中。”⑥P23
舍恩试图揭示专业实践的真相。在他看来,有能力的实践工作者所知道的通常多于他们所能说的。真正的专业认识是一种实践中的认识(knowing-in-practice)或行动中的反思(reflection-in-action),或者说是一种反思性的实践(reflective practice)。那种基于科技/技术理性(technical rationality)的占支配地位的专业实践解决了眼前的问题,却带来了长远的问题、功能固着的问题和等级化的问题。⑥P19~59这就是一种意义的丧失,这种意义的丧失是从将我们与知识乃至于与客观世界分割开来开始的。这种分割最终导致了我们彼此之间的分割与对立。我们在各种事物之间建立了人为的界线,将所有外在于我们的世界都界定为对象世界,最终,将我们自己紧紧地封闭在自己的内心。就像托克维尔所说的那样,“民主把一个人永远地抛回给他自己,最终将他完全禁锢在内心的孤独里。”⑦P26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客观认识这个世界,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这种专业化其实也是一种浪漫化。这种看来是技术主义的东西,与浪漫主义不是对立的。事实上,任何一种东西,都有其形而上的、浪漫的维度。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技术主义是很浪漫的。技术主义比浪漫主义、比我们在本文中可能透露出来的那样一点点浪漫主义浪漫得多。技术主义它认为,我们可以有一套标准的东西、一套规范的东西、一套专业的知识或技术,可以适应于所有的人和事,可以战胜我们的天性,可以战胜知识的天性,也已压抑和遮蔽我们自己所有的东西。在这样一个专业化的世界中,人们只能从结果与旁观中受益,根本不能参与其中,感受不到过程之中本应有的快乐,除非你自己将远距离学习接纳别人整理出来的这些专业知识本身看成是一种快乐。由此构建的近乎一个机械的世界,我们只有从物质消费中才能获得暂时的解脱与满足。
而且在技术主义的浪漫实践中,我们事实上看到的,并不是技术主义所想象的那样一套东西。技术主义并没有造就我们今天所说的那样一种熟练、专业的教师。事实上教师们通常有两套话语,而且这两套话语都不健全。一套是专业性的话语,他们有那样一些组织教学或沟通的专业化技巧。但他们经常忍不住地要流露出自己的个性,经常要忍不住地表达自我。所以在一个需要我们普度众生的公共的课堂空间中间,他们总是被少数人所左右,总是被少数亮晶晶的眼睛所吸引。我们很多的时候对学校有一些虚幻的假设,有一些虚幻的判断,总觉得我们学校是在传递一套精英的文化,在传递一套规范的文化。事实上教师在学校生活中传递的是五花八门、因对象而异的东西。在这样一种情境中间,我们老师的教学,我曾经称之为“随意随性的教学”。⑧在一个需要专业素养的课堂空间,他们并没有或不能完整地推行那样一套专业的技巧。我们有的时候去听课,可以发现这个老师很可爱,经常真情流露。他的喜怒哀乐皆形于色,吹胡子瞪眼睛流露的就是他真心的那一面。这一面对于学生有什么影响呢?有些学生非常喜欢,有些学生非常讨厌。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跟有些学生不是生活在同一个世界,我们很多的时候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这个就是技术主义的真相。
因此,技术主义并没有造就一个专业的实践,也没有造就一个专业的教师。技术主义只是把我们很多的东西给遮蔽了。但我们本身的力量、我们的个性、我们的人格和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肤色和我们的发型都在说话,虽然是在暗中说话,但它们始终是在跟这一套建基于技术主义的东西在冲突。技术主义的浪漫是一种特定类型的浪漫,它没有在这样一个技术主义的时代真正取得成功。而且技术主义的浪漫是少数人的浪漫,它不是试图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浪漫。它是专家的浪漫、精英的浪漫、上层的浪漫和领袖的浪漫。而对于我们所流露的那种浪漫的东西来说,它实实在在地,其实是每一个人试图自我确认、自我表达、需要得到认同、需要借助于已有的东西、借助于自己的天性和人格、借助于自己的学识来跟学生沟通的东西,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要求。但我们现在很多的时候,这一套东西都需要遮蔽,所以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实践中间,就造成了这样一些内在的分裂。要做到我们所推崇的那些东西,其实并不是需要一个很浪漫的环境,它只是需要一个很宽松、很自由、很平和、很民主的一个环境。整个的民主化的进程跟我们自身的复兴,跟我们个人的成长,跟我们内在的觉醒是同步的。当然它很浪漫,只是因为我们缺这些东西,不是因为我们没办法走到这一步。
三、教学内容知识的概念及其问题
今天的一种教师专业发展理论试图提升教师、学生乃至课题因素在教育教学中的地位。为此,它试图强调教师对现有知识——既包括教学知识(专业教育学或教学法),也包括内容知识(教学内容)——的改造,而且强调这种改造活动的实践或情境性质。在这里,教学过程不再是按照外在的专业教育学行动的技术过程,而是在情境中实现对教学知识和内容知识的整合过程。借此,它强调了教师的个人经验或个人理论,发现了教学内容知识(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简称PCK)——教学知识和内容知识的实践结合——的独特地位。⑨⑩按照这种教师专业发展理论,专业的教师并非单纯受到良好学科与教育学训练的新手,而是那种能将教学知识与内容知识有机结合的“专家教师”。而新手教师虽然大量拥有这两种知识,但在实践中需要对它们临时组合,因而经常挂一漏万,并不能发挥所有知识的教育力量,常常陷于有力使不出的尴尬境地。与此相适应的新的教师专业发展体系,强调教育实践、教师发展学校和大学-中小学联合的价值。其目的,就是试图通过系统的实践,实现对教学知识和内容知识的实践整合。利伯曼(Lieberman A.)所推崇的“扩展的专业发展观”(broader conceptions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就强调不仅要在学校之外通过课程、通过工作坊及通过会议学习,而且应在学校中通过同伴辅导、经验分享、个案研究,及在学校外通过网络、伙伴和合作等多种非正式学习渠道推进教师的专业发展。(11)
但即便对教师专业发展的这种全新的制度化改造依然存在着难以弥补的缺陷。教学内容知识虽然是一种全新的知识类型,但始终建立在专业教育学和学科内容知识的基础之上,最多是再增添了一个情境性知识的元素。在这里,教师的主体性依然不是体现为其对内容知识的独特理解,也不是体现为其将一种新的教育学形式纳入了教学实践。学科知识以及教师本身所承载的深层的教育学在这里依然居于教师专业发展体系之外。这样培养出来的教师被认为已不再是单纯的技术熟练者,但他们与“技术熟练者”之间的区分又在哪里呢?他们已经有反思,但他们只是反思教学,而且只是以一种客观中立的态度反思教学,他们依然没能在自己的心灵、知识的本性与课堂教学实践之间建立起深层的联系,教学在这里依然只是一种技术过程,而不是一种生命或社会生活实践。当然,新的教师专业发展体系更多强调了教学经验的价值,但经验在这里依然只是技术的一个要素。这样的训练或者磨炼,能弥补教师对知识的独特理解不足的缺陷吗?能引导教学走向一个新的教育境界吗?教学活动本身能成为一种创造性的教育实践吗?不可能,因为教育教学依然取决于教师个人的知识、经验和教育学训练,这本身不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只有单一的变化源泉,只能从这一专业发展体系中汲取能量,而这一专业发展体系又只能从其上位体系中汲取能量。当然,教师个人已经成了一个重要的源头活水,因为他们能提供宝贵的经验。但如此依赖于个人经验的体系不仍是缺乏活力的体系么?而且,纯粹的教学经验对于教育教学的意义显然被高估了。重要的不是这些经验,也不是被剥离了教育意义的学科知识,或脱离了教育活动主体的个人身份与人格魅力的教育学,重要的是将教育教学建立在深层教育学的基础之上。
我们认为,在卢梭(Rousseau,J.)下述很少被关注的观点中,包含着他某些最卓越的教育思想:
“一个孩子的教师应该是年轻的,而且,一个聪慧的能够多么年轻就多么年轻。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他本人就是一个孩子,希望他能够成为他的学生的伙伴,在分享他的欢乐的过程中赢得他的信任。在儿童和成年人之间共同的地方不多,所以在这个距离上永远不能形成十分牢固的情谊。孩子们有时候虽然恭维老年人,但从来是不喜欢他们的。”
“人们也许希望他的教师曾经是教过一次学生的,这个希望是太大了;同一个人只能够教一次学生,如果说需要教两次才能教得好的话,那么他凭什么权利去教第一次呢?”(12)P30
“你把教师和导师加以区别,这又是一种愚蠢的想法!你还区别不区别门徒和学生呢?只有一门学科是必须要教给孩子的:这门学科就是做人的天职。这门学科是一个整体,不管色诺芬(Xenophon)对波斯人的教育说了些什么,反正这门学科是不可分割的。此外,我宁愿把有这种知识的老师称为导师而不称为教师,因为问题不在于要他拿什么东西去教孩子,而是要他指导孩子怎样做人。他的责任不是教给孩子们以行为的准绳,他的责任是促使他们去发现这些准绳。”(12)P31
卢梭在别的地方也强调过一些与此类似的观点,如“用热心去弥补才能,是胜过用才能去弥补热心的”,又如“我甚至希望学生和教师也这样把他们自己看作是不可分离的,把他们一生的命运始终作为他们之间共同的目标”。(12)P26,33我们究竟该怎样来理解卢梭这些话的意义呢?如果不是被表面上的一些东西所迷惑,那么应该能够认识到:教育力量的根基不在教师能教学生什么东西,也不在他能否以最有效的方式让学生记住某些结论,而在他与学生的关系结构——这种关系结构既体现在他与学生的相互认同,也体现在他与学生之间的那样一种毫无预设的开放性的探索状态之中——只有这种关系才能导向杜威所说的那种经验的连续不断的改造。教师不应拿一套现成的东西去教学生,他甚至也不知道自己有这样一套现成的东西,他真正需要的是一种探究的态度和能力。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并不是字面上的教师,而是卢梭所说的“导师”。导师和教师的区分,就在于前者能引导我们走向真理,而后者则只能教我们真理。这不禁让人想起了第斯多惠。他说:“一个坏的老师奉送真理,一个好的老师则教人发现真理。”真正优秀的教师可能像孔子一样,最初的时候“空空如也”,但待得叩其两端则昭然若揭,他们就在与学生互动的过程中悟道助人。这样,他们既解决了学生的困扰,又将思维或探索的过程展现在学生面前,实际上也是将一个真实的自我呈现出来。这也就是舍恩所说的专业工作者真正的品质——行动中反思。这种过程最具教育意义。这当然不是说我们教师任何时候都应当“空空如也”,但教师最好的品质却是有这样一种“无中生有”或“行动中反思”的能力。事实上,如果我们的任务是做事,我们就需要将最有效的手段和程序明确地传播开去。但如果我们的任务是育人,我们从一开始就需要将对教师和学生的尊重摆在我们教育学的第一位,或者说,摆在教师专业发展实践的第一位。这样一来,重要的就不是能教给他们结论,而是有能力与他们建立一种最有教益的关系。
四、兼容创新精神的专业发展道路
正是在教育性关系的建构方面,显示了近现代专业教育学的限度。它不但不能够很好地尊重学生,也不能够很好地尊重教师,也不是倡导在师生之间建立这样一种关系结构,而只是试图赋予教师一种清晰表达与合理组织的能力。受这种思想观念的支配,现有的专业发展体系,主要就是一套技术功能论的体系。这种体系不尊重个人本原的主体性,而是试图在个人身上再造主体性。人本身在这里不是被作为主体看待,而是被作为再造主体的原料看待。只有通过别人的再造他们才被承认为主体。然而经过这样的培训,我们的教师拥有的只是教常规科学的能力。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样的教师教育,致力于培养的是教师教常规科学的能力。我们这个社会对数学的关注,在很大意义上就是对常规科学的关注。数学中的解题,按照库恩(Kuhn,T.S.)的见解,就是一种最为典型的常规活动。而“解答常规研究问题,即以一种新的方式实现预期”。(13)P33数学经常被认为是对思维的训练。但我们的数学教学,经常是对常规思维的训练,是对技巧和逻辑推理、论证的训练。这种训练培养的,是猜谜或解题的常规能力。这种数学始终只能是一种工具,而不是全部的思维体操。如果它还称得上思维的体操,那也只是一种常规思维的体操。题目已经给出来了,事实上也已经预设了答案,这时需要的就是扫尾工作——解题的思路和技巧。在其他更为开放的学科或课程中,我们本可以发现一种与波普尔(Popper,K.)所说的猜测与反驳更为接近的思维活动。但很显然,我们的一切知识和教学似乎都已经常规化了,我们只能在题目所设定的范围内行动。这一范式下成长起来的专业化的教师能带来何种教育创新?
在近现代的专业教育学不断强调自身的教育功能的时候,韦伯(Weber,M.)对创新精神(资本主义精神)却做了一番完全不同的解释。在韦伯看来,近代雇主为从其雇佣者那里获取最大可能的劳动量,所使用的技术手段之一是计件工价(piecerate)的方法。但提高计件工价常常招致这样的后果:在同一时间内做完的活儿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因为劳动者对工价提高的反应不是增多而是减少其工作量,毕竟,挣得多一些并不比干得少一些来得那样诱人。人并非“天生”希望多多地挣钱,他只是希望像他已经习惯的那样生活,挣得为此目的必须挣到的那些钱。无论如何,只要近代资本主义通过提高劳动强度而开始提高人的劳动生产率,它就必然会遭到来自前资本主义劳动的这一主要特征的极其顽固的抵制。由于这样,资本主义从它一开始起步,就一再地采取减少工资的方法。即减少劳动者的工资,迫使他们付出更多的劳动以挣得与先前数目相同的工资。但是,这种表面上非常有效的方法,其效能实际上也是有限的。它阻滞了质的发展,尤其阻滞了向使用更高劳动强度的企业类型的过渡。(14)P19~20因为“即便是从纯商业的角度来看,如果生产的商品需要任何一种熟练劳动,或者需要使用易于损坏的机器,或一般地讲,如果需要高度的专注和创新精神,那么,低工资的方法就必定要失败……因为,在这里,不仅高度的责任心是绝对必不可少的,而且,一般地讲,至少在劳动时间内容不得半分的分心,来计算怎样才能最省事最省力地挣得已经习惯的工资。相反,劳动必须是被当作一种绝对的自身目的,当作一项天职来从事。”(14)P21因此:
“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相反的情况则是违背事实的。但它的出现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各种怀疑、仇恨甚至道德义愤总是滔滔不绝地涌向第一个革新者。人们还千篇一律地——这类事例我略知几个——捏造出一些关于他从前生活的隐私污点的传说。只有超乎寻常的坚强性格才能使这样一个新型的企业家不至丧失适度的自我控制,才能使他免遭道德上和经济上的毁灭。否认这一事实当然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而且,只是因为这种新型的企业家具有确定不疑且是高度发达的伦理品质,以及洞若观火的远见和行动的能力,他才在顾客和工人中间赢得了不可缺少的信任。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能够给予他克服重重障碍的力量,更重要的是,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能够使他承担起近代企业家必须承担的无比繁重的工作。”(14)P25~26
在此我们不多评价韦伯有关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对资本主义扩张的意义的看法,在我们看来这其实是与真正起作用的资本主义精神互为因果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他对资本主义精神本身性质与起源的认识。在韦伯看来,“这样一种态度绝对不是天然的产物。它是不能单凭低工资或高工资刺激起来的,它只能是长期而艰苦的教育的结果。”(14)P21而韦伯所说的教育,“在这里是家族共同体和父母家庭的宗教气氛所首肯的那种教育类型”(14)P5,而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学校教育。在韦伯看来,“根据人种学的全部经验,革新的最重要的源泉似乎是个人的影响,他们肯定有过某些形式的‘不正常的’经历(从今天的治疗学的观点看,把它们评价为‘病源’并非罕见——然而也并不总是或者经常这样评估),并且拥有受这些经历制约的、影响他人的能力。”(15)358而“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在宗教教育的背景下最有可能战胜传统主义”。(14)P11,22韦伯所说的宗教就是那种“要求伦理认可的确定生活准则”的宗教,或者更确切地说,就是那种有着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当然,对韦伯来说,今天已经不存在把获取财富的生活方式与任何单一世界观进行必要联系的问题了,或者说,资本主义制度已经不再求助于任何宗教力量的支持了。但是所有这些都是近代资本主义在它已经取得了支配地位,已经摆脱了旧有支柱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现象。而在此之前,资本主义精神的出现是以其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这种有节制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14)P28,9正因为如此,韦伯强调道:
“事实上,这种伦理所宣扬的至善——尽可能多地挣钱,是和那种严格避免任凭本能冲动享受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因而首先就是完全没有幸福主义的(更不必说享乐主义的)成分掺在其中。这种至善被如此单纯地认为是目的本身,以致从对于个人的幸福或功利的角度来看,它显得是完全先验的和绝对非理性的。人竟被赚钱动机所左右,把获利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在经济上获利不再从属于满足自己物质需要的手段了。这种对我们所认为的自然关系的颠倒,从一种素朴的观点来看是极其非理性的,但它却显然是资本主义的一条首要原则,正如对于没有受到资本主义影响的诸民族来说这条原则是闻所未闻的一样确定无疑。”(14)P15
比韦伯稍后的熊彼特(Schumpeter,J.A.)虽然不像他这样将企业家理解成宗教教育的产物和天职的捍卫者,但他也认为,企业家所特有的动机毫无享乐主义一类的意味,他们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经济人。恰恰相反,他们的动机倒是表现出了如下三种非享乐主义的特质:首先,存在有一种梦想和意志,要去找到一个私人王国,通过工业或者商业上的成功,他们在这里可以达到的地位是现代人可能达到的最接近于中世纪的封建贵族领主的那种地位,由此带来的权力和独立的感觉,并不由于这两者主要是一种幻想而有丝毫的损失;其次,存在有一种征服的意志或战斗的冲动,一种证明自己比别人优越的冲动,一种追求成功本身而不是为了成功果实的强劲动力;最后,存在有创造的快乐,把事情办成的快乐,或者只是施展个人的能力和智慧的快乐。(16)p102~104正因为如此,企业家不愿适应环境,而力图创造性地破坏市场均衡:
“典型的企业家,比起其他类型的人来,是更加以自我为中心的,因为他比起其他类型的人来,不那么依靠传统和社会关系:因为他的独特任务——从理论上讲以及从历史上讲——恰恰在于打破旧传统,创造新传统。虽然这一点主要是适用于他的经济行动上,但也可以推广应用于他的经济行动的道德上、文化上和社会上的后果。”(16)P102
韦伯和熊彼特的研究对我们的启示,首先在于他们都强调一种基于个人品性或信仰的特质在创新中的重要作用,而且这种品性看起来还不可能是专业的教育培训的结果(韦伯更是明确地否定这一点)。而我们今天的专业教育学却并不关心这种来自个人生活及其人格本身的力量,反而千方百计将教育教学与这种深层的教育学划清界限。因此,如果说我们今天还有信念,那就是一种对知识的信念、一种对非个人关系的信念、一种对就事论事的工作态度的信念。说到底,这只是一种对于技术(包括制度技术)的信念,而不是对于那种深藏在我们本身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中的教育力量的信念。其次,韦伯和熊彼特的研究都揭示出,创新与其说是在完成既定的甚至社会公认的技术目标的过程中实现的,不如说是在实现某种亚文化群体的天职或使命感的过程中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创新对创新行动者看来不但可能显得不是新的,在很大意义上还可能就是传统的。因为这一创新过程不是对自我的否定,而是以自我为根基的重建。最后,他们对企业家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还都表明,创新不是一个本来就预计好的事情,也不是以成败论英雄的。韦伯自己就曾明确指出:“宗教改革的文化后果在很大程度上,大概在我们重点研究的这些方面,是改革家们未曾料到的,甚至是不想达到的。这些结果往往同他们本人所想要达到的目的相去甚远,甚至相反。”(14)P41而那些致力于将挣钱变成一种天职的清教徒们最终创造了一种“铁笼”体制,这一点显然也出乎他们的意料。而现代的专业教育学将教育创新看成专业教育者的理性成就,这是非常单纯的。
五、基于深层教育学的专业发展体系
今天,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在清晰地认识和表达我们见解的能力之外,我们还拥有另外一种缄默地认识的能力。而且在这两种不同的能力之间,后一种更为关键。它不但构成了前一种能力的基础,很多时候就是后一种能力帮助我们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波兰尼(Polanyi,M.)就认为,在追求和表述科学的过程中,我们通常所使用的测量、计算和代数公式当然是不可或缺的,但外显思维唯有靠一种缄默的运演方能得到发展和理解。因而,它完全是建立在缄默认识的基础之上的。说到底,“所有知识要么是缄默的,要么根源于缄默认识之中。”(17)P137专业教育学也是这样建立在缄默认识的基础之上的。看起来我们将一切都规范化、显性化、理性化了,但经验的事实表明,“亲其师,信其道”的传统教育的铁律,在这里依然起着重要作用。而且,教师以不同的精神状态投入教育教学,绝对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教育效果。此外,即便在教师们看起来确实像是专业教师的条件下,在内心他们还是他自己。他们总是试图在课堂中间寻找自己的有缘人,或者总是被少数有缘学生的问题引向“歧途”,而且似乎只有在这里他们才能感受到自己的真正价值。波兰尼满怀欣喜地写道:
“不要痛惜关于外部实在的陈述有不确定的内容,我们能够引以为豪的是,我们能够因此而看到既定事实以外的东西;不要懊悔我们不能界定自然界中一致性的品质,我们能够为有感受实在的那些微妙的、实际上看不见的信号的才能而心满意足。不必为我们不能陈述经验知识的所有依据而难受,我们能够坚决认为我们有知道远远超过我们能够告知的东西的力量。一旦我们承认缄默的认识是所有经验知识的合理的而且事实上必不可少的根源,这些就的确是我们将需要的能力。”(17)P126
对帕克·帕尔默(Palmer,P.)而言,缄默的教育力量无处不在。他曾引用别人的诗歌来暗示这一点:“一切可见的事物,/都蕴藏着:/看不见的富足,/黯淡了的光,/谦恭的无名,/隐性的完整。/这神妙谐美的凝聚和完整,/是智慧,是万物之母,/是创造万物之灵!”(18)P63他不断要求我们全面认识世界。但他最为关注的,还是根源于每一个教师的心灵的力量。帕尔默认为,就像任何真实的人类活动一样,教学不论好坏都发自内心世界。我在教室里体验到的纠缠不清只不过是折射了我内心生活中的交错盘绕。认识学生和学科主要依赖于关于自我的知识。这种“认识你自己”的要求既不是自私也不是自恋。作为教师,无论我们获得哪方面有关自我的知识,都有益于更好地服务于教学和学术。优秀教师需要自我的知识,这是隐蔽在朴实见解中的奥秘。(18)P3然而,在匆忙的教育改革中,我们忘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如果我们继续让称职的教师所如此依赖的意义和心灵缺失,仅仅依靠增加拨款额、重组学校结构、重新编制课程以及修改教科书,改革永远不能够成功。教师确实应该得到更多的补偿,从官僚制度的困扰中解脱出来;我们应赋予其学术管理方面的职责,为他们提供尽可能好的方法与材料。但是,如果我们不能珍惜以及激励作为优秀教学之源泉的人的心灵,提供上述所有这一切都不能改变教育。(18)P4因此,在他看来,真正好的教学不能降低到技术层面,真正好的教学来自于教师的自身认同与自身完整。(18)P10下面这段文字更是他的点睛之笔:
“……不好的老师把自己置身于他正在教的科目之外——在此过程中,也远离了学生。而好老师则在生活中将自己、教学科目和学生联合起来。”
“好的老师具有联合能力。他们能够将自己、所教学科和他们的学生编织成复杂的联系网,以便学生能够学会去编织一个他们自己的世界。这些编织者用的方法不尽相同:讲授法,苏格拉底式的对话,实验室试验,协作解决问题,有创造性的小发明。好老师形成的联合不在于他们的方法,而在于他们的心灵——这里的心灵是取它古代的含义,是人类自身中整合智能、情感、精神和意志的所在。”
“当优秀教师把他们和学生与学科结合在一起编织生活时,那么他们的心灵就是织布机,针线在这里牵引,力在这里绷紧,线梭子在这里转动,从而生活的方方面面被精密地编织伸展。毫不奇怪,教学牵动着教师的心,打开教师的心,甚至伤了教师的心——越热爱教学的老师,可能就越伤心!教学的勇气就在于有勇气保持心灵的开放,即使力不从心仍然能够坚持,那样,教师、学生和学科才能被编织到学习和生活所需要的共同体结构中。”(18)P11
那么,什么才是专业的教育实践呢?至少,我们现在已经能够区分出两种不同的专业实践形态。一种专业的教育实践强调专业教育学的学习和实践。另一种则强调深层教育学的意义。(19)前一种专业发展体系看起来解决了眼前的问题,适应了滕尼斯(Tǒnnies,F.)所说的从共同体到社会的那样一场结构性转型,但却带来了更为深层的问题,那就是教育者的日常生活与个人人格本身所蕴含的教育力量被排除在专业的教育教学过程之外,传统共同体的教育力量被驱逐出正规教育过程,教师与学生的亲密关系被一种对事不对人的工作关系所取代,知识本身的魅力也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人们的缄默认识能力被严重忽视,不单纯学生,就是教育者本身也成了专业教育学改造的对象。这样一来,它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长远的问题。教育创新在这里只能依赖于一种工具或技术理性,而且只能在既定目标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创新过程就这样等同了科恩所说的猜谜、问题解答或解题过程,对问题本身的设定则被排除在了创新行动之外,只有少数的精英或特权人士才能涉足这一领域。在这样的专业实践中,教师们只需要know how(how to teach),外加在最粗浅的意义上 know what(即知道结论,而且屈从于已有的认识),不需要know why(实际上是另一种全新的意义上的 know how[how to think/create/construct])。近现代学校的教学组织使得对这种专业教育学的需求激增,但教育教学在根本上还是需要建立在我们所说的深层教育学的基础之上。为此,我们一方面要在学校内部推行一种更自由也更亲密的师生组合方式和更具探究取向的教育教学范式,将教育教学更好地建立在深层教育学的基础之上,大力提升中小学教师的学术声誉,将更多的优秀人才引向教育教学的第一线,打破中小学与大学在文化上的二元对立;另一方面,在教师专业发展的外部体系的建构上,我们要更好地推行导师制,加大学术研究在专业发展中的比重,加强师生学术共同体的建设,加强大学与中小学的联系,同时倡导一种更为单纯、宽松、平等的学术氛围。只有这样,才能将教育教学建成一种令人上进与幸福的职业。
注释:
①李泽厚.《论语》今读[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②康永久.魅力、情境与教育学——教师专业化之历史反思与重构[J].教育资料与研究(双月刊)(台北),2010,96(5):117-146.
③[美]哈斯金斯.大学的兴起[M].王建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④[法]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M].李康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⑤[美]杜威.我的教育信条[A]//[美]杜威.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C].赵祥麟,任钟印,吴志宏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⑥[美]舍恩.反映的实践者——专业工作者如何在行动中思考[M].夏林清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
⑦刘瑜.民主的细节——美国当代政治观察随笔[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⑧康永久.随意随性的教学[N].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12-1(8).
⑨Shulman,L.S.(1986).Those Who Understand:Know-
ledge Growth in Teaching[J].Educational Researcher,Vol.15,No.4,pp.4-14.
(10)Shulman,L.S.(1987).Knowledge and Teaching:Foundations of the New Reform[J].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Vol.57, No.1,pp.1-21.
(11)Lieberman A.(1995).Practices that Support Teacher Development:Transforming Conceptions of Professional Learning[A]//Westat,Inc.(1995).Innovationg and Evaluating Science Education:NSF Evaluation Forums(1992-94)[C].pp.67-78.http://www.nsf.gov/pubs/1995/nsf95162/nsf_ef.pdf.
(12)[法]卢梭.爱弥儿——论教育(上)[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13)[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4)[德]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修订版)[M].于晓,陈维刚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15)[德]韦伯.经济与社会(上)[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16)[美]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何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17)[英]波兰尼.缄默的认识[A]//施良方,唐晓杰.教育学文集:智育[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18)[美]帕尔默.教学勇气:漫步教师心灵[M].吴国珍,余巍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9)康永久.教师知识的制度维度[J].教育学报,2008(3):54-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