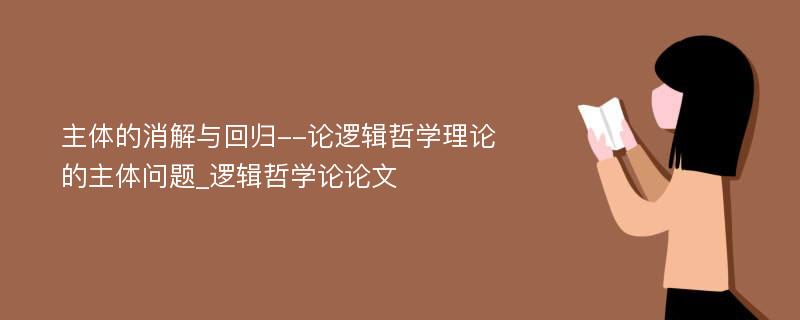
主体的消解与复归——论《逻辑哲学论》的主体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体论文,逻辑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内学术界有关《逻辑哲学论》的介绍已为数可观,维特根斯坦研究成了又一“热点”。不少青年学者凭借外语方面一技之长率先引进维氏之说,从之者竞相传抄,颇有“生吞活剥”之势。从某种意义上说,以拾人牙慧为本,以著书“立说”为荣,已成为今日某些学术领域的一种时髦“景观”。在这种情势下,有必要对维特根斯坦作些认真的研究。本文论涉《逻辑哲学论》的主体问题,并非侈言“救弊”,而只是对这个重要概念作一些探讨。
一
主体(subject)、形而上学主体(metaphysical subject)或我(1)这个概念是《逻辑哲学论》中许多令人困惑的概念之一。这个“我”与维特根斯坦论涉的“唯我论”相联系,但又与之有很大区别。《逻辑哲学论》的“哲学的我”肯定不是传统唯我论所说的那个“我”,但也不是笛卡尔不断怀疑的自我或康德为自然立法的主体。事实上,维特根斯坦的反心理主义倾向和实在论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使他消解了主体,但是在涉及生活的意义和价值问题时,他又引进了主体。这虽然使《逻辑哲学论》中的主体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但这却是整个问题的关键之点。只有牢牢抓住这一点,结合《逻辑哲学论》与《1914—1916年笔记》的具体内容,才能发现维特根斯坦赋予主体这一概念的重要内涵及其意义,从而理解《逻辑哲学论》后半部分的所谓“神秘主义”,并对它的哲学精神有较为深入的体验。
在对维特根斯坦所作的大量评论中,一般倾向于将《逻辑哲学论》的主体问题视为一种唯我论。但这却是一种误解。由于维特根斯坦说过唯我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一种正确的理论,对这句话的误读,使得维特根斯坦被描绘为一个唯我论者。
《逻辑哲学论》中的唯我论问题相当复杂,而且与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的见解密切相关。不了解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批判理论,就不可能理解他的主体概念。大卫·皮尔斯认为,一个相当流行的错误信念是以为维特根斯坦承认是一个唯我论者,这个信念的结果导致了对其哲学的错误解释(False Prison,P188,Oxford,1968)。在皮尔斯看来,维特根斯坦是把唯我论作为强加于语言的人为限制(personal limit)的失败尝试而引进《逻辑哲学论》的,他将它处理成一个自我中心的(egocentric)界限。这样,维特根斯坦把唯我论作为一个界限从而将其要求从事实语言(discourse)中排除出去,同时作为形而上学的主体,在描述世界的语言的某些方面显示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唯我论的有些东西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所说的主体,不是个人化的主体,而是世界的某种界限(Ibid,P153-167)。
皮尔斯对维特根斯坦的主体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揭示出它的某些特点,但是他没有更进一步揭示出维特根斯坦的主体概念所蕴含的深刻意义。皮尔斯的观点在西方学术界有一定的代表性,有为数不少的西方学者把维特根斯坦仅仅看作纯粹的分析哲学家,对其主体观存而不论。即使论及主体,也大多像皮尔斯那样,不把它看作《逻辑哲学论》以至整个前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的要害概念,因而难以把《逻辑哲学论》中逻辑的部分和所谓“神秘主义”部分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从而把握它的哲学趣旨。
维特根斯坦是在谈论语言的界限也即世界的界限时引入唯我论的。逻辑揭示了广阔的逻辑空间。逻辑充满了世界,世界的界限也即逻辑的界限。世界由事实的总和所构成,事实被命题所描述,命题的总和构成了语言,语言的界限意谓着世界的界限,“我”的语言的界限意谓着“我”的世界的界限。然后,维特根斯坦肯定了唯我论:
5.62 这段评论为唯我论中有多少真理这个问题提供了钥匙。
唯我论意谓的东西是完全正确的,只是它不可说,而只能自己显示出来(makes itself manifest)。
世界是我的世界,这在语言(我懂得的唯一的语言)的界限意谓我世界的界限这一事实中显示出来。
5.63 我是我的世界(小宇宙)。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London,1961。下引此书,不注书名)
显而易见,维特根斯坦是把唯我论的我作为一种“界限”来看待的。如果说唯我论是正确的,那么它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我”作为一个界限实际和我的语言是同一的。不能离开语言去评论这个我。
根据维特根斯坦的理解,语言的本质在于描述实在,其特性反映了世界的逻辑特性。语言中的语词必须意谓对象(object),这是语言成为语言并且具有意义的关键所在。语词相互联结的形式(form)正是世界中对象的配置形式,这是语言和实在共有的逻辑形式。任何一种语言,只要它是一种语言,就一定具有这种形式。人虽然有构造语言的能力,但人无论如何不能创造逻辑形式。正是这种作为世界实体(substance)的对象的配置形式亦即逻辑形式,决定了语言和语言的使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能非逻辑地思考,也不能“说”(表达)不能思考的东西。无论谁使用语言,只要他是在有意义地使用语言,他都必须选择以“对象”为其确定意谓的语词,并遵从语言和实在所共有的逻辑形式。语言描述实在,我们虽然使用语言,但语言绝对不是任意的。
这种对待语言的看法是典型的本质主义观点。但实际的状况是,语言总是使用中的语言,因此它不仅仅是本质性的,同时也具有工具性、功能性。这是维特根斯坦在后期的《哲学研究》中充分发挥的观点。在《逻辑哲学论》中,他主要从本质主义的角度来限制语言。但语言总是处于使用之中这一事实使维特根斯坦引进了唯我论,这也埋下了他后期反叛自己前期的种子。但是他的唯我论不是我们熟知的任何一种唯我论。语言总是处于使用之中这个事实意味着“我”的存在,因此一种唯我论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唯我论的“我”不论以何种形式出现,不论是作为“我”还是作为“我们”,都必须受到世界中对象的配置形式即逻辑形式的制约。“我”与其说是加于语言的一个限制(Limit),不如说是与语言同格:
5.64 从这里可以看出,严格贯彻了的唯我论与纯粹的实在论相一致。唯我论的我缩为一个无广延的点,而与其一致的实在则保持不变。
从这种实在论的观点看,“我的语言”与描述实在的“事实性语言”是一致的。唯我论的我,无论作为什么样的主体出现,都不能违反逻辑。因此,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是语言的界限,亦即世界的界限。维特根斯坦在肯定唯我论时虽然引进了主体,但他同时也消解了这样的主体。我作为主体,其含义只不过表明那是一个界限而已。
二
“我”作为一种界限从世界中消失,并因此进入哲学。这样的“我”,即哲学的我,不是世界中的一个对象,而是形而上学主体。
哲学的我不是人,不是人的肉体或具有心理学属性的人的灵魂,而是形而上学的主体,世界的界限(而非世界的一个部分)。然而,人的肉体,特别是我的肉体,在其它东西中间,在动物、植物、石头等等之间,是世界的一个部分。
无论谁,只要认识了这一点,就不会要为他自己的肉体或人类的肉体取得一个优越的地位。
他将非常朴实地视人和动物为相似对象而把它们归为一起。
(Notebooks,1914-1916,Blakwell,1961。下引此书均简称NB。P82)
因此,哲学的我不是一个个体,或人们所谓的灵魂。但是这个主体也不是传统哲学中所说的主体或笛卡尔意义上的那种思维的自我。在维特根斯坦看来,那样的东西是不存在的。
5.631 没有思维或拥有观念(thinks or entertains ideas)的主体那样的东西。
如果我写一本叫作《我发现的世界》的书,我必须说到我的身体,说到哪些肢体服从和哪些肢体不服从我的意志等等。这是孤立主体的一种方法,或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在重要的意义上表明没有主体的方法;就是说,唯独对于主体,书中是不能提到的。
因此,把主体、自我看作一个内省的实体是一个错误。唯心主义者强调自我的独特地位,把实在作为思想的对象,相信实在因为我们的思想而被改变。维特根斯坦早在评论柯菲《逻辑学》的短文中,就断然否定了这样的主体。与此相关的是传统唯我论所说的主体。那种唯我论把一切存在的东西都当作我心灵的一个部分,唯有我及我的心灵是真正的存在,其余的一切不过是它的内容。很显然,当维特根斯坦说唯我论的有些东西是正确的时,他指的不是这种唯我论。如果说《逻辑哲学论》在某种意义上肯定了唯我论,那么,它肯定的是被维特根斯坦修正过的唯我论。当他使用这个概念时,他赋予它十分不同的涵义。皮尔斯断言,在这一方面,维特根斯坦受到罗素独创性观点的强烈影响。罗素肯定唯我论者不仅对他的真理的知识,而且对他亲知的对象设立界限,因此对他的语言设了界限(On the Nature of Acquaintance in Logic and Knowledge,P130-134)。原因在于他有意义的语言的范围(Scope)被语言建基其上的亲知对象的范围所决定。但与罗素不同的是,维特根斯坦拒绝将唯我论视为一种可能真的理论。他认为它是一个形而上学理论,一个不能用事实语言表达的真正的洞见(False Prison,P34)。
对唯我论说来,一个意识主体是必不可少的,存在的一切都是这个意识主体的内容。维特根斯坦对唯我论的修正就是取消了这个意识主体,它不在世界中,又不与世界中的任何东西相联系。唯我论者主张中的一切内容即被排除,只剩下一个语言主体。这个主体失去了传统哲学中主体这个概念所具有的意义,因为它成了被世界中对象的配置所限定的东西。这种主体观很容易使人想到休谟。休谟认为唯我论者希望发现意识主体,一个自我,但是他只发现越来越多的对象,却从来没有发现有任何主体(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Iiv.6)。但与此不同的是,维特根斯坦淘空了主体的内容,却保留了它的形式。这个主体因此仅仅成为语言主体,并且是必不可少的。即便如此,它还是失去了昔日的光辉,只是一个被动的主体。
维特根斯坦从对世界进行解构开始,逐步地揭示出语言的本质。语言之所以能够描述实在,原因在于它与世界同构,共同具有逻辑形式。语言的界限于是意谓着世界的界限,而语言由于实际上被运用就成为“我的语言”,我的语言的界限则因此意谓世界的界限。
“界限”是至关重要一个概念。它不是像一个栅栏或一堵墙那样的东西,我们既可以跨越,又可以回过头来观看我们究竟到了何处。维特根斯坦的“界限”是不能跨越的东西,它表明的是这个事实的世界的最终疆界。但是这个隐喻毕竟暗示出“界限”之外的某种东西,那是有关意义和价值的东西,是主体的世界。因此,维特根斯坦的主体于是从世界中分离出来,作为一种界限从事实的世界消失,并因此进入“哲学”。
三
主体,被维特根斯坦称为哲学的我,不是人,不是人的肉体或心理学所处理的人的灵魂,而是形而上学的主体,即世界的界限而非世界的一个部分。在哲学里必须以非心理学的方式谈论自我。自我不是思维的、表象的主体,而是一种“意志的主体”。这个主体、自我要解决的是生命、生活的意义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主体的任务并不是要去认识世界或者要去改造世界。世界本身不可改变。世界由事实所组成,事实由对象的实际发生的配置所组成。从逻辑上说,对象可以出现于无穷的配置之中,这些配置被维特根斯坦称为“事态”(State of affairs),是一种可能性。虽然对象可以出现于多种多样的配置之中,但只有一种配置实际地发生,构成了事实,构成了世界。这是我们所能够拥有的唯一的世界。人们无法预先知道到底哪种配置会出现,但最终是一种配置而且只有这一种配置实际地发生。这是“碰巧”(happen)发生的,是偶然的,但也是确定的。我们无法改变世界的事实。
世界的事实不能改变,并不是说世界只有一种面貌。当世界以不同的面貌出现时,并不是世界的事实有所改变,而是主体看待世界的方式不同罢了。正因此,维特根斯坦才说:“幸福的人的世界与不幸的人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幸福的人正在实现存在的目的。”(NB,P73)
主体和世界因此具有了密切的联系,它是看世界的“眼”(eye)“眼”这个比喻来源于叔本华。正是由于这个看世界的“眼”看待世界的方式各不相同,世界才有了善与恶的区别。善与恶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价值。事实的世界本身不具有这种价值。只有主体才真正具有善与恶这种价值。维特根斯坦说:“主体将善与恶带进世界。”主体作为一种界限从事实的世界中消失,又恰恰在作为界限这一点上进入哲学,从而进入世界。这就是主体的消解与复归。由此,我们看到,维特根斯坦的这个主体不能用认识主体或改造世界的主体这些概念去比附。它只是这个主体,解决的只是如何在世界中有意义地生活的问题。但是这个进入世界的主体并不是一个对象,而是一个界限,它只是“看”世界。主体以不同的方式和态度“看”世界,世界才有不同的面貌,才有价值,才有善与恶的区别。“看”并不仅仅是我们通常所谓的观看,而是把世界作为整体的一种掌握。主体的作用和意义正在于此。如何使世界具有价值,并实现生活的目的,关键在于主体如何“看”(掌握)世界。
善与恶是主体的本质,而非世界中的一个事件。事实就是事实,事实的世界里不存在善与恶这样的价值。主体将善与恶带进世界。“这个主体是意志主体”(NB,P87)。这种关于主体的见解与叔本华哲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叔本华将世界区分为表象的世界和意志的世界,把事物的现象世界归结为表象世界,因此他把经验和科学的对象看作表象世界里的东西。哲学不能仅仅停留于描绘表象世界。哲学最应关注的是意志,意志是人的真正的存在。人们超越现象范畴达到自在之物,这个世界不是主体中的某种表现,而是真正存在的东西本身。这个世界就是意志。作为意志的主体就不再像其他对象那样是一个对象。作为主体的意志,其基本特征就是求生存,因此这个主体就是“生存意志”或“生活意志”。一旦我们作为意志主体存在,就从表象的世界中解脱出来,超越了痛苦(参阅《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76、286页)。
在叔本华看来,作为表象的世界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充满痛苦。如果主体是世界中的对象,它将属于事物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而委身于痛苦之中,痛苦的消除就在于人不再作为个体存在,而作为意志主体存在,那样我们就可以从贪得无厌的人生梦幻中醒来,获得高于一切理性的心境和平。这只能通过审美并在美的境界中达到。在这种美学的境界中,人才能作为真正的意志主体而存在,世界成为意志的世界,“原先使我们不安的世界之辽阔,现在却已安顿在〔心〕中了;我们的依存于它,已由它的依存于我们而抵销了。然而这一切并不是立刻进入反省思维的,〔其初〕只是作为一种看到的意识而出现的,意识着在某种意义上(唯有哲学把这意义弄清楚了)人和宇宙是合一的,因此人并不是由于宇宙的无边无际而被压低了,相反的却是被提高了”(同上书,第287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主体)方可以称作小宇宙,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可以说大、小宇宙是统一的。
叔本华的意志主体还带有认识论的痕迹,而维特根斯坦的意志主体则完全是个行动的主体,并且以其自身的行动为对象。基于这种见解,维特根斯坦在《1914—1916年笔记》中对“意志”(to will)作了多方面的深刻阐述。他区分了“意志”和“希望”(to wish)。这是十分重要的。他说,“希望先于事件,意志则伴随着事件”(NB,P88)。意志不涉及任何期望(expectation)、欲望(desire)或希望(hope),它并不试图改变事物的是其所是。更确切地说,当意志发生时,它不和事实在一起。
希望(Willing)不是行动(acting)。但是意志是行动。
显然,没有意志的行动的实行是不可能去意志(to will)的。
意志的行动(act)不是行动(action)的原因,却是行动本身。
没有行动(acting),一个人不能行使意志力。
如果意志在世界上必须有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可以是有意的行动本身。
而且意志确实必须有一个对象。
世界独立于我的意志。
我不能使世界的事件屈从我的意志:我完全没有力量。
所有经验就是世界,但不需要主体。
意志的行动不是经验。
意志是对世界的一种态度吗?
意志是主体对世界的一种态度。
(NB,P73—82)
显然,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意志是一种活动,它本身就是对生活的意义的追求。虽然我们很难知道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活动究竟是什么,但我们确实可以断定它绝对不是指改变现实的活动。而且他的意志主体的活动也不是要改变世界。因为世界就是这样的,它不可改变。因此,“我只能通过消除任何对发生的事情的影响使我自己独立于世界,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掌握(master)世界”(NB,P73)。这种对世界的掌握,其真实含义就是与世界保持某种一致。这种与世界的一致性,是生活幸福和幸福生活的保证。所以维特根斯坦说:“要幸福地生活,我必须和世界和谐一致”,这就是“成为幸福的(being happy)所意味的东西”(NB,P75)。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维特根斯坦才说:我是我的世界(小宇宙);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和生活才能是一回事。
维特根斯坦所说对世界的“态度”或对世界的“掌握”,实际上是主体对生活的一种选择,即如何实现生活的价值和目的。他同时也把这样的主体称为“伦理主体”。因为在他来,“伦理学所要解决的是关于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问题”。在有些场合,他把《逻辑哲学论》看作一本伦理学著作。他所说的伦理学,不是大学里开设的伦理学课程,也不是所谓伦理学知识或伦理学体系,更不是一套道德箴言或行为规范。在后来关于伦理学的讲演中,维特根斯坦又重申了这个观点。他说:“伦理学是探讨什么是有价值的,或者什么是真正重要的,或者我可以说,伦理学是探讨生命的意义,或者探讨什么使生命值得活下去,或者探讨生活的正确方式。”(“伦理学讲演”,转引自穆尼茨《当代分析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49页)。因此伦理学是更高的东西,不属于世界,只属于意志主体,是这一主体带给世界的某种东西。伦理学的赏罚以及作为这种赏罚后果而出来的愉快的东西和不愉快的东西,与意志主体对世界的不同态度而产生的幸福与不幸福相关并一致,而且在意志主体对世界的“态度”即某种行动的自身体现出来。因此,追求伦理的东西就是追求一种正确的生活,一种好的生活,一种幸福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追求伦理的东西就是信仰上帝。因为只有在对上帝的信仰中,主体才能达到与世界的和谐一致。在《1914—1916年的笔记》中,维特根斯坦说:
我对上帝和人生的目的究竟知道些什么?我知道这个世界存在。我知道我被置于这个世界,如同我的眼在其视野中。我知道有关这个世界的某些东西是捉摸不定的,而这种东西被我们称为它的意义。我知道这个意义并不存在于它里面,而是存在于它的外面。我知道人生便是世界。我知道我的意志穿透了这个世界。我知道我的意志是善的或恶的。因而我知道美和恶以某种方式与世界的意义相关联。人生的意义即是世界的意义,我们可以称它为上帝。而把上帝比作父亲也与此有关。去祈祷便是去思考人生的意义(NB,P72—73)。
维特根斯坦的主体不是一种概念或者一种学说,而是一种寻求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最终消除痛苦,获得幸福的一种活动。哲学于是不再是一套理论或体系,而更是一种活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生活。然而不幸的是,维特根斯坦的主体最终却把我们引向上帝。
四
如何评论维特根斯坦的主体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难题。这个行动主体在追求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时最终走向了宗教,希求在对上帝信仰或一种“美学体验”中超越痛苦(与世界割裂难以与其和谐一致而引起的痛苦),通过改变自己而非改变世界(从一种意义上说世界是无法改变的),重新获得与世界的和谐一致,达到灵魂的宁静。这个世界于是与那个世界十分不同,这是“我”的世界,生活的世界(生活和世界是一回事,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世界是可以改变的)。世界的改变不是改变世界中的事实,而是“我”对世界的态度的改变,亦即“我”的改变,并以此与世界保持一致。维特根斯坦把这种方式称为“掌握”世界。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世界的改变是影响巨大的社会变革的结果,决不可能仅仅是主体内在活动的结果。维特根斯坦那个一直在体验、在超越的具有生命力的主体最终只有在信仰中走向上帝,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结局。这除了根源于人类自身不倦地寻求终极慰藉的伟大情感之外,还有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维特根斯坦当时所处的时代充满了苦难、丑恶和战争,他对这一点有着刻骨铭心的深切体验。直到50年代,他在《哲学研究》的前言中还说我们处在一个巨大的黑暗时代。社会的黑暗足以毁灭一切,如果这个世界可能有“幸福”、“安宁”的话,这些美好的东西也只能成为主体的一种内在状态。这是人类遭遇的可怜而悲惨的经历(或是命运?),是一种最大的悲剧。在东部的战壕里,维特根斯坦对生存方式的意义有更加独特、深刻的感受。战争的威力是那样强大,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把无论多么坚强的主体打碎。
世界是其所是,我们难以改变世界的事实。但这并不重要。对维特根斯坦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有接受这个世界的勇气。他从十三岁开始就企图自杀,此后在生命的不同阶段又曾几次企图结果自己。但是最终在东部的战壕里,在恐惧和战栗中找到了那个主体,找到了上帝。当维特根斯坦于战后说这场战争拯救了他时,他并非是在颂扬战争,而是试图向世人昭示一种更为深刻而悲怆的东西。西方有位学者指出,20世纪的西方作家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种法西斯主义倾向。实际上,西方20世纪的作家中也有相当数量的人具有某种宗教倾向和热忱。这二者均与时代具有密切的关系。维特根斯坦便是一个显例:他走向“上帝”的苦难历程,深刻地折射出哲学精神的顽强和黑暗现实对哲学精神的摧残。这是一个真正的作家和时代所能具有的真实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像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那样的表面看来那么“纯粹的”哲学家也对其所处时代大加谴责的原因。因此,无论多么动人的普遍之爱或多么宏伟美妙的“超越”学说,绝对不可能超越这种关系。只有从这种关系入手,我们才能更深入地认识时代和作为这个时代精神之精华的某种哲学的价值。这并非某些“纯学术”所不屑一顾的所谓“庸俗社会学”批判,而是我们从事研究应当和必须采取的态度。尤其是当维特根斯坦的学说被雕琢成一种贵族化的精妙绝伦的玄学工艺品时,我们更应注重把握这种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