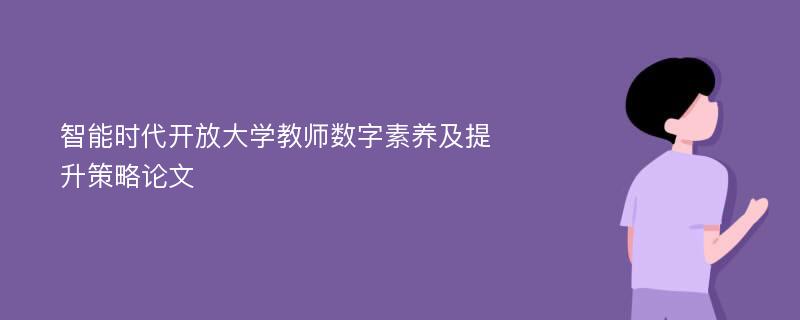
智能时代开放大学教师数字素养及提升策略
佘雅斌1,黄姣华2
(1.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广西 南宁 530022;2.广西教育学院,广西 南宁 530022)
摘要: 人工智能时代已呈不可抵挡之势影响着教育各领域的发展,开放大学作为新时代的新型高等学校承担着学习型社会的重任,如何在新时代把握机遇,应对挑战?教师是核心力量,开放大学教师要积极应对智能化变革,意味着必须具备适应时代的新素养即数字素养。从数字素养的缘起与内涵切入,论述了数字素养是开放大学教师发展的新要求及现实境况。基于此,提出了智能时代开放大学教师数字素养的三大提升策略,首先是观念更新,尽快从信息素养过渡到数字素养;其次是系统培育,作为连续统的能力发展必须遵循内在规律;最后是全面保障,从素养课程的系统规划到教师发展机构的支撑都需要系统设计。
关键词: 智能时代;开放大学;数字素养
前言
人工智能的出现对人类生存与发展影响巨大,它正以不可抵挡之势促使教育各领域产生深刻变革。当前,教育已置身于人工智能时代,各种智能化技术的广泛应用,悄然地改变了教育的生态。开放大学作为应用现代教育技术的新型大学,面对着巨大的机遇与挑战。开放大学教师如何应对人工智能、面对机遇与挑战教师的素养需要如何改变,这已然成为开放大学教师发展研究应当关注与反思的问题。
入室常规监测心电图,血压,脉搏和血氧饱和度,并建立静脉通路。两组均接受气管插管并连接呼吸机进行机械通气。
一、数字素养缘起与内涵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职业被机器取代,这也引起了教师的担忧。不久的将来,教师是否会被机器替代?教师作为一种职业不可能被人工智能代替,但教师的一些机械、确定、重复性的工作将会被机器替代。可见,当前教育史现在处在一个极为重要的拐点,学习时空已然改变,“无处不在的数字工具和数字资源让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学习知识内容”[1]。泛在学习已成为学习的新常态。这意味着“教师不需要再去亲自传授广泛的知识内容,学校也无须传授那些理论上学生以后生活所需的全部知识”[1]。这必然会引发教师职业的根本性变化。对教师素养的要求,特别是智能化环境下教师的新素养,成为开放大学教师面临的现实问题。
数字素养这一概念经历了系列的演变过程,基本上与技术的变革同步进化。进入21世纪,标志着人类进入新的时代,新时代对人们在学习、工作、生活中基本能力的要求均有所提高。在数字化时代,如何运用信息技术获取、筛选、甄别、处理、发布信息的能力已经成为公民的必备素养。1974年,美国信息产业协会主席Paul Zurkowski首次提出信息素养(Information Literacy),强调要运用信息工具解决问题的能力[2]。1998年,美国国家图书馆协会出台了《学生学习的信息素养标准》,从不同的领域衍生了不同领域特征的信息能力与素养的概念。1994年,以色列学者Yoram Eshet-Alkalai首次提出了数字素养概念,明确了数字素养的内涵包括五个方面,即图片-图像素养、再生产素养、分支素养、信息素养和社会-情感素养[3]。2006年欧盟提出了未来教育的8项素养,其中就有数字素养,其经历了4个阶段的演进,分别是信息技术、信息技术技能和使用、信息技术技能、数字素养。2015年美国新媒体联盟(New Media Consortium)发布的《地平线报告》指出,提升数字素养是未来教育面临的挑战之一[4]。2016年10月,新媒体联盟发布了《数字素养:NMC地平线项目战略简报》,提出了数字素养模型的3个维度,一是通识素养,要求熟练掌握并使用基本的、常用的数字化工具,如office办公软件、图形图像处理、云应用、数字内容编辑、网页等工具;二是创新素养,要求基于通识素养掌握更高技能工具并进行创新活动;三是跨学科素养,要求能够融合不同学科、不同情境的课程开展研究。可见,数字素养并不是一种单一技能,而是与人生活相关的、复合的、跨界的重要能力,它可促使个体获得其他的一些重要技能,如文化意识、学会学习、语言学习、数学学习等,以至于被称为 “数字时代的生存技能(Eshet-Alkalai)”[5]“信息社会的重要资产(van Deursen)”[6]。
数字素养从信息素养发展而来,是信息素养在智能时代的升华与拓展。面对智能时代的“客观存在,我们只有积极面对它才能获得‘生存’”[3]的机会与权利。数字素养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完善,动态的、开放式的概念。“当一种生活行为或方式日益大众化并影响加深时,传统素养内容的作用或价值日益边缘化,其教育效果逐步递减,客观上需要提出并倡导一种新的素养要求来与之相适应”[7]。数字素养是指在遵循信息伦理的基础上能够熟练地利用各种与生活、工作、学习有关的数字化工具或技术,能够创新性运用技术开展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并促进自我能力不断提升[8]。
二、数字素养与开放大学教师
数字素养是一种应对复杂的、不确定的、易变的、多元情境的能力,其培养必须是整体化、复合式的培育,非单一技能训练,必须进行系统化的培育,方能实现数字素养入脑入心。素养不是技能,而是能力,能力的培养不能进行分段,不能是割裂式培养,必须遵循其内存规律,即连续统。
(一)数字素养:人工智能时代开放大学教师发展的新要求
2016年,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办好开放大学的意见》,文件明确指出了开放大学功能定位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新型高等学校,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适应“互联网+”发展趋势,重点加强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营造数字化学习环境,建设远程学习服务中心,建设“云教室”,实现远程双向高清视频和互动教学,形成可供学习者多样化选择的虚拟实验、演习和实践环境。要强化信息技术应用,提高在线教育水平,实现学校日常运转和师生教育学习活动可监测、可分析、可调控,提高服务水平,提升管理效率。要创新学习组织模式,满足学生使用多种终端进行学习,确保学生网络自主学习严格、规范,可监测、可评价。转变教师角色,从授课者转变为咨询者、引导者、组织者,使以教为主变成以学为主,提高教学效率,确保学习质量。要创新师资队伍建设,适应教学变革需要,重点建设课程设计、资源开发、软件开发、学习咨询、教学组织、学习引导等专职教师队伍。通过培训开放大学系统的教师,广泛聘请高水平教师、行业企业专家等措施,形成一大批提供远程学习导学、助学和促学的专兼职教师[9]。从办好开放大学的任务中发现,开放大学是服务终身教育的学习型社会,面对智能化的未来社会,对开放大学的教师提出相当高的要求,强调了应对技术不断发展要不断提升素养,提出了面对未来教育的发展,教师的角色与定位都要发生改变,而且重点建设专职教师队伍,要吸收兼职教师形成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没有一支适应开放教育特点、擅长运用信息技术教学的专兼职结合教师队伍是无法支撑开放大学的发展,更无法面向智能化环境下的学习型社会。
面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变化,唯有与时俱进,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美国NMC发布的《数字素养:新媒体联盟地平线项目战略简报》强调指出,一是数字素养是当前高等教育领域中最大的共识,聚集于学习者在智能化的世界中不再只是知识消费者而是创生者,这需要培育学习如何利用数字化工具进行思想表达、创新呈现,特别关注意识与能力的培养。二是清晰理解数字素养模型三者之间的关系,通识素养是创新素养的基础,创新素养处于核心地位,而跨学科素养是创新素养的表现形式,这三者共同指向学习者数字潜能与创造力的培育[12]。对于人工智能时代开放大学教师而言,通识素养是基础,是未来社会生存的基础技能,如果没有通识素养相当是新时代的“文盲”,属于“功能性文盲”。创新素养是桥梁,以通识素养为基础,通过技术、技能与文化素养的结合运用,可以开展创新活动,在人工智能新时代教师必须要具备资源生成能力,这样才不至于每天依葫芦画瓢,能开展创新性的工作,形成自己独特的教学理念与行为。跨学科素养是目标,未来的教育教学情境会更多元、更复杂,教师面对复杂的情境,这不再是单一素养可以解决的问题,必须储备跨学科的素养,通过整合而达到学科之间的融合,才能真正具有适合未来复杂工作的能力。育人的工作是一项相当复杂的工作,对跨学科素养的需求更甚。
当前,开放大学教师的数字素养状况如何、是否满足开放大学发展的实际需求,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通过相关调研发现,当前开放大学教师队伍建设的现状并未达到新要求,从数字素养的角度解析,发现相当部分教师未达到数字素养的要求,只是具备了一定的通识素养,未形成创新素养,更没有形成跨学科素养,还停留在信息素养要求的层次,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如下:其一,素养理念未更新,信息意识比较淡薄。由于体制的原因,较多的教师满足于现状,忽视环境的新变化,对于技术变革缺乏敏感性,缺少主动求变意识,只是基本上掌握了多媒体设备操作,对于先进的技术跟进比较慢,不太乐意接受新技术的应用,理念与意识严重滞后,亟待更新。其二,整合手段单一,创新运用能力弱。教师没有感受到外界环境巨变带来的生存压力,还只是在广播电视大学系统里打转,对于远程教育的改革理解不到位,只习惯于PPT与教材的整合,没有把新的技术应用教学之中、融入教学材料之中,过度依赖于技术人员的支撑,创新运用技术能力弱,缺乏开拓的视野与发展的意愿。其三,缺少有效保障机制。素养的培育除了教师主体能动性因素之外,学校的培育保障机制存在一定的问题,教师发展规划比较空泛,教师培养与培训呈现碎片化、零散化,缺少系统性的教师发展组织支撑,有些学校建立了教师发展机构,但没有专业的专职人员提供服务。
人工智能时代领军人物杰瑞·卡普兰在《人工智能时代》一书中指出,智能时代的到来,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两大灾难性冲击:持续性失业与不断加剧的贫富差距。不管你是蓝领还是白领,机器正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人类的工作。在未来时代,淘汰的不仅是工作,更是技能。驾驶与教育,将可能不再需要人亲力亲为,教师很多重复性的、确定性的、机械化的工作都将由机器替代,而教师的工作重心从应试教育中的教书走向人本教育中的育人,教师未来最大的价值体现将会在育人方面。为避免被机器所圈养,教师必须淘汰过时的技能,掌握智能时代需要的新技能,具备良好的数字素养[10]。
(二)理想与现实:人工智能时代开放大学教师的数字素养
2.项目实施必须全员、全面、全过程
信息时代背景下,“互联网+”成为社会发展的关键词,对小学阶段的教学过程也有着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对于数学科目的教学来说,更要遵从这一趋势去改革教学思想与教学方式,提升教学效率与质量,为此文中对“互联网+”趋势下小学数学的教学策略展开集中讨论。
基于此,开放大学的教师如何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变化,成为重中之中的工作。无论技术如何发展,出现“何种形态的教育,要取得预期的理想成效,教师都是最为关键的因素”[11]。教师作为教育教学的灵魂,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带来的巨大冲击,将会让开放大学教师受到日益严峻的挑战。如何提升开放大学教师的数字素养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智能时代开放大学教师数字素养的提升策略
(一)更新观念:从信息素养到数字素养
采用SPSS 25.0统计学软件对该次研究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其中计量资料为血糖水平控制情况,用(±s)表示,进行t检验,治疗效果为计数资料,用[n(%)]表示,进行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开放大学教师是终身教育的实践者、引领者,是现代教育技术创新应用的高等学校的从业者。面对智能化时代引发的教育变革,面对开放大学的定位与发展,面对学习型社会的支撑,观念更新成为教师发展的必然使命。从中可见,信息素养的观念已经无法适用新时代的要求,无法适用于人工智能时代,唯有更新观念,建构正确的数字素养观念。观念的更新不是简单地记忆、理解数字素养的概念,这只是更新观念的基础,更重要的是深入理解其内涵、背景及意义,追问有关数字素养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等一系列问题,通过答案寻求可以清晰明确观念之间的差距与未来努力的方向,以帮助开放大学教师更快地、更高效地实现观念的转变,实现从信息素养到数字素养的观念更新。
(二)系统培育:从单一讲座到连续统学习
智能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发展又前进了一大步,使得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开放大学面临着诸多的挑战,意味着原来的技术会被淘汰,新的技术迅猛发展。开放大学教师的信息素养是否能跟得上时代的潮流,跟得上技术的革新,是否能适应开放大学发展定位的需要,这都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1.任务设计必须专业、系统、全面
数字素养是人工智能时代每个人必备的素养,不是只要对教师进行培育,而是全员、全面、全过程。项目实施的对象是开放大学所有教师包括行政人员与管理人员等,因为是系统培育的过程必须是全员、全过程参与,不是只进行某一部分,或者说有些教师觉得自己素养不错,不需要学习。对于素养较高的教师一定要让其参与这个过程,使其成为项目实施中的引领者,承担协助者、辅导者、支持者的角色,这既保证了整体性的发展,又充分地尊重个体的成长。
随着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不断推进,服务的理念也渐渐深入人心。但是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政府的服务行为方式很难在短时间得到彻底转变。在税务工作开展过程中,主要呈现出以下三方面问题:一是部分税务人员将服务与执法割裂,仅将纳税人看作管理对象,重管理轻服务,缺乏服务主动性,未能以服务者的姿态来面对纳税人;二是服务手段僵化单一且行为形式化,征纳双方未能树立平等的法律地位;三是在制定规章标准时,以方便管理为主,盲目追求效率,未能将纳税人的感受和需求纳入制定的指标之中。
不管是开放大学的定位与发展,还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变革,都对开放大学教师的发展提出了素养的高要求。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理念要求与时俱进。要服务于全民终身学习、适应“互联网+”发展、满足多样化学习需求、转变教师角色等,明确人工智能的变革影响。二是能力要求从静态播送到双向互动。这是素养最核心的变化,也是开放大学教师与众不同的特点。在广播电视大学时代,教师的主要任务是录课、分发、学生自学+短期面授。而在开放大学的新时代,要求教师能开展双向远程互动教学,强化信息技术应用,实现学习活动的可监测、可分析、可调控,创新学习组织模式等。三是教师角色与职能转变。以前的教师角色是讲授者,现在教师角色必须转变为引导者、组织者与咨询者,从以教为主转变为以学为主,满足学习者的多元化要求,促进学习者的自主学习,形成一支提供远程学习导学、助学、促学的专兼职教师队伍。这三个方面的素养要求与人工智能时代结合,发现其充分地体现了数字素养对开放大学教师的要求。经过了从广播电视大学到开放大学,教师具备了一定的通识素养,置身于人工智能与开放大学背景审思,从上述三个方面的要求不难发现,面对人工智能的挑战如何求变如何适应,特别是从静态到动态、从异时到实时的教学方式及教学角色等转变都突出了教师的创新素养与跨学科素养的要求。
素养是最难培养的。它具有连续统的特性,在培养的设计上必做足功夫,数字素养培育课程的设计必须找专业的团队进行精心的打造。这是一个长期项目,是可持续发展的课程,内容设计必须覆盖全面,保证宽度、广度与深度三维无死角;形式与方法上,绝不能采用讲座说教式的方法,必须是基于行动导向的学习,可以是项目学习、探究式学习,也可以是研讨式学习。培训需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直截了当的态度,灵活的理智兴趣或虚心的学习意志,目的的完整性和承担包括思维在内的人人活动后的责任心[13]。
3.课程学习必须线上与线下相结合
课程学习既是数字素养的学习过程,也是数字素养的实践过程。在学习中获得素养,在素养实践中巩固学习。数字素养的培育与工作实际进行融合,让所有教师在工作实际中把数字素养培养进行落地。因为在人工智能时代,每个人都生活在数字化的空间,也是数字化空间的组成部分,颇有“不知素养何面目,只缘深在此山中”之意境。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让教师作为学习者感受一下自己的设计与教学方式是不是学习者喜欢,另一方面作为资源的生成者与创生者,体验数字素养在其中的作用与意义。
4.培育问题收集反思机制系统化、过程化
为了保证培育效果,对培育过程进行全面的记录,最终会形成系统化的材料,全景式地呈现全过程。数字素养的培养,是能力不断发展、积累的过程,必然会碰到许多的问题,每个人的问题会不一样,个别化、即时性的问题可通过智能化网络平台进行收集并处理。除此之外,还要专门设置集中研讨的问题收集,主要是相互商讨、相互答疑、形成共识性的问题。如果现场不能及时解决问题,则由教师发展中心人员进行系统收集、归纳整体,形成问题集提交数字素养培育任务设计团队进行集中协商解决,并及时进行反馈,依据问题的类型采取对应的方式反馈,必须保证及时性与有效性的统一。而后,培训过程出现的各种问题再次提炼、分类归纳,形成共性问题与个性问题,并对问题与解答过程进行详述,形成电子版与纸质稿。问题收集是一个动态、不断完善、不断丰富的过程,既要关注系统培育的全过程,又要关注素养培育的小细节,真正做到全面、系统、过程化。
(三)全面保障:从素养规划到机构支撑
数字素养的培育不是一项简单的技能培养,而是一项复杂的、系统的技能学习过程。要实现素养培育的全面保障,必须建立教师发展中心等相关专门机构支撑。开放大学作为现代信息技术支撑的新型大学,必须要系统地落实贯彻教育部的政策文件要求。首先,将数字素养培育纳入开放大学师资队伍建设的整体规划,并单列专项的数字素养培育任务。从培养时间、人员、机构、机制等进行系统、全面的规划,确保教师数字素养的培养工作落地。其次,开展系统的调研,以数字素养的三大维度为基础,结合开放大学的发展目标,对数字素养的内涵进行细分,编制调查问卷,开展开放大学教师数字素养的现状调查。以此问卷为基础,每个学期进行一次调查,系统收集培养前后教师数字素养的变化,形成教师专属的、个性化的数字档案袋,为教师发展提供支撑性的材料,为系统培育提供数据支持。第三,建构教师发展中心提供全面保障的物质基础。数字素养的提升不是立竿见影,而是一个慢慢积累、逐渐发展的过程,只是依靠单次的、培训类的讲座想解决数字素养的培育,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开放大学教师发展必须由专门的机构来支撑师资队伍建设系列任务的落实,这也是保证培育的系统性与连续性。
以生物资源开发创新工程为突破口,寻求地域、季节和市场差异,利用当地特色资源,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基层政府要及时转变职能,变管理为服务,通过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服务体系,帮助农民抢抓市场机遇,大力发展订单农业、合同农业和创汇农业,正确处理好生产与市场的关系,克服结构调整中的盲目性和分散性[6]。
结语
“来而不可失者时也,蹈而不可失者机也”[14]。面对人工智能时代,作为开放大学的教师不可螳臂挡车,应顺应时代潮流而上,与时俱进,充分把握时代机遇,积极应对现实挑战。提升教师的数字素养是开放大学的职责,也是每个开放大学教师自我发展的发展需求。教师数字素养的提升,将让中国的学习型社会建设更顺,让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更畅。
读者们,去想像一张地图。在这张打开的地图上,有一些枝枝蔓蔓的地形构造,但这些不属于某个人,属于那些说“这里”的风景们——就像我们所有的说话者都说“我”那样。想象一下与我们通行有关的记忆,这种记忆指向你的前方,同时又指向着你的后背,一步一步地以某种不规则的方式慢慢扩展着,令人不快的是,它是非个人的。记忆没有腿,但它会将我们拖曳至现在的深处,因为当我们向后看时,我们只能从“这里”开始,从“这里”凝望那个不存在的向我们迄迤而去的过去。因此,过去有双层皮肤,两种触觉:一个过去指向现在,一个过去指向非现在。
参考文献:
[1]富兰·迈克尔,兰沃希·玛丽亚.极富空间:新教育学如何实现深度学习[M].于佳琪,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63.
[2]任友群,随晓筱,刘新阳.欧盟数字素养框架研究[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4(5):3-12.
[3]肖俊洪.数字素养[J].中国远程教育,2006(5):32-33.
[4]新媒体联盟(NMC).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2015图书馆版[J].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5):39-43.
[5]ESHET-ALKALAI, Y. Digital literacy: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survival skills in the digital era [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ultimedia and Hypermedia,2004,13 (1):93-106.
[6]VAN Deursen, A. J. A. M., VAN DIJK, et al. M. Using the Internet:Skill related problems in users' online behavior [J]. Interacting with Computers,2009,21(5/6), 393-402.
[7]陶侃.略论读图时代的“游戏素养”及构建要素[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09(2):14-18.
[8]叶兰.欧美数字素养实践进展与启示[J].图书馆建设,2014(7):17-22.
[9]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办好开放大学的意见[EB/OL](2016-01-21)[2019-03-23].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7/moe_726/201602/t20160202_229322.html.
[10]杰瑞·卡普兰.人工智能时代[M].李盼,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1.
[11]田爱丽.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教师角色转变与综合素养提升[J].教师教育研究,2015,27(5):84-88.
[12]张晴.《数字素养:新媒体联盟地平线项目战略简报》研究[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7(5):110-114.
[13]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196.
[14]许欢,尚闻一.美国、欧洲、日本、中国数字素养培养模式发展述评[J].图书情报工作,2017 (16):98-106.
中图分类号: G6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719( 2019) 7-0051-05
作者简介: 佘雅斌(1977-),男,湖南邵阳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教师教育与教育信息化;黄姣华(1980-),女,湖南邵阳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教师发展。
收稿日期: 2019-04-20
修稿日期: 2019-05-19
基金项目: 2016年度广西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双师型’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GXGZJG2016B043)。
(责任编辑:王本贤)
标签:智能时代论文; 开放大学论文; 数字素养论文;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论文; 广西教育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