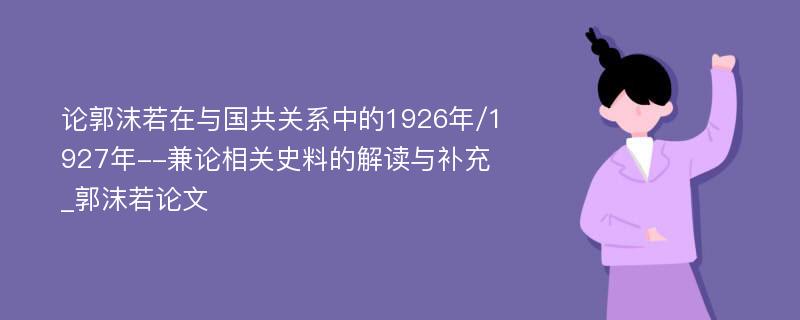
在与国共两党的关系中看郭沫若的1926—1927——兼论与此相关的史料之解读及补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郭沫若论文,与此论文,史料论文,中看论文,在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25(2007)01—0020—08
因为正在做的一个课题,对于郭沫若的生平史料都需要再来检识一遍。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发现现有史料中存在着一些完全属于史料是否确切的疏误(甚至是很大的疏误),因此有必要重新做一番考辨的工作之外,还感觉有另外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即对于许多现有史料,还需要去除其中实际上包含着的非历史的因素,也就是说属于史料提供(回忆)者主观判断的内容。这主要是指后人回忆文章所涉及的史料(这在有关郭沫若的生平史料中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今天来回忆几十年前的人、事(或者依据口口相传),出现记忆上的错误,甚至张冠李戴,在所难免。这可以结合一手的资料或者与其它资料相互印证、补充来确定其真正的历史存在或历史状态。但在提供(回忆)者的叙述中已经包含了解读性的主观判断的内容,而它们又反映着某种时代氛围的话,那是会在无意中模糊了历史真实性的。这一点似乎还没有被研究者们充分意识到。
譬如,关于郭沫若1926年初南下广州,到他投身于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的这段经历。人们已经熟知并认可的叙述,大体上是这样一个过程:
1926年2月,郭沫若得到广东大学校长陈公博的信函,邀请他去广东大学任教。这是共产党人瞿秋白推荐的。3月底,郭沫若到达广州,林伯渠安排了他到广东大学的事宜。这时,他结识了毛泽东,不久又结识了周恩来。在广东大学任教的四个月中,担任文科学长的郭沫若的重要经历有文科革新、择师风潮,参与中山大学筹备工作,有多次与时政有关的演讲及许多社会活动,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加入了国民党。6月,在共产党人周恩来、孙炳文等人的推动、推荐下,担任了北伐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科长,随军北伐。10月,郭沫若升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即往南昌主持总政治部在总司令部行营和江西方面的工作,并再一次提出入党申请。在此期间,一方面是蒋介石拉拢郭沫若,另一方面则是他逐渐看清了蒋介石的真实面目。1927年3月底,郭沫若撰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与蒋介石决裂,并遭通缉。南昌起义后南下广东途中,郭沫若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一概括叙述所依据的史料,为行文简便,在这里不一一注明,它们都是郭沫若研究者们所知悉的。我要说的是:从这样一个历史叙述的梳理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一条脉络,即它主要或者说是侧重于在郭沫若与中国共产党发生政治关系的过程中,去描述郭沫若在大革命时期的人生经历,而他与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交道往来则被包含在这一关系中,或者仅仅是从这一政治关系去解读那些史料。
在郭沫若的人生行旅,尤其是其政治经历中,广州的四个月和此后一年时间的北伐军旅生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段,他与国共两党和与之相关的许多政治人物的关系,都是从此开始的,他作为文人知识分子由士而仕途的最初尝试,也是从此开始的,抗战时期他的政治经历更与此直接相关。所以,对于他这一时段的经历,尽量能够还原其历史的真实状态,对于郭沫若研究实在是必不可少的。但以上的描述是否就是曾经的历史,或者说历史是否仅仅就是这样一些内容、这样一种状态呢?
我以为,这还是一个需要再斟酌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对上文所涉及到的一些史料的考辨,与另外一些未被提及的史料以及相关的史料综合起来进行考察,再来看看历史叙述的文本应该是个什么样子。
第一次大革命以国共合作为其政治态势最根本的特征,这是考察此一时期郭沫若生平史料格外需要注意的一个历史背景,而在很多情况下,这一点实际上是被忽略了。
先说郭沫若的受邀去广东大学。陈公博(国民党人)邀请,瞿秋白(共产党人)推荐,我们把这两者都确认作史料,但一直以来人们强调的实际上是后者的作用,似乎是有了瞿秋白推荐(与此相关的是,郭沫若到达广州后先去了林伯渠处),才有陈公博的邀请。其涵义当然是以共产党作为促成郭沫若南下广东的政治背景。且不说关于瞿秋白的推荐只有间接的史料,陈公博的邀请则是直接的史料,在这一叙述中,还有一个被忽略了的历史细节:陈公博特意致函邀请的是两个人,郭沫若之外,另一位是田汉(信函的抬头即为“沫若田汉先生”)。我不知道当初资料的发掘者是有意还是无意忽略了这一点。陈公博邀请信的内容也是值得注意的,信中写道:“我们对于革命的教育始终具有一种恳挚迫切的热情,无论何人长校,我们对于广东大学都有十二分热烈的希望,于十二分希望中大家都盼望先生急速南来”。“现在广州充满了革命紧张的空气,所以我更望全国的革命的中坚分子和有思想的学者们全集中到这边来,做革命青年的领导。深望先生能刻日南来,做我们的向导者。”①
广东大学不是一般的国立大学,而是相当(国民党)“党化”了的大学,是国民党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阵地。在将要把广东大学改名为中山大学的计划里,国民党人是准备让其“达到党化地步。将来凡系党员入校肄业,一律免费。非党员则要交纳学费。”② 陈公博当时在国民党内也有比他作为广东大学代理校长更重要的份量。他是自1925年底原广东大学校长,西山会议派的邹鲁去职后暂时代理广大校长的,是去收拾邹鲁留下的一个乱摊子。在代理校长期间,陈公博施行了几项新的校务措施。事实上,在邀请郭沫若南下广州时,陈公博因代理期满,已提交了辞呈,继任校长为褚民谊。而在郭沫若到达广州后,陈公博即已就任广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部长(北伐开始后该部改组为邓演达任部长的总司令部政治部)。北伐开始后,他是蒋介石最重要的幕僚之一。
从这些相关的史料中,我们是不是可以把邀请郭沫若去广东大学理解为,它应该是作为国民党人的广东大学校长陈公博的主动行为,他是为广东大学延揽人才(并非只是一个郭沫若。事实上,创造社的几员干将后来都被广东大学延聘:郁达夫任英国文学系主任兼教授,成仿吾任文科兼预科教授,王独清任文科教授。③ 瞿秋白推荐可以是郭沫若被邀请的原因之一,但并不是决定的因素。陈公博的政治背景又表明,他为广大延揽人才并非个人之举,而是出于国民党政治利益的需要。那么,郭沫若的南下广东,理应主要是由国民党人的意愿促成,共产党人则从旁推动了此事。
郭沫若进入广东大学任文科学长不久,就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举动:提出了一些革新教务的具体措施,由此引出了广东大学的择师风潮,他也一时成了风云人物。在此期间被我们特别注意的史料是:他提出了加入中共的申请,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交往,几个月后,在共产党人的推荐安排下投笔从戎,进入北伐革命军总政治部。在这里,他与国民党的关系,几乎又是被忽略掉了,包括他加入国民党一事。有的年谱没有记录此事,也有在6月的记事中含糊地写一句“此时已加入国民党”。
郭沫若加入国民党一事被人们忽略,可能是因为郭沫若自己就把它忽略掉了。本来他在《脱离蒋介石以后》中清清楚楚记下,他是在1926年5月中旬加入国民党,入党介绍人是广东大学校长褚民谊,可后来,他从发表的文章中删去了这一段文字,使得只看今文的后人搞不清此事了。④
加入国民党,应该是郭沫若在大革命时期政治生涯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不只是此前作为一位浪漫派诗人的郭沫若在表面上一个政治身份的变化,而且是串联连起他前后经历因果关系的一个历史细节,使我们对于他在此期间的活动可以获得一个具有相对准确政治涵义的解读。
往前看,郭沫若3月下旬到广东大学,5月中旬,即由褚民谊介绍加入国民党,其间只有短短不足两个月时间。与此相关的是,他在这之前要求加入共产党的申请没有被批准。这一方面可以从侧面看出,邀请他来广东大学一事于国民党方面的政治背景;另一方面则说明,国民党广东大学特别党部对于他在文科学长任上的工作表现是充分肯定的。那么在这两个月中让国民党人格外看重的郭沫若的工作表现,应该就是文科革新和他在择师风潮中的表现了。
郭沫若甫任文科学长即提出革新教务措施,其实并非他个人的行为,而是从陈公博代理广东大学校长到褚民谊接任校长以后,在广东大学推行改革过程中的一个举措(在文科之后,其它学科也有做出同样革新者)。在陈公博之前,广东大学是被国民党右派的西山会议派邹鲁所代表的守旧势力把持着,他聘请了一批前清的举人、贡生,也有着洋装而无实学的教授任教,早就引起学生的极大不满,国民党人感到需要对广东大学进行革新,也已经着手在进行革新。陈公博代理期校长的时间只有两个多月,即施行了“设立专修学院、公开图书馆、邀请名流演讲等几项新校务措施”,继任校长褚民谊继续着这一革新,但革新受到守旧势力的阻碍。郭沫若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入长文科的,他显然了解这一政治态势,并且果断地顺应了革新的趋势。这应该也是邀请他来广大的国民党人所期待于他的。所以,在初到广州被记者问到整顿广大文科的计划时,他表示还需要与褚校长“详细商订,乃能确定”,二十余天后,即与校长褚民谊联名发出了革新教务的公告。国民党广东大学特别党部后来在关于广大择师风潮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也写道:“文科学生,从前曾屡次要求学校改革文科,其要点有二:(一)撤换不良教师;(二)设立文科图书馆。但是一路都没有结果。到了郭沫若先生担任了文科学长,知道他是一位有革命性的人,所以又旧案重提,向他要求。”⑤
革新措施受到一批代表守旧势力教师的顽固反对。以教育系主任兼文学及专修学院教授黄希声为首,串联了部分文科教授讲师26人开会,于4月21日宣布罢教,同时呈文校长,要求“罢斥”郭沫若。22日,又将呈文在广州报纸上登出,并向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广东省教育厅呈送。⑥ 于是,这次教务革新在广东大学演绎为一场激烈的风潮,郭沫若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此时,他得到了国民党广东大学特别党部的全力支持。该党部专门召开了党员大会,到会者有五百余人,推毕磊为主席。大会通过四项议案:“(一)援助文科同学之择师运动;(二)拥护为学生谋利益之褚校长及郭学长;(三)拥护褚校长郭学长改革文科之计划;(四)普遍择师运动于学校。”紧接着,文科学生全体大会通过的《文科全体学生宣言》,宣布全力支持革新;又决议组织“文本预科革新委员会”,选出委员9人,办理一切事宜。会后,并分别呈请国民政府、中央党部及广大校长,要求撤换“不良教师”。⑦ 5月3日,褚民谊函呈国民政府,报告校务革新情况申请预算,同时,报告了文科部分教师罢课风潮的经过及解决。对于参加罢课的26位教员,除已经公意恢复授课的11人外,呈请对于另外15位罢课教员,“从轻处分,即日免其职务,不使借本校教员名义在外煽动,以正学风”。国民政府接到呈文后,于12日批示:“准如所请办理。”⑧
这一次风潮是以革新势力的胜利宣告结束,郭沫若则得到国民党广大特别党部的高度评价。在该党部写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认为,“各科学长,只有文科学长郭沫若先生,很能帮助党务的进展”,“他的文字和演说,很能增加党化宣传的声势”,“能够在重大问题发生的时候,有彻底的革命表示和主张”。⑨ 有一个历史细节,还可以从侧面看到在革新风潮后,郭沫若如何受到器重。5月3日,设在番禺的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开学典礼。这是讲习所开办以来首次在广东之外招生,参加开学典礼的来宾多为国共两党的重要人物: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谭延闿、妇女部长何香凝、农民部长林伯渠、青年部长甘乃光、全省农民大会代表彭湃、广东大学校长褚民谊、国民大学校长陈其瑗等。开学典礼由林伯渠主持,所长毛泽东报告讲习所筹备经过和招生情况,来宾相继发表演讲。郭沫若只是以广大文科学长的身份参加了典礼,但作了演讲,显然这是一个刻意的安排,应该与褚民谊或国民党广东大学特别党部有关。⑩ 这也是一种政治评价。能得到这样的政治评价,应该就是郭沫若很快由褚民谊介绍加入国民党的主要原因。5月中旬入党,6月初,郭沫若即受命为国民党广东省党部青年夏令营讲习班的教务工作负责人之一,并将讲授“革命与文艺”。其他将开设的课程有:蒋介石讲授“北伐计划与国民党政策”、周恩来讲授“国民革命与党”等。紧接着,他又与吴稚晖、张太雷、何香凝等受聘为国民党广大特别党部暑期政治研究班教授。(11)
再往后看,是郭沫若投笔从戎进入北伐革命军,这与他加入国民党是不是也有因果联系呢?我以为应该有。
在郭沫若参加北伐革命军的问题上,一直以来,认可这样的说法,即,是经由共产党人(周恩来、孙炳文、李民治等)的推动和安排。并且在回忆资料中还有这样的说辞;政治部宣传科长一职,蒋介石不愿意让共产党人担任,但国民党里面又没有人可胜任此职,于是认可了共产党人推荐的郭沫若。我以为,历史的真实大概也未必尽是如此。
这一说法首先就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郭沫若是国民党员。而且,作为政治部的主要干部都应该具有党派身份(国民党或共产党)。其次,这一说法没有考虑到当时国共两党对于北伐的态度是有很大不同的这一历史背景。以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的军事行动是国民党极力推行的,当时由陈独秀主持的中共中央,对于这一军事行动并不积极,也不抱“过分之希望”,而是把“国民会议”作为这一时期党的“总的政治口号”。陈独秀认为,广东当时还需要积聚北伐的实力而不要冒险,北伐的时机尚不成熟。因而,中共方面甚至一度把北伐看作只是国民党的事情,当然也就不会热心参与其中。郭沫若进入政治部任宣传科长一事,应该与他南下广州的情况相似,有共产党人的推动,但更主要的原因,恰恰还在于他本人就是国民党员,又在广东大学任职期间显示出宣传方面的才干,于是被国民党方面所看中。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是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改组而成的,陈公博是政治训练部主任。政治训练部应该算是政治部组建的前期。在6月21日,政治部召开第一次战时政治工作会议时,陈公博以两部交接工作的关系参加了会议,郭沫若则以准备进入政治部,还未到任的身份也参加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邓演达高度称赞了陈在军队政治工作方面的创建性作用。在这次政治工作会议第三天的会议日程上有这样一项报告事项,“褚民谊报告广东大学党务概况”,而其他报告事项都是各军政部门的工作报告。(12) 这说明,广东大学的党务工作是纳入政治部工作范畴。那么,郭沫若以广东大学文科学长身份进入政治部,似乎应该也不仅是一种个人行为(即使他有这样的个人意愿),更大的可能,是带有国民党广东大学特别党部党务安排的背景。事实上,身为广东大学校长的褚民谊后来也参加了北伐(校长一职留给戴季陶继任)。而且,从政治部组建的过程看,这是不是意味着,陈公博仍然有可能在郭沫若进入政治部一事中起过作用?当然,这一点只能是揣测了。
郭沫若曾经说到过,政治部的人员构成,基本上是国民党左派与中共党员两部分,事实确实如此,当然掌权者是国民党左派。那么作为总政治部一个重要的人物,我以为,我们在描述这一时期郭沫若的经历时,对于他的政治身份应该有一个基本认定:即,他是一个国民党左派人士。如果说在郭沫若刚到广东时,共产党人是把他作为一个具有革命倾向的知识分子看待的话,那么在北伐期间,共产党人则应该是以国民党左派人士来看待他了。
从赴广东大学任教到参加北伐,郭沫若在这一段时间的政治经历可以这样概括:国民党人看中并选择了他,他也选择了国民党并以左派人士的身份投身于国民革命之中。但是,随着北伐军事行动的一步步前进,国民革命的政治形势逐渐发生了变化,郭沫若的政治经历也随之而发生着变化。
北伐革命军攻克武汉之后,邓演达身兼了数职,他向蒋介石提出任命郭沫若为总政治部副主任,这在蒋介石年谱中有明确的记载。蒋介石的总司令部驻扎在南昌,按说总司令部政治部也应设于此地,但由于邓演达主政湖北,所以总政治部设在武昌,于是,邓演达将总政治部分为两部分,分设于武昌、南昌两地,他让郭沫若在南昌主持总司令部政治部的工作,主要管江西方面和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三军、第六军的政治工作。这表明他对于郭沫若是非常器重的。
被派驻于南昌的郭沫若直接在蒋介石手下工作,蒋介石应该也是很欣赏他的才干的。郭沫若于1926年11月8日晚启程赴赣,而到这个月底之前他的工作日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记录:16日,蒋介石电令郭沫若从将到南昌的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毕业生中挑选人员,担任各连党代表及政治工作人员。(13) 17日,蒋介石电催郭沫若“本日订定”俘虏宣传大纲。19日晚,郭沫若应召与从前线回到南昌的蒋介石谈话,所谈之事为在总司令部或总政治部应设立经济科,“以调查占领区域一切经济状况而建设之”。(14) 26日,郭沫若参加了蒋介石在总司令部行营召开的政治、经济、党务联系会议,讨论江西政治、经济、党务方面的问题及提案。可见前几天蒋与他的那次谈话,是在征询他对于经济建设方面的意见。在这次联系会议上,政治部受命起草“文官考试”、“惩吏条例”等有关吏治的条例,并指导江西党务工作。(15) 29日,在总司令部的总理纪念周活动中,蒋介石发表演说,郭沫若做政治报告。(16) 也是在这个月,蒋许诺给郭沫若每个月加发两百元津贴。不久,蒋的夫人陈洁如来到南昌,蒋特别将陈洁如介绍给郭沫若,几次让郭沫若请陈到政治部去玩。(17) 1927年2月,郭沫若与张群、陈公博、陈立夫等在总司令部就任“中国国民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南昌特别党部”执行委员职,(18) 蒋介石又私下任命郭沫若做他的总司令部行营政治部主任。
从这样一些历史细节中,我们可以一窥当时蒋介石与郭沫若之间的关系,他欣赏郭沫若的才干,希望郭可以成为自己信赖、倚重的幕僚。在外人眼中,这一时期蒋郭之间似乎也具有了这样的关系。当然,蒋介石这时倒不是在与中共争夺人才,他一方面是在培植自己的亲信,一方面是与武汉方面(后来则是武汉国民政府)的国民党左派势力在争夺人才。
然而事与愿违,郭沫若并非趋炎附势之人,他对国民革命有自己的认识,也就在政治上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与蒋介石共事,使他一步步看清了蒋介石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本质。1927年3月下旬,他致信邓演达,表明反蒋的态度,并申明要公布蒋介石的罪状,坚决站在武汉国民政府(国民党左派)一边。3月31日,他开始起草《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以此文公开表示与蒋介石的决裂。在南昌的这段时间,郭沫若与共产党人的关系愈益密切。当时在南昌有一个由李富春、林伯渠、李民治、朱克靖、朱德等人组成的中共南昌军事委员会,以统一领导中共在驻南昌国民革命军中的党的工作。这个军事委员会对郭沫若不保密,讨论什么事情,李民治还会向郭沫若征求意见并向他报告会议内容,郭沫若也常就工作征询军委会的意见,如蒋介石给他加发津贴一事,他就是先征得了军委会的意见才予以接受的。
与蒋介石决裂,显然是使得共产党人对于郭沫若给予了特别重视的一个缘由。1927年3月30日,周恩来在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特别委员会会议上建议,在民众方面,推举郭沫若为知识分子的领袖。郭沫若因被委派去上海主持总政治部上海分部而4月14日到上海,周恩来面见了他,特别听取了他对于蒋介石在九江、安庆捣毁党部、工会,屠杀民众等情况的介绍及建议。之后,周恩来根据蒋介石在江西、沪、宁等地叛变革命的行经,起草致中共中央意见书《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19) 当宁汉合流以后,共产党人在筹划南昌起义的时候,更把郭沫若推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
“推举郭沫若为知识分子的领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细节,大概周恩来当时也不会想到,此后几十年的历史就是按照这样一种预设的方式发展下去了。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策划和领导的,但从策略上考虑,起义时仍然打着国民党的旗号,所以起义之时,即召开了一次国民党部分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海外各党部代表联系会议。会议发表宣言表示要继续革命,选举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20) 这个委员会的核心机构是一个主要由国民党左派人士组成的七人主席团,郭沫若为主席团成员之一,并被任命为宣传委员会主席,起义军总政治部主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团的另外六名成员是: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张发奎、贺龙、恽代英。(21) 与他们相比,郭沫若无论在政治经历还是军旅生涯方面都是资历最浅的,可见此时,中共已经非常看中他了,但也仍然是视其为国民党左派。(起义军军力的主体是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部队,郭沫若则是第二方面军的副党代表、政治部主任。)
郭沫若是在8月4日晚赶到南昌的,起义部队已经准备南下。在革命委员会的七人主席团中,宋庆龄、邓演达早已在国外,并未参与起义之事,张发奎不但未加入起义,而且站在起义军的对立面,谭平山、恽代英则具有国共两党的双重政治身份,那么实际上,以国民党人身份参加了起义及南下行动的,只是郭沫若、贺龙二人。南昌起义是国民革命时期的一个转折点,它表明,共产党人要独自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了。所以,当郭沫若随起义部队南下至瑞金时,他由周恩来、李民治作为介绍人,与贺龙一起成为中共党员。
从此时开始,郭沫若的政治生涯与中国共产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在北伐初期以后,郭沫若的政治经历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脉络:作为一个国民党左派,郭沫若从蒋介石的行径中逐渐看出了其反革命的本质而与之决裂,并被开除出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人则选择了他,他也选择了共产党。
从郭沫若与国共两党的关系中来看他从1926年到1927年,即大革命时期的经历,与目下许多他的传记、年谱的记述中所能描述出的那种历史文本相比,应该是有不小的差异的。但这种差异,并不是因为援引了什么新的关键性的史料,而主要是缘自汇集许多被忽略的,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资料的补充、记述,对于回忆性的史料,尽可能地剔除其包含的主观判断性的内容,以此,来求得还原于真实的历史存在。
有关郭沫若在大革命期间经历的史料并不多,而能让我们直接做出肯定判断的史料在数量上更少,大量的史料来源于后来的回忆文章,包括郭沫若的自传也是在多年后才写出的。所以对于当时出现、发生过的人、事,如果我们不能以直接确凿的史料予以记述,相关历史资料的补充叙述是非常必要的。也就是说,我们即使不能做出十分肯定的判断,应该尽量完整、真实地描述出那一历史场景,那一历史存在状态。这比简单地认可一种判断更接近历史真实,也才更具有学术价值。譬如,郭沫若在自传中写到他到广州后先去林伯渠处接洽,然后才去了广东大学,后人在实际上就把此处的林伯渠解读为(共产党人)林伯渠。林伯渠是共产党人不错,但此时的林伯渠也是国民党员,而且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秘书处秘书、农民部长。作为在当时广州政坛上活动的一个政治人物,林伯渠先以农民部长,后以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常常在公众活动中露面。那么,郭沫若最初与林伯渠相识,打交道,究竟是与共产党人林伯渠还是与身为国民党政要的林伯渠呢(这实际上涉及的是与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发生的关系)?我们或者并不能对此做出肯定的判断,那就应该把这些内容完整地、真实地记录在与郭沫若相关的历史情节之中去,否则,历史反而被模糊了。
涉及郭沫若在大革命时期经历的史料,有相当大的部分是源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回忆文章。今天来回看这些资料,有一个问题尤其值得郭沫若研究者再作思考,即,当时的许多回忆文章,或多或少都因为时代的政治背景而在对历史资料的叙述中,无形地具有了某种倾向性。它们以郭沫若去世后对于他在政治上所做的盖棺论定的评价,来框定出一个叙述他人生行旅的政治脉络。郭沫若入党介绍人之一的李一氓(民治),在他出版于2001年的回忆录中谈及郭沫若入党经过时的一段话耐人寻味。他写道;“在瑞金的时候,周恩来同我商量,要介绍郭沫若入党。究竟是郭沫若提出在先,还是组织上要他入党在先,现在无从说起。我看这不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当时对郭沫若来讲,入党的时机已经成熟了。”(22) 这段文字值得寻味之处有二:其一,提出了是郭沫若主动要求入党,还是组织上要发展他入党的问题。如果说这一次郭沫若没有主动提出申请,那么此前的两次申请应该并不存在一个有效期的问题。(在广东大学提出入党申请是依据徐彬如《大革命时期我在广州的经历》的说法,在南昌提出申请一事出自朱其华的《一九二七年底回忆》一书,两者都是当事人之外者的回忆)而且,至少半年多前在南昌提出的那一次,李一氓是应该知道的(假使有过的话)。李一氓回忆录中写到了在南昌那段时间,中共南昌军委与郭沫若的关系,但没有记下他提出入党申请之事。这是不是意味着郭沫若提出入党申请的史实,是还有待直接的史料再予证实的。其二,提出“时机”成熟的问题。这“时机”如果仅仅针对郭沫若个人而言,应该指的是他具备了条件,却不是什么时机。那么,主要的应该是针对组织而言。它的含义是:周恩来认为(当然是作为党组织的意见),南昌起义的行动进行到此时,郭沫若作为国民党左派的政治身份不再有多少实际意义了,因此,已经被南京国民党中央开除党籍的郭沫若应该发展为中共党员。李一氓应该是了解郭沫若研究这一学术领域的,他的回忆既没有轻易否定什么,也不做无史料依据的认可,但却是审慎的、客观的。当然,他是历史的亲历者,而我们这些从史料去了解历史的研究者们,就需要对过目的史料做出考辨。
郭沫若生平的史料,我们所能找到和拥有的,当然是越多,越充分则越好,但肯定是无法做到十全十美,难以穷尽的。所以,问题的关键还不完全在于我们是不是记录了郭沫若生平所有的史料(即使我们现在做出一部郭沫若的年谱长编,也还会不断有新的史料需要补充进去),而首先在于,我们是不是能以真正历史的、客观的眼光去发掘史料、考察史料,去分析已经拥有的史料,并且恰当地运用这些史料。如果在我们的意识中存在有一个预设的倾向性,那么势必在发掘、考察、分析、运用史料的时候出现偏颇,对一些相关的史料没有应有的注意,在同一史料中忽略掉一些重要的历史信息,在叙述历史的时候掺入了主观推断的内容。为什么关于郭沫若在大革命时期与国民党的关系会在不同程度上被忽略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此。
本文所谈到的史料问题,不只是存在于对郭沫若大革命时期经历的历史记述中,所以,在我们回顾、展望郭沫若研究(这是近些年来常被提到的话题)的时候,有必要对于这一学术领域的史料的基本建设再做一番努力了。
注释:
①《陈公博函催郭沫若等南归》,1926年2月18日《广州民国日报》。
②1926年4月9日《广州民国日报》。
③《国立广东大学概览》1926年5月。
④发表于1927年5月23日武汉《中央日报·中央副刊》的《脱离蒋介石以后》上是这样写的:“说我投机呢,我的确是个投机派;我是去年五月中旬才加入国民党的,而且介绍我入党的还是我们褚公民谊。”
⑤⑨《广大特别党部报告》,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编《党务月报》1926年第2期。
⑥见1926年4月26日《广州民国日报》。
⑦《广大特别党部报告》,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编《党务月报》1926年第2期;1926年4月26日《广州民国日报》。
⑧1926年5月14日《广州民国日报》。
⑩《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纪盛》,1926年5月4日《广州民国日报》。
(11)据1926年6月2日、4日、9日《广州民国日报》。
(12)《李一氓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1926年6月《广州民国日报》。
(13)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19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5月。
(1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档案出版社1992年12月。
(15)1926年12月13日《广州民国日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档案出版社1992年12月。
(16)《林伯渠日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7月。
(17)(22)《李一氓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
(18)1927年3月8日《广州民国日报》。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20)《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海外各党部代表联系会议宣言》(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新国家》1927年12月1日第1卷第12号。
(21)《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令》(一九二七年八月二日),1927年8月2日、3日江西《工商报》。
标签:郭沫若论文; 陈公博论文; 林伯渠论文; 褚民谊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蒋介石论文; 邓演达论文; 国民党论文; 历史学论文; 世界大战论文; 辛亥革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