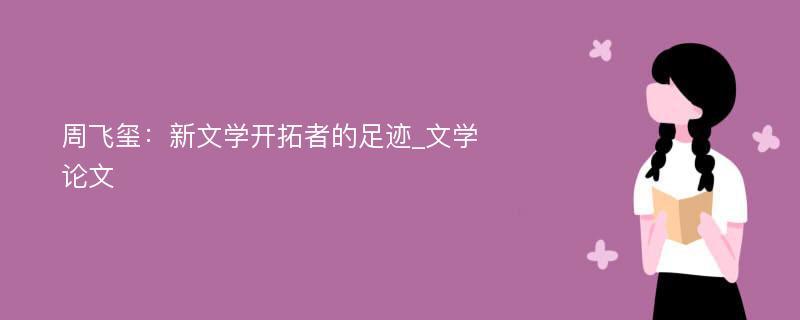
周仿溪:一个新文学开拓者的足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学论文,开拓者论文,足迹论文,周仿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周仿溪(1892—1950),河南临颍人,原名周景濂,字仿溪。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新文学创作,发表作品多署名周仿溪,遂以字行。
周仿溪出生于农民家庭,幼年读过私塾,稍长进县高等小学堂读书。1916—1921年在河南省立师范学校求学。这个时期,正值中国新文学运动开展之时,他在河南省的中心城市开封接受了《新青年》等进步书刊的影响,受到新思潮的洗礼,成为河南最早一批运用白话写作的文学青年。同时,在这里他结识了徐玉诺与于赓虞,并与他们结成亲密朋友。在省立师范学校毕业后,周仿溪先在叶县、舞阳等地教书,1924年回到临颍出任劝学所所长,1925年,被聘为临颍甲种蚕业学校国文教员。这期间,他开始接触河南早期共产党人李翔梧、谷滋生、韩文治等人,参加共产主义小组的地下革命活动,并于1926年加入共产党。1927年春天,受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的感召,周仿溪和当时许多进步知识分子一样,毅然投笔从戎,响应北伐。“4·12政变”后,为逃避国民党当局的追捕,周仿溪远走澳门、西安、天津等地,度过多年的亡命生活,最后定居河南罗山,仍以教书为生。1950年,在“镇反”运动中被人诬陷而遭冤杀,时年58岁。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仿溪是个彗星式的人物,他的文学活动,主要集中在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期。1923年3月,他的新诗《破寨之后》和两篇文学短评在《小说月报》14卷3期上同时刊出,标志着他以较高的起点正式步入文坛。嗣后他的名字便频频出现在《小说月报》、《绿波》、《文学周报》、《中州文艺》、《豫报副刊》等报刊上,作品有诗歌、小说、散文、评论等多种形式,成为当时写作最勤奋、知名度最高的河南籍作家之一。大约1924年加入天津绿波文学社。1925年年初在临颍甲种蚕业学校发起成立飞霞文学社,1926年8月创办纯理论批评刊物《飞霞三日刊》,1927年年初增设《飞霞创作刊》,俱通过当时在河南发行量最大的《新中州报》刊出,在省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1927年3月,飞霞文学社的主要成员投入北伐战争,两个刊物随之停刊,周仿溪亦从此在文坛上突然消逝了。可能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那首发表在最后一期《飞霞创作刊》上的诗歌《弹花纷飞下写给她》,竟成了他对文坛和读者的告别辞。此时距他在《小说月报》上首次发表作品,不过四年。
这实在太过短暂了,但就在这短短的四年间,周仿溪成了较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诗人和评论家,与当时人称“农民诗人”的徐玉诺、“魔鬼诗人”的于赓虞,各自在不同的领域、以不同的方式,为河南乃至全国的新文学运动做出了无愧于那个时代的贡献。
在文学活动上,周仿溪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率先组织发起了河南新文学运动早期最有代表性的新文学社团——飞霞文学社。飞霞文学社成立于1925年3月,主要由临颍甲种农校一些爱好文学的师生组成。临颍甲种农校本来是一所以蚕桑养殖和蚕丝加工为主要课程的职业技术学校,但由于著名诗人徐玉诺、叶善枝曾先后在这里担任国文教师,把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作品作为教材搬上课堂,教学生用白话写作,培养了学生们对新文学的浓厚兴趣。文学社成立之前,有些学生在徐玉诺的鼓励和帮助下,已开始在外地的刊物上发表作品。周仿溪与徐玉诺、叶善枝夙有来往,加上出任劝学所所长的工作关系,对这里的情况早有所知。根据他先前曾经参加北京绿波社和协助于赓虞筹建河南分社的经验,知道在临颍甲种农校发起成立文学社团的条件已经水到渠成,所以1925年年初他受聘于该校伊始,便立即着手筹建文学社。他的想法,得到校长田鉴海和学生中的文学爱好者张耀南等人的热情支持。经他介绍,学校又从开封聘请一位新文学作家王皎我,专门负责指导学生写作和编辑刊物。经过不长时间的筹备,以周仿溪、王皎我、张耀南为发起人和主要骨干的临颍飞霞文学社便宣告成立了。其成员除上述三位发起人外,还有程守道、张向明、刘永安、卢景楷等学生。
这个由十多师生组成的文学社团,有半数以上的成员进社以前在省内外的报刊上公开发表过作品。就在1925年4月《小说月报》以“文坛杂讯”头条新闻的位置报道飞霞文学社成立的消息时,正值列入“小说月报丛刊”的新诗集《眷顾》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问世。该书入选作者有朱自清、俞平伯、徐玉诺、朱湘等30人,而飞霞社成员就有周仿溪、张耀南、刘永安、卢景楷四人列名其中。还须要说明的是,这本诗集的书名,就是借用所收周仿溪的一首诗的题目。飞霞社还办有《飞霞三日刊》和《飞霞创作刊》两个社刊,前者以批评为主,每周两期,后者以创作为主,每周一期。所登载作品,绝大部分出自飞霞社成员之手。作为一个远离省城的县办职业学校自发性的文学团体能有如此实力和影响,不仅在河南绝无仅有,而且在全国也不多见。
飞霞社的十多个成员不仅有较高的创作水平,而且有比较一致的进步思想倾向。由于受徐玉诺、叶善枝的影响,临颍农校的学生开始习作便走的是“人生写实”的路子。周仿溪和王皎我作为教师和社团的核心人物,进一步引导他们把作文与做人联系起来,把创作和参加社会斗争实践联系起来,鼓励他们在实际斗争生活中发现素材,用革命的进步的思想来指导创作,从而使这个社团越来越鲜明地显示出左翼的色彩。1925年夏天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临颍,临颍各界民众、青年学生和驻军官兵立即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声援活动,他们集会、游行,罢工、罢课,通电、演讲,封存英日货物,各种活动此起彼伏,长达数月之久。飞霞社成员积极投入其中,发挥了重要的骨干作用。1927年2月,北伐军攻克驻马店,直系军阀靳云鹗部驻守临颍的刘培绪师宣布起义,改番号为“河南保卫军第一师”,响应北伐,并仿效北伐军的编制,设立政治部。当时已是共产党员的周仿溪受组织委派,出任政治部副部长,飞霞社大部分成员亦随之加入政治部做战地宣传工作。不久保卫军作战失利,政治部撤回漯河解散,周仿溪带领部分成员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成为临颍县早期共产党组织的中坚力量,作为文学社团的飞霞社遂告结束。
截至临颍飞霞文学社成立,河南境内似乎还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新文学社团。徐玉诺是最早加入文学研究会的河南人,但他更喜欢散兵游勇式的创作,而对社团活动始终不感兴趣。于赓虞是个群体意识和组织能力都比较强的热心人,曾与赵景深、焦菊隐等发起成立国内著名的绿波文学社,但他当时主要活动在北京和天津,虽然有发展绿波社河南分社的打算,但最终没有结果。到1925年前后,在省会开封的大中学校相继出现了一些社团,如中州大学的霞翳社、文艺研究会、晓钟社、心波社,中州大学附中的春潮社、曙光社,省立二中的微实学社等。但是这些社团或因创作实力不足,或因活动时间太短,大都没有产生大的影响。并且,微实学社其实是继20年代初曹靖华发起的青年学社之后建立的学术团体,这从“学社”的名称便可看出。至于文艺研究会,则明确宣称“以研究国故及文学为宗旨,所谓文艺,盖取其名之广义,如所谓欧洲之文艺复兴者然”。① 研究会内部,没有散文、骈文、韵文、小说戏剧、考证、书法诸组,其中属于“研究国故”者自不必说,与文学相关的,也似乎看不出对当时方兴未艾的新文学有特别关注的迹象。因此,如果没有周仿溪发起的飞霞文学社活跃于其间,当时的整个河南文坛都会逊色很多。
飞霞社作为一个社团已经结束以后,它的主要成员还继续对河南新文学的发展产生着影响。1928年,正在开封参与筹建省农会的张耀南被捕入狱,在狱中还组织“政治犯”们办手抄的文学刊物,用诗歌鼓动战友们的士气,同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著名诗人苏金伞晚年回忆说,当时在开封第一监狱与张耀南一起写诗歌、编刊物的经历,影响了他一生的文学道路。② 到了30年代,原来飞霞社中两个年龄较小的社员张向明(更名张洛蒂)和程守道(更名程率真)后来居上,成为河南左翼文学阵营的中坚。程守道在漯河《警钟日报》主办的“警钟”副刊,成为河南左翼文学的重要阵地。在“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高潮中,另一个影响更大的进步文学期刊《沙漠诗风》在郑州诞生,创刊号就以程守道的诗歌《我们为什么歌唱》作为“代发刊词”:
大众的希望成了破碎的梦影,
水旱天灾加重了心中的创伤,
胸腔中充满了愤激的热情,
都市的铁门关不住苦恼的燕子,
一双双飞进人们的心中。
这是一个梦,
——想把现实粉饰的美丽玲珑,
天是这么冷,心是这么穷,
诗人的笔杆不是驯顺的畜生,
把满嘴的苦汁喷作悲壮的歌声。③
这是进步文学青年的共同心声,它激励着魏巍、穆欣、栾星、周启祥、刘晓等更年轻一代河南文学青年纷纷加入左翼文艺队伍,为呼唤真理和正义放声歌唱。1936年,张向明、程守道与开封的陈雨门、郑州的高紫瑜、许昌的王兆瑞、叶县的刘心皇等15人,发起成立了有一百多个会员的劲风文艺社,实现了全省进步诗人的大联合,把河南新文学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茅盾在回顾中国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后半期的状况时,曾这样评价“青年的文学团体和小型的文学定期刊蓬勃滋生”现象:
这一大活动的主体是青年学生以及职业界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团体和刊物也许产生了以后旋又消灭……然而他们对于新文学发展的意义却是很大的。这几年的杂乱而且也好像有点浪费的团体活动和小型刊物的出版,就好比是尼罗河的大泛滥,跟着来的是大群的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他们在那狂猛的文学大活动的洪水中已经练得一副好身手,他们的出现使得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期顿然有声有色!④
回顾飞霞社的经历及其对河南新文学运动的深远影响,我们对茅盾这段话将会获得更加深刻和生动具体的认识。
通过勤奋的创作实践,拓展和深化了表现20年代河南兵灾匪祸的“火灾”题材,是周仿溪对新文学运动的又一重要贡献。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实际上处于封建割据状态,新老军阀和各种封建残余势力为了争夺地盘,连年征战不息,广大的劳苦大众特别是农民不但要背负用于战争的各种沉重的赋税,而且还要源源不断向战争各方输送兵员,大批被驱赶到前线充当炮灰的青壮年农民和无辜者在军阀混战中丧生,更多的农民流离失所,大片的农田荒芜,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河南地处中原腹地,为各方势力志在必得的军事要冲,战事尤为频繁,经受的灾难也尤为深重。在这里,频繁的兵祸造成了大批农民破产而沦为土匪,而多如牛毛的大大小小的土匪武装又进一步加剧了兵祸给民众带来的灾难,在兵祸匪患交互作用之下,河南大地如同遭遇到一场空前规模的大火,到处烈焰滚滚,到处弥散着死亡与毁灭的恐惧。20年代兵匪横行民不聊生的河南农村生活状况,正是当时文学创作中非常引人注目的“火灾”题材赖以产生的生活基础。在创作中最早表现这一题材的,是自幼生活在豫西农村、对匪患有着切身体验的文坛新秀徐玉诺,而大力倡导这一题材并使之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则是一向以“为人生”为宗旨的文学研究会骨干叶绍钧。1992年夏天,徐玉诺自闽返豫,绕道上海看望叶绍钧,向他口述了家乡鲁山一带土匪横行、杀人放火的惨况以及产生这种状况的社会心理原因。听到这骇人听闻的消息,一向坚守“为人生”创作理念的叶绍钧敏锐地发现这是一个极有开掘价值的题材。他根据徐玉诺口述的素材赶写了一篇纪实性小说《火灾》,与徐玉诺的诗歌《火灾》在1923年元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4卷第1号上同时刊出,从此“火灾”便成为河南匪患的代名词,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徐玉诺那几篇曾经引起鲁迅和茅盾关注和称许的“火灾”题材代表作,如《在摇篮里》(一)、《一只破鞋》、《祖父的故事》、《到何处去》等,便都是在这以后产生的。
叶、徐诗文发表以后,迅速做出热烈回应的是周仿溪。事隔仅一个月,他便在《小说月报》第14卷第3期同时发表3篇内容相关的诗文,其中有两篇评论,分别高度评价叶、徐的《火灾》,并借此进一步申述了以文学形式反映中原匪患的紧迫性和现实意义,表现了他对“火灾”题材的高度重视和对叶绍钧良苦用心的深切理解,同时也表明了他愿意“稍分一点言信(徐玉诺字——笔者)君的重担”,也来从事“火灾”题材创作的郑重承诺。另有一首题为《破寨之后》的诗歌,说明他已经开始实践自己的诺言,并向世人初步展示了自己驾驭这一题材的优越条件与潜在的功力。在此以后的几年间,他主要以《小说月报》为阵地,陆续推出“火灾”题材作品数十篇,与徐玉诺共同成为这一创作领域的两大台柱。
与徐玉诺同期创作的“火灾”题材作品相比,周仿溪的同类作品不仅自有特点,而且别具分量。与徐玉诺的激情控诉不同,周仿溪的一些描写“火灾”的短诗如脍炙人口的《眷顾》,以冷峻取胜:
死神寄居在土匪的枪管里,
小鼠一般探首管外,
眼睁睁望着我,而且啪啪振它的两翼说:
“不要恐怖,不要愁闷了,我随时——
无论白昼或黑夜——
都可以飞快的眷顾着你呢!”⑤
这首诗曾与朱自清、俞平伯、朱湘、徐志摩等五四著名诗人的作品一起结集,作为“小说月报丛刊”第58种出版,书名就借用该诗题目“眷顾”二字,足见它在时人心目中的地位。但周仿溪并不以精致的小诗为满足,而是按照他对叶绍钧提倡“火灾”文学用意的理解,努力营造能够较为全面反映河南兵灾匪患的史诗性的作品。发表在1924年8月出版的《小说月报》“非战文学”专号上的组诗《炮火之花》,就是这种具有史诗性的作品。这组诗共7题47节200余行,其篇幅之大,气势之恢弘,不仅在当时豫籍诗人中绝无仅有,而且在全国范围内也不多见。揭开书页,首先映入读者眼帘的,是被兵匪蹂躏之后的河南城乡一幕幕凄渗悲凉的景象:“暴风急雨般的枪声寂了之后,/什么都毁灭了,/却留下一幅伤心的红色图画。”“一摊摊涂地的鲜血,/一个个躺着的死尸,/都腌芥似的浸浴着我的凄惨的心。”“两岁的幼儿,/活泼泼地笑喜喜地,拿着小竹竿,/挖着爸爸的血摊玩……”“小孩子拍着尸身,/叫着不答应的妈妈……”(《破城之后》)“懒洋洋的蝇儿,/群飞集在沟涯边的弹壳上,‘听呵!/愚蠢的蝇儿,/秋姑娘喊索你的生命呢!/你还在贪食人们的血臭!’”(《战后》)河南自古以来就是最适合人类繁衍生息的地方,是古老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在这里,曾经到处是先民们遗留下来的“巍峨的建筑”,“彩霞下密接着的村落”。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有过自己“全家聚乐的庭堂”。是谁忽然间把它推入灾难的深渊,使这里“只剩下一片凄寂的荒凉”?对此,诗人没有过多地追究那些直接参与杀人放火的兵匪们,而是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北洋军阀,并进而指出连年战乱的深层原因在于他们“心田里的虚荣”、贪婪的私欲与凶残的本性:
军阀是衔着屠刀的屠夫,
小百姓不过是躺在杀床上四肢受缚的瘦猪。
我们的命运呀,
怕只有白刃一闪的瞬间了吧……
军阀们是赌赛胜负的顽童,
小百姓不过是竞走场上的不幸的嫩芽;
我们的生命呀,
都在他们游戏的争赛的脚下断送了。
军阀是铁铸的榨油机,
小百姓不过是烈火炒过的芝麻;
照他们长夜之宴的红灯里,
那不就是我们的膏脂吗?
(《大兵过境时的饮泣声》)
在组诗的主要部分《炮火之花》的最后一节,诗人代表渴望和平、渴望能过上正常生活的普通百姓对反动军阀制造的战乱发出愤怒的控诉、严正的声讨:
炮火之花呀!
你就是悲凄之花吧!
你就是罪恶之花吧!
你开放之地,
便是毁灭之神的宫殿。
我要拿我诅咒恶魅的诅咒,
诅咒你赤红的炮火之花呀!
短篇小说《一束红笺》⑥ 也是周仿溪表现“火灾”题材的一篇值得重视的佳作。小说有一万余字,分为7节,由被劫为人质的主人公清和在匪窟中分别写给朋友和家人的7封书信组成。清和是个家境还算殷实的青年学生,被劫后曾设法同家人联系以求获得赎救,最终却因继母不肯配合而惨遭土匪杀害。7封信只是他在匪窟所写书信的一部分,但内容已涉及人票的日常生活,土匪的审票、撕票,兵匪遭遇,土匪与苦主之间的讨价还价,土匪内部的矛盾,人票与家人之间的利害冲突等各个方面。在人物塑造上,除利用第一人称书信体的方便,极尽委曲地展示了主人公恐惧、悲哀的心理与强烈的求生欲望之外,二架杆霍老六尚未完全泯灭的仁爱之心,继母的冷酷无情,也都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与徐玉诺同类题材的小说相比,本篇在气魄和格局上似乎稍胜一筹。通过这个短篇,仿佛可以看到比周仿溪晚一辈的河南作家姚雪垠20年后创作的《长夜》的雏形。
茅盾曾经敏锐地发现和高度评价1922年以后几年间中国文坛发生的一个喜人的变化:“创作是在向多方面发展了。题材的范围是扩大得多了。作家的视线从狭小的学校生活以及私生活的小小波浪移转到广大的社会的动态。‘新文学’渐渐从青年学生的书房走到十字街头了。”他用来证实这一变化的首要的依据,就是“那时有满身泥土气的从乡村来的人写着匪祸兵灾的剪影”,并特别指出“如同徐玉诺”。⑦ 在促成这一重大变化方面,曾郑重承诺愿意“稍分一点言信君的重担”,并确实出色地实践了这一承诺的周仿溪,也是功不可没的。
与创作的实绩相比,周仿溪在理论批评方面的建树更为重要。在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前半期,整个理论批评界根本听不到河南的声音。直到1923年年初于赓虞的两篇诗论和周仿溪关于《火灾》的两篇短评分别在《新民意报》和《小说月报》发表,才开始改变这种状况。在其后直至第一个十年结束的四年间,于赓虞尚在天津、北京两地一边求学,一边从事绿波社的文学活动。这时他的主要兴趣在于诗歌创作,偶有诗论发表,影响也不大。而坚守在河南的周仿溪却先后以鲁迅热情支持的《豫报副刊》和他自己主办的《飞霞三日刊》为主要阵地,发表评论文章数十篇,成为这一时期河南新文学界唯一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批评家”。⑧
周仿溪有自觉的现代批评意识。1925年8月他在《豫报副刊》第95、96两期连载的《谈谈文艺批评》,是目前所知河南新文学作家最早的一篇研究文艺批评的文章。翌年他又在《飞霞三日刊》连续发表《批评与中国文坛》、《我骂人的态度是这样的》、《再谈谈我骂人的态度》等文,密切联系当时中国与河南文坛实际,就此话题进一步展开论述,内容涉及文艺批评的性质、任务,文艺批评与创作的关系,开展文艺论争的迫切性,文艺论争的方法以及文艺批评的社会作用等诸多方面。他认为,从创作的角度讲,“批评是文学的指南针”,从阅读的角度讲,“批评是文学的解释”,“进步的活跃的动力,常是生于两力的冲突间”。要想得到创作的繁荣与艺术的普及,“文学不能没有批评”。根据国外文坛的情况,他甚至提出“批评之量要多于创作”的主张,以为没有足够的量,“质那一面更不用问了”,批评的价值也就无从实现。而当时中国文坛的实际情况又是怎样呢?他非常痛心地指出,那些“稍有一点文名”的所谓“批评家”,对于普通作家特别是文学青年的新作,往往采取“不理主义”,“你请求一句批评,他只是泥佛一般地不理”;他发现当时全国著名的几十家刊物所载批评文字非常有限,创作与批评数量之悬殊,“竟得出六十与一之比”。为此他大声呼吁更多的人来从事和关心批评工作,特别对名不见经传的文学青年们寄以厚望:
兄弟,和我一样无名的走卒们,我们虽渺小,然而我们是有眼的,会看见现在文坛上的缺乏者;我们是活着的,会叫出现在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我们知道文艺要有批评,知道一篇创作至少要有好几个批评家的批评,然后在批评里才会给我们文艺的真价……我只希望和我一样无名的走卒们都睁大眼睛看,张大喉咙嚎。⑨
周仿溪的这些论述,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大多已是常识,但在现代文学批评产生之初,在远离全国新文化运动中心的边缘地带河南,能够发出这样的声音,却是异常地难能可贵。在充分认识到文学批评的重要性的基础上,周仿溪经过艰苦努力,创办了当时国内唯一的文学理论批评专刊——《飞霞三日刊》。《飞霞三日刊》每逢周一、周四随报刊出,每期另印单页50份,分送文学社成员及有关部门或读者。该刊于1926年8月创刊,至1927年3月停刊,前后大半年时间,共出五十多期。与当时全国二百多家比较有名的文学期刊相比,它最突出的特点便是“专载评论不载创作”,是一份纯理论批评刊物。飞霞文学社为什么把自己的刊物办成批评专刊,旗帜鲜明地提出“专载评论不载创作”的原则呢?对此,周仿溪撰写长文《批评与中国文坛》,郑重声明:
我们的《飞霞》不是为我们飞霞社同人而存在,而是为全国文坛的欠缺而存在,我们兼载创作,那是于同人们最便利不过的,而尤其便利了我和皎我。但我们为国内文坛计,为同人对国内文坛应负的责任计,都不能让我们这个小小刊物兼载创作。现在国内每三日出现的创作有多少,读者自然会知,多我们一篇或半篇,那有什么要紧?可是那么一来,中国现在立刻便没有文学评论的专刊。不必说六十与一这比例,即此缺少文艺评论专刊这一项名目上,仍亦觉得有好大损失了。
愿爱我们的朋友们哟,我们的不敢作背弃良心的谦让,恐正是你们所期待的吧!⑩
正是出于对中国文坛的高度责任感,出于一代具有清醒的批评意识的新文学作家的学术良心,周仿溪及其同人坚定不移地把《飞霞三日刊》办成纯理论批评刊物,而且把它办得有声有色。从评论的范围上看,这份刊物虽然偏居一隅,其眼光却不为地域所囿,而能立足本地,面向全国。从学生的习作、无名作者的小说,到五四时期中国新诗的扛鼎之作《凤凰涅槃》,以至刚被介绍到中国不久的世界名著《少年维特之烦恼》,无不在它的批评之列。从评论的对象上看,它几乎涉及了文学运动、理论建设、文学批评、文学创作、作家修养、外国作品的翻译介绍等各个方面。被评论到的刊物,有《小说月报》、《创造月刊》、《洪水》、《沉钟》、《黎明》、《文周》、《文旬》、《一般》、《文艺》、《铎声》、《幻洲》等数十家之多。至于被评论到的作家、评论家,从大名鼎鼎的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郑振铎,到活跃于全国文坛的成仿吾、赵景深、宗白华、郭绍虞、谭正璧、穆木天、王鲁彦、高长虹,再到河南作家徐玉诺、于赓虞、段凌辰、陈子翼,以至刚刚崭露头角的文学青年王志刚、王锡钦等,不胜枚举。从形式上看,所载文章既有内容厚重、富于学术性和理论性的长篇宏论,也有文笔犀利、形式灵活的文学短评。其中还有一些专栏,如周仿溪的“诤言”,王皎我的“读书短札”、“不平言”,“肚痛话”,程守道的“诗林概评”等交替刊出,更使这份刊物从内容到形式都显得丰富多彩。这样一份批评专刊,又借助《新中州报》的发行优势得以在省内外广泛传播,其对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河南新文学运动的积极促进作用是不难想见的。
周仿溪在文艺批评方面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贡献,就是在河南最早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文艺现象和文艺作品,热情呼唤“第四阶级的革命文艺”,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沈雁冰、沈泽民等遥相呼应,为三十年代左翼文艺主潮的到来做了理论的探索和舆论的准备。他在《评郭沫若〈曼陀罗华〉》(《飞霞三日刊》第20期)一文中说:
现在主张漫无限制的唯情主义的一切作家,主张漫无限制的自由主义的一切作家,都反对一切的法律、道德和规约,这是与共产主义最不相容的。他们老是漫无限制的任情去动,这是一种最危险不过的恶趋势,是比一般人视为危险的共产主义犹危险万分的恶趋势。得有另一种力量去阻挡它的,只是在现在的文艺里,现在国内的文艺里,是寻不出阻挡这恶趋势的另一种力量。有之,便是第四阶级的革命文艺。
在那时,周仿溪能把握时代的脉搏,对“第四阶级的革命文艺”寄以厚望,预见革命文艺主潮的兴起,表现了一个早期共产党人不同寻常的眼光。正是由于这种眼光,他在评论当前的小说创作时,特别关注描写民众尤其是“无产的穷迫的民众”的疾苦的作品,但他没有阶级论的教条,而认为好的作品应该是“充满着人生追求的理智渴望和感情渴望的作品,是充满着人性中的神性的活跃与健旺与奋厉与伟大的作品,是充分区分着人性中的神性与兽性的作品,而绝不是孕育卑劣兴趣迎合卑劣兴趣的那种卑劣的小说作品”。(11) 刚刚步入文坛时,他是“人生写实”派的忠实信徒。在初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以后,他开始用辩证的观点解释文艺与人生的关系:“文艺固然离不开人生,但决不只是人生的再现,决不只是人生的照抄,决不只是无选择无剪裁一丝不遗的将杂乱或无精彩的人生描绘下来便算了事”,文艺还应该是“人生的解释”、“人生的指导”、“人生精义的提炼”。(12) 1927年3月,大革命的烽火即将燃到中原腹地,他又组织同人在《飞霞三日刊》发表文章,进一步指出在社会革命高潮来临之际,文学又是“社会走向真正改革之路的预兆,是人类的丑恶灭亡的丧钟,是正义与强权的握手”(13),呼吁文学家关注火热的斗争生活,投入火热的斗争生活,血与广大民众流在一起,在革命烈火中“产生血的作品篇章”。(14) 在这里,我们似乎提前听到了30年代激进的左翼文艺批评家的声音。
周仿溪虽然过早地离开了文坛,未能给后人留下更多的足以传世的作品,但他为新文学的发展而努力开辟草莱之功,是不应忘记的。
注释:
①③李允豹主编《河南新文学大系·史料卷》第44,45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②苏金伞《创作生活回顾》,《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3期。
④⑦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茅盾文艺杂论集》上集第527,53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
⑤《小说月报》第14卷第8号(1923年8月)。
⑥《小说月报》第17卷第1号(1926年1月)。
⑧孙广举主编《〈河南新文学大系·理论批评卷〉导言》第2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⑨⑩周仿溪:《批评与中国文坛》,《飞霞三日刊》第27、28期(1926年11月22日、25日)。
(11)周仿溪:《驱逐卑劣的小说作家》,《飞霞三日刊》第20期(1926年10月28日)。
(12)周仿溪:《文艺与人生》,《飞霞三日刊》第19期(1926年10月25日)。
(13)王皎我:《炮火血光中的一朵花》,《飞霞三日刊》第53期(1927年3月14日)。
(14)王皎我:《给中国文艺研究者打几针六○六——中国人的血与中国文学研究者的血》,《飞霞三日刊》第53期(1927年3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