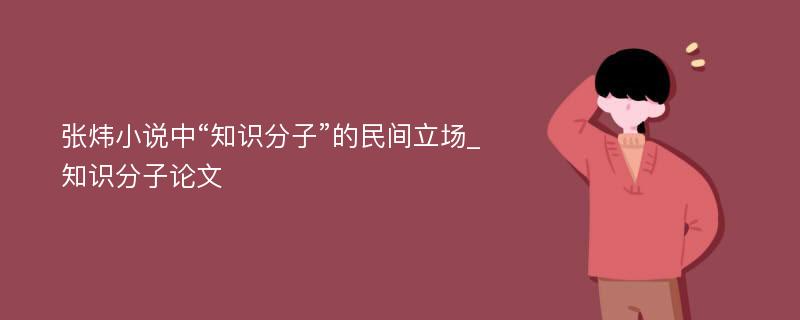
张炜小说中的“知识分子”民间立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分子论文,立场论文,民间论文,小说论文,张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4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12x(2012)04-0044-04
作为一个植根于山东半岛辛勤耕耘的作家,张炜始终用饱满的笔触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进行忘情书写。早期的短篇小说汩汩流淌着对昔日农村自然、美丽、纯朴、和谐环境的深切怀恋;在一系列长篇小说中,或者半自叙性地对出生地不惜笔墨地热烈回想追忆,或者借小说人物的经历体验细节性地呈现远河远山的蔚然、神秘和无尽藏,或者直接讴歌赞美,或者通过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批驳痛斥来表达自己坚守田园领地的决心;更多地是把关切的目光深入到乡野,审视这片热土上生生不息的人和古往今来的事,把悲悯的人文关怀和对历史文化、社会现实的批判立场指向“民间”。对于民间的内涵,陈思和教授最早从描述文学史的角度出发作了概括[1]。自从民间问题提出以来,众所公认,张炜的小说创作张扬着鲜明的民间立场,蕴含着多样化的民间审美形态,呈现出别具特色的民间文化品格。他不仅承认自己的创作源泉来自民间,相信民间大地的“生力”,作品具有浓郁的民间底色,亦从不避讳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写作者。实际上,张炜的知识分子立场比他所持有的民间立场更加鲜明而坚决。
一、意义域界的包容性分述: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立场
一般认为,民间与国家(庙堂、政治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知识分子处于三个不同的层次,甚至是相互对立的。民间“是指中国文学创作中的一种文化形态和价值取向”,“指一种非权力形态也非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形态的文化视界和空间,渗透在作家的写作立场、价值取向、审美风格等方面。”[2]当代作家不仅眼光向下,置身民间,精神上也与民间大地的气息相贯通,在写作立场上普遍呈现出一种深切的民间关怀。然而绝对纯粹的产生于民间的文化立场是不存在的,它只能通过知识分子的精神表现来传达。所有作家包括张炜的所谓民间立场只是一种“知识分子”立场,必然是知识分子的一种文化立场转换。这种立场是以试图真实表达民间的原始存在为指向的,除了记录民间的生活琐事,描述风情民俗,开启被历史尘封的民间记忆,尤其是通过还原和想象等技术手段,描画了广袤的民间大地上芸芸生灵的生活图景和精神图谱,传达着作者对于民间的思考,特别是作者在民间背景下的价值确认和精神追索。
王光东把张炜的写作归为知识分子的“民间想象”[3],既然是想象,那么在对民间大地的描述上就会与现实存在距离,或者在精神上有所隔阂。“子非鱼,焉知鱼之乐?”这种见解虽显偏颇,不过倒让人思考张炜到底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来进行小说叙述?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立场是否冲突,能否达成协调统一呢?论者又指出,他(陈思和)所说的“民间”有两层意思:一是作为自在的民间文化空间,一是作为价值立场的民间价值取向,也就是自觉地把“民间”与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和精神追求联系在一起,在自在的民间文化空间中发现精神寄存的意义。在谈到民间与知识分子精英文化之间的关系的时候,王光东认为两者不应该是对立的关系,“知识分子永远也无法摆脱与民间之间的关系,关键在于以什么样的价值立场和原则走进民间。”[4]这实在是对陈思和先生非此即彼相互对立的民间论调的一个有益补充。
意大利葛兰西把所有的人都看作是知识分子,以其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来剥离出真正的知识分子角色。班达、福柯、萨义德也把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推及为类似“天下为公”的责任承担者。[5]张炜崇尚劳动,把写作视为一项与农民耕种一样值得尊敬的劳动,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理解的知识分子绝不是不食人间烟火、远离劳动人民的方外之士,也不会把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对立起来。张炜对在文学作品中轻贱糟蹋知识分子的做法感到不满,认为“知识分子是劳动精神的集中体现者,是辛苦和勤劳勇敢的典型,像工人又像农民——像一切好的劳动者。嘲笑知识分子就是嘲笑劳动者”,知识分子是劳动者中的“顶尖人物”,不应该被挖苦和诽谤。[6]在这个想做知识分子而不得、想承担社会责任而不能够的今天,张炜在小说中过分关心知识分子命运自有其独特意义——如果连知识分子自己的命运都把握不了,还谈何“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张炜是以一个传统知识分子或者文人的身份出场的,他所表达的民间立场实际上是一种知识分子立场。以精英知识分子的身份,站在民间的立场,表达出的应该是两种混合起来的声音。似乎很矛盾,但也很真实,这正是张炜的特异之处。中国文学或者中国文化历来都由两种人来书写,上层文人(知识分子)以及下层民众的自身写照和情感表达,它们并不互相排斥。就像作为民间歌谣总集的《诗经》,“采诗之官”既是采集者、记录者,同时也是加工者、创造者,知识分子的介入使得这些歌谣具有了代言人,使其更具有文学审美价值和传播意义。在张炜的小说中,真实也好,想象也好,它们竞相托出,都放到了最大化,他始终用知识分子的眼光看视芸芸众生,精心构筑自己的民间世界,他在思考,在倾诉,在行动,其间安放着一颗知识分子起码所具有的“良心”。
二、复杂社会域界中的自我体验:知识分子叙事
知识分子深入民间、书写民间早已经不是问题,比如,莫言对高密东北乡近现代乡村历史的血腥和变态的描写,贾平凹对于陕西商州城乡间鸡毛蒜皮事无巨细的实录,都获得了极大成功。如果说贾平凹这个大俗大雅的作家在作品之外还有一个知识分子在冷眼观看的话,那么张炜则把自己的知识分子角色完全融进了小说中,甚至可以从小说中找到作者的影子,寻觅到作者的生活经历,更能触摸到作者的思想理路和精神品质。与其他作家不同,张炜很少与描述的对象保持绝对的距离,这决定了他不擅长于冷漠的叙事;他的一些小说视角转换非常明显,或者采用第一人称,或者第二人称,或者第三人称,跳跃反复,却很容易让人理清;而作品中的人物命运及个性与作者的命运及个性又互相映衬、补充、对接,形成多声部的复调韵味。张炜的小说中总有一个“我”在,其中许多都是以有文化有知识的人作为叙述主体,对知识文明和文化力量的追求也往往成为表达之目的,追问着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郁结着知识分子的文化情感。
知识分子是作者不可抛却的身份,尽管这种身份在小说世界中常常被邪恶势力、政治权力、世俗力量或者商品经济所摧折,正因为如此,知识分子身上才更有故事可说,知识分子的命运浮沉更能反映庙堂、民间及社会的动荡变迁。在《我的田园》、《柏慧》、《家族》、《外省书》、《能不忆蜀葵》、《你在高原·西郊》(即《你在高原》系列十部书之《曙光与暮色》)、《怀念与追记》、《刺猬歌》等小说中,我们能看到作者的人生履迹和精神文化脉络。张炜笔下知识分子的命运,反映了社会知识阶层的变化,他们从受人尊敬的位置上崩落下来,跌进实实在在的民间,是一个去神圣化的过程。《刺猬歌》中的老校长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受到村霸唐老驼的嘲谑欺凌,斯文扫地,残害致死。他的儿子廖麦受到通缉追杀,接受文化教育回到乡村后只想过“晴耕雨读”的生活,但是唐老驼儿子的拆迁机器逼近了家园,女儿认贼作父,妻子与自己产生隔阂,孤独的他只得选择离开。连独善其身的愿望都实现不了,知识分子的处境可想而知,其尴尬情势是知识分子在社会运程(商品经济大潮)中的真实记录。
张炜小说作品中重点描写的人物,有些看上去是“粗人”,从事的是与文化无关的工作,但他们却对知识、文字、书写保持着执迷的兴趣和虔诚、崇拜心态,有着不懈的追求。看葡萄园的老得(《秋天的思索》)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喜欢用铅笔在纸片儿上写写画画,不准别人看,又想让人了解这项神圣的工作,于是让小来“把手放在衣服上擦干净”,把给杂志社寄送的信封纸放在蓑衣上,上面整齐地写着一行行的字,他说:“这就是‘诗’,你慢慢看吧,不要吱声。”他高兴的时候吟唱自己的诗:“……春天一般化/春天干燥/秋天很好了/秋天往家收东西/到了秋天/我高兴得笑嘻嘻……”他感叹:“书是个好东西啊!”老得在《护秋之夜》中再度出现,是被青年男女谈论的偶像,形象高大光辉,昭示的是光明的未来。这些作品反映的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社会景象,农村封建势力或者强权者披着合法化的外衣中饱私囊,欺凌农民,老得这个没有多少文化的人通过写“诗”,向杂志社投稿,以期达到揭露不法干部的目的。知识就是力量。张炜小说描写了特殊年代人们对知识的渴求,以及对文化人的崇拜心理。《远河远山》中的小主人公对纸与笔情有独钟,不停地写,为了寻找志同道合的写作者疯狂奔走,是一次渴求知识的心路之旅。《丑行或浪漫》中大胆泼辣的刘蜜蜡丝毫不掩饰对有着身体残疾的老师雷丁的崇敬和对铜娃的爱意,她学会了阅读,对农村邪恶势力也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古船》中的隋抱朴通过阅读《共产党宣言》,在书中寻找真理和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最终从老磨房中走出,成为力挽狂澜、敢于担当的人物,主持了粉丝厂的局面。
三、现实压迫中的心灵突围——知识分子精神启蒙的无奈
把希望寄托在知识理性身上,从中寻找突破人生,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是张炜表达的一个主旨。一方面作者本身就是一个知识分子,有着类似的经历,在小说创作时也刻意地进行点染抒发,这没有什么问题。另一方面,在作者看来,知识分子沉到民间,其处境并不好,还要与周围的“黑暗的东西”进行斗争,武器即是知识和文化以及科学理性。作者也认识到,斗争对象不仅是“敌人”,还有亟待启蒙觉醒的大众,而未开化的大众则是站在不理解知识分子立场上的,甚至是敌视的,势不两立的。“好的知识分子像泥土一样质朴,而且具有强大的滋生力。”“从历史上看,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警觉和反对技术主义的传统”[7],张炜沉入民间不仅是为了个人的情趣,为了逃避社会现实,安托不为主流意识形态所容的心灵,而是借助民间性的表达试图开辟一块净地,重新建筑扶植知识分子信心的文化飞地,因为这里的情形更为复杂,这将是一个艰巨的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最新出版的《你在高原》系列十部书中,张炜一如既往地采用知识分子视角观察社会。作为知识分子身份的“我”直接出现在作品中,对于弱者一方,他是抱打不平、解人困厄的角色,同时代表的又是理性,矛盾的时候主张通过合法途径解决,避免付诸非法行动。但是当“我”试图介入的时候,却发现一己之力的微小,获得真相阻力重重。知识分子们不仅受到特权阶级或者既得利益者的威胁、武力报复,还不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所理解。《橡树路》、《鹿眼》、《忆阿雅》、《荒原纪事》等,都通过制造激烈的矛盾,写出了“我”周旋于矛盾边缘或者置身于事件漩涡时的无能为力感。作者几乎在所有的小说中都动用了大量篇幅,来写青年知识分子的流浪之旅。他们是被迫逃离城市的。如果说在过去他们的祖父辈遭受的是无奈的政治迫害,今天的知识分子(被讥讽为“叽叽分子”、“鸡巴分子”)所处的环境和形势一样严酷,他们不仅要面对情感危机、亲人的背叛,还要体验生存的艰难,非正常化的学术之争,利益之上的党同伐异,不能不让不善此道的人落荒而逃,以不合作的姿态来抵制对抗。
对于知识分子在民间性叙述中的价值,王光东认为,因为有了知识分子独立的精神介入和自觉反思,关注个人,关注那些受到抑制、伤害,脆弱地呈现甚至隐蔽存在的生活状态,通过叙事文本形成一种意义的敞开。知识分子的批判和反思在同时面向知识分子主体、民间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禁忌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民间的反抗意识,在精神上与被压抑和遮蔽的民间世界产生深刻的同构,民间的生存言说和审美意义就可以通过知识分子的主体转换而得到实现。[3]正如他所言,进入新时期的知识分子因为主要借助理性精神将文化反思集中在自我疗伤和政治意识形态批判上,从而进入了一种盲区。然而在当代,知识分子的歌哭似乎已没有多少市场,也已无资格去做鲁迅《药》中的人血馒头。在非难者看来,张炜远不如莫言、贾平凹、余华、苏童等人聪明,他们在写作中干脆放弃了知识分子立场,只用通俗的故事打动人。张炜似乎并不精于此道,在知识分子备受奚落消解的时代,其“矫情”评价也在于放不下知识分子的身份。“民间对苦难的承受力并不能打动张炜。他告别了小村,继续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孤独之旅,他并没有把民间大地上的天然生机带进行囊。用‘退守民间’来形容他们是非常恰当的。”[3]如何在主体反思、文化关怀和人文建构等多重维度下进行民间意识形态的表达,知识分子作家确实应该承担起批判和重建的双重责任。
四、拯救与自救的悖论——张炜民间立场的不彻底性
陈思和在使用“民间”这个概念时,包含着两个层面的意思:第一是指根据民间自在的生活方式的向度,即来自中国传统农村的村落文化的方式和来自现代经济社会的世俗文化的方式来观察生活、表达生活、描述生活的文学创作视界;第二是指作家虽然站在知识分子的传统立场上说话,但所表现的却是民间自在的生活状态和民间审美趣味,由于作家注意到民间这一客体世界的存在,并采取尊重的平等对话而不是霸权态度,使这些文学创作中充满了民间的意味。[1]张炜属于后者。如上所述,他不仅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且小说中的重要人物或者叙述者往往可以纳入到知识分子范畴。《刺猬歌》中的廖麦读过大学,具有传统文人的思想观念,向往晴耕雨读的生活,固守自己的家园,对抗现代文明的侵蚀,对过去经历的苦难要写一部“丛林秘史”。廖麦身上有作者自己的影子,凝结了作者自己的亲身感受。然而,正是这种借他人之口来表达自己的主观立场的做法导致了其民间立场的不彻底性。因而我们可以认为,作者具有民间情怀,小说中流溢着民间意识,沾染了民间文化的气息,但尚不能称之为民间立场坚定,更不将其纳入到民间文学的范畴。
张炜曾说,“真正的知识分子立场与民间立场在其内部又是相通的、一致的,它们二者可谓殊途同归。知识分子立场正是以民间立场为依据的。”[8]诚然,知识分子有责任去表述民间,或者通过对民间的书写来表达其对立面——国家的或政治的意识形态。但是知识分子是否能够与民间保持一致,特别是张炜能否坚定地融入到民间中去,却是个问题。我们只能说,民间丰富的资源让张炜获得了充沛的想象力,给了他自由翱翔的空间,给了他复杂多样的情感世界,以及一个进行道德曲直判断的尺度,[9]而很难让他的表现能够像陈思和说的那样达到民间自在的生活状态和民间审美趣味完全契合。“要有放眼世界的气度,先得自己有根。”[10]张炜认为自己的根深深地扎在民间。但是作为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城市人,张炜与民间大地是油水分离的,融入野地只是一声宣言,实际上他只是徘徊在故乡民间上空的一个孤魂野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