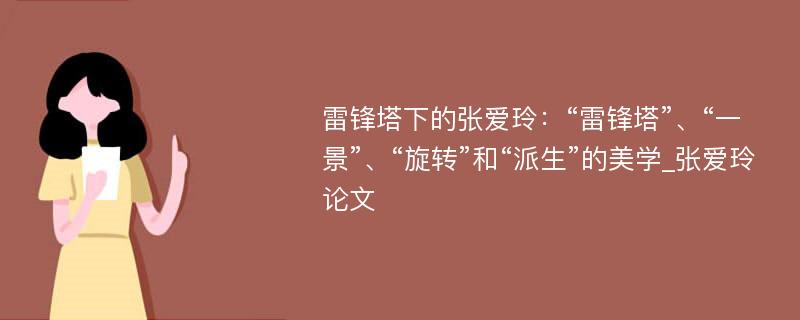
雷峰塔下的张爱玲:《雷峰塔》、《易经》,与“回旋”和“衍生”的美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雷峰塔论文,易经论文,美学论文,张爱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爱玲(1920-1995)研究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显学。近年随着旧作不断出土,张的文名与时俱进,各种相关著作也层出不穷。但其中有一个面向仍然没有得到充分探讨:那就是张爱玲一生不断重写、删改旧作的倾向。她跨越不同文类,兼用中英双语,就特定的题材再三琢磨,几乎到了乐此不疲的地步。因此所呈现出一种重复、回旋、衍生的冲动,形成张爱玲创作的最大特色之一。
2009年,张爱玲的两部英文小说《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和《易经》(The Book of Change)重被发现,经过整理,于2010年问世。这两部小说皆写于张爱玲初抵美国的50年代中后期。两部小说都有浓郁自传色彩,也为张爱玲反复改写(revision)与双语书写(bilingualism)之美学提供了最佳范例。张爱玲对自己生命故事的呈现无时或已;从散文到小说到图像、从自传式的喁喁私语到戏剧化的昭告天下、从中文到英文都多所尝试。正是在这两部新发现的英文小说中,我们得以一窥她种种书写(和重写)间的关联。两部小说的题目,一则指涉中国民间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传奇,另一则取法中国古典玄奥晦涩的《易经》,似乎也暗示张爱玲有心要将她的创作融入更为宽广的历史想象和时间轮回。
通过对这两部小说及其它文本的比较阅读,本文将就以下三个方面作出进一步观察:
1.相对于写实/现实主义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形式,张爱玲反其道而行。她穿越修辞、文类以及语言的界限,以重复书写发展出一种特殊的美学。这一美学强调“衍生”(derivation)而非“揭示”(revelation);突出“回旋”(involution)而非“革命”(revolution)。
2.透过对自身故事的多重叙述,张爱玲以重复枝蔓的形式颠覆传统家族历史的大叙事(master narrative)。她的记忆不断节外生枝,瓦解了“过去”独一无二的假设。更重要的,通过书写,她化记忆为技艺,也重塑过往吉光片羽的存在与形式。
3.张爱玲创作中回旋、衍生的倾向也带出了一种独特的(文学)史观。这一方面她的前例是《海上花列传》(1894)与《红楼梦》(1792)。张的史观促使我们思考她后四十年的创作其实不只限于她以各种形式重写的自传故事,也同时包括另外两项计划:一是将吴语的《海上花列传》翻译为国语,再翻译成英文;另外则是通过细读文本、文献考证以及传记研究的方式参详《红楼梦》。
20世纪文学的典范以革命和启蒙是尚。严守这一典范的作家和批评家自然不会认同张爱玲的创作意念和实践。但我以为她的写作其实是以一种“否定的辩证”(negative dialectic)方式体现历史的复杂面,也为我们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考察,提出发人深省的观点。
1938年,上海的英文报纸Shanghai Evening Post(《大美晚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What a Life! What a Girl's Life!”的文章①,作者是一位十八岁的中国女孩,名叫Eileen Chang(张爱玲)。在这篇文章中,张爱玲描述自己在一个衰败的贵族之家成长的点滴,她与父亲和继母的紧张关系,以及曾被父亲禁闭在家中一个空屋里的经历。期间她患了伤寒,因为没有及时用药而几乎送命,最后她在奶妈的帮助下得以逃脱。
这篇文章是张爱玲初试啼声之作,也预告了20世纪中国天才女作家的登场。②历史的后见之明告诉我们,张爱玲未来写作生涯中挥之不去的主题已然在此出现:颓靡的家族关系、充满创伤的童年记忆以及对艳异风格的迷恋等。这篇英文文章同时也预示张爱玲穿梭于双语之间的写作习惯。“What a Life! What a Girl's Life!”发表六年以后有了中文版本《私语》(1944)。同一时期的其它中文文章如《童言无忌》也有所印证。到了1950年代后期,这些文字统统化为了她的英文小说《易经》的素材。③
《雷峰塔》原是《易经》的第一部分,后来却被张爱玲取出独立成书。在撰写英文《易经》的过程中,张已经开始构思写作它的中文版。这便是张1976年大致完成、却积延不发的《小团圆》。此书迟至2009年方才出版。
从散文到小说、从自传性的“流言”到戏剧化的告白,穿梭于中英文之间的张爱玲几乎用整个一生反复讲述“What a Life!”的故事。但就她重复书写与双语书写的美学而言,这远非唯一例证④。从《十八春》(1950)到《半生缘》(1968),从英文的“Stale Mates:A Short Story Set in the Time When Love Came to China”(1956)到中文的《五四遗事》(1958)⑤,都是如此。我已在别处讨论过张爱玲的英文小说The Rouge of the North(1967)的多个分身⑥:1943年张创作了中篇小说《金锁记》,50年代将其翻译为英文,并在1956年扩充为长篇小说Pink Tears。Pink Tears经过60年代的多次重写,最后以The Rouge of the North的面貌问世。同时,她又将The Rouge of the North题为《怨女》,译回了中文。就这样,在二十四年的时间里,张爱玲用两种语言至少写了六遍《金锁记》⑦。
我们可以将张爱玲的重写习惯归结为一种弗洛伊德式的冲动;借着一再回到童年创伤的现场,她试图克服创伤所带来的原初震撼。我们也可以将她故事的多个版本解读为她为对“家庭罗曼史”的多重叙述;对过往琐事每一次的改写都是诠释学的实践。另一方面,张爱玲重复迭加的写作也不妨看作是种女性主义诉求,用以挑战父权社会主导的大叙事。张仿佛不再能相信她所置身的语境。通过对语言、文类的反复跨越,她消解了父权社会号称说一不二的话语。她将英文和中文视为同等传播媒介,因为理解她的生存环境既已疏离隔膜如此,在传达人我关系的(不)可能性时,异国语言未必亚于母语。这也使得她的双语书写更具有辩证性。
总而言之,对于张爱玲来说,重写既是袪魅的仪式,也是难以摆脱的诅咒。尽管写实/现实主义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形式,张爱玲穿越修辞、文类以及语言界限的重复书写却孕育出一种特殊的创作观。她的写作不求“重现”(represent)而只是“揣摩”(approximate)过往经验;它深入记忆的洞穴,每下一层甬道,就投下不一样的光亮。更重要的是,通过写作,记忆转化为技艺:藉由回忆,过往的吉光片羽有了重组的可能,并浮现种种耐人寻味的形式。书写与重写是探索性的艺术。追忆似水年华并非只是宣泄和耽溺,新的、创造性的欢愉(和痛苦)也随之而生。
张爱玲是抗战上海沦陷时期最受欢迎的作家。在一个爱国文学和宣传口号大行其道的时代,她用小说和散文(包括中文和英文)描绘历史的偶然与人性的脆弱,并以此大受欢迎。她的离经叛道还体现在她与胡兰成(1906-1981)的短暂婚姻上;胡是个新旧夹缝之间的文人,其时依附南京傀儡政权。由于张爱玲的政治立场暧昧,写作风格特立独行,战后颇受到同行抵制。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她更被排挤到文坛边缘。
1952年,张爱玲离开大陆。在她滞留香港的三年间,她写作出了两本英文小说《秧歌》(The Rice Sprout Song)和《赤地之恋》(Naked Earth)。1955年,张爱玲移居美国。为了持续写作事业以及生活需要,她决定以英文创作。1956年,她完成了Pink Tears,一年后又开始了另一个计划。从张爱玲和老友宋氏夫妇——即宋淇和邝文美——的通信来看,这个新计划将以她的个人经历为蓝本,从孩提时期写到与胡兰成相恋。⑧张爱玲在1961年提及了这一作品的名字:《易经》(The Book of Change)。之后她似嫌这部小说太长,希望分册出版。到了1963年,小说的前半部分被命名为《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
如上所述,张爱玲出版英文作品的经验颇为曲折。Pink Tears经历了数次修改,直到以The Rouge of the North为名方才出版。《易经》和《雷峰塔》的命运甚至较Pink Tears更不顺利。在1964年张爱玲给宋淇的信中,她谈到屡遭退稿,挫败的感觉与日俱增;与此同时,她也发现越来越难按最初的设想完成这部作品。依目前所见,《易经》的最终版本根本未触及张胡之恋,它只讲述了张爱玲在香港的学生时代(1939-1942),以珍珠港事变、香港沦陷后张爱玲返回上海为结局。
1964年之后,张爱玲似乎全盘放弃了出版《易经》的希望,但显然对她未完成的计划念兹在兹。她继续写作,而这一次用了中文。十多年后,《小团圆》的初稿完成。张爱玲曾期待这部《易经》的中文(延伸)版面世,以交待前半生的一切,然而事与愿违,《易经》和《小团圆》都未能在张爱玲生前出版。
我们现在可以回到《雷峰塔》。我们要问,相对于它的前后分身,像“What a Life! What a Girl's Life!”《私语》以及《小团圆》等,这本小说的意义何在。小说中的主人翁名叫琵琶(Lute),也是张爱玲的自我投射。全书以她四岁那年目送母亲露(Dew)与姑姑珊瑚(Coral)出国赴欧为开端,讲述了她童年成长的各个阶段,一直到她与父亲和继母大吵一架后,被禁闭起来几乎送命。在保姆何干(Dry Ho)的帮助下,琵琶最后脱逃,寄居已经离婚的母亲处。最后她准备负笈海外、何干告老退休。小说在两人道别声中戛然而止。
对于熟悉张爱玲早期作品的读者来说,这些内容全都似曾相识。小说主要源自《私语》和张爱玲其它的描述童年及青少年时期的文字,在人物和情节方面的改动微乎其微。然而,《雷峰塔》毕竟不仅仅是张爱玲早期自传式散文的小说化。“What a Life! What a Girl's Life!”写于少女张爱玲劫后余生之际,不啻是对自己所遭受的家庭虐待的控诉。《私语》时期的张则已是战时上海文坛新星,笔下充满着将身世现身说法的表演冲动。到了写作《雷峰塔》的时候,她已远离家国、自我放逐。当年那些创伤已经过了二十年,自然拉开了时空和情感上的距离。当然,《雷峰塔》的写作也不乏其它动机。张的母亲在1957年去世,同年她开始了这部小说的写作;她的父亲则已早在四年前故去。因此,《雷峰塔》不妨视作张爱玲在脱离父母阴翳,重获(小说创作)自由之后,开始讲述家族故事的第一步尝试。
就文学形式而言,《雷峰塔》从一个“风尚喜剧”(comedy of manners)逐渐演化为“哥德式的惊悚小说”(gothic thriller)。琵琶的父亲榆溪(Elm Brook)与母亲露皆出身于名门望族,自小订亲却婚姻失和。榆溪的妹妹珊瑚倒成了露的密友;她们结伴游历欧洲,并在与榆溪决裂这件事上结成了同盟。琵琶的家族各房名为独立却又互相影响,衍生出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小说几乎是以人类学式的姿态描写这些关系,不免使人想起《金瓶梅》以及张爱玲最为钟爱的《红楼梦》。
但张爱玲也敏锐地意识到,那烘托《金瓶梅》、《红楼梦》的家族关系、使之成为传奇的时代早已一去不返。琵琶所面临的只有矛盾和畸变。在迷离的鸦片烟味中,这个家庭一方面沉浸在往日的风光里,另一方面却又勇于追求汽车电影这些洋玩意。无论如何,挥之不去的是荒凉和颓废。琵琶的父亲纵情声色,母亲则迫不及待地要成为新时代的娜拉。两人有志一同的挥霍祖产,孩子成为他们最后的纽带。小说所铺陈的时代其实充满历史动荡,十月革命、满洲国成立、抗日战争这些事件就发生在他们的周遭,但却不能激起任何涟漪;内部的腐朽已经让这个家庭麻木不仁了。
张爱玲以嘲弄却也不乏同情的眼光看待笔下人物,但对他们居然还洋洋自得的一面则极尽讽刺之能事。榆溪与其它家族男性成员的固步自封诚然可笑,露和珊瑚的立志成为新女性也显露着过犹不及的怪态。当张写到露拖着解放小脚英勇地游泳滑雪,或榆溪和琵琶的继母荣珠(Honor Pearl)异想天开、在家中荒废的花园养鹅营生时,是要读者莞尔之余又不免唏嘘的。
琵琶的继母荣珠性格阴晴不定,从进门起就对琵琶怀有敌意。在继母的操弄下,琵琶发现父亲和弟弟都和她日益疏远;当她被迫穿着继母的旧衣服上学时,她感到前所未有的屈辱——这是她日后难以忘怀的创伤之一。露在战争爆发后回到上海,琵琶和母亲住了一阵,这又成为荣珠找碴的口实。接下来便是我们熟知的情节:琵琶被父亲暴打一顿后关了起来;她差点死于肺炎,终于侥幸脱逃。
读者会发现怪诞小说的基本要素在此几乎无一不备,像是鬼影幢幢的大宅与梦魇般的监禁,柔弱的女孩与邪恶的继母等等。但即使在最危险的关头,张爱玲的叙述仍然保持了一层疏离感。这层疏离感既是她的英文行文风格使然,也得之于时过境迁多年后产生的情感距离。比起张的亲身经历,小说在情节上多了一层转折。琵琶逃离父亲的家后,她的弟弟陵成为下一个牺牲,死于肺结核。这是《雷峰塔》与张爱玲其它中文自传作品最显著的不同之处。无论如何,(虚构的)兄弟的死亡证明了张爱玲作为小说作者的权力,仿佛不看到琵琶(或张自己)的弟弟——也是家族最后一位男性传人——死去,不足以说明家庭创伤对她是如何的刻骨铭心。
在小说结尾,琵琶有了出国留学的机会。熟悉张爱玲早期作品的读者当然知道这是一个虚妄的希望,因为更多的考验将要降临到琵琶身上。战争爆发了,任何期待都注定落空,这也是张爱玲在《易经》中将要阐述的主题。因此,《雷峰塔》最后一章的开头充满了暗示:“琵琶总是丢三落四的。”的确,这一聚焦于“失去”的场景不啻是整部小说的隐喻。琵琶的故事其实是一个关于“失去”的故事失去天真,失去童年,失去父亲、家庭,尤其是失去母亲。小她与母亲告别开始,以与作为母亲替身的奶妈告别结束。张以此为一部中国女性“成长小说”(Bildungroman)写下令人心碎的句点。
相较于《私语》,《雷峰塔》因为篇幅较长,在讲述张爱玲或琵琶的童年与少年经验时更为从容。但张爱玲对英文读者是否理解她生活过的中国缺乏信心,下笔就显出碍手碍脚的倾向。小说共二十四章,每章都刻意安排一个显眼的事件或主题,这使得全书的结构显得呆板。尤其与她后来在《小团圆》中展现的多变且迂回的风格相比,《雷峰塔》的问题更为明显。张爱玲也有意夸张小说的异国情调,刻意给笔下的人物取些中国风的英文名字,像是“榆溪”(Elm Brook)和“柔柳”(Pussy Willow)等;又突出诸如纳妾和裹小脚之类的东方主义式奇观题材。小说的名字《雷峰塔》搬演中国家喻户晓的白蛇传说更不在话下。张爱玲努力摆平东西文化和心理上的差异,企图将自己中文的风格融入到英文语境,可谓用心良苦,但成功与否就另当别论了。
《雷峰塔》采用了张爱玲所谓的儿童视角来讲述故事,倒给了我们深思的余地。照理说张爱玲的童年如此不堪,对儿童的观点应该避之唯恐不及,但她却反其道而行,隐藏在这里的心理动机耐人寻味。儿童视角有效地将《雷峰塔》与“What a Life!”、《私语》以及《小团圆》等作的叙事观点区别开来。张爱玲似乎有意借琵琶的视野重访早年的创伤场景,并试图重新理解当年那些不能理解的人与事。擅用精神分析学的批评家们大可就此探讨张爱玲的复杂心态:她试图通过“重述”创伤来抚平童年创伤;或更辩证的,只有在回到她原应回避的创伤里,她才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不论如何,这都为我们揭示琵琶作为一个“青年(女)艺术家的画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Woman)后的深层矛盾。
当然张爱玲并不是第一个书写童年经历的中国现代女作家。冰心(1900-1999)曾以牧歌式风格描绘童年岁月;萧红(1911-1942)念念不忘她早年在东北寂寞的日子;凌叔华(1900-1990)则透过英文回忆录《古韵》(Ancient Melodies,1953)讲述她在“高门巨族”里的成长经验。可以顺带一提的是,凌叔华的回忆录在西方出版后受到好评,可能也触动了张爱玲书写类似题材的心意。即使如此,《雷峰塔》仍有其特色。张爱玲的成长世界里既没有冰心或萧红笔下的纯洁天真,也没有凌叔华回忆里潜藏的菁英自觉。张爱玲所要塑造的是一个女孩如何从小就被扔进成人世界,还没有开始她的青春年华就已然是个老灵魂了。
尽管张爱玲采用了儿童视角来叙述一个半新不旧的“现代”中国家庭怪现状,琵琶的所见所思其实透露出更复杂的调子。张爱玲曾向宋淇抱怨儿童视角限制了她小说中对现实更微妙的描述。事实上,这恰恰带来了一种特殊的叙述吊诡。就在琵琶迷上了迪斯尼卡通的当儿,她的父亲榆溪正不亦乐乎的泡着一个(面目平庸的)妓女;琵琶渴望母爱,而她母亲连过马路要不要牵着女儿的手都有点犹豫。在这些时候,琵琶(或张爱玲)作为小说人物也许貌似天真,但作为叙事者,她的口气无疑是讽刺的。张爱玲认为她生命不快乐的核心所在是父亲不像父亲、母亲不像母亲。这让我们想起张爱玲在散文《造人》中的话:“小孩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胡涂。父母大都不懂得子女,而子女往往看穿了父母的为人。”⑨
《雷峰塔》中的成年角色虽然病态如斯,却并非总是纯粹的邪恶代言人。张爱玲从多方面指出:她的父母那一代人之如此怪异反常,必须要归咎于父母的父母辈也一样怪异反常。以此类推,她的伦理观和历史感的叛逆性可想而知。她也明白,这一代中国人生长于中国现代史上最动荡的时刻,不断面临着新旧价值的双重挑战,最终能成为“健全”的现代人的幸运儿其实少之又少。大多数的中国人就和琵琶以及她的父母一样,在找寻自己的社会和伦理身份的过程中付出昂贵代价,到头来却不过是一场空。就这点来说,张爱玲对其笔下人物的命名,像榆溪、谨池(Prudent Pool)、荣珠(Honor Pearl),栋梁(Pillar)、陵(Hill)、远见(Aim Far)、昌盛(Prosper)等等,充满反讽意味:命名与现实、父母的期待与个人的经历间的惊人差距,竟至如此。
张爱玲下一步将孩童与父母的问题连锁到婚姻的问题。她对小说中所有的婚姻关系都投以病理学的观照,将之视为无尽的流言、怨怼、阴谋与丑闻的渊薮。榆溪和露这对怨偶几乎没有过什么快乐时光,只结出了琵琶和陵这样的苦果。其余人物,从榆溪的异母兄弟到露的兄弟和他们的配偶,也不见得好到哪去。丈夫们流连于烟花柳巷,或者通奸纳妾,妻子就此都成为“怨女”。即便仆佣们也不能免于婚姻的惨淡结局。
《雷峰塔》因此颇投射了一层意在言外的阅读法,让我们一窥张爱玲自身失败的婚姻。回看《雷峰塔》的前身《私语》;《私语》写于1944年夏天,其时她正与胡兰成缱绻难分,尚未经历感情的低谷。1944年8月张胡结为夫妇,三年后分手。1957年张爱玲开始撰写《雷峰塔》时,她已与胡兰成离婚十年,且刚刚再婚。她已不复是《私语》中无助地看着父母吵架的柔弱女孩,而是一位切切实实经历了前夫背叛、父母过世的女人。⑩
在这点上,最生动的案例并不来自琵琶的父母,而是她的继母荣珠。荣珠在娘家是庶出,母亲已经失宠。她原来是个温驯的女孩,却也受到“五四”恋爱自由的影响,拒绝包办婚姻,爱上一个穷表兄。这对恋人得不到家庭支持,最后决定自杀。但荣珠的心上人却不能同生共死,竟在荣珠服毒后落荒而逃。荣珠求死不成,被她父亲监禁了起来,之后染上了鸦片烟瘾,聊以解脱。待到嫁给榆溪后,荣珠摇身一变,成了个阴鸷的妻子、上瘾的烟枪、残忍的继母。她的蜕变就像是对自己情路多舛的苦涩复仇。
荣珠也许是《金锁记》中曹七巧和姜长安的合成体,从一个不堪一击的女儿变成一个恶毒妇人。荣珠曾经几乎跨过了“五四”启蒙的门坎,却只落得被打回了礼教吃人的下场。荣珠的毁灭发人深省,因为让我们联想到张爱玲自己在遭受了胡兰成背叛之后,是不是也有可能选择这样的道路。我们甚至有理由怀疑,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孽缘与其说是新派自由恋爱的惨败,还不如说是传统才子佳人最后的诅咒。
张爱玲对于新旧形式婚姻的疑虑并不就此打住。在另一章中,露与珊瑚闲聊到一宗发生在英格兰格拉斯米尔湖(Lake Grasmere)的谋杀案。一对新婚华人学生夫妇在这个风景区度蜜月,但某天妻子被发现身亡,“赤着脚,一只长丝袜绕在脖子上”,手里还拿着阳伞。凶手原来就是她的丈夫。这个故事似乎暗示不圆满的婚姻不仅能伤人的心,甚至还能要人的命。有意无意间,张爱玲也许投射了她与胡兰成关系里一股致命的暗流。到了《小团圆》中,当男女主角的婚姻变质后,他们每一个身体接触都引起重重杀机。
最后我们谈到小说的标题《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张爱玲在她给宋淇的信中说得很清楚,“塔”指的就是《白蛇传》里“永镇白娘子”的雷峰塔。(11)年幼的琵琶从奶妈那里第一次听到了这个故事,深受魅惑。这一章写《白蛇传》的内容在张爱玲自传性质的中文散文和创作中都未曾出现过。张在此援引一个具有鲜明的异国情调的传说,也许是为了迎合英语世界的读者。除此,对雷峰塔的指涉也为张爱玲自己那段遭到禁锢和侥幸逃脱的经历提供了一个有神话意味的潜文本。
更意味深长的是,“雷峰塔”把我们带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互文世界。我们最容易想到的大概就是鲁迅著名的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在这篇文章中,鲁迅猛烈抨击中国社会令人窒息的道德教条,认为不仅扼杀了人间对真爱的追求,而且养成一种虚情假意的文化。鲁迅因此乐见雷峰塔的倒掉,并嘲笑那些依旧抱残守缺的人们。(12)张爱玲在创作《雷峰塔》时,也许想到了鲁迅的这篇文章,也许没有。重点在于张爱玲和鲁迅一样,就着“雷峰塔的倒掉”这个事件产生了一系列联想——从阳具崇拜的瓦解到父权的坍塌,从传统封建制度的压迫到现代民族主义的霸权。小说中几乎所有男性角都被赋予了负面色彩。这些男性色厉内荏,其实和传统家庭体系一样千疮百孔。我们还可以注意,鲁迅的文章最初发表于1924年,正是那一年张爱玲的母亲和姑姑离家出洋。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她们的决定不啻是对高高在上的男性威严的迎头痛击。
中国新文学中至少还有三个文本以塔为象征:殷夫(1909-1931)的诗歌《孩儿塔》;白薇(1893-1981)的剧本《打出幽灵塔》;台静农(1903-1990)的小说集《建塔者》。孩儿塔存放夭折的孩童的骸骨,用以纪念过早被摧毁的灵魂。作为鲁迅的追随者,殷夫的诗歌回响着鲁迅笔下狂人的呼号:“救救孩子!”。而在“左联五烈士”事件中,(13)殷夫是被国民党杀害的五位左翼作家中最年轻的一位。白薇是五四以后最具争议性的女作家之一。在她的剧作中,幽灵塔是囚禁处女以满足地主恶霸性需求的牢笼。剧中的孤女被迫嫁给地主,却在最后关头发现自己竟是地主的私生女;与此同时,她也与自己同父异母的哥哥坠入情网。当革命分子赶来营救这个女孩时,一切为时已晚。乱伦的禁忌与革命的图腾在这部剧作中相互纠缠,最终以女孩的生命作为献祭。
在这样的阅读脉络里,我们要说现代中国文学里以“塔”形成的“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其来有自,张爱玲的《雷峰塔》只是一个迟到的版本。然而对于雷峰塔的倒塌,张爱玲毕竟别有感悟。鲁迅、自薇和殷夫等人都是革命阵营的作家。他们有多期待推倒代表封建中国的雷峰塔,就有多期待看到一座新的、现代巨塔在原地建起。这座现代之塔可以名为革命、政党、或民族国家。准此,他们也是建塔者,正如鲁迅的密友、北方左联的奠基人台静农的小说集《建塔者》中的那些革命人物一样。
张爱玲则不在建塔者之列。作为一个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者和极端的讽世者,她对一切以崇高(sublime)为名的主张和架构永远充满怀疑。如果“雷峰塔的倒掉”在中国文化的想象图景中代表一个天启般的瞬间,那么对于张爱玲来说,这天启的意义就在于塔的倾颓,而非任何重建的可能。在雷峰塔倒以后写作,意味着反省原初建塔的虚妄和野心,观察游荡在断壁残垣间的幽灵,或更诡异的,“欢迎”那阴森幽密的氛围从此笼罩中国大地。
操持革命话语的作家和批评者当然不会认同张爱玲的观点。但我们必须正视面对当代“历史”与“进步”话语,张爱玲的写作内蕴一种“否定的辩证”力量,因此不该仅仅被视为一个反动例证。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已经有太多论述根据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历史的天使”来讨论现代性的可疑之处;历史的天使如何面对着过去的废墟,被现代的狂飙吹着背向未来前进等等,早已成为老生常谈。(14)如果我们以张爱玲笔下的白蛇代替本雅明的天使,或可以看到另一番景象:美丽的蛇妖为人间的欲望所痴迷,却也为人类的脆弱和残忍而牺牲,永远被幽禁到雷峰塔下。古老的传说记忆荒诞邈远,却始终与我们若即若离,尽管到了启蒙以后的现代,千回百转,它还是幽幽的盘桓在那里。就此张爱玲重述了她在《自己的文章》(1944)中的观点:
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瞭望将来要更明晰、亲切。于是他对于周围的现实发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疑心这是个荒唐的,古代的世界,阴暗而明亮的。(15)
我由此认为张爱玲的《雷峰塔》中投射出一种内倾性的回旋话语(involutionary discourse)与革命话语(revolutionary discourse)不同,“回旋”的展开并不依靠新的元素的注入或运作,而是通过对思想、欲望和行为的现存模式的深化、重复、扭曲来展现前所未见的意义。它就这样盘旋着,卷向自身内部。这样的倾向可以视为保守甚至颓废。但张爱玲未尝不以此提供了一个警醒的视角,让我们一窥历史上每一座人造的巨塔之下,都潜伏着幽灵——白蛇也似的幽灵?
而在1950年代,又有什么能比新中国的成立所投射的象征巨塔更雄伟,更崇高?张爱玲却选择在这个时候永远地离开祖国。她从任何奉民族、国家之名的建构抽离,退居到自己所发掘的记忆洞穴中。在那潮湿阴暗的所在,她默默探究中国——社会,文明,人性——最曲折扭曲的面向。她回到那“荒唐的,古代的世界”,反而揭露了“阴暗而明亮”的现实。1950年代后期,张爱玲以最离经叛道的方式为中国招魂,也同时为中国祛魅。她写的不是奉任何名义的塔的高高崛起,而是塔的倒掉。
1939年夏天,张爱玲从上海来到香港,成为香港大学英文系的学生。她本想到英国留学,但这个计划因为二战爆发而流产。然而战争到底还是影响了她的学业:1941年12月7日,日军攻占香港,就在同一天,珍珠港事变爆发。英国殖民政府经过十八天的抵抗后,于12月25日宣布投降。香港大学随之关闭,所有的学生被迫疏散。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张爱玲和许多赴港求学的学生一样滞留港岛。此时香港与外地通讯不便,交通往来异常困难。为了谋生,张爱玲不得不从事秘书和看护的工作。她最终弄到了一张开往上海的难民船的船票。当她回到家时,已是1942年的夏天。
这段香港经历成为张爱玲生命和事业的转折点。赴港之前,她和父亲和继母格格不入,也和生母关系疏离。相形之下,她在香港的学生生活反而快乐些,但战争让这段时光戛然而止。香港沦陷带来了历史的大变动,也为张爱玲上了珍贵的一课:战争可以摧毁一切。在残酷的战火中,任何人生的牵挂或努力都证明只是徒劳。1942年夏天当张爱玲回到家时,上海也已经沦陷。这座城市的转变让她对战争的感受更为深刻。就在此时,张爱玲开始了她的写作生涯。
张爱玲早期作品多和她的香港经验有关,因此不难理解。其中最有名的应是《倾城之恋》(1943)。这个中篇小说以战时香港为背景,写一个失婚的上海女人和一个华侨花花公子的恋爱传奇。这对情侣在交往之初各怀鬼胎,却因适逢香港陷落,反而让他们在对方身上找到真爱。一场历史浩劫意外地促成一段罗曼史,将露水姻缘转变成终身的婚约。在张爱玲冷眼看来,成千上万的人在战争中死去,仿佛只是为了成全这对平凡的夫妻。(16)历史的无常和命运的偶然是张爱玲创作恒久的主题。就此香港提供了一个微妙的隐喻:这座城市的兴起充满传奇,本身就是变与常相互纠缠的呈现。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张爱玲的散文《烬余录》(1944)。这篇文字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提供了沦陷时期香港生活的第一手纪录,也在于它对战争和在战争下生存的意义作出独特观照。在张爱玲笔下,香港的沦陷并没有带来什么惊天动地的反抗或可歌可泣的牺牲;相反的,沦陷只揭露了人性的怯懦和自私。沦陷之初的香港先是人人自危,要不了多久就都习以为常了。张爱玲也早早告诉我们,她自己就是文章所要讽刺的对象之一。她写自己面对空袭中的意外死亡无动于衷,从事救护工作时心不在焉;她最关心的是怎么张罗食物。从沦陷的生活里她看出人由于求生的本能而产生的怪诞行为和“奇异的智慧”。她的叙述混合了黑色幽默和犬儒的自嘲,既尖刻又惫懒,甚至产生一种心照不宣的“热闹”效果。
张爱玲意识到这些现象看似没有人性,却是人性之常。在战争乱象和道德怪态背后,她见证人性的局限,并且深深感到悲哀。用她自己的话说,这是“乱世”——历史大劫毁的时刻。核心价值溃散,人为的努力毫无意义。就算她的写作也无非是劫后余烬里一点微弱的见证。这才有了《烬余录》: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17)
对熟悉张爱玲中文作品的读者来说,《易经》的第一印象大概就是《烬余录》的英文版。以上有关《雷峰塔》的讨论已经说明张爱玲藉由双语和跨文类的方式展现的重写冲动。《易经》提供了另一个例证。这篇小说写于1950年代后期,此时的张爱玲似乎打算用不同的语言和文类重温她的战争体验。几乎《烬余录》里所有的事件都被写进这部小说里,有些插曲甚至被扩展成独立的章节。张爱玲显然有意透过小说形式,释放她散文中所内蕴的张力。然而《易经》读起来却不像《烬余录》那般有力。虽然小说形式让张有了更多空间表述她的战争经验,但就事论事,《易经》并不能激发出《烬余录》那样错综的心理反应和道德暧昧性。张写于战争期间的散文出入历史灾难与日常琐事、民族主义呐喊和个人生存欲望、无所不在的死亡威胁和青春年少的漫不经心之间,在在充满张力。如果以此来看《易经》,自然要让人觉得若有所失。
然而《易经》确实为我们了解张爱玲的生平和创作提供了不同的东西。这本小说首次揭露了张爱玲和她母亲的矛盾关系;它也让我们了解张爱玲滞留在沦陷以后的香港如何谋生,又如何设法回到上海。这些细节都让《烬余录》点到为止的部分变得饱满起来,也为张爱玲的历史与个人记忆添加了新的面向。
我们还记得《雷峰塔》曾是《易经》的第一部分。在《雷峰塔》里,琵琶的母亲露抛夫弃子到海外追求自由生活。小说将尽,露回到上海,琵琶在此时离开父亲的家,并听从母亲的建议准备出国留学。《易经》的故事就接着《雷峰塔》往下讲。全书二十二章,从琵琶进入母亲浮夸的生活圈起,接着写战争爆发,琵琶被迫放弃了留英计划改往香港求学,以及她与母亲在港岛的短暂相聚。这部分有十章,以露在日本攻占香港前夕赴印度作结。
小说最后一章写琵琶的回乡之旅。当时香港与大陆之间的海运几乎停顿,回到上海的机会微乎其微。然而琵琶发现了她任职的医院管理不善的证据,竟凭着这些证据“说服”上司,为自己和同学弄到了船票。她最后登上的是日军驻港总司令矶谷廉介特别批准的客轮,载送的都是名流级的难民,包括京剧大师梅兰芳。
准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地探究《烬余录》与《易经》之间的关系。《烬余录》集中描写战争所带给张爱玲玉石俱焚的印象,《易经》则关注琵琶在战火中求生存的历程。如果《烬余录》讲述战争如何让张爱玲顿悟生命的脆弱和虚无,《易经》则让战争“家常化”了;不仅琵琶必须学着每天把日子过下去,她甚至把回到上海的家作为克服战争恐惧的前提。尽管琵琶自小失去父母的关爱,上海却始终是让她感觉心有所属、并乐意称之为“家”的地方。《易经》以琵琶离开上海始,以她回到上海终。无论在主题上还是在形式上,这样的循环结构与《烬余录》所暗示的一切荡然无存形成强烈对比。
如果我们考虑作为小说题目的《易经》所含有的指涉意义,以上观察更显得意味深长。毫无疑问,张爱玲的灵感来自中国的经典《易经》。小说中有一个场景写到琵琶在她工作的临时医院里发现了一大堆废弃的旧书,她“盼着找出一本《易经》来”:
是一种以阴阳、明暗、男女为根基的哲学,讲究它们之间的此消彼长、相生相克,并可根据八卦,龟甲来算命。她还从未读过它。它晦涩难懂,是五大经典中最深奥的一本,所以课堂上也不教授,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它涉及到性。(18)
张爱玲从未以通晓《易经》著称。她将小说命名为《易经》,不免使人好奇她的动机何在。她也许是想借重这部经典的“东方”魅力来吸引西方读者,也许真是希望求助古代的智慧来参详琵琶或她自己的命运,又也许是对前夫胡兰成微妙的反戈一击——胡兰成自战时起就以《易经》的阐释者和实践者而洋洋自得。撇开这种种可能,我认为,奉《易经》之名,张爱玲不仅在“东方主义”与个人命运之间多所玩味,更力图从中汲取一种创作哲学:小说创作不正如《易经》,以其多变的“象”诉说着人生种种起落无常?
《易经》的“易”字在中文里意涵丰富,它可以指“变易”,同时也可以指“不易”,又有“简易”、“交易”、和“交换”的含义,(19)张爱玲以此来表达自己复杂的战争经验,用心不难理解。虽然小说《易经》主要是描述香港沦陷和女主人公回到上海的历险,但张爱玲写作此书时已经是50年代后期。回顾将近二十年以前的经验,她其实是有着历史的后见之明的,也必然明白回忆性的写作在操作已经发生的和尚未发生的事件上,所产生的时间和知识的多重落差。除此,写作《易经》时期的张爱玲还体验了另一轮的国族危机:1949年共产党获得政权,建立新中国。张在1952年离开上海,来到香港。这与十年前她从香港逃到上海的路线恰恰相反。张在香港逗留了三年之后,移居美国。自1942年以来,张爱玲也经历了两段罗曼史:她和胡兰成的婚姻1947年结束;1957年,她嫁给了赖雅(Ferdinand Reyher,1891-1967)。比起当年写作《烬余录》时期的风光,1950年代末在美国的张爱玲已是一个两度结婚,移民他乡,依靠非母语写作的中年作家了。回望1938年初入文坛以来的种种遭遇,她有理由为自己所经历的变化唏嘘不已,从而理解“易”的意义所在。
在更深的层面上,《易经》这一标题指出生命流变和人世兴衰中的种种悖论。识者已经指出“易”可以指涉宇宙运行的道理,人世浮沉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此,我们对易就有了不同的理解:生老病死、花开花落既然已是恒常的定数,“易”也就成为千古“不易”的道理。(20)正如琵琶所说,那古老的文本传授着“阴阳、明暗、男女”、“此消彼长、相生相克”。貌似相反的两种力量互为印证,轮回辩证的模式才得以生出,而恰恰是这些展示出了“易”之道。这个“道”虽然难以言诠,传达的却是直指本然的真理,是简单的、“容易”的易道。
相应地,时间也不只意味着线性发展,而是一种“空间的流转”,在其中变与不变、交相变化与相互作用,形成复杂的结构。这就带出了“易”的第三层含义:作为一种打破现状的力量,“易”总蕴含着无休无止的变化——也是生发的——动力,是为“生生之谓易”。(21)“易”构成了开启生命宇宙论的基本法则。只从这个角度思考,我们才能理解张爱玲有关重复书写所暗含的哲思。重复既不是对现有事物的乏味的复制,也不是回归事物的原点。重复是“生生”的过程,是脱胎自现存事物而又对其作出反应,也是原点的微妙位移,由此“易”的力量相应而起。(22)
回到《烬余录》与《易经》,我们可以看出这两部作品中一系列的你来我往、变动不居的关系:自传式的见证与虚构性的叙述,创伤和创伤的代换,历史的先见之明与历史的后见之明互为前提或结果,产生出种种意想不到的含义。张爱玲选择用英文来重写她的战争经验也使我们想到,作为意义的载体,语言所具有的“善变”性质和战争本身带来的“嬗变”状态不相上下。我们也可以由此探讨张爱玲看待时间、历史以及语言间形异质同(isomorphism)的倾向。同样以香港陷落为主题,《烬余录》对人性投以末世的观照,《易经》则像它的题目所暗示的,讲述的是人性的回归与重生。世事多变,但否极泰来,总有一些经久不易的东西重启生命又一层次的意义。
我们甚至可说在张爱玲以后的岁月中,“易”的观念其实左右她的创作观。1976年,张爱玲基本完成了中文小说《小团圆》。如前所述,这部小说叙述张爱玲从童年到与胡兰成离婚的经历,也是她的英文小说《雷峰塔》和《易经》的原始蓝图。值得注意的是,《小团圆》写的基本是张爱玲(或她的女主人公)的上海回忆,而以香港沦陷作为框架。另一方面,《易经》写的是张爱玲的香港经验,则以主人翁离开和返回上海作为框架。在两部小说中,上海与香港互为语境,以循环往复的方式为张爱玲“变化”与“交叉变化”(change and interchange)的诗学提供了空间上的模拟。
《易经》以琵琶进入她母亲的世界为开端。小说的第一句话是:“琵琶从来没有看过朝鲜蓟。”张爱玲写琵琶在露的餐桌上首次“遭遇”一种奇特的蔬菜,充满象征意味。对于露来说,朝鲜蓟散发着她挚爱的巴黎风味;对琵琶来说,它的特殊形状和口味却体现着母女关系的疏离:剥开一层又一层的叶片,才能尝到朝鲜蓟心,滋味却未必可口。
这场“朝鲜蓟事件”如此琐碎却又意味深长,正是张爱玲典型的讽刺法,也为一个女孩在历史困境中成长的故事,拉开“伪英雄”式(mockheroic)的序幕。就在露和琵琶的姑姑珊瑚大啖朝鲜蓟的同时,战争已经迫在眉睫。“仗随时可能打起来”,露好整以暇地评论着。但在战争展现毁灭力量以前,琵琶已经在家中看到了一切价值的崩溃。
琵琶和露母女之间疏离的关系在《雷峰塔》中已经浮现,虽然张爱玲所选择的孩童视角对她的描写有所限制。到了《易经》开始,琵琶已经十八岁了,可以更直接地感受她和母亲间的种种。琵琶离开了父亲的家投靠母亲,却发现自己格格不入。她不善应对,在社交场合举止笨拙,以至有次露情急之下脱口骂她是“猪”。当她逐渐拨开母亲那个圈子神秘的屏幕,她为流窜在后面的闲话和丑闻惊讶不已。她听到的谣言包括母亲和姑姑可能是同性恋;她的姑姑又曾经与她的表兄上过床;她的母亲同时有几个外国男朋友;更令人震惊的是,她的舅舅并不是她的亲舅舅,而是从一对乞丐夫妇那里调包来养大的假货。
露的生活自行其是,对女儿的态度反复无常,似乎是个中国版的“邪恶母亲”。但细读这个角色,我们会发现她的善变正呼应着《易经》的主题。露是封建婚姻的牺牲品,希望琵琶找到新的生活方式,但她又像传统父母一样,准备在女儿未来的婚姻上捞点好处。她从不掩饰对于新奇外国事物的爱慕,可又声称只有具备了外国人的眼光,才更能欣赏中国。张爱玲在小说中几次提及女性的“阴性”力量,认为是传统的《易经》(道家?)智慧的表征。就这一层面而言,她的母亲理应是最佳人选。既冷漠又实际,既有所坚持又不可捉摸,露所体现出的这种女性本能后来也体现在张爱玲身上。阴性原则教人守雌通变,死里求生,但由于它无视(男性社会里)约定俗成的礼教,所以同样会带来伤害。
当琵琶意外地从她的历史教授布莱斯戴尔先生(Mr.Balisdell)那里得到一笔私人奖学金时,小说有了第一个转折。琵琶告诉母亲这个好消息,却只让露怀疑女儿为此卖了身。更糟糕的是,琵琶后来发现露打麻将输光了她所有的奖学金。这引发了母女间的争吵。琵琶觉得,既然露挥霍光了她的奖学金,她也就算还掉了露在她身上的投资,两人算是互不相欠了。
张爱玲就此开展出“易”的经济学层面:中文对“易”字的解释,不仅包括交叉变化(interchange)和交替变化(exchange),也指“交易”。细读琵琶和露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会发现她们之间在伦理与情感的纽带之下,总有一种锱铢必较的思维。母亲自私自利,女儿斤斤计较,这样的关系读来像是传统女性主义的恶女版。然而张爱玲自有她的反驳:难道这样精打细算的本能不是出于自保的必要?正是这种自保的能量凸现了女性求生存的“阴性原则”。
所以在小说第十章的结尾,当琵琶与露告别时,她已经不知不觉从母亲那里学到了一记绝招:人生实难,哪里能够诚实以对?在香港沦陷的日子里,琵琶牢记母亲的教诲,很快掌握了求生所必需的自立与自私。倘若她没有心眼,她不可能要挟上司,拿到回上海的船票。战后张爱玲母女在上海短暂相聚,以后终生未再相见。然而,在小说的虚构世界里,只要创作不止,她就离不开母女间的爱恨纠缠。
小说中段部分聚焦于1941年香港的沦陷。就在琵琶和她的同学们紧张地准备期末大考的那个上午,日军进攻香港。这些学生们惊恐之余,反而兴奋起来。他们对战争一无所知,只知道学校关门大吉,考试便会取消,岂不是一大好事。有人马上关心跑警报的时候要怎么样配备行头。张爱玲描绘学生们为突如其来的解放欢欣不已,哪里知道马上就要大难临头。即便到了后来这些学生历经了饥饿、逃难和死亡,深受其苦,张爱玲仍怀疑她们是否从战争中学到了什么教训。她甚至对所有香港人都有所保留;这个殖民地小岛上的人“从未见识过战争,包括了造就了香港的鸦片战争”。历史的巨变不过是给人性的无情、怯懦及自私提供了舞台。
张爱玲这种讽世态度和战时的正统话语截然不同。她好奇地打量着身边人们的种种反应,认为既可笑又可怕。琵琶的朋友比比(Bebe Sastri)(23)是个印度女孩,同样来自上海。她在轰炸期间冒死上城里看卡通电影;空袭警报响起,她可是照旧洗澡唱歌,哪怕炸弹已经掉到宿舍边上。琵琶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刚听说港英政府投降的消息,她和几个同学就迫不及待的离开学校好去找冰淇淋吃,全然不顾街上横七竖八的尸体。
小说第十四章,琵琶坐电车到城里报名担任空袭志愿服务员,却赶上了空袭。这次琵琶直接面对了死亡的威胁。当时她和其他乘客一起跳下电车,匆匆找地方避难。事后回想起来,琵琶才意识到要是炸弹正好落在自己藏身的马路这一边,她就完了。然而真正让她无言以对的是,即使在轰炸中,世界运转如常,天空还是像往常一样蔚蓝,空荡荡的电车就停在路中间,盛满了怡人的阳光。轰炸结束了,乘客又奋不顾身的挤上电车,一切很快回到常轨。琵琶忽然意识到四下的荒凉:
轰炸结束了。她乘同一班电车回家。走着走着,她忽然意识到这件事没有人可以告诉。比比已经走了。不单是在香港,就是在整个世界上,还有谁呢?……有一天她会告诉珊瑚姑姑,虽然她不愿姑姑因为她差点死掉而大惊失色。如果她死了,比比会想念她吧,可是比比永远是快乐的。(24)
历史教授布莱斯戴尔被枪杀的消息更让琵琶感到世事无常:他不是被日本兵打死的,而是被自己人误杀的。我们都还记得,就是这位布莱斯戴尔教授给了琵琶一笔私人奖学金。琵琶从来没有认真听过他的历史课;老师的死倒为她补上了最艰难的学分。
尽管面临死亡的威胁,日子还是得过下去。食物成了最迫切的需要。琵琶注意到因为担心食物短缺,有的同学反而胃口大开;而食物的配给制又造就出走私和囤积的新“经济”效应。沦陷后的香港百物匮乏,却有无数的小吃摊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琵琶后来在医院里做看护,有天晚上和其他的同事用做肥皂的椰子油烘了盘小面包。她们美美的吃了一顿,尽管——或者正是因为——几步以外就有垂死的病人不停地呻吟或嗥叫。
琵琶还发现在战争期间罗曼史多了起来,正如张爱玲所暗示,在和平年代里这些爱情故事是不会发生的。大家在炮火中纷纷坠入爱河,仿佛就怕落了单,或根本就是图个方便的庇护。相濡以沫的渴求和得过且过的动机互为表里,不能自已的欲望和虚无幻灭的冲动合纵连横。通奸、同居以及堕胎统统变得可以接受了。毕竟这是乱世,种种反常的人和事都变得稀松平常起来。用张爱玲的话说,人们为了生存,不惜要攀住一切实在的东西。身体的亲密关系,也和食物一样,成为传达人类根本需要的指标。
但张爱玲想要探究的不只是战争所带来的伦理或是政治后果。她对于战争“经济学”的考察才更引人注目。她告诉我们,在一个价值崩溃的时代里,人不是放弃算计,而是更加算计了。食物和性——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就成了最原始的交易筹码,启动了从生存到投机的种种目的。在这方面,张爱玲1940年代的中篇《倾城之恋》已经提供了极为生动的例证。但如果《倾城之恋》仍然认为战争中“真爱”仍有一二残留的价值,《易经》则将食物、性、婚姻以及意识形态的交易完全降到日常讨价还价的水平。香港沦陷带来的改变再惊天动地,要不了多久也就成为常态。一般人要的不过就是过日子。
我认为琵琶能有这样适应力其实得益于张爱玲的成长经验。从童年时代起,她就活在人际关系的算计之中,而当她搬去和母亲同住后,她对钱变得更格外敏感。香港的陷落使张爱玲对“易”的经济学有了学以致用的机会;她跟她的上司做了笔交易,终于离开了香港。
《易经》以琵琶安全回到上海圆满收场。但这样的结局有暧昧之处,因为琵琶靠的不是爱国主义或英雄情怀之类的美德,而是精刮算计的“恶信念”,才克服了重重难关。虽然这是琵琶为成长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我却怀疑张爱玲在这里透露更深的嘲讽。让我们再想想《倾城之恋》的主题:成千上万的人在战争中不明不白地牺牲了,似乎只是为了成全一对平凡的夫妻。同样地,《易经》的结局暗示香港的陷落带来了各种灾难,似乎只是为了成全一个少女。琵琶的“胜利”来自一种侥幸,她所见证的道德教训没有别的,就是人生的祸福无常。这一悖论进一步解释了张爱玲小说中“易”的辩证法(the dialectics of [ex]change)。
以上我们从张爱玲的个人以及文本经验讨论了她的《易经》。我认为张爱玲通过援引《易经》这一标题,开启了一个层层反复、相互作用的主题轴:诸如深层与表面、晦涩与简明、历史与自传、哲学的思考与虚构的尝试,以及更为有意义的,“变易”之为“易”与“交易”之为“易”等。本文的最后,我将焦点转向20世纪中期以来张爱玲写作所具有的“衍生”(derivative)趋向。(25)
在关于《雷峰塔》的讨论中,我提出张爱玲写作的“回旋”美学。这种叙事实践一反线性、前进的序列,代之以反转内敛的倾向。我认为在《易经》中,张爱玲不仅将回旋的原则发挥得淋漓尽致,更展开一种衍生的美学。所谓衍生,指的是叙述的动力并不在于(浪漫主义定义下的)原创性,而在于一种赓续接踵的能量,或是修辞意义上的代换与变形,从而颠覆一般对于“真实”、“发生”、“缘起”的诉求。就此而言,《易经》既是张爱玲早期《烬余录》的再造,也是未来《小团圆》的预演。而《易经》本身也有它自己衍易与分合的过程。现在独立出版的《雷峰塔》原来就是从《易经》一分为二、衍生出去的。
张爱玲必定意识到自己写作中的衍生倾向,因此在结构和意念的铺陈上都有所阐述。早在《易经》的第二章,张就描写琵琶发现了曾朴(1872-1935)的《孽海花》(1907),晚清最著名的影射小说。小说描写当时的政治和历史,所涉及的人物、事件以及轶闻每有所本,名为虚构,实则纪实,也因此成为读者趋之若鹜的作品。阅读小说有如对号入座的游戏,甚至可以依照小说与真实人物之间的对照按图索骥。琵琶的祖父母(或者张爱玲的祖父母,张佩纶[1848-1903]和李菊藕)的罗曼史也是《孽海花》着墨的对象。这类的野史轶闻当然不见于一般正统历史。
琵琶对《孽海花》的发现促使她展开了对自己家族史及其杜撰成分的平行考察。小说的描摹无异成了家族史的幽灵版本,让琵琶为了辨别孰真孰假而迷醉不已:
这些是她能够爱的人。她爱她的母亲和姑姑,但他们来来去去,更像朋友。她的祖父母总也不会离开她,因为他们已经死了。他们没有什么不同意的,也不会发怒。他们只静静地躺在她的血液里,等她死的时候再死一次。(26)
张迷们当然知道以上引文的斜体部分在《对照记:读老照片》会再次出现。换句话说,从一部作品到另一部作品,从一代到另一代,张爱玲文本谱系所形成的轮回正对应着的家族谱系的轮回。
这一例子也表明,终其一生,张爱玲的自我书写既来自她自我表白的冲动,也来自她自我虚构的欲望。通过琵琶的故事,张爱玲暗示:如果她能藉《孽海花》这样的小说虚构来进入家族历史,那么她未尝不可以将自己的经历安置回小说虚构里去。
张爱玲写作中回旋、衍生的倾向至少还有两个重要的例证可以参照。众所周知,张爱玲心仪晚清作者韩邦庆(1856-1894)的《海上花列传》,这本狎邪小说取材自韩邦庆本人流连19世纪末上海风月场所的经历。《海上花列传》当时并不受欢迎,但张爱玲却对它情有独钟,因为它颠覆了狎邪小说的传统。这本小说并不渲染青楼纸醉金迷的色彩,反而营造一种充满着世俗琐事与平庸人性的家常氛围。它因此可视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写实主义的先驱。用日常琐屑来装点、填充(家族)历史,并在一切人生华丽的表象下看到那彻骨的荒凉,在这方面《雷峰塔》和《易经》的写作都追随《海上花列传》所留下来的印记。(27)
《海上花列传》本身的结构与风格特征也有所本,那就是曹雪芹(1723?-1763)的《红楼梦》。这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也是张爱玲灵感的源头。张爱玲八岁第一次读《红楼梦》,1934她甚至尝试创作现代版的《摩登红楼梦》。(28)《红楼梦》之所以打动张爱玲,想来是因为她从中看出了同样家族盛极必衰的命运,更不必说青春与伤逝的色彩,以及繁华苍凉总成一梦的启悟。
更引起我们关注的事实是:随着年岁渐长,张爱玲越来越理解曹雪芹终其一生不断修订——重写——手稿的苦乐。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最终仍未能完成这项大工程。(29)《红楼梦》随着作者个人际遇的变化而不断改换面目,死而后已。而张爱玲晚期书写不正演示了类似命运?
我因此认为张爱玲在她写作生涯的后四十年里一再重写自己的生命故事并非巧合。在写《易经》、《小团圆》的同时,她也从事了两项平行计划。她将吴语版的《海上花》翻译成国语,又从国语翻译成英文。另一方面,她孜孜不倦的细读《红楼梦》,文本分析、文献考据、传记研究三路并进。她的红学考证后来以《红楼梦魇》(1977)为名结集出版。
对张爱玲而言,这三个书写计划——创作、注释、翻译——密不可分,更确切地说,它们构成了一个文本互涉(intertexual)、跨文类(cross-generic)、多重语言(multi-lingual)的网络,这一网络正指向张爱玲衍生美学的多个层面。
张爱玲在《海上花》国语翻译的后记里回顾自己所下的功夫,不无反讽地写下:
张爱玲五详《红楼梦》,看官们三弃《海上花》。(30)
这不仅是张爱玲对两部古典小说杰作的命运有感而发,也是对她个人阅读与写作的心得总结。从英文(《易经》、《雷峰塔》)到中文(《小团圆》),从小说到图像(《对照记》),从翻译到批评、考证,张爱玲游走其间,将所谓的“创作”视为一个不断变形的有机体系。她既不受限于“影响的焦虑”(anxiety of influence),更不在乎“诠释的政治”(politics of interpretation),这些都是西方文学理论的症候群,不值一顾。当她将创作和修订合而为一时,她重新启动了传统“述”而不“作”的微妙诠释循环。
张爱玲从事自己或他人作品的翻译时,也无意将自己置身于所谓的“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中,彷佛看出这样的理论总是在意义的播散与权力的制约中打转,形成另一种诡圈。她反而是在时尚的变更(changing fashions)里找到了相通之处:翻译作为一种语言转换行为,就像从一种装束换成另一种装束一样,总已经内蕴了时代的动机、性别化的个人欲望,还有更重要的,物质性和身体官能的感受,因时制宜,变动不已。我们应该记得,张爱玲脍炙人口的《更衣记》(1944)就是自己英文文章“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1943)的中译,这也是她早年双语写作的例子。(31)由此看来,翻译的“译”也可被附会为广义的“易”的另一种解释方法。
我在本文中详细阐述了《易经》的“变形记”,以突显张爱玲在创作时所走过的曲折道路。我认为,正如小说标题所暗示的,《易经》体现了张一生的写作随着生命发展不断变化,辗转曲折,死而后已。每一次尝试都显示她面对早年经历的不同态度,以及不断更新的叙述策略。就这点而论,张爱玲不啻是在书写她自己的《追忆似水年华》。以此她证明“往事”并非是冰封在时间彼端的静态事物,任我们予取予求,而是记忆中的活跃成分,时刻与创作者的当下此时互动。
传统观点认为张爱玲在1952年离开大陆后,创作力急遽下降。如果我们根据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有关“原创”、“创新”、“突破”等定义来看待“创作力”的话,这样的结论并不为过。但《雷峰塔》、《易经》这类作品的出土,促使我们从不同角度思考张爱玲的创作立场。当中国的大部分作家回应着“五四”所标榜的现代性召唤,孜孜不倦地弃旧迎新,并期待着“史无前例”创举时,张爱玲选择回望那些被进步作家和批评家们视为颓废、反动、私人的题材和形式。也由此,她示范出一个“回旋”而非“革命”、“衍生”而非“揭示”的书写谱系。我们一直要等到另一个新世纪来临后才理解,张爱玲的许多同辈作家所信仰的“现代”可能未必那么现代,而张爱玲所坚持的“传统”其实一点也不传统。
本文原以英文写成,根据作者为香港大学出版社所出版之张爱玲英文小说The Fall of the Pagoda,The Book of Change的两篇序言发展而成。经王宇平博士翻译为中文,蔡建鑫、高嘉谦教授提供修改意见,谨此致谢。译文已由作者本人大幅修订。
注释:
①《大美晚报》(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由美国报人卡尔·克劳创立。他是一位出生在密苏里州的商人与作家,1911年来到上海,并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详情参见Paul French,Carl Crow,A Tough Old China Hand:The Life,Times,and Adventures of an American in Shanghai(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6)。张爱玲的文章名为报纸编辑所加。
②夏志清是第一个将张爱玲作为经典作家介绍到英文世界的学者。见夏志清(C.T.Hsia)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1)中张爱玲相关章节。
③1963年4月2日张爱玲致宋淇函。
④关于张爱玲双语写作与重复写作的更多讨论,见刘绍铭《轮回转生:张爱玲的中英互译》;张曼《文化在文本间穿行:论张爱玲的翻译观》,均收入陈子善编:《重读张爱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214-233页、第234-246页。
⑤根据宋淇的说法,张爱玲先创作了英文本。亦可参见高全之《张爱玲学》,台北麦田出版,2008年版,第418页。
⑥见王德威introduction to The Rouge of the North(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第viii页。
⑦见高全之的分析,第321-344页。
⑧1957年9月5日张爱玲致宋淇函。
⑨张爱玲:《流言》,台北:皇冠出版社,1984年版,第126页;英文版我采用Andrew Jones的翻译,见Written on Wate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5),P131.下同
⑩同样值得注意的是1956年张爱玲与赖雅(Ferdinand Reyher,1891-1967)结婚。由于赖雅的健康问题和种种经济压力,这场婚姻很快不堪重负。张爱玲在对赖雅以及他们前途的惴惴不安中,创作了《易经》。
(11)1963年6月23日、1964年1月25日张爱玲致宋淇函。在1963年的信中,张爱玲称她的小说为“雷峰塔倒了”;而在1964年的信中名之为“雷峰塔”。
(12)关于鲁迅及其同时代作家对于“雷峰塔的倒掉”所作的回应,参见汪跃进(Eugene Wang)在'Tope and Topos:The Leifeng Pagoda and the Discourse of the Demonic'一文中的精辟分析,该文收入蔡九迪(Judnh Zeitlin)与刘禾(Lydia Liu)编Writing and Materiality in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第517-535页。
(13)夏济安(T.A.Hsia)The Gate of Darkness(《黑暗的闸门》)(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8),第4章。
(14)Walter Benjamin,Illuminations,trans.Harry Zohn(New York:Schocken,1969),P257-258.
(15)张爱玲:《流言》,第21页;Andrew Jones译本,第18页。
(16)张爱玲:《倾城之恋》:“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城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台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230页;Karen Kingsbury的译本Love in A Fallen City(New York:New York Review Books,2007),第167页。
(17)张爱玲:《流言》,第54页。
(18)张爱玲The Book of Change(《易经》)(手稿),第322页。下同。
(19)成中英:《易学本体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4页。
(20)同上,第5、29页。
(21)《周易正义,繋辞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1页。
(22)见Gilles Deleuze,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trans.Paul Patt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也可见J.Hillis Miller关于重作为小说创作的美学原则的讨论,该文收入Fiction and Repetiti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第一章。
(23)这个人物以张爱玲那时最好的朋友炎樱(Fattima Mohideen)为蓝本,她的父亲是锡兰人,母亲是天津人。
(24)《易经》,第254页。
(25)衍生美学更详尽的讨论参见Fin-de-siècle Splendor: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1849-1911(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第76-80页。
(26)《易经》,第27页。
(27)参见我在Fin-de-siècle Splendor中的讨论,第89-101页。
(28)该小说是对曹雪芹巨著的戏仿之作,张爱玲只完成了开头几章,未曾出版。
(29)我在此处用的是David Hawkes的译本The Story of the Stone,volume 1(New York:Penguin,1973),第51页。
(30)《张爱玲五详〈红楼梦〉,看官们三弃〈海上花〉》。张爱玲:《国语版〈海上花〉译后记》,张爱玲注译《国语海上花列传Ⅱ》,台北:皇冠出版社,1995年版,第724页。
(31)1943年张爱玲为英文期刊《二十世纪》撰写了“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该文经张爱玲翻译和修改后发表在中文杂志《古今》上,更名为《更衣记》;后又被收入张爱玲散文集《流言》。见Andrew Jones的译本Written on Water,第65-77页。该文章完成了一个三角之旅:由张爱玲从英文译为中文,又被Jones译回英文。
标签:张爱玲论文; 雷峰塔论文; 易经论文; 文学论文; 小说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小团圆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金锁记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