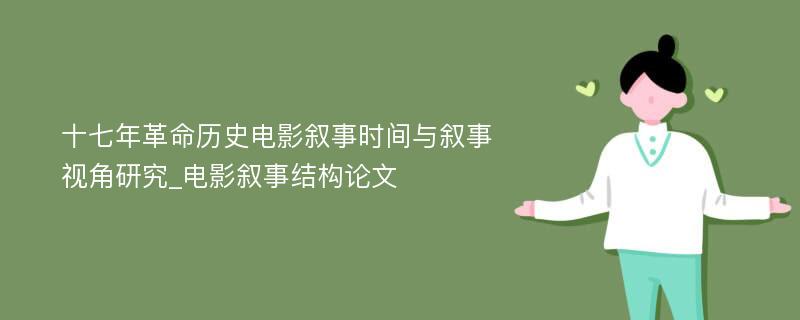
“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的叙事时间和叙事视角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题材论文,时期论文,时间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9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302(2015)02-0063-06 叙事是以事件的转变为前提的,它意味着从一个事件转向另一个事件,在这个过程中,总有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叙事就是一种“把时间和空间的信息组织到一条包括事件的开始、经过和结束的因果链中的方式”[1]3,叙事意味着时间性,因此,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才会提出,叙事是叙述者与时间进行游戏。运用电影手段对时空进行压缩或延展是电影独具魅力的地方,因此,叙述者如何安排时间是电影创作者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只有时间得到重新的安排,叙事才存在。 一、“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的叙事时间 叙事时间是故事时间与文本时间相互对照所形成的时间关系。 我们可以从对时间的选择、时间顺序的安排和时距(时间的变形)三个方面来考察“十七年”(1949-1966)时期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的叙事时间。 (一)时间的选择 叙述者面对的银幕放映时间是有限制的,伸缩度非常有限,叙述者必须把现实世界中无限的时间纳入到一个有限的时间范畴内。 世界是多向度的,同一时间内在不同的空间会发生无数的事件,而且,各自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可是对叙事来说又都是重要的事件,必须有所交待,但银幕上不可能同时呈现两个时间,只能把共时性的事件排列成历时性的事件。 因此,叙述者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选择时间。在罗兰·巴特所说的“将现实转换为言语”的过程中,放弃是必须的。有些创作者往往拘泥于史实,或者不忍割舍任何材料,或者不善于进行概括,面面俱到,平均使用力量,这样就会让次要的东西占据了宝贵的篇幅,冲淡核心内容的分量,而成熟的艺术家却有去芜存精的本领。选择或保留哪一段时间,可以依据这四点原则。 第一,保留跟表现主题有关的时间;第二,保留跟情节推进有关的时间;第三,保留跟塑造人物有关的时间;第四,保留跟现实生活密切相关、能够引发观众更多思考的时间。有些时间段虽然看上去和故事情节的推进没有直接的关联,但通过它可以反映民风、民俗、宗教、信仰等,可以更立体地表现人物的性格,它也可以成为文本时间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个成熟的艺术家面对浩繁的时间世界,能够表现出极强的选择、集中、概括的能力。“十七年”时期的创作者在这一点上是做得比较出色的。因为受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的影响,创作者已经把对“典型性”的追求内化为一条相当自觉的创作原则,渗透在从创作构思开始的每一个阶段。 以影片《上甘岭》为例,叙述者对时间处理就显得收放自如。实际的战役共持续43天,经历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经过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战斗,产生了无数惊天动地的英雄故事。那么,应该凸显哪段时间?最终,编导选取了三个阶段中最残酷、最足以表现人物精神面貌和英雄品质的第二阶段,也就是把坑道斗争阶段作为影片的核心时间段。但24天坑道战的时间跨度也不可能完全搬上银幕,因此,叙述者又面对时间选择的问题,叙述者从生活出发、合乎逻辑地把重点放到水的问题上,作为主线、矛盾的焦点贯穿全剧。创作者这样的时间处理方式,从完成影片的效果看是极佳的,战争的残酷性有了,人物的性格出来了,矛盾冲突也更集中。 同样在时间处理上,《农奴》的创作者也做得相当出色,导演能够利用节奏的变化、时间的选择对重要的环境、段落进行渲染。如影片的开头,从直冲云霄的喜马拉雅山化入雅鲁藏布江镜头,再化入喇嘛庙的金顶,摇到喇嘛吹长号的长镜头,导演用两分半钟时间展示了西藏特有的地域和文化背景。对于从未在银幕上出现过的西藏,这样的描绘是必要的。紧接着是强巴的母亲和戴着木枷的一队农奴向领主交粮的两个长镜头;强巴背负老爷前往解放军驻地一段,也运用了多个镜头进行渲染,不是轻描淡写一扫而过,而是突出了统治者的千钧重压及被压迫者的愤懑之情。 (二)时间的顺序(时序) 现实中的时间不可逆转,以线性的状态向前推进,事件的发生有先后时间关系,叙述者完全可以按照事件本身的时间形态展现出来,这是一种相对简便的方式,也是叙述者经常采用的方式。叙述者面对时间这样一种可变的因素,经常采用的有两个选项,即顺叙和倒叙。 顺叙:常规电影中最常用的一种时间处理方式是顺叙,以故事时间本来的前后顺序来叙述事件。它的优点是这样的时序安排和观众的审美经验一致,并不需要观众在不同的时间体验中穿行,容易让观众有认同感,是一种对创作者和接受者都比较省心的方法。“十七年”电影中大部分的时序安排是顺序,但如果所有的影片都选择同一种时序,那就失去了探索其他时序的机会,也不能体会到时序的变化有可能带来的叙事的活力。同时,从顺序本身来考察的话,按部就班的处理方式有可能因为面铺得太开,而使整个叙事结构显得松散。 时间倒错:时间倒错有两种形式——倒叙和闪回。倒叙是通过某个主人公的回忆,比较完整地叙述故事来龙去脉的一种叙事时间安排方法,中间一般不会再有意打断叙事的进程(也有叙述者先把故事的关键情节呈现出来,然后再话说从头)。影片《南岛风云》就是通过主人公的回忆,倒叙整个故事;《柳堡的故事》也是通过连长的回忆来讲述故事;在影片《芦笙恋歌》中,拉枯族老人用了整整50分钟回忆在国民党统治下一对恋人的不幸遭遇。 闪回是倒叙的一种,但它持续的时间很短,有时可能因为主人公的回忆而持续几个段落、几场戏,有时就可能只是配合主人公的内心情绪而出现几个关键性的画面。在《达吉和她的父亲》中有达吉的父亲回忆小达吉,给她刻长命锁的段落;《洪湖赤卫队》中韩英在狱中回忆彭霸天强占田地、茅房,把临产的韩英娘赶到一条破船上的悲惨经历;《柳堡的故事》中刘胡子强迫二妹子父亲要他把女儿嫁给他的段落,也是通过闪回段落表现的,刘胡子狰狞的面目通过一场戏就充分暴露了;在《青春之歌》的第一组合段中,崔嵬插入了一个括入组合段来倒叙林道静生母的身份、被逐与投河自尽的惨痛经历,确认了林道静在阶级属性上的归属问题。《大浪淘沙》中的闪回段落把靳恭绶替父报仇、砍杀地主、遭官府通缉的几个代表性的段落呈现出来,充分表现了这个人物对剥削阶级的深仇大恨。 (三)时间的变奏 按照传统的、约定俗成的习惯,一部影片要在两个小时内完成叙事行为,创作者必须对时间作出处理,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对文本中的时间进行改造,文本的时间流动就完全控制在创作者手中。在“十七年”电影的优秀作品中,导演对时距的控制可谓得心应手。 时距在热奈特的表述中被称为时间的变形。时距也可称为叙述的步速。热奈特指出,时距探讨的是事件实际延续时间和叙述它们的文本的长度之间的关系,在分析电影叙事时,叙事的速度主要可以分为三种方式:时间的省略、时间的膨胀和时间的复原。 时间的省略指的是文本时间少于故事时间,创作者往往对整段故事时间不加表述就直接跳过去,完全忽略它。文本时间的有限性决定了叙述者对时间的省略是不可避免的,而需要解决的是省略什么、省略多少的问题。在跳过的这段故事时间长度中,文本时间长度为零,因而,可以说叙述的步速是无穷大。 1.切是电影中最常见的省略时间的方法,是剪除枝蔓的有效方法,导演经常用切来进行时间上的跳跃。通过切,场景转换了,从一个时间直接过渡到另一个时间。以《农奴》为例,大量的省略恰到好处:领主的鞭子一扔,紧接着是一个特写镜头,鞭子已落在强巴家,而中间鞭子是怎样从领主的地上被捡起来,路上花了多少时间送到强巴家都一概被省略。在影片后半部中,如昏死过去的强巴被解放军搭救,护士为他作了精心的包扎,但管家却硬要先带走强巴。解放军军官和医生目送着强巴骑马远去,紧接着就是强巴的两手被管家拴在马后、拖曳狂奔的全景。导演在此用了六个短镜头组接在一起:被马拖着的强巴、管家骑在马上奔驰、强巴被拖而过、管家回首恶视、强巴仍被拖着、管家挥鞭策马,这六个镜头的长度相等,每个镜头不到一秒钟。然后,插入格桑在石头后面注视的镜头,紧接着是强巴被拖过镜头,鞋脱落在地上,下一个镜头则是强巴被拖的绳子松落,摇至喘息的马,却不见管家人影,而后,从地上的衣物摇至厮打中的格桑和管家,直至格桑制服管家。这场戏,从管家把强巴拴在马后对他说“我给你去去邪气”开始,一直到强巴被格桑所救,一共用了20个镜头,1分40秒时间,就表现了强巴被折磨、管家被杀和强巴被救的整个过程。 2.“十七年”电影中,常见的省略或者时间过渡的手法还有叠化、淡出、淡入等手段。 淡出和淡入相当于戏剧中的幕下和幕启,用来表现情节段落间的过渡。影片《红旗谱》中,朱老忠回乡后,从盖房种地、犁地的镜头直接叠化成收获的场景,中间的几个月时间就跳过去了。影片《刘胡兰》中,伴随着“沿着几千年封建社会的道路,刘胡兰渐渐长大了”的画外音,镜头从石磨拉开,叠化成青年刘胡兰,空间没变,时间已经过去十来年了。 影片《农奴》中,强巴的母亲从石阶上滚落下来,即用渐隐,紧接着是渐显的婴儿特写,配合着婴儿的哭声,母亲自语:“别哭,你已转世投胎成人。”从母亲晕倒转为新生婴儿的特写镜头,节奏相当紧凑。小强巴不堪“少爷”的折磨,想跳江自尽,导演利用江水滔滔的画面,叠印少年强巴的特写镜头,再接以成年强巴的特写镜头,然后渐显成年强巴在马厩旁喝水的特写镜头,中间强巴如何熬过来的时间直接被省略了。在创作者看来,强巴在这段时间里一定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但这样的日子多是重复性的苦难,并没有给强巴的生活带来多大的改变,所以这段时间完全可以省略。 影片《逆风千里》中,有一场解放军指战员押着俘虏前往军区驻扎地奉城的戏,镜头是这样处理的: 镜头1:画面上先是木牌的特写,上面写着“此处离奉城15里”,镜头往画左摇成指导员的中景,再拉开,出现部队行走的全景; 镜头2:战士脚的特写; 镜头3:行军中战士的中景,画面往右摇到写着“10里”字样的界碑; 镜头4:界碑上的字叠化成“8里”,镜头从特写摇到战士的近景,指导员边走边说:“敌人已经有新动作,有些蹊跷”,再移、摇到树梢; 这组镜头运用得很灵活,动静结合,巧妙地叠化处理,表示时间的推移和场景的变换,不是简单的交待,而是流畅的组接。 3.用画外音或字幕说明来进行时间的省略 在威虎山大摆“百鸡宴”那场戏中,已经取得座山雕信任的杨子荣奉命筹备庆祝座山雕60大寿晚宴,杨子荣为了把土匪一网打尽,设计把土匪集中在一起。宴会前,杨子荣出现在空荡荡的威虎厅,他巡视着四周,这时内心独白又适时地响起,伴随着1分37秒钟的长镜头,由全景摇成中景,威虎厅里摆满了空桌子:“今天就是旧历的年三十,侦察英雄杨子荣凭借着他的勇敢和智慧,当上了威虎山的司宴官,并说服了座山雕这个老匪,把今年的百鸡宴全部摆在了威虎厅里,白天杨子荣指派全山的匪徒,把威虎山前前后后总共安排了六六三百六十个松明火把,说这是山光普照……”画外音没有中断,镜头切换,又是一个长2分15秒展示威虎厅外的长镜头,杨子荣沉思着——“……把威虎厅的里里外外也安排了60盏野猪油灯,说这正应了座山雕的60大寿了……”接下来还是一个长3分12秒的长镜头,杨子荣的中景——“……所有这些行动,不但没有引起座山雕的怀疑,反而使这老匪非常的满意,非常的赞赏……”这段7分钟的独白,时间并不短,如果直接用画面表现杨子荣白天的行动,也是一种方法,但导演并没有采用,而是选用了用画外音来交代,可能有两方面原因。如果直接用画面表现,那几场戏只是行为的罗列,会显得零散。另外,在这样相对安静的环境中出现画外音,观众的注意力更加集中,情绪被调动起来了,紧张感加强,更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阵势。 在影片《红旗谱》中,朱老忠回乡在保定车站广场的一场戏,安排了一对唱大鼓书的艺人说唱“朱老巩大闹柳镇”的事迹,来交待25年的时光已经过去,同时又以此来反映河北的地方风情,是极具匠心的。 在进行大段时间省略时,“十七年”电影中经常采用的手法是用字幕直接说明,用“×年后”表示时间的流逝,接下来的画面内容就是若干年后的场景,从中可以判断创作者对某些时间段的重视程度。 一般来说,文本时间是经过压缩的,但有些时间又需要延展,叙述者出于美学上的考虑,需要把一刹那间的情景扩充,以便对某段时间进行格外强调,于是时间被放大和膨胀了。 膨胀(减缓)时间的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导演通常用增添大量细节和局部描绘的镜头来展示情节,故事发展的速度自然被延缓下来。 影片《董存瑞》最后的华彩段落,故事时间可能就是爆炸的短短几秒钟时间,但影片却用了近1分30秒钟、14个镜头来渲染:1.董存瑞托起炸药包的全景;2.董存瑞托炸药包的中景;3.董存瑞的近景,高呼:“为了新中国,前进!”;4.炸药包的特写;5.董存瑞眼睛的大特写;6.导火索的特写;7.董存瑞的脸部特写;8.桥头堡被炸的全景;9.连长的特写;10.(叠化)董存瑞要求参军的中景;11.王兵找董存瑞谈心;12.董存瑞行军的中景;13.董存瑞的标准像;14.长城的全景。在这个蒙太奇段落中,时间的放大把英雄的成长、最后的壮举、战友的怀念和永垂不朽的形象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观众的情绪也在这一刻得到总爆发,如果按照生活中的实际时间来表现,这场戏就会显得轻描淡写,起不到让人热血沸腾的强烈效果。 另外,创作者还可以用镜头速度的变化以及镜头角度的变化来达到时间膨胀的目的。高速摄影的手法在“十七年”电影中运用得并不多。 时间的复原是指叙事时间和故事时间是一致的。时间复原在电影中经常是以长镜头的手法出现,它保持了时间上的延续性和空间上的完整性,时间得到创作者最大限度的尊重。长镜头在《小兵张嘎》《风暴》等影片中都有实践,有些段落也成为了影片视听处理中的华彩篇章,但总体而言,在这一时期的电影中并不多见。 二、全知视角与限制性视角 讲述一个故事意味着构筑一个可供观看的文本,而要构筑一个文本,就会遇到一个关键的问题:由谁来讲述这个故事?同样的事件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就可能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在不同的人看来也会有不同的意义和结论。叙述的魅力不仅在于讲述了什么事件,还在于是什么人、从什么角度观察和叙述这些事件,这就涉及到叙事视角的问题。叙事视角是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切入点,视角问题也被称为视点问题,一般可以把视角分为两大类:全知视角和限制性视角。 (一)全知视角的美学效果 全知视角的叙述者隐身在文本背后,但他似乎无处不在,可以在同一时间内出现在不同的空间,他对每个人物身上发生的事情都了如指掌,有人把全知视角称为是上帝的视角,因为,创作者像上帝一样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编导采用全知视角是尽力想让观众沉浸在故事之中,感觉不到有个叙述者在讲述,不要出现间离效果。 采用全知视角讲述故事的优点在于:文本会显得比较客观、真实,创作者隐藏起摄影机运作和叙述话语的“讲述”痕迹,尽可能顺着事件发展过程中的因果联系,制造出一种“现实幻象”。影片《革命家庭》的原著是用第一人称回述的一个故事,在改编成电影时,编导对素材进行了大幅度的取舍和调整,将原来是次要人物的母亲改为主人公,大量增加她的戏份。剧作上更大的一个变动,就是把限制性视角改成了全知视角,在表现手段运用上享有更多的方便和自由,内容也容易被观众接受。 对于用全知视角讲故事的电影,较真的观众会怀疑故事的真实性。他在观看过程中,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当时主人公又不在现场,他怎么会知道那么多细节?就会明显感觉到是编导“编排”的结果。一旦观众起了疑心,察觉到人为的痕迹,就会“出戏”,导演试图让观众信服的意图就很难实现。叙述者对人物的命运、对所有事件可完全预知和任意摆布,观众在观看中只能被动地等待叙述者将自己还未知悉的一切展现出来,这样就剥夺了接受者探索、解释作品的权力。全知视角往往是面面俱到,平均用力以后,有可能对某事或某人的性格特征挖掘得不深,它更注重外在行动的变化,而缺少人物内心活动细致的变化。 (二)限制性视角的美学效果 限制性视角是以影片中某个人物的视角来叙事,银幕上只表现他(她)看到的、听见的人和事,只知道部分事实,所叙述的既可以是往事,也可以是正在发生的事件。限制性视角主要分第一人称视角和第三人称视角。 第一人称视角。在第一人称叙述的作品中,叙述者同时又是故事中的一个角色,借“我”之口来讲述故事,画外音经常是第一人称视角的外在形式。这个人物作为叙述者兼角色,他不仅可以参与事件过程,又可以跳出事件的进程,进行即时的描述和评介。这双重身份使这个角色带有特殊性,它比其他故事中人物更“透明”,更易于理解,当画面上出现人物时,叙述者就用旁白配合他“现身说法”。从某种意义上讲,用画外音来讲述故事、发表议论,会使影片更多地暴露人为介入的痕迹,文学味浓了点,但运用得好,却能给人丰富的联想和对时代、人物和事件更为完整的体验。 叙述者会努力把声音上的“我”和画面上的“我”等同起来,最大限度地让观众相信他说的,看到的都是真实,是没有经过加工的事实。 第三人称视角。叙述者的视点是附在影片中的某个人物之上的,他只向观众讲述他在场时经历的、目睹的事实,凡是他缺席的时间段是不被叙述的。在遮蔽和暴露之间有一个张力,在这种张力的牵引下,驱动故事有序地向前发展,限制视角能够不时引发观众的好奇心和探究真相的欲望,使接受者的神经像拉牛皮筋那样,获得某种“弹性的快感”。 限制性视角具有以下五点美学效果。 第一,这一视角运用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叙述范围上的“有限性”或“假定性”,受到角色身份的限制,不能叙述本角色所不知的内容。就影片来看,这种限定并非一定要固守在主人公身上,或许可视为故事中的一个特殊“人物”,排除了“作者的无所不知,或者说排除了主人公的智力所及范围之外的见闻,从而一开始就显得‘超现代化’”[2]。《柳堡的故事》是以第一人称叙事的,影片开始时,连指导员骑在马上回到柳堡,画外音响起:“5年以前,那是1944年的春天,我在新四军的连队里当指导员,部队曾经开到这里来休整过,我们连就住在最前哨的庄子——柳堡。那时候刚解放,庄子里寂静得像没人一样,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在这柳堡会留下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在影片叙事的展开过程中,指导员不仅是目睹了事件发生和发展的整个过程,而且参与了其中的某些决定性意见,他直接影响了副班长的行为,因为他的决定和意见使得副班长没有一味地把精力放在个人的感情生活上,而是及时克制了自己的情感。应该说,这样的视点更增加了影片的说服力,因为在战争年代,指导员对每个战士的思想状况、情绪波动都是了如指掌的。 第二,采用限制性视角显得更亲切,它会产生一种更接近于正常感知过程的理解方式,对于观众认同和理解故事、参与叙事进程、触发思考是大有裨益的。因为,在法国电影理论家马格尼看来,“暗室中的人”无所不知但“有点置身事外,他客观地投身到他过去不曾体验过、现在也不再体验的故事中去,他可以一个接一个地站在每个人物的位置上,他认为能看到某些本来绝无可能看到的生活景象是完全正常的,倒不是因为这些生活景象是荒诞的或不可思议的,而是因为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视听方式是完全不同的”[3]。 第三,采用限制性视角显得更逼真,更有说服力。这种限制造成了叙述的主观性,能产生身临其境的逼真感觉。影片《上甘岭》是以日记体的形式叙述故事的,开篇就是一则战斗日志:“1952年10月14日,美国侵略者为了破坏和平,扩大战争,他们在板门店拒绝了和平谈判以后,就在今天早晨5点15分向我上甘岭地区两个山头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然后,导演又选取了10月18日、19日、25日、30日和11月11日共五天的“战斗日志”作为导引,讲述了发生在那些天的战斗经历,期间有一天内打退敌人23次进攻的,也有爆破失利的,最后是取得决战的胜利,迫使敌人在板门店谈判。这样的视角在“十七年”电影中显得独特新颖,既给人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又因为日期的确切标识,增加了纪实性,有一种载入史册的庄重感。 第四,采用限制性视角可以让观众更轻松地进入故事。观众只需认同其中的“这一个”,跟随着他(她)的行动,便能顺畅地体验到这个故事,免去了全知视角下逐个地注意和同情众多角色,要先滤清各种线索的麻烦。 第五,采用限制性视角,影片的情感描绘显得更细腻。这样的讲述方法更带有感情色彩,容易让人相信事情的真实性,另外它是“走心”的戏,就有篇幅去关注人物的内心生活,表现他(她)的情感波澜,不是粗线条的勾勒,而是细致的铺排。 当然,采用限制性视角也有它的问题,在影片叙述中,纯粹“我”的叙述实际上是没有的,纯粹客观是创作者的一厢情愿,从某种意义上说,电影里就只有一种全知视角,那就是编导的视角,限制性视角是叙述者对全知视角的一种伪装,目的是想打消接受者的某些疑问,摆在创作者面前的问题也就是把伪装做得更隐蔽一点,更巧妙一点。其实,不管是全知视角,还是限制视角,都无法回避观众对电影是一场人为编制的“白日梦”的心理预设。另外,限制视角是通过某个主人公的视觉和听觉来认识世界,往往有一定的局限性,面不是那么宽,因而带有很浓的主观色彩,过分渲染后,就会显得矫情。 “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的视角主要是以全知视角,以及限制视角和全知视角相结合的方式叙述故事。创作者更多地选择了让叙述者恰当地“隐身”在作品背后,尽可能突出形象魅力,靠情节自身的推动力向前发展。 全知视角让接受者知道故事的一切,这是创作者为了对应“人民电影”的要求,让群众“看得明白,看得顺畅”是最主要的,而艺术家个人风格的凸显是次要的。即便是采用限制视角的作品也不是纯粹的限制视角,它也是结合全知视角来叙述的。比如《女篮五号》中有从教练田振华、林洁的视角讲述的段落,但影片整体上采用的还是全知视角。《柳堡的故事》是以“我”(连指导员)叙述的方式来讲述故事,是限制性视角,但影片中的某些场景,比如副班长和二妹子两人的交谈场景,指导员实际上是不在场的,这时影片就明显转换了叙述角度,变成了全知视角。 “十七年”时期的电影工作者将叙述的重心放在“讲述故事”上,而不在“怎样讲述”上,因此在视角的探索上还比较保守,但这并不影响那个时代作品的成色。事实上,电影人拍出了众多无愧于那个时代的作品,共同铸造了一个以“红色经典”为标识的辉煌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