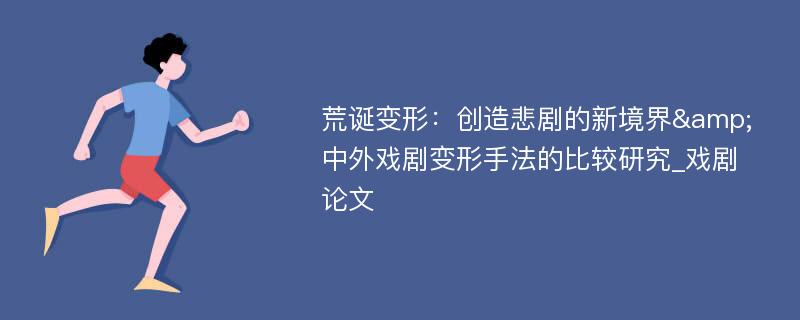
荒诞变形:创造悲剧的新境界——对中外戏剧变形手法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荒诞论文,手法论文,戏剧论文,中外论文,悲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我们把探寻的目光从法国荒诞派戏剧移向更久远、更广阔的世界戏剧舞台时,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六百多年前法国的《亚当的演出》、本世纪初的《蒂雷西亚的乳房》,还是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关汉卿的《窦娥冤》,或是中国当代话剧《车站》、京剧《潘金莲》等无数作品,对荒诞变形手法都有出神入化的运用,从而达到创造悲剧新境界的目的。本文拟就此作些探讨。
一
1950年尤涅斯库的《秃头歌女》在巴黎首演,开创了一代荒诞派戏剧的新风,随后塞缪尔·贝克特、阿达莫夫、让·冉奈的戏剧纷纷在法国上演,荒诞派戏剧已成为本世纪戏剧舞台和戏剧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文学现象。其所以重要是在于荒诞派戏剧极尽荒诞变形手法之能事,描绘了我们这个到处充满着荒诞事物、多事而不安宁的世界及其生活于其中不知所措的人。尤涅斯库的《犀牛》便是这类戏剧最好的说明之一。
尤涅斯库曾经这样说过:“我确信先锋派(荒诞派的另一种称呼)的目的在于在它们的最纯的状态里去重新发现——而不是重新发明——戏剧的永久形式和遗忘了的理想。”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的戏剧选择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现实,经过变形和放大处理,好比哈哈镜上的影像,使之来自现实又超越现实。然而,经过这种变形——不是一个人,而是所有人;不是一件事,而是整个舞台上所发生的一切,全方位地荒诞变形,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不理解,人与社会、自然的对抗,人受高度资本主义化的社会机器的摆布和人不甘受其摆布而发疯发狂变为犀牛(犀牛正是人性异化、疯狂之极的变形),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关系的荒诞性均毫无例外地凸现出来,使人们被压抑、被扭曲的心灵一展无余,从而向人的存在本身、向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提出疑问。由此看来,以尤涅斯库为代表的荒诞派戏剧常用的荒诞手法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身不失为一种有力的批判方式,即:揭示资本主义世界的荒诞是人世悲凉的根本原因。
其实,荒诞变形手法的运用,在法国戏剧史上可以说是源远流长,从12世纪中期的《亚当的演出》到19世纪末A ·伽利所创作并演出的《乌布王》(Ubu roi)和另外两个以Ubu为主人公的戏剧,一直到本世纪初阿波利奈尔的《蒂雷西亚的乳房》(1917)中都不难发现这一点。事实上,在欧洲早期剧作中,变形手法也是广泛使用的,就连莎士比亚也不例外。关于《哈姆莱特》中的丹麦王子在鬼魂的启示下为父报仇,莱辛在《汉堡剧评》中指出:“迷信鬼魂的种子深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尤其是深藏在他主要为之而创作的那些人的心里。他的艺术就在于使这种种子发出芽来,运用某些技巧的目的就在于说明它的真实性的理由转瞬之间即呈现出生气勃勃的形象。”“莎士比亚就是这样的作家……不论你信或不信,在他的《哈姆雷特》里的鬼魂面前是要毛发悚然的。”“因为它出现在庄严肃穆的时刻,出现在恐怖的寂静的夜间,出现在充满着忧郁、神秘气氛的环境中,犹如我们当年和乳母在一起等待想象的鬼魂一样。”
莎士比亚虽然是现实主义作家,却在自己的悲剧中穿插一些幻想的成分(如亡父的鬼魂)。使整个舞台和情节笼罩了一些神秘的气氛,但倘若我们稍稍拨开一下迷雾,就不难看出莎士比亚对当时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社会的阴暗面是有所认识的,但在王权至高无上的一统天下中,又有什么可以凌驾于“王公贵族”之上呢?唯有神,神力无边,借助神力主持正义既符合基督教的教旨,也符合西方“神人合一”的传统精神,进而表明,即便是“丹麦王子”也只有借助神力才能明辨事实,才能为父报仇这种超越王朝、王权统治之上的整个国家、社会、人民的悲剧事实。而且我们应该记住,对莎士比亚的同时代人来说,这并不是幻想,他们是相信鬼怪的。莎士比亚的观众只觉得鬼魂可怕,却不以为是捏造。
二
无独有偶,象《哈姆莱特》这样借助鬼魂达到复仇目的的戏剧在文化渊源完全不同的中国元代也已有上演。所不同的是,一个是王子复仇,一个是贫女洗冤,这当然也给作品的思想意义带来不少差异。
一般人往往把关汉卿的《窦娥冤》第三折说成是悲剧的高潮,或者说最重要的戏——悲剧的升华皆在此折中了——因而评论的重点都集中在这折戏上,这是欠妥的。当然我并不是说这折戏不重要,确切地说,悲剧在这折戏中确实达到了高潮。关汉卿在这折戏中,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最完美地表现了他对人民的同情和对封建统治者、压迫者的痛恨,他把全部感情都融进了对窦娥死前的最后刻划。先是把窦娥放在现实生活矛盾最尖锐的冲突中,以大段的唱词,抒发她的悲愤感情,把窦娥之死提高到悲剧的最壮烈的境界,增强了悲剧效果;接着又通过浪漫主义手法,把窦娥的三个誓愿一一应验,这种本正末奇、真幻相生的结果,使整个悲剧达到了高潮。问题是,这种高潮在第四折中并没有消退,且可以说有所升华,至少是保持在同一水准上向着喜剧性的结尾过渡,其中起桥梁作用的正是窦娥的魂灵。
这鬼魂“每日哭啼啼守住望乡台,急煎煎把仇人等待”,希望报仇雪恨。恰好做了肃政廉访使的父亲到了本县,照理大权自家手中握,平反冤狱该是不在话下,其实不然,因而就使得鬼魂的斗争从一开始就很艰难。
这首先表现在肃政廉访使窦天章的昏庸上。他拿起窦娥一案的文卷一看,“头一宗文卷,就与老夫同姓”,便以为不祥,借口这是“问结了的文书,不看他罢”,随即信手压在下面。当他知道一再出现的鬼魂就是自己的女儿时,他也仍把她看作十恶不赦的杀人犯,并大发一通“三从四德”的感慨,俨然是一副秉公守法的封建卫道士形象。
其次是他办案不力。当窦娥的鬼魂以血泪控诉封建统治的残酷和虚伪,窦天章改变了对女儿的看法,但真当他复勘此案时,他又显得无能,面对张驴儿的耍赖,窦天章穷于无词以对,只好请窦娥的鬼魂上场,当面对质,张驴儿不敢再耍赖,窦娥的冤案始得以平反。
戏演到这里给了我们一个启示,纵使窦天章“廉能清正”,其作用还抵不上一个鬼魂。这一启示以及带给我们这些启示的所有戏——鬼魂的所作所为,更有人与鬼的当面对质,看上去是不合人之常情,倒象是鬼魂在为所欲为——按照它自身的逻辑行事。事实上,第四折中的三番“翻文卷”,几次“剔灯”——为争取父亲重审冤案的说理,还有那平反冤案的关键所在——出堂作证,与其说是鬼魂超现实的魔力,还不如说是人民的、作者的愿望,是按现实生活的逻辑加以规划并升华的,在一定意义上说,是窦娥至死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的升华,这种升华到最后以她的一曲[收江南]达到了最高峰:
“呀!这的是衙门从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痛杀我娇姿弱体闭泉台,蚤(早)三年以外,则落的悠悠恨似长淮!”
窦娥的鬼魂是清醒的!窦娥是清醒的!那么观众呢?是鬼魂使窦娥蒙受的不白之冤得以洗清,然而,世上何有鬼魂出堂作证之事?所以[收江南]反映的是现实生活的实际,这就把单纯的窦娥个人的悲剧上升到了封建社会全体劳动人民的悲剧的高度。由此可以肯定,关汉卿借助窦娥的鬼魂,其真意不是为被压迫者提供死后憧憬,而是通过这种超现实的手法的运用,把“衙门从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的封建社会的荒诞性昭示出来,进而更强化了封建统治下普通大众的悲剧性命运。
其实,在许许多多的文艺作品中都存在这种对现实生活原型作大幅度变形的事例,并且从广义上,一切艺术即变形,只是各自的变形程度不同即抽象的程度不同而已,作为艺术的戏剧亦如此。它必然对生活有所取舍、概括、加工,生活中的素材到戏剧中必然有所变动——变形,因此也就必然需要补充、想象和虚构原型的某些细微末节,以此来反映出生活的本质真实。中国古典美学中的一条重要原则是“离形得似”,窦娥的鬼魂大概就是从这一原则出发而产生出来的一个别具一格的形象吧。
这种借鬼魂或其它替代物同常人混同,并为常人所不能的变形手法在中国古代神话、神怪小说、戏剧中是十分多见的,而且变形的手法更加多样化,及至当代的话剧舞台也时有所见。
三
中国当代剧作家高行健对现代西方戏剧流派的各种戏剧观,并未简单地一概排斥、否定,对其创作技法也未简单地加以模仿,而是从建构自己的戏剧出发,以西方现代派的艺术观为参照系,对包括荒诞派在内的多种创作技法进行了广泛的选择和学习。同时,他也从中国传统戏剧那里摄取营养,拣回了时空自由、唱念做打、虚拟表演等一系列表现手法,得其神而遗其形,达到驾驭舞台时空的高度自由。因此,当我们把《等待戈多》与他的《车站》放在一起,进行表现手法上的比较研究时,我们发现二者的联系只是表面上的近似,其差别却是更深刻,更本质的。我们从他们运用较多的象征、比喻、抽象和非逻辑化这四个方面作些考察,便可认识到这一点。
1.象征是《等待戈多》和《车站》中的一个重要表现手法,意在塑造象征性的舞台形象。《等待戈多》运用的是同构象征手法——使具象与观念一体同构化,目的在于使舞台与整个世界及人类达到一种同构,那么戏剧就是对世界本质和人类生存状态的揭示和展演。那两个等待戈多的人,不是具体环境中的具体人物,而是丧失理性、又茫然幻想的现代人类的象征;那个破碎、混乱的舞台,就是破碎、混乱的世界。《车站》的象征手法则是诗意化的——对生活的感受和提炼,通过象征使看似寻常的生活场面得以强化、耐人寻味。为此,作家在剧中运用了多声部道白、立体化表演区域、象征性主题音乐等方式,无论是对时间还是空间的处理——瞬间十年,废站通知——置人于绝望之境的骗局,都是作者对中国那段特殊年代的主体感受和内在情绪的外化。
2.直喻是荒诞派戏剧最基本的表现手法。其大致含义是,舞台上的一切,都是荒诞观念外化的具象,无论是人物、语言、行动,还是布景、道具,都构成为喻示的“场景”,本身就具有“纯粹戏剧性”。以动作而言,荒诞派戏剧家取消了它的传统含义,并不让动作来说明其他内容,如塑造性格,而是把动作当做喻体,作为仅仅表白它自身含义的“视觉形象”——只说明行动的荒谬令人难以理解。高行健在创作《车站》时运用了隐喻,因而不象荒诞派戏剧那样直接与其观念相联系加以展现。音响在《车站》中是主要的隐喻体,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作者创造性地让音响也成为一个独立的角色,同剧中人,也同观众,进行对话。《车站》的音响,一是汽车的声音,一是沉默的人的音乐,它们交相在剧中出现,不只是具有说明性或烘托的意义,更带有丰富的喻示意味:汽车声带来诱惑,是让人一等十年的这场骗局的直接参予者;沉默的人的音乐却时而坚定,时而嘲弄;时而激越,时而又宏大而诙谐,喻示着人和社会的理性内容。它们以两种不同的角色,对比着抗衡着反复出现,一次比一次强烈,所蕴涵的形象意义,已远非一般戏剧音响所能比拟。如果说贝克特是通过直喻来把握世界,高行健则是借助隐喻强化了其戏剧中带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写意性。
3.科技进步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人们对这个世界仍感到茫然无措。贝克特认为,这一切都不可名状、不可思议、不可表达。如果要通过舞台来直喻这种虚无感,只有用虚化的表现手法。在《等待戈多》中,人物和场景几乎全是虚幻的,看不出什么特指的现实内容。弗拉基米尔和爱斯特拉冈,从大幕拉开时就在那里,直到大幕关上,关于他们的身份、他们在干什么没人知道,他们虽顽强地等待着,但又是那么无聊,似乎等待并不是他们的目的,更何况等待的究竟是什么,他们也全然无知。那个“戈多”,更是难以猜测。虚化手法的运用,使作品剥去非本质的东西,剩下的便是更直接的“纯粹戏剧性”。在表现人物、设置场景、安排情节方面,高行健运用的是抽象化或在中国传统戏剧里称为虚拟表演的手法,使它们既有特指内涵,又是抽象化的。他把车站的铁栏杆设计成十字形,使它抽象为人生道路上的一个交叉点或是各个人物生命途中的一站。剧中那位沉默的人,也被抽象化了,变为一种带有感召呼唤情绪的音乐形式。这种具象又离象并独立存在着的抽象物,加上虚拟表演,不仅强化了作品的诗意内涵,使之更富于视觉与听觉上的冲击力和感染力;而且也使有限的舞台,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得以拓宽与加深。
4.无论是《等待戈多》还是《车站》,都是以打破生活现象逻辑为特征的,作者都力求按照他们自己所理解和需要的逻辑形式,来延伸作品的内涵。荒诞的观念在通常意义上就是非理性、非逻辑的观念,因而对非逻辑手法的运用,就成为表达这种观念的必然选择。《等待戈多》的道白处理,集中体现了这种非逻辑化:语言与心理动机的分离,因果关系的割裂,语言的非表意性,从而导致了语言功能的丧失,但这却正是荒诞派戏剧所要追求的最佳效果,这个世界本来就“不可思议”、“不可名状”。《车站》也不是象传统话剧那样,按照生活的逻辑组织起来的,更主要的是一种诗意的逻辑演绎,比如瞬间过十年,虽然违背逻辑,但也不是与荒诞观念相联系的非逻辑化,而是符合作家的戏剧观与创作个性相联系的诗意逻辑,与中国传统艺术的写意性是一脉相承的。高行健在创作这部作品时,试图摸索把现代戏剧与现代诗歌更融洽起来,努力表现出一种戏剧性的诗意效果:《车站》把抽象、象征、喻示以及夸张等变形手法,都纳入到诗意逻辑化的表现之中。在叙述上,为了更突出地表现心理情绪及其发展变化,除了用中国戏剧传统叙述一贯采用的线性(以时间先后为序)方式,作者还试用了音乐艺术的多声部结构,并借用了奏鸣和回旋两种曲式。这样,就产生出更深刻、更丰富的戏剧诗意效果。
应该指出,法国荒诞派戏剧运用超现实主义手法所达到的艺术抽象,是把一切都推向极端,而这极端便是社会悲剧的根源所在,是人物悲剧命运的根源所在。由此创造出一种气氛:既有强烈的喜剧性,又有强烈的正剧意味。面对这样一种场面——如犀牛四处横行,我们虽然害怕,但是我们却要笑;我们笑了,可全身充满恐怖;我们笑着,眼睛却是湿的。
由此可见,中外戏剧艺术观、戏剧观乃至世界观不尽相同,所使用的变形手法也不尽相同,抽象程度各异,但却是殊途同归,他们通过变形,使作品中的人或事超常,使舞台上虚实相生,真幻相融,极大地增强了作品视觉、听觉的感染力,进而达到作家理想的悲剧境界:让人们在悲中见喜,既悲亦喜,或既喜亦悲,喜悲相随,不得分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