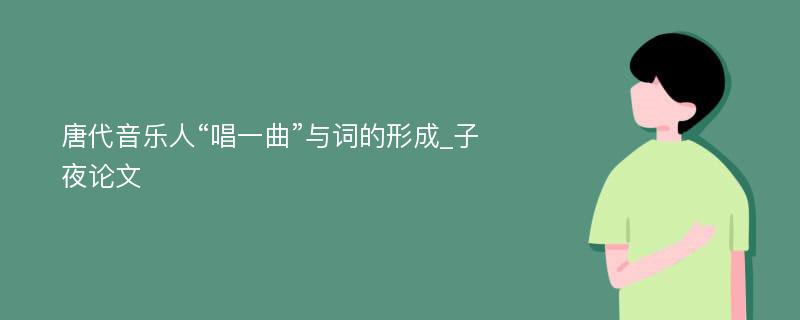
唐代乐人“善唱某曲”与词之生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代论文,善唱某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6)03-0135-05 一、某乐人“善唱某曲”是唐代乐界的普遍现象 唐代有许多文献记载了某乐人“善唱某曲”。如杜佑《通典》卷一四五:“大唐贞观中,有尚书侯贵和,妾名丽音,特善唱《行天》。……有郝三宝亦善歌《行天》。”①李德裕《次柳氏旧闻》载唐玄宗入蜀前登楼奏乐,“毕奏,上将去,复眷眷,因视楼下,问有乐工歌《水调》者乎?一年少心悟上意,自言颇工歌,兼善《水调》。使之歌。”②元稹《答姨兄胡灵之见寄五十韵》一诗注云:“歌者华奴,善歌《淅淅盐》。”③白居易《不能忘情吟》序云:“妓有樊素者,年二十余,绰绰有歌舞态,善唱《杨枝》,人多以曲名名之,由是名闻洛下。”④欧阳詹《闻邻舍唱凉州有所思》:“有善《伊》《凉》曲,离别在天涯。”⑤《云溪友议》卷下:“(周)德华者,乃刘采春女也。虽《啰唝》之歌不及其母,而《杨柳枝》词采春难及。”⑥《酉阳杂俎》前集卷三:“荆州贞元初,有狂僧……善歌《河满子》。”⑦许浑《听歌鹧鸪辞》序云:“妓人善歌《鹧鸪》者,词调清怨。”⑧这些文献都出自唐人之手,颇为可靠,反映出当时歌曲演唱的真实情况。 当今的一些研究者依据上述文献及其他相关资料,对唐代乐人“善唱某曲”的事实亦有所认识和阐发。任半塘《唐声诗》上编中说,唐代“工伎之奏弄歌啭尤擅长者,乃有某一曲,或某数曲,特别流行,超诸一般之上”⑨。在下编的一些曲调考证中列出了善歌该曲之乐人,如《子夜四时歌》下云:“初唐曹娘、中唐刘安皆擅歌之。”《何满子》下云:“善此曲之歌舞或琵琶者,先后见何满子、胡二姊、骆供奉、僧些些、沈阿翘、孟才人、唐有态、鱼家、叶氏诸人。”《想夫怜》下云:“大和中,有妓名多美者,善歌此。”⑩孙菊园《唐代文人和妓女的交往及其与诗歌的关系》一文亦云:“在唐代众多的妓女里,还形成了许多以专唱某一曲出名的妓女,如曹娘歌《子夜歌》……等。”(11)此外,杨军、李正春的《唐诗在当时的传播》,徐君、杨梅的《妓女史》,廖美云的《唐伎研究》,管林的《中国民族声乐史》,李剑亮的《唐宋词与唐宋歌妓制度》,徐有富的《唐代妇女生活与诗》等研究成果中都有类似的描述。 其实,倘若我们对见于书面记载且存留至今的唐代乐人资料进行分析就会发现,当乐人们从事歌唱表演活动时,往往把现成的诗歌配入自己擅长的曲调进行演唱。如《云溪友议》载刘采春善唱《望夫歌》,其“所唱一百二十首,皆当代才子所作”,而其女周德华善唱《杨柳枝》,“所唱者七八篇,乃近日名流之咏也”(12)。此段材料十分典型地说明了当时乐人选取文人诗歌配入自己所擅长的曲调进行演唱的情况。如果是文人现场作诗后立即交付乐人演唱,情况更是如此。如《南部新书》载:“卢常侍鉟牧庐江日,相座嘱一曹生,令署郡职,不免奉之。曹悦营妓名丹霞,卢阻而不许。会饯朝客于短亭,曹献诗云:‘拜玉亭间送客忙,此时孤恨感离乡。寻思往岁绝缨事,肯向朱门泣夜长。’卢演为长句,和而勖之曰:‘桑扈交飞百舌忙,祖亭闻乐倍思乡。樽前有恨惭卑宦,席上无聊爱靓妆。莫为狂花迷眼界,须求真理定心王。游蜂采掇何时已,却恐多言议短长。’令丹霞改令罚曹,霞乃号为《怨胡天》。”(13)这表明,歌妓丹霞善于演唱的曲调是《怨胡天》(此曲调见载于《教坊记》,非为丹霞临场自制),所以她能轻而易举地把一首七言律诗配入该曲调进行表演。 唐代还有许多现场演唱的事例,我们都可以做出类似分析。如李濬《松窗杂录》中载,开元中,唐玄宗与杨贵妃月夜赏牡丹,李白“进《清平调》词三章”,玄宗“命梨园子弟约略调抚丝竹,遂促龟年以歌”(14),必定是李龟年熟悉《清平调》,故在现场立即将李白所作之辞进行演唱。再如,《唐诗纪事》卷五十八载:“(韦)蟾廉问鄂州罢,宾僚祖饯,蟾曾书《文选》句云:‘悲莫悲兮生别离,登山临水送将归。’以笺毫授宾从,请续其句。逡巡,有妓泫然起曰:‘某不才,不敢染翰,欲口占两句。’韦大惊异,令随念。云:‘武昌无限新栽柳,不见杨花扑面飞。’座客无不嘉叹。韦令唱作《杨柳枝》词。”(15)由于这名歌妓善唱《杨柳枝》,所以她接到命令后能马上把七言四句诗配入《杨柳枝》曲调进行演唱。 综上所述,我们大体上可以做出判定:唐代乐人在歌唱表演中特别善于演唱某一曲调。而这正是唐代歌唱艺术的一大特点。 二、产生某乐人“善唱某曲”现象的主要原因 唐代的乐人为什么仅会“善唱某曲”?本文认为,其中的原因有三: 一是与音乐创作有关。我国古代的歌曲创作与今天不同。今天流行的“作曲”观念源自于西方的音乐传统,他们十分重视作曲家的作用,当新的歌词出现后,作曲家会立即创作出一首新的曲调与之相配,表演者只能依照曲调歌唱。而我国古代不是这样,“作曲”既不是独立的行业,也不是歌唱过程中的独立环节,它往往与表演“合二为一”,赋予表演者较大的主动性。表演者将一首新歌辞配入原有的曲调,进行增减变化,然后就可以付诸歌喉。在唐代,专门的作曲家或曾经创作过曲调的乐人很少。杨荫浏先生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九章中列出了将近百人的唐代乐人名单,作曲者仅有8人(16),所占比例极低。而且,所谓“作曲”,也只是创作了一二首曲调而已。何况当时的乐人以歌妓为主,属“贱民”阶层,文化素质低,并非都懂乐理、善作曲,不可能碰到一首诗歌便立即写出一首新的曲调,她们的主要职责就是表演,大部分人是以演唱某一曲或某几曲为谋生手段。唐代乐类文献中虽然频频出现“新声”一词,但其实它们大多是指对旧曲进行加工与改造,或者配上新的歌辞,并不是今天所说的“创制新曲”。如孟浩然《崔明府宅夜观妓》云:“长袖平阳曲,新声《子夜》歌。”(17)顾况《听刘安唱歌》云:“《子夜》新声何处传,悲翁更忆太平年。”(18)这里提及的《子夜》本是南朝流传下来的旧曲,所云“新声”是因为配上新辞后对旧曲有过一些加工,不同于原来的曲调。 二是与音乐传承有关。一般认为,我国古代是以人传乐,采用“口传心授”的方式,故乐师会将自己擅长之曲传给徒弟或子女,如李讷《纪崔侍御遗事》中载,歌妓盛小丛是“梨园供奉南不嫌女甥也,所唱之音,乃不嫌之授也”(19)。任半塘先生认为,教坊南不嫌善歌《突厥三台》,因而“教其女甥盛小丛”,盛小丛便经常歌《三台》。(20)在唐代,乐籍制度已确立,乐人世世代代从事乐舞表演,虽然维持了音乐曲调传承的稳定性,也导致其走向保守和封闭,致使各“音家”、各乐户都形成了自己的“保留曲目”,自然会促成有些乐人“善唱某曲”。而且,从当时乐人的社会地位和人生经历来看,他们学习新歌需要有机遇。比如泰娘,据刘禹锡《泰娘歌序》中说,她本是苏州人,韦夏卿任苏州刺史时“命乐工诲之琵琶,使之歌且舞。无几何,尽得其术。居一二岁,携之以归京师。京师多新声善工,于是又捐去故技,以新声度曲”(21)。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乐人都如此幸运,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忙于营生,难有再次学习新曲的机会,一生中就只能演唱某几个曲调了。 三是与音乐接受有关。按照音乐心理学的研究,人们在欣赏音乐时常有“从众”心理,对日趋流行的乐曲往往更易接受。在唐代乐坛上,流传着一批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曲调如《杨柳枝》《水调》《凉州》《子夜》等,在社会上、下层文化空间均大受欢迎,因而乐人在演唱这些曲调时,既易传播,又易接受,对他们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都有益处。 或许有人要问:“如果乐人只唱数个曲调,岂不单调乏味?”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一方面,即使有数个乐人善唱同一曲调,但他们在继承和学习的过程中必然会根据自身的歌唱条件对原先的声腔有所扬弃,在表演过程中还会进行“二度创作”,所以效果可能会完全不同。据《碧鸡漫志》所引《乐府杂录》的佚文云:“灵武刺史李灵曜置酒,坐客姓骆,唱《何满子》,皆称妙绝。白秀才者曰:‘家有声妓,歌此曲音调不同。’召至令歌,发声清越,殆非常音。骆遽问曰:‘莫是宫中胡二子否?’妓熟视曰:‘君岂梨园骆供奉邪?’相对泣下,皆明皇时人也。”(22)骆供奉与胡二子同唱《何满子》,但“音调不同”,说明他们对原来的“基本调”进行过富有个性的加工,已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因而对听众而言,并不单调乏味,就像今天人们在听各个流派表演的传统剧目时仍会觉得津津有味。另一方面,歌唱者虽然采用相同的曲调,但歌辞却在不断翻新,如白居易《杨柳枝词》中说“听取新翻《杨柳枝》”(23),刘禹锡《纥那曲词》中说“调同词不同”(24),当配入新的歌辞演唱时,必然要对原来的曲调进行调整方能做到辞乐相谐,这类似于当今的“民歌新唱”,因而给听众的感觉始终是新鲜的。 三、某乐人“善唱某曲”对词体生成的促进作用 词的起源是学术界热烈讨论的问题,相关的说法很多,有学者称之为“千年学案”(25)。事实上,任何事件的发生归根结底都与人的活动有关。在词体的发生过程中,乐人的歌唱实践必然会对其产生一定的影响。胡适在《词的起源》中说:“我疑心,依曲拍作长短句的歌词,这个风气是起于民间,起于乐工歌妓。”(26)王书奴《中国娼妓史》谓:“到了晚唐,词已入于成熟时期,但无形中妓女促成之功,实不可没。”(27)杨海明《妙在得于妇人——论歌妓对唐宋词的作用》一文中说:“在词的初起阶段,歌妓曾对词的生成,起过直接参与的作用。”(28)李剑亮《论唐宋词的实用功能及其与歌妓的关系》一文中认为,词的兴起与发展与歌妓的活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29)在笔者看来,正是由于唐代乐人“善唱某曲”这一行为,才促进了词体文学的生成与繁荣。 1.形成了词牌及词牌的生存方式 我们知道,词在音乐方面的特点是具有词牌。那么,词牌是如何形成的?它与唐代乐人“善唱某曲”有关。由于乐人始终演唱的是某几首曲调,逐渐使这些曲调稳定下来,遂“造成了曲调的规范性”(30),长此以往,就成为早期的词牌,如《杨柳枝》《水调》《鹧鸪曲》的形成便是如此。乔建中先生在研究曲牌时指出,唐代“已有了固定的曲名和相对稳定的‘腔格’和‘词格’。唯其如此,才酿成了延续几百年的‘倚声填词’之风”(31)。而那些“相对稳定的‘腔格’”正是因乐人的“善唱某曲”而形成的。 这些词牌(主要指词乐)在当时怎样生存并流传呢?这同样要得力于乐人的“善唱某曲”。从书面记载中所见的唐宋乐谱并不太多这一事实可以推知,当时将音乐写谱记录并进行传承的风气还未流行,因此,大量的词牌音乐只能是靠乐人的“口耳相传”,尤其是在乐籍制度的背景下,乐户们世世代代传承并创造着曲牌音乐(32),而他们中的老一辈自然会把“善唱”的“词牌”传给下一代。我们发现,宋金时期依然有许多歌妓擅长某曲或某几曲,并将文人之词配入其中进行演唱。如蔡松年的《雨中花》序云:“数日来,蜡梅风味颇已动,感念节物,无以为怀,于是招二三会心者,载酒小集于禅坊。而乐府有清音人雅善歌《雨中花》,坐客请赋此曲,以侑一觞。”(33)因有乐人善歌《雨中花》,遂使文人填词并付诸演唱,其情形与唐代并无二致。 2.一调多辞与文人“依调”填诗、填词 乐工歌妓善唱一曲,故常常将文人诗歌配入该调演唱,导致的结果便是一调多辞。任半塘先生指出,“用一调以唱多辞,乃唐人歌诗常态”(34)。王昆吾先生亦说:“专业演唱并造成了大量的一调多辞。例如《杨柳枝》,即使排除《柳枝》《添声杨柳枝》《折杨柳》等等调名下的传辞不计,它拥有的存至今天的歌辞总数,亦达到了91首。”(35)宋词更是一调多辞,一个词牌名下往往会有许多首作品,这显然是承袭唐代辞乐配合的传统而来。 从创作的实际发生过程来看,文人走上“依调”填写的道路,乃是环境需要的召唤所致,应时而为之。当文人参加饮宴时,用来助兴的歌妓只善唱数个曲调,他们要想听到“新声”,便只能是为这些曲调改换新辞。如薛能《柳枝词》五首序云:“乾符五年,许州刺史薛能于郡阁与幕中谈宾酣饮醅酎,因令部妓少女作《杨柳枝》健舞,复歌其词,无可听者,自以五绝为《杨柳》新声。”(36)在这样的背景下,唐代“依调填诗”的创作方式被普遍运用,如《新唐书》卷一六八载,刘禹锡被贬朗州时,该地“每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声伧宁……乃倚其声,作《竹枝辞》十余篇。于是武陵夷俚悉歌之”(37)。任半塘先生说:“唐代声诗固有先诗而后声,以声就辞者,多数则先声而后诗,以辞就声,即所谓‘依调填词’。”(38) 唐代文人经过“依调填诗”阶段的实践,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由于这时有一些文人也善歌,如薛嵩曾“以歌送酒”(39),刘瞻会唱《竹枝》韵(40),刘禹锡“能唱《竹枝》,听者愁绝”(41),或如元稹、白居易、温庭筠等人那样知音懂律,因而他们能做到“依曲拍为句”或“逐弦吹之音”,实现了从“依调填诗”向“依调填词”的转变,不仅填写了最早的一批文人词,而且为后来的宋词创作提供了技术示范。 3.杂言的出现 词的形体特征为杂言长短句,而杂言长短句的出现也与乐人“善唱某曲”有关。在一调下演唱的多首歌辞,在形式上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具有一定的自由性。如《云溪友议》载刘采春所唱的《望夫歌》一百二十首,“其词五、六、七言,皆可和者”(42),可见曲调对所配歌辞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这种情况在唐代十分普遍。依任半塘《唐声诗》下编格调部分“同调异格一览表”,具有不同体式的曲调很多,如《破阵乐》有五言四句、六言八句、七言四句三体;《胡渭州》有五言四句、七言四句两体;《皇帝感》有五言八句、七言四句两体等。这意味着什么?它表明:乐人所唱之曲调可以配入各种不同形式的歌词——长短句就是从这里而来的。 一方面,随着歌唱技术的成熟,乐人为了求新以吸引观众,在专精一曲的基础上充分发挥音乐技巧,采用添声、减字、摊破、复叠等手法,在客观上改变了原来的声诗曲调;文人则将其填实,致使新辞也改变了原先的齐言形式,开始向杂言长短句迈进。王灼在《碧鸡漫志》卷五中所言《杨柳枝》曲的情况即是如此。他说:“今黄钟商有《杨柳枝》曲,仍是七字四句诗,与刘白及五代诸子所制并同。但每句下各增三字一句,此乃唐时和声。”(43)“和声”的加入显然是乐人所为,本是为了使音乐更为丰富悦耳,却导引了杂言长短句的出现,后来五代时期顾夐的《添声杨柳枝·秋夜香闺思寂寥》便在每个七言句下各增一句三言。 另一方面,有些乐人散入民间,他们在民间演唱该曲调时,可能会配入长短句形式,因为民间的歌唱形式灵活,多是口语化的,可随意增加衬字,故极易出现杂言句式。宋代陈旸在《乐书》卷一五七中说,“唐末,俗乐盛传民间,然篇无定句,句无定字”(44),揭示的便是这一事实。任半塘《唐声诗》上编中亦说:“民间歌曲运用衬字,使口气明畅,益惯常事。”(45)从敦煌发现的歌辞中就有许多这样的例证,如《杨柳枝》《浪淘沙》等都是长短句。人们常谓“词起于民间”,或许从这里可以得到贴切的解释,即如秦序在《中华艺术通史·隋唐卷》中所言:“民间歌手历来善于在一定的歌曲形式中去创新发展,无论是歌辞还是曲调旋律,都可以巧妙变化并保持辞、乐的协调,因而杂言曲子辞最早产生和流行于民间。”(46)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致使在当时产生了大量的同调诗词:同一曲调,在以文人士大夫为代表的社会上层文化圈中往往传唱的是齐言声诗,而在民间则传唱的是杂言的词体。 4.促进了词体文学的大众化传播 唐前诗歌,除民间歌谣以外,基本上都是在文人贵族的文化圈中流传。到了唐代,诗歌有了较大程度的普及。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很多,但乐人善唱某曲也是应该考虑的一个因素。试想,乐人善唱某曲,便可以在一调下产生多首歌辞,并快速使词乐结合,变成数以千计的歌曲进入表演场所。这一方式对乐人和文人来说都是极为实惠简省的。乐人在职业技能方面的要求不算太复杂,文人也只需要按照该曲调的格式填写新辞,故生产效率颇高,歌曲资源十分丰富,从而保证了社会各个阶层和各种场合的消费需求。因此可以说,词的出现是古代诗歌由小众传播走向大众化的产物。 总之,当我们讨论词的生成问题时,不应该忽视乐人所起的作用。正是乐人“善唱某曲”才促进了词体的发生,并为词的发展建构了诸多传统,从而对词体文学的繁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①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4年,第760页。 ②李德裕:《次柳氏旧闻》,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3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08—409页。 ③冀勤点校:《元稹集》,中华书局,1982年,第123页。 ④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中华书局,1979年,第1501页。 ⑤⑧(17)(18)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第3905、6097、1642、2964页。 ⑥范摅:《云溪友议》,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3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09页。 ⑦段成式撰、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中华书局,1981年,第40页。 ⑨任半塘:《唐声诗》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75页。 ⑩任半塘:《唐声诗》下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4、66、77页。 (11)孙菊园:《唐代文人和妓女的交往及其与诗歌的关系》,《文学遗产》1989年第3期。 (12)范摅:《云溪友议》,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3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07、609页。 (13)钱易撰、黄寿成点校:《南部新书》,中华书局,2002年,第121—122页。 (14)李濬:《松窗杂录》,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3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58页。 (15)计有功撰、王仲镛校:《唐诗纪事校笺》,巴蜀书社,1989年,第1568页。 (16)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第239—246页。 (19)董诰等:《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第4470页。 (20)任半塘:《唐声诗》下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509页。 (21)(24)卞孝萱校订:《刘禹锡集》,中华书局,1990年,第350、364页。 (22)王灼:《碧鸡漫志》,见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108页。 (23)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中华书局,1979年,第714页。 (25)李昌集:《词之起源:一个千年学案的当代反思》,《文学评论》2006年第3期。 (26)胡适:《词的起源》,见《胡适全集》第三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35—736页。 (27)王书奴:《中国娼妓史》,团结出版社,2004年,第110页。 (28)杨海明:《妙在得于妇人——论歌妓对唐宋词的作用》,《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年第2期。 (29)李剑亮:《论唐宋词的实用功能及其与歌妓的关系》,《杭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30)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第81页。 (31)乔建中:《曲牌论》,《中国音乐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327页。 (32)闫永丽:《略论乐籍制度与中国传统曲牌的创承》,《音乐创作》2009年第5期。 (33)唐圭璋:《全金元词》,中华书局,1979年,第21页。 (34)任半塘:《唐声诗》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77页。 (35)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第80页。 (36)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第6519页。 (39)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5129页。 (38)任半塘:《唐声诗》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23—124页。 (39)杨巨源:《红线传》,见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中华书局,1959年,第262页。 (40)尉迟偓:《中朝故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3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13页。 (41)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中华书局,1979年,第604页。 (42)范摅:《云溪友议》,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3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07页。 (43)王灼:《碧鸡漫志》,见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117页。 (44)陈旸:《乐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1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22页。 (45)任半塘:《唐声诗》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47页。 (46)秦序:《中华艺术通史》(隋唐卷)上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