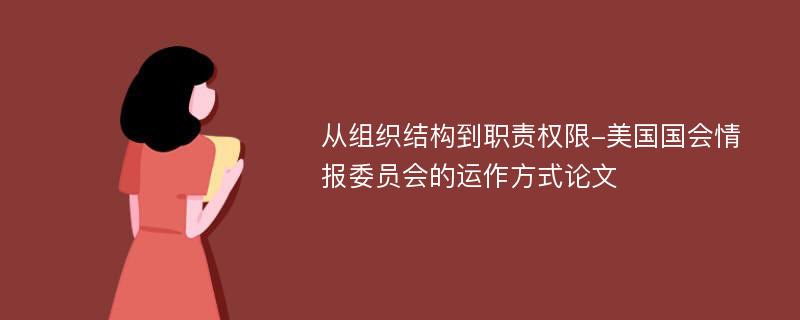
【历史研究】
从组织结构到职责权限
——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的运作方式
刘 磊1, 邵 煜1,2
(1.西北大学 历史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9; 2.西北大学 期刊管理中心,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要: 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会情报委员会的设立,是美国国会现代委员会体制走向完善的重要一环。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的建立,在美国国会史上第一次拥有一个负责监督政府整个情报领域的专门委员会,也是美国迄今为止唯一的国会常设特别委员会。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享有广泛的情报监督和审查权,主要包括:立法倡议权、预算监督审查权、人事任命“咨询权”及相关的调查权和传讯权。国会情报委员会因此成为美国国会与总统争夺情报决策权的得力助手和工具,构成了越战和水门事件之后美国国会权力复兴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 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众议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情报监督
美国国会在1976年5月和1977年7月分别创建的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以下简称SSCI)和众议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House Permanent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以下简称HPSCI),合称为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Congressional Intelligence Committee)。该委员会是一种兼具常设委员会和特别委员会双重特征的新型委员会,也因此成为美国国会委员会中唯一拥有立法倡议权的特别委员会。事实上,从二战结束初期中央情报局的创建直到1970年代中期,不断有议员在国会提出过上百个议案,要求参众两院各自建立专门负责情报监督的常设委员会,或者建议组建一个参众两院情报联合委员会[1](P2-19)。但美国国会最终选择建立一种新型的常设特别委员会。那么,这一新型委员会的组织结构都有哪些特点?又具有怎样的职责权限和运作方式?关于这些问题,在国内外学术界至今尚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和研究。
美国国会委员会是“国会权力的重镇”[2](P55),被美国政治学者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称为“行动中的国会”[3](P4),在美国内政外交决策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早在2002年,著名国会研究学者孙哲、王义桅、赵可金在为《美国国会研究I》合写的“前言”中,郑重地将“委员会研究”列为“可兹国内学者参考的美国国会研究的方法与方向”[4](P15)之一。然而十多年过去了,国内关于这一重要课题的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尤其是关于委员会的个案研究亟待弥补[注]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美国国会委员会的专门研究十分欠缺,相关研究专著尚未出现,而论文方面,结合笔者广泛搜集的、包括台湾在内的其他公开出版物,截至目前,专门研究美国国会委员会的文章仅有10篇左右,其中对委员会体制及运作进行专门个案研究的更是凤毛麟角,而关于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的研究尚未出现。对美国国会委员会进行整体研究的有:蒋劲松:《美国国会里的委员会制度透视》,《法学杂志》1992年第3期;秦亚青:《美国国会委员会的构成与权力──新制度主义和信息学派评介》,《外交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尹德蓉:《论美国国会委员会制度对国会困境的补强作用》,《江汉论坛》 1999年第9期;赵可金:《美国国会委员会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国际观察》2003年第5期。而对委员会体制及其运作进行的个案研究,也集中在极少数个别委员会,相关研究有:王玄:《后PNTR时代中美经贸关系政治化的机制化——以美国国会内针对中国的两个专门委员会为研究对象》,《理论界》2011年第6期;孙哲:《美国国会中国问题委员会评析——兼论我国的外交对策》,《国际观察》2003年第1期;孙哲,邵育群:《美国国会关于中国事务的两个委员会评析》,孙哲主编: 《美国国会研究II》,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林正义:《1980年代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之组织及运作》,郑哲民主编:《美国国会之制度与运作》,“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1992年版。 。国外学术界对美国国会委员会的研究相对比较深入,在美国国会政治制度的研究领域,有不少研究著述在宏观上探讨了美国国会整个委员会体制的发展,或者对参众两院某个特定委员会进行案例研究[注] 代表性的专著有:William J. Keefe and Morris S. Ogul. The American legislative process: Congress and the States,Prentice Hall, Inc., 1993. Richard J. Fenno, Jr.. The Power of the Purse,Little, Brown, 1966. Frank John Smist. Congress oversees the United State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1947-1994,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94. 。其中,美国情报监督研究专家弗兰克·约翰·斯密斯特(Frank John Smist)所著的《国会对美国情报机构的监督:1947—1994》一书,重点考察了1947年以后在国会情报监督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一系列委员会,包括参众两院的丘奇委员会(the Church Senate Committee)、派克委员会(the Pike House Committee)以及国会情报委员会(SSCI and HPSCI);作者利用他与国会议员、情报机构官员等进行的500多次一手访谈资料及部分委员会档案,从制度性监督和调查性监督的视角出发,对这些委员会的成员组成、委员会内部关系、委员会与其上级议院的关系、委员会与行政部门的关系进行较为细致地梳理[5]。但遗憾的是,本书对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的特殊组织结构和职责权限缺乏深入和系统的理论分析。
Enterprise Container Cloud PaaS Solution Based on Kuerbnetes and Docker……………WANG Junxiang, GUO Lei(3·51)
本文选择20世纪70年代建立的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进行案例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广泛搜集到的相关档案文献,包括组建委员会的一系列提案和决议案、国会相关委员会的听证会记录和辩论记录、情报委员会通过的年度情报授权法和相关情报立法,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和年度报告以及美国新闻媒体的报道,等等,细致分析国会情报委员会的特殊组织结构,深入探讨国会情报委员会在美国情报决策领域中的职责权限及运作方式,透视其对美国国会与总统权力争夺的影响,以期能对美国国会委员会的研究增益补缺。
一、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的组织结构
(一)美国国会现代情报监督体制的确立: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的创建
现代委员会制度是美国国会运作的核心。 20世纪40年代和70年代, 美国国会先后进行了两次重大改革, 以专门法律推进国会委员会及其小组委员会的制度和功能建设。 首先, 1946年国会重组, 对许多功能相似和不重要的委员会进行合并或裁撤,使参议院中的委员会数目由33个减至15个, 众议院的委员会由48个缩减至19个。此后, 国会参众两院的委员会数目基本维持在这一水平上[6](P182)。 其次, 此次改革还明确赋予国会委员会以监督权, “国会正式承担起监督政府的宪政职责, 国会的宪政权力从此不再仅仅是立法, 而是立法与监督并重”[6](P22)。 而70年代的改革, 则进一步规定“小组委员会享有监督权”[6](P198), 将国会监督权具体落实到每一个小组委员会。 国会委员会及其下设的小组委员会作为“国会权力的重镇”, 继续扮演着“行动中的国会”的关键角色。 国会现代委员会制度的演进表明, 在政府的每一政策领域有针对性地设立相应的国会委员会, 是现代国会委员会体制完善与成熟的重要标志。 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的创立, 是美国国会现代委员会体制走向完善的重要一环。
由于飞机所包含的参数量是巨大的,涉及飞机的各个方面,管理和调用的难度很大。使用数据库技术可以高效地管理飞机数据,其与互联网的结合使信息的传播速度和范围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也有利于数据库的进一步完善。将飞机数据库的搭建与“互联网+”相结合,飞机设计者能够便捷地使用飞机数据库中现有的飞机数据作为依据,为今后的飞机设计进行指导,对于飞机设计者而言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的特殊组织结构
尽管经历了40多年的发展沿革,时至今日,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在组织结构与功能等方面均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目前,第116届国会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拥有15位成员,其中多数党共和党拥有8个席位,少数党民主党占据7个席位,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分别是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理查德·波尔(Richard Burr)和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马克·沃纳(Mark Warner)。此外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少数党领袖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军事委员会主席詹姆斯·英霍夫(James Inhofe)、军事委员会高级成员杰克·里德(Jack Reed)也成为委员会的当然成员[15]。第116届国会的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总计拥有22位成员,其中多数党民主党占13个席位,少数党共和党拥有9个席位,现任委员会主席是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人亚当·希夫(Adam Schiff)[16]。
一方面,由于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SSCI)和众议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HPSCI)都是永久性特别委员会(Permanent Select Committee),因而国会情报委员会实际上跟常设委员会一样都是永久性的(Permanent),具有常设委员会的一般特征:如,常设委员会是美国国会立法过程的核心,拥有广泛的立法权;两个情报委员会都具备只有常设委员会才拥有的立法倡议权,而这是普通的特别委员会所不具备的。这是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在功能和权力方面区别于一般特别委员会的最突出特点。
立法权是美国国会最基本的权力。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自建立伊始就注重以倡议立法的方式,就国家情报体制和各情报机构法定职责权限、情报活动的范围与责任以及国家情报法律监督制度等方面积极推动国会立法。美国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建立以后,一直致力于为整个美国情报界制定一部综合性的情报立法章程,以明确美国各情报机构的组织程序、职责权限及其情报活动的范围,等等。然而,由于总统及各情报机构首脑的抵制以及国会内部委员会之间的矛盾等原因,国会情报委员会最终放弃为整个情报界制定一部综合性情报立法章程的努力,转而试图从具体的情报活动立法规范方面取得突破,并取得了一系列单独立法的成就。主要包括:《1978年对外情报监视法》《1980年情报监督法》、1982年制定通过的《情报人员人身保护法》、1984年的《信息自由法》以及《2004年情报改革与预防恐怖主义法》,等等。而在整个立法领域,情报委员会最常规性的立法活动就是帮助国会起草年度情报授权法案,这与委员会的情报预算审查权密不可分。
首先,美国国会常设委员会的成员主要由国会两党党团小组会议选举产生;而国会情报委员会的特别委员会性质赋予了政党领袖在直接挑选委员会成员方面的特权,委员会所有成员均由政党领袖挑选,包括主席和副主席经由委员会多数党和少数党领袖推选后,最终由两院议长任命。此外,政党领袖还有权设定委员会多数党与少数党的席位比率,从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两党议员组成情况看,HPSCI两党成员的比率通常根据众议院两党议员比例分配确定;相比之下,参议院更加注重寻求情报监督中的两党合作,努力体现情报监督委员会的超党派立场,避免委员会以党派划线甚至分裂,因此SSCI两党成员的分配,始终坚持多数党比少数党多一个议员席位[11]。可见,正是由于SSCI的特别委员会的性质赋予政党领袖在挑选委员会成员以及设置委员会两党席位分配比例时的灵活性,使其更符合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情报领域的监督需求,体现了一种情报监督“例外论”的观念,即认为情报工作因其众所周知的秘密性和敏感性,使议会无法像监督其他行政机构那样对情报机构及其活动进行监督,因此,美国国会在情报监督方面应更慎重,“情报对于美国政府的正常规则和问责准则是一个例外;秘密行动太脆弱,太依赖于保密,无法进行正常的严格监督”[12](P43)。
而根据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SSCI and HPSCI)的各自规则,其小组委员会的设置需要委员会成员通过多数投票来确定,每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由本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分别挑选出来[13]。与此不同,常设委员会下设小组委员会的成员,是由所在委员会内两党党团会议根据各自委员本人的申请而投票决定;小组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分别由所在委员会多数党党团和少数党党团选举产生。
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创立伊始便努力为美国各情报机构确立情报章程,为情报活动的限制与许可提供法律依据;委员会也会定期考虑单独的立法;委员会还负责起草年度情报授权法案;有时SSCI还会在参议院请求下,对需要由参议院批准的美国与外国订立的条约中的情报部分进行审查。
除此之外,考虑到国会军事、外交(众议院称为国际关系委员会,参议院称为对外关系委员会)、司法和拨款委员会同样都拥有对部分美国情报活动的管辖权,因此,组建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的S.Res.400和H.Res.658都体现了这四大常设委员会的利益。如,H.Res.658特别规定,HPSCI的成员中,军事委员会、国际关系委员会、司法委员会和拨款委员会必须至少有1名成员参加[14]。而S.Res.400也规定,SSCI的15名成员中,必须有8名是分别来自拨款、军事、对外关系和司法委员会的各2名成员[11]。这种安排有助于国会情报委员会与拨款、军事、外交和司法委员会之间,协调有关美国情报立法和监督方面的活动。
按照美国现行的委员会体制,国会里的委员会主要分为四种类型:常设委员会(Standing Committees)、特别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s)、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ttees)和会议委员会(Conference Committees)。其中常设委员会是美国国会委员会体制的核心和主体,在委员会中占绝对多数,一般是按照功能和领域进行划分的,在每个对应的行政政策领域都会设立相应的常设委员会;特别委员会的设立通常是为了补充常设委员会的不足,特别委员会基本都是为了对特定急需处理的事项进行研究和提出建议而设立,在任务完成后就自动取消,具有临时性。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是常设委员会和特别委员会的“孪生儿”,同时兼具常设委员会和特别委员会这两种委员会的某些属性,因而具有了相异于国会常设委员会和特别委员会的特殊组织结构和功能。
总之,随着《1947年国家安全法》的颁布和中央情报局的建立,美国逐渐建立起庞大而复杂的现代情报体系,要求美国国会加强情报监督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美国国会在多次拒绝成立一个负责情报监督的常设委员会或联合委员会的动议后,最终选择组建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和众议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这种兼具常设委员会和特别委员会属性的新型委员会。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由此成为美国国会史上迄今为止唯一的国会常设特别委员会,也是美国情报发展史上唯一专门针对政府情报领域设立的、对整个美国情报界负有直接立法和监督责任的委员会。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的创建标志着美国现代情报监督体制的建立。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自建立伊始,便根据参议院第400号决议案(S.Res.400)和众议院第658号决议案(H.Res.658)所授予的各项权力和功能运作,逐渐发展成为美国国会与总统争夺情报决策权的得力助手和工具。
二、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的职责权限
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SSCI)就总统提名的、需要参议院批准的情报官员提供意见和建议。根据美国宪法,参议院对总统任命的高级政府官员拥有“建议与同意”的人事批准权。参议院有权批准总统对美国各情报机构主要领导人的任命,如中央情报局局长、副局长、法律总顾问和总检察长等。SSCI经常召开听证会,对总统提名的人选进行审议,而情报委员会的态度往往能够影响到参议院的最后表决结果。如,在中央情报局第13任局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的任命过程中,SSCI发挥了重要作用。1987年,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总统提名盖茨接任病故的威廉·凯西(William Casey)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但由于SSCI怀疑盖茨与伊朗门事件有牵连,并以盖茨在“伊朗门事件中严重失职”为由提出质询,迫使他不得不要求白宫撤回对自己的提名。1991年5月,当布什(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总统再次提名盖茨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时,引起国会和公众的普遍关注。在经过国会长达半年之久的马拉松式的听证会后,参议院才于1991年11月5日以64票赞成、31票反对批准了对他的任命[23](P509)。盖茨由此成为美国情报史上唯一通过两次提名、任职审查听证时间最长以及反对票最多的中央情报局局长。
(一)情报领域的立法倡议权
其次,与常设委员会的成员一般没有任期限制不同,国会情报委员会成员则设置了任期限制,其中SSCI成员任职期限设为8年,HPSCI的成员任职期限为6年,而且由于SSCI和HPSCI的特别委员会性质,国会情报委员会成员的任职不会影响其在国会其他常设委员会的任职,以提高SSCI和HPSCI对国会议员的吸引力。
但另一方面,从委员会组织结构来看,由于SSCI和HPSCI又都是特别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因而其委员会成员的组成和任命方式不同于普通的常设委员会。
20世纪70年代中期, 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的建立, 表明国会终于决心针对美国情报领域设置专门的委员会进行监督, 标志着美国国会现代情报监督体制的正式确立。 冷战初期, 由于受到“冷战一致”“国家安全第一”以及“情报例外论”[7](P189)的影响, 美国国会总体上非常信任总统及其领导的情报机构,国会情报监督是非正式的、 松散的, 被称之为“相互信任的时期(1947—1974)”[8](P103)。 但即便如此, 国会内部要求加强情报监督的呼声也一直不断。 事实上, 自《1947年国家安全法》建立起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 国会就开始通过各种方式试图建立国会对美国政府情报活动的密切监督。 1948年, 众议院就曾提出创建一个情报联合委员会的提案, 这是美国国会关于加强情报监督的最早提案。 此后, 在国会参众两院接连不断地提出了100多个要求加强国会情报监督的议案[9](P3)。 但这些议案当中没有任何一个被通过而成为法律。 如, 1955年1月, 民主党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Mike Mansfield)开始推动一项决议案(S.Con.Res.2), 希望效仿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the Joint Committee on Atomic Energy)[注] 原子能联合委员会被普遍认为是美国国会对国家安全敏感领域进行监督的典范,委员会在一个国家高度敏感的领域长期保持了非常好的有效监督记录。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内部希望仿照原子能联合委员会组建一个负责情报监督的联合委员会的呼声一直存在,如,1975年1月4日,福特(Gerald R.Ford)总统下令成立一个由副总统尼尔森·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领导的调查委员会,对《纽约时报》等媒体所指控的中央情报局的不法行为进行调查。1975年6月,洛克菲勒委员会发布了最终报告,报告中提出30条建议,其中第3条写道:“总统应该向国会建议组建一个情报联合委员会,承担目前由军事委员会所从事的监督职责。”参见Report to the President by the Commission on CIA Activities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June 6, 1975,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D. C.。 , 建立一个负责情报监督的参众两院联合委员会。 该决议案还被提交参议院审议和表决, 但未获通过[10](P3)。 直到1976年5月和1977年7月, 国会参众两院才先后通过参议院第400号决议案(以下简称S.Res.400)和众议院第658号决议案(以下简称H.Res.658), 分别创立了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SSCI)和众议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HPSCI), 合称为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 从此, 美国国会便拥有了对美国整个“情报界”(Intelligence Community, IC)负有直接立法和监督责任的专门委员会,这是美国国会情报监督发展史上的创举。 而且, 正如它们的英文名称所显示的, 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具有常设委员会和特别委员会的双重特征, 是一种新型的委员会, 是美国迄今为止唯一的国会常设特别委员会。
(二)情报预算审查权
美国宪法明确赋予国会“掌握钱袋的权力”(Power of the Purse),通过拨款和预算审查来影响和监管行政部门,一直都是美国国会所掌握的最有效的监督工具。正如丘奇委员会在其最终报告中所强调的:“国会掌握钱袋子的权力能成为国会监督最有效的工具,只要它有勇气并且愿意使用这个权力。”[18](P448)美国国会自创立之初就确立了“先授权后拨款”两步走的立法程序,并在国会内部相应地组建一系列的授权委员会,形成了与国会预算拨款制度相互平行的国会授权制度[19]。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属于国会的授权委员会,负责对行政部门制定与实施国家情报政策与情报活动的程序和预算举行听证会,进行调查、审核与评估。虽然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都被授予广泛的预算审查职责,但二者在具体的情报授权范围上并不完全一致:SSCI仅对国家对外情报活动(National Foreign Intelligence Program, NFIP)拥有授权,而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保留了对联合军事情报计划(Joint Military Intelligence Program, JMIP)和战术情报及其相关活动(Tactical Intelligence and Related Activities, TIARA)的授权。换句话说,SSCI只能对中央情报局、国防情报局、国家安全局等情报机构所从事的国家对外情报项目及其预算进行监督和审查。相比之下,HPSCI有权为“政府所有部门和机构的情报及其与情报相关的活动,包括国防部战术情报及其相关的活动”[20](P6)进行预算审查和授权。
调研是有程序的,一般都是先参观后座谈再吃饭。为了迎接这次调研,大春提前一天命人制作好形象展板,连夜整理汇报材料,并将公司上下打扫得一尘不染。调研当天,他带领全体员工提前站在公司门口,列队迎接领导莅临。调研团一行下车后,在大春的解说下,边考察现场,边听取公司发展汇报。然后按照议程召开座谈会,畅谈成果、分享经验、总结不足。各位“专家”纷纷出谋划策,献策建言,为公司发展指点迷津。基层相关系统的负责人陪同参会,整个座谈会气氛热烈又活泼。
S.Res.400和H.Res.658都明确规定,除非经过参议院或众议院“在同一财政年度或前一财政年度为本财政年度执行这些活动而制定法案或联合决议案予以授权”[17],否则不得为中央情报局、国防情报局、国家安全局等情报机构及其情报活动提供任何资金。此后,美国情报活动的授权一直是通过国会情报委员会审查和批准独立的情报授权法案的方式进行,委员会负责起草年度情报授权法案,并最终为情报活动确定资金授权的水平,即为情报机构资金使用设置上限。1978年9月,由卡特(James Earl Carter)总统签署的《1979财年情报授权法》(P.L. 95-370)是美国国会发展史上首个情报授权法。此后,除了在2006—2009财年,因总统与国会以及国会内部各委员会的矛盾,导致情报授权法案未能被批准通过成为法律,国会每年都照例通过这样一项情报授权法[20](P12-13)。
此外,美国国会还经常利用批准年度情报授权法案之机,通过要求相关情报机构提交报告的方式来强化情报界对美国国会的责任。如,2018年7月12日,美国众议院以363∶54的投票通过了HPSCI主席德温·努内斯(Devin Nunes)提出的H.R. 6237,即后来的《2018和2019财年情报授权法》(the Matthew Young Pollard Intelligenc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s 2018 and 2019)。该法案是由“2018财年情报授权法”和“2019财年情报授权法”两个独立部分组成,在其各自的第五章“报告与其他事务”中,法案详细列举了要求提交的报告,主要包括:“对俄罗斯在国外选举运动和全民公决中的重大影响的评估”“对联邦竞选活动的国外反间谍和网络安全威胁”“联邦调查局反情报活动简报”,等等,并对报告的基本内容和提交时间都做了具体要求[21]。委员会主席德温·努内斯在新闻发布会上针对本法案(H.R. 6237)评论道:“情报授权法是国会用来确保情报界获得其所需要的、保护美国免受外来威胁的资金和资源的最好工具。本法案将会使情报界受到来自国会的强有力监督,我希望这个法案能够在参议院获得通过。”[22]
秋明Сг—6井位于俄罗斯西西伯利亚北部[2],井深7502m,按研究程度地质剖面被分为三段:0~3650m有设计所需要的必要信息;3650~5000m有需再钻进过程中明确的地质条件资料;5000~8000m没有所需信息。
(三)情报机构人事任命的“咨询权”
创建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的S.Res.400和H.Res.658,开篇就明确规定了委员会的目的和任务:对美国政府的情报活动和计划进行监督和持续的研究;向各自上级议院提交适当的立法建议,并就这类情报活动与计划向参议院提交报告;对美国的情报活动提供警觉性立法监督(vigilant legislative oversight),以确保这些活动遵守美国的宪法和法律[17]。为了保障两个情报委员会能够顺利完成使命,S.Res.400和H.Res.658还赋予委员会以相应的权力。从权力的视角看,国会情报委员会在情报决策领域中的作用源于国会的两大功能——立法功能和监督功能。根据S.Res.400和H.Res.658,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的主要功能和权力包括:享有情报领域的立法倡议权、情报预算审查权、情报机构人事任命的“咨询权”、对美国整个情报界及其情报活动的例行监督权、调查权和传讯权。
(四)对美国情报界及其情报活动的例行监督权、调查权和传讯权
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的创建,使国会首次拥有了对美国整个情报界进行监督的专门委员会。S.Res.400第5条明确规定:委员会有权“(1)对其管辖权范围内的任何事项进行调查……(4)举行听证会……(6)通过传讯或其他方式,传唤证人出庭作证以及获取其他通讯、书籍、文件和档案资料等”[11]。据此,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拥有明确的监督权、调查权和传讯权,可以对国家情报项目或活动进行监督,范围和方式非常广泛,从例行监督(如要求情报机构负责人提交年度报告)到举行调查听证会,或者直接要求情报官员前来接受正式质询,等等。同时为了保证这些权力有效的行使,SSCI 和 HPSCI的议事规则对其传讯权做出具体规定:“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及其指定的委员会成员,都有权发出传票,要求相关证人前来作证,或提供备忘录、档案、记录及其他材料。”[24]最新修订的《1947年国家安全法》第五章“情报活动责任”的第502条明确规定:国家情报主任以及情报活动涉及的美国政府各部门、机构和其他实体的负责人有义务确保国会情报委员会完全、实时地知晓美国政府任何部门、机构或实体所从事的情报活动,包括重要的预期情报活动或情报工作的重大失误;向国会情报委员会提供其履行监督职责所必需的任何与情报活动相关的信息或材料[25]。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3.0软件处理数据。计数资料以n(%)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样本率与整体率的比较采用二项分布检验。对于不同程度先天性上睑下垂合并先天性心脏病发病率的比较,采用秩和检验。检验水准(α)为0.05。
在具体的监督实践中,每当美国发生重大的情报失误或丑闻时,国会情报委员会便会积极敦促国会对情报机构及其活动进行调查,通过举行听证会等方式,对情报失误或丑闻进行深入调查,并以提出研究报告或立法议案等方式,对现有的情报体制和各种弊病进行改革,以期能提高美国政府的情报效能。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HPSCI对美国情报界进行调查研究后提出的报告“21世纪的美国情报界”[26],“9·11”事件后任命的“9·11”恐怖袭击联合调查委员会及其最终调查报告[27],等等。
三、余 论
在“机构分立、权力共享”的三权分立与制约平衡的政治体制下,美国总统和国会的权力长期处于一种“周期性”的“动态平衡”关系之中。随着冷战开始后美国总统权力的膨胀,直到越战期间美国总统权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甚至被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评论家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称之为“帝王般的总统”权力。20世纪70年代之后,在越战失败和水门事件的影响下,“帝王般的总统”权力由盛转衰,国会权力开始一个新的复兴期。正如国内研究美国政治与美国国会的著名学者孙哲所言:“国会与总统之间有一种周期性的关系,作风强悍的总统们都会碰到国会议员的抨击和反弹。也就是说,总统占了上风之后,国会便会重新复兴。”[4](P15)
(2)企业自我监测与自证守法。《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三条提出:“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监测规范,对所排放的水污染物自行监测,并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同时,提出了相关设备联网与(监管机构)信息共享要求,并要求企业对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排污许可证信息包括:排放水污染物的种类、浓度、总量和排放去向等。随着信息的公开透明,将有力地促进企业守法、自律、诚信。
故乡,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自《诗经》里征人思妇的反复歌咏始,远离家乡,对亲朋思念的乡愁一直是游子吟唱不完的话题。游子漂泊异地,漫漫求仕不进,在孤独的旅途中,倍感寂寞,倍含艰辛,无处言说,行诸于笔下,常常以饱蘸深情的笔墨倾述对家乡亲人的无尽的思念之情。马戴的羁旅行役诗亦是如此,在长期羁旅行役的途中,久因思念而夜不成眠,诗人无时无刻不在表达其内心对亲人深切的挂念。如其在《夕次淮口》云:
20世纪70年代,美国总统与国会这种权力制衡格局的转变,集中体现在双方关于美国情报决策权的争夺上。实际上,自美国独立战争至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情报决策主导权总体上是由以总统为首的行政部门掌控着。因此,当国会从70年代开始试图扩张其对情报决策权的影响时,议员们不得不选择以调查监督的方式渗透进来,以打破总统对美国情报决策权的垄断。1976年和1977年美国国会先后创建SSCI和HPSCI,使国会首次拥有了负责监督美国整个“情报界”的专门委员会,也是美国迄今为止唯一的国会常设特别委员会。SSCI和HPSCI的建立和发展,表明国会对长期以来由总统行政部门主导美国情报领域的不满,并开始积极利用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所享有的广泛的情报监督和审查权,与总统展开情报决策权的争夺,由此构成了后水门时代国会权力复兴的重要途径,并对未来美国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的权力发展起到“再平衡”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 KAISER F M. Legislative History of the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R]. Washington, D. 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1978.
[2] BAILEY S K. The New Congress[M]. NY: St. Martin’s Press, 1966.
[3] 伍德罗·威尔逊. 国会政体:美国政治研究[M].熊希龄,吕德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6.
[4] 孙哲. 美国国会研究Ⅰ[C].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5] SMIST F J. Congress oversees the United State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1947-1994[M]. 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94.
[6] 孙哲. 左右未来:美国国会的制度创新和决策行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7] 张晓军. 美国军事情报理论研究[M].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 2011.
[8] JOHNSON L K. Accountability and America’s Secret Foreign Policy: Keeping a Legislative Eye on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J].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2005, (1):99-120.
[9] CONGRESS U S.Senate. Committee on Government Operations. Senate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Report to Accompany S. Res.400[R]. Washington: U. S. Govt. Print. Off., 1976.(94th Congress, 2d session. Senate. Report no. 94-675).
[10] RAIFORD W N. To Create a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A Legislative History of Senate Resolution 400 [EB/OL]. [2018-05-10].https:∥www.intelligence.senate.gov/sites/default/files/762155.pdf.
[11] RES S. 400[Z]. 94th Cong., 2d Sess. 1976.
[12]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Intelligence Accountability[M]∥by Loch K. Johnson, in Russell A. Miller, US National Security, Intelligence and Democracy: from the Church Committee to the War on Terror, London: Routledge, 2008.
[13] Rules of Procedure for the Permanent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7. SUBCOMMITTEES, (a)”, 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115th Congress [EB/OL]. [2017-06-05].https:∥intelligence.house.gov/uploadedfiles/hpsci-rules-of-procedure-115th-congress.pdf; Rules of Procedure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Rule 3. Subcommittees [EB/OL]. [2017-06-05].https:∥www.intelligence.senate.gov/sites/default/files/about/SSCI%20Committee%20Rules-FINAL022317.pdf.
[14] RES H. 658[Z].. 95th Cong., 1st Sess. July 14, 1977.
[15] U. 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EB/OL]. [2019-04-03]. https:∥www.intelligence.senate.gov/about/committee-members-116th-congress-2019-2020.
[16] Permanent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EB/OL]. [2019-04-03].http:∥intelligence.house.gov/about.
[17] RES S. 400[Z]. 94th Cong., 2d Sess. 1976; H.Res. 658[Z]. 95th Cong., 1st Sess. July 14, 1977.
[18] Final Report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Foreign and Military Intelligence, Book Ⅰ[R].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19] 刘磊. 美国国会现代情报授权制度探析[J].人文杂志, 2013, (6):96-103.
[20] GRIMMETT R F, lANGE R S. Intelligence Authorization Legislation: Status and Challenges[R],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R40240, May 21, 2012.
[21] Matthew Young Pollard Intelligence Authorization Act 5 for Fiscal Years 2018 and 2019 [EB/OL]. [2018-07-20].https:∥intelligence.house.gov/intelligence-authorization-act/fy18-intelligence-authorization-act.htm.
[22] RELEASES P. House Passes FY18 and FY19 Intelligence Authorization Act, Washington, July 12, 2018. [EB/OL]. [2018-07-20].https:∥intelligence.house.gov/news/documentsingle.aspx?DocumentID=903.
[23] 祁长松. 美国情报首脑全传[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24] Rules of Procedure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Rule 7. Subpoenas. [EB/OL]. [2017-06-05].https:∥www.intelligence.senate.gov/sites/default/files/about/SSCI%20Committee%20Rules-FINAL022317.pdf.
[25] National Security Act of 1947, SEC.502, Public Law 235 of July 26, 1947; 61 STAT. 496 (as amended through October 7, 2010).
[26] House Permanent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IC21: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in the 21st Century[R], 104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1996.
[27] The 9/11 Commission Report[R].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4, [2013-02-15]. http:∥govinfo.library.unt.edu/911/report/index.htm.
From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to Responsibility and Authority :A Study on the Modus Operandi of U .S .Congressional Intelligence Committees
LIU Lei1, SHAO Yu2
(1.School of History,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2.Center of Periodical Manage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In the mide-1970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ngressional Intelligence Committees constitutes the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U.S. congress modern committee systems. The Congressional Intelligence Committees are so far the first congress permanent select committees, and make the congress for the first time in its history to have select committees responsible for overseeing the entir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The U.S. Congressional Intelligence Committees have a wide range of intelligence oversight and review powers, including the right of submitting proposals for legislation, budget supervision and review, the advice and consent for important personnel appointments by president, and related investigative and subpoena power. Therefore, the U.S. Congressional Intelligence Committees become right-hand tools for congress to strive for intelligence decision-making power with American presidents, which comprises an important approach for the resurgence of U.S. congressional power in the aftermath of Vietnam War and Watergate scandal.
Key word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House Permanent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intelligence oversight
收稿日期: 2018-12-27
基金项目: 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计划项目(15JK1716)
作者简介: 刘磊,男,山东临沂人,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从事美国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 K712.54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6152/j.cnki.xdxbsk.2019-05-017
[责任编辑 刘炜评]
标签: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论文; 众议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论文; 情报监督论文;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论文; 西北大学期刊管理中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