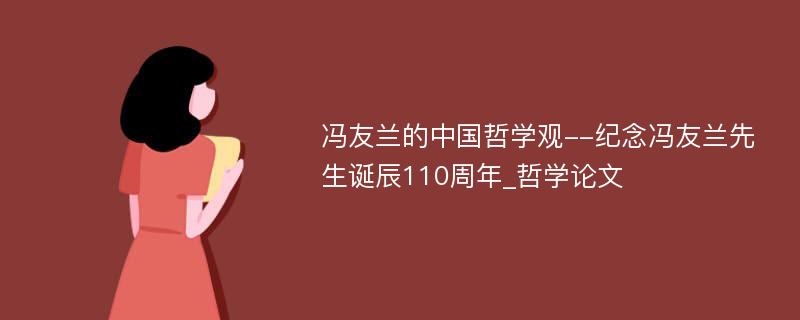
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观——纪念冯友兰先生诞辰11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诞辰论文,中国论文,哲学论文,周年论文,冯友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05)01-0001-06
“中国哲学观”指有关中国哲学的基本观点,既包含对中国哲学的总体看法,也包含对中国哲学具体内容的看法。作为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开创者之一的冯友兰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哲学史》和40年代的《中国哲学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中就明确表述了对中国哲学的总体看法,形成了自己的儒学观、道家观、佛学观等。在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受到质疑的情况下,重新解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观有着重要的认识意义。
一、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总体看法
冯友兰是按照西方哲学的框架来解读中国哲学的,他对中国哲学的精神、特点等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冯友兰指出,所谓中国哲学“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所谓中国哲学家“即中国某种学者,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家名之者”[1](P8)。
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或基本特点可以概括为“既入世又出世”,“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面前”。有了这种精神,中国哲学可以说既是最理想主义的,同时又是最现实主义的;它是很实用的,但并不肤浅。一般来讲,入世与出世、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是对立的,“中国哲学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反命题统一成一个合命题”[2](P12)。如何统一起来?中国哲学的精神正是体现在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中。中国哲学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人格示范,这就是“圣人”,它既入世又出世,内圣而外王,它所体现的也正是中国哲学的精神。
冯友兰肯定了中国哲学的发展性,并对中国哲学的一些特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特点有些是长处,有些是缺失。
1.中国哲学是发展的,进步的
冯友兰指出,人类历史是不断进步的,中国哲学史也是这样。比如说,就哲学所研究的问题和范围来看,汉代以后的哲学不如汉代以前的哲学所涉猎的多和广,但就其明晰或清楚的程度来看,汉代以后的哲学确实超过了前代。有人以孔子讲尧舜,董仲舒、朱熹、王阳明讲孔子,戴震、康有为仍然讲孔子,“遂觉古人有一切,而今人一切无有”,这是不对的。实际上,董仲舒只是董仲舒,王阳明只是王阳明。如果我们懂得了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只是董仲舒的哲学,王阳明的《大学问》只是王阳明的哲学,也就懂得了中国哲学总在进步之中。有人以为,董仲舒、王阳明的学说在以前儒家哲学中已经见到端倪,他们只不过是发挥引申而已,不能算自己的哲学和新的贡献。冯友兰同样反对这种看法,他形象地说:“即使承认此二哲学家真不过发挥引申,吾人亦不能轻视发挥引申。发挥引申即是进步。小儿长成大人,大人亦不过发挥引申小儿所已潜具之官能而已。鸡卵变成鸡,鸡亦不过发挥引申鸡卵中所已有之官能而已。然岂可因此即谓小儿即是大人,鸡卵即是鸡?……由潜能到现实便是进步。”[1](P23-24)冯友兰所坚持的显然是哲学上的进化论观点,强调了中国哲学史发展的客观性,具有历史辩证法因素。但冯友兰没有区分质的飞跃和量的变化,错误地把康有为、梁启超时代的哲学统归到经学时代,忽视了中国哲学走出中世纪的突破性。当然,这种阶段划分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已经改变,由原来的两阶段(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论发展为四阶段(古代、中古、近代、现代)论。
2.中国哲学缺乏形式上的系统,但有实质上的系统
所谓“形式上的系统”指论理结构方面的条理、层次等,“实质上的系统”则指前后一贯的思想内容。当时有些人通过中西哲学比较,认为中国哲学无系统。冯友兰认为这种说法不准确。实事求是地说,与西方哲学相比,中国哲学确实缺乏形式上的系统,即逻辑论证不足,“中国哲学家之哲学,在其论证及其说明方面,比西洋及印度哲学家之哲学,大有逊色”[1](P8)。这并不是因为中国哲学家没有这个能力,而是由于他们之“不为”,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的价值观。中国哲学家重行,不十分重视著书立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中国哲学家深信“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即立德,外王即立功,成为圣王是他们的最高理想,不得已才去著书立说,著书立说在中国哲学家的眼里是最倒霉的事情。所以在中国哲学史上,那些精心结撰而又首尾相贯的哲学著作很少,往往都是哲学家本人或其门人后学,杂凑平时书札语录而成,虽然道理足以自立,而扶持此道理的议论,多失之于简单零碎。除此之外,冯友兰指出,中国哲学缺乏形式上的系统还可能与古代的书写质料和方式有关,古人写书用的竹简,极为夯重,故著书立说务求简短,结论鲜明而论证较少,长此以往,形成了一种著书的风尚或传统。在1982年版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中,冯友兰依然坚持了上述对中国哲学的看法,认为中国哲学中“术语”缺乏,比如“天”可以指与地相对的“苍苍者”,也可以指“上帝”,也可以指自然。由于术语少的缘故,“论证往往是不很详尽的,形式上的体系往往不具备”[3](P36)。
冯友兰承认中国哲学缺乏形式上的系统是“逊色”之处,但对这一点给予了“同情的理解”,“正因为中国哲学家的言论、文章不很明晰,所以它们所暗示的几乎是无穷的”[3](P17)。这种评价是客观的。中国哲学虽然缺乏形式上的系统,但这不能否认中国哲学确实有实质上的系统。冯友兰说:“中国哲学家的哲学,虽无形式上的系统,但如谓中国哲学家的哲学无实质上的系统,则即等于谓中国哲学家之哲学不成东西,中国无哲学。形式上的系统,希腊较古哲学亦无有。苏格拉底本来即未著书。柏拉图之著作,用对话体。亚里士多德对于各问题皆有条理清楚之论文讨论。按形式上的系统说,亚里士多德之哲学,较有系统。但在实质上,柏拉图之哲学,亦同样有系统。依上所说,则一个哲学家之哲学,若可称为哲学,则必须有实质的系统。所谓哲学系统之系统,即指一个哲学之实质的系统也。中国哲学家之哲学之形式上的系统,虽不如西洋哲学家,但实质上的系统,则同有也。讲哲学史之一要义,即是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1](P13-14)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冯友兰坚持了这一观点,认为形式上的系统不等于实质上的系统,比如《论语》,其中记载的都是孔子回答学生们的话,就形式上讲是没有系统的。但这并不等于孔子的思想没有实质上的系统,“如果是那样,他的思想就不成为一个体系,乱七八糟。如果真是那样,他也就不成为一个哲学家了,哲学史也就不必给他地位了”[3](P38-39)。这种形式和内容相分离的系统决定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特殊任务,“就是从过去的哲学家们的没有形式上的系统的资料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找出他的思想体系,用所能看见的一鳞半爪,恢复一条龙出来”[3](P38)。如果以经典的西方哲学体系为参照,中国哲学形式上的系统确实薄弱,思想上的系统则与西方哲学一样明显。就表现形式说,中国哲学和其他民族的哲学有所不同,就内容说,中国哲学和其他民族的哲学是一样的,“如果不是如此,它就不能称为哲学”[3](P35)。
冯友兰有关中国哲学这一特点的概括是合理的,它对于我们今天认识中国有无哲学依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中国无哲学”的观点由来已久,黑格尔虽然在名称上不否认中国哲学的存在,但总体上是极其鄙视的。他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认为,孔子的教训是一种“常识的道德”,在哪一个民族里都可以找到,“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4](P120)。《易经》虽然达到了“对于纯粹思想的意识,但并不深入,只停留在最浅薄的思想里面”[4](P120)。胡塞尔认为,只有希腊人才对宇宙论真正感兴趣,相应地出现了一种纯粹的理论形态,而东方哲学则不存在纯理论的生活兴趣,从本质上说依然是一种原始的、自然的、不带有普遍的概念意义的神秘主义[5]。德里达认为中国只有思想,而无哲学,等等。时下,国内也有一些学者讨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问题。笔者不认同“中国无哲学”的观点,因为其在理论上缺漏颇多,难以自圆其说。海德格尔、德里达等人认为,中国有思想,无哲学,在思想与哲学间划了一条无法逾越的界限。这里有三点需要说明:第一,德语、法语中的“思想”和“哲学”的界限在哪里?如果是两个完全没有重叠意义的词,中国有思想、无哲学的说法尚可理解。第二,退一步说,哲学特指概念思维,思想特指非概念思维,难道中国人仅仅有非概念思维,没有概念思维吗?第三,从汉语语义上讲,哲学与思想两个概念是一而二又二而一的,哲学本身是一种系统的思想,思想的精华部分是哲学,所以,说中国有思想,无哲学,不符合汉语语言逻辑。有的论者指出,在中国传统思想史上,既没有哲学这一名词,也没有哲学这个门类。这一点是符合实际的。但没有这个名词,没有这个学科门类就等于没有哲学吗?应该着眼于内容。对中国有无哲学的判定,不是无关紧要的一家之言,而是关涉到重大的原则性或前提性的问题。如果承认中国无哲学,那么就等于说,由胡适、冯友兰所开创的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毫无意义,建国以后人们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工作也是徒劳一场,这无疑对于近百年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具有釜底抽薪的意味。应当承认,用西方哲学的框架研究中国哲学的确有削足适履的偏颇,但这并不等于说用西方哲学的框架研究中国哲学毫无意义。人类思想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地被重新解释的历史,因此也就是一个不断地被创造的历史,运用新的参照系统重新认识和解释原有的对象是合理合法的,并在很大程度上推进着思想史研究的进步。这种原则也完全适用哲学史的研究。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Cassirer,Ernst)在他的《人论》(An Essay on Man)中对这一观点的表述可谓经典,他说:“在哲学上属于过去的那些事实,如伟大思想家的学说和体系,如果不作解释那就是无意义的。而这种解释的过程是永无止境的。当我们的思想达到新的中心和新的视野时,我们就一定会修改自己的看法。”[6](P228)哲学历史的文本正是在这种不断的被解释中获得了永恒的价值活力。冯友兰也指出,所谓历史有两类:一类是“事情之自身”,他又称之为“历史”或“客观的历史”;另一类是“事情之纪述”,他又称之为“写的历史”或“主观的历史”。哲学史也是一样,本来的哲学史只有一个,而写的哲学可以有多个[1](P16)。随着时代的变迁,任何人写的历史或哲学史都必须改写或重写。因此,从主流上来说,不论胡适、冯友兰用西方近代哲学的框架研究中国哲学,还是人们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框架研究中国哲学,都是具有开创性的事业,对于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的创立和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哲学研究走出中世纪的历史进步。相反,在当代解释学的大背景下,试图回归到传统的经学巢穴,运用传统的经学方法去治国学,去重新发现“原汁原味”的中国思想,其价值维度倒很令人怀疑。
3.中国哲学以道德哲学及其修养方法见长,但缺少知识论和宇宙论
在冯友兰看来,由于中国哲学家十分重视“内圣”,所以其所讲的多是成圣的学问和修养方法。而极为详细的修养方法即“为学之方”与西方哲学中的认识论方法不同,所反映出的是中国哲学中道德本位的倾向,这一特点与不重视知识论有关。冯友兰指出,中国哲学注重道德,不为知识而知识,圣人为圣人,恶人为恶人在于道德上的评判,与知识多少无关。中国哲学中知识论不发达的主要原因是未实现“我”与“非我”即人与宇宙的分离。冯友兰指出,在西方近代史上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之自觉。“我”自觉之后,就有所谓“非我”与之对立,也就是主观和客观的对立,而二者之间的界限是分明的。这种对立自然产生“我”如何才能知道“非我”的问题,即知识论问题。在中国人的思想中,没有显著的“我”之自觉,也没有显著的“我”与“非我”的分离,所以知识论问题未能成为中国哲学中的大问题。另外,中国哲学家特别重视“人事”,所以对宇宙论的研究不能说没有,但大都比较简略。
冯友兰对中国哲学这一特点的指认应该说反映了中国哲学的一些实际情况,成为多数人能够接受的观点,比如后人用“实用理性”概括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就明显地与冯友兰的思路相吻合。但是,这里有一个参照点问题,即何谓“逻辑”,何谓“知识论”或“认识论”,确立的参照点不同,结论自然有异。冯契不反对中国哲学长于伦理的说法,但反对中国哲学认识论不发达和缺乏逻辑的观点。针对中国哲学认识论不发达的观点,冯契对何为认识论的问题进行了重新厘定,提出了一种广义认识论,并由此确定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认识论相当发达,在作为人类认识史精华的世界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针对中国哲学缺乏逻辑的观点,冯契指出,中国传统哲学的确缺乏对形式逻辑的研究,但这不等于缺乏逻辑,由于较早和较深入地探讨了辩证逻辑,所以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逻辑思想是很发达的[7]。应该说,冯友兰和冯契的见解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二、冯友兰的儒家哲学观
作为一个现代新儒家的代表,冯友兰对儒学的看法是怎样的呢?笔者此处以原始儒学、新儒学为重点,探讨冯友兰儒学观的主要内容。
冯友兰指出,所谓“儒”即“有知识材艺者之通称”,“是一种有知识、有学问之专家;他们散在民间,以为人教书相礼为生”[1](《附录》P26)。儒家的兴起,为子学时代的开端;儒家的独尊,为子学时代的结束。儒学在汉代的独尊有其自身的原因,因为“儒者通以前之典籍,知以前之制度,而又理想化之,理论化之,使之秩序有序,粲然可观。若别家仅有政治、社会哲学,而无对于政治社会之具体办法,或虽有亦不如儒家完全。在秦汉大一统后之‘建设时代’,当然不能与儒家争胜也”[1](P486)。因此,儒学在整个中国的中古时期独领风骚,有其内在的缘由。
冯友兰对原始儒学和新儒学进行了自己的阐释,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观点。
1.原始儒家哲学
原始儒学是今人的概念,与先秦儒学相同。在对先秦儒家哲学的看法上,冯友兰充分肯定了孔子、孟子、荀子学说的重要意义。
冯友兰指出,儒学系统的形成有赖于“以述为作”的方式。孔子虽然说过“述而不作”,但原始儒家实际上都是以述为作。“此种精神,此种倾向,传之于后来儒家,孟子荀子及所谓七十子后学,大家努力于以述为作,方构成儒家思想之整个系统”[1](P92)。冯友兰举例子说,《易》是儒家所述,《系辞》、《文言》等是儒家所作,而《易》在思想史上的价值,体现在《系辞》、《文言》中,而《春秋》与《公羊传》、《仪礼》与《礼记》等亦复如是。这说明他们虽然自称述而不作,实际上是以述为作,“作”的价值在“述”之上,这是儒家学术赖以成为系统的根本方式。
冯友兰反对胡适把老子作为中国哲学第一人的观点,认为《老子》一书晚出,孔子才是中国哲学的开山。“就其门人所记录者观之,孔子实有有系统的思想。由斯而言,在中国哲学史中,孔子实占开山之地位。……以此之故,此哲学史自孔子讲起,盖在孔子以前,无有系统的思想,可以称为哲学也”[1](P29)。
孔子作为中国哲学的开山由冯友兰系统提出,但对孔子的高度评价,早已见诸孟、荀。孟子从德的角度认为孔子是“集大成”,荀子从学的角度认为孔子“仁智且不蔽”。而冯友兰对他们三人在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也作了肯定性的评价。冯友兰指出,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就像苏格拉底在西方历史中的地位一样,而孟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就像柏拉图在西方历史上的地位一样,而荀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就如同亚里士多德在西方历史上的地位一样。冯友兰还具体分析了他们三人在学术上的不同之处:在对天的看法上,孔子之天是主宰之天。孟子之天有时为主宰之天,有时为运命之天,有时为义理之天。荀子之天则为自然之天。在对人性的看法上,孔子一方面注重个人性情之自由,一方面又注重个人行为之外部规范。孟子较注重个人性情之自由,也重视个人之道德判断。荀子较注重人之行为之外部规范,即所谓“礼”。在正名的问题上,孔子、孟子的正名主义“仅有伦理的兴趣”,荀子作为辩者,其所讲正名“逻辑的兴趣亦甚大”。另外,冯友兰还谈到了孟子和荀子哲学的性质,认为孟子是“软心的哲学家”,其哲学具有唯心论倾向;荀子是所谓“硬心的哲学家”,其哲学具有唯物论的倾向。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冯友兰对孔、孟、荀三人的学说进行了客观的描述和公正的评价,作为第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史》,其所提出的观点不仅具有原创性,而且独具只眼,影响深广,即便我们今天对先秦哲学的研究,也很难说能够跳过或完全超越冯友兰的见解。在冯友兰的视阈里,孔子虽是中国哲学的开山,儒学的创始人,但荀子却是原始儒学的集大成者,其所言之天是自然之天,其人性论重“礼”,其正名具有逻辑兴趣,其学说具有唯物论色彩,这些在今天看来仍为不刊之论。荀子历来被看作非正统的儒家学者,或者是一个和稀泥的乡愿型学者,但冯友兰却给予他很高的评价,反映出冯友兰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在哲学史领域中实事求是的客观精神。
2.新儒家哲学
冯友兰明确把宋明理学或宋明道学称作“新儒学”,探讨了新儒家哲学的奠基、确立、特点、代表人物以及朱陆异同等一系列问题。
冯友兰认为,新儒学的奠基人是唐代的韩愈、李翱,“宋明道学之基础及轮廓,在唐代已由韩愈、李翱确定矣。而李之所贡献,尤较韩为大”[1](P811)。
虽然如此,但新儒学的真正确立却是二程,“濂溪、康节、横渠,虽俱为道学家中之有力分子,然宋明道学之确定成立,则当断自程氏兄弟”[1](P868)。
新儒学当然本之于儒学本身,但它的“新”就其理论来源或思想内容上说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援佛入儒,吸收佛学抽象化、形式化的特长,发挥禅宗的一些思想,“可以说新儒家是禅宗的合乎逻辑的发展”[2](P309);二是援道教入儒,“道教有一个重要成分是阴阳家的宇宙发生论。新儒家的宇宙发生论主要是与这条思想路线联系着”[2](P309),比如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邵雍的象数学等。
冯友兰在谈到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时,曾经提到过一些自己的原创性发明,比如把名家分为“离坚白”与“合同异”两派,把二程分开来,一个作为理学的代表,一个作为心学的先驱,等等。在谈到二程的学说时,冯友兰说:“兄弟二人之学说,旧日多视为一家之学,故《二程遗书:》中所载二人语录,有一部分俱未注明为二人中何人之语。但二人之学,开此后宋明道学中所谓程朱陆王之二派,亦可称为理学心学之二派。程伊川为程朱,即理学一派之先驱;而程明道则陆王,即心学一派之先驱也。”[1](P869)而理学之集大成者为朱熹,心学之集大成者为王阳明。
冯友兰探讨了理学与心学的根本差别,即所谓的朱陆之争、朱三之别。冯友兰指出,“朱陆之不同,实非只其为学或修养方法之不同,二人之哲学,根本上实有差异之处”,“朱子言性即理,象山言心即理,此一言虽只是一字之不同,而实代表二人哲学之重要的差异。盖朱子以心乃理与气合而生之具体物,与抽象之理,完全不在同一世界之内。心中之理,即所谓性,心中虽有理而心非理。故依朱子之系统,实只能言性即理,不能言心即理也。象山言心即理,并反对朱子所说心性之区别”[1](P938-939)。朱子哲学和阳明哲学的区别根本上就是理学和心学的区别,按照朱子的系统,只能讲性即理,而不能讲心即理;按照阳明哲学的系统,则在事实上与逻辑上,无心即无理。
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冯友兰还对朱熹和王阳明的学说以及整个新儒学进行了价值评判。他指出,照朱熹的说法,为了了解永恒的理,原则上必须从格物开始,但是这个原则朱熹自己就没有严格执行。在他的语录中,我们看到他的确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进行了某些观察,但是他的绝大部分时间还是致力于经典的研究和注释。他不仅相信有永恒的理,而且相信古代圣贤的言论就是这些永恒的理。所以他的系统中“有权威主义和保守主义成分”,这些成分随着程朱学派的传统继续发展而日益显著。程朱学派成为国家的官方学说以后,更是大大助长了这种倾向[2](P365)。照王阳明的说法,良知所直接知道的是我们意志或思想的伦理方面。它只能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但是不能告诉我们怎样做。要知道在一定情况下怎么做我们应该做的事,王守仁说还必须根据实际情况研究实际做法。可是后来他的门徒发展到似乎相信,良知本身能够告诉我们一切,包括怎么做。这当然是荒谬的,陆王学派的人也确实吃尽了这种谬论的苦头[2](P366)。新儒家是儒家、佛家、道家(通过禅宗)、道教的综合。从中国哲学史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综合代表着发展,因此是好事,不是坏事”[2](P367)。
冯友兰是最早的中国哲学史家之一,他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没有更多可资借鉴的现成资源,因此自家体贴和发明的东西也就是原创性的观点比较多。他对儒学的许多看法今天仍然具有生命力,我们今天的中国哲学史研究除了在方法论上经过了马克思主义化的洗礼外,在许多哲学史事实的解读上,依然难以跨越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如他对孔、孟、荀哲学的比较分析,对新儒家先驱、代表人物、学派、集大成者、学术特色、朱陆异同等的确定和理解,至今仍为权威之论。
三、冯友兰的非儒哲学观
冯友兰几乎对中国哲学史上的所有学派都有研究,墨家、名家、杂家、阴阳家,等等。我们重点看一下他的道家观和佛学观。
冯友兰认为,先秦道家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属于杨朱的那些观念,代表第一阶段;《老子》的大部分思想代表第二阶段;《庄子》的大部分思想代表第三阶段。老子的学说,荀子批评过,庄子称述过,韩非子“解”过“喻”过,《战国策》引用过,这说明老学在战国时期已经成为“显学”。道家“为当时一切传统的思想制度之反对派”,道家哲学的出发点是“全生避害”。我们可以说,先秦道家都是为我的。只是后来的发展,使这种为我走向反面,取消了它自身。冯友兰还提出了“新道家”(Neo-Taoism)的概念,用以指称魏晋玄学,把以向秀、郭象等为代表的玄学称作新道家中的“主理派”,把以《列子·杨朱篇》等为代表的学说称作“主情派”,并对其学说特点进行了分析。
冯友兰对佛学有诸多研究,尤其是探讨了佛学的中国化问题。冯友兰指出,佛学是印度的产物,但是中国人讲佛学,往往加入了自己的理解,也就是融入了中国人的思想倾向,这种佛学可以称作“中国之佛学”。冯友兰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这一问题:第一,佛学派别虽然很多,但大体的哲学倾向在于阐明“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认为外界都是我心所现,虚幻不实。但中国哲学的见解多倾向于“实在论”,认为除了主观之外,客观外界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中国人讲佛学的“空”是“不真空”。第二,作为佛教最高境界的“涅”即圆寂,它是“永寂不动者”。中国人注重人的活动,儒家所说的最高境界即在活动中。所以中国人讲佛学,多以为佛之境界并非永寂不动。佛之净心,亦“繁兴大用”。第三,由于印度社会中等级分明,所以佛教中讲某种人没有佛性,不能成佛。中国人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所以中国人讲佛学多以为人人皆有佛性,一阐提也可成佛。另外,中国人讲佛学还主张“顿悟成佛”,以为无论什么人,“一念相应,便成正觉”,等等。
不难看出,冯友兰对道家哲学和佛学的看法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道哲学与儒家哲学一样,它的成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只有用动态的理念去审视,才能把握它的真实面貌。冯友兰“新道家”的提法以及分类颇有新意,对我们今天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依然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佛学中国化的问题在今天来说已经成为共识,它反映了解释学背景的重要性和中国文化的强大同化力,任何学术要想在中国生存和发展,必须融入到中国文化的传统和现实中去,任何脱离中国传统和现实的学术注定是短命的。
收稿日期:2004-10-13
标签:哲学论文; 冯友兰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 儒家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西方哲学家论文; 哲学史论文; 王阳明论文; 孔子论文; 荀子论文; 道家论文; 佛学论文; 佛教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