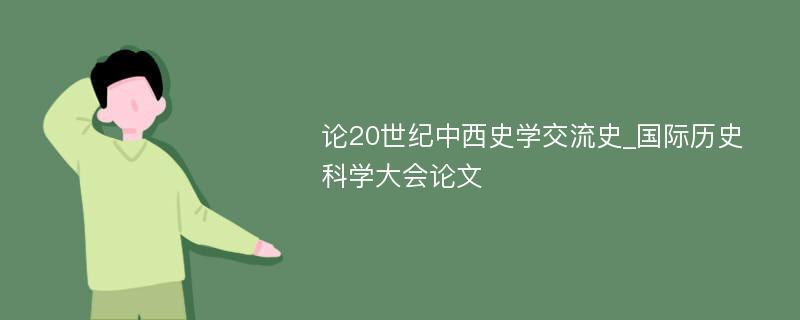
三论二十世纪中西史学交流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中西论文,二十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已经谢幕,但对20世纪那风雷激荡、色彩斑斓的历史进行研究,还刚刚揭开序幕。历史的审视,总是在创造世界的活动之后,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深度。 倘若说到20世纪的世界历史研究,中外(西)史学交流史当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选项,有道是文明(或文化)以交流而出彩,史学交流尤甚,理由呢?因为史学是文化的枢纽,换言之,它是文化中的文化。 故此,中国新世纪以来,中外史学交流史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尤其是对20世纪中西史学交流史的研究。近年来,笔者也积极参与这一工作,落笔亦多为20世纪的人与事。①我除几篇关于20世纪中西史学交流的个案之作外,②从理论上专门阐发20世纪中西史学交流史,本文为第三篇,③故曰“三论”。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这篇文章集中谈下列三点,或可作为前“二论”的“补白”,拙文不当与疏漏之处,尚望方家指正为盼。 一、徘徊于“两支巨流”之间 纵览20世纪的世界史学,概括地说,能引领国际史学潮流的,主要有“两支巨流”,正如当代法国历史学家居伊·布瓦所指明的:“两支巨流贯穿在当今的历史编纂学中,一支是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支是那些为之感到自豪的人所说的‘新史学’。”④布瓦的概括,是对20世纪世界史学的一种宏观的考察,自有其独到之处,这里借“两支巨流”说,意在阐明它与20世纪中西史学交流的牵引与关联。 一支是“马克思主义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20世纪50年代大规模地输入中国的苏版马克思主义史学,而不是二战后在西欧北美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勃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那要另作讨论。 众所周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仅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也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主要是从苏俄引入(有时也借助东邻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应当说自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十多年间,早期苏俄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成就不斐,它的输入对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如李大钊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从20年代末开始,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演变为“官方史学”,至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出版,就被烙上了教条主义与僵化色彩的斯大林主义印记的马克思主义占据了统治地位。这种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抗日战争的延安地区传播,对当时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如范文澜等)也有不小的影响。不过,需要明确指出的一点是,在20世纪前期输入中国的域外史学中,苏俄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从总体来说还很微弱,唱主角的是西方资产阶级史学。 苏版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我国史学发生重大影响的是在50年代。新中国成立伊始,“以俄为师”、“向苏联学习”庶几成了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中国史学焉能例外。其时通过多重途径输入了苏联史学,就个人的阅读经历,记得多卷本《世界通史》以及《穷途末路的资产阶级历史哲学》、《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等书的中译本,于我大学时代历史学专业的学习甚有影响,至今仍未消失。⑤至60年代后,由于中苏政治关系的恶化及中国的“文革”,炙手可热的苏联史学输入中国史,由冷转为空白,后终于为西方史学的大规模引入所淹没。 一支是“新史学”,我这里说的是西方新史学。西方新史学发端于19世纪末,自此迄今,它经历了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演进的历史过程。在20世纪前期,西方传统史学(以兰克史学派为代表)还显示出强劲的实力,卷轶浩繁的“剑桥三史”(即《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和《剑桥近代史》)的出版,即为显例。即使到了20世纪后期,在1984年美国历史协会的年会上,恪守传统史学的“顽固分子”希梅尔法布,还向新史学发难。其实,从西方史学发展的关联性而言,西方新史学总是跟传统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法国年鉴新史学派总是深深地扎根于法兰西的史学传统之中。在20世纪前期中外史学交流中,这里的“外”主要是“西方”,以兰克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史学,以鲁滨逊学派、文化形态学派等为主的西方新史学的早期代表,其人其著纷纷传入东土,并在30年代前后形成了20世纪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第一次高潮。⑥ 上述这“两支巨流”,在1917年以前,总体上处于对立状态,这之后两者逐渐抛弃敌视态度,开始接近,直至1955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明确指出:“大约以1955年起,历史学研究进入了迅速转变和反思的时期。”⑦保罗·利科也说:“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把50年代中期以后的年月描绘为在西方对历史主义的论点和在东方对教条主义和程式化进行批判地再检讨的时期。”⑧是的,这“两支巨流”亦即东西方史学都在发生剧变,进入反思(再检讨)时期,即巴氏所说的“重新定向”。 1955年9月,在罗马举行第十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苏联在中断20余年后重新与会,“两支巨流”汇合了东西方史家在二战后首次会晤。出现了西方新史学派、西方传统史学派与东方(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同场博弈、互争雄长的对话场景,正如参会的苏联史家潘克拉托娃在总结此次会议时所说:“经验证明,为了巩固和平与发展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学者之间的合作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⑨ 然而,苏联史学虽在斯大林逝世后,经历50年代的“解冻时期”和改革年代,曾在方法论探究、历史研究领域的开拓等方面显示出某种新气象,出现新成果,但到步入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后,史学也止步不前了,直至苏联解体,苏版马克思主义史学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与之相反,西方新史学则以蓬勃生机在60年代获得了迅猛的发展,70年代则是它的“巅峰时代”。它揖别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又携手经过革新的传统史学,终而成了史坛“霸主”并以强锐之风,劲吹在改革开放初启时的华夏大地,在80年代很快出现了20世纪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第二次高潮(这岂止是史学,也当然包括史学之外的其他文化领域)。这次中西史学交流之盛况,许多学界人士都是亲历过的,有的还是参与者,对此,就毋须在这里赘说了。 20世纪中外(西)史学交流的行程,徘徊于“两支巨流”互为雄长之间,既显示了色彩斑斓,散发出各自的个性色彩,但也有许多共同的方面,比如:译书均在交流中占首要地位,这“两支巨流”在中国流淌,无不证明梁启超之论:“今日中国欲为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义。”⑩先贤之见,也适合于史学文化之交流。曾记得,50年代《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译本在坊间广为流传,80年代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的中译本首次印刷就有8万册,一时洛阳纸贵,一书难求……通过这类译书,国人领略苏版马克思主义(亦即斯大林主义)的特色,学人知晓了国际史学(而主要是西方史学)的发展及其流向;又比如,留学生在交流中的重要作用,不管是30年代前后的何炳松,50年代的一批留苏学人(如陈启能等),80年代之后的“新何炳松”(如王晴佳等),在中外史学交流与沟通中,他们都充当了“马前卒”的先锋作用。这“两支巨流”的流入,当然也给我们一个共同的经验教训:我们为食洋不化与生搬硬套付出了太多的代价,事实证明,“全盘西化”不行,“全盘苏化”(“俄化”)也不行,中国史学只有在与国际史学互动中,汲纳他人之长,建构自己的“主体意识”,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之路,舍此别无他途。 二、从“一花独放”到“精彩纷呈” 纵观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史,其亮点当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西史学交流。的确,中国自新时期以来,与现当代西方新史学的沟通与交汇,如译书之多、人员往来之众、成果刊发之多等等,都是前所未有的。 回溯这段历史,在繁杂的西方新史学引进的诸多流派中,个人以为年鉴学派可居鳌头,似乎是“一花独放”,或可视为20世纪80年代我国第二次引进西方史学高潮中的一个标杆。其实,发端于上个世纪20—30年代的法国年鉴学派,一开始也默默无闻,属于地区性的学派,在20世纪前期并未对西方史学发生过多大的影响。年鉴学派真正登上国际史坛是在1955年罗马召开的第十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从50年代至70年代,年鉴学派声誉日隆,直至俨然成了现当代西方新史学的范型,被塑造成西方史学的一种主流形象,其识见泽被史学,惠及其他社会科学,在国际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至于年鉴学派在中国的传播,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60年代初,前辈学者张芝联先生就在中国南疆一座城市的学院,向莘莘学子介绍过年鉴学派,(11)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下,当然是空谷足音,直至1978年改革开放,张芝联先生又写《法国年鉴学派简介》,(12)才日益对我国史学发生重大影响。真是一花引来春满园,自此,西方史学的引进,驱动着中国的西方史学研究步入了快车道。事实确是,8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西学东渐,其中最具代表性与集中引进是对年鉴学派的介绍、评述、研究,乃至将这个学派的理论运用于中国史学。比如,就以译书为例,年鉴学派的中译也居多,仅以年鉴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布罗代尔的著作,已大体译出,在汉语学界流布,一时竟成了学界关注与研究的一个热点。对此,学界已多有评介,(13)我这里仅补充两小点: 一是在20世纪80年代,除张芝联先生引荐年鉴学派于中国卓有成效外,还应关注到其他学者。手边就有一例:1983年,中山大学汤明檖先生赴法国讲学期间,曾和年鉴学派学者有较为密切的接触,当国内学界对该派尚处在介绍阶段的时候,汤先生已开始指导他的学生(如刘志伟、陈春生等)运用年鉴学派的理论进行具体的中国史学研究。1993年,年鉴学派的第三代领袖人物勒高夫首次来中国进行学术访问,其第一站就选在华南学派大本营——中山大学,这反映出勒高夫的识见与华南学派所倡导的“历史人类学”理论有其合拍之处。(14)这类例子当然不是个案。 二是运用年鉴学派的理论于中国历史学的研究。一种外来的理论再好,倘输入后,缺乏对其的真切体会,生搬硬套,也会水土不服,难以做到水乳交融,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史学交流的最终目的,是将异域的种子,在本土培植,使之发芽与成长。在我看来,这种尝试与努力总是应该受到鼓励,倘有失误,也不要求全责备,更不能乱戴帽子。笔者曾尝试用年鉴史学范型中的时段理论,分析西方基督教自1860年至1900年这一时段在近代中国的命运,这一尝试获得了学界的认可。(15)又如,当代中国学者用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念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将长时段理论运用于中国的古史研究,也取得了成绩。在此,不再一一例举。 观察中西史学交流史,在20世纪末发生了变化,这就是现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的引入及其对我国史学的影响。美国史学史家伊格尔斯曾指出过:“在20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期间,历史研究的重点继续是从分析的社会科学转移到更加强调文化因素。”(16)伊格尔斯所指,正是说的西方新文化史在当代的兴起,(17)它成了晚近三十余年且一直影响到当下的西方史学新潮。 这股潮流,初起微澜,继而淙淙,终而汹涌,这在西方,进而在中国的流传,都是如此。80年代初,此时的西方新文化史之风尚处于青蘋之末,虽吹起水波涟涟,但在东土成思潮的却是上文所说的“一花独放”的年鉴学派以及它的史学理念,还真的说不上西方新文化史诸家对当时中国史学带来什么影响。当然,这需要时间,也需要等待。西方新文化史入华的最佳时间终于在世纪末来临了:1999年9月,当代西方新文化史旗手之一彼得·伯克访华,从北向南,一路走来,开始了他在中国的学术之旅,到处宣传他的新文化史理念。(18)在黄浦江畔,也留下了他的足迹。伯克曾先后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校作学术报告,笔者曾有幸在复旦聆听过他的精彩演讲。在上海两校讲演的内容,已公布于众,此处不再复述。(19) 我在上面说过,在中西史学交流中的译书之重要,在这里还需带上一笔的是学者讲学之交流功能也不可忽视,尤其是某一学科领域内的大学者。确实,无论是大家早已熟知的杜威在20世纪20年代来东土讲学,苏联历史学家群体在50年代烜赫一时的在中国的讲学活动,还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盛况空前的域外(主要为西方)学者来华讲学,都是显例,他们都为传播域外史学之新说提供了便捷的通道,在互动中,也可实现让他们了解中国的现在,了解中国的过去,进而了解中国的史学,这对消除误解、纠正偏见,不无助益。总之,学者讲学在中外(西)史学交流史上也留下了他们的足印。 西方新文化史引进后的“精彩纷呈”还得归功于年鉴学派第三代领袖人物勒华拉杜里著作中译之媒介。(20)1997年,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被译为中文出版。(21)这部名著在西方史学文化转向进程中,是一部代表性的著作,开创了中国大陆新文化史中译的先导。真如“蝴蝶效应”一般,《蒙塔尤》中译竟引来新文化史中译之“精彩纷呈”,据青年学者周兵的归纳,近年来中译的新文化著作,大体可分为四种类型:物质文化史,疾病和医药的文化史,身体和性的文化史,实践与表象的文化史。(22)这四类书籍,既有学术性很强的理论著作和专题研究,比如弗朗索瓦·弗雷的《思考法国大革命》、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娜塔莉·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罗伯特·达恩顿的《屠猫记》等;更有无数的通俗性的新文化史作品,比如《食物的历史》、《医药文化史》、《调情的历史》、《幽默文化史》等,在当今国内书肆或网上选购,足以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据周兵粗略统计,自2000年至今这类新文化史中译本已达百余种。不过,国内译作,这仅是其中一小部分,不难想见当代西方新文化史在它的发源地之繁荣景象,伯克说它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流行过。在新文化史琳琅满目的背后,不由令人感叹“还有什么不是文化史”吗?甚至可以发出克罗齐式的“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史”的惊世之言。 对于这样一种文化景观,我们应当怎么看,这自然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我赞同周兵的下列看法:“总体而言,当前西方新文化史的研究可以说是既精彩绝伦,但又不免繁琐杂沓。新文化史的写作常常是学术性与通俗性兼重,既多出自专业的学院派历史学家之手,也多以人们日常熟知的主题入手,同时新文化史的通俗性也吸引了越来越多非专业作者踏入历史学的领地,使得历史学成为一门可以雅俗共赏、为人喜闻乐见的学科。而过分的标新立异也使一部分著作走上了欺世媚俗、庸俗无聊的另一极端,客观上给人造成了新文化史良莠不齐的负面印象,因此对各类(新)文化史著作有时还需区别地(甚至是鉴别地)去读、去看并加以研究。”(23)此见,切中肯綮,深以为然。上见发表六年后,周兵以《新文化史的回顾与反思》为题撰文,进一步论证了西方新文化史的缺陷:“文化”因素被过分夸大、“文化”概念被滥用。(24)我以为,对于现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的引进,对于西方新文化史之中译,都应当十分关注这些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新文化史作品的中译,我国的西方新文化史之史的研究,多在中国新世纪(21世纪)显示“精彩纷呈”。台湾学者卢建荣先生指出:“台湾引进的新文化史研究风潮,较之曩昔七十年来两波的移植西学运动,成果显得辉煌,大有直逼与国际史坛同轨、或同步发展的况味。”(25)卢先生说的是台湾学界的情况,大陆学界在新文化史方面或移植,或研究,近十年来,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这里略举一例,以见一斑。从这两三年在上海连续举办的“新文化史与上海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传来的信息表明,会议主题的拟定充分显示域外新文化理论与本土问题的紧密结合,这些议题包括:我们应如何更好地认识近代上海的政治文化、物质文化、商业文化和日常生活?涉及中西文化交流的话题,能否基于出版史、阅读史更好地展开等。中外与会者的共同感受是,平等对话,互学互鉴,借用卢氏之语,就当代新文化史研究而言,从这个系列会议,看到了“与国际史学同轨”、闻到了“同步发展的况味”。倘与上作比较,这有别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引进年鉴学派等西方史学流派在华的回应,相异于那些年的顶礼膜拜的“心态”,那些年的食洋不化的“况味”。总之,历史在前进,行至20世纪末,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中西史学交流史,而不只是单向的输入。 不管怎样,现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理念的引入,体现其理念的作品之中译与广布,对汉语学界正在勃兴的新文化史研究,是起了推波助澜作用的。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面对西方学界新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的挑战,不只是移植,更重要的是如何奠建自身的“主体意识”,如何将西方新文化史范型与中国本土问题相结合,即前面所说的将域外理论运用于中国史学的个案研究,还是大有文章可做,这当然也是中国的西方史学研究从总体上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 三、一章独特的中西史学交流史 现当代西方史学的发端,一般说来我们可以从19世纪90年代卡尔·兰普勒希特与兰克学派,亦即新旧史学之间的争论开始,这自然是不错的。(26)但学界大多忽略世纪交替之际西方史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那就是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召开。在我看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召开,或许可以作为20世纪西方史学的开篇与西方史学史上第四次重大转折的新路标。(27) 在此有必要简单梳理一下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历史。从1898年在荷兰海牙召开的预备会议至2014年即将在我国山东济南举办的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百余年间,二十二次大会(大体每五年召开一次),大致可分为三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为“创立时期”,从1898年的预备会议至1950年第九届巴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前;第二阶段为“发展时期”,从1950年第九届巴黎大会至1990年第十七届马德里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第三阶段为“国际化时期”,从1995年第十八届蒙特利尔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至今。(28)回顾历史,20世纪初开的这个会议,在当时并没有发生多大影响,但它伴随着时代的风云,且行且壮,终由淙淙细流演为波澜壮阔,成为当今国际史坛演变的一个“风向标”,瞭望西方史学发展变化的一扇窗。 是的,一百多年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的联系,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一过程与现代中国历史与史学相关,也与西方史学和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几个发展阶段联系,构成了一章独特的中西史学交流史,以下逐一说之。 1、在20世纪30年代里的初步接触,时值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创立时期”。其实,这一时期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还是区域性的,每届主题多以西欧地区的民族史/国别史为中心而展开,主办城市在欧洲范围内“轮流坐庄”,说它是西方史家的“自娱自乐”并不为过。 在这期间,1926年成立了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当时国人简称“国际史学会”),这个每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闭幕后的常设机构的建立,为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走上正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国际史学会欲想“跳出欧洲”,极力想在非欧地区发展新的委员国,中国自然成了它的“发展对象”。1928年初,国际史学会曾致函,邀请中国参加是年8月在挪威奥斯陆召开的第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当时教育部研究后回复称“本国拟暂不派员出席”,(29)不知何故?这就失去了一次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牵手”的良机,实为可惜。而此时,苏俄与日本均已是国际史学会的委员国(两国均参加了1898年的预备会议)。 八年后,1936年11月16日,时任国际史学会会长、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哈罗德·泰姆普利(一译“田波烈”,或“吞泼来”)在北京作了题为“致中国历史学家”的演讲。他这样称颂中国:“有一点可以肯定,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声称自己在思想和知识方面做出的贡献比中国多。中国吸收西方的知识,丰富自己不朽的传统,她一直很伟大。”(30) 泰姆普利鼓励中国应当融入国际社会,走向世界。于是,他进而指出:“中国仅仅发展和吸收西方的文化是不够的,她应该带着复兴的民族文化面向世界。每一个国家都应该有一个包含其文化的国际形象,就像它应该拥有一个包含其文化的民族形象一样。”(31) 最后,他诚邀中国加入国际史学会,并派一二名史家为代表参加1938年8月于瑞士苏黎世召开的第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如果中国敲了这扇门,我想她不用等太久就可以进来了,中国史学家的兄弟们,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机遇啊!”(32) 真是机不可失,中方作出了热烈的回应,即使1937年7月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时局动荡不定,参会的工作流程,也未受到任何影响。中方旨意已决,决定派胡适一人前往,代表中国参加了苏黎世大会,并发展成了国际史学会的新会员国。胡适忠于职守,以《新发现的关于中国历史的材料》(“Newly Discovered Materials for Chinese History”)为题向大会提交并报告论文,使这次在二战全面爆发前的苏黎世大会上,第一次听到了中国历史学家的声音。这是一页被尘封的历史,或许在胡适的总体研究中并不重要,但在中西史学交流史上却有着不凡的意义,值得我们予以重视。(33) 2、在50—60年代里的“藕断丝连”,时值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发展时期”。由于二战,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断了12年,直到1950年的巴黎大会才开始恢复正常的活动。此时,中国的政治编年史和中外史学交流史都发生了变化。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进程,也开创了中国史学的新篇章。从后者说,由于苏版马克思主义史学长驱直入,中国史学从“西化”演为“苏化”,至于西方史学的引入,当时采取了排斥与批判否定的态度,试想,在这种“文化语境”下,怎能再次与带有浓厚西方色彩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牵手”呢?是时,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行进,但中国却与之疏远,乃至陌生了。 然藕断丝连,在中外(苏)史学交流的夹缝中,还是能够捕捉到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点点滴滴: 比如张芝联撰文《介绍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34)篇幅虽短,但所披露的信息,却让中国学人知晓在国际史学界还有这样一个“世界性”的组织。 从苏联史学期刊,比如从苏联史学界权威刊物《历史问题》上译出了多篇文章,介绍在1955年罗马召开的第十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如上文引用过的潘克拉托娃的长文《第十届国际历史学家代表大会的总结》,还有零星的译文,都发表在当时中方创办的《史学译丛》上,(35)加上中译《苏联史学家在罗马第十届国际史学家代表大会报告集》一书等,(36)从中可以窥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动向,也许有限,但却是那“闭关锁国”年代里了解西方史学的一个重要途径,虽则可能是被扭曲了的西方史学,自然也包括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了解。不管怎样,它反映了中国史学界从20—30年代就萌发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情结”不断,这就不难理解中国改革开放伊始就与它重新连接了。 3、在改革开放年代里的重新连接,时值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发展时期”的后期及充满活力的“国际化”时期。正是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的春风,再次叩开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大门。1980年,中国派观察员参加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第十五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982年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重新接纳中国为委员国。从1985年开始,在每五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中国史学会都组团与会,都可在会场内外见到中国历史学家活跃的身影,直至明年,以东道国身份主办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那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展示自身形象的一个平台,更是我国历史学家向国际史学界展示华夏文化,以及渊源流长的中国史学自身形象的最好时机。 如今,当人们重新回眸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前世”与“今生”,蓦然发现,它于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开拓与创新,进言之,也与中国当代史学的行进,都有着非凡的意义。因而这章独特的中西史学交流史其重要性日渐显现,并应受到我们的格外关注。 四、余言 以上为20世纪中西史学交流史之三题,当可作为前几年发表的“两论”的一种补充。正文说罢,文末似有“余言”。这里,只说一点吧,即史学交流的基础。毋需多言,当然是交流双方的了解,倘双方互不了解,何谈对话,遑论沟通,于是任何形式的文化交流都是白搭,史学交流尤甚。 从大的来说,倘问中西之间,谁更了解对方?答曰:中国,至少在现当代。比如以译书为例,据有学者研究,20世纪英、法、德、意、西、俄六种文字在中国的翻译情况,统计结果共为100680册,而同时期西方诸国的中译本总共为800多部,于是统计者不由惊叹:“我们太了解西方了,而西方对中华民族完全是隔膜的。”(37) 还可再举一例。美国学者史景迁在《大汗之国》提到一个细节,说尼克松和基辛格当年到中国访问,在白宫的代号为“马可·波罗二号计划”,在他们看来这是继马可·波罗之后的又一次沟通东西方的“壮举”。如何看待这件事,论者分析道:“似乎更意味着时至今日,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仍然没有突破马可·波罗的眼界。这不是反讽,而是一个事实。如果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只是西方的文化想象,真实的中国则永远处在西方文化之外,只能是一个比想象更遥远的国度。”(38)上例似乎可以为此论作注。 当然,上述之见,忽略了时代与社会进步的因素,仅从互译的数字统计作结论,也许有以偏概全之嫌,似可商榷。不管怎样,现在重要的任务是中西双方在各个方面都需要加深相互了解,具体到史学交流也是这样。一方面,我们应通过多种渠道,对西方史学有一个真正的了解与研究,择其长处,以作借鉴,为我所用;另一方面,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任务是,让西方学界进一步了解中国和中国史学,以纠正他们对中国史学所留有的种种误解与偏见。这后一点,任重而道远,尤其是在从“史学大国”走向“史学强国”的进程中。然现实与未来的目标,总是不尽如人意。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的脚步总是跟在洋人后面,洋人“冲击”,国人“回应”,摆脱不了为西方“高人”“新说”做“小工”的下手角色,真令人有一种“骨化成灰恨未休”的遗憾了。面对这样的情况,当代中国历史学家,当志存高远,肩负时代的重任与历史的使命,拿出彰显中国史学特色的学术成果,在中西史学交流中出彩,在与国际史学的互动中前行,在重绘世界史学地图中给力。 注释: ①近几年,笔者曾主编《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著有《克丽奥的东方形象:中国学人的西方史学观》,专论近现代西方史学的入华及其对我国的影响(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②这类个案之作近二年有《域外史学在20世纪前期的中国回响》,《历史教学问题》2013年第1期;《二十世纪西方史学的中国声音——以近十年来青年学者的相关论著为中心》,《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7期;《1938年:中西史学交流史的一页——胡适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学术研究》2013年第10期;《希罗多德史学的东方形象——以近十年中国学者的相关论著为中心》,《甘肃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③这几篇专论依序为:《关于20世纪中西史学交流史的若干问题》,见瞿林东主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2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再论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史的若干问题》,《学术研究》2006年第4期;《中外史学交流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江海学刊》2008年第5期。其中两篇专论20世纪,一篇泛论。 ④居伊·布瓦:《马克思主义与新史学》,载《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1年第4期。 ⑤进一步情况,参见张广智:《珠辉散去归平淡——苏联史学输入中国及其现代回响》,陈启能、王学典、姜芃主编:《消解历史的秩序》,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⑥关于20世纪前期西方史学入华史,可参见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52—1949),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⑦[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⑧[法]保罗·利科主编:《哲学主要趋势》,李幼蒸、徐奕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42页。 ⑨[苏]A.M.潘克拉托娃:《第十届国际历史学家代表大会的总结》,陈敏、一知译,载《史学译丛》1956年第5期。 ⑩梁启超:《续日本书目志后》,《饮冰室合集》(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3页。 (11)张芝联:《从〈通鉴〉到人权研究》(代序),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版。 (12)张芝联:《法国年鉴学派简介》,《法国史通讯》1978年第1期。 (13)参见李勇:《年鉴学派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载入张广智主编:《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5—352页。 (14)参见王传:《华南学派探渊》,2012届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263页。 (15)笔者撰文《近代中国对基督教入华的回应——一项现代新史学的分析》,曾在1997年复旦大学召开的“中韩基督教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报告,引起与会学者的关注与讨论。拙文后刊发在《复旦学报》1998年第3期上,又载入《韩国研究论丛》(第五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再后,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宗教学》1998年转载。笔者之所以晒出这些,绝不是自诩,而在于说明一位西方史学工作者涉足中国史,并试图用西方史学理论来探讨中国近代史上的个案,在当代中国学术环境下所受到的重视与关爱,令我欣慰。 (16)伊格尔斯:《近十五年西方历史学的发展》,载《文史哲》2005年第4期。 (17)关于现当代的西方新文化史研究,可参看周兵:《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18)关于彼得·伯克的新文化史理念,可参见蔡玉辉:《每下愈况:新文化史学与彼得·伯克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又,伯克在南京大学接受杨豫教授的访谈,后由杨教授整理,以题为《新文化史学的兴起:与剑桥大学彼得·伯克教授座谈侧记》的访谈纪要,发表在《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1期上。 (19)彼得·伯克:《西方新社会文化史》,刘华译,载《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4期。 (20)这里的“精彩纷呈”系借用周兵一文的题目:《精彩纷呈的新文化史》,《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1期。 (21)埃玛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许明龙、马胜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22)(23)周兵:《精彩纷呈的新文化史》,《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1期。 (24)周兵:《新文化史的回顾与反思》,《历史教学问题》2013年第6期。 (25)转引自张仲民:《新文化史与中国研究》,《复旦学报》2008年第1期。 (26)参见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一章。 (27)西方史学史上五次重大转折说,见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第三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6页。 (28)参见张广智:《中国史学:在与世界史学互动中前行——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为中心的考察》,《文史哲》2014年第2期。 (29)《外交公报》1928年3月14日。 (30)(31)(32)刘鼎铭、林周佳、徐志敏辑译:《中国申请加入国际史学会及派胡适参会相关史料一组》,《民国档案》2007年第3期。 (33)关于胡适此次与会的相关情况,参见张广智:《1938年:中西史学交流史的一页——胡适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载《学术研究》2013年第10期。 (34)《历史研究》1957年第6期。 (35)刊发在《史学译丛》1956年第6期和1957年第3、6期。 (36)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出版。 (37)参见王岳川:《在文化创新中建立强国文化战略》,《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6期。上文所引数字,也是出自王岳川的统计。 (38)李勇:《比想象更遥远的国度——读史景迁〈大汗之国〉》,《文汇读书周报》2014年4月11日。标签: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论文; 年鉴学派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中外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新史学论文; 新文化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