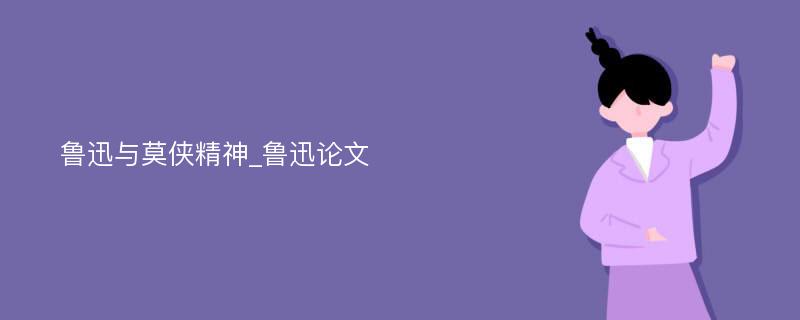
鲁迅与墨侠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即使是激烈的反传统者,不管其为思想家还是艺术家,都不可避免地属于传统,在传统中白手起家是不可能的,一个民族的文化遗留物总是决定、至少是影响和提示着后来者。这一矛盾可以从传统的构成中得到解释。传统是复杂的,可分解的,是多种思想体系和因素的混合物,按一定的高低秩序存在于典籍和(或)活社会中,而每一个思想家或艺术家都会在现实需要和个性气质的支配下从中做出选择,从而把自己和传统(其实是其中的某些部分)联结起来。在中国悠久的思想传统中,儒道两家一直在以研习经典为立命根基的读书人及其当政分子中占支配地位,它们是决定和代表统治阶级思想精神状态的上层文化,儒家思想同时塑造了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和伦理面貌。当二十世纪初人们一步步把中国贫弱不振的原因追问到文化层次时,儒道两家,特别是占主导方面的前者就在劫难逃,不可避免地承当罪责从而受到毁灭性的激烈攻击,它凝结为“五四”时一个简洁的口号:打倒孔家店。鲁迅在这一场批判运动中占据首要位置。被称为鲁迅小说总纲的《狂人日记》就“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①]这两者正是儒家思想的实践和社会衍生物。不仅进入民国后的每一次尊孔复古的浪潮鲁迅都有议论和抵制,他的离开绍兴进江南水师学堂就是对儒家经典滋养出来的人们的叛离和逃脱,“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②]。“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③]鲁迅的出走求学是有象征意味的,表现了他对正统儒家文化的失望和厌弃,显示出他的异端渴望。到了更加“异地”的日本,不料弘文学院的规章中对中国留学生竟有“凡逢孔圣诞辰,晚餐予以敬酒”[④]的要求。鲁迅回忆说,入学后不久的一天“学监大久保先生集合起大家来,说:因为你们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的孔庙里去行礼罢!我大吃了一惊。现在还记得那时心里想,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来的,然而又是拜么?”[⑤]这表明,鲁迅对儒教文化的失望和厌恶由来已久,并非突然产生于“五四”。如果说离开绍兴到南京进洋学堂仅出于感性的、朦胧的反叛冲动,到日本去则完全是明晰的理性行为,完全是出于对“孔夫子和他的之徒”的绝望,是一次文化叛逃。
与儒家思想互补共存同为中国读书人精神支柱或调节器的道家并不构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显性攻击目标,但其空疏逃避的思想倾向一再受到鲁迅的批判。阿Q的精神胜利法和道家思想有一定关联,或说是它的一个变种,都是对现实失败的心理“超越”。在鲁迅看来这是一种自我欺骗,实际问题解决不了,这种欺骗也是难以长久的。老子式的阴柔与鲁迅刚健爽利的性格相悖,其反对干预现实的无为而治的策略也和鲁迅积极地改造社会的思想背道而驰,他崇尚的是作用于现实的实际行动,“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⑥],鲁迅虽然绝望于孔夫子,但对儒家积极的入世态度还是首肯的。他说:“儒墨二家起老氏之后,而各欲尽人力以救世乱”。[⑦]又说:“老,是尚柔的;‘儒者,柔也’,孔也尚柔,但孔以柔进取,而老却以柔退走。这关键,即在孔子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老则是‘无为而无不为’的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⑧]。到晚年鲁迅仍有《起死》、《出关》二文,对老庄进行调侃,他对作为上层文化的道家思想的否定是终生不渝的。
对中国主流文化的否定和叛离使鲁迅必然向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支流认同,对主流文化来说,支流就是异端(后来接触的外国文化在性质上也是异端)。从官僚士大夫的儒道文化走向它们的反面,鲁迅几乎是不自觉地走进了两千多年间备受压抑和打击的墨侠传统,它们构成了鲁迅整个叛逆行为的精神基石,指导着他一生的行为,并在其著述中不时地显现出来。鲁迅对墨侠这种下层文化传统的接受是其天生秉性、个人遭遇、社会危机和时代趋势多重作用的结果。儒教文化的固有弊端当时已暴露无遗,成为反生命的文化僵尸;鲁迅的性格是质而烈,好动而真诚,与讲等级、禁锢、虚伪、冷酷的上层文化天生地不能相容,而平等、自由、真诚、仁爱的下层文化与其性格同质,其亲合力自然不言而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固然是1919年前后,但新文化运动主角的思想是早就奠定了。他们在文化上的总趋向是放弃和背叛他们的阶级和他们自己所秉承的垂死的士大夫文化,在各自不同的程度上向民间文化靠拢,去文重质,表现出鲜活的生命力。在文学上的表现是白话文、民谣体诗、小说由小道变正宗等等。
儒墨在先秦并称显学,且有社会目标的某种一致性。《吕氏春秋》说当时“儒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天下”。鲁迅也说:“孔墨都不满于现状,要加以改革”[⑨]。又说二者“各欲尽人力以救世乱”[⑩]。都是儒墨并称的。但到西汉,墨家已湮没无闻。虽然墨子也是儒者出身,虽然他也讲“仁义”,要“救世乱”,但墨子却是非儒的,因社会理想的根本分歧而和孔儒相对立。先秦非儒的学派并非墨子一家,但只有墨家真正代表了民间的、下层的、工农的思想和世界观,荀子就指斥墨学是“役夫之道”,在形成于秦汉两朝的政治专制和思想专制的格局下,和代表统治者利益、适合统治者要求的儒学对抗就是墨学一蹶不振的原因所在。事实上,在整个封建时代,墨学和居于正统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各方面都不相容,被视为异端。直到清乾隆年间,学者汪中因著《墨子序》还被斥为名教的罪人。对《墨子》的整理研究也只有晚清的两三家,历代注经大师对它都视而不见。
墨学的式微和儒学的被定为一尊几乎是同时发生的,而墨子精神的重新抬头和儒学权威的丧落也不分先后,两者互为参商。这决不是巧合。在封建专制等级制度的文化代表儒家被定为一尊时,体现科学逻辑和平民精神的墨家只能潜隐遁形,而当封建专制制度及其文化被挑战的时代到来时,墨家思想就乘潮而起,它的平等、博爱、科学、注重实际很容易成为新时代精神成长的根苗和一部分。做为新文化代表人物的鲁迅是重视墨学的,在其著述中,提及和引用墨家故事者凡十三见。《集外集拾遗补编》中有《〈墨经正文〉重阅后记》一文,说明他对墨子曾反复研读,更重要的是因秉赋上的暗合而对墨家精神心领神会,这自然具有了反封建文化的社会时代意义,做为古代文化的墨学和现代鲜活的心灵的要求交融为一。可以说,墨家思想是现代思想在中国本土的源头,做为异端,正好被不为正统文化拘禁的异端分子吸纳,形成对正统文化的时代性否定,虽然这一事实在当时没有形成明晰的理论话语。鲁迅思想行为的许多方面都可上溯到墨家,或说,和墨家精神遥相呼应。
反抗压迫伤害、追求诚爱自由贯穿了鲁迅的一生,这也是墨家宗旨和理想。等级是压迫的前提和保障之一,墨家倡导的“兼以易别”,爱无差等,不承认儒家对等级秩序的论证,墨子因平等兼爱的理想被儒家骂为“禽兽”,大概是禽兽不会像人那样自身分为权利各各不同的等级。鲁迅对人的被分为十等深恶痛绝,对它的为害认识得全面而深刻。《狂人日记》是为揭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而作,它们其实就是坚硬残忍的等级制度,这制度正是数千年中国历史的本质,鲁迅痛斥为“吃人”。《故乡》写童年时的朋友见了自己叫“老爷”,展示了等级制度在个体身上的发育过程。童年人处于“自然状态”,没有等级观念;成年后就进入了“文化状态”,领会和接受了自己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而这无疑是鲁迅最感悲哀和痛心的,他说:“别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这就是我们古代的聪明人,即所谓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说是高下各不相同。其名目现在虽然不用了,但那鬼魂却依然存在”[11]。他又说:“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12]隔膜和凌虐是等级制两个相互关联的后果,更为严重的是人们对这种无自由、不平等、互不关心痛痒的事实默默承认,不思改变。鲁迅于是发为大声疾呼,号召掀掉这吃人的筵席,诅咒这罪恶的现状。
由于能深切感受到被压迫和侵凌的痛苦,痛恨这种现实,于是起而为弱小者呼吁,为弱小者抗争,对象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国家,这一点几乎和墨者等同。墨子历尽艰辛劝阻楚王攻宋是为弱国小国请命,鲁迅在从事文学活动之始就有意识地介绍东、北欧被压迫民族的作品,传递反抗和痛苦的声音,其直接目的自然在警刺中国的国民,但其精神根基都在为所有遭压迫的弱小国家呐喊,鲁迅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的胸怀是博大的,爱是普施的。曾经使他激昂不已的英国诗人拜伦,与其说是因为他的诗,不如说是因为他亲自支援希腊抗击土耳其侵略的正义行为,这和墨子在楚宋间的外交努力也是大同小异。进化论论证生存竞争中强胜弱汰的自然性,鲁迅的思想却有明显而强烈的道德主义倾向,一生都在抗拒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与进化论冷漠的科学规则比起来,鲁迅的胸中沸腾的是一腔诗人的热血。
儒墨两家都讲“仁”,但儒者之仁建立在等级差别的基础上,无法彻底,最终流为空谈;墨者之仁则是无条件的,因而才可能是真正的仁。鲁迅体现的是墨者之仁。许寿裳说:“鲁迅是大仁,他最能够感到别人的精神的痛苦,尤其能感到暗暗的死者的悲苦。”[13]周晔在讲到鲁迅和周建人救治被玻璃扎破脚的车夫一事时说:“伯父严肃的容貌仪态中,却有一颗天下至仁至爱的心。他的心,他的血,他的情,是如此的热切,如此的真诚”[14]。许寿裳也说,鲁迅的“举动言笑,几乎没有一件不显露着仁爱和刚强”[15]。这也几乎是对墨子的概括了。鲁迅的大仁大爱直接决定了他的职业选择。他“原来到日本去学海军,因为立志不杀人,所以才弃海军而学医。后来因受到西欧革命和人道主义思潮的影响,思想起了变迁,又放弃只能救个人和病人的医学而改学文学。”[16]许寿裳的解释更切本质,“他的学医,是出于一种尊重生命和爱护生命的宏愿,以便学成之后,能够博施于众。他不但对人类的生命,这样尊重爱护,推而至于渺小的动物亦然[17]。他的改学文学不过是因为他觉得人的精神的疗效更迫切更重要罢了。
利他主义和自我克制(禁欲)是墨家道德的核心,他们总是在为别人忙碌。上述社会使命的承诺无疑是利他主义,在家庭生活和社会交往方面鲁迅都表现出这种精神。他对老母的孝爱,对兄弟的关心,家庭生活中的迁就,对朋友和青年的帮助,都是忘我的,近于极限的,完全是一个四处奔波努力的墨者形象,虽然受惠者当中常有背叛他和得寸进尺者。对自己,鲁迅却表现出明显的禁欲主义色彩,衣食住行皆不讲究,简朴得超过一般人。关于他的衣着有许多回忆的描述,和他在《非攻》中对墨子衣着的描述所差无几。民元前在杭州,“衣服是不讲究的,一件廉价的羽纱——当时叫洋官纱——长衫,从端午前就着起,一直要着到重阳。一年之中,足有半年看见他着洋官纱,这洋官纱在我记忆里很深”。[18]许寿裳说:鲁迅在南京时就是“夹裤过冬,棉袍破旧得可怜,两肩部已经没有一点棉絮了”。“杭州教书时,仍旧着学生制服,夏天只做了一件白羽纱长衫,记得一直穿到十月天冷为止”[19]。鲁迅在广州时的形象是:“穿蓝布或黑布长衫,穿那种叫做‘陈嘉庚’的帆布胶底鞋,抽比‘美丽牌’还便宜一半,一毛钱二十根的廉价‘彩凤牌’香烟,胡子长长的,头发也是长长的,几个月也不理一次发,好像是一个乡下老头子。”[20]还有一则回忆说:“一般道学先生比不上他的朴素”,“他却与普通人一样的,穿的是小袖子的长布衫,橡皮底的布鞋;头发好像没有多余的时间常理似的”[21]。这后一句和鲁迅在《非攻》中写的墨子对自己衣裳的说明几乎只有文字上的差异。
鲁迅的住行怎么样呢?“鲁迅先生家里,从楼上到楼下,没有一个沙发,鲁迅先生工作时坐的椅子是硬的,休息时的藤椅是硬的,到楼下陪客时坐的椅子又是硬的。”[22]]在北京时期,鲁迅生活也极为简朴,睡硬板床,褥单被薄,冬天穿得也罕见地少,当时有人自作聪明地下结论说,这是为了压抑性欲,这一显然受到弗洛伊德影响的简单化的论断没有考虑鲁迅一贯的自苦背后深刻的文化原因。中国人有一种传统认识,认为艰苦生活的磨炼能使人意志坚强、抱负远大,舒适的生活却足以销磨人的意志,鲁迅既有救苦救难的大心,也就有意地过艰苦生活,虽然这样做是反本能的,因而需要极大的毅力。与拒绝物质享受相关联,鲁迅一生极少游玩,这不仅因为游玩不是正经事,浪费时间,更因为游玩是一种享受,是一种放松,它会使人软弱,意志松弛。许寿裳说:“鲁迅生平,极少游玩。”[23]]萧红说:“鲁迅不游公园,住在上海十年,兆丰公园没有进过,虹口公园这么近也没有进过。”[24]川岛记录了鲁迅对西湖美景的看法:“至于西湖美景,虽然宜人,有吃的地方,也有玩的地方,如果流连忘返,湖光山色,也会消磨人的志气的。”[25]这说得已经极为明白。墨家都是一些有非凡气质的人,几乎反对任何享受,生活有如教徒,被认为“俭而难遵”[26],鲁迅的弃绝享受,艰苦俭朴,同样让人望而生畏。
鲁迅在价值观、思维特征以及文风等方面也上承墨学。墨家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完美结合,他们为理想奔走奋斗,同时又清醒地面对现实,丝毫不幼稚虚妄。《墨经·大取篇》说:“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非取害也,取利也”。这一思想被鲁迅多次引用,他看到世界的不理想,但却要积极努力在其中做到最理想。鲁迅的心灵是理想主义的,理想是现实主义的,他是两者共有的典范。墨家在学术上以论辩逻辑的严密著称,还是专门从事思维科学研究的学派。他们最不感兴趣“文学性”,文字质朴平白。鲁迅是文学家,自然有其文采丰瞻的一面,但鲁迅最擅长最注重的是写杂文,这种文体具有春秋战国散文之风,富于强烈的论辩性,鲁迅爱以杂文笔法入小说、散文,他甚至说:“就是我的小说,也是论文,我不过采用了短篇小说的体裁罢了。”[27]]“议论”居鲁迅著述目的的中心位置,其逻辑的严密和说理的透辟为世所公认,因此在思维特征上明显是墨家一派。即使是艺术趣味和偏好,也可以把鲁迅附会为墨家。和其它方面一样,鲁迅在艺术趣味上也具有反上层反士大夫的强烈的民间倾向,相当接近墨家,他这种反儒道上层文化的其它表现出于同一心理根源。鲁迅的“反叛”是深入到审美层次的。墨家崇实尚质,几乎要抛弃形式,鲁迅毕竟是艺术家,不可能这么极端,但他确实不爱精细的巧滑的装饰风格,偏爱粗朴本色。他的小说整体上“以质胜文”,有些小说如《阿Q正传》甚至有筋骨裸露之感。鲁迅喜爱质拙的汉代碑刻,不依赖色彩的版画,没有背景的粗质社戏,只求传神的线画等。鲁迅在《苏联版画集》的序文中说,那些作者“没有一个是潇洒,飘逸,伶俐,玲珑的。他们个个如广大的黑土的化身,有时简直显得笨重……我们可以看见,有那一幅不坚实,不恳切,或者是有取巧,弄乖的意思的呢?”[28]]儒家精神是破坏艺术的,它贡献于中国艺术的是趣味和评判上的崇古。墨家根本上“非乐”反对人的审美享受,同样有碍于艺术的发展,墨家根本没有“文人趣味”,以道家精神为重要基质的文人文学艺术本质上是和墨家对抗的。鲁迅当然不是百分之百的“墨”,他并不反对艺术,只是有所选择和偏重。诗是中国传统文学的代表,最能显出文学的特征,但鲁迅说:“我是散文式的人,任何中国诗人的诗,都不喜欢”[29]。这大概是因为诗表现的是上层文化情调,且有形式的束缚。鲁迅对古老的楚辞倒是情有独钟,并且深受其影响,需要注意的是,楚辞不属于儒道文化传统,它传达的是更加原始的浪漫精神,这种异端性可能正是它受到鲁迅喜爱的原因。从学术研究的兴趣和选择上也可以看到他对下层文化的靠拢。他搞古小说钩沉,撰中国小说史,而没有去治诗史或散文史,是有深刻的个人气质和文化精神的原因的,因为小说是俗的、民间的,为士大夫所不齿的文学。并非仅仅因为小说自古无史、去填一个空白。
墨家的行为含有天然的侠义,比一般的侠更高尚。孙诒让《墨学传授考》说墨者“勤生薄死以赴天下之急。”鲁迅在《三闲集·流氓的变迁》中也说:“墨子之徒为侠”。可见墨和侠的关系,但墨侠并不是同一事物。墨家做为一个学术流派,其思想有它的阶级基础和社会使命,行动思想并重。墨子后学有所分化,“一派趋于思维规律的专门研究,成为先秦名辨思潮的重镇;一派变为社会运动的游侠,推行墨子的宗教思想。”[30]这后一派就与侠合流,虽然他们比非墨的侠更有思想根基和明确的行动目的。一般的侠要更零散自由,任性而为。它也不是一个学派,没有思想体系,更具有人性的本能色彩。墨家的思维科学和兼爱思想长期断流,倒是其中侠的部分随非墨的武侠阶层生存下来。侠更多的是一个气质共同体,这气质就是侠气,其行为模式和道德情感也一代代沿袭,成为几乎历代都有的特殊社会阶层和几千年未断的精神传统。侠的成分极为复杂,侠的行动目的也千差万别,并不是为下层阶级服务的,但侠的暴力色彩和个人英雄主义都冲击着现有的社会秩序和官方权威,因而历朝历代都备受打击,使它成为和上层正统力量对立的民间文化和阶层。儒道是成人的文化,中国社会是成人本位的社会,而侠文化则是中国孩子的文化,这也是一种“下层”。虽然侠客不专为百姓办事,但体现在正面侠客身上的急人所难、尚武好斗、睚眦必报等性格精神确能为处于政治及恶势力重压下的下层民众所醉心和向往,以至剑侠被称为“佩剑的民间神”[31]。鲁迅是从上层文化反叛到下层文化的典型。有学者说:“如果说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中都隐隐约约地深藏着儒的影子,那么,中国民间社会平民百姓的内心深处则忽隐忽显地闪动着侠的影子。”[32]鲁迅身上存在的儒家气质确实不浓,侠的风采则十分触目,成为这种文化反叛的证据。
少年时代的鲁迅就爱打抱不平,表现出好斗的、仇恨欺凌的正义性格,而且常常把内在的侠气付诸实践,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绍兴城里有一家叫广思堂的书塾,塾师外号“矮癞胡”,极会体罚学生,打手心时手背要顶着桌子角,撒尿还得从他手上领一枝竹签,还常常罚跪,三味书屋的学生鲁迅就带人去“管闲事”,砸砚折签,尽兴而还。在这前后,鲁迅又听说附近的一个贺姓武秀才欺负过路的小学生,就约一帮人去教训他,这位十四五岁的少年为了战胜那个武秀才,还别了一把腰刀在大褂下,那天,秀才没有出来应战,也算不战而胜。这时的鲁迅简直就是少年武侠的形象了。在南京读书期间,鲁迅依然侠心如故,不仅喜欢骑马,而且自取别号“戛剑生”,并刻有“戎马书生”、“文章误我”的印章,足见他对传统儒生角色的不满和对武功的渴望。鲁迅的舅父曾受人讹诈,鲁迅只身赴会,解救舅父于危难,他的胆气使对手不敢露面,更是侠客风范。杭州打击夏震武的“木爪之役”,北京女师大风潮中和校长杨荫榆乃至教育总长章士钊的对抗,这些举动都不是为他自己,而为别人,为一种原则,为正义,表现出的是侠肝义胆,无私无畏。鲁迅的性格中还有记仇的一面,有仇必报,决不宽恕,其程度超过一般人。而儒家讲恕道,道家等是非齐万物,无法提供复仇的教导和理论根据。
对侠的崇尚和向往也不时表现在鲁迅的著作中。在早期的论文中,鲁迅就极力赞扬反抗叫喊,破坏既有秩序的摩罗诗人,已经揭开了“五四”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的序幕。《女吊》等散文赞美复仇的意志,说女吊是“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在小说《铸剑》中直接描写了山中侠客帮助眉间尺而自我牺牲的壮举,也褒扬了眉间尺的复仇精神,他们热得发冷的性格也很像作者。
杂文是鲁迅性格和作风的主要体现者,而他把他的杂文称为“匕首”,珍爱它就像他钟爱钢铁的剑,那是他常提到的,还说这匕首是“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33]。郁达夫评论说:“鲁迅的文体,简练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重要之处,抓住了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点破。”[34]这指的就是他的杂文。当他已不可能真的去仗剑行侠时,鲁迅显然找到了他得心应手的替代方式,就是用笔代剑,去行侠,去刺杀,就像他的同乡秋瑾的以剑代笔一样。这位文坛的侠客用笔的利剑刺开的不是人的血肉身躯,而是人的灵魂:文化和社会的肺腑,在鲁迅的匕首前,它们皆无从遁迹,真是“利剑手中鸣,一击两尸僵。”[35]
鲁迅与侠的姻缘同样是他刚强好战的性格被侠文化孕育的结果,也得益于地域的民风和时代气氛。侠的传统一方面被闾巷少年一代代实践着延续下来,发挥着人固有的原始的野性,同时也通过书面方式影响着少年和成年人。中国文学中有大量歌咏侠气和游侠的,鲁迅自是耳濡目染,他十岁时已接触了《剑侠传图》等图书,《山海经》中无头“而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执干戚而舞”的刑天的故事也使鲁迅神往并受到影响,这影响当然来自两者的同质性,鲁迅喜欢“金刚怒目式”,喜欢“扬眉剑出鞘”,所以和朱光潜尚静穆的古典主义和新月派的柔和洒脱的绅士风度总是无法相容,这是秉性使然,也是文化性格和系统的冲突。鲁迅和墨子一样厌恶上等人和他们的文化。
鲁迅对侠文化基本精神的认同和侠性的养成也与浙东地方文化的遗传和时代风气密切相关。绍兴地方民气强悍坚韧,善于报复,充满内在力量,绍兴师爷的阴狠全国闻名,是这种民风的一种表现。明季的王思任说:“夫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也”。这句话鲁迅在书面言论中曾引用三次。在散文《女吊》中引用了王思任的这句名言之后,鲁迅接着说:“这对于我们绍兴人很有光彩,我也很喜欢听到,或引用这两句话。”[36]这两句话简真就是对侠的一个侧面的概括,因为仗剑复仇乃是侠的基本形象之一。到1936年春,鲁迅还在一封信中说:“身为越人,未忘斯义”[37]。他在《女吊》中也说“女吊”是绍兴人的创造,是一个“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女吊是绍兴民气和地方文化的产物,鲁迅醉心其“强”和“复仇性”。大概正是由于这种地方性格,晚清的排满运动首倡于浙江,以至形成光复会,这是一股民族性的复仇思潮。在这场运动中,绍兴一带出了不少革命家,佩剑的秋瑾便是他们的代表。这批人是民族革命的斗士,是超越通常侠客的,但侠的气质则是他们政治活动的心理基础,身上表现着明显的侠气。鲁迅正是这群体中的一员。
侠的构成和行为极为复杂,有的急人所难,有的鱼肉乡里,有的代父报仇,有的充当杀手。虽然它具有“有血性、重信义、轻名利、逞意气”[38]的品质,虽然抽象的侠义是可嘉的,是社会所需要的,但若导向不对,就会成为破坏社会的力量,任侠变成犯罪行为。“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与正义无关。从社会的角度看,这种诉诸武力的个人行为只能扰乱社会。身赋侠气的鲁迅对侠这个阶层却颇有微辞,他注意的是侠的一种堕落的倾向,是侠在官方压力下的变质。鲁迅说,老实的侠“逐渐死完,止留下取巧的侠,汉的大侠,就已和公侯权贵相馈赠,以备危急时来作护符之用”[39]。这是鲁迅所蔑视的。更加不堪的是侠的沦为强盗和奴才,“‘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40]。最后梁山好汉被招安,“终于是奴才”[41],和后来《施公案》、《彭公案》中的侠客已没有大的不同,只是后来的黄天霸之流奴性更足罢了,这其实是对侠的背叛,是侠义的消失,鲁迅的批判倒是对侠义的坚持。事实上,由于侠客和侠行从来都是复杂的,能够始终以暴抗暴,维持意志和人格的独立和自由的侠只是侠的一部分,鲁迅肯定和钟情的是这类侠的品格。鲁迅厌恶等级,厌恶上等人,为他们利用和服务的侠自然就在摒斥之列。这仍然证明了,文化的承传和接受是选择性的,这选择决定于接受者的性格、观念和理想。
注释:
①《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②《朝花夕拾·琐记》。
③《呐喊·自序》。
④细野浩二《鲁迅的境界——追溯鲁迅留学日本的经历》,1976年(日本)《朝日亚洲评论》冬季号。
⑤《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⑥《华盖集·青年必读书》。
⑦ ⑩《汉文学史纲要·老庄》。
⑧《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
⑨ [39] [40] [41]《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11]《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12]《坟·灯下漫笔二》。
[13] [15] [17] [19] [23]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
[14]周晔《伯父鲁迅二三事》,《鲁迅回忆录》,第321页。
[16]尚钺《怀念鲁迅先生》,《鲁迅回忆录》二集,第189页。
[18]夏丐尊《鲁迅翁杂记》,《我心中的鲁迅》第22页。
[20]欧阳山《光明的探索》,《我心中的鲁迅》第96页。
[21]俞念远《我们记得的鲁迅先生》,《我心中的鲁迅先生》第83页。
[22] [24]萧红《回忆鲁迅先生》。
[25]川岛《忆鲁迅一九二八年杭州之游》,《鲁迅回忆录》第255页。
[26]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
[27]见冯雪峰《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我心中的鲁迅》第162页。
[28]《且介亭杂文末编·〈苏联版画集〉序》。
[29]《书信·350117致山本初枝》。
[30]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第197页。
[31]陈山《中国武侠史》第6章。
[32]同上“引子”。
[33]《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
[34]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
[35]曹植诗句。
[36]《且介亭杂文末编·女吊》。
[37]《书信:360210致黄苹荪》。
[38]同注[31]第30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