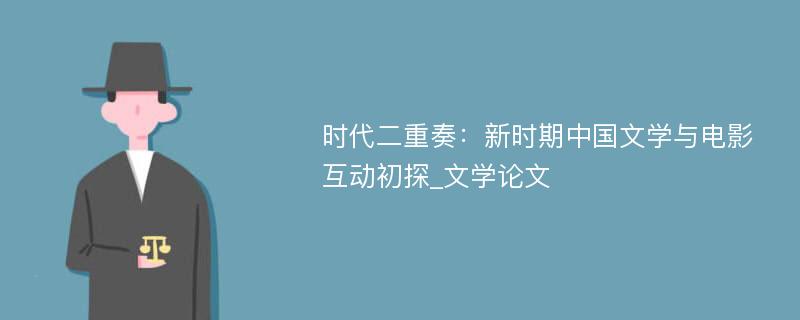
时代的双重奏——初探新时期中国文学与电影的互映互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论文,新时期论文,中国文学论文,时代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1)01-0096-05
跨过千年之交的“临界点”,我们已经踏上21世纪的征程。回顾中华民族半个世纪以来的沧桑步履,从满目疮痍到百废俱兴,从僻远的“边城”走向世界,从闭关锁国妄自菲薄到融入国际化现代化的时代滚滚洪流,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改革和“嬗变”。在这样一个大变革的年代,随着经济结构全面转型,人们的价值观念、社会理想和生存方式也遭遇了全方位的解构和重组。在世界商业化大潮的驱动下,实用功利主义原则正以强势话语姿态渗透到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一切现实领域之中,市场经济原则主导着文化生产与消费的走向,生活的平面化、空虚感逐渐加强,消解了意义的感官享乐和无端消遣在商业化的语境中愈加变得理所当然。
我们把对艺术本文的理解和探索建立在历史本文基础之上,将具体的考察界定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中,无疑更有利于实现文化叙事语境与社会历史语境的重合,从而发掘艺术本文中所蕴含的时代精神和历史深度。笔者在本文中将中国文学与电影二者“提炼”出来加以解读,并非是要汇总新时期内中国文学与电影之概状,而是试图在将二者联系起来进行交叉阅读的过程中,梳理整合二者之间互动互映的关系,从而找到这一时代历史语境下文艺领域里存在着的带有某种普泛性的“契合点”。
一
文学、电影在世界范围内的双峰对峙局面由来已久,而且早在半个世纪以前的默片时代这种抗争就已呈现出强弱分明的态势。在20世纪末期的二三十年时间里,更是出现了电影宰制文学、文学受制于电影的局面,文学做为艺术宝殿中最神圣最富光彩之堂奥的辉煌时代已不复再,一派喧嚣之中的电影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了世界文化的主流。作为众多艺术发生发展“母体”的文学,在电影狂疾迅猛的发展势头面前,就好像目睹自己亲手育养的尚未成年的小孩突然间不顾长幼尊卑与自己进行直白而“蛮横”的对话,一时间惊奇万分而又无可奈何。而“在电影诞生之前的时代,恰恰是文学成为主导艺术形态,只有文学能够最充分地反映异常复杂的生活矛盾,满足更加广泛、更多层次、‘多声部’地把握现实的迫切需要”[1]。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敞开国门迎接世界浪潮的中国,汹涌的商业化洪流挟带着无往而不胜的气势裹卷了人们的思维观念,个人的生存状态乃至整个社会的行为模式都遭遇了一场“脱胎换骨”的改造。理想淡漠、信仰阙如成为时代特征,人们削平深度的思想只迎合于具有现实操作性的功利性藉口。在快节奏、高效率、讲求实效的生活模式里,需要用“心灵的眼睛”去细细品读的文学作品仿佛成为了供奉在象牙塔里的宝藏一般难以企及,而大众更倾向于喜爱用“肉眼”就可以看到的影视作品,不需要费力思索,放弃精神层面的积极参与,只需要机械地理解和认同,从而在一种便捷而直接的条件下完成审美体验,让在忙碌的工作生活中紧绷的神经和疲顿的身体得到暂时的轻闲与休憩。于是,中国自先秦以降民间大众积极参与文学创作、关注文学的传统在当下的现实语境中幻化成一个模糊而遥远的标识,曾经在中国文化史上撰写了壮丽篇章的诗歌日渐衰微、少人问津便是明证;散文跨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有复兴之势,但在更大程度上这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化现象,掺杂了诸多非文学因子及现实因素。唯有小说,自80年代末以来不但毫无衰颓之态,竟还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与生机(据有关统计显示:90年代出版的长篇小说超过2 500部,等于建国初期17年320部的8倍之多),以致于它事实上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文学的最后“壁垒”。思想禁锢的放松,现实生活的纷繁复杂、动荡变迁以及对社会历史本文的多元理解固然是“小说热”勃兴的有效催化剂,然而我们同时也应当看到:这种现象的生成,与当今作为主流文化的电影也存在着不可抹煞的深刻关联,而且这种关联实际上已经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孕育和演变。
“一个电影导演是可以从崇高的文学典范中学到很多东西的”,“伟大的文学所积累的经验能够帮助我们电影工作者学会怎样深刻地去研究复杂多样的生活”[2]。巴赞也说过:“电影是年轻的,而文学却同历史一样古老。”电影自诞生之日起就与文学缔结了亲缘关系,首先从二者的艺术本质来看,文学中的小说属于民间文学样式,不管是汉代的神话故事,六朝的志怪小说、轶事小说,唐传奇,还是宋元话本小说,明清章回体小说、拟话本小说,其产生、发展、繁荣都离不开民族文化沃土,与平民大众、市井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而电影则更是一种典型化的大众艺术,直观演绎的具体操作形式决定了其不可能摆脱世俗大众力量的左右,特别是在成为“文化工业”的一种“产品”之后,与市场反响、经济收益的直接挂钩更使电影艺术无可避免地展现出迎合大众口味的世俗化倾向。艺术本质的暗合,则成为二者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内在基础。其次,从艺术表现技巧的层面来考察,电影与小说同属叙事艺术,都可以采用各种组合切割的叙述方法,法国评论家埃·马格尼在《电影的美学和小说的美学比较》一文中曾指出:“电影和小说二者均为叙述作品,叙事有它自身的规律,与展示的规律有很大的不同,它的基本要求之一是连续性,小说的各种程式和电影的各种常规技巧大抵是为了保持连续才产生的。”电影诞生初期所带来的强劲观念冲击和视觉新鲜感日渐消隐之后,单纯的影像愈来愈无法满足社会生活多元化和艺术陌生化的要求,因此向文学尤其是现代派小说借鉴叙事技巧成为了电影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必要手段。同时,电影中成熟而严密的蒙太奇结构也给予了小说创作相当程度上的启发,二者在“技”的层面上也的确是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再次,站在艺术客体受众的立场上来讲,削平深度、消解形而上意味的庸常生活让人精神靡顿、身心疲乏,潜伏在内心深处的审美欲望及人文理想在平面化的单一生活模式里找不到寄托对象而倍受压抑,这种不受理性支配的“无意识”(弗洛伊德语)往往就只能通过梦幻的形式才能得以表达和释放。而以虚拟叙事为基本特征的小说和电影恰好可以承担起这项“制梦”的责任,二者通过尽情的想象和大胆的虚构编织出形形色色、五彩斑斓的“白日梦”,以求最大程度上满足人们各式各样不同程度的精神愉悦和情感满足。这种使命的同构性便成为了文学与电影实现交流沟通的现实基础和客观前提。
然而,自本世纪中期电影被时代潮流推上文化前台之后,它便俨然以一种成熟的姿态强烈要求彻底摆脱这种依赖性而实现形式上的完全独立。但正是由于电影与文学艺术内在特质上的上述种种关联决定了二者不可能“划清界限”,于是电影不得不放弃了这种努力而转换为以一种恃强凌弱、居高临下的话语姿态来标榜自身的“价值”与“尊严”。与此同时,最初对电影文化的张狂持抵制态度的文学界也逐渐从对影视文化大潮的观望转为默许进而主动顺从。一方面,电影因其大众化娱乐的特质无疑相对文学而言有很大程度的功利上的“优势”:它能使艺术转变为一种产业,更加符合商品社会的运行法则,能更快更直接地使文化产品转换成实质性的利益。另一方面,在“王朔现象”的刺激下,一直对商品经济持保守观念的艺术家们终于按捺不住“闺房”寂寞之苦,纷纷带着尴尬的微笑向电影圈靠拢。作家可以借助电影哄抬身价,小说也因为被改编成电影作品而倍受青睐,更重要的是,与电影的“结缘”可以直接换取相当程度上物质利益的满足。因此,只能甘当“阳春白雪”、“象牙玉器”的诗歌、散文自然为艺术家所“忍痛割爱”,而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则由于其故事性、可读性,特别是改编成电影剧本二度创作的便捷性而成为大家竞相追逐的“猎物”。此种境况直接导致的后果有其积极意义亦有令人忧虑的一面。作家的关注和参与无疑使电影拥有了更广阔的选择余地和更大的发展潜力,必然导致电影作品题材及思想上的相对丰富和深刻;而与电影的“结缘”又显然有利于文学借助时代潮流的伟力而重现昔日耀眼的光辉,电影所特有的蒙太奇叙事理念也大大促进了文学形式探索的步伐。然而,由于一些小说家向影视“看齐”的愿望过于迫切,以致于他们中间有相当一部分进行的已并非纯文学意义上的艺术实践,而是在创作中刻意追求故事的新奇和形式的精巧,为了引起导演的青睐和世俗的轰动效应而不惜标新立异,诱人“伎俩”变幻莫测、层出不穷。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许多曾经极富才华的作家自从到影视圈“镀金”一遭尝到甜头之后,他们往后的作品都明显地透露出某种影视“信息”,更像只要稍事改动就可以搬上银幕(荧屏)的“影视脚本”,体现艺术生命力的个性风格、主体意识则一步一步淡漠、褪隐。这不能不说是90年代乃至整个新时期中国作家群体的一种悲哀。
二
可以这么讲,电影与文学的亲缘关系早已是不争之事实,而文学向电影的倾斜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受市场经济潮流驱动所致。这两种结合的意义不尽相同,前者属隐性阶段,文学作为一种被描摹的客体纯粹站在被动或者说是不自觉的立场之上;而后者则属显性阶段,不仅二者之间的衔接更为紧密,更为“和睦”,而且二者都是前所未有地能动积极地参与到结合当中来。从隐性阶段到显性阶段的变迁在经历了文革浩劫后的中国找到了契机,而这种变迁在新时期20年时间里也呈现出某种渐变的趋势。最初一段时期里,为突破原有的艺术禁锢,电影从文学(主要是小说、诗、戏剧)中汲取经验,与文学思潮合流,创作出一批当时令人耳目一新的电影作品,如从“伤痕文学”“嫁接”而来的《天云山传奇》、《人到中年》,由张弦婚姻爱情题材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等。然而由于某种沿袭已久的美学观、价值观和思维惯性使然,这一时期的电影与文学同样未能彻底摆脱“题材决定论”的纠缠,其艺术探索仍旧明显处于稚嫩的阶段,也并没有在对电影本体艺术特性的认识和开掘上更进一步。而电影与文学的结合也由于仅仅出自前者的“一厢情愿”而变得软弱乏力。电影要突破“临界点”实现“飞跃”,要在与文学的对话中重拾话语权力、占据强势地位,呼唤着一批具有使命感的艺术家的诞生。我以为,这样的一个群体恰恰在80年代后期这个于中国文化而言举足轻重的时期应运而生,它用积极求索、勇于创新的精神回应着时代的呼唤,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高扬电影本体意识、振兴民族电影的责任。这个群体指的就是声名显赫的“第五代”。
以陈凯歌、张艺谋、黄建新、吴子牛、周晓文等文革后北京电影学院首届毕业生为骨干的“第五代”导演群体所创建的卓越功勋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作为中国电影界第一次高度自觉的艺术运动,它在中国乃至世界影坛激起了持续高涨的狂澜。这一批才华横溢、具有独创性思维的艺术家“用惊世骇俗的电影语汇,宣告了一个与世界文化发展同步的中国电影的开始”[3],并使中国电影在一系列国际电影节中连连摘桂捧杯而回,在真正意义上使中国电影走向了世界。“第五代”的辉煌,其丰富的人生阅历、优秀的专业禀赋以及时代赋予的开放性思维模式无疑出力不小,然而我们同样不应回避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所创造的一大批题材、风格各异而审美取向相似的电影作品中,其“经典”之作几乎全部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来。“第五代”发轫之作《黄土地》其母本为柯蓝的散文《深谷回声》;张艺谋成名作《红高粱》由莫言同名小说改编而成;张军钊《一个和八个》源于郭小川同名叙事诗;张贤亮《浪漫的黑炮》脱胎而成《黑炮事件》;吴子牛将乔良的《灵旗》重事组合而成《大磨坊》;刘恒《伏羲伏羲》改编成《菊豆》;史铁生《命若琴弦》改编成《边走边唱》;陈凯歌巅峰之作《霸王别姬》也是由香港作家李碧华同名小说改编而来……
以“第五代”导演为代表的一批中国电影艺术家对文学所抱有的关注,切实地体现为其作品中从题材、主旨到表现方法、叙事技巧等等“细微”之处都明显地展露出鲜明的文学色彩。他们热衷于将一些体现时代思潮、反映审美风尚、挖掘民族文化积淀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加以“雕琢”后搬上银幕,小说原著的基本题材及整体叙事框架得以保存,影片的思想倾向仍与原著维持相当程度上的一致性,但又由于附着了导演强烈的主体意识和主观艺术体验而呈现出与原著不尽相同的艺术风格和个性色彩。作家进行文学创作时对思想内涵的铸造无疑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心血,他们的情怀心智时刻关注着民族命运和现实人生,往往在作品中能鲜明地体现特定时代的民族生活特征和时代情绪,这对于电影创作的取材以及思想具有旗帜鲜明的指导性意义;而文学本身臻于完备的丰富表现技巧以及以语言为载体带有极大自由度和伸展性的内化创作特性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电影加以借鉴的源泉,例如:电影从现代小说中引用了“意识流”、“零度叙述”、“生活流”等大量叙事技巧,从而使其本身拥有了更多形式创新的可能,也拥有了更丰富、更深刻的生活内涵。正是这种与文学从内容到形式全方位的“并轨”,成为了新时期中国电影从荒芜走向喧嚣的一个主要动因。
电影在文学作品的原有模型上进行二度创作,显然有利于导演十分便利快捷地汲取文学原著中的“菁华”,在文学作品现成的完好构筑基础之上,只需朝个人主观思维及艺术感觉的方向上作一些“无关大局”的取舍和改动后再将其转化为直观的电影语汇,从而大大约化了从构思到实际拍摄之间能动的艺术创造过程。如此一来,电影从底本变成拷贝周期的相对缩短无疑有利于电影作为一种商品能以较高的生产速率投放市场加速流通,更符合“电影产业”的运行法则;而电影对文学具有明显依附关系的事实又使电影本身时刻追随着文学的步伐和视域,从而能站在时代思潮的前沿高地,以更深邃透彻的目光来感悟人生,瞻望民族的前途命运。我们在这里还可以发现一个看似悖论的有趣现象:标榜形式独立的电影向文学靠拢其初衷显然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现实功利性,然而与文学的“接轨”又反而使电影作品的思想蕴涵和艺术品味大大提高,特别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多元并举、百花齐放的繁盛局面对中国电影整体水平的提升起到了直接的催发作用。正是由于时代的文学为其提供了再创造的诸多可能性,新时期才有众多优秀中国影片的诞生和风行;倘若没有文学的“支助”和参与,它们确实“大多数都不会存在”(张艺谋语)。
三
80年代中期中国文学界涌现的“寻根”热潮让人至今记忆犹新。以韩少功、贾平凹、莫言、阿城等人为代表的“寻根”作家退出对政治、历史的关注反思,把目光投向厚重的民族文化积淀和地域文化传统,在现实语境里执着于对民族文化的挖掘和对民族文化心理、行为观念的深层探究。“寻根小说”的风靡,是“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世界性”相互交织的社会历史语境的产物,也是新时期一大批优秀作家追寻“民族之根”、探索文艺民族特色的集体性创作心理自觉。倘若就整个新时期的中国文学来考察,我们还可以看到:韩少功、莫言、余华、苏童、张承志、贾平凹、陈忠实等一批才华卓越的作家虽然分属于不同的风格流派,活跃于不同的地域和时期,但他们的创作在开放性地借鉴西方文艺思潮、表现技巧的同时都附着了鲜明的“寻根”色彩,而正是他们对民族历史与现实的深度探索以及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反思和“扬弃”,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相对繁荣。然而,一个民族的优秀文艺作品往往是以自己的浓郁的民族特色走向世界,并将自己民族的独特性和丰富性呈现在世界面前;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由于多种原因的制约,新时期文学“走向世界”的步伐显然未与迅猛发展的时代潮流合拍,中国文学尽管经过了二十年的自我充实、自我完善,却仍然未能占据“世界文学”中的“合法席位”。更令这一时代的文学家深感尴尬的是,作为文学“派生物”的电影却在同时期里取得了空前辉煌的成就。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前期短短数年间,中国电影几乎获得了包括戛纳、柏林、威尼斯电影节在内的世界所有A级电影节的奖项,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巨大的反响和振荡。而我们检阅这一大批流光溢彩的影片时可以发现:它们不仅几乎全部改编自文学作品,而且受“寻根”文学思潮的影响也沾染了浓郁的“寻根”意识,都展露出鲜明的民族特色。
中国电影不仅在题材内容、思想蕴涵乃至表现方法上都受到了文学“寻根”的启示,而且还凭借其直观具体的表现形式、开放性的影像语言将文学作品中透露出来的某些带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字信息还原成直观可感的银幕影像,从而更容易引起大众的情感效应和心灵共鸣。单就“第五代”导演藉以名世的几部“经典”作品来看,从《黄土地》到《红高粱》、从《秋菊打官司》到《大磨坊》……这一系列影片各自从不同的侧重点切入民族历史生活的深处,凝聚着艺术家对民族历史文化发自内心深处的凝重忧思和深切感慨。他们习惯于把视角对准贫瘠荒凉的土地和承受苦难的人民,“透过农民和土地,一个是探索民族性格‘沉默’之伟大;一个是探索‘贫瘠而又内热’的民族自信心”[4]。正是由于艺术家把镜头对准了多元丰富而又为自己所深深熟悉的民族生活空间,执著于对中华民族文化源流和精神命脉的探究和反思,从而使作品沾染了浓郁的文化气息和主体意识;而具有思维独创性的主体意识正是展现艺术个性的生命,也是艺术创作永葆活力的不息源泉。新时期的中国电影以及文学从刻板走向灵动、由衰微走向繁荣,也恰恰可以看作是艺术家追求主体性精神体验、张扬艺术本体生命力的真实写照。
如前文所述,由于与文学的合流加之电影艺术家独创精神和主体意识广泛而深刻的介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中国电影迎来了空前繁盛的局面。然而时至90年代中前期,鉴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某些艺术家创作生命力的枯竭,中国电影逐渐消褪了“神秘感”和“陌生感”而陷入僵化的类型演绎之中。在一大批套式化的影片中,对民族文化内蕴的发掘变成了以过于旺盛的精力开垦中国文化缺失性的“富有矿藏”,“奇异的民俗、严厉的性与政治的禁忌、被压抑的欲望与人性的挣扎变成了‘中国’的全部”[5]。而经历了这一场短暂的迷茫和困惑之后,新时期的中国电影90年代中后期又迎来了第二座发展高峰。在中国电影摆脱困境的历程中,曾经给予了电影充分“养料”和动力的文学依然犹如一面鲜明的旗帜,昭示着“涅槃”之后的中国电影在崎岖中迈向美好的未来。例如,在“新写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之下,一批资历颇深的艺术家和成长之中的“第六代”都流露出对中国“当下”进行表述的意旨,他们试图从现实具体的生存状态中发掘和体现“生动”而“可感知”的民族特性,将民族文化现象与当代中国人的具体生存状态相关联,用更贴切生活的艺术语汇来透视民族的现状和未来。1998年改自述平小说《晚报新闻》的《有话好好说》、改自刘恒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没事偷着乐》,1999年改自施祥生小说《天上有个太阳》的《一个都不能少》以及改自鲍十小说《纪念》的《我的父亲母亲》等便是其代表之作。除此之外,“新历史主义”、“现实主义冲击波”、“乡土文学”、“城市民谣”等诸种文学流派和思潮也在同期的影片中可以找到电影与文学“并轨”的注脚。这种尝试虽然刚刚起步,但它实际上代表着中国电影未来发展的走势和方向。当然,这不仅仅是就电影这一“个案”而言,从具体的、历史的、发展的民族生活沃土中汲取源源不竭的养分,用艺术的语言反映民族的现实生存状态和时代情感特征,也是中国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艺新世纪里责无旁贷的使命。
收稿日期:2000-1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