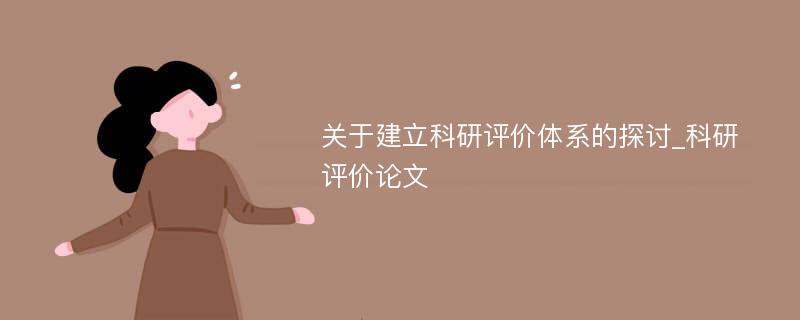
关于建立科研评价体系若干问题的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若干问题论文,评价体系论文,科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G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348(2001)05-117-02
1999年,科技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协联合发布了《关于科技工作者行为准则的若干意见》。该意见指出,在科研立项、科技成果评审、鉴定和验收中,应本着客观、公正、准确的原则,如实反映水平,不得滥用“国内先进”、“国际领先”等抽象用语,不得随意冠以“重大科学发现”、“重大技术发明”等夸大性用语进行宣传、推广。这一意见的出台,对于纠正我国前一阶段科研成果评价中存在的“天方夜谭”现象有积极的作用。本文就如何在实践中正确贯彻落实上述意见,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科研成果评价体系提出一些看法。
1 科研成果评价中的若干认识误区
我国有些科研成果评价与奖励正走入怪异境地。一方面,成果评价与奖励的信誉度极低,不仅是一些省部级奖励,甚至少量国家级的奖励也到了令人鄙夷的境地;而另一方面,获奖者一旦获奖,将在课题立项,在荣誉、提职,分房等方面又得到极大好处,甚至受奖者单位也能得到相应的好处。在这种获奖和后效益的驱动下,科研成果评价中的“天方夜谭”现象层出不穷——“国内先进”、“国际领先”等抽象用语在科研评价中满天飞,动辄百万、千万、上亿,甚至数亿、几十亿的经济效益证明满处皆是,而所在企业则年年亏损。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笔者以为以下一些认识和操作中出现的误区也是其主要原因:
(1)对职称和权威的认识误区。职称的高低不应是成果评定专家的依据。我国已故著名科学家严济慈,一生共发表科研论文53篇,其中2篇在国内发表,其余在国外发表。这些科研论文发表于1925~1938年间。1938年(38岁)后,他再没有发表一篇科研论文。他认为,一个人在科学研究中最能干,最好的时间是30岁左右。王选——我国三院院士,曾说:“当我26岁在最前沿、处于第一个创造高峰的时候,没有人承认。我38岁搞激光照排,提出一种崭新的技术途径,人们说我是权威,这样说也马马虎虎,因为在这个领域我懂得最多,而且我也在第一线。”“我55岁以后就没有什么创造了,反而从1992年开始连续三年每年增加一个院士头衔。”“61岁我才开始卖狗皮膏药。”这后一句话完全是王先生的谦虚。可王先生的这番话也大体反映了人才成长和创造的基本规律。应该说,正在科研和教学第一线担纲的教授们,是某一方面的真正权威。此外,正在做课题的优秀硕士生和博士生们,他们大多没有高级职称头衔,但正是他们,是最了解他们所从事研究领域前沿的真正权威,而遗憾的是,因他们缺少所谓的高级职称,而被拒之评审的门外。
(2)科研成果水平评估的误区。我们首先对中国科研水平的高低评价应有个基本的估计。在当今中国,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就整体而论,科研水平处于差距尚大的层次,只有极少数的领域的某个(些)方面达到甚至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而在我们的评审中,信口开河者不在少数。一个几十万,甚至几万元经费的科研项目也可给个“国内领先”、“部分国际先进”、“国际领先”的评价结论,也可得个国家级大奖。其发展趋势似乎是若不给个被评审者满意的结论,以后再也赚不到评审费似的。
(3)科研成果评价参照系的误区。人们应该明白,有些科研成果是保密的,很难进行国与国之间的比较,有时甚至国内的比较也很困难。1957年,前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美国就开始了要在计算机和信息方面领先世界的研究,而人们恍然大悟计算机信息技术是20世纪末、21世纪的最主要产业之一时,早已过了几十年。北大激光照排的相关研究立项开始于1974年,到90年代才尽人皆知。除业内人士外,90年代前人们很难评价国内的照排系统孰优孰劣。而我们的评审专家,多数是“熟人专家”、“隔行专家”,很难给个符合实际水平的评价结论。
(4)科研成果评价标准的误区。科研成果应该是得到大家公认的,而不应该是由少数“专家”确定的东西。科研成果大致可分为应用型和基础型的。应用型的科研成果应以产品和人们的认可程度来确定,如杂交水稻;基础型的应以真正从事本领域研究人员的看法,或以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书,以及被权威机构收录,如SCI和EI收录,和被他人引用率等加上专家的评议为准。因此,对于基础型的研究成果(保密的除外),完全可以通过量化,如发表的成果被SCI的收录情况,被人引用情况,收入教科书情况等等,来确定其水平。对于应用成果,可以分阶段评审。首先评定实验室成果的水平,结合该成果通过工业试验后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大小来确定该成果的最终水平。应用成果的评定应有较详细的技术经济评价指标和参数。在大多数情况下,真正创新性的重大成果,是很难在成果初创阶段被世人所认知的。
(5)成果评价范围和时间的误区。几个专家关门评出的东西难免有失公正,更何况有许多科研成果的评审人员是由被评审者自己提出名单,基本上是他们自己请人评审。慎之又慎的诺贝尔奖,一般是在成果公布几十年后评审给奖的,这还有误发的;众目睽睽下的足球还有误判和“黑球”、“假球”之说,黑箱操作难免。在我国,目前有不少的科研评审结果被知情者嗤之以鼻,有些与成果评定时间短,暂时无法认定有关,有些则主要是“人情”与“外行专家”、“头衔专家”评审等有关。这种现象极大地损害了国家各级基金管理和评审的信誉。
2 建立专门评审机构的设想
之所以在科研成果评审中出现屡见不鲜的天方夜谭成果,主要是没有人对造成这种后果负责,也即无法追究责任人。一个连年亏损,连工资都难以发出的企业,数百万、千万,甚至数亿、几十亿的经济效益是如何算出来的?为在今后的评审中尽量避免或减少上述种种误区,建议建立专门的科研成果评审机构。这类机构类似国外商业和工程咨询机构,或类似于专利申请管理机构。这类机构应是自负盈亏的公司型机构,而不是政府所属机构。那么,这类机构的生存源和资质认定应如何确定呢?
评审机构的生存依赖其工作的业绩。这类机构从事的工作应包括两大方面:科研成果的评审和科研经费再申请及科研成果转化的中介。从理论上来说,单位和个人都可从事经营该类机构。在初始阶段,具备什么样资质的单位或个人有权经营这类机构呢?
就目前来说,中国科学院所属的单位,国内(外)有相当声誉的高校,各部委的一些行业专业协会及所属机构有优先申请建立评审机构的条件和优势。要申请评审机构的单位,应具备下述基本条件:具有国内公认的学术地位,拥有优势的本专业专家群,建有或能迅速建立查询论文发表和被权威机构收录情况、本行业专家情况和历年获奖情况的数据库。具备上述基本条件的单位,对基础研究成果的评定,只要从数据库中调出数据,就能对成果进行量化的评价。在此基础上,结合专家评审,就能得出较符合实际的成果评价结果来。如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它对中国某行业的论文发表情况、收录情况、相对排名情况等都能给出定量的数据;如清华大学建立了期刊光盘数据库,只要对资料加以处理,就能对某项基础科研成果的水平作出定量的评价。在此基础上,根据近年发表论文的多少,找出某领域真正的权威,进而进行专家评审。
对于应用型成果,可根据专利申请情况进行定量化初审。然后,再组织科技和技术经济专家对工业试验和应用前景等作出评定。
这类机构的生存依赖两个经费来源:专家评审费和中介费。有的项目评审所花费的评审费是几万,加上为报奖而所作的“活动”经费,可达10多万。如果将评审全权委托专业评审机构,项目送审费大幅度增加,实际上却减少了送审者的负担,在某种程度上又抑制了评审中的不正之风。科研成果的正确评价,又为成果的转化提供了方便。这类机构不仅能为人才流动作中介,而且能为应用成果方提供可靠的保证,从中收取中介费。因为,评审机构不仅为真正的科研成果拥有者推销出成果,而且也为应用成果方提供了可靠的技术和投资预算方案,收取中介费理所当然。
国家也可以在道义和政策上给予评审专家以支持,即将评审专家参加评议的次数和质量作为类似发表论文似的提职等的指标之一,还可作为拥有该类机构的单位的水平评价的指标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