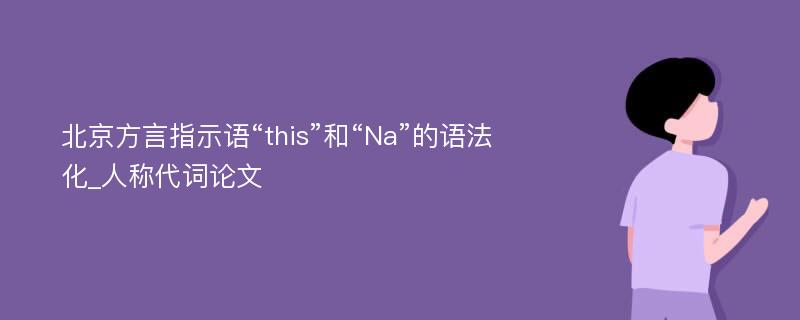
指示词“这”和“那”在北京话中的语法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话论文,语法论文,指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传统上对指示词的描写通常是以指示中心为坐标,借以区分远指、近指以及中指等等。近些年来有学者运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对汉语口语中的指示词进行考察发现,说话人选用哪个指示词不仅仅取决于所指对象与指示中心的空间关系,还取决于言谈结构的变化(是对话还是叙事)、所指对象的指称性质(是有指还是无指)、所指对象与上文的相关程度、说话人的态度,以及言谈过程中说话人对表达的设计等诸多因素。(参看Tao 1999;Huang 1999等)对“这”、“那”和“这个”、“那个”在口语当中的非指代用法的关注超过了以往。(参看张伯江、方梅1996)
本文对指示词的考察以上述研究为起点,使用的材料是个人收集的北京话录音转写材料,包括独白和对话两种语体。
一 “指示词+名词”组合的篇章一语义属性
1.1 指示词在篇章中的功能
本文主要讨论“这”、“那”在口语篇章中的虚化现象。在讨论虚化现象之前,我们首先从篇章角度看一看“这”和“那”作为指示词在言谈中的功能。(注:指示词的篇章用法,本文参考了Himmelmann (1996)的框架。与陶和黄不同,本文把单语素的“这”、“那”与其复合形式“这个”、“那个”区分开来,只讨论“这”、“那”。)
1)情境用(situational use):所指对象存在于言谈现场、或者存在于谈话所述事件的情景当中。指示词用来引入一个新的谈论对象。例如:
(1)—她动不动就大耳贴子贴我,啊,跟拍苍蝇一样, 我想不通,我想不通。
—我不信,一定有演义,作家嘛!
—啊?我演义了?你瞅这脸上,你瞅,……你还不信呀?得,我也不怕寒碜,你看这腿,这就是跪搓板儿跪的!
(2)以前我在北方的时候,有这小米面饼子,现在还有吗?这种用法下的指示词虽然位于名词之前,却并非用作指别。其中的“指示词+名词”都不能作为“哪个”的回答。
2)示踪用(tracking use):用在回指性名词之前。 所指对象是上文中已经引入的一个言谈对象。例如:
(3)它是棒子面儿,和得很瓷实,弄一个大圆饼, 就放到锅里煮。煮出来就连汤带这大饼就一块儿吃。
(4)—还有一东西是,叫疙瘩的。就是,在山西农民, 晋南一些人就吃这种东西。
—那疙瘩是,多半儿是白面做的是吧?
(5)对,乌贼,乌贼,他们常吃那东西。示踪用法下的“指示词+名词”用作回指上文中提到过的某个对象,可以被“这个”或“那个”替换,但也不是用来回答“哪一个”的问题,换句话说,其中的指示词也不用作指别。
3)语篇用(textual use):所指为上文的陈述或者上文所述事件。例如:
(6)—听说你揍过他?
—揍,这你也听说啦?
(7)要是闹出个人命来,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4)认同用(recognitional use):用于引入一个可辨识性相对较弱的谈论对象。所引入的对象不是上文或语境里已经存在的,但却是存在于听说双方的共有知识当中的。
(8)还有、还有那芝麻酱烧饼,我常常想起这个,想极了。
从所指关系的语义类型上来说,情景用、语篇用和示踪用这三类用法当中,指示词的所指对象都是存在于语境当中、或存在于言谈的情境中的实体。情境用和认同用的相同点在于,由指示词所引入的名词,其所指对象是第一次在谈话中出现。与情景用、语篇用和示踪用三类不同,认同用里,指示词的所指对象不是语境当中已经存在的某个确定的个体,也不是说话人要谈论的对象。至于用“这”还是用“那”,并不取决于所指对象在真实世界中与指示中心(注:指示词是直示(deixis)系统中的一类。其语义指向情景或语境中的对象的语言成分,它们的具体意义所指只有联系情景或语境才能确定。传统对直示成分的分析特别强调“指示中心”,也就是对时间、空间或人指称时的发出点。语法范畴中的“远指”与“近指”的范畴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远指用于指称离指示中心较远的事物,近指用于指称离指示中心较近的事物。)之间空间距离上的远近,而取决于它在说话人内心世界中的地位,或者说话人的主观态度。比如上面例(8), 里头的“那”换成“这”以后也是语法上可接受的句子。
指示词的上述四种用法的异同可以表示如下:
情景用 语篇用 示踪用 认同用言谈对象存在于语境/现场+ + + -言谈对象首次出现于谈话 + - - +
一般认为,北京话里“这”和“那”都有单元音韵母和复合元音韵母两读,即zhè/zhèi,nà/nèi,其中zhèi和nèi是口语化读音。我们的调查结果是,回指性的成分倾向于说成复合韵母形式zhèi、nèi。
1.2 “指示词+名词”组合中名词的指称属性
正是因为指示词“这”和“那”有了相对较虚的篇章用法,既非指别又非替代,它后面的名词的指称属性也呈现出多种可能。把掌握的材料归纳起来看,指示词之后名词的类型有下面这样几类:(注:回指、有指、定指、通指几个概念的译法从陈平1987,分别指co-referential,referential,identifiable,generic。)
1)[+回指],[+有指],[+定指]
(9)那个吃辣的吃得邪啊。我以前在四川的时候记得、 看见有些个人呐,没钱,没办法儿买菜呀什么等等,就弄着一碗饭啊,向这个饭上面儿倒上一包辣椒面儿,红辣椒面儿啊。什么都没有,就是、就是干辣椒,磨成粉呐,然后就倒到饭里和,和得那饭呐都成红颜色儿,然后就那么吃。
2)[-回指],[+有指],[+定指]
(10)比方现在美国的市场里买点儿那些个,罐头里的菜,你打开罐头以后啊,那四季豆也黄不啦叽的,是,菠菜也黄不啦叽的,什么都黄不啦叽的。
3)[+回指],[+通指]
(11)—还有窝头没有?
—有窝头,对。那窝头就是黄金塔啊。
4)[-回指],[+通指]
(12)你们什么时候儿听说过这文化人办文化上的事儿,还自个儿掏钱的?都是要掏别人腰包。
(13)—现在吃肉大概比以前稍微好点儿吧?
—对。那城市里面,很多人就是,每个星期都要去买点儿肉。
5)[-回指],[+无指]
(14)有的人他是把白薯煮熟了以后,风干,弄成白薯干儿,那个就,我很喜欢吃那个玩艺儿,呃,就是,一咬就跟那橡皮筋儿一样。
从上面的几类用法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印象,光杆名词的指称属性具有不确定性,篇章中,名词短语的有定性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它前面的指示词去标定。是否使用指示词、用哪个指示词,不仅仅是篇章需求,同时也有可能是句法需求。
二 指示词功能的扩展
2.1 弱化谓词标记
“一+动词”是一个很常见的格式,《现代汉语八百词》对这种格式的解释是“表示经过某一短暂动作就得出某种结果或结论”。下面是《八百词》里的例子:
(15)医生一检查,果然是肺炎。/我一想,他回去一趟也好。
我们感兴趣的是,“一+动词”格式的用法特点。首先,用于这个格式中的动词都不能带“了[,1]”、“着”、“过”。
(16)[*]她一检查过/了身体,果然是肺炎。/[*]我一想了/着/过,他回去一趟也好。
第二,句法上不自足。不能单独作谓语构成独立的陈述句,只能用作表示条件的小句。即便带句末语气词,也不能结句。
(17)[*]我一检查身体 [*]她一检查身体了 [*]她一检查身体呢
第三,可以出现在典型的谓宾动词——真谓宾动词之后。
(18)想好了,决心一死/准备一搏/难免一伤显然,“一+动词”构成的小句不表现内在的时间过程,不参与事件的叙述,不具备典型谓词性成分的属性,是一种弱化的谓词短语。
这类弱化的谓词格式前面很容易加上“这”、“那”,“指示词+一+动词”用来指称某种行为。篇章中这种用法都是回指性的,在我们的语料中还没有发现非回指性的例子。
(19)—我哭了,实在忍不住了。
—这一哭,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我想。这类“一+动词”格式前面还可以加人称代词,例如:
(20)—我哭了,实在忍不住了。
—你这一哭,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更进一步,指示词可以直接加在动词前,构成“人称代词+指示词+动词”的格式。例如:
(21)—我哭了,实在忍不住了。
—你这哭太管用了,所有问题都解决了。这时候的指示词“这”、“那”能说成zhèi、nèi, “人称代词+指示词+动词”整体上仍然是回指性的。非回指性的情形往往有比较严格的限制。例如:
(22)—你跟他挺熟,你觉得他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我就佩服他这吃,他可真能吃!
这种非回指用法的“人称代词+指示词+动词”有一个条件,即所指对象必须具有较高的可及性(accessibility, 也有文献称“易推性”)。换句话说,尽管它未曾出现在上文,但却是说话人和听话人双方的共有知识当中已有的内容,或者是通过共有知识易于推及的内容(如上例中的“他”是个体型较胖的人)。指示词的这种用法是对系统中已经有的“人称代词+指示词+名词”格式的套用,用于构建一种指称形式。无论是名词做中心语还是动词做中心语,由非回指性“这”构成的“人称代词+指示词+动词”和“人称代词+指示词+名词”,其中的中心词都具备“高可及性”特征。(注:可及性(accessibility)的高与低实际是信息的确定性(givenness,familiarity)程度问题,本文参照Ariel(1991)的描写。下述各名词性成分的可及性从低到高,依次为:零代词>轻声的代词>非轻声的代词>非轻声的代词+体态>(带修饰语的)近指代词>(带修饰语的)远指代词>名>姓氏>较短的有定性描写>较长的有定性描写>全称名词>带有修饰语的全称名词)除此之外,指示词的语音形式也同于回指性的“人称代词+指示词+动词”,“这”说成zhèi。
再进一步,指示词可以直接加在动词或形容词之前,构成“指示词+动词/形容词”。例如:
(23)—不产面的地方,实在没有这个东西的地方,就是,每人,就是过年发二斤面。这样话能吃饺子。
—啊哈。至少过年这吃饺子这事儿得办到。
(24)—这个这个,还有一个这个菜,我觉得名字很有意思,其实这菜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叫蚂蚁上树,上树啊。
—这上树是怎么回事?
(25)—您扔这砖头哪?
—就听“扑通”。
—深。
—就冲这深……
—跳。
—不跳!“人称代词+指示词+动词/形容词”一般用作回指,当中的“这”说成zhèi。
“人称代词+指示词+动词”(如:你这哭)以及“指示词+动词/形容词”格式的产生,是“人称代词+指示词+名词”(如:你这脑袋)格式一步一步类推的结果。“人称代词+指示词+名词”这种格式清代就有。这些例子当中,名词所指的事物在语境里或是独一无二的,或是无需分别的。因此,指示词虽然在定语的位置,但是它的作用都不在于区别,属于我们上文谈到过的“情境用”。例如:“偏你这耳朵尖,听的真!(《红楼梦》)”、“恨的我撕下你那油嘴(《红楼梦》)”(例子引自吕叔湘,1985)。这种用法沿用至今。例如:
(26)你要是不答应,我就把我这头磕出脑浆子来!指示词甚至可以用在抽象名词之前。
(27)咱这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在哪儿了?就是有人情味儿。
2.2 话题标记
“指示词+动词”构成的弱化谓词短语可以用在句首作话题,指称上文中叙述的某种行为或某个事件。例如:
(28)—不过,你要说到糖的话,南方做菜总是要搁糖的。
—啊,可是那搁糖是,好像是调味儿性的。
(29)—您就拿我来说吧,过去净想发财,现在我就不那么想啦,就变啦。
—对!
—过去这个想法就不对,净想发财,这叫什么思想呢!
—就是嘛!
—发财的思想我可没有。
—你比他们强。
—提起这发财来有个笑话。上面的用例中的“这”还不是我们所说的话题标记。我们所谓用作话题标记的指示词是指,指示词介绍出来的对象是第一次在谈话中出现的那种非回指性的用法。这种情形下的“这”、“那”不能换作“这个”、“那个”。这种非回指性的指示词不仅可以用在名词前面,也可以用在谓词性短语前面。指示词说成zhè、nà。例如:
(30)这要孩子给太监做老婆,我怎么对得起女儿啊?
(31)这过日子难免不铁勺碰锅沿儿。(30)与(31)稍有不同。(30)当中“这”后面的“要孩子给太监做老婆”没有作为短语在上文中出现过,虽然在前面的对话中的确是在谈论把一个姑娘嫁给太监这件事,见(32)。因此,就“要孩子给太监做老婆”的所指而言,是确指的,并不是全新的信息。而(31)不同。“这”后面的“过日子”在上文当中没有出现过,整句话是对前面一段两口子打架故事的评论。句中的“过日子”表达的是一个无指概念,既不指具体的某个事件,也不能被回指。(注:这里“过日子”我们不分析作“通指”,理由是“过日子”在语境中不可以被回指。而通指成分虽然不指称语境中的具体事物(这一点与无指成分相同),却代表语境中一个确定的类,是可以被回指的。比如,下面一个例子当中的“麻雀”是一个通指成分,它后面可以用“它”来回指。
麻雀虽小,但它颈上的骨头数目几乎比长颈鹿多一倍。(此例引自陈平 1987)而无指成分是不可以被回指的。例如:
他们下星期要考研究生。(此例引自陈平 1987)既可以理解为他们要报考研究生,也可以理解为对研究生进行考试。作前一种理解的时候,其中的“研究生”是无指成分;作后一种理解的时候,“研究生”是有指成分。作有指成分的“研究生”可以被回指,如:
他们下星期考研究生。这批研究生进校两个多月了,这是第一次对他们进行考试。但是作无指成分的“研究生”却不能用任何一种代词去回指。)
(32)康六 宫里当差的人家谁要个乡下丫头?
刘麻子 这不你女儿命好吗?
康六 谁呀?
刘麻子 大太监,庞总管!你也听说过庞总管吧?伺候着太后,红的不得了哇!人家家里头,打醋那瓶子都是玛瑙的!
康六 这要孩子给太监做老婆,我怎么对得起女儿啊?
我们认为,指示词作为话题标记是指示词情境用法的延伸。它的作用就在于把一个未知信息处理作已知信息,或者把一个确指程度不高的成分处理得“像”一个有定名词。因为典型的话题是一个已知信息、或有定名词(沈家煊1999有充分的论证),“已知”和“有定”是话题位置的默认值(或缺省值)。运用指示词直接加在一个未曾提及的事物或行为前面,这是信息包装的一种手段,目的在于让这个位置上的成分在形式上符合话题位置的默认条件。这种现象张、方(1996)处理作指称标记,比较看重它变陈述为指称的功能,或者说名词化的功能。但是,现在看来,这样分析不能很好地说明它与回指性指示词的区别,尤其不能很好地说明与不带指示词的动词话题的区别。
2.3 定冠词
指示词的基本功能有两方面,一是单独用来指称话语中的某个确定的对象,二是在名词前面充当限定成分。前者是所谓“替代”(如:这是新发的工作服),后者是所谓“指别”(如:那演员是奥斯卡得主)。无论是指别还是替代,都可以针对其所指对象用“哪个”来提问(哪个是新发的工作服?哪个演员是奥斯卡得主?)。换句话说,指示词本身或者指示词与其后的名词一起用于指称一个在说话人看来听说双方确知的对象。
世界上的各种语言几乎都有指示词,但是有冠词的语言并不是很多。很多语言里,用来指称一个确定对象的时候就是用指示词(Payne 1997)。过去我们对汉语的认识正是这样,一般语法书上都说汉语没有冠词。另一个方面的事实是,在一些有冠词的语言当中,冠词来源于虚化以后的指示词。指示词由于经常被用在名词前来指称确定的对象,久而久之,逐渐变成一种黏附性的前加限定成分。那么,如何确认一个指示词依然是指示词还是已经虚化为冠词,Himmelmann(1996)通过跨语言的考察,提出了如下尺度:
1)指示词不可用于唯一的所指对象,如:[*]this/that sun;[*]this/that queen,但是冠词可以。
2)指示词不用于由于概念关联(frame-based)而确定的对象,比如,如果上文中出现了tree,在下文中如果指称这个树的枝干的时候不能用this/that branch,而要用the branch。
回过头来我们看看北京话里的情况。北京话里的指示词虚用,首先在形态上已经独立出来,它在语音上附着于其后的名词,且不能重读。除此之外,指示词的用法可以概括为下面几种情况。
1)在专有名词前, 但是整个名词性短语并不指语境中或谈话双方共有知识中实际存在的某一个体,而是具有这个个体所代表的某些特征的一类对象。“指示词+专名”构成一个通指性成分。例如:
(33)你以为呢!这雷锋可不是那么好当的。
2)在通指名词前,整个名词性短语指某一类对象, 而不是语境中或言谈现场中的具体的个体。例如:
(34)你知道吗,就这外国人呐,他们说话都跟感冒了似的,没四声。
3)只用在光杆名词、 或相当于光杆名词的“的”字式(如:男的、拉车的)以及黏合式偏正结构(如:木头房子、高个男孩儿;参看朱德熙 1982)的前面, 不用在数量名结构或含有描写性定语的组合式偏正结构之前。
(35)而且,乌贼,以前在学校念的时候,据老、老师说,这、这鱼啊,一下去喷出来啊,一家伙黑,是不是?我一想,这人怎么能吃那东西啊,是不是。
(36)—你说我们这位吧,过去挺好的,任劳任怨,让往东啊,他不敢往西,现在倒好,成大爷了。
—没错。这男的呀,稍微长点本事,就跟着长脾气。
4)在非回指名词前,名词的所指是由于概念关联(frame-based)而确定的对象,而不是上文中已经出现的确定的对象。例如:
(37)在中国你要做炸酱面。那也是,把这肉搁里面,噼里啪啦一爆,把酱往里一搁,就行了。
上面几种用法中的指示词的作用是,把一个指称属性不十分确定的名词身份确定化。因此,我们认为,这种指示词在用法上已经同于定冠词的用法,无论从形态上还是从功能上都可以确认已经虚化为定冠词。从收集到的材料看,只有近指词“这”有虚化为定冠词的用法,远指代词“那”还没有那么高的虚化程度。关于这一问题,将在下一节讨论不对称现象时作进一步论证。
北京话里指示词还可用如副词表示程度。如:你没看见,她这不高兴!(“这”zhè,且重读);用作连词,如:你们都这么懒那我也不去了。(“那”nà)(参看张、方 1996)除此之外,与指称相关的用法可以概括如下。
情境用 示踪用 语篇用 认同用 定冠词这
zhè/zhèizhèizhèzhe zhe那
nèi/nà nèi nà na/ne
我们认为,“这”在北京话里的定冠词用法是篇章中的“认同用”进一步虚化的结果。
第一,“认同用”只用在名词性成分之前,是一种“唯定”用法。
第二,“认同用”指示功能的弱化已经有相应的语音表现形式。
第三,“认同用”后面的名词不依赖上文或言谈现场实际存在的对象,已经开始脱离了指示词的基本功能,既非指别又非替代。
尽管不是每种语言都有冠词,但是在那些有冠词的语言当中,由指示词演化出定冠词的用法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现象。(参看Himmelmann 1996等)
三 “这”、“那”虚化的不对称现象
关于“这”与“那”在语法上的不对称,徐丹(1988)有过详细的论述。在她的文章中也提到“这”、“那”在使用频率上的悬殊,“这”位于常用词第10位,而“那”位于182位。Tao(1999)对“这/那”和“这/那+X”里面“这/那”使用频率的统计显示, “这/那”在情境用的使用频率接近,而语篇用更偏重用“这”。从“这”、“那”使用的总体情况看,认同用的使用频率最高:
认同用>示踪用>语篇用/情境用据此,Tao主要讨论了在近指词与远指词的选择上, 超出具体空间概念的用法。并提出,“这”、“那”的选择,受下面五个方面因素的影响:
1)话语模式(discourse mode)。 比如情境用的“这儿”在对话中指言谈发生的地方,而在叙述或报道性语篇中,则不指说话人当时所处的地方,而指向言谈中的某个处所。
2)语篇性(textuality)。 用来指称前面相邻小句所叙述的内容,而不是某个具体对象时,倾向于用“这”。
3)指称的现实性属性(hypotheticality of reference)。 对现实事件中的对象倾向于用“这”,对非现实事件中的对象倾向于用“那”。
4)推断性通晓(assumed familiarity)。指说话人推想听话人对他所述对象的确知程度的假设。一个在说话人看来不容易被听话人辨识的、新的对象,倾向于用“这”,较容易被听话人辨识的新的对象用“那”。
5)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指说话人的态度。Tao的观察是很有见地的,尤其是上面的1)、2)和5)。我们认为,“这”的确有着意推出一个新的言谈对象的作用,这一功能是它作为话题标记的基础。除此之外,在“这”、“那”的分别上,本文提出两点看法。第一,“这”具有较强的言谈连贯功能,(注:Givón(1995)曾谈到,英语自然口语当中引入一个新的言谈对象时,常见的是两种形式:a+N,或this+N,后者用作引入重要话题。 )比“那”更容易表现“相关性”。第二,“这”具有较强的定指化功能。
3.1 相关性
“这”的言谈连贯功能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在Tao (1999)所述“这”用作语篇用的高频现象(占93%),另一方面表现在“这”有比“那”更强的保持话题连续性的作用。
一个名词性成分作为新信息在语篇当中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常常在宾语位置或定语位置上,尤其是“有”字句或存现句的宾语。这时候如果这个成分在下文中作为话题重提的话,用“这”和“那”的例子都有,但是用“这”更为常见。例如下面这段话当中,用“这”把一个不在前台的对象推到前台来,并且用“这”保持谈论对象的“前台身份”。请注意下面例子当中“窝头”、“慈禧太后”、“老百姓”、“御厨”在语篇中的连贯方式。比如“这[,1]”到“这[,11]”后面的名词都不是第一次出现在谈话当中,用“这”是讲话人偏爱的保持连贯性的选择。
(38)—还、还有窝头没有?
—有窝头,对。那[,1]窝头就是,黄金塔啊。(介绍制作方法)
—以前说起这[,1]窝头来啊,以前还有那么个,哦,也不知道是真事儿啊还是笑话儿还是怎么着。就是这个,讽刺慈禧太后的事儿。这[,2]慈禧太后啊,这个,清朝末年的时候儿,这个,人民的生活也是越来越苦了是不是?那么就有很多这个倡兴革新的大臣呢,在这个朝廷里说,说是这个,老百姓啊这个生活真是苦极了,这个,一天到晚啊就吃这个棒子面儿窝头,这个没什么别的东西可以吃。这[,3]慈禧太后就说,“呵,吃棒子面窝头,棒子面儿窝头是什么东西啊?给我吃一吃,我看一看这个你这[,4]老百姓生活到底是怎么样。”就下令啊,说是得吃一顿棒子面儿窝头。就跟这[,5]御厨说啊,做、做窝头。这[,6]御厨一想啊,呦,这个老佛爷要吃这个窝头啊,这[,7]可得小心点儿,不能乱做。就啊把棒子面儿啊磨得很细很细,做出来,丁不点儿大的小窝头儿,啊,很小的小窝头儿。里头还放上这个蜂蜜啊,这个糖啊什么等等的,做得精制的,给她端了一盘儿来了。端了一盘来呢,这[,8]慈禧太后来了,说是我这得跟老百姓共甘苦是吧,吃窝头。老佛爷吃窝头,把这[,9]窝头拿起来一吃,呦!说这[,10]好吃极了!这[,11]老百姓吃这个还一天到晚诉苦,这还得了!把那[,2]几个大臣给我逮起来,杀喽!”那[,3]事儿就给解决了。在上面这段话中,三个“那”都可以换成“这”,但是“这”却很难换成“那”。本文不打算进一步讨论指示词完全虚化为言语行为手段的现象。不过,稍加注意就不难发现,在自然随意的谈话中,“这个”比“那个”更多的被用作延续谈话的话语手段。(注:据梁敬美(2002)《“这-”、“那-”的语用与话语功能研究》一文的统计,从使用频率看,“这”用作言语行为手段(如:找词、找话语、填词)是“那-”的两倍。)这也从侧面说明“这”具有较强的言谈连贯功能。
上文中我们曾经指出,“这”可以用作话题标记,把一个新信息做成一个“像”旧信息的形式。通过(38)例我们可以看到,“这”也是说话人保持话题连续性的偏爱的手段。这样,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这”在实际使用中的出现频率远远高于“那”。
一个新的谈论对象第一次被引入谈话作为话题时如果用“那”,往往用来表现与前面谈论的对象形成对比或相反的情形。这种用法当中的“那”都不能换作“这”。例如:
(39)美国人在这儿就是喝一杯咖啡,烤两块面包。那(na)中国人要是,主要讲究喝粥。
(40)西方人吃那个面条儿的时候很小心的,弄个叉子在那儿转悠转悠,转悠半天,然后再往嘴里喂、嘴里搁。那(na)中国人,你看看,要是那样就不成其为吃面了。
综上所述,话语中用“这”表现“相关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的谈论对象第一次被引入谈话作为话题时倾向于用“这”。
2)保持话题的连续性倾向于用“这”。
3)引入对比性话题,着意表现“不同”的时候用“那”, 不用“这”。
“这”既可以用作回指,也可以用作引入一个新话题。“这”引入一个新话题,用于拉近语篇距离,把一个未知信息当作已知信息处理。“那”既可以回指,也可以引入一个未知信息作新话题,但是“那”引入的这个新话题是作为对比性或参照性的对象提出的。这种用法和意义上的区别实际上是“这”、“那”沿着它们本来的近指与远指两个方向进一步虚化的结果。
3.2 定指性
北京话里,“这”和“那”都有不同程度的虚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跟“这”一样,“那”也可以用在非回指性的光杆名词前,但是“那”与这类名词的组合却很难出现在那些典型的要求定指成分的句法位置上。比如句首位置,“这”的使用频率占压倒多数。但是,在不要求定指名词的位置上,比如介词“跟”的宾语,“那+名词”或“这+名词”都比较自由。
(41)有的人他是把白薯煮熟了以后,风干,弄成白薯干儿,那个就,我很喜欢吃那个玩艺儿,呃,就是,一咬就跟那橡皮筋儿一样。这个例子里的“跟……一样/似的”的框架都是非现实的表述,里面可以用“那”也可以用“这”例如:
(42)熬熬熬,熬到最后熬成一锅黏乎乎的,跟这稀浆糊似的那样的汤,这个拿起来就喝。“跟……一样”有两种意义,一是表示两事物相同,二是表示比拟。表示两事物相同的“跟……一样”,可以用“不”否定作“跟……不一样”,但是不能把“一样”换成“似的”;表示比拟的“跟……一样”可以把“一样”换成“似的”,不能用“不”否定。另外,表示相同的“跟……一样”自然重音在“一样”上,而表示比拟的“跟……一样”重音在“跟”的宾语上。(朱德熙 1982)用这个区分标准看(41)的“跟……一样”,显然是表示比拟,而不表示两事物相同。沿着这个思路考察表示比拟的“跟……一样”当中“跟”的宾语名词,我们发现这些名词与“似的”前面的名词一样,都具有非现实性特征。例如:
脸色跟纸一样白 脸色白得跟纸似的
[*]脸色跟纸不一样白 [*]脸色白得不跟纸似的
[*]脸色跟一张纸一样白
[*]脸色白得跟一张纸似的
[*]脸色跟这张纸一样白
[*]脸色白得跟这张纸似的这样看来,(41)当中“跟……一样”中的名词与(42)当中“……似的”中的名词性成分,在现实性的程度上是相同的。换句话说,表示比拟的格式“跟……一样”当中“跟”后面的名词与“似的”前面名词同样是“非现实性的”。这个现象表明,用Tao 文提出“现实性”的差异来解释用“这”还是用“那”仍然有问题。
当然,(41)(42)还勉强可以用Tao 文第四条推断性通晓来解释,也就是说,指说话人推想听话人对他所述对象是不容易被听话人辨识的、新的对象,倾向于用“这”;较容易被听话人辨识的新的对象用“那”。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解释“把”后面宾语位置上“这”、“那”的选择限制就有些困难。比如在上面(37)中的“这”的位置上,就不能换用轻声的“那”(na)。如果用“那”,只能是非轻声形式nèi,即回指性的成分,而且“那”后面的光杆名词在上文中已经出现过。
(37’)[*]在中国你要做炸酱面,那也是,把那(na)肉搁里面,噼里啪啦一爆,把酱往里一搁,就行了。
在中国你要做炸酱面,那也是,把那(nèi)肉搁里面,噼里啪啦一爆,把酱往里一搁,就行了。
所以,更完满的解释是,对一个指称属性不明确的光杆名词来说,用“这”可以标定这个名词性成分的定指性身份,用“那”没有这个作用。据此,我们认为,只有“这”有了虚化为定冠词的用法,而“那”还没有虚化为定冠词。
四 语法化的系统背景和类型学意义
北京话里指示词开始出现定冠词用法,这个现象不是孤立的,是系统性变化的反映。因为,在共时材料中,已经出现了“一”作不定冠词的用法。(注:现代北京话里,数词“一”在光杆名词前具有不定冠词的作用,笔者在第30届国际汉藏语讨论会(北京 1997)论文中曾经指出这一现象。在第十一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上(芜湖,2000),刘祥柏也讨论了北京话的“一”在名词前不按照系统中“一”的变调规律发生变调的现象。)
4.1 “一”的不定冠词用法
吕叔湘(1944)曾指出,汉语里的“一个”具有不定冠词的作用,而且“(一)个”应用的使用范围比不定冠词要广,可以用于不可计数的事物乃至动作与性状,可以用于有定的事物,甚至用于非“一”的场所。“一个”常常省“一”留“个”。这样的“(一)个”在元代以后就已经很普遍了。
或许是因为“(一)个”的语法意义负载过重,现代北京话里出现了一种省“个”留“一”的用法,专门用在名词前,“一”后没有量词同现。例如:
(43)—这女的是你妹妹?—一亲戚。
—不是。 —什么亲戚?
—你姐姐?—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这里,名词“亲戚”反复出现,说明“一+名词”的所指对象的不确定性。或者说,说话人没有把这个名词的所指对象当作一个确定的对象来处理。
上述这类“一”的用法,我们认为是“一个”脱落“个”进而虚化为不定冠词。因为这种用法下的“一”在以下几方面不同于真正的表数量的“一(个)”。
1)不遵循数词“一”的变调规律,而一概说作第二声。例如, 下面的例子中“一”后面的名词分别是四个不同的声调,但“一”一概说作yí,而不随其后名词的声调变调。例如:
一狮子 一熟人 一老外 一耗子声调上的一致性说明,这类“一”有可能是从省略第四声的量词“个”而来。
2)这类“一+名”重音总是在名词上,“一”不能重读。
3)这类“一+名”不能用作跟其他数量成分对比。如果对比, 对比项只能是名词的所指对象,而不能与相关的数量形成对比。在收集到的50条用例中没有找到反证。例如:
(44)我就带了一个帮手儿,可是他领了仨。
[?]我就带了一帮手儿,可是他领了仨。
4)这类“一+名”多用在宾语位置,从不作为回指形式。
(45)宾语位置:只当是东三省被占了,我是一你们用得着的少帅行吗?
我替我姐说吧,你还不能算一坏人。
我沿着桌子喝一对角线,你喝一中心线。
你在一小单位里工作,算上你总共才六个人。
有一朋友倒是愿意帮这个忙儿。
所以呢,他不敢打我,还给我一官儿当。
(46)主语位置:我这货好销,一老外昨天从我这儿买走好几条。
我一朋友昨天约我喝酒,一喝就喝到半夜了。
使用“一+名词”,往往是用在根据谈话者的共有知识不能确认名词所指事物的场合。其中的名词的所指事物在前面或未曾提及、或假定听话者还不熟悉。与“一+名词”形成互指关系的一般为相应的有定形式。汉语里这类有定形式为代词、指示词/代词+名词、光杆名词和部分偏正短语。下面看一看“一+名词”连续话语中的情况。
(47)(已经很晚了,来不及了,……我一想呢,我就说,画一半儿就够了,我就画了一半儿。我想那一半儿攥我手里,给他看画上的一半儿。)我就来了,还拿一凳子[,1],还在同学那儿拿一凳子[,2],因为你拿着凳子[,3]就让人家以为你有电影票呢,哈,要没有电影票,你拿凳子[,4]干什么。上面的例子引自一个人讲他画假票混进礼堂看电影的故事。这一段叙述中“凳子”第一次出现的时候用了“一+名”形式,第二次出现的时候因为是套用重复上一句,“凳子[,2]”前面仍然有“一”;而回指性成分“凳子[,3]”、“凳子[,4]”则一概采用光杆名词形式。
“一”用作不定冠词与指示词“这”用作定冠词都是北京话在近几十年当中产生的。相对而言,“这”用作定冠词的用法大概要早于“一”脱落“个”用作不定冠词。我们查阅了80年代初北京话调查的资料,老年组的材料中已经有了“这”用作定冠词的用例,但是“一”用作不定冠词仅出现在青年组,也就是60年代前后出生的北京人的谈话当中。老年组的材料中没有发现。(注:80年代初,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林焘教授主持的北京话调查,对北京市区、郊区和河北部分地区进行了系统调查,本人参加了对北京城区的调查。目前,这部分语料由北京大学中文系保存。)
总之,北京话里指示词虚化作定冠词这个现象不是孤立的,指示词的定冠词用法和“一”虚化作不定冠词用法在现代北京话里是成套出现的,指示词功能上的这种变化是系统性变化的一个部分。
4.2 类型学地位
我们看到,北京话里虚化的有定性标记可以表述作:
定指标记:这个→这[zhe]
不定指标记:一个→一[yí]
其他方言中指示词的虚化情况,我们参考了黄伯荣主编的《汉语方言语法类编》和李如龙、张双庆主编的《中国东南部方言比较研究丛书(第四辑):代词》等文献,发现北京话“这”的虚拟程度是比较高的,虚化类型相近的似乎只有福州话。福州话有分工明确、句法功能互补的三个指物的近指代词(陈泽平 1999)。
□[tsui[53]] 单独做主、宾语,不做定语、状语,不与量词、方位词组合。
只[tsi[33]] 黏附形式,单独做主、宾语,不做定语、状语, 不直接修饰名词。可以与数量名结合、与其他语素组合成复合指示词。
者[tsia[33]] 黏附形式,唯一的功能就是直接与光杆名词结合。其中的“者”是一个由近指代词“只”[tsi[33] ]和通用量词“介”[ka]合音的、“唯定”单语素指示词####它的功能单一,并且语音形式上也区别于其他功能的指示词。
有定性标记在北京话的变化途径是量词脱落,这种情形跟吴语用个体量词、粤语用量词“个”表示定指形成对照。比如:
(48)粤语:(张双庆 1999)
个太阳都落咗山咯。太阳已经落山了
个月光好圆。月亮很圆
(49)上海话:(潘悟云、陶寰 1999)
支钢笔是啥人个?这支钢笔是谁的?
帮我拿扇门关脱渠帮我把门关上
据潘悟云、陶寰(1999)的描述,上海话的这种定指标记量词声调中性化,重音在名词上,而且不能与相应的近指或远指成分对举,认为这类现象不是“指示词+名词”的省略形式。上海话里的另一种定指标志是省略了近指词“个”的量词,它既表示定指,又表示距离指示意义如:“本书好,哀本勿灵。(这本书好,那本不好)”。这类结构中,量词的声调与指量短语中量词的声调相同,重音在量词上,并且可以和相应的远指量词对举。(注:吴语中其他地方也有量词用作定指标记的现象,虚化程度各有不同。潘文还提供了吴语中的另一种类型,温州话。表定指的量词只一种,且保留近指的距离意义。这种量词在语音上与量词在“近指代词+量词”结构中的连调形式相同,是“近指代词+量词”省略了近指代词的结果。石汝杰、刘丹青(1985)也描述了苏州方言量词的定指用法。)
我们认为,潘、陶文所述两种情形反映的是虚化过程中共存的、虚化程度不同的两种情形而已。这种虚化现象与北京话中的指示词的虚化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就是指示词语义上的中性化倾向。可以初步假设,汉语里定指标记有两种不同的虚化途径,一种是北京话的模式,脱落量词,近指词的指示义弱化,而后虚化为定冠词。另一种是粤语、吴语为代表的南方方言的模式,“指+量”复合形式中的指示词脱落,量词表量意义弱化,而后成为定指标记。
五 结语
当代语言学文献中所说的“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研究有两个主要方面。一种研究关注语法中的“形式”从何而来,也就是从词汇形式到句法和形态的演化,考察哪些实义词语在演变中逐渐失去实义,变成表达语法范畴的虚词或构词构形的虚语素。另一种语法化研究关注语法中的“范畴”从何而来,也就是语义内容和话语一语用功能是怎么样逐渐发展固化为专门的形态手段的。事实上,这两个方面也不是截然无关的。本文对指示词虚化的研究也说明了这一点。
语言的变化产生于语言的使用过程当中,因此,在语言的实际使用环境当中探寻演变过程和演变的动因自然是一个有效的途径。80年代有语言学家提出,昨天的章法就是今天的句法,强调的是演变产生于交际过程,句法范畴的产生与凝固化的动因是交际要求。90年代以后,随着语法化研究的深入和篇章语言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语法化的理念与话语分析的方法结合起来,通过对共时系统中的种种变异的研究透视历史演变的过程和动因,用这种思路考察语言,在其他语言研究中的成果越来越多。
现代汉语共时系统的研究有重视用法、重视口语的传统。前辈学者精心选取材料,细致描写用法,为我们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希望对共时系统中口语的考察不再拘泥于“能说”与“不能说”,哪些人这么说,哪些人那么说;而是更多地从基本的语法范畴着眼,去发现口语表达中那些具有形态句法学意义的现象,去考察那些体现语用原则的话语组织手段在共时系统中固化为句法手段的动态过程。这样,共时的细致描写才有可能揭示出一些更有意义的现象,进而深化我们对历时演变机制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