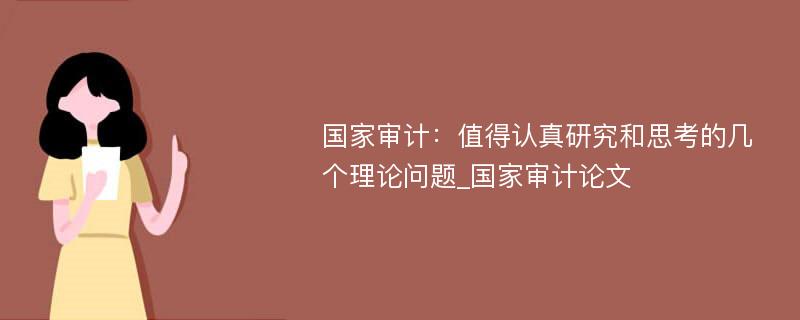
国家审计:值得认真研究思考的若干理论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真研究论文,理论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是“国家审计”还是“政府审计”
国家审计机关、内部审计机构和社会(民间)审计组织,这是指审计的主体。而作为被审计客体的,可以是政府部门或机构,也可以是企业单位、事业单位等等。因此,将国家审计与民间审计作为主要的对称,将政府审计与企业审计作为主要的对称,这是比较准确的。作为审计主体而言,应当使用“国家审计”一词,而不宜使用“政府审计”一词。
审计基础理论研究中,讲究基本概念的准确,对于国家审计的若干专业术语或名词,可以而且应当予以规范。但是,只有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入,才能为专业术语和名词的必要规范,创造一定的前提条件。
二、当代审计有没有一个什么“审计体系”
“审计体系”的说法,不知具体始于何时。这一说法的最基本表述,十分简单:当代审计包括国家审计、社会审计(民间审计)和内部审计,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审计体系”。但是,从理论思维的角度冷静地思考,究竟有没有一个由国家审计、内部审计和社会(民间)审计共同构成的什么“审计体系”,却值得仔细斟酌。
国家审计的主体是代表国家行使审计监督权的审计机关,社会(民间)审计的主体是加入某一个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各自的活动和行为,都有各自不同的法律予以规范。两者的职责和审计范围都各自不相同,怎么能纳入同一个什么“审计体系”呢?
至于内部审计,其本身就既有不同的主体及各种隶属关系,又有与国家审计、社会(民间)审计不同的工作范围和对象,更无法与国家审计、社会(民间)审计纳入同一个什么“审计体系”。
从世界范围来看,至今也没有发现哪个国家将国家审计与民间审计、内部审计归于一个什么“审计体系”。
从“审计体系”这一说法出发,我国审计理论和实务界部分人士,又进一步推衍出关于“体系”内三者“关系”的种种说法,而且持续多年围绕这样一个“伪问题”,始终争论不休,无端地耗费了宝贵的研究资源。
三、某些“审计理论”,能否“覆盖”国家审计
如果并不存在一个什么“审计体系”,如果我们承认国家审计、社会(民间)审计和内部审计是三种不同类型的审计;那么,至少可以初步明晰它们三者的理论分野。
毋庸讳言,目前在我国流行的某些“审计理论”,是从国外引进的。这些“审计理论”,绝大部分实际上是西方的民间审计理论,而不是国家审计理论。
当然不能否认,国家审计与民间审计在实际操作的若干方面,确实有共同点。但是,更不能否认,两者最早产生的时间不同,产生的历史背景也不同;两者存在的基础不同,因而审计的对象等等方面也大大地不相同。
我国有的学者曾经提出,我们所构建的“审计理论”,应当能够覆盖国家审计、民间审计和内部审计。这种愿望是良好的。遗憾的是,目前的某些“审计理论”,并没有进入这种理论“境界”,并不能达到“覆盖”的目的。
难道说国家审计就不存在自己特有的理论,而必须由民间审计的理论来“覆盖”吗?国家审计的历史,远远地比民间审计的历史悠久。当代国家审计已经成为国家组织的构成因素之一,它不需要建立真正科学的理论,用来正确解释并指导自己日益丰富的实践吗?
四、国家审计的产生是因为“两权分离”吗
“两权分离”的真正涵义是什么?“两权分离”究竟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国家审计产生的基础是由于“两权分离”吗?经济责任都是由于“两权分离”所带来的吗?这些最基本的理论问题是不能含糊的,也是不能回避的。问题的症结何在?可能在于理论的命题缺乏缜密的理论思维,也可能在于缺乏强有力的史实证明。
笔者迄今所见,是李凤鸣教授最早力排众议,提出不同看法的。李教授在《审计学》(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中写道:“审计是因授权管理经济活动的需要而产生的。”并且多年来始终坚持这一观点。“授权管理”还是“两权分离”,其内涵各不相同。在国家审计基础理论的研究中,这一问题决不可含糊其词。笔者期盼审计学界展开学术争鸣。
五、历史上的某些监督和经济监督活动就是国家审计吗
在中国审计史研究中,确实存在一种将国家审计庸俗化的倾向。这种倾向衍发的结果,必定为我国“审计重复论”和“审计取消论”提供威力不可低估的重型炮弹。
历史上的某些监督活动就是国家审计吗?
历史上的财政监督就是国家审计监督吗?
历史上的一切查账活动都是国家审计吗?
历史上的行政监察就是国家审计吗?
历史上的统计活动就是国家审计吗?
以上种种审计史研究中遇到的问题,都需要根据确切的历史事实,一一予以辩析考证,都说明切实弄清国家审计特定的基本内涵、切实加强审计基本理论研究的重要性。
六、所谓国家审计的“类型”,能否成立
国家审计机关隶属于议会,就是“立法型”吗?很遗憾,这些国家的审计机关并无立法权。称其为“立法型”是否名不副实?
国家审计机关的名称为某某审计法院,就是“司法型”吗?很遗憾,这些国家的审计机关并不隶属于司法机关,有些反而隶属于议会。
国家审计机关由政府或政府首脑领导,就是“行政型吗”?有的国家的审计机关由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领导,又不能算“行政型”,那究竟是什么“类型”呢?
关于国家审计机关的隶属关系或领导体制问题,显然不能与国家审计的“类型”划等号,但在国家审计基础理论研究中仍然值得重视。应当提请研究者注意的是,我国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决不等同于西方国家中政府与议会的关系,决非西方国家三权分立中的行政权与立法权鼎足对峙。因此,我国国家最高审计机关究竟是设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还是设在国务院,与西方国家最高审计机关是否设在议会,不存在任何可比性,不可能套上任何一种所谓“类型”。对于各国最高审计机关的隶属关系或领导体制,也要具体进行分析,不能认为只有某种领导体制最好。
七、国家审计与节约监督成本有什么关系
如果国家审计的存在,仅仅是为了对国家财政财务收支实施有效的监督;那么,财政部门所实施的财政监督,税务部门所实施的税务监督,银行部门所实施的金融监督等等经济监督形式,完全可以从不同的方位或角度出发有效达到监督目的,而无须专门建立审计机关,实行国家审计监督制度。可是,人们已经直觉到,各种经济监督形式都存在,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监督的作用,但仍然无法达到预期监督目的;正是在此前提下,才迫切需要专门建立审计机关,实施国家审计监督,从而真正有效地达到监督目的。这种直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国家审计为什么而存在,因而是极其可贵的。
然而,更深层次的思考可以发现,国家审计虽然花费一定的监督成本,但是从总体上能够降低整个社会的巨额监督成本。国家审计特有监督程序和方法技术的科学运用所获得的审计成果,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的效益;国家审计制度的存在本身所构成的一种威慑力量,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节约整个社会的监督成本。节约监督成本,难道不正是构成国家审计在当代世界各国得以普遍存在的最根本理由之一吗?
八、国家审计在经济监督中究竟处于何种位置
我国当代国家审计监督权,由宪法和审计法律所赋予,具有较高的独立性和权威性,这是由国家审计工作本身的特点和需要所决定的。国家审计没有对经济业务进行具体管理的任何职责和权限,因而实施审计监督需要法律保障。这样一种法律保障,并不意味着国家审计作为一种经济监督形式,高于其它各种经济监督。国家审计不能居高临下。
国家审计也不可能包打天下。国家审计的监督对象,并不是国民经济的全部活动,而只是国家财政财务收支及其相关经济活动。国家审计机关对财政财务收支的监督,也不是实施全面的、普遍的、日常的检查(否则,国家审计人员再增加十倍也无济于事),而只能是采取带综合性的、有重点的、定期的审查。我国国家审计与其它各种经济监督的关系,只能是在科学分工的基础上,相互配合、共同协作的关系。
国家审计与其它经济监督,在监督的对象、范围、内容、程序和方式方法等方面,有同也有异。如果只从表面去观察国家审计与其它经济监督在若干方面具有相同点,而忽视他们各自深刻的内涵,不注重深入研究他们在监督的范围、程序和方式方法等方面的本质差异;那么,既可能错误地得出国家审计是一种“重复监督”的结论,从而导致国家审计取消论,又可能走向将国家审计地位无限制拔高的另一个极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