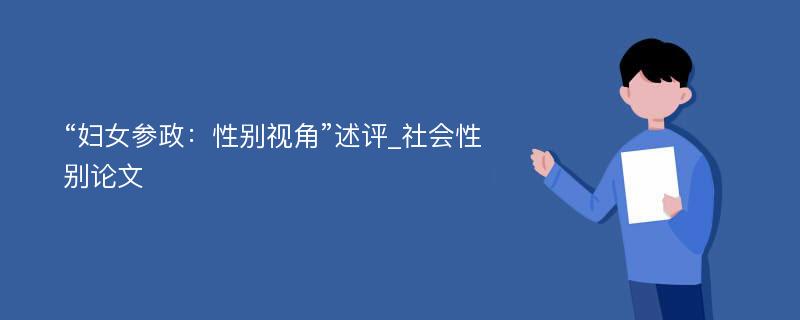
《女性参政——社会性别的追问》评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性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治,让女人走开”,这句话似乎适用于古今中外的各个国家,即便在现代社会也是如此。鲍静博士(2013:2)在其著作《女性参政——社会性别的追问》(以下简称《女性参政》)一书的开篇即发问:“生活世界和政治世界果然已经改观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女人和男人可以有着同等的权力,并同等程度地改变着世界的面貌吗?”即便是在男女平等俨然已成为常识的今日,答案显然也是否定的。鲍静博士的《女性参政》一书以社会性别理论为基础,透过社会性别的视角,对女性参政问题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对其在西方的起源和早期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和探讨,对中国共产党的女性参政思想及其实践进行了细致梳理,并对当代中国女性参政的现状与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国家主导式的提升女性政治参与度的对策。 一、社会性别理论与女性参政的理论考察 社会性别理论是《女性参政》一书的理论分析基础,因此,全书首先梳理了与这一理论相关的概念。第一个被考察的概念是“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的概念相比,社会性别概念突出强调人的性别意识、性别行为都是在社会生活的制约下形成的。女性所扮演的性别角色,并非是由她们与生俱来的生理和心理因素所决定,而是社会生活的产物,并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变化”(鲍静,2013:15-16)。在此基础上,作者考察了第二个重要概念——“社会性别制度”,并对社会性别制度中的权力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社会性别是人类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在生理性别的基础上塑造出的男女两性之间的权力不平等。一方面,社会通过社会性别来塑造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二元对立,认为一个人要么是拥有坚强、进取的男性气质,要么是拥有温顺、依赖的女性气质,二者不可兼容。另一方面,社会又通过构建性别的刻板印象来塑造社会性别关系秩序,即对男性的社会角色期待是与男性气质相吻合的从事生产、竞争、充当家庭生存的供养者,对女性的社会角色期待则是与女性气质相符的操持家务、照料家庭,这种社会性别分工制度就形成了等级化的性别关系秩序,使男性的统治地位合法化。在对“社会性别”和“社会性别制度”两个重要概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作者还梳理了女性主义的思想流派,包括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四个流派,并对各个流派的社会性别观念和主张进行了比较分析,向读者展示了社会性别理论的开放与多元。 在做好基础理论准备工作以后,作者以社会性别理论的视角对女性参政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审视。作者认为,长期以来政治参与中女性视角的缺失,使得政治领域中男性的经历被假设为普遍经历,而女性的权利则被置于男性家长的权力之下,中外历史莫不如此。女性参政在主流政治行为中的缺失,使得政治行为具有暴力性、缺失公共性,并具有对男性气质的复制性等特点。因此,女性参政对于现代政治生活和政治行为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女性参与公共事务,在维护公共利益、遵循政治规范、增强民众的认同,维护政治稳定和促进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社会化等诸方面都将起着重要作用,是实现双赢或多赢的有效方式”(鲍静,2013:60)。 二、女性参政的历史分析 在理论分析之外,历史分析是《女性参政》一书的重要分析方法。 在历史分析方面,该书首先以英国为例,描述了自1866年“女士请愿书”开始,到1918年部分英国女性获得选举权为止的波澜壮阔的女性选举权运动,并分析了英国女性在这一伟大历史运动中的各种策略。“女子请愿书”运动发生在1866年6月6日,两位女性在英国议会大厅提交了请愿书,要求议会考虑在适当的资格条件下给予女性选举权。她们受狄斯雷利关于妇女投票权讲话的启发,召集成立了一个非正式的女性选举委员会,并在短时间内征集了1 499个“杰出的受人尊敬的女性”的签名,以请愿书的形式表达了英国女性的政治要求,公开地提出了要求女性与男性一样拥有选举权。在英国女性选举权运动的初期,有一位知名的男性自由主义思想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就是英国著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穆勒强烈呼吁女性的参政权、工作权、受教育权和婚姻自主权,对英国女性参政运动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他认为,“女性长期被排斥在政治等崇高的职业之外,无法表达自己的意见,只能从属于男人。因此,只有让女性与男性享有平等的法律权利、受教育权利、就业权利,女性才能真正享有自由,而女性参政是保障这些权利的主要手段”(鲍静,2013:82-83)。1867年5月,在英国女性选举权运动者再次向议会提交大量请愿书的情况下,穆勒提出了女性选举权修正案,要求“扩展选举权(给妇女)”,并认为这是“公平/公正的要求”。尽管这一修正案最终还是被否决,但这也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毕竟英国议会正式提出了女性的议会选举权问题。 接下来,作者将视线转向中国,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性别制度和社会性别模式。中国传统社会是典型的父权社会,在其中,“男子处于支配、统治的地位,而女性则处于与之相对的被支配、被统治的地位,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男刚女柔、男外女内的社会性别模式”(鲍静,2013:103)。在这种社会性别模式下,女性缺乏独立自主性,更无法进行有效的政治参与。在谈到中国传统社会对女性的控制时,作者认为女性缠足现象便是一个重要的表现。“缠足不仅是中国历史上对女性身体摧残的丑恶现象,更是实行男权文化控制的证明”(鲍静,2013:104)。在中国历史上,能真正参政的女性极少,即便参政,也被认为是“干预朝政”,时至今日仍然遭受各种非议,比如吕后、武则天等人。中国传统社会往往将女人干政视为大逆不道乃至祸国殃民,因为在儒家的观念中,女子掌权是与天命相违的,必将带来横祸,因此,“红颜祸水”常常成为男性政治失败的替罪羊。女性参政在中国近代逐渐开始兴起,但它并不是一场独立的女性平权运动,“近代中国的社会性别理论和实践是配合着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的,其批判性大于建设性,缺乏系统的理论建构和深入的理性思考,这样的理论和实践极易淹没在革命的冲动和喧嚣中,而迷失其独立的价值”(鲍静,2013:125)。 三、当代中国女性参政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女性参政》一书最重要的落脚点在于对当代中国女性参政的现状进行分析,剖析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要真正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当代中国女性参政问题,必须先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女性参政思想和理念。该书用了较多的笔墨来论述从革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共产党女性参政思想和政策的发展演进过程,以社会性别理论为视角,将其分为革命模式、政治动员模式、发展模式三个阶段,并对当代中国女性参政的环境、政策和现状进行了描述和分析。 作为世界上较早建立性别平等政策的国家之一,当代中国在女性参政环境建设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尤其是在女性参政的相关法律法规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女性参政权利在法律上得到了完整的保护。同时,政府成立了专门的组织——妇联——来促进包括参政权利在内的妇女权利的主张和实现,并采取了多种政策和措施鼓励女干部的培养和选拔。然而,尽管当代中国女性参政已经有了较好的环境,但女性参政的实际水平还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 《女性参政》一书将当代中国女性参政的障碍归结为女性参政意识缺乏、参政能力薄弱、参政机会缺乏。女性参政意识缺乏,一方面源于社会性别意识的不断强化,对于男人和女人而言都是如此;另一方面则源于参政理念中的“男性意识主流化”,使得女性如果要在政治领域取得成绩,就必须按照男性的模式开展活动。女性参政能力薄弱,作者则认为是社会性别制度下形成的职业隔离所造成的结果。女性参政机会缺乏,在作者看来,与社会性别的政策盲视有着密切的关联,即相关政策没有考虑到男性与女性的差别,使得看似男女平等的政策,在现实中却造成了女性参政实际机会的缺乏。 在对当代中国女性参政的现状和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女性参政》一书提出了相关的对策。第一,理念重塑:从追求男女平等到寻求两性共治的性别公正。“性别公正的实现,是在承认两性先天生理差异、后天社会性别差异的基础上来认识两性关系,这样既可以避免性别本质主义对两性生理差异的忽视,也可以处理性别构建主义所形成的在女性特殊性上越走越远的问题”(鲍静,2013:197-198)。第二,社会性别主流化,即将性别观点纳入所有政策和方案的主流,在制定政策和方案时分析其对男性和女性分别有什么样的影响,同时,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也要评估其对男性和女性的实际影响,以确保政策结果的公平。第三,女性赋权,即通过加强培训等措施,提升女性参政能力,并加强女性组织建设,使得其在推动社会性别主流化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鲍静博士的《女性参政》一书最大的价值在于将社会性别理论运用到公共管理的研究中,以社会性别视角来审视女性参政问题,丰富了公共管理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具体而言,该书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第一,对中国女性参政问题进行了历史分析,梳理了中国女性参政的兴起和发展历程;第二,对中国共产党的女性参政思想和实践进行了归纳和总结;第三,分析了中国女性参政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根源所在;第四,提出了促进中国女性参政的国家主导式政治参与模式。该书倡导的从追求男女平等转向追求性别公正的两性共治的理念,以及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的观点对于提升女性参政水平极富启发性。当然,该书也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可以考虑增加当前国外女性参政发展现状和政策方面的内容,并适当进行国别比较研究,这样全书的论证将会变得更为严密,论据也会更加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