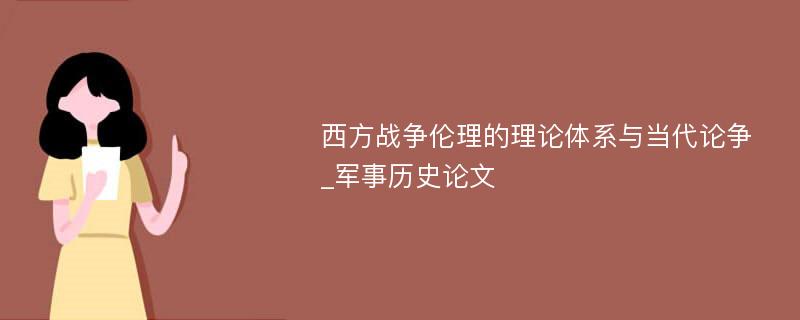
西方战争伦理的理论体系及当代论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理论体系论文,当代论文,战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1)07-0004-17
[修回日期:2011-04-21]
西方对战争伦理的研究由来已久。美国的约翰·坦普尔·司温(John Temple Swing)认为:“自史前时代起,人类社会的一大特点就在于,人们总是试图通过武力来解决分歧。人类基于对战祸的厌恶而对使用武力加以理性限制的努力几乎和前者的历史一样久远。”①早期部落群体打斗的记载表明,某些道德关怀受到了勇士们的重视,包括不伤及妇女儿童和宽待俘虏等。有明确记载的,战争伦理领域的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发生在公元1139年,当时欧洲的教皇因诺森特二世从伦理角度出发,认为某些武器太过残忍,号召基督教各公国禁止在战争中对基督徒使用穿透力强的硬弩。这可以认为是对战争行为进行限制的早期努力。而现代意义上的西方战争伦理理论则诞生于1905年,时年H.E.沃纳(H.E.Warner)出版了《武力的伦理》(Ethics of Force)一书,这是世界近现代历史上第一部有关战争伦理的系统专门著作。②
一 西方战争伦理的理论体系
经过多年的发展,西方战争伦理已经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概括起来,可分为战争权利伦理、战争行为伦理及战争责任伦理三个部分。
(一)“向敌对国家宣战的权利”③——战争权利伦理
战争权利伦理,也有学者称之为“开战正义”,④即某一行为体在何种条件下具有合法使用武力的权利。关于战争权利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中世纪。⑤自近代以来,对战争权利的研究得到了很大发展。1919年,在国际联盟成立之际,其《盟约》第12条第1款就规定“不得从事战争”。⑥而1928年由当时的主要大国签署的《巴黎非战公约》第1条也规定“废弃以战争为国家相互关系中施行国家政策的工具”。⑦然而,这两个公约基本只具有象征意义,并未在实践中具有有效的国际道义约束力。可以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战争一直被视为国家推行政策的一种正常工具。国家只需在战前向敌国履行宣战义务,宣告进入交战状态,战争即可视为“合法”,而对武力使用的正当性检验则总是以正义战争、非正义战争、侵略性战争、防卫性战争等措辞来辨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因为主权原则的首要地位与武器技术不断提升的摧毁性相结合,人们普遍接受战争再不能被合理地视为治国的‘正常’工具这一观点”。⑧人类开始谋求“一般性禁止武力使用”,⑨被称为“约束武力使用的法律王冠上的明珠”⑩的《联合国宪章》(以下简称《宪章》)应运而生,其第2条第4款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11)根据这一规定,武力使用受到了一般性的禁止,即使之成为非法。当然,《宪章》也对武力使用做出了例外规定。《宪章》第51条规定:“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武力攻击时,在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办法,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以前,本宪章不得认为禁止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会员国因行使此项自卫权而采取之办法,应立向安全理事会报告,此项办法于任何方面不得影响该会按照本宪章随时采取其所认为必要行动之权责,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12)《宪章》中这两个相互作用的条款共同构成了“禁止武力使用”的当代战争伦理的基本准则,为国际社会处理这一问题提供了根本性的依据。
人们普遍认为,《宪章》既规定了“一般性禁止武力使用”,同时也为开展正义战争的权利留下了窗口。国际法专家路易斯·亨金(Louis Henkin)认为,在《宪章》的框架下,“国家应当享有独立、在其领土内的完全自治以及不受干涉的权利。改变——除了通过内部武力实现的内部改变——都必须通过国际协定和平实现。今后,应该有一定的秩序,以便国际社会能够集中精力更好地满足正义和人类福祉的需要”。(13)关于在《宪章》的约束下有没有合法战争的问题,亨金认为:“将来,唯一的‘正义战争’将是抗击侵略者的战争——由受害国自卫、由受害国之外的其他国家或所有国家进行集体自卫。”(14)简单地说,就是自卫战争和联合国授权的战争为合法战争,其余战争均被定性为非法。也有西方学者为了更好地确认战争权利,区分合法战争和非法战争,把诉诸战争的权利分解为六个方面,即正当理由、合法权威、正当目的、成功的可能性、相称性和最后手段。(15)满足这六个方面的要求,即认为拥有诉诸战争的合法权利,所从事之战争为符合战争伦理标准的合法战争。
(二)“战争期间的权利”(16)——战争行为伦理
战争行为伦理,也有学者称之为“交战正义”,(17)即战争双方的行为都应受到相关战争法直至国际道义的约束,其基本的逻辑来源于“程序正义”思想,即认为目的的道德性不能直接证明手段的正当性,正义和实现正义的手段不可分离。
按照西方战争伦理的主流观点,战争行为应主要遵循两个原则:相称性和区别性。所谓相称性,其“关键的问题就是对某个战争行动导致的罪恶同那相同的行动获得的收益进行权衡”,即或者是“将益处最大化并且将害处最小化”,或者是“某一战争行动的破坏性的效果不能同它追求的目标不相称”。(18)所谓区别性,指的是“非战斗人员的生命和财产以及某些种类的民用目标不应该被作为军事暴力的目标……区别性原则的应用主要是集中在那种虽居于次要的地位但却是基础性的‘非战斗人员豁免权’原则上”。(19)基于这两个原则,西方针对战争行为形成了大量的伦理规范和道义约束,而且基本都法典化了,大致分属于海牙体系和日内瓦体系,前者重在对战争手段和方法的限制,后者重在对战争中战俘和平民的保护。
海牙体系并不只包括两次海牙会议所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其往上可以追溯到1856年在巴黎签订的《巴黎会议关于海上若干原则的宣言》,规定“从此以后永远取缔私掠船制”。(20)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对战争手段的限制进一步细化,推动签署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等,这些条约对武装冲突中的作战手段和方法进行了全方位的规范。值得一提的是,1977年《日内瓦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提出的限制战争行为“三原则”受到了广泛的认同,并对其后各公约的签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一,在任何武装冲突下,冲突各方选择作战方法和手段的权利,不是无限的;第二,禁止使用属于引起过分伤害和不必要痛苦的性质的武器、投射物质及作战方法;第三,禁止使用旨在或可能对自然环境引起广泛、长期而严重损害的作战方法和手段。”(21)
日内瓦体系则主要侧重对战争中战俘和平民的保护。1862年的《日内瓦公约》提出了保护战场伤病员的规则。1868年第二次《日内瓦公约》将之扩展到保护海战中受伤的士兵。1929年第三次《日内瓦公约》规定保护战俘,指出战俘不是罪犯,交战双方必须人道地对待对方战俘,并且在战后释放战俘。1949年第四次《日内瓦公约》增加了战时保护平民的内容。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战时平民置于国际法的保护之下,明确禁止战争期间有意杀害、刑讯、绑架平民,禁止对平民实施超出司法权范围的审判和处罚。1977年,《日内瓦公约》把对平民的保护延伸到非正式宣布为交战国的公民、内战冲突中的平民以及在交战国家或区域活动的任何提供宗教、医疗和人道援助的人士。关于区分战斗人员与平民的问题,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主张,难以识别并不等于给予政府以滥杀的权利,政府负有区分战斗人员与平民的责任。(22)
(三)“战后的权利”(23)——战争责任伦理
战争责任伦理,也有学者称之为“战后正义”,(24)即战胜国不应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来处置战败国,而应遵从某种规范,因为“犯罪不能从他人的罪行中遗传下来”。(25)现代意义上的战争责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清算战争罪行、确保战败国的政治自由、承担重建义务。
关于清算战争罪行,这是西方在战争实践中最初认识到的“战争责任”,主要是对发动非正义战争负有责任的国家和个人进行审判和惩罚。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就认为,领袖和官员对战争负有责任。(26)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也认为统治者应负战争责任,因为“作为发动战争的统治者,他得不断为这些人(追随者——笔者注)提供精神的和物质的必要奖赏,无论这奖赏是来自天国还是凡世,否则这架机器就不会运转”。(27)西方对清算战争罪行的侧重点的认识经历了从清算整个国家到清算具体战犯的一个过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侧重于对战败国整个国家的惩罚,即通过《凡尔赛和约》惩罚德国,逼其割地赔款,防其东山再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盟国普遍认识到,对战败国本身的过分惩罚无法消除战争的根源,于是转而侧重于对发动战争的战争罪犯进行审判,比较典型的是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
关于确保战败国的政治自由,最早意识到并将之上升到理论高度加以概括的是德国大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康德用“战后的权利”这一概念来概括战胜国的战争责任,指出:“被征服的国家和其臣民,都不因国家被征服而丧失他们政治的自由。这样,被征服的国家不会降为殖民地,被征服国的臣民不至于成为奴隶。否则,这场战争便成为执行惩罚性的战争。”(28)
关于承担重建义务,指的是战胜国的任务并不是简单地推倒一个旧政权。战胜国和其他任何有能力的国家都应该对战败国进行人道主义援助,迅速重建一个政治独立、经济稳定的自由国家,以利于国家重返国际体系,最终消除战争根源。战胜国和国际社会的责任主要包括政治和经济两大方面。政治上,战争责任的终点是完成向支援民政当局过渡,使其能够自行保障安全、法治、社会服务与经济活动,并尽可能消除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从而减少另一次危机再度出现的可能性。经济上主要是包括:雇佣当地民众恢复必要的服务,如食品和水分配、垃圾清除和基本医疗服务;恢复基础设施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改革经济体系,使其重新加入国际经济组织,参与国际分工;改善当地人的福利。(29)
总之,当代西方战争伦理是一个庞杂的理论体系,由于受到基督教传统伦理的影响,主要持和平反战立场。(30)但相比于之前曾在西方盛行一时的无原则的和平主义,当代西方战争伦理的主流思想并不否定一切战争,而是吸取了和平主义和正义战争理论的有益成分,站在更加务实的角度看待战争与和平的关系问题。因此,当代西方战争伦理的主流思想可称之为是“务实的和平主义”。同时应当指出,在当前的国际社会,那种幻想认为单纯依靠战争伦理就能够缔造世界和平的纯理想主义、片面否定战争伦理并认为战争伦理纯粹只是大国最大限度追求国家利益工具的虚无主义以及认为“战争本质上就是道德的”并从根本上否定战争伦理的军国主义,在当今世界的影响力都日渐式微。
二 西方战争伦理的当代论争
长期以来,西方在战争伦理领域提出了很多创新性的新思想、新概念,体现了西方在战争实践中不断改造战争伦理以适应时代和战争需要的创造力。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的行为体根据不同的目的对其进行了不同的解读,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这里仅以人道主义干涉、先发制人、核伦理和太空军事化四个问题为例加以阐述。
(一)人道主义干涉问题
关于干涉的合法性特别是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问题,一直是战争伦理领域争论的焦点问题。正如约瑟夫·奈(Joseph S.Nye)所指,干涉的界定之所以困难,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是规范性概念,人们需要对之做出道德性判断。(31)
赞同者认为,为了保护某些民族不受血腥的镇压或者肆无忌惮的侵犯人权的伤害,对相应的国家采取军事行动是正当的。(32)著名的英国国际法学者、前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劳特派特(Hersch Lauterpacht)认为:“《联合国宪章》承认促进基本人权与自由的尊重是联合国组织的主要目标之一。这标志着朝向把人道主义干涉原则提升为有组织的国际社会的根本原则方向前进了一步。”他还宣称:“因为‘人权与基本自由’已经成为宪章的经常特点,并且具有法律义务的性质,这些权利和自由可能已经不是在本质上属于国内管辖的事项。”(33)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打的就是人道主义干涉的旗号。通过展示所谓的南斯拉夫军队屠杀阿族平民的证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试图说服全世界相信科索沃正面临人道主义灾难,并最终为获得武力干涉南斯拉夫事务,发动科索沃战争确立了“国际道义”基础。有些学者据此认为,当今国际社会时有发生的人道主义干涉实践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从而证明国际习惯法关于人道主义干涉规则的存在。(34)应当指出的是,科索沃战争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号,但无法获得联合国的授权,联合国更没有直接参与。然而2011年3月17日和30日,联合国先后通过第1973号和第1975号决议,虽然决议中并无明确授权使用武力的条款,但其中强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可能遭受袭击的平民和平民居住区”(35)以及“防止对平民使用重型武器”(36)的内容却直接成为武力干涉的理由,联合国甚至直接参与了武力干涉科特迪瓦的军事行动。人道主义干涉大有“合法化”、“常态化”的趋势。
也有许多西方学者对国际人权保护持谨慎的怀疑态度。(37)以弗里德利希·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武力代表强制,强制本身就是“恶”,因此一切使用武力的干涉皆不正当。(38)他们认为,虽然联合国武装干预的参与者是在人道主义的旗帜下采取行动的,具有相当的合法性,比如联合国处理索马里、波黑和海地危机。但联合国往往不能实施有效的控制,对人道主义的武装干预仍然主要由大国主导,这也就意味着联合国武装干涉行动经常在事实上背离了人道主义方向成为某些国家追求私利的工具。因此,目前西方许多学者并不愿意将人道主义干涉正式合法化,因为在当今世界上,个人仍然主要“依附于国家,是国家使其相对的安全成为可能”。(39)更何况,“战争会造成最大的不公、对人权最严重的侵犯以及对民族自决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严重的破坏。战争本来就是非正义的”。(40)当前西方著名的国际人权法学者杰克·唐纳利(Jack Donnelly)也认为:“现有的国家主权原则仍然禁止任何国家为了制止迫害以及大多数其他种类的违反人权行为而采取强制性的对外行动。”(41)所以,以别国的人权危机作为干涉的理由,目前国际社会尚存在较大争议。而针对有部分学者认为应当按照结果来评判人道主义干涉合理性的问题,尼古拉斯·惠勒(Nicholas J.Wheeler)指出,尽管干涉的结果很重要,但干涉方不可能对结果进行明确的事先判定,故而依照结果来评判干涉是不合适的。(42)
(二)先发制人问题
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基本精神,只有等到威胁变得非常严重和明显时,才可以实施自卫反击。然而,关于先发制人的理论却从来没有远离人们的视线。2001年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借助其在国际道义上的巨大“软实力”,适时提出先发制人战略。关于先发制人的合理性问题成了西方学术界争论的焦点。
赞同者认为,先发制人的主要依据来自于《联合国宪章》所赋予的自卫权,即一方有权使用武力打击任何可能来自未来另外一个国家的攻击,即使这样的攻击实际上并未发生。最典型的对先发制人理论的辩护来自于美国前总统小布什。2002年6月,小布什在西点军校发表演讲称:“如果我们等待威胁完全形成,我们就会等得太久了……反恐战争不能仅通过防御取胜。我们必须向敌人开战,打乱他们的计划,在最坏的威胁形成以前就面对它。”(43)其后,先发制人正式成为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威胁越大,不采取行动的风险也就越大,采取预先的自卫行动的迫切性就越大,即使我们还不明确敌人将于何时何地发动攻击。为了防止我们的对手采取这种敌对行动,美国将在必要时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44)这一战略后来在2006年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得到进一步确认。
反对者则认为,没有限制的“先发制人”必然导致战争像脱缰野马般不可驾驭,最终损害自己的利益。卡尔·米勒(Karl P.Mueller)认为,如果先发制人成为惯例,不仅会扰乱当前的国际秩序,还会成为其他国际行为主体用来对付美国的手段,而这两种局面到头来均有害于美国的安全和价值观。(45)西方许多学者提出要对“先发制人”的条件进行限制。如妮塔·克劳福德(Neta C.Crawford)就认为,从战争伦理角度出发,2003年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是“不合法”的,美国将战争对象从打击恐怖组织转移到颠覆“流氓国家”政权是一个“大有问题的跳跃”。她指出,先发制人战争只有同时符合以下四项条件才是合法的:准备实施先发制人的一方应当对自卫概念做出严格的限定;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近在眼前的”;能够极大地减少甚至消除威胁及其即将造成的伤害;军事力量必须是最后的手段。(46)
(三)核伦理问题
西方关于核伦理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综观当代西方核伦理的论争,根据对核伦理能否有效限制核武器扩散和使用的态度,可分为以下三大流派。
其一,现实主义流派。其代表人物是约瑟夫·奈,他提出的核武器战略的五条伦理原则至今仍深具影响。这五条原则为:核防御应是正当的;绝不能视核武器为常规武器;把对无辜平民的核伤害减少到最低限度;实行“平衡威慑政策”,充分运用调停、斡旋、谈判等外交手段避免核战争;逐步减少对核武器的依赖,建立一整套更有效的限制核武器的试验、生产和扩散的“国际机制”。(47)现实主义流派的许多人还认为,维持国际秩序的最重要手段是“均势”,因而实现核均势能够避免核大战。
其二,怀疑论者,对核伦理的作用持怀疑态度。比较典型的是“宿命论”流派,代表人物是迈克尔·曼德尔鲍姆(Michael Mandelbaum),认为核战争太恐怖,打不得,以至于打不起来。核裁军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太艰难。“没有核武器的世界”与“没有核战争的世界”同样是不会出现的,或许在公元3000年以前,将是一个核均势为特征的“核和平的世界”。他们认为,人类将长期生活在一个以核均势为特征的“核和平的世界”。核武器就好比是人类的一种疾病,一下子治不好,但也死不了,只要查明这一痼疾,对症下药,也能维持一个正常人的生活。(48)还有一种不同的怀疑论主张,如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提出,核武器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战争的样式,人们关于道德的观念以及由此而来的正义战争理论便都成了多余的东西。(49)
其三,理想主义流派。比较典型的是“无核世界”的信仰者,但目前摇旗呐喊的主要是政治人物,其真实意图还有待进一步观察。早在1987年,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就已经提出了“无核世界”的口号。(50)奥巴马在当选美国总统后也提出过这一倡议。当然不能据此简单地推断,戈尔巴乔夫和奥巴马都是“无核世界”理论的真正拥护者。但身为核大国的总统提出这一倡议,毕竟对于动员世界军控舆论、促进核裁军与核不扩散运动的发展还是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的。同时应认识到,在当前以及可预见的将来,“无核世界”仍然只是一个理想,或者说只是一个梦想,在当前以现实主义为国际关系主流价值取向的情况下,这种理想主义的主张在融入实际政治进程中通常会发生现实主义的变异。
(四)太空军事化问题
关于太空到底是应该军事化还是非军事化的问题,西方现在争论十分激烈。目前,西方赞同太空军事化的主要是在技术和资金上都占有绝对领先地位的美国。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投票支持谈判制定一个防止在外空进行军备竞赛的条约,只有美国反对,以色列弃权。美国政府认为,目前已经存在的武器控制机制已经足够,无须对一个并不存在的威胁花费精力。(51)
大部分国家对太空军事化持反对态度。因为它们意识到超级大国探索空间的努力可能严重损害其权利和利益。(52)反对者的主要依据是《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活动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简称《外空条约》)中所确认的关于外空利用的“和平目的”原则。有“外空宪章”之称的《外空条约》的导言就载明:“承认为和平目的而探测及使用外层空间所取得的进展关系到全人类共同的利益……愿意在为和平目的而探测及使用外层空间的科学以及法律方面的广泛国际合作做出贡献。”(53)根据对“和平目的”的不同理解,反对太空军事化的国家又可分为多数派和少数派。约翰·J·克莱因(John J.Klein)在《太空战——战略、原则和政策》一书中将多数派的主流概括为“隐匿派”。隐匿派认为既然太空力量能够合法地在别国的上空“观察”该国内部的信息,那么就应该让太空“无战争化、无武器化”,这样才能继续保持在别国上空侦察的合法性。(54)少数派主要是西方一些空间技术不很发达的国家。它们认为,“和平”是指“非军事化”,这一要求非常高,按照这一观点,甚至和平时期的日常性军事活动(比如通信和气象观测)都应该禁止。(55)
应当指出,在当前的战争伦理领域,关于“绿色战争”问题或称战争环保问题、对战争罪行的审判权问题以及对恐怖主义概念的界定问题,国际社会战争伦理学界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鉴于篇幅所限,此处不做阐述。
三 战争伦理作用趋势的辩证分析
通过对战争伦理作用的现实环境的解读,我们可以认清,在当前及可预见的未来,西方战争伦理仍将长期受到现实环境的极大制约。同时,随着战争伦理作用机制的不断发展和强化,其对战争的制约作用以及对战争行为的规范作用必将进一步增强。
(一)战争伦理作用的发挥仍受现实环境的制约
当代西方在民间确实有对战争伦理持理想主义态度的力量,但从国家层面而言,对战争伦理的实际运用仍然主要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受到现实环境的极大制约。
1.国家利益仍然是发动战争的根本动因
由于人类社会总体上仍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仍然是最具影响力的行为体,国家利益仍然是国家处理战争伦理相关问题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首先,是否介入战争以及在何处介入战争,主要是受国家利益最大化和长期化的驱使。对比20世纪90年代美军因损失18名士兵而匆忙撤出索马里以及如今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虽阵亡数千人而坚持实施稳定行动,并不是现在的美国政府比当时的克林顿政府强硬,而主要是因为美国在索马里的现实利益十分有限。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利益则不然,前者是重要的海湾产油国,后者拥有任何争夺世界霸权的国家都梦寐以求的地缘资源。二者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其次,当代西方战争伦理无法阻止为了拓展国家利益而发动的战争。主要反映在目前国际社会还没有执行战争伦理的强制机制。以2003年伊拉克战争为例,美国并未获得联合国授权。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也都反对对一个主权国家动武。但美国仍然能够召集“志愿同盟”,绕开联合国入侵伊拉克,为入侵主权国家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对此,连许多西方学者都感慨,《联合国宪章》只能界定正义,却无法维护正义。
2.现实主义仍然是运用战争伦理的主要行为准则
首先,阻止战争的最强有力的因素仍然主要是实力。具体而言,就是战争被动方是否具有足够的反制能力,让企图主动挑起战争的一方在权衡利弊之后因为顾忌对手的报复而选择“高姿态”的妥协。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自从核武器诞生以来,从来还没有哪一个拥核国家受到过另一个国家的全面进攻。其次,即使存在理想主义,但理想主义的主张在融入实际政治进程中经常发生现实主义的异变。以奥巴马提出“无核世界”的口号为例,这一倡议反映出民间确实有一股对战争伦理持理想主义态度的力量存在。但是,在现实政治中,奥巴马除了推动同俄罗斯进行核军备裁减以外,他做得更多的是投入越来越多的资金进行反导系统的构建、进行核武库的维护与更新等。这充分说明,理想主义在美国政治中根本没有生存空间。在保守主义占主流的情况下,奥巴马尽管提出了不少理想主义的口号,但仍沿着现实主义路线走下去。最后,战胜国对本方所犯战争罪行的追究通常“举重若轻”。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对战争罪行的审判仍然主要停留在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审判。正如康德所言:“战争的结局已经决定了正义属于哪一方。”(56)战后的正义往往就是战胜者的正义,而不是普遍的正义。这就决定了国际法庭主要针对战败国进行审判,而战胜方自然不会将自己的军人移交国际法庭受审。即使犯下战争罪行,国内法庭一般也是“从轻发落”。如在“米莱大屠杀”中对越南平民下达“杀无赦”命令的威廉·凯利中尉,起初被美国军事法庭判处终身监禁,但由于尼克松总统插手,对他的处罚一再减轻,最终不了了之。而伊拉克“虐俘”事件的焦点人物——女兵英格兰,虽然对其指控多达19项,最高可判处38年监禁,但最终只宣判监禁2年。
3.功利主义仍然是“创新”战争伦理的基本价值取向
西方战争伦理从来就不缺乏“创新”,从奥古斯丁运用基督教基本教义对正义战争进行基本界定,到当前西方所提出来的各种新的干涉主义理论,无不体现着西方在战争实践中不断改造战争伦理以适应时代和战争需要的创造力。但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些“创新”只有一个轴心,就是以功利主义为根本价值取向。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挖空心思找寻种种“趋近”法理和伦理的战争借口,为干涉别国事务服务。“人道主义干涉”就是西方近年来屡次为干涉别国主权而打出来的旗号。第二,利用技术优势,以限制战争行为的名义限制对手的竞争。以美军提出“绿色战争”概念为例,美国试图在北极的争夺战中打“环保”牌,在强调本国航母编队和战斗机“绿色环保”的同时,要求其他国家的军舰和战斗机也要“环保”,否则就指责对方破坏北极本已十分脆弱的环境。美军提出“绿色战争”概念的实质是通过在军事上设立“绿色壁垒”来争夺话语权,从而赢得地缘战略角逐中的主动。第三,根据形势变化,利用国际舆论环境,因势利导降低战争门槛,为侵略提供“合法”性。比如,美国借助九一一事件之后在国际道义上积累的巨大“软实力”,适时提出先发制人战略。通过说明先发制人有理,降低了发动战争的门槛,从“基于威胁”降低为“基于能力”——只要对方有威胁我方国家安全的能力,无论其客观上是否有意愿,都能成为美国发动战争的理由。
(二)战争伦理发挥作用日趋增强的历史必然性
从总体上而言,随着文明不断发展进步,人类要和平,社会要发展,已经成了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尽管在实际运用中,战争伦理仍然受到现实环境的极大制约,但客观地看,随着人类良知的觉醒、世界人民鉴别力的提高以及所有其他有利因素的共同推动,战争伦理必然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战争制约及规范机制的完善
尽管相对于武器和军队这种“硬实力”,战争的制约与规范机制只是一种“软约束”,但这种“软约束”在当今世界正逐步发展为一种制约资源的力量。因为只有通过争取联合国、各国政府以及人民的理解、支持,至少是不反对,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全世界的资源为己所用;只有通过争取本国的“民心”、“军心”,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调动本国的战争潜力以及鼓舞官兵的士气;也只有通过道义的力量影响敌方的民心士气,才有可能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里的“道”虽然不能直接转化为杀伤敌人的“硬实力”,但这种“软约束”通过影响民心士气能够转化为一种动员或制约本国、全世界甚至是敌国资源的力量。
第一,国际舆论。21世纪的头两场局部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让我们认识到,舆论战正逐步使战争伦理具有现实性。这主要是因为,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逐步实现了战争全过程的全球现场直播。战争双方从发动战争一直到战后行动的行为都被放在聚光灯下。客观上,欧美等发达国家掌握了较强的话语权,但却无法垄断话语权,也无法进行长久的欺骗。伊拉克战争进一步教育了全世界人民,使爱好和平的力量进一步增强,使崇尚战争的政客越来越没有舞台。
第二,国际法。如果说国际舆论声讨战争体现了人类良知的觉醒,那么国际法的完善则体现了人类的智慧。二战以后,人类已经成功地推动了被称为“约束武力使用的法律王冠上的明珠”(57)的《联合国宪章》的签署,而且签订了一系列条约,部分限制了对核、生、化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地雷等“非人道”武器的使用。尽管在实际的战争中,战争各方经常对国际法做出利己式的解读,但这种行为本身同样说明了国际法所具有的影响力。如果一意孤行,只是根据本国的国家利益任意发动战争,战争的发起方即使暂时赢得了胜利,也必将承受“软实力”遭受巨大损伤的严重后果。
第三,反战的各行为体,包括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各国政府和人民力量的壮大。总体上看,世界的反战趋向越来越明显,反战力量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强大。对比20世纪中叶的朝鲜战争和21世纪初的伊拉克战争可以发现,朝鲜战争尚能打着“联合国军”旗号,而今天即使是有着诸如“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将伊拉克人民从暴政下解放出来”等冠冕堂皇的理由,但对一个主权国家动武仍然遭到了来自全世界的反对——联合国不予授权,各国反战浪潮风起云涌,这里面甚至包括了美国的传统盟友如法国、德国等,即使是参战的美、英等国家,其国内反战的声音也十分强大。
2.战争观念的转变
通过20世纪的两场世界大战以及之后接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人类的战争观念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首先,从对待战争的态度上,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空前的生命财产损失驱使人类的良知迅速觉醒。人类从最初的崇拜战争,认为“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58)到认为战争是一种“施行国家政策的工具”,(59)再到现在试图“一般性禁止武力使用”,(60)足可见人类在不断经历战争的过程中逐渐厌倦战争并深刻反思战争,并在此基础上试图禁绝战争。
其次,从战争目的上看,不再轻易将战争作为解决国家间矛盾、谋取国家利益的战略选择。“现代化国家之间的武装冲突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它作为国家政策手段的效应,战争已不再能够达到它在现代化前社会中所能达到的目的。”(61)旧有的那种“以牙还牙”式地解决国家间矛盾的方式已经让位于新的安全战略选择,各国在“选择战争方式解决国家间矛盾的时候将会更加慎重,‘积极防御’、‘合作安全’、‘威慑’、‘预防性外交’将成为更多国家的战略选择”。(62)过去那种以武力开拓市场、掠夺殖民地的方式已经让位于通过外交、经济和科技手段达到目的。战争不再是谋求国家利益的最好的手段,靠经济和科技手段利用甚至控制别国资源,其阻力更小、效费比更高。
最后,从战争方式上看,已经从“先四肢后大脑”式的消耗战进化为“先大脑后四肢”式的体系破击战,使限制对平民的攻击具有了更多现实基础。以往的战争受制于当时的技术水平和战略思维方式等,主要是考虑通过削弱敌方的战争潜力从而从根本上打败对方,因此只要有可能,就倾向于进行“地毯式的轰炸”,从而造成大规模、无差别的破坏,进而迫使对方在肉体上臣服、心理上屈服。因此,对战争行为的限制如限制轰炸民用目标等就不可能实现。而如今,高技术武器的大量装备以及“基于效果作战”、“五环目标”理论主导战争过程,使得“斩首行动”、“重心打击”成为战争的新的思维方式,从而使得战争行为符合“区别性”和“相称性”原则具有了现实基础。(63)
3.战争博弈的推动
战争的棋局从来就是双方博弈或多方博弈的结果——一方的行动必须考虑到对方可能的“反行动”所带来的破坏力,这种利弊权衡很容易形成对战争和战争行为的制约。例如,此方很容易意识到,对对方的打击极易造成对方也采取相应的方式,或者以别的方式进行报复。又比如,在大部分国家都已经有能力制造生化武器的条件下,禁绝这一类武器的使用能够在国际社会迅速形成共识。这不仅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更是各方博弈的结果。这种博弈很像是一种“交易”,即共同遵守一定的战争“游戏规则”。这些“游戏规则”的成熟以及逐步积累就构成了战争伦理发展的基础。
当然,这种制定规则的过程并不像简单的商品交易那样清晰和直接,通常在双方不断的战争实践中以及双方各自的得失比较之后逐渐实现,并且时常出现反复。如果此方率先“修改”已有规则,不按牌理出牌,不按规则对抗,其结果通常有两种:第一,对方用实力迫使此方回到已有规则上来。第二,对方也不按规则对抗,实施更加无限制的报复,其结果是双方都受到更大的打击,直至战后形成新的战争伦理规范。正因为战争伦理的违犯者通常不能获得相对于对方的实际利益,反而容易因此失去国际舆论的支持,并进而失去一部分资源的支配权和使用权。所以从国家层面而言,世界各国长期以来不断建立新的战争伦理规范,但却少有国家公开予以否认。
4.军事技术的发展
早在19世纪末期,西方就出现过一股被称为“工业技术和平主义”的思潮,认为战争需求推动战争技术的发展,而战争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将使战争行为“人道化”并最终制约战争本身。(64)时间的车轮迈入了21世纪,这些预言部分实现了。
第一,核武器的发展成为有核国家制约战争的有利武器。一旦拥有了“死亡武器”,也就意味着具有对敌方的足够的反制能力,让较强一方在权衡战争利弊之后因为顾忌对手的报复而放弃选择战争。因此,自从核武器诞生以来,从来还没有哪一个拥核国家受到过别国的全面进攻。例如,印度和巴基斯坦在拥有核武器之前曾爆发过多次全面战争,而一旦双方都拥有了核武器以及相应的投送能力,双方之间的战争反而得到了控制。这跟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之间形成的核威慑之下的“冷和平”有许多相似之处。
第二,精确打击技术为减少对非军事目标的附带损害提供了技术基础。精确制导武器出现之前,战争一方即使有心避免对平民造成附带损伤,也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长眼睛的炸弹经常落在普通平民的头上。精确制导武器的出现让避免附带损伤成为了可能。从海湾战争起,精确制导武器的使用比重逐渐加大,一直到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使用比例已高达68%。虽然减少对平民的误伤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战争的性质,但即使是一方“粉饰”战争的努力,客观上也减少了战争对普通民众的伤害。
第三,非致命武器为实现真正的“零死亡战争”提供了可能。非致命武器通过暂时使敌人失去行动能力等方式削弱敌人的战斗力,通过减少战争中的伤亡给战争罩上了一层温情的面纱,它是在人类还不能彻底消灭战争的情况下,在军事上所能达到的文明和人道的伦理表现。
四 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认清这样两个基本事实:其一,战争伦理的作用是客观的。其二,战争伦理理论体系并不是静态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的、发展的,其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目前在世界上都存在广泛争议。特别在当前,战争伦理仍具有极强的可塑性。中国应当积极参与当代战争伦理的“再构建”,使战争伦理更好地服务于中国争取和平发展战略机遇期的需要,更好地服务于世界的安全与和平。
在对待战争伦理的问题上,不同的态度就必然导致不同的角色认定,其成本和收益也截然不同。当前,在这一问题上还存在两种认识上的偏差:追随者以及搅局者。追随者认为,我们应当紧随西方战争伦理构建的脚步,以西方的原则为原则。然而,“只讲道德价值而不考虑它们是否可以实现,最终会出于它对社会的进程缺乏实际的考虑变为不道德”。(65)追随者的路显然行不通。搅局者认为,战争伦理纯属骗人的把戏,是大国追逐国家利益的工具。然而,面对国际社会已然形成的“游戏规则”,走“先破后立”的路并不明智。
我们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法辩证地看待和对待战争伦理。现行战争伦理确有虚伪之处,但同时也包含着有利于世界和平的有益成分。在当前时代背景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应当扛起国际道义的大旗,积极充当现有伦理秩序的合作者和主要参与者,逐步争取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和主导者。游离于体系之外,中国则既享受不到体系的权利,更是对体系中的不合理之处无能为力。只有首先成为合作者,与各大国际行为体共同维护和巩固现有秩序,然后才能联合体系中的进步力量改变现有规则并逐步成为体系的主导者。这是成本最小而收益最大的方式。
(《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使笔者深受启发,特此致谢。文中可能的错漏由笔者负责。)
注释:
①[美]约翰·坦普尔·司温:《序》,载[美]路易斯·亨金等著,胡炜、徐敏译:《真理与强权——国际法与武力的使用》,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②Lucia Ames Mead,Educational Organization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Friendship,World Peace Foundation Pamphlet Series 3(1910-1912),http://www.heinonline.org.
③[德]康德著,沈叔平等译:《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82页。
④[比利时]布鲁诺·考彼尔特斯、[美]尼克·福臣、时殷弘主编:《战争的道德制约:冷战后局部战争的哲学思考》,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
⑤参见R.B.Potter,War and Moral Discourse,Richmond:John Knox Press,1969.
⑥许光建主编:《联合国宪章诠释》,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30页,附录三《国际联盟盟约》。
⑦刘海山、李玫:《裁军与国际法》,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页。
⑧[比利时]卡尔·赛莱曼斯:《正当理由》,载布鲁诺·考彼尔特斯、尼克·福臣、时殷弘主编:《战争的道德制约:冷战后局部战争的哲学思考》,第34页。
⑨参见[德]沃尔夫刚·格拉夫·魏智通主编,吴越、毛晓飞译:《国际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793-795页。
⑩路易斯·亨金等:《真理与强权——国际法与武力的使用》,第91页。
(11)许光建主编:《联合国宪章诠释》,第681页。
(12)许光建主编:《联合国宪章诠释》,第693-694页。
(13)(14)(40)路易斯·亨金等:《真理与强权——国际法与武力的使用》,第37页。
(15)详见布鲁诺·考彼尔特斯、尼克·福臣、时殷弘主编:《战争的道德制约:冷战后局部战争的哲学思考》,第131-140页。
(16)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第183页。
(17)布鲁诺·考彼尔特斯、尼克·福臣、时殷弘主编:《战争的道德制约:冷战后局部战争的哲学思考》,第139页。
(18)[比利时]盖尔·范戴姆、尼克·福臣:《相称性》,载布鲁诺·考彼尔特斯、尼克·福臣、时殷弘主编:《战争的道德制约:冷战后局部战争的哲学思考》,第142页。
(19)[美]安东尼·哈特:《区别性》,载布鲁诺·考彼尔特斯、尼克·福臣、时殷弘主编:《战争的道德制约:冷战后局部战争的哲学思考》,第155页。
(20)《国际条约集》(1648-1871),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427页。
(21)《中华人民共和国多边条约集》(第三集),北京: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124-125页。
(22)Michael Walzer,Just and Unjust Wars:A Moral Argument with Historical Illustrations,New York:Basic Books,1992.
(23)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第184页。
(24)Michael Walzer,Just and Unjust Wars:A Moral Argument with Historical Illustrations,pp.113-119.
(25)(28)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第185页。
(26)[美]约翰·罗尔斯著,张晓军等译:《万民法》,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页。
(27)[德]马克斯·韦伯著,冯克利译:《学术与政治》,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00页。
(29)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National Strategy for Victory in Iraq,November 2005,pp.14-18.
(30)西方的和平反战伦理思想正是直接发源于《圣经》中暗含的战争中的道德行为以及和平主义的观念。同样也是在《圣经》的基础上,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和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奠定了西方的正义战争理论。
(31)Joseph S.Nye,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New York:Pearson and Longman,2005,p.155.
(32)沃尔夫刚·格拉夫·魏智通主编:《国际法》,第809页。
(33)[英]劳特派特修订,王铁崖等译:《奥本海国际法》上卷《平时法》第1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36页及该页注(31)。
(34)Gary King and Langche Zeng,"Improving Forecasts of State Failure," World Politics,Vol.53,No.4,2001,pp.623-658.
(35)参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973(2011)号决议,2011年3月17日安全理事会第6498次会议通过。
(36)参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975(2011)号决议,2011年3月30日安全理事会第6508次会议通过。
(37)R.J.Vincent,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7.
(38)[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著,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64-165页。
(39)R.J.Vincent,"The Idea of Rights in International Ethics," in Terry Nardin and David R.Mapel,eds.,Tra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261.
(41)Jack Donnelly,"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in Tim Dunne and Nicholas J.Wheeler,eds.,Human Rights in Global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85.
(42)Nicholas J.Wheeler,Saving Strangers: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40.
(43)President Bush Delivers Graduation Speech at West Point,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West Point,New York,June 1,2002,http://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sws/releases/2002/06/20020601-3html.
(44)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September 2002,Washington,D.C.:The White House,September 20,2002,p.15.
(45)Karl P.Mueller,Striking First Preemptive and Preventive Attack in U.S.National Security Policy,Santa Monica Rand,2006,pp.10-16.
(46)Neta C.Crawford,"The Slippery Slope to Preventive War,"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17,No.1,2003,p.31.
(47)Joseph S.Nye,Nuclear Ethics,Portland:The Free Press,1986,p.99.
(48)Michael Mandelbaum,The Nuclear Futur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p.121.
(49)Michael Walzer,Just and Unjust Wars:A Moral Argument with Historical Illustrations,1992.
(50)参见苏群译:《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1986年6月-1987年6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3页。
(51)Periale Gasparini Alves,Prevention of Arms Race in Outer Space,A Guide to the Discussions in the Conference on Disarmament,United Nations Institute for Disarmament Research,1991,pp.106-107.
(52)[意]Marco Pedrazzi、赵海峰著,吴晓丹译:《国际空间法教程》,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53)《关于各国探测及使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活动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载航空航天部政策法规司编:《外空条约汇编》,北京:宇航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54)John J.Klein,Space Warfare:Strategy,Principles and Policy,London: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Croup,2006,p.17.
(55)Thomas C.Wingfield,"Legal Aspects of Offensive Information Operations in Space," USAF Academy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Vol.9,1998/1999,pp.121-146.
(56)[德]康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02页。
(57)路易斯·亨金等:《真理与强权——国际法与武力的使用》,第91页。
(58)转引自[英]罗素著,马元德等译:《西方哲学史》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70页。
(59)刘海山、李攻:《裁军与国际法》,第42页。
(60)参见沃尔夫刚·格拉夫·魏智通主编:《国际法》,第793-795页。
(61)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国外社会科学著作提要》第1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67页。
(62)王逸舟主编:《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2-83页。
(63)关于“区别性”与“相称性”的论述,具体见本文第一部分“理论体系”中的“战争行为伦理”。
(64)Michael Howard,The Causes of Wars,Vale:Guerrrsey Press,1983,p.65.
(65)[美]威廉·奥尔森、戴维·麦克莱伦、弗雷德·桑德曼编,王沿等译:《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7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