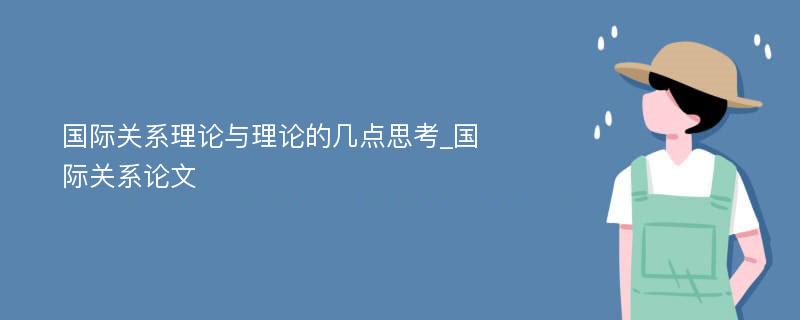
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一些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国际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理论研究及国际关系学在中国的发展状况,笔者曾在别处发表过一些看法,因感言犹未尽,故再试申论,以就教于学界同行。
一 关于理论
什么是理论?对这一问题,据说有两种回答。一种回答是,理论是与某种特定的行为或现象有关的规律的集中或组合。在这种观点看来,理论比规律要复杂,但只是在数量上更复杂而已。在理论和规律之间,没有质的差别(注:[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另一种回答是, 理论是解释规律的陈述,而不仅仅是规律的集中。理论同规律有质的差别。规律指出恒定的或很可能存在的联系,理论揭示这些联系为什么普遍存在。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对于天体上和地球上的现象做了统一的解释。它的力量在于能够把大量过去互不联系的、凭借经验的概括和规律,纳入一个解释的体系之中(注:[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7页。)。肯尼思·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就是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理论”这一概念的。
对“理论”一语,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的理解。最为普遍的,是把理论理解为具体行为的指导思想和指导原则,即理论是指导实践的,例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等。我们这里所讨论的理论及国际关系理论不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理论”一语的。在国际关系学界,人们多把理论理解为对规律的探求。例如宦乡就说:“把过去的行为总结起来,从中提出若干规律化的东西,把它条理化,规律化,这就是理论。我们就用这个理论指导未来的行为。国际关系理论也是如此。”(注:宦乡:“关于建立国际关系学的几个问题”,见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编:《国际关系理论初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另有学者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应该是从主权国家与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中抽象出来的本质和规律”(注:谢益显:“中国外交与国际关系理论”,宦乡:“关于建立国际关系学的几个问题”,见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编:《国际关系理论初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照此看来,理论是对规律的一种揭示和陈述。也许这是一种在中国被人们所广泛理解的“理论”的涵义,我们也不妨就在这种意义上来使用它。易言之,理论是对大量或众多的事实和现象具体有解释能力的陈述,它具有普遍性。
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第467页。)一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也同样不能没有理论建设。 这种理论建设能使人站得比较高,看到一些现象和事件背后的东西,而不至轻易受一些事件和现象的左右。同样,一个具有理论思维的研究者,往往是在研究中更具有理论意识和思维穿透力的。
对理论存在着种种误解。一种情况是轻视理论,似乎只要是谈理论,便是脱离实际,就是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理论是来源于实际而又高于实际的。理论来源于实际,是指理论形成过程中的思想材料都是来自于历史或现实。为什么说理论又高于实际?因为它是从实际生活中抽象来的、在理性认识基础上的一种思想活动的升华。国际关系理论也是如此,它来源于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现实,而又对众多、反复发生的现象具有解释能力。理论也激发人们去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去比较、验证、证明或证伪。从历史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历史;或者说从特殊到一般,再从一般到特殊,如此循环往复,人们对国际关系的理性认识就是这样发展的。
对理论的功能也存在着误解。第一种是“指导实践”说,即认为理论总是用来指导实践的,因此理论研究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指导实践。就国际关系理论而言,实践一般说来是外交实践。于是乎便推理出“我们的理论是为外交实践服务的”,这样一路下去,理论研究往往就变成了外交政策的诠释和发挥。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应当认真反思,它与中国人的实用理性太强有关系。就是说应用意识过于强烈,脑子里总是念念不忘一个“用”字。不是去穷究学理,而是生怕自己的研究不能为实际服务。但现实中所发生的情况往往是,一个研究者越是心里想着用,理论研究到头来却越是没有“用”,研究的“成果”就越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而总是被时间的浪涛迅速地淘汰。国外的理论亦如此。西方的理论在多数情况下并不是为了应用而建立起来的。很显然,若是与本国的外交政策亦步亦趋,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理论就不可能建立起来。“我们的任务是在重大的理论课题上建立起经得住考验的知识,而不管这种知识是否能直接明显地应用。”(注:[美]贝蒂·齐斯克:《政治学研究方法举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版, 第10页。)过于强调为实际工作服务,反而抑制了理论的繁荣和发展。这些年来国内国际关系学界在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也出现过不少经不起时间考验的研究结果和出版物,便是一个例证。问题的关键恐怕在于研究者有没有真正揭示事物的规律或内在的理路,而不在于是否能直接应用。找到了事物的规律,服务于实践事实上也就水到渠成了。然而,这是需要经过艰苦的研究工作之后才会出现的。
第二种误解是“拉近与现实的距离”说,即认为我们的理论研究与现实有距离,因此要拉近。这是进入了认识的误区。理论与实际的关系已如上述。从理论产生的规律来看,它对实际既要“入乎其内”,又要“出乎其外”,最后要“拉开”距离才能产生。理论思考是较之事实研究高一个层次的思考,它要求超越一般的对事件的描述和梳理,而达到建立理论所需要的抽象度。这样看来,理论与事实之间存在着一个“有效距离”定理。也就是说,理论研究与事实研究和政策研究是属于不同层次的工作。没有一个“有效距离”,没有升华,就事论事是产生不了理论的。不难设想,如果仅仅停留于对事实的描述,是不可能出摩根索、沃尔兹的。
能否这样说,国际关系研究既要“就事论事”,又不能就事论事。就事论事是说要把事实和现象的来龙去脉搞清楚,要“进得去”;不能就事论事是说还要“出得来”,不能停留在对事实和事件的描述上,而要窥其堂奥,探其究竟。一句话,要提高我们国际关系研究的水平,需要训练理论思维,具有理论意识,学会理论思考。
二 关于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中国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根据这方面的情况,可以把建国以来的50年分为前30年和后20年。在前30年这样一段很长的时间内,与理论有关的研究反映在:第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理论的阐释,如关于帝国主义及其与时代的关系等;第二,对本国外交政策的诠释或对领导人外交思想的整理、综合与阐发。30年代曾提出过“三个世界”说,被称为“三个世界”理论,实际上它是把国内斗争的经验推而广之,根据敌友我而对世界进行的划分。第三,意识形态色彩强烈。宁左勿右,越左越革命;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都反对;认为当前的时代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等等,一度还自以为是世界革命的中心。第四,受非学术性因素影响大。例如受中国对外关系变化的影响非常大,理论性的思考因之“随风飘荡”。
于是 80 年代有一位外国学者称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基本上是“solid journalism rather than scholarship”。大意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者所做的工作是比较深入的新闻分析, 而不是学术研究。 这话虽然说得绝对,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过去的实际情况,也是攻玉之石。不过,80年代情况已经在开始发生变化。
自改革开放以来的这20年间,理论研究真正得到了发展,包括理论概念、理论观点、理论意识等,这是20年来中国社会科学获得巨大发展的总体的一部分(注:俞正梁、陈玉刚的“中国国际关系和国际关系理论二十年”一文对此作了较全面的概括和分析,见《新时期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时事出版社,1999年。)。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正在走向成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理论研究取得了成果。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的外交实践也日益碰到各种理论问题而需要人们深入研究,例如主权、人权、安全、全球化,等等。
与此同时,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还存在不少弱点,有些还十分突出。要发展我们的理论,这些问题是要很好地加以解决的。我以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要从如下一些方面去努力,以改进和推动我们的理论建设和理论发展。
第一,要注重学理的探求。科学研究有其一般的规律,它要求发现问题、提出假设、验证假设、建立理论。有学者指出,科学研究方法的核心成分有3个相互关联的步骤, 首先是对现有理论的借鉴与批判;其次是在讨论现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与研究的问题密切相关的理论假设;第三是对这些假设进行验证,从理论角度分析验证结果,得出结论(注: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 —10页。)。现在的情况是我们还太缺少这样的研究,太缺少学术的自觉。如果理论研究者能够注意培养这样的学术自觉,并且身体力行地认真去做,形成习惯,理论的发展不是不可以预期的。
第二,增强我们的解释能力。“科学的目的在于解释。科学工作者观察了大量现象,并试图寻找出能够解释这些现象的一种理论。”要使我们的思维超越common sense(“常识”),就必须致力于增强解释能力。常识是经由观察获得的,但要对事件和现象的发生具有解释能力,就需要获得对于事物间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的认识。
我们目前的状况是长于描述,短于解释。例如大家都知道美国有一种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使命感”,问题在于这种使命感为什么会那么强烈?对于美国的所作所为,用“粗暴干涉内政”、“新霸权主义”乃至“世界警察”等来批判是很容易的,但这并没有解决问题。批判当然是有必要的,尽管要掌握分寸,但更重要的是“批判以后怎样?”我怀疑我们是不是连批判的武器都还没有掌握,更别说“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对话不能是“聋子的对话”,要有沟通才行,否则总是谈不拢。美国的观念中,唯我独“革”的色彩甚浓。这里的“革”作“正确”解。别人要么是未开化,要么是受了蒙蔽。美国人常常居高临下,仿佛绝对真理在握,我的制度和文化是最好的,你们都应该接受,我是为你好,你越早接受、越早实行对你越有利。这种认为世界上只有唯一一种最好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和价值观的观念,从其思想根源来看,是一种来源于启蒙运动的一元论。要真正理解它,就得深究:它的哲学基础是什么?它与宗教(基督教)有什么联系?为什么它比较缺少宽容精神?中国文化有没有可能提供一些有益的补正?等等。又如,克林顿政府外交政策的理论依据之一是“民主和平”论,要实现“和平”,就要让全世界都实行整齐划一的、他们所理解的民主制度。这也是一种一元论。就是说,世界各国的制度应是一元的,而不是多元的。同时,这也是把国内政治制度与国际关系联系起来,挂起钩来。那么,在各国选择政治制度方面,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有没有道义的优越性呢?是应一元呢还是多元呢?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艾赛亚·伯林曾经深刻地揭示了他所视为启蒙运动最根本的谬种:启蒙运动的信念即真理只有一个,各种好的东西不会最终发生冲突。伯林认为,有可能找到最终答案的想法“是一种幻想,而且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幻想。”如果有人认为的确有可能找到这种答案,那么就会认为付出再高的代价也是值得的:若能使人类永久地公正、幸福、和谐并拥有创造力,任何代价都不昂贵。于是,“你宣称某项政策可以给你更多的幸福,更多的自由、更大的生存空间,但我知道你是错的。我知道你需要什么,全人类需要什么。”伯林说:“我认为,对人类最大的毁灭莫过于那种对完美生活的狂热追求,并将这种追求与政治和军事力量融为一体。”(注:“哲学与人生——以赛亚·伯林访谈录”,见《万象译事》(卷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这些话是80年代时讲的,伯林本人也已经飘然仙逝,却至今读来仍如空谷足音,仿佛他预见到了90年代乃至21世纪的发展。1999年在巴尔干所发生的战争,不正是在政治和军事力量支持下的“狂热追求”吗?对于今天有人宣称的“民主”万能论、“市场”万能论,认为他们是最终找到了人类终极真理的人,难道不是深刻的思想批判吗?可以说,伯林思想的核心本质上是多元主义。他看到了人类困境的复杂性,强调了不同文化同等的存在价值。……如此等等的问题,难道不需要我们去作出理论的分析?
第三,进行具有原创性的研究。这是学科和理论得到发展的关键。现在的问题是原创性的研究甚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未能提出原创性的问题。比较普遍的现象是我们所讨论的很多问题产生于国外,然后我们加以引进。对于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提出解答固然有必要,但知识创新更重要的是要提出原创性的问题。我们为什么没能提出自己的问题?我们是否提不出具有原创性的问题?这是需要深长思之的。牛顿从人们习以为常的现象中提出了“物体为何都往下掉”的问题,这个问题别人没有提出过,他提出了,这导致他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合作安全”是一个新型的概念,“亚太地区能否建立起合作性安全”就是一个具有原创性的问题,因而已成为安全理论的一个新生长点。“问一个‘为什么’有效地激发了对其可能的缘由或目的的想象。‘怎么样’也是有用的问题,可引起对过程机理的思考。(注:[英]W.I.B.贝弗里奇:《科学研究的艺术》,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6页。)”提出原创性的问题,咬住不放,锲而不舍,就可能产生知识的创新。创新不是为新而新,而是由于它是知识增长和积累的途径,是在于使我们增强对事物的一般性认识。
第四,苦练内功,增长学问。“苦练内功”一语大约是在国营企业改革过程中得到广泛使用的,实际上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也完全适用。理论研究的发展最终是要通过研究者个体的创造性研究来实现的。具有创新性的研究需要有多种准备,包括知识的准备和学术素养的准备。“也许,一个训练有素的思想家的主要特点在于,他不在佐证不足的情况下轻易做出结论;而未受训练的思想家则很可能这样做。(注:[英]W.I.B.贝弗里奇:《科学研究的艺术》,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7页。)”学者们总是带着深思过的思想、学术性的研究以及他们提出的问题进入那些能激起好奇心的研究领域。这是一种必要的支援,若没有这种支援,就不可能结出硕果。反之,在有了知识、创新意识等多种准备之后,研究者遵循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和途径,持之以恒,深入思考,就有望登堂入室,作出创造性的研究。
有人提出理论研究应为国家利益服务,这个提法需要推敲。其实服务不是任何一种理论的目的,而只能是科学研究的结果。理论有别于政策,它首先不是为政策服务的。政策经常变化,具有易变性。而理论是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是对事物间相互关系的洞察,它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西方的理论也未必就是为西方国家的利益服务的。服务的虽有,但在更多的情况下是学者的学术探索,例如沃尔兹通常被称为新现实主义的理论,认为在重要关头,国家最终关心的并不是权力,而是安全。这是新现实主义对现实主义的重要修正。又如以寇汉(Robert Keohane)为代表的强调相互依存和国际制度之作用的“新制度主义”理论等,也是如此。实际上,理论研究应避免过于强调为某某利益服务的观念,否则就成了意识形态,而不是理论。事物本身的辩证法,常常是越是念念不忘服务,就越是服务不好。随风倒的“理论”,不是理论。
90年代曾出现过关于是不是应该提建立有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理论或国际关系学的争论,有赞成的意见和反对的意见(注:持赞成立场的如梁守德:“国际政治学在中国——再谈国际政治学理论的‘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研究》,1997年第1期。 持反对立场的如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写在前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我个人是不大赞成提“中国特色”的,因为这多多少少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套用。但是同时必须指出,中国的学者一定要有一种志向,一种创新意识,要致力于建设中国人自己的理论观点和理论主张,进而至于理论系统,因此我比较赞成提形成“中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
有人认为,理论能不能够建立,进而能不能够在国际上有一定地位,是与一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或曰国际地位分不开的。换言之,一国要想建立自己的理论并产生一定影响,首先这个国家要成为国际上有影响的大国。这话有一定道理,注意到了客观的方面。美国的理论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影响,是与它的超级大国地位分不开的。但是,恐怕还有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即研究者的主观能动作用。拉美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并不高,但产生于拉美的依附论和依附发展论不是同样产生了巨大影响而自成一家?新加坡小得不能再小了,但以一些政治家和学者型外交家为代表的新加坡人发出了他们的声音,概括并肯定“亚洲价值观”,被称为“新加坡学派”。不管有多少争论和不同意见,毕竟它独树一枝,自成一派。
学派的形成是有条件的,关键是要有自己的东西,首先是有别于其他理论流派的基本概念,如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 internationalsociey)概念,“新加坡学派”提出的“亚洲价值观”等等。其次是围绕核心观念进行的一套言之成理并能继续发展的论说。
通常被称为“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绵延不绝。“现实主义”认同的是“力”,实力、强力,认定国际关系都是力的较量。传统现实主义有3个核心的预设:1)国家中心预设,认定国家是国际行为主体,而不及其余。2)理性预设,即国家是统一的理性的行为体, 它会仔细盘算各种不同选择的成本,力图使其预期效用最大化。国际政治都可以这样去分析,尽管国家的这种行为是在不确定情况和不完全信息条件下进行的。3)权力或实力预设, 即国家都是追求权力或实力的(包括影响他人的能力以及可用于发挥影响力的资源),它们根据权力来计算其利益,不管这种权力是作为目标还是实现目标的必要手段(注:Robert O.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Westview Press,1989,P.40.)。现实主义是个美名,只要是现实的就没有什么不好。 但是,标签常常容易导致误解,现实主义并非没有缺陷。首先,它是不是能很好地解释国际关系的实际?其次,如果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处理彼此之间的各种关系一律凭借“力”、只能凭借“力”来进行,那么,国际关系就不会有进步。而实际情况是世界上存在着种种不平等、不公正、非正义,国际秩序的不合理、穷国与富国的两极分化还在继续。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切都由“力”来决定的国际秩序所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而这恰恰是有违公平和公正的。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那么便不难得出共识,即仅有现实主义是不够的。世界上爱好和平与公正的人们还应有和谐与正义的价值选择,使和谐并存、共同繁荣和共同进步成为世界的目标。因此,我们要作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有理想、有原则但又不失现实的态度。这样看来,中国的国际政治理论应该有道义的方面。外交政策也应该是有原则的外交政策,提倡并实践这些原则。这些问题,恐怕都需要好好地研究。
这些问题也与一国的哲学文化思想有关。西方文化重强力,中国文化重和谐。西方重黑白之分,中国重太极中庸。前者求异,喜欢寻找利益的对立;中国求同,偏爱寻求立场的汇合。崇尚强力、迷信强力的国际政治观在历史上虽屡次遭到失败,甚至是惨重的失败(例如在越南),却至今仍有市场(例如在科索沃)。如何从不同文化入手来解析不同国家的国际政治观念?这又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
建设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是一个长远的目标,并不是短期内所能做到的。但是应该看到,这种建设已经具备了若干有利的主客观条件,我们至少可以列举出如下一些:
1 )中国博大的文化传统和丰厚的文化遗产为中国的外交思想和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有力的文化依托和取之不尽的思想材料。
2)当代中国的外交实践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养料,而且这种实践还在源源不断地提出新的问题。这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要动力。
3)经过20年的努力, 国际关系学界对国外多年间发展起来的国际关系理论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并已做了一定的消化吸收工作。
4)已经形成了一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队伍。 资深的国际关系学者仍在继续产生研究成果,与此同时,新一代学者正在成长。
5)中国的国际地位已经并在继续提高, 在世界上的影响在继续增强。国力的增强为中国的理论思想产生国际影响奠定了基础。
因此,建设中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前景是可以谨慎乐观的。建立中国的理论,并不是要刻意追求与西方理论的对立,为了求不同而不同,而是说中国人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不要拾人牙慧;要有自己的学说,不要总是跟着别人走。一言以蔽之,要有我们中国人的理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