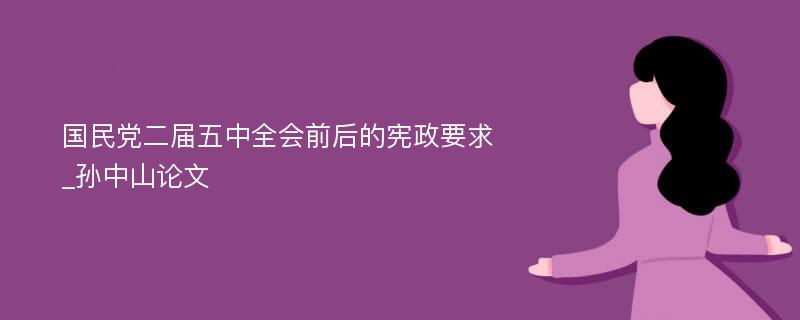
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前后的制宪诉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会论文,国民党论文,五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融会中西,研究创新制定一部适合中华民国需要的宪法[1] (p5),是孙中山一生的刻意追求,为此他在理论上作了精辟的论述,并颇有远见地提出一切政党和团体都要在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思想[2] (p235),他为护法作了不懈的努力和奋斗,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念念不忘宪法的实现[3] (p638),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孙中山有关在中国实现民主和法治的思想是,通过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阶段实现。其中军政时期是军法之治,训政时期是约法之治,宪政时期是宪法之治。[4] (p297~298)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宣称继承孙中山遗愿[5] (p80~81),1928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宣言把法制建设作为全力以赴的要事,“内政的建设,一以实行建国大纲所指示之工作为目的。而如何能达到此目的,则第一项决定确立法治主义之原则。……须知一切的政治主张若不成为具体的法律,政治之组织若不造成宏远精密之制度,不特一切理论尽成空文,而社会之秩序、人民生命财产及一切生活关系,均无保障。建国的中国国民党之重要任务,固在唤起民众,而尤在建设国民生活之秩序与保障。此实吾党今后应以全力赴之者也”,[5] (p511)北伐完成后,1928年6月12日,南京国民政府所发表的《国民政府对内宣言》表示了要实行法制的精神:“厉行法治,欲谋政治之建设,必先发扬法治之精神,……今全国统一,开始训政,一切政治主张务使成为有条理之法律”。[6] 在训政开始之时,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政府与人民的权利义务关系,尤其显得重要,国民党上述方面的所作所为,就给全国一个印象,即国民党要在法制方面有所作为,因而,各界利用国民党于1928年8月8日~15日召开二届五中全会的机会,纷纷要求制定约法,在国民党方面,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朱霁青、南京特别市指导委员会,国民政府方面有国民政府法制局在大会召开之前正式提出制定约法的议案于前,国民党中常委将法制局的建议作为提案提交大会,社会团体方面有上海商业请愿团于大会期间请愿,要求制定约法,有着重要社会影响的《大公报》的舆论推波助澜于后,又有上海市党部指导委员会于会后积极要求起草约法,形成了蔚为壮观的要求制定约法的声势。这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首次大规模要求制定约法的一次尝试,史学界缺乏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本文拟对这次要求制定约法的主张作一评析,以期推动民国时期法制思潮课题的研究。
一
国民党内部在二届五中全会召开之前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南京特别市指导委员会提出制定中华民国约法的建议案。
(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朱霁青建议颁布约法。他认为,一国不能无根本大法。其一,以党治国需要约法。朱霁青认为国民党北伐完成后,以党建国目的已经实现,进入到以党治国时期。在这一时期,应内审国情,外察大势,遵守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原则,根据建国大纲程序,制定训政时期之法,这样可以收双重效果:规定政府与国民行动,树立革命政权基础。其二,训政时期需要约法,且刻不容缓。这是因为,根据建国大纲的规定,县为自治单位,必须各县自治完成之后,方为一省之宪政开始,全国过半数省份宪政开始后,方为一国宪政开始,在宪政开始前制订宪法草案,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并颁布宪法,从现在到建国大功告成,至少须有数年或十年以上,才能实现宪政,在这一长时期内,若只遵照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之政纲而施行,远远不够,因为政纲性质简略,只规定民众的最低限度的要求,而党及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相互关系,均付缺如,故在训政开始时期,约法之制定,实为刻不容缓之事。其三,要使全国人民了解国民党的建国主张,需要制定约法。朱霁青认为,国民党以党建国的成绩已为全国人民所了解,而国民党以党治国之主张也有为全国人民了解与认识的必要。他说,国民党以党建国之成绩,固已昭然于国人耳目,然而以党治国主张,尚未为一般民众所了解所认识,例如人民之权利义务,各级政府之组织,中央与地方之关系,政权之发动,治权之行使,五权之实施,四种直接民权之训练,民众团体之保障,农工商事业之发展,华侨回国投资之待遇以及国家军制之确立,教育宗旨之规定等,皆为训政开始之时亟应明白规定,昭告天下,俾全国民众有充分之了解与明确之认识,然后乃可以立一国之大本,树天下之大信,确立政权,共图建设。其四,从确立国际信用、安定国内人心方面看,有迫切制定约法的必要。他认为,世界各国都有宪法一类根本大法的颁布,中国也不能例外,国民党虽高悬实行五权宪法以为鹄的,然一则为期尚远,二则尚未成文,决不能应付目前革命之时机与环境,况且国民党党章规定全国代表大会每年举行一次,自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已连续三年没有开会。国际方面是以中国政局能否稳定而决定对中国方针的,因而,为确立国际信用,安定全国人心起见,制定约法,实为今日时势迫切之要求。[7] (p214~215)朱霁青提议组织中华民国约法起草委员会,从速制定约法草案,以便提交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颁布。[7] (215~216)朱霁青上述要求迅速制定约法的主张和建议,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为极少数(时有中委25人[5] (p216)),他所陈述的制定约法的现实性和紧迫性,指出了国民党北伐完成后治理国家所应解决的主要问题。
(二)南京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在二届五中全会开幕前向大会提交制定约法的建议,主张:第一,中央党部掌握制定法律的最高权。按照孙中山以党治国遗愿的原则,国民政府重要法规,“皆由中央党部决定,实合以党治国之旨,亦可为党治方式之规范”[8]。第二,以约法确定国民之权利义务及政府之统治权。南京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认为,现在训政开始,应立即颁布约法,以规定国民之权利义务及政府之统治权。其中要注意以下问题:其一,孙中山有关约法的论述是制定约法的理论基础。总理云“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在此时期内,施行约法(非现行者),建设地方自治,促进民权发达,以一县为自治单位,每县于敌兵驱除战事停止之日,立颁约法,以规定人民之权利义务与革命政府之统治权”,因而约法是训政时期根本大法,正如宪政开始时期之宪法草案及宪政时期之宪法一样。其二,政府统治和以党治国必须有法律作依据。若无约法,则国民权利义务及国民政府之统治权,均漫无限制,必至冲突零乱,纠纷莫解,训政实难着手,且国民政府本身无法律根据,以党治国,亦无法律根据,又有何权进行训政。其三,为将来制定宪法奠定基础。将来制定宪法要有根据,而宪法草案之根据在约法,三种根本大法,一系权承,不容遗漏或紊乱,请立颁约法,以为训政时期之根本大法。[9] 南京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得地利之便,首先提出了制定约法的要求。该委员会站在维护国民党以党治国的立场要求制定约法,在国民政府完成北伐,全国统一,人民望治之时,要医治长期以来的战乱创伤,必须有根本大法来经纬万端,这一制定根本约法的主张,反映了当时的客观要求。
在国民党党务机关中,除南京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正式建议制定约法之外,还有南京特别市第十区党部筹备处提出《制定约法草案交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施行》的建议,江苏赣榆县党务指导委员会明确提出《确定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自由权》的建议。[5] (p737)上述党部的建议都对二届五中全会作出制定约法的决议起了推动作用。
(三)8月4日,南京国民政府法制局向中国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议案:《拟请组织中华民国暂行约法起草委员会并限期完成草案以备提付第三届代表大会批准施行案》[7] (p211),建议组织中华民国暂行约法起草委员会,限期完成草案,以备提交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批准施行。[p10]其建议的主要内容为:1.指出制定约法的理论依据。“总理于其所定革命方略中,明认训政时期为施行约法时期,各地于战事停止之日,原应概改军法之治为约法之治,而所谓约法者,依总理之解释,即‘规定人民之权利义务与革命政府之统治权’之大法,盖即现代诸国之所谓根本法,特此种根本法,仅适用于训政时期,其性质为暂行者耳,兹全国军事俱告终结,为遵行总理遗教起见,此种根本法,自应从速颁行。”2.关于颁布约法的必要性。第一,约法是巩固秩序的主要工具。“革命之终极目的,不在破坏,而在建设,然一切建设事业之发展,必在新造之政治秩序确定巩固以后,而所谓约法或根本法者,便即巩固新造的政治秩序之主要工具。”约法的性质决定了颁布约法的必要性,因为“就一般国家通例而言,此项大法,其效力既高于一切其他法律”,[7] (p211)其修改之机关或程序,亦异于普通法律,新造政治秩序,一经规定于此法,即不致频受其他新颁法影响,因为此种大法修改,须经特别机关或特别程序,修改或要求修改之事,亦必随而减少,所以一切新建国家,在经过政治革命后,无不有此种根本法之颁行。第二,训政本身需要约法。训政时期党部及政府主要任务,是使一般民众,对于其本身权利义务以及政府之组成与职权,有相当之了解,要使这些问题,一一以单行法规定,一般民众必感了解不易,因为一般民众,决不能搜集众多的单行法,了解此类政治问题。反之,如将人民权利义务,与革命政府统治权,于一种根本大法之中,为概括的规定,一般民众,对新造政治秩序,便不难一目了然。约法的颁布,足以巩固新造之政治秩序,对一般民众也有教育的作用。3.有助于国民明了个人权利义务。国民政府成立已逾三载,社会对于政府机关之组织,以及立法行政诸权行使之程序,尚多茫然不省,探究其原因,由于法令变更无常,关于国家根本组织之事项,未尝纳诸一种大法之中,以昭国人,民众对于新的政治组织无从了解。4.颁行约法,已成为党内外的普遍要求。南京特别市党部已提有颁行约法之建议,此前胡汉民孙科所拟国民政府改组案,对政府各机关及其相互关系,都有详细规定,该案性质,仅是一种暂行约法,至于社会为明了个人权利义务范围,以期个人生命财产与自由获得较大保证,更期望约法早日颁行。5.现有国民政府组织法已不能满足需要,必须颁布新的约法取而代之。现在的国民政府组织法,对于人民权利义务,中央与地方关系,党与政府关系概未规定,就所规定的政府机构而言,亦仅列有各机关名称,而与各机关组织原则及其职权性质,亦毫无规定,不能向社会说明政府统治权方式。世界上只有英国实行的是不成文法,而在中国,政局初定,旧的政治习惯,都须一一铲除,新的政治习惯,大都尚未形成,如果仿行英国的不成文法主义,徒增紊乱,毫无益处。6.关于制定约法的具体操作办法。第一,由二届五中全会指定中央委员数人、专家数人组成“中华民国暂行约法起草委员会”,责其于一定期限内,提出中华民国暂行约法案;第二,中华民国暂行约法决议案应规定下列内容:(甲)人民之权利义务;(乙)中央政府之组织;(丙)中央与地方之关系(地方职权及地方制度之大要);(丁)党与政府之关系;第三,中华民国暂行约法案应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国民党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批准,国民政府公布。[7] (p213)作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编制法律的机关,法制局详细陈述了制定约法的理由根据和操作办法。国民党中央常会接受国民政府法制局上述建议,将该建议定名为《组织中华民国暂行约法起草委员会案》作为向二届五中全会的提案。[7] (p211)法制局长王世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达了与法制局建议相同的看法:“值兹训政开始,颁布约法,实属急要,国民政府政制与前不同,旧临时约法完全不适用,如人民之权利义务,中央政府之组织,中央与地方之关系等必须由中央颁布约法,基础方能稳固,否则政治成不稳状态,时有被动之可能,……本局已向五中全会提出建议,希望五中全会能指定委员及专家,组织中华民国暂行约法起草委员会,以解决此重要问题。”[11] 胡适从保障言论自由的角度主张有必要制定约法,“希望定一切实易行政策,逐步实行”,使人民得保障、言论有自由。[12]
二届五中全会成立提案组,审查向大会提交的提案,其中第二组负责党部与政府之关系及其权责,由于右任等12人为审查委员,于右任负责召集。[5] (p549)该组对朱霁青、南京市党部、法制局制定约法的建议,合并审查,作出审查结论:“训政时代,应遵总理遗教,颁布约法,此次全会,应即组织中华民国约法起草委员会,限期完成,由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赶于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时,呈请通过公布。”[13] 这就表明,制定约法之主张得到审查组支持。这是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对制定约法的主张的最初反映。
二
在要求制定约法的社会团体中,上海商业请愿团要求制定约法的主张具有一定的代表性。1928年8月6日,虞洽卿在上海发起上海总商会组织上海商业请愿团,8月8日开第一次会议,上海总商会代表冯少山、林康侯、陆凤竹及其他各业代表50余人到会,由冯少山主持,通过了向二届五中全会的请愿书,定于8月10日晋京递交请愿书。[14] 代表团8月10日清晨抵达南京,参加的商会除总商会外另有45个专业商会,虞洽卿、冯少山等90人参加请愿团。[15] 8月11日上午,商业请愿团代表虞洽卿、冯少山、林康侯等18人来到二届五中全会开会地点中央大礼堂,向大会递交请愿书,大会推中央执行委员李烈钧接见代表,表示接受商业请愿团的要求。[16] [17] 上海商业请愿团在其请愿书中以孙中山制定约法的遗教为依据,要求颁布约法:“现在军政已告结束,训政已在开始,根据总理以训政时期为约法时期之遗教,应请于三月内,颁布约法,以确定国家与人民权利义务。伏读钧会四次会议宣言,以法治为骨干,人民无不额手称庆,然根本法不立,普通法均属效力不强,而无以举法治之实,由报诵悉法制局提出组织约法起草委员会,可谓百年大计深得人心之议案,恳请钧会即予议决,组织该会,起草约法,并于三个月内颁布,则总理之根本建国遗教得以实行。”[18] 上海系全国工商业发达地区,上海商业请愿团这一临时组织,有45个专业商会派人参加,仅就上海而言,是有一定代表性的,因而他们从约法作为根本法的角度陈述颁布约法的重要性,其颁布约法的请求,直接代表了上海商业团体的愿望,间接反映了全国商业团体的利益。
报界请求制定约法的舆论呼吁同上述要求相比较,其舆论导向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大公报》在呼吁制定约法中,起了舆论先导的作用,其《新约法与五次全会》社评,表达了要求制定约法的主张:起草制定约法,“实训政时期切要之举”,“今全国统一。时移势易,非有齐一之规模,不足以坚民众之信仰,而国民之权利义务,中央地方之权责范围,党政国政之关系连络,均须根据国民党之理论,制为党义的结晶品之新约法。既符以党治之旨,又正为事实之所急需”。社评还颇有预见性地主张,约法制定之后,要严格实施,“此项约法,一经制定,即应严格实施,从上澈下,悉受部勒,不得再有旧约法时代违法玩法之弊。在上者以身作则,然后国民乃凛然于根本大法之不可侮”。《大公报》对是否制定出约法以及能否实行表示忧虑:“新约法能否草成,草成后能否由第三届全体代表会通过,以及通过后能否见诸实施,实施后有无窒碍,又当视五次全会有无真正成绩矣”[19]。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十分关心约法问题,当该报驻京记者访问审查约法起草案的邵力子、于右任,得知他们将约法审查通过之后,撰写社评《约法审查案成立》一文赞同制定约法。[20] 当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于1928年8月11日第5次会议通过“依照总理主张,训政时期,颁布约法”决议案之后,该报第二天发表《颁布约法案成立》社评,认为“约法之颁布实为必要”,称“五中全会通过此案,实在值得全民众称颂的一件事”[21]。
综上可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南京特别市指导委员会、国民政府法制局要求制定约法于前,上海商业请愿团的请愿于会期,《大公报》的舆论推动,国民党中央常会注意到这些来自不同方面的制定约法的主张,将国民政府法制局上述建议定名为《组织中华民国暂行约法起草委员会案》作为向二届五中全会的提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于1928年8月11日第5次会议通过“训政时期,应遵照总理遗教,颁布约法”决议案,在8月15日通过《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宣言》,决定“迅速起草约法,预植五权宪法之基础”。[5] (p534)值当北伐完成,全国进入建设时期,迫切需要一部根本约法,规定人民的权利义务,规定政府的权限,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制定相关法律,建立完善的法制体系,这是以孙中山事业继承者自居的国民党遵照孙中山遗嘱的需要,也是标榜“以党治国”的国民党之必需,正是出于这些考虑,国民党决定制定和颁布约法。
三
按照常例,作出决议之后,应当按照决议去实施。出于这样的考虑,二届五中全会之后,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于1928年10月3日,就如何贯彻组织起草约法的决议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建议案:1.依据孙中山的遗教实行约法之治。“由军法之治而至约法之治,由约法之治而至宪法之治,此为本党施政之程序,亦总理遗教所昭垂,今当训政开始,施行约法之治,自不待言”。2.提出制定约法的具体操作办法,由全国党员选举代表组织约法会议决定。“约法如何产生之问题,在第五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案内,未有明文,职会之意,拟由全国党员选举代表,组织约法会议。盖训政时期人民既不能行使政权,不能自治约法,则不能不由代表人民利益之本党代为制定,本党为一民主之集团,如此重大之根本问题,自当由全体党员之意志决定之,如钧会以训政实施,急不容缓,不能复待明年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决定,似亦宜召集以全国代表约法会议制定之。”3.提出先在国民党内实行了民主,才能在全国普及民主。“设此根本之约法,不由全国党员共同决定,则是有集权而无民主,已违本党组织之原则,在党内尚不能实行民主之制,欲使民主之制,普及全国,实非梦想。”[22] 上海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所论及的先在国民党实行民主,以之做基础,然后在全国推而广之,这一建议,直指国民党的集权,指出了问题所在,是当时所迫切需要的,并未为国民党所看重。
国民党作出制定约法的决定之后,没有去认真执行,颁布执行也就遥遥无期了。二届五中全会之后,国民党要人纷纷离开南京,李济深赴杭州莫干山游玩,缪斌、朱霁青去上海,蔡元培坚辞一切职务,蒋介石患病在上海治疗,李宗仁也称病在外,制定约法的工作无形中处于停顿状态,远游的胡汉民正在从新加坡回香港的路途中。待胡回国之后,按照他和孙科提议的《训政大纲》组织国民政府,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此时虽有上海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于1928年10月3日向中央陈述制定约法的重要性,督促国民党起草制定约法[22](已如上述),但国民党要人正忙于在1928年双十节宣告成立政府,制定约法一事无形中搁浅。这些只是表面现象,至于深层原因,则由胡汉民1928年10月15日在中央党部纪念周的报告中揭开了国民党不再制定约法的谜底:“至于法,事实上所需要的,乃所谓约法或宪法中最紧要的一部分,政府组织法,我们正不必舍掉这最紧要的一部分大法,而去很迂阔的马上要求一部整个的什么约法。何况如民二民三之间的约法,总理当时根本不赞成”。[23] 在胡汉民看来,已经颁布的《国民政府组织法》就是根本大法,同时认为孙中山根本反对约法,这样,国民党五中全会言之谆谆的郑重承诺就放在了一边。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要求制定约法的呼声中,舆论界虽然表示了支持的态度,就《大公报》和《民国日报》相比较,前者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为制定约法鼓与呼(已如前论),而国民党人主办的《民国日报》则大相径庭,如当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通过制定约法的决议后,《民国日报》的社评曾发出这样的提醒“所当注意的是,约法通过之后,当要运用它底力量以助人民彻底消灭一切反革命势力”[21],国民党党报的地位和立言决定其在拥护制定约法的问题上不可能走得太远。
综观上述制定约法要求,有以下特点:
1.在建议制定约法的主张中,普遍认为应以孙中山有关约法的论述作为制定约法的理论依据,这是所有主张制定约法的一个显著特点。在提议者方面,当然是希望其建议案为国民党中央接受的策略而已,在当时,只有以孙中山的理论作为制定约法的主张,才能为信奉三民主义的国民党所接受。
2.从要求制定约法的各主张中,可以看出国民党党政机关及其领导人在倡议制定约法时,居于主体地位,其建议较为全面也具有操作性,尤其是国民党上海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在二届五中全会结束之后,积极推动制定约法。这表明,作为当时的执政党,国民党对训政开始时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较为清醒的认识。
3.继承孙中山遗志,完成孙中山未竟事业,国民党在历次大会中言之谆谆,1925年5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届第三次中央全会专门作出《接受总理遗嘱宣言》,表示“吾人今日唯一之责任,则在完全接受我总理之遗嘱,自今而后,同德同心,尽吾人之全力,牺牲一切自由及权利,努力为民族平等,国家独立而奋斗,以继总理未竟之志”,并希望“全国国民及世界民众实昭鉴之”[5] (p80~81)。此后,国民党历次代表会议都有类似表白。制定约法,规定人民的权利义务和政府的权限,这是孙中山的重要遗愿。国民党是真继承还是假继承孙中山的遗志,能否把约法制定出来就是一个考验,恰巧在这一问题上,纵有二届五中全会的决议,可谓郑重其事,还是开了一张空头支票,自食其言。到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把胡汉民反对制定约法的主张写进大会决议:“确定总理所著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及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之根本法。”[5] (p654)至此,围绕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要求制定约法的主张统统告吹。国民党的决议未果而终,国民党在制定约法这个至关国家大政方针的问题上发生了逆转,《大公报》所担心的事变成了现实。
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又有大会的正式宣言,表示制定并颁布约法,看来人们所期望的约法是为期不远了,然而会后不久,就不予履行,抛在一边,另行作出相反的决议,这印证了二届五中全会召开期间社会舆论对国民党会议的评价:“决议是一回事,把纸上写的决议付诸实行又是一回事。……开会的时候,一字一句都要争,一步也不肯让,及至会开完了,大家各自散去,对于通过的议案或法规,即时抛到九霄云外,听其自然。”[24] 无怪乎人们切中时弊的讥讽国民党会议的通病是:“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动”。[25] 如此,制定约法一事不再提起,就不难理解了。
标签:孙中山论文; 国民政府论文; 孙中山遗嘱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南京国民政府论文; 宪法修改论文; 大公报论文; 历史论文; 民国日报论文; 国民党论文; 九·一八事变论文; 辛亥革命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