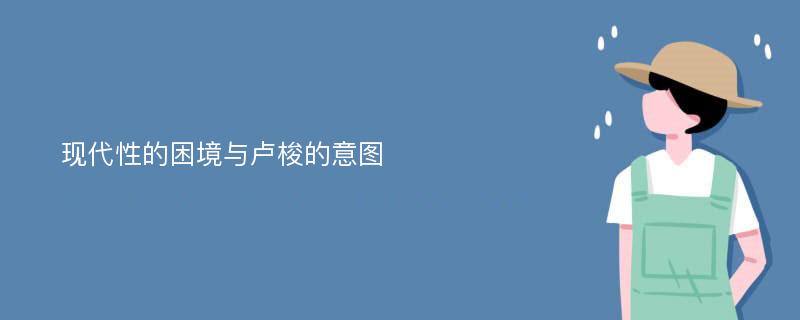
摘要:卢梭认为,霍布斯的自然权利论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内在困境,这一困境导致了现代性的困境,即自由政体的困境。为了化解这一困境,卢梭本可以从德性出发,在古典政治哲学的层次上批判现代自然权利论,但他对自然和自由的教条主义理解促使他重新把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当作思考的起点,选择在现代自然科学的地基上创建自己的学说,从古典政治哲学的阵营回到现代政治哲学的阵营。卢梭从霍布斯的前提出发,彻底改造了“自然状态”概念的实质意涵,这不仅没有化解现代性的内在困境,反而使现代性离理性精神越来越远,从而更加激进地推进了现代性。
关键词:政治哲学;现代性;卢梭;自由政体;自然状态
一、引言
卢梭是政治哲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他的学说自诞生以来就争议不断,这些争议不仅让卢梭的反对者抓不住要害,也常常困扰着卢梭的支持者。
研究者们通常将争议归咎于卢梭在观点上的自相矛盾以及修辞上的含混不清。基于卢梭作品的这两大特征,欧美学界的研究者曾一度放弃全面理解卢梭。他们要么满足于阐发卢梭思想中的某一特定主题,要么宁愿运用别的“主义”来诠释卢梭,着眼于总体的研究屈指可数,朗松(Gustave Lanson)是为数不多的、愿意对卢梭思想做全面研究的先驱。1912年,他在《卢梭学会年鉴》上发表论文《让-雅克·卢梭思想的统一性》,提出“要严肃认真地权衡文本的意义与重要性,不要用从作者思想中推演出来的结论替换作者本人的思想,要赋予其观念恰如其分的意义”。1932年,卡西勒(Ernst Cassirer)在法兰西哲学学会上做了“让-雅克·卢梭著作的统一性”的报告,主张从“作为一个整体的卢梭作品去理解卢梭,以揭示其思想的意义”。1947年,施特劳斯(Leo Strauss)在其任教的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的院刊《社会研究》上发表书评《论卢梭的意图》,主张从探究卢梭写作的总体意图出发,厘清他在现代启蒙思想中的地位。正是在朗松、卡西勒和施特劳斯等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欧美学界对卢梭思想的反思才逐步往前推进。
在卢梭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卢梭的继承者们虽然都自命洞悉卢梭思想的本质,但大多数是从各自立场出发取其所需,难免会歪曲卢梭的学说。卡西勒试图将卢梭思想中相互冲突的地方解释为“一致而融贯”的整体。[1](1-2)他把所谓的“卢梭问题”描述为“与现代性社会的决裂”。
实验2 仿真中设置Tw=1.5Ts和Twc=1.5Tsc,盲检测算法对接收信号的处理输出如图4(a)、4(c)、4(e)所示.再考虑Tw=4Ts和Twc=2Tsc(满足前文提出的周期参数设计方案),盲检测算法对接收信号的处理输出如图4(b)、4(d)、4(f)所示.
它[现代性社会]不仅掌控我们的外部行为,而且还主宰我们所有内在的冲劲,我们所有的思想与判断。这种力量挫败了一切独立、一切自由、一切判断的原创性。不再是我们来作出思考与判断了:社会思考我们,社会替我们思考。我们不必再去寻求真理:新鲜出炉的真理被塞到我们手中[1](40)。
起兴,又叫“兴”。起兴先说其他事物,再说要说的事物。有起情,营造作品气氛,协调韵律,确定韵脚和音步,拈连上下文关系等的作用。“水向东流”可以看做一个起兴,先说水,再说时间。使得歌词音律和谐,同时使语言咏唱自由,行文更加顺畅。“水向东流”无疑打破了这个美梦,水和时间都无法逆流,揭露了残酷的现实:过去的已经过去,也无法回去。
卡西勒发现,卢梭不认为现代性社会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因为它使人丧失了自己的天性,人在现代性社会中看似自由,却必须依靠他人的意见才能拼凑出自身存在的意识。卡西勒将卢梭与现代性社会决裂的原因归结为卢梭的道德冲动,但他没进一步解释道德冲动与现代性社会有何冲突。施特劳斯透过道德冲动的表象看到,决裂的深层原因在于现代性社会表现出某种教条主义的品质,它忽略目标、关注制度,忽略品质、着重技术,必然会与道德分道扬镳[2](107)。
只有将“一论”放置在霍布斯所开创的现代政治哲学的语境下审视,卢梭的意图才会充分展现出来。如前所述,自我保存既是人最根本的欲望,也是优先于一切义务的自然权利。自由政体即是以自然权利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而保障自然权利最有效的手段是增加和积累自己的财富。由此可见,自由政体势必会发展成关心财富的政体,它鼓励人们的才干和勤劳,对德性非但漠不关心,反而将那些有利于实现自然权利的品质当作德性,替换德性的实质意涵。“一旦人们不惜任何代价只求发财致富,德性会变成什么样子呢”?[14](43)卢梭的结论是:推崇科学与文艺的社会,很容易贬低德性的价值,从而导致道德风尚的衰败。
在这五个要点中,前三个要点证明了科学与包括自由政体在内的一切政体都不相容,后两点证明了科学与自由政体不相容。由于卢梭已经证明了德性与自由政体相容,那么科学自然与德性不相容。如果卢梭当真旗帜鲜明地支持这一点,他就不会那么让人头疼了。实际上,卢梭在鼓吹科学与德性不相容的同时,又暗中承认二者其实可以相容,有部分研究者就以此为依据批评卢梭自相矛盾。其实,卢梭在“一论”第一部分的开篇就曾说过:“人类应当凭借自己的理性之光驱散自然包裹住他的阴霾。”[14](19)无论对这句话作何理解,它至少都暗示,“理论知识或自然科学是认识人及其责任的必要基础”[16]。“一论”结尾处,卢梭称培根、笛卡尔和牛顿为人类的导师,他们“能以智慧教育人民从而增进人民的幸福”,与前文相呼应。如此一来,科学似乎的确与德性不相冲突[14](60)。
羊群走路靠头羊,无私的领导带出奉献的兵。多年来,王丽霞全身心扑在工作上,带领全院谋求食检事业发展,淋漓尽致展现了一心为公、检验为民的朴素情怀。在急难险重任务面前,她带头加班加点,冲锋在前;在名利面前,却主动将荣誉和机会让给年轻骨干。先后培养出“三三三人才”、青年拔尖人才11人,培养国际ISO专家1人,国家和省级专家50余人。她带领的团队先后荣获“河北省直五一奖状”“河北省直先进集体”等10余项称号。她连续8年考核优秀,受嘉奖8次,荣立三等功1次,并荣获“河北省直五一奖章”。
上述论断如果成立,至少需要澄清卢梭著述中的三大疑问:第一,为什么卢梭认为霍布斯开创的现代政治哲学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困境?第二,卢梭为何不愿意从古典的立场出发批判现代性?第三,对现代性的批判为何反过来会推进现代性?
红军在雪山草地筹粮过程中,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一、号召节约粮食,严格拟定粮食分配计划;加紧粮食宣传工作,动员群众将自己的粮食和食物支援红军。二、缴获战利品。三、通过苏维埃政府没收劣绅、地主的粮食。四、向商人和当地群众购买粮食。五、运走藏匿在老百姓家的粮食和窖藏,留下银元或欠条,收割地里成熟的青稞、小麦等,插上木板借条。
二、自由政体的内在困境
施特劳斯在《论卢梭的意图》开篇指出:“有关卢梭意图的古旧论争,隐藏着有关民主性质的政治论争。”因为“民主或一般自由政体与科学的相容性是一个重大问题”[4](69)。这句话表达了两层意思:第一,卢梭把民主政体等同于自由政体;第二,卢梭的意图与自由政体的性质有关。具体来讲,卢梭思考的核心问题是自由政体与科学的关系问题,这也是1749年第戎学院有奖征文——《复兴科学与文艺是否有助于纯化道德风尚?》——的题中之义。卢梭在晚年曾袒露心声:“自第戎学院征文题目鼓动了他以来,这个问题就一直萦绕在他心中……之后的写作尽管涉及诸多主题,但始终遵循着同样的原理:始终是同样的道德、同样的信仰、同样的准则,还可以说是同样的观点。”[5](30-31)
现代社会不但是卢梭试图逃避、却又避无可避的现实处境,而且是他全部思考的出发点。在卢梭看来,现代性的危机源于自由政体的内在困境,自由政体是现代政治哲人的理性设计,它的设计师是自诩为现代政治哲学创始人的霍布斯。这一看法让人生疑:一般的流行看法认为,洛克才是自由政体之父,霍布斯不是国家主义的鼻祖吗?为何霍布斯又成了自由政体的设计师?卢梭会不会搞错了?
《黑暗圣徒》创作于1987年,是威特金艺术追求的代表之作。通常都是如此,这次也不例外:某个有着某种身体残疾的人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朋友们跟他提起一个坐着轮椅、没有脸和胳膊的人。威特金受到启发,将脑中的创意画成草图——一幅潦草的涂画或者说是一张素描。
其实,流行的看法夸大了洛克与霍布斯之间的差异,往往忽略了洛克对霍布斯学说中关键性原则,即“权利优先于义务”原则的继承。霍布斯无所顾忌地宣称,自我保存的权利不以任何义务为前提,义务是在权利结束的地方出现的,“没有人有义务去接受他所遭到的死亡(即自然中最高的损害)的威胁以及伤害或其他难以承受的身体损害”[6](19-22)。于是,自我保存的权利成为道德的唯一正当性来源。道德的本质在于权利,而非义务。只有绝对的、无条件的权利,没有绝对的、无条件的义务,义务只有在不危及人的自我保存时才具有约束力。这是霍布斯自然法理论的基础。自我保存是人的自然权利,正是这项自然权利赋予人们自由。相比之下,洛克的自然法虽然同样强调“权利优先于义务”的原则,但他委婉的行文、温和的表述很容易令人忽视其霍布斯主义者的身份:
上帝既创造人类,便在他身上,如同在其他一切动物身上一样,扎下了一种强烈的自我保存的欲望……既然上帝亲自把保存自己生命和存在的欲望,作为一种行动的原则,扎根于人的身上,作为人类心中的上帝之声的理性,就不能不教导他并且使他相信,按照他所具有的自我保存的自然倾向行事,就是服从他的创造主的旨意[7](74)。
卢梭不仅发现了自由政体的困境,还洞察到这一困境源于启蒙与道德之间的裂隙——关于个人权利的启蒙无法提供政治共同体所必需的社会德性,所以他打算从重建启蒙与道德的关系上寻找突破口。这构成了卢梭写作《论科学与文艺》(以下简称“一论”)的主要思考方向。正是在这一点上,卢梭对现代性发起了第一次攻击。
根据霍布斯的学说建构起来的国家虽然会限制人们原初的绝对自由,但绝对自由对人不见得有益。有益的自由是“让每个公民保持他在和平中过得安宁所需要的自由,同时又取消别人的某些自由,使他足以摆脱对别人的恐惧”[6](102)。为了摆脱无益的绝对自由,实现有益的自由,必须加强国家的统治权力。换言之,只有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利维坦”国家,个人自由才能从抽象的概念“道成肉身”,落到实处。自由主义追求的不只是享有自由权利的个体,更应当追求以自由权利为政治诉求的自由政体。如此看来,霍布斯的国家主义难道不是自由主义吗?保守派自由主义大师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就深谙霍布斯的自由主义底色,他说:“霍布斯本人虽然不被看作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他哲学中的自由主义成分比多数自称自由主义的捍卫者的还要多。”[9]可见,卢梭把霍布斯看作自由政体的设计师,非但没有搞错,反倒把握住了霍布斯政治哲学的实质。
鳗鱼带肉骨→预处理→净鳗鱼带肉骨→烘干→干鳗鱼带肉骨→粉碎、均质→鳗鱼肉骨粉→水提→鳗鱼肉骨粉料液→酶解→酶解液→均质→喷雾干燥→成品。
为了实现如此政治诉求的自由政体,霍布斯不得不与整个古典政治哲学传统决裂,他抱怨古典哲人们没有正确地揭示伦理学说中的全部公理,甚至编造了一则寓言来嘲讽他们的不切实际:
伊克西翁应朱庇特之邀赴宴时,爱上了朱诺本人并骚扰她。在这女神的位置上,有一片形似朱诺的云出现在他面前。从云中诞生了塞恩托,一个半人半马、好战而不安分的物种。如果改变一下名称,他们仿佛是在对我们说,个人聚集在讨论国家这种最高问题的议事会上,企图让作为主权之姐妹和妻子的正义屈从于他们自己的理解,但他们所拥抱的正义女神只是一片错误而空洞的浮云,于是产生了道德哲学家那些模棱两可的教义,它们既有正确和吸引人的成分,也有野蛮和非理性的内容,这就是一切争执和杀戮的起因[6](8-9)。
田间数据的采集、处理以及各项数据的调查、汇总、整理存档,统一由专人负责,确保数据准确规范并及时上报。同时加强耕地质量监测的档案管理,分类整理立卷,包括耕地质量监测报告、田间原始数据调查记载表等。
简而言之,霍布斯将所有的古典政治哲学都看作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它们往往满足于对最佳政体的描述,却又众说纷纭,彼此冲突,不愿花心思考虑实现最佳政体的可能性。古典政治哲学的要求对人性来说既高不可攀又不切实际,真正可行的方案是从“低而稳健的地基”上建立起全新的政治秩序[6](38-39)。霍布斯在自然状态这块道德的“新大陆”上发现了新的地基:自然状态是产生一切社会秩序之前的状态,亦即缺乏公共权力统治的状态。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彼此平等,因为他们不受任何人的支配,有着同等(最大)程度的自由,但如上所述,这自由对他并没有什么益处,因为,如果说每个人都被看成是天生追求自己利益的行动者,而伤害他人在某些情况下又是对自己有益的,那么这自由便包含了依据自己的自由意志去伤害别人的权利;反之,别人也有同等的自由权利来伤害自己[6](7-8)。这无异说,每个人都有不受约束杀死他人的潜在的权利;与此同时,每个人的生命也时刻遭受着死亡的威胁。在一切人敌视一切人的战争状态下,每个人虽然都享有自由,但他们的自由无法摆脱对暴死的恐惧。这恐惧成为一切情感中最强烈的情感,驱使着人们去寻找和平与安宁。出于对这一普遍情感的克服,人们愿意放弃自己的部分自由(权利),同意将之让渡给主权者,缔结契约,建立国家[10](92-97)。就这样,人们获得了“理性、安全、财富、光彩、交往、高雅、科学和仁厚”,他们失去的不过是“激情、战争、恐惧、贫穷、龌龊、孤独、野蛮、无知和残暴”[6](102-103)。
卢梭表面上佩服霍布斯的理性设计,内心却不以为然,“这项政治技艺的杰作越是令人赞赏,就越难纳入所有洞穿它的眼睛”[11]。因为,自由政体这一理性设计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内在困境。
霍布斯的理性设计以“对暴死的恐惧”为基石,只有当这种恐惧成为普遍人性中最为强烈的情感,国家才有可能建立在社会契约之上[12]。然而,霍布斯心里明白,现实中的国家并非建立在社会契约之上,因为“对于暴死的恐惧”并非现实中的人最强烈的情感——在霍布斯生活的17世纪,宗教依然保持着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上帝往往比暴死更加让人感到恐惧。现实情况不会让人们萌发让渡自由的念头。因此,霍布斯的理性设计若想成功,必须借助于一个特定的前提:他必须说服民众,“对上帝的恐惧”归根结底是对未知事物的畏惧,它不是对真实对象的正确反映,而是基于“不同的想象、判断和激情”所形成的偏见。也就是说,必须通过启蒙将“对上帝的恐惧”纠正为“对暴死的恐惧”,并灌输关于自然状态的观念,将民众从传统宗教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自由政体的理性设计才会生效。即便如此,经过启蒙的民众却并不见得会因此而变得富有德性,因为民众获得的并不是道德教诲,而是关于自由权利的意识。自由政体根本没有被赋予教育民众的政治权利,反过来,经过启蒙的民众倒是意识到自己有限制自由政体施行统治的自然权利。这样一来,自由政体中的民众何以可能富有德性就成了问题[13](8)。更重要的是,既然建立自由政体的理由来自对死亡的恐惧和自我保存的欲望,既然人们可以出于趋利避害的目的组建自由政体,当这自由政体到了危难之际,需要民众用血肉之躯去保卫它的时候,它能够指望这些在德性上可能成问题的民众吗?我们完全有理由设想,这些民众也会出于趋利避害的目的离自由政体而去。对死亡的恐惧和自我保存的欲望完全有可能成为自由政体解体的理由。
第二,霍布斯一方面认为自然权利来自于人类对于暴死的恐惧,恐惧是一种情感,所以自然法根植于人的情感当中,因而是优先于理性的;可另一方面,他又将理性的诫命视作是“由定理推出的结论”。推论是一种理性行为,所以自然法也是理性的。卢梭从霍布斯的自相矛盾中得出结论:人并非天生就是理性的动物,“动脑筋思考是有悖于自然的状态;沉思的人是一种堕落的动物”[15](56),自然人只需要关心自己的利益、听从自己欲望的指挥足矣,不需要在行动之前专门请教理性。可见,在自然状态下,自然人根本不需要理性,“只有生活在社会状态下,他才需要培养理性思考的才能”[19](25)。
自由政体的实现离不开启蒙,但启蒙又不足以维系自由政体,甚至有可能瓦解自由政体。这是霍布斯哲学在逻辑上的必然结果。其基本思路就是把人从传统政体中分离出来,变成自然状态中的孤立个体,然后再让这些个体按照契约重新结合在一起组成国家。但是,这样的国家不过是许多孤立个体的松散集合,随时有解体的危险。因此,如何把自由政体中的公民黏合起来,形成有凝聚力的有机统一体,这成为卢梭必须面对的巨大挑战。由此可见,按照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所打造的自由政体确实存在难以克服的困境。
洛克以上帝的名义重申了霍布斯的“权利优先于义务”原则。他注意到,人的自我保存首先需要的是食物,人必须拿财富换取食物。因此,自我保存的欲望便顺利成章地转换成获取财富的欲望。理论上的微调引发了实践上的蝴蝶效应:既然最根本的政治问题被还原成以正当的方式获取财富和分配财富,那么 “用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就成为最优雅的解决方案”[8](41)。所谓的自由主义之父洛克暗地里以霍布斯为师,说霍布斯是自由主义的鼻祖并不奇怪。
三、德性:《论科学与文艺》提出的解决方案
卢梭在“一论”开篇交代了他的写作意图,“我绝非是在攻击科学,我对自己说,我这是在有德性的人们面前保卫德性。”[14](18)实际上,卢梭并未对科学手下留情,他从“所有时代和所有地方观察到同样的现象”——科学的繁荣将导致德性的腐化[14](25)。“德性”无疑是“一论”的关键词:德性是“纯朴灵魂的崇高科学”,是“真正的哲学”,[14](61)它不需要科学,因为它存在于每个人的良知之中,只要反求诸己就可以不思而得。德性对于政治共同体的强盛是唯一要紧之物,“那些不受虚浮的知识所污染的民族,以自己的德性造就了自己的幸福,成为了其他所有民族的榜样”[14](29)。科学与文艺是由“骄奢淫逸”的作风滋养出来的,助长它们的是启蒙,“随着科学与文艺之光在我们的视野中出现,德性也就随之消逝了”[14](26),“科学与文艺越是臻至完美,我们的德性就越发腐败”[14](23)。为何卢梭会将科学与德性对立起来呢?
作者首先讨论了诗歌译者的意向活动并提出:诗歌翻译的重点在于对原诗创作意向活动中意向性质、质料及其统一体意向本质的还原。这些意向内容的还原决定着译诗对原诗的关指度,并进一步决定着译诗和原诗之间除普遍存在的跨语指向关系外,究竟是构造关系还是包含关系。译诗是译者意向性关指的结果。然而,译诗的意向性关指和原诗的意义影响之间的矛盾会让译者产生“影响的焦虑”。作者借助玄言诗、佛理诗和禅趣诗,考察了译者在翻译意向活动中的焦虑,解析了焦虑的根源。
面对无视德性的自由政体,卢梭尝试从关心德性的古人那里寻求帮助,他找到了苏格拉底、老加图和法布里乌斯。通过列举这三位古人的言行,卢梭重新界定了德性的内涵,使其有别于自由政体意义上的德性:第一,卢梭是从公民政体的角度出发来理解德性的,德性通常被看作热爱公民政体的品质,换言之,德性被卢梭界定为公民德性。公民德性与公民权利并不直接相关,它首先是一种主动履行自己义务的责任。第二,公民德性与公民政体互为前提,只有在统一的公民政体中才找得到公民德性;反之,只有当公民德性为公民政体注入凝聚力和向心力时,公民政体才不会涣散和解体。自然权利一旦失去了其作为公民政体的奠基性地位,便从法理上杜绝了出于自我保存的行为而导致公民政体解体的可能性。第三,德性既指公民德性,理智便无法充当德性的基础,因为每个人的理智存在着高低不一的自然差异。不过,每个人都有一种先天的厌恶之情,他不愿看见有知觉的生物尤其是自己的同类死亡或遭受痛苦[15](40)。德性的自然根基不是理智,而是同情心(the sentiment of compassion)。从有差别的理智出发,我们无法得出平等的民主诉求;从无差异的同情心出发,民主的诉求就显得合乎情理。通过将同情心而非理智看作德性的自然根基,卢梭从德性与公民政体的普遍联系中发现了同情心与自由政体的特殊联系。
2) 地统计学分析。采用GS+9.0软件计算,以区域化变量理论为基础,以半方差函数为主要工具,通过块金值、基台值、块金效应、决定系数、残差以及变程等定量地描述各要素在空间异质性程度、组成、尺度和格局特征。
既然卢梭已经认定德性与自由政体相容,那么他只需证明科学与自由政体不相容,就可以证明科学的进步无助于德性的提高了。根据施特劳斯的归纳,卢梭的论证可以分成五个要点:第一,任何政治共同体在本质上都是一个特殊的、封闭的社会,自由政体也不例外,而科学是普遍的,会削弱、破坏政治共同体独特的公民德性。第二,任何政治共同体都要求其成员全心全意地献身于公共之善,而追求真理的科学家或哲学家实质上是在追求个人之善,他们不关心公共之善,或者说,他们对个人之善的关心优先于公共之善,从而很容易被当成对政治共同体无用的游手好闲之徒。第三,政治共同体的基础是信念或意见,而科学追求真理的道路是由怀疑主义的精神所铺就的,它容易动摇特定政治体的精神信念。第四,自由政体的前提是让公民放弃自然自由来换取公民自由,而科学家或哲学家一定要顺从自己的天才,不会为了迁就自由政体的需要而牺牲自己的自然自由。第五,政治体用习俗性的平等取代自然的不平等,哲学家若要充分实现自己高人一等的智性天赋,必须重申自然的不平等[3](262-265)。
现代性社会是现代知识人的发明,确切地说,是霍布斯所开创的现代政治哲学的理论设计。随着这一理论设计在实践层面徐徐展开,隐含在现代性社会逻辑深处的内在困境也慢慢浮出水面。为了克服这一困境,卢梭不得不丢弃霍布斯思想中残存的古典要素,反而推进了现代性的进程[3](257)。
科学何以可能既与德性相容,又与德性不相容呢?对于这显而易见的自相矛盾,卢梭提供了三种解决方案:首先,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科学不可避免地会动摇社会的根基,它对于一个好的社会是坏的,对于坏的社会反而是好的。当人们处于一种比蒙昧无知还要糟糕的状态中时,为了使人们恢复常识,就必须来一场革命。科学对于腐化社会的任何抨击都可以视为合理的。这样,科学在坏的社会中与德性相容,在好的社会中与德性不相容[14](19-20)。其次,存在两种天分不同的人,科学对他们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普通人不懂科学,为了让他们认识科学,必须将科学普及化,而科学一经普及,就容易沦为偏见,偏见对普通人有害,而未经普及的科学却对于少数天才大有裨益。这样,科学便与少数天才的德性相容,与多数普通人的德性不相容[14](26-29)。最后,存在两种性质不同的科学:一种是苏格拉底式智慧,另一种是形而上学。苏格拉底式智慧是一种“无知之知”,它有利于保护“纯朴的心灵不至于误入歧途”,而形而上学只关心真理[14](32-34)。这样,苏格拉底式智慧与德性相容,形而上学与德性不相容[3](265-269)。
最后一种解决办法似乎最为全面,因为它同时包含了前两种办法。卢梭本可以通过区分苏格拉底式智慧和形而上学来解决科学与德性的相容性问题,但卢梭认为哲学家的天才比普通人的德性更接近“自然”的本真含义。对“自然”概念的特殊领会促使他放弃了第三种解决方案,以至于施特劳斯以略带惋惜的口吻说,“如果卢梭的最高标准乃是有德性的公民而非‘自然人’的话,这种解决方法就可以看作是一劳永逸的了”。[3](269)
倘若卢梭认为德性的公民更值得追求的话,这意味着他最终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中选择了古典哲人的立场,即凭靠苏格拉底式智慧去矫正自由政体。可是,卢梭仅仅表面上颂扬苏格拉底,实际上仍旧以“培根、笛卡尔和牛顿”为榜样,即相当于以自然科学为榜样。这促使他不得不在《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以下简称“二论”)中以自然的名义同时对科学和德性提出质疑。卢梭对“自然”概念的理解有何独特之处,以至于自然竟与德性不相容?卢梭在“二论”开篇引用过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一段话,也许有助于我们窥得卢梭是如何理解“自然”的:
车身侧面最动人的无疑是SAV标志性的车身比例。相比上一代车型,全新BMW X5尺寸全面加大,轴距比前代车型长42毫米,由此带来了更加舒展的车身。同时精确的腰线从后门处上扬,构成了富有力量感的肩部特征,并与伸展到侧翼的3D立体悬浮LED尾灯相融合,展现了富有艺术气息的科技感和雕塑感。环顾全新BMW X5不难发现它散发着X家族强劲、清晰而精确设计特征,让时尚感与豪华感并存。
凡属于自然的东西,我们就不要再自然[天性]已经败坏的人身上去寻找,而应当在依据自然[天性]就是好的那些人身上去寻找[15](19)。
在《政治学》中,这段话所在的段落旨在证成“存在着天然的奴隶”。亚里士多德论证道,统治与被统治的区别见于自然界中的有生命物,也见于无生命物。对于人这一特殊的生物而言,灵魂对身体的统治、理性对欲望的统治符合人的自然目的。这样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只有在那些自然天性充分实现的人身上去寻找,而不可能出现在那些未能实现或已败坏的自然天性的人身上[17]。不过,卢梭却不这样认为。紧接在这段引语之后的序言部分就清楚地表明,卢梭并未像亚里士多德那样把自然的事物理解为充分实现的事物,他径自把自然的事物等同于原初的事物,所谓人的自然状态就是人的原初状态,而人的自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世事的沧桑,被弄得难以辨认,已经失去了造物主为其打上的纯朴烙印”[15](35-36)。
经过近代自然科学的启蒙,古典哲人主张的自然目的论到卢梭这里几近全面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对自然的机械论理解。一方面,卢梭用事物的原初状态取代事物的充分实现状态来描述“自然”概念;另一方面,卢梭用“人天生是情感的动物”取代亚里士多德的“人天生是理性的动物”。卢梭的“自然”概念是机械论式的“自然”概念;卢梭的自然人是缺乏理性的野蛮人。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定义,德性是一种以实现善为目的、以中道为手段的品质,中道介于过度与不及之间,它的尺度由理性来规定[18]。卢梭反对从目的理解自然,反对从理性理解自然人,他当然也不会赞成自然与德性的相容。这多少可以理解,卢梭为什么不愿意站在古典的立场上批判现代性。
四、自然:《论不平等》提出的解决方案
与“一论”相比,“二论”的批判有两个特点:第一,卢梭在“一论”中是以日内瓦公民的身份去质疑自由政体的正当性,“古代政治家们不厌其烦地讲风尚和德性;我们的政治家们则只讲生意和赚钱。”[14](43)在“一论”中,德性被卢梭当作批判的武器,尽管卢梭赋予“德性”一词的含义含混不清,但它在“一论”中至少是不证自明的前提。然而,卢梭是以哲人的身份写作“二论”,他将柏拉图和芝诺克拉底这二位古典哲人当作自己的仲裁。在哲人面前,德性不再被当作不证自明的前提,批判的武器也要接受武器的批判。第二,由于卢梭认定必须从人的原初状态中去考察人性,亦即必须从自然状态出发研究人性,这意味着他重新接受了霍布斯自然权利论的前提,摈弃了古典哲人从人的目的去理解人性的自然权利论。从“一论”到“二论”,卢梭的立场发生了一个反转,他不是站在古典的立场上认为现代性不可取才批判现代性,而是站在现代的立场上认为霍布斯的现代性方案还不够“现代”。
实际上,研究者们通常只注意到了卢梭反对霍布斯的一面,却往往忽略了卢梭赞同霍布斯的一面:首先,卢梭同意霍布斯对古典自然法的攻击,自然法不见得非得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其次,他也同意霍布斯对自然法的革新,即从自我保存的欲望中发现自然法的原则,他甚至同意,自然状态是人在政治状态之外的状态。卢梭不满的地方仅仅在于,霍布斯走得还不够远,他并没有抵达真正的自然状态,虽然他自以为做到了。在卢梭看来,霍布斯在设计自然状态时显得“犹豫不决”,没能将他设计的原则一以贯之。反过来讲,为了将霍布斯的原则贯彻到底,卢梭又不得不把批判的矛头对准霍布斯。
第一,霍布斯虽然否认人天生是社会性的动物,而且也认为必须将人的自然本性追溯到自然状态,但他没有真正追溯到这种状态,从而犯了时代错乱(anachronism)的错误。霍布斯把“人类只有在社会状态中才有的观念拿到自然状态中来讲,他讲的是野蛮人,但他笔下描绘出来的却是文明人”。他为自然状态中的自然人保留了原本不属于自然人的太多社会属性,比如,“需要、贪心、压迫、欲望和骄傲”[15](48-49)。然而,严格意义上的自然状态不仅是抽离了“社会”的状态,更是抽离了“社会性”的状态。自然状态下的自然人是社会性阙如的个体,他不仅没有家庭和国家等社会关系,也不会产生只有在社会状态下才有的社会情感,诸如自卑、嫉妒、骄傲。
目前我国地铁建筑工程的施工人员几乎每天都会有变动,流动性比较大,在建筑单位进行进场前的安全教育培训的过程中,加大了工作量,导致安全培训过与形式化,不能将培训效果最大程度的发挥出。当相关工作人员没有安全意识时,就会非常容易出现安全事故。
基于上述两个理由,卢梭决心不再对霍布斯亦步亦趋,打算独自前往连霍布斯也不曾抵达的道德“新大陆”。而要想抵达真正的自然状态,卢梭必须将霍布斯保留在人性中的社会性和理性涤荡干净。实际上,卢梭在打扫霍布斯的“残余物”时凭靠的正是“霍布斯的扫帚”,正是由于卢梭严格遵照了霍布斯的原则,才得出了与霍布斯本人截然不同的结论。
施特劳斯注意到,卢梭在继续霍布斯的“未竟之业”时创造性地将缺乏社会性与缺乏理性关联在一起,并且试图用前者证成了后者[3](276-277)。理性的观念有别于一般的观念,一般观念的构成要素的记忆或想象,理性观念的构成要素是概念。概念以定义为前提,而定义以语言为前提条件。语言是社会交往的产物,只有当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足够频繁、足够深入时,才会产生语言。尽管自然人偶尔也会交流,但偶然的交流无法形成“有关物质、精神、质料、形式、形象和运动”的概念,也就无法产生语言。语言是社会习俗的产物,它不是自然的,所以理性也不是自然的产物[15](71)。自然人没有理性,也就不可能获得关于自然法的知识,他像其它动物一样受自然法则的支配。就算承认自然人有理性,他的理性与动物的“理性”也没有实质性的差异,用卢梭的话讲,自然人是与动物没有本质区别的次人(sub-human)。
Piloti是一个加州的鞋履品牌,上世纪90年代初成立时主攻赛车鞋领域。在积累了一定技术之后,Piloti决定进军市场更为广泛的日常鞋履领域,专注设计、制造最适合日常驾驶的鞋子。这款Pistone X驾驶鞋采用了柔软的橡胶外底和特别设计的杯型后跟,以及带有特殊泡沫缓震技术的中底,使得整双鞋的脚感轻盈直接,开车时用脚后跟支撑数小时都不会疲倦。鞋面采用了特殊的合成材料,透气且柔软。最重要的是,这双鞋的造型流畅美观,日常穿着也没有问题。
如此一来,“二论”便彻底否定了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的本质的古典定义,原本只是隐藏在“一论”中的否定性要素被彻底揭示出来。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理性是人人享有自然禀赋,但每个人享有的理性在程度上却有所不同,这势必存在着上智和下愚的自然差异,由此所导致的上智对下愚的统治以及由这统治所导致的不平等便为自然所允许。卢梭在“二论”中一直强调,理性不是人与生俱来的,而是人在脱离自然状态之后才获得的。既然理性不是自然的,所谓的自然差异也就不复存在了,由这差异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便不再被自然所允许。如果说霍布斯对亚里士多德的否定只是动摇了理性的统治地位,打碎了束缚情感的枷锁,那卢梭对亚里士多德的否定则相当于釜底抽薪地废黜了理性的统治法权。霍布斯虽然解放了激情,但理性继续以遥控的方式统治着,然而在卢梭眼里,激情本来就是主动的,理性僭越了激情本来的地位,才导致德性的败坏和人的堕落,要恢复人性的崇高,不得不恢复激情的原初地位[3](257)。
于是,卢梭终于依据霍布斯的原则完成了霍布斯的“未竟之业”,他发现了真正的自然人。但他的发现却导致了一个霍布斯也未曾料到的结果:作为次人,自然人既不具备理性也不具备社会性,他是一个无规定性的抽象存在。唯有两项特质可以用来描述自然人,将他与动物分开:自由是其中一项特质,“动物的行为完全受自然的支配,而人却不然;人是一个自由的主体,他可以把受自然支配的行为与自己主动的行为结合起来。动物根据它的本能来决定它对事物的取舍,而人却可以自由地选择什么或放弃什么。动物的行为不能违背自然给规定的法则,即使某些行为对它们有利,它也不做;而人却不然,即使某些事情对他有害,他也想做就做”。另一项特质是可完善性(perfectibility),“这项能力在环境的帮助下可以使其他的能力不断发展;这个能力既存在于我们种类中间,也存在在个人身上。而动物则不然,一个动物在几个月之后长成的样子,以后终生都不会改变;它的种类,即使时光过了一千年,它们还依然是这一千年开头那一年的那个样子”[15](59-61)。然而,自由和可完善性充其量只是对人的描述,无法为人提供任何规定性。
对人来说,没有什么自然的构成可言:一切专属人类的东西都是由人为或习俗而获得的,或者说最终是依赖于人为或习俗的。人本于自然几乎是可以无穷地完善的。对于人的几乎无穷无尽的进步而言,或者说对于他使自己从邪恶中解放出来的能力而言,并不存在什么自然的障碍。基于同样的理由,对于人的几乎无穷无尽的堕落而言,也不存在什么自然的障碍。人本于自然有着几乎是无穷的可塑性。用芮那尔神父的话来说,我们想让人类变成什么样子,它就变成什么样子。如果说本性的确切意义是给人能将自己造就成什么样子划定界限的话,那么人就是没有本性的[3](277-278)。
我们惊奇地发现,自然状态下的自然人没有人性(humanity),人性不是自然人与生俱来的,而是自然人在克服自然、改变自然的过程中逐渐获得的。这无异于说,人性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渐生成的。卢梭发现,“由霍布斯的前提出发,就必然要全盘抛弃掉在自然、在人性中找寻权利的基础的图谋”。历史过程与自然状态相比显得更为可取,因为“人们似乎有可能在历史过程中找到人类行动的准绳”[3](280)。卢梭虽然没有迈出这一步,但他掏空“自然状态”的做法将古典的与霍布斯的理性主义连根拔起,堵死了后人返回古典的道路,迫使他们成为现代性的共谋者,所谓历史主义就是沿着这一思路拼死突围的结果。卢梭不愿意接受突围的安排,因为,历史过程充斥着无数没有因果联系的偶然性事件,它要么没有意义,要么它的意义无法被人认识。卢梭不相信历史能够为人性提供永恒不变的根基,成为人类行为的标准。
后来的研究者们对于卢梭的选择常感到迷惑不解:卢梭希望返回自然状态,深入自然状态中的人性去寻找权利的基础,可当他真正返回自然状态时才发现,他几乎掏空了“自然状态”概念的全部意涵,使之成为一个消极的概念。同时,卢梭又拒斥历史主义,不愿意承认历史过程对于塑造人性来说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无论是遵从自然还是遵从历史,都无法找到人的规定性,卢梭似乎因此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
其实,所谓的“卢梭困境”完全是一个误会,借用朗松的说法,它不过是后来的研究者“从卢梭思想中推演出来的结论来替换卢梭本人思想”的结果而已。对于卢梭本人来说,兴许“卢梭困境”根本就不成立。当卢梭说历史过程无法取代自然状态为人性提供自然参照时,他并不打算将“自然状态”看作消极概念。恰恰相反,卢梭认为将“自然状态”看作消极概念的是霍布斯。在霍布斯笔下,自然状态是一种不稳定的矛盾状态,它的矛盾性一方面体现在,自然状态下的人虽然享有绝对的自由和平等,但他也时刻遭受着暴死的威胁;更重要的是,这种矛盾是一种理性的矛盾,因为自然权利在自然状态下是无法发挥作用。尽管每个人都可以任意地行使自己的自然权利,但他对自然权利的行使将受到别人对自然权利的行使的限制。自然权利驱使着人们退出自然状态,进入公民社会。可见,霍布斯在设计自然状态的时候就有意将其设计成必须被克服的否定性概念。
卢梭洞察到了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的矛盾性,一个矛盾的自然状态只能成为扬弃的对象,而无法成为积极的标准。所以,当我们说卢梭把“自然状态”变成一个空洞的概念时,这绝不等于说,他把“自然状态”变成了一个消极的概念,更不等于说他彻底抛弃了“自然状态”概念。毋宁说,卢梭祛除的是“自然状态”的矛盾性,他这样做是为了赋予“自然状态”全新的积极含义:这样的“自然状态”指向“一种不再对人性的考虑为基础的自然权利论,或者说,它所指向的是不再是作为理性法则的自然法”[3](282)。但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和一个“愚蠢的动物”又能为卢梭提供什么样的积极标准呢?
当卢梭接受自我保存这一霍布斯的前提时,他其实有所保留。因为他很清楚,自我保存的权利奠基于某种人与动物所共有的欲求之上。如前所述,它既可以成为建立公民社会的理由,也可以成为公民社会解体的理由。若想避免后者,一个常见的解决方案是把人设想为某种社会性的动物,比如格劳秀斯的思路。卢梭曾在“二论”的献词中提到,他儿时曾读过格劳秀斯的著作,而且记忆深刻[15](30)。格劳秀斯就认为,人天生就有一种社会欲(desire of society),倾向于跟他的同类生活在一起[20]。其实,格劳秀斯的思路已经与古典政治哲学分道扬镳,尽管如此,卢梭还是不愿意接受任何关于“人天生是社会性动物”的学说。因为,任何社会对于自然状态中的自然人来说,都不啻为一套枷锁,社会是导致人性之恶的罪魁祸首,所以他希望保全个人相对于社会的优先性[1](66)。卢梭保留自然状态的意图有可能在于,只有在自然状态下,人才具有绝对的自然自由。这在最大程度上为建立以个人自由为政治诉求的自由政体提供了一个参照标准。因此,卢梭的“自然状态”虽然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却是一个积极的概念。自由是人所特有的属性,而自我保存是人与动物共同的欲望,用自由取代自我保存成为一切德性的基础,无异于将德性从动物性的基础之上挪到人性的基础之上。为了实现这一点,卢梭甚至放弃对“自由”这一概念进行必要的反思,从而使得“自由”获得了某种教条主义的优先性。卢梭坚信,唯一可靠的道德是我们作为其原因的道德,它是一种在本质上属于自由的创造性活动。这样,自由就等同于道德或德性本身。
自然状态下的自然自由为公民社会中的公民自由提供了一个可以效仿的参照标准,但按照卢梭的表述,这毕竟还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自由:公民自由是“处于枷锁之中的”自由,而自然自由是“受盲目的欲望支配的”非道德的自由。卢梭一方面严格区分二者,另一方面又刻意模糊二者的区别,毕竟,只有将自然自由与公民自由混淆在一起,卢梭真正向往的道德自由才能凌驾于前两者之上,为公民社会奠基—人通过自己的善良意志为自己立法,使自己既不屈从于外在的强制,也不屈从于内心的欲望,从而接近绝对意义上的自由。所谓自由的人,就是只服从自己的自由意志的人。卢梭的自由观直接影响了康德对自由的看法。康德将自由界定为“自律的行动”,亦即根据自己所立的法则而行动,而不是听从于欲望或社会习俗等偶然的、不能由自我操控的因素。借助康德的眼光,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勒特别能体会卢梭的道德自由:
自由并不意味着随心所欲,而是指克制与摒弃一切随心所欲,是指服从于个体为自身所设立的严厉而不可侵犯的法则。决定自由的真正特性的,不是拒斥或免除这一法则,而是自由地同意它[1](48)。
本次对照组患者采取血塞通治疗而观察组患者加入复方丹参滴丸治疗经过临床应用后观察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为85.2%,显著高于对照组为73.5%,提示加入复方胆滴丸可明显提高临床治疗效果,缓解相关临床症状;此外经过不同治疗后均具有改善,观察组改善情况显著优于对照组,提示观察组患者神经功能缺损恢复明显,生活能力显著改善,结果与郭红玲报道基本一致[4]。总之,经过本次对于分析我们认为:对于脑梗塞患者使用复方丹参滴丸治疗可提高临床疗效,和对照组相比,观察组头颅CT影像变化更为显著,此药物能够改善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荐使用。
卢梭开创了一种“自由的哲学”。尽管霍布斯被称作自由主义的鼻祖,但他并没有赋予自由绝对崇高的地位,自由必须服从于人的自我保存,一个人为了活命而放弃自由在霍布斯那里完全经得起辩护——自我保存而非自由才是最基本的自然权利。卢梭认为自由优先于自我保存,人若为了活命放弃自由,无异于放弃做人的尊严而甘为禽兽,这样自由就成为人之为人的德性。通过行使自己为自己立法的道德自由,“人们决定以自己的同类作为自己的主人”,建立一种公民宗教。所谓公民宗教,就是在集体层面上的自我立法,它把“对神明的崇拜与对法律的热爱结合在一起;而且由于它能使祖国成为公民崇拜的对象,从而就教导他们:效忠于国家也就是效忠于国家的守护神”[19](166-174)。公民宗教可以塑造公民的精神品质,培养公民热爱祖国的情感,这就保证了公民政体不会在特殊状态下因为公民的自我保存需要而解体。如此一来,卢梭建立自由政体的解决方案似乎成功了。
五、结语
然而,卢梭在“一论”中已经明确表明,宗教的根基不是知识,而是意见。公民宗教也是一种宗教,关于公民宗教的真理在本质上仍然不过是意见而已。由公民宗教所培育起来的精神仍然抵挡不住由科学精神所培育起来的怀疑主义的诘难,一旦公民宗教开始被公民怀疑,它就丧失其信服力,自由政体同样难以维系。
卢梭意识到,当他用“人是自由的行动者”的现代观念取代“人是理性的动物”古典观念时,依据该原则所设计出的自由政体也难以成为人类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任何公民政体都会对人造成束缚,绝对的自由在公民社会中难觅,但积极的“自然状态”概念为人们在公民社会中获取自由提供了观念上的依据。当卢梭谈起摆脱社会的真正自由时,他想到的未必是原始森林中的野蛮人,兴许是游离于公民社会边缘的孤独沉思者[21]。
卢梭对自由的执着使他难以忍受公民社会的约束,哪怕这些约束是一个健康的社会秩序必不可少的要素。只要政治哲学仍然被看作是对正义和善的政治秩序的思索,那么无论出于何种原则远离社会,都将被排除在政治哲学的范畴之外。在这个意义上,卢梭克服现代性的困境、重新设计自由政体的意图至少在政治哲学的层面上是注定要失败的。
我们现代人在今天重新审视卢梭为现代性的困境而设计的解决方案时,仍然感到难以理解。或许,所有的难题都可以还原为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事实:卢梭试图在霍布斯设计的自由政体的现代基础上保留德性的古典意涵。卢梭相信,霍布斯所设计的自由政体是人类值得追求的生活,前提是它能成功克服自身的内在困境。卢梭接过霍布斯的论题,并试图从霍布斯的原则出发去解决这一困境,最终却无奈地发现,他提供的方案也绝非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卢梭痛苦地发现,满足个人的自然欲望与履行公民的社会责任总是相互撕裂着,无法逻辑自洽地统一起来。换言之,卢梭希望在苏格拉底的层面上去解决霍布斯的难题,无奈这样的沉思太过不合时宜,不仅未能解决现代性的困境,反而使得号称理性的现代性事业离理性精神越来越远……
参考文献:
[1] 卡西勒.卢梭问题[M].王春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2] 李明坤.霍布斯与现代政治哲学的问题[J].学术月刊,2015,47(12):107.
[3] 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M].彭刚,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
[4] 施特劳斯.论卢梭的意图[A]// 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冯克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69.
[5] 卢梭.致博蒙书[M].吴雅凌,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30-31.
[6] 霍布斯.论公民[M].应星,冯克利,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
[7] 洛克.政府论:上[M].瞿菊农,叶启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74.
[8] 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A]// 什么是政治哲学.李世祥,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41.
[9] 奥克肖特.《利维坦》导读[A]// 现代性与自然.应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30.
[10] 霍布斯.利维坦[M].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92-97.
[11] 卢梭.卢梭全集:第5卷[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482.
[12] 方博.自由、公意与社会契约[J].哲学研究,2017:108.
[13] 刘小枫.设计共和[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8.
[14] 卢梭.论科学与艺术[M].何兆武,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15] 卢梭.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16] 普拉特纳.卢梭的自然状态[M].尚新建,余灵灵,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10.
[17]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4-15.
[18]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47-48.
[19] 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20] GROTIUS H.The rights of war and peace[M].Indianapolis,Liberty Fund,Inc,2005:79-80.
[21] 卢梭.卢梭全集:第3卷[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05-106.
The dilemma of modernity and Rousseau’s solution
WANG Jiangtao(School of Marxism,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Shanghai 201620,China)
Abstract:Rousseau believed that Hobbes’s teachings of Natural Rights had an unsolvable problem,which led to the dilemma of the modernity,namely,the dilemma of free government.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Rousseau should have started from the view of virtue,criticizing the modern natural rights,but his dogma about the nature and freedom prompted him to take Hobbes' the state of nature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inking,and to choose to establish his own theory on the basis of modern natural science,which means that Rousseau changed his standing from the classic political philosophy to the modern one.Starting from Hobbes' prerequisite,Rousseau completely changed the essential implication of the “state of nature.” This,far from resolving the inherent dilemma of modernity,pushed instead modernity further and further away from rational spirit,hence promoting modernity in a more radical way.
Key Words:political philosophy; modernity; Rousseau; free government; state of nature
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9)01-0154-09
DOI:10.11817/j.issn.1672-3104.2019.01.019
收稿日期:2018-03-06;
修回日期:2018-09-1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美’的政治哲学探源”(16YJC720018);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哲人与智术师”(2016JG009-EZX077)
作者简介:王江涛(1986—),男,重庆人,哲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古典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邮箱:potameus-wang@foxmasl.com
[编辑:游玉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