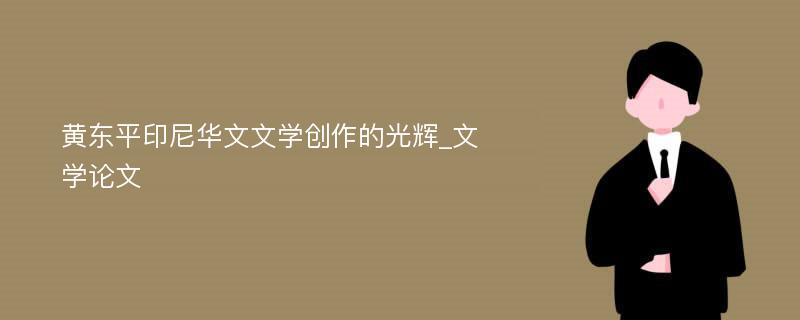
黄东平印尼华文文学创作的异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尼论文,异彩论文,文学创作论文,黄东平论文,华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被誉为印尼华文文坛开荒牛的黄东平在几十年的创作中,能够运用各种文学体裁如小说、诗歌、剧本、散文、杂文甚至寓言和童话表现广阔的社会生活。他的作品是二十世纪海外华侨华人的那些可歌可泣、可惊可叹的事迹的历史记录,也是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侧面写照。
黄东平是一位具有历史使命感的印尼当代华文作家。他坚持创作四十余年,辛勤笔耕了三百多万字,体裁多样,有诗歌、散文、小说、剧本等,他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近一个世纪以来印尼华人的奋斗历史和现状,为海外华文文学塑造了崭新的人物形象和艺术典型,在东南亚华人社会中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他的作品成为东南亚华文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一
黄东平在其文学生涯的初始,就萌发了为千百万海外华侨华人写历史的心愿,并为此做了长期的积累和准备。我们可以这样说,他的小说是二十世纪海外华侨华人的那些可歌可泣、可惊可叹的事迹的历史记录,也是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侧面写照。
长篇巨著《侨歌》三部曲(《七洲洋外》、《赤道线上》、《烈日底下》)正是反映了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间的海内外政治、社会和思想大变动的历史图景。作者站在时代的高度,通过细致地审视华侨社会——居住在坷埠中国人大街上的华侨的命运,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形象地再现了彼时彼地华侨社会的风貌,高度概括了广大华侨当时的生活遭遇和悲惨命运。
在第一部《七洲洋外》中,小说回溯了华侨在故乡时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和摧残的情景,揭露了殖民统治当局对华侨的迫害,倾诉了浪迹天涯的游子“无根”的痛苦和刻骨铭心的乡愁。小说在绘写华侨日益觉醒,互相团结,与国内恶霸势力和荷兰殖民者等邪恶势力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的同时,还热情讴歌了华侨与当地劳动人民和睦亲善同舟共济的感人事迹。第二部《赤道线上》,则反映了在经济“不景气”大难的打击下,华侨生活日趋困难,但由此也促使他们不断觉醒。小说生动地描绘了社会不同阶层,各行各业的华侨民众声援斯达干矿区的华工及当地工人与残酷压榨他们的殖民主义者展开斗争,真实地反映了二十年代末殖民统治者与华工、当地工人尖锐的阶级矛盾,深刻地揭示了反殖斗争的必然性,热情赞扬了华工与当地人民同仇敌忾、团结奋进,最终斗败殖民者的壮举。《烈日底下》则描述了三十年代中后期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入侵以及中国人民的奋起抗战,极大地激发了印尼华侨的民族感情。他们纷纷响应祖国号召,勇敢地冲破殖民政府的种种限制和阻挠,用各种形式和方法,以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支援祖国的神圣抗战事业。小说中强烈的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意识,赋予了小说深刻的思想性。
这部巨著表现了不同时代变迁对华侨华人社会的影响,以及华人华侨在各个历史时期对群岛之国做出的巨大贡献。从中可以窥见昔日成千上万漂洋过海的中国人在海外生活的艰辛历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侨歌》三部曲虽然描绘的是荷印群岛华侨社会的生活图景,但它却是整整几代华侨、华人的一部苦难史、创业史、奋斗史,又是爱国史和友谊史。
黄东平不仅能用小说出色地描绘出印尼华侨华人社会的几个历史阶段的发展面貌,还能用其他艺术形式表现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四幕话剧《红溪》揭露了十八世纪荷兰殖民者为了牟取暴利,对华侨华人进行残酷的镇压,迫使华人与同样受殖民压榨的当地劳苦人相约起义,最后华侨被杀一万多人,血染红溪,造成了惊震世界的“红溪惨案”。电影文学剧本《老华工》则写了华工们在苦难生活和斗争中逐步觉醒,从个人奋斗走上团结奋斗,从自发斗争到自觉斗争并最终赢得抗争胜利的坎坷历程,再现了中国人在海外团结当地人与殖民者抗争这一重要历史事实,揭示出殖民者对华人和当地人实行“分而治之”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
二
黄东平文学创作的异彩还在于塑造了华侨华人社会形形色色的艺术形象。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几乎囊括了华侨华人社会在内的整个南洋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和各行各业的各色人等,有华商、店员、苦力、矿工、小摊贩、教师、学生、社会青年和侨生,侨生中又有中国化、西化和当地化的人物;同时又有从贵族,回教士直到穷苦村民的各类型当地居民;有从大官员、洋行经理直到监工的殖民者和各种洋人;还有海内外的进步人士和恶霸反动势力以及其他国侨民等等。他出色地塑造了系列反映不同社会时期生活实况的人物形象。如华商人物李熙昌(《侨歌》)、陈子轲(《老头家》)、阿开福(《大家的一天》)、林鼎盛(《华人世界》)等,知识分子徐群、卢健中(《侨歌》)、萧长鸣(《一位教师的遭遇》),劳工大众吴阿贵、张亚枚(《侨歌》)、丘振祥(《海外这一家》)、亚畴伯(《在椰城“甘榜”里》),小职员傅有财(《华人世界》),以及当地人细蒂(《女佣细蒂》)等。在刻画这些人物形象时,作者不仅善于抓住人物的某些突出特点并借此揭示同一群人共同的属性,而且还从特有的南洋生活出发,对自己描写的对象进行艺术概括,着力刻画人物性格,使人物形象既有鲜明性又有一定的典型性。因此这众多身世地位不同,神情秉性迥异的人物都在作者的笔下以其鲜明独特的形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海外华文文学特别是东南亚华文文学的人物形象画廊里增添了不少新的色彩。
艺术形象的典型化是黄东平小说的一个特色。《侨歌》三部曲中的华商李熙昌、丘联福、李德财、黄世铎、郑水源等,在他们身上既有同一群人的共性又有各自的特性。而“福昌”号的李熙昌则是这些华商头家中的一个典型人物。他是坷埠“中国人大街上”一家土产店的头家。“打杂倒痰盂出身的”,好不容易当上了“头家”。由于徐群的请求和为了顾面子,熙昌为阿贵付了“按地金”并收容了阿贵。这事使李熙昌不仅赢得了乐善好施的美誉,也得到了免费的劳力。在李熙昌看来,他对阿贵是“大恩大福”,对阿贵来说,却无法给唐山亲人任何帮助,因而终日受着自责自疚的折磨。李熙昌虽然对华侨社会的公益事物总是都么热心并因此获得了众所公认的好名声,但每次捐钱赠物之前总又免不了仔细地盘算一番;他对众人及伙计是那样的专横不可违逆,而面对荷兰大狗的敲榨勒索又是那样的忍气吞声、可怜巴巴。于此人们也许可见华商头家李熙昌的一些性格特性。尽管这样,他也和其他大小头家们一样,受殖民统治的压迫和打击,因此,他们有着共同的命运,一样的斗争目标。比如集资兴学,组织中华会馆与侨众一起抗击殖民者,同情和支持穷苦的华工和侨众,与市民互济互助共渡经济危机的难关……
作者在塑造李熙昌这一典型人物时,紧紧抓住他是一个“商人”的性格特征,不但通过他的一言一行表现他的“做什么”,而且将艺术的笔触伸入人物的心灵深处,揭示出他“如何做”的心理奥秘,多层次多角度地描画出商人复杂多变的性格。这个典型人物的意义不仅反映了荷殖时代南洋华商的命运,而且也可以说是当时华侨华人社会中小商业者的事实写照。
把人物放在具有历史特色的具体环境中加以表现是黄东平创作上又一特色。《侨歌》三部曲中的徐群是侨众出资从国内聘来的新教师,作为一名有进步倾向的青年知识分子,他给坷埠的华侨华人社会带来了新思想。他一到坷埠任教的学校,就大胆进行教学改革,改变了落后而死气沉沉的“中华学校”的局面,给华侨社会投下了兴奋剂,在与出卖同胞的恶势力发生激烈斗争时,他得到了进步的知识分子侨领卢健中及其父卢老先生的大力鼎助,使华侨在事实的教育下,更加团结进步,办好教育,关心祖国,团结御侮,维护合理权益和民族尊严,反抗殖民压迫。老年人开通了,穷苦人觉醒了,年轻人成长了,坷埠的华侨社会由此开创了新的一页。人物的活动或直接或曲折地体现了现实发展的趋向。徐群的生活道路就鲜明地反映出时代斗争对他的巨大影响,也表明了他的活动对于改造社会环境的积极作用。他代表着生活进程中的主导力量,是海外先进知识分子与侨众结合并做出贡献的典型。
三
黄东平的文学创作又一特色是在题材的选择、文学体裁的运用以及语言风格等方面都有独到之处,表明他对东南亚华文文学作出的重要贡献。
首先,创作题材富有地域性。黄东平的代表作《侨歌》三部曲是以反映荷印时代的华侨生活为题材的。他说:“《侨歌》中的大部分素材,是我自己发掘的,书中的许多生活、人物、情节,还是第一次出现在文艺作品上的”。它的篇幅和其所反映的历史面貌比其他同类题材的作品更为广阔,这一成就不但成为黄东平在题材开掘上的一个独特贡献,也使他的小说在同类题材的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因而被誉为是一部“现代南洋华侨社会的生活民情、风俗习惯,社会风貌,言语社交的百科全书”。
中短篇小说集《远离故国的人们》、《头家——估俚》,在写作题材方面又有了新的拓展。它多侧面、多角度地反映了印尼华人社会生活各个侧面的世态人情的真实状况及其随着时代风云变幻所产生的深刻变迁。
善于开拓、发掘题材,必然形成了题材的广泛性。而题材的多样化,也必然导致了多种多样的体裁和独特的艺术特色。被誉为印尼华文文坛开荒牛的黄东平在几十年的创作中,能够运用各种文学体裁如小说、诗歌、剧本、散文、杂文甚至寓言和童话表现广阔的社会生活。
在长篇小说的写作形式上,黄东平有着与众不同之处。从《侨歌》三部曲的创作上就可以看出。他在《我与侨歌》中曾经说过:其一,不准备象某些名著以一家庭为中心来写,他要更广泛地反映华人社会生活,各角色都在作品里承担一定的使命,所以,这部巨著在反映社会生活之宽广,规模之宏大,结构之复杂,描写人物手法上多样化等方面表明了作者对长篇小说表现样式上所做的新探索。
在中短篇小说的表现形式上,黄东平近年来的作品也有引人注目的变化。在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法上,作者也敢于放手从各个方面,调动多种艺术手段精细入微地刻画与描写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如《嫁后》在刻画人物时就采用了朴实的白描手法,让人物在重要的事件中自己去行动,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其性格的发展,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有女初长成》则溶入了西方小说刻画人物心理的手法,深入人物的灵魂,使人物更富于立体感。
从运用散文这种文学体裁上来看,黄东平也有独到之处。他注意将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命运、思想感情,与他们的生存状态和所处的具体环境紧密联系起来,展示出丰富的思想容量。如《短稿一集》中的《闽南家乡琐记》、《格蔺旅社留记》、《忆母亲》等篇。其次,作者善于通过描写日常生活小事,以人们司空见惯的事实作比方,把人们内在的精神状态形象地突出出来,用以小见大、借此喻彼的手法,从小题材中发掘出事物的深刻内涵。比如用谈吃饭(《奇癖怪行与吃饭》)、讲青春(《身外的青春》)、叙述街边事(《街边所见》)等来探索人生意义和生命价值,表明了作者鲜明的爱憎,歌颂了真善美,鞭挞了假丑恶,充满了人生哲理,做到了一事一议,多姿多彩,有感而发,多层次多方位地呈现了印尼各种行业的风采和世态人情。
黄东平的作品不仅以平易朴素的语言,表现生活情趣,写活人物,而且善于用舒缓的语调,不动声色地在描述了生活中琐细的人物时,把对人物的褒贬和价值判断,深藏在形象背后。此外,作品中还运用了有助于刻画人物形象和渲染气氛的方言,像“头家”“大狗厝”“公班衙”等,以及当地生活特色的语言:“浪帮”、“山顶客”、“甘榜”、“峇务”、“沙笼”等,这使得黄东平的作品既不同于中国国内的语言风格,也有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华文的风格,而是富有浓厚的南洋社会色彩和生活气息。不过,作者在章节过渡上有时过多依靠关联词语承前启后,显得不够圆熟自如。总之,黄东平在题材选择,人物艺术形象塑造以及文学语言特色等方面,都为东南亚华文文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这些成就的取得与作家坚持正确的创作方向,且长期生活在海外而又勤奋学习、多方采集资料、严谨创作分不开。正如有人所说:“方北方(马来西亚)、黄东平两位生活在本地区的作家,其作品中具有的乡土、民族色彩,是作品落实在当下时空的直接产物。”“他们的业绩与事功,是一个富有使命感的作家对时代的具体交代,成就令人刮目,勇气更使人钦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