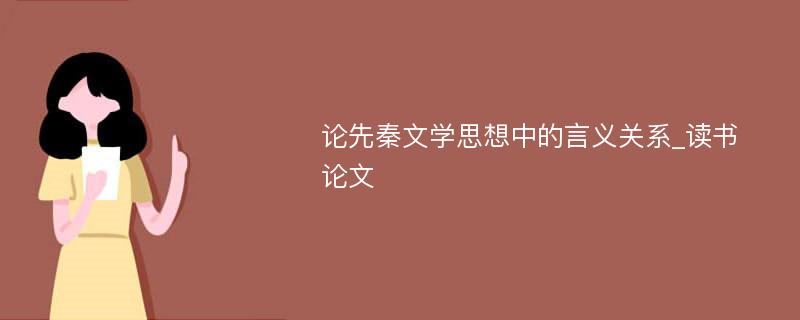
先秦文学思想中的言意关系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秦论文,思想论文,关系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03)04-0014-06
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发轫期,各种典籍对文学思想中的言意关系之认识表现出纷乱复杂的特点,在对待言意关系上各有所云,有的主张言达意,有的主张言不尽意,有的主张得意忘言,有的杂而取之,合而论之。因此,疏理先秦文学思想中的言意关系,找到某些带普遍性和规律性的认识,对于我们研究先秦文学和先秦文学思想,颇有启发。
《尚书》为儒家经典,其《旅獒》云:
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不作无益害有益,乃功成。此为儒家于言意关系中较早之涉及言达意者,“言以道接”,不为有害,功利之目的明矣。而在《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中,记载了孔子关于言达意的最肯定的表述:
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
夫子引经据典,振振有辞,故其弟子在追述其此类言行时,亦如实语录。《论语·卫灵公》云:“子曰,辞达而已矣。”《正义》云:“辞皆言事,而事自有实,不烦文艳以过其实。”可见,语言必须如实表现事意,而且在达意时,必须恰如其分,若名与实必须相符,故《论语·子路》云:
子曰:“必也正名乎?……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什么样的语言表达什么样的事意,反过来,什么样的事意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于人也亦然。故《论语·尧曰》云:“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卫灵公》又云:“巧言乱德。”《宪问》亦云:“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此一点在后来的《易传》、《孟子》中亦有所承,容后述。
明了的事意,能用语言清晰明白地表达出来,如其深奥幽隐之事意何?故儒家又主言不尽意,《论语·阳货》有云:
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天是那么高远,语言怎能穷尽?故子贡对此深有感悟,慨而为言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论语·述而》又云: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为什么“志于道”?盖道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只能心领神会之,故郑玄注云:“志,慕也,道不可体,故志之而已。”正始玄学家王弼倡得意忘言,修本废言,实源于此(他的另一个源头是《易》、《老》、《庄》)。天难言,仁亦难言,故《论语·颜渊》云: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琤。……为之难,言之得无琤乎?”
诸如此类言不尽意之语,在夫子那里随处可见,此不一一征引。
要之,夫子的言尽意,言不尽意皆着眼于现实事理、仁义道德,其政教目的论显明有加,不带任何艺术之色彩。
言与意之关系,犹表与里、华与实,表里必一,华实必符,故《国语》对《论语》的正名实又继承之(《国语》、《论语》均成书于战国初年,太史公谓左丘明小于孔子,与孔子弟子同时,则其《国语》当有承《论语》处,或有与《论语》不谋而合处),其《晋语五》云:
夫貌,情之华也。言,貌之机也。身为情,成于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发之,合而后行,离则有衅。
如上所述,夫子认为语言有难于尽意的局限,所以不得已,只好心领之、神会之;语言的蹩脚,有时会让人有强词夺理之嫌,故夫子感叹,尧的“巍巍乎”、“荡荡乎”使“民无能名焉”,夫子也只好强其名曰“大哉”、“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尧则天,夫子则谁?则老子。太史公云夫子曾问礼于老聃,师事老子,就把这一套“强字之”、“强名之”之法也学了过来。《老子·一章》云: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又《二十五章》云: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在老子看来,语言表达宇宙本体这个深奥的道是力不从心的,不但如此,对于探索了道的奥妙的人的形象也是难于描绘的,这就开始进入对艺术的把握了,故《老子·十五章》有云:
古之善为士者,微妙元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焉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严兮其若容,涣兮若冰之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
用艺术的方法描绘形象,此形象必臻于一种境界,而老子主张自然之境为最高之境,达到此境界则为圣人,那么圣人怎样处理言与意之关系?故《老子·五十六章》有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又《八十一章》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又《二章》云:“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要之,老子认为言不尽意,唯不尽意,故由之自然,不事夸饰广辩,此为高境。这又直接影响庄周、王弼关于言意关系之论述,而其艺术之色彩显明地浓厚了。
降及墨子,墨家尚质,主张节俭,故在言意关系上倡明辞达意,《墨子·说经上》云:“执所言而意得见,心之辩也。”又《墨子·小取》云:
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慕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
言意之论,在《管子》书里来了一次小的总结,把儒道之说、孔老之论合而述之,这与它的杂家(杂取众家)思想是分不开的,故一则曰言必准确地表达事务,必合于理义,故《法法》云:
是故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国。……故言有辨而非务者,行有难而非善者。故言必中务,不苟为辩;行必思善,不苟为难。
又《心术上》云:“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当谓之圣人。”又《戒》云:“多言而不当,不如其寡也”又《形势解》云:
人主出言不逆于民心,不悖于理义,其所言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复言也。出言而离父子之亲,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众,此言之不可复者也,故明主不言也。故曰言而不可复者也,君不言也。
可见,儒家的政教功利色彩是较浓的。
再则曰言难于穷尽道理,有些道理隐微深邃,多言不如寡言,寡言不如不言,不言者,意会也。故《心术上》云:
大道可安而不可说,真人之言,不义不顾,不出于口,不见于色。……故必知不言之言,无为之事,然后知道之纪。
道也者,动不见其形,施不见其德,万物皆以得,然莫知其极。故曰:“可以安而不可以说”也。真人,言至也;不宜,言应也,非吾所设,故能无宜也。不顾,言因也。因也者,非吾所顾,故无顾也。不出于口,不见于色,言无形也。四海之人,孰知其则,言深囿也。
这里已是融孔老言意之说为一体了,至于“大道可安而不可说”则直通庄周的“得意而忘言”。不仅如此,而且由于《管子》认识到语言是不可能涵盖万物的,所以第一次明确地提出“计意”,故《宙合》又云:“是故辩于一言,察于一治(一说辞),攻于一事者,可以曲说,而不可以广举。圣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博之治(辞)而计其意;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名为之说,而况其功。”
《管子》言意之论作为对孔老言意之说的一个总结,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者探讨了创作中的构思问题,认为先虚静,然后才知道“不言之言”,才能体会个中深意,然后借助于语言把这个“意”表现出来,故《心术下》云:
外敬而内静者,必反其性。……意以先言,意然后形,形然后思,思然后知。
这显然也是受老子的“致虚极,守静笃”(《十六章》)的影响,或许还影响着庄周的“心斋”与“坐忘”。
历史的发展及于商鞅时代,法律的制订、实施越来越提倡议事日程,因此,语言必须毫不含糊地表达法律之意,不能留下艺术般的想像空间和因人而异的主观意会,故《商君书·定分》有云:
夫微妙意志之言,上知之所难也。夫不待法令绳墨,而无不正者,千万之一也。故圣人以千万治天下。故夫知者而后能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知。贤者而后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贤。故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遍能知之;为置法官,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令万民无陷于险危。故圣人立天下而无刑死者,非不刑杀也,行法令,明白易知,为置法官吏为之师,以道之知,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
战国中期,儒墨成为显学,百家局面已然形成,饰言辩辞,是非迷惑,立己排他均需从言辞入手,故孟轲云“我知言”,《系辞》曰“叛辞渐”,庄周说“不谴是非”(实则谴是非,一部《庄子》皆“正言若反”)。然对言意关系之认识,三者又各有侧重,下面分述之。
孟轲为人为学,一贯着眼于现实,立足于社会,在对待言意关系上也从现实之目的出发,要求辞达意,言尽意,所谓“言无实不祥”(《离娄下》),因此,他对什么样的语言体现了什么样的旨意了如指掌,故《公孙丑上》有云:
“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何谓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谄,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在孟轲看来,言辞除了达意,还要于政于事有用。但孟轲也认识到语言在达意上有所局限,所以他一则认为“浩然正气”是“难言”的,这与夫子在说“天”上同;再则曰“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万章上》);三则曰“言近而旨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尽心下》)——用浅近的语言表达深远的意旨,做到语约而意丰。
成于战国中后期的《系辞》,亦是从儒家政教功利的角度来看待言意之关系,强调言辞必须准确地反映事意,通过知言以知人,故《系辞下》云:
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辨物而言,则断辞备矣。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因贰以济民行,以明失得之极。
又云:
将叛者其辞渐,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
上所引第二条,仿佛是孟轲“我知言”的翻版。
但是,也象此前的儒家人物孔孟一样,《系辞》的作者也同样发现了语言达意的有限性,只是他在对待这种局限性时不象圣人那样隐约其辞,而是公开明确予以肯定和承认,故《系辞上》有云: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这几乎是言不尽意论之宣言书,王弼以老庄解《易》,把言不尽意视为体认玄学本体的方法,在更高更抽象的层面上看待言意关系,得出得意忘言的观点,就是很好地读懂了这本宣言书,以致玄学在我国哲学史、文学史上均影响深远。
自从言不尽意论在《系辞》里以命题的形式坦明于世以后,我们虽没有证据说明庄周曾受这个命题的影响,但毋庸置疑,他是言不尽意论之集大成者。一则因为他的言不尽意论有一种独特的表达形式——寄寓之言;二则因为他的言不尽意论已飞跃成为一种对艺术的忘我境界之追求的创作理论,发展了老子的艺术表现与要求,而不只是拘泥于现象世界的只要意会不可言传,如孔子之言“天”,孟子之言“气”,《系辞》之言“爻”与“象”。下面我们征引《庄子》有关材料来证明之。
首先,庄周象所有其他熟悉语言特质的人一样,指出语言是有局限性的,特别是书面语言,“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天道》),所以在《知北游》里有一个“知问道”的寓言,庄周假托黄帝之口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同篇又借无始之口说:“道不可言,言而非也。”象孔孟一样,庄周还发现现象世界中深层次范围中的问题也是无法用语言和人的知识来确定的,因此只好存而不议,故《庄子·则阳》有云:
太公调曰:“阴阳相照,相盖相治。四时相代,相生相杀。……言之所尽,知之所至,极物而已。睹道之人,不随其所废,不原其所起。此议之所止。”……太公调曰:“鸡鸣狗吠,是人之所知。虽有大知,不能以言读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将为。斯而析之,精至于无伦,大至于不可围,或之使,莫之为,未免于物而终以为过。或使则实,莫为则虚。有名有实,是物之居;无名无实,在物之虚。可言可意,言而愈疏。……吾观之本,其往无穷。吾求之末,其来无止。无穷无止,言之无也。与物同理,或使莫为。言之本也,与物终始,道不可有,有不可无;道之为名,所假而行。或使莫为,在物一曲。夫胡为于大方?言而足则终日言而尽道,言而不足则终日言而尽物。道物之极,言默不足以载。非言非默,议有所极。”
又《齐物论》有云:“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辩也者,有不辩也。”为什么存而不议(“议之所止”)?有两个理由可以解释,一则如上所述“道物之极,言默不足以载”;二则如陈鼓应先生所云:“语言文字还常常藏着使用者的心机”,人们常有主观之偏见,“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齐物论》),故庄子反对人有这种偏见,而主张“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追求无言之美:“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知北游》),追求“大辩不言”(《齐物论》)和“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同上),“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谓天府。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来,此之谓葆光”(同上),达到一种“葆光”状态。
其次,庄周为那些能用语言表达和只可意会的东西分类:“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以不能论,意之所不能致者,不期精粗焉。”(《秋水》)于是庄周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结论:“(孔)丘所治之《诗》、《书》、《礼》、《乐》、《易》、《春秋》,皆先王之陈迹也(《天运》)”;桓公所读之书,皆古人之糟粕也:
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矣。”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天道》)
这个结论的另一种表述方式是“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天道》)
既然言不足贵,而人又不能离开言辞,包括庄周自己,最后庄周找到了解决语言局限即言意矛盾的办法,故《外物》有云:
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
这里的得意忘言,是要求我们在语言文字之外去寻找丰富的意蕴。当然做到这一步,需要有丰富的想像和联想,文学艺术创作便是这种实践。由于艺术形象的内涵超越语言的内涵,因此艺术家、文学家必须把握言外之意,象外之象,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要到言辞之外去追求,到自然之道上去寻找,任其自然就能领会其意。找到了这种言外之意,就是出入于忘我之境地,这就为后来意境说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老子的不言之言,只是处理言意矛盾的一种简单回避,尽管他也要求达到自然,但没有向更高的阶段超越,庄周的得意忘言,既作为一种解决言意矛盾的方法,更作为一种最高艺术境界的追求,甚至成为后来玄学家融合儒道体认本体的认识方法,王弼的得意忘象,得象忘言即本于此。由此观之,庄周的言意之论意义非常重大。
时及荀卿,儒法双遣,正名定分,脉承夫子,用辞造句,言以达意。他首先为言意关系正名,故《荀子·正名》有云:
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
名正了,则言顺了,于是有“君子之言”和“愚者之言”,故《正名》又云:
君子之言,涉然而精,俛然而类,差差然而齐。彼正其名,当其辞,以务白其志义者也。
愚者之言,芴然而粗,啧然而不类,誻然而沸。彼诱其名,眩其辞,而无深于其志义者也。
但不管什么“言”,都要达意而后止,故《正名》又云:
实不喻然后命,命不喻然后期,期不喻然后说,说不喻然后辨。
然言达何意?无疑是达仁义礼法之意,这是言所追求的最高准的,故《荀子·非相》有云:
故君子之于言也,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言而非仁义中也,则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辨不若其讷也。言而仁之中也,则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矣。故仁言大矣。
所以,“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同上),因为言有以风化也,有以助道德施礼义也,言意关系在这里再一次归宿于政教功利。故《非相》又云:“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虽辨,君子不听。”但是,值得肯定的是,荀子第一次较好地在逻辑思维上处理了主观思维、客观事理、语言文辞三者之间的关系,这是他对形名学的一个总结性贡献,其《正名》有云:
辨说也者,心之象道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之经理也。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正名而期,质请而喻,辩异而不过,推类而不悖,听则合文,辨则尽故。以正道而辨奸,犹引绳以持曲直,是故邪说不能乱,百家无所窜。
在这里,“心”是主观思维,“道”是客观事理,“说”是语言文辞,其关系是主观反映客观,语言表达这种主观对客观的反映。
《晏子春秋》在言意关系上大致属于墨子一派,反对辩言巧辞,“君无以靡曼辩辞定其行,无以毁誉非议定其身”(《内篇问上》),提倡辞以达意,“言不中不言”(同上),显然受墨子“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非命上》)的影响。另外,《晏子》也从个人道德规范上来约束人的言辞,“所言不义,不敢以要君,……所言无不义,故下无伪上之报”(《内篇·问上》。
韩非属于法家一派,在言意关系上,一如商君那样要求简约严明,体现了法家峻刻的风格特质。其《八说》有云:
书约而弟子辩,法省而民讼简。是以圣人之书必著论,明主之法必详事。尽思虑,揣得失,智者之所难也;无思无虑,挈前言而责后功,愚者之所易也。明主虑愚者之所易,以责智者之所难,故智虑力劳不用而国治也。
他反对儒家的微言大义,主张明白晓畅,言必尽意,故《忠孝》云:“恍惚,无法之言也。”又《五蠹》云:
且世之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民无从识之矣。故糟糠不饱者不务梁内,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今所治之政,民问之事,夫妇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智之论,则其于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务也。
用妇孺皆懂的言辞把政事表现出来,是由于韩子充分相信语言的表达功能,故《说难》有云:
凡说之难,非吾知有以说之难也,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佚而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
在韩子那里,语言毫不蹩脚,没有任何局限,说之难,难就难在所说之心,以他的才华,“臣(自指)非难言也”(《难言》),因此,对于孔老的“强字之曰‘道’”,他是毫不苟同的,故《解老》云:“而常者,无攸易,无定理。无定理,非在于常所,是以不可道也。圣人观其玄虚,用其周行,强字之曰‘道’,然而可论。故曰:‘道之可道,非常道也’。”
有趣的是,作为先秦又一部杂家思想代表著作的《吕氏春秋》,在言意关系上也与《管子》一样把儒道之论合而述之,即把儒家的政教功利色彩和道家的艺术表现色彩结合起来,一方面强调言要达理(即辞达意),另一方面主张得意忘言。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不韦首先强调“言尽理”(辞达意),故《吕氏春秋·开春论》有云:
开春始雷,则蛰虫动矣。善说者亦然,言尽理而得失利害定矣。
“得失利害”,儒家的功利目的是很显明的。
既明了“言尽理”,那么怎样的语言才能尽理?故不韦主张“直言”和“极言”,因为它们能把臣忠于君的愿望尽情表达,故《贵直》篇云:
贤主所贵莫如士。所以贵士,为其直言
也。言直则枉得见矣。
又《直谏篇》云:
言极则怒,怒则说者危。非贤者孰肯犯危,而非贤者也,将以要利矣。要利之人犯危何益,故不屑主无贤者,无贤则不闻极言,不闻极言则奸人比周,百邪息起,若此则无以存矣。
“直言”、“极言”都能表达言者之意,这“意”小则“要利”,大则忠于人君,故言与意是不能相悖的,否则,祸莫大焉,故《离谓篇》云:
言者以谕意也,言意相离,凶也。乱国之俗,甚多流言,而不顾其实。务以相毁,毁誉成党,众口熏天,贤不屑不分。以此治国,贤主犹惑之也,又况乎不屑者乎?
言与意既不能相违背,言与行又何能相违背?故《淫辞篇》云:
非辞无以相期,徒辞别乱。辞之中又有辞焉,心之谓也,言不欺心,则近之矣。凡言者,以喻心也,言心相离,而上无以参之,则下多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诡,不祥莫大焉。
这“不祥莫大焉”与孟轲说的“言无实不祥”又有何异呢?
再看第二个方面。言与意之关系既是那么相依为命,那么可以通过把握其中一端就能通向另一端,因此,不韦提出“以言观意”,故《本味篇》有云:
凡贤人之德,有以知之也。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非独琴若此也,贤者亦然。
通过高山流水之音来观鼓琴者之意,目的是要说明“以言观意”,故《离谓篇》有云:
夫辞者意之表也。鉴其表而弃其意,悖。故古之人,得其意则舍其言矣,听言者以言观意也。听言而意不可知,其与桥言无择。
听懂了言外之意,正象听出了弦外之音一样,谁还拘泥于言与弦呢?故得意以忘言了,因此不韦的言意关系论,又通向了道家庄周的艺术一派。
要之,先秦时期言意关系的发展,到《吕氏春秋》之撰成,呈现出道家重艺术表现、艺术追求之倾向,儒家、墨家、法家等表现出重政教事功的趋势,而杂家则兼而合之,而且出现了两次儒道合流、功利与艺术合论的现象,第一次是在《管子》书里,第二次是在《吕氏春秋》书里。
[收稿日期]2002-1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