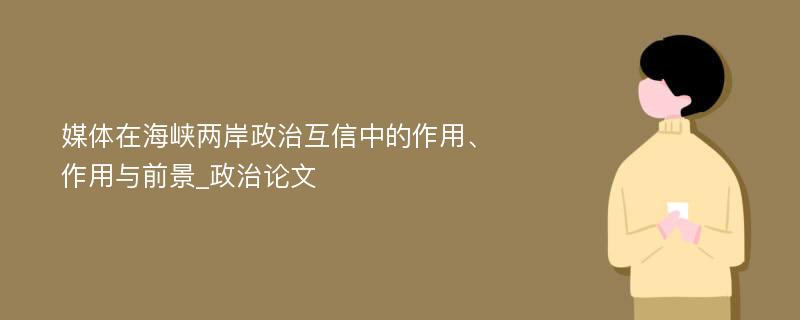
两岸政治互信中的传媒角色、功能及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岸论文,前景论文,角色论文,政治论文,传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D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4)05-0064-11 “两岸的根本问题是政治问题。”①这种双方一致的共识使得两岸之间的交流必然最终以政治考量为依归。在此观念指导下,两岸传媒的互动总是不可避免地被打上政治烙印,传媒本身的多重属性反而遭受遮蔽。于是,在两岸政治互信研究中,“传媒”究竟是什么?“传媒”发挥着正向功能还是反向功能,这些似乎都成了不是问题的问题。 两岸政治互信进程是基于两岸关系共同的开放系统,又受两岸社会结构彼此独立的子系统的制约。若依照尼可拉斯·鲁曼系统传播的观点,系统并非由身处其中的个体行动构成,而是由“传播”(communication)构成,并且“唯有在‘连锁的传播’中不断地实现自我维持”。②鲁曼所言的传播虽意指“世上人与人之间的全部‘交往’行为”,③但在两岸特殊地缘隔绝与社会距离的事实下,两岸相互认知的“传播”体系又显然以传媒为中心。两岸政治互信是两岸博弈过程中一种社会建构的现实,④在学界共识之内,人们认知与理解世界的“想象”,则在相当程度上由大众传播媒介所建构。⑤或许正是过度关注于传媒设置议程(agenda setting)与建构议程(agenda building)的力量,在讨论两岸关系中传媒所扮演角色之时,政治导向始终是驱之不散的魅影。因此,历来两岸传媒的研究,集中于两个面向:其一,热衷于框架与文本解读,进而透视对方“如何看待我们”,折射出何种政治观念;其二,关注于传媒如何输出观念,建构符合政治需求的“真实”,却不论这种真实传播的有效性。这种以“观念”为核心的传播,犹如鲁曼所诟病的,使得“在传者与受者之间,缺乏一种共时性(co-present)的互动”。⑥传播对象始终被陷于带有绝对目的的考量。传媒在两岸交往中有何角色归属,建构着何种功能,此一问题实际上被有意无意地简单化了。 巩固两岸政治互信,需要以增进政治认同为基础,重构新的政治认同对象。⑦有如福柯所言,“对象存在于某个关系的复杂网络的积极条件中。”“这些关系建立在机制、经济和社会过程、行为的形式、标准的体系、技术、分类的类型和特征化的方式之间。”⑧两岸视域之下的传媒,实际有着颇为复杂的面向:其既是政治宣传机器的一部分,又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独立存在;既是双方彼此社会结构与体制制度的“代言人”,又是执政当局与两岸政治精英的“扩音器”,更在民间情感往来上承担着纽带作用。换而言之,两岸政治互信进程中的传媒并非局限于政治认同声音的“传送带”,其功能体现在从官方意图到民间声音,从政治空间到经济结构,从内容观念到技术实践领域的全方位交往。在新时期两岸交往与政治互信进程之中,我们亟待更清晰地认识传媒在这种结构互动之中所扮演的角色,分析其在不同面向所呈现功能的有效性与有限性,进而探讨当前两岸政治互信如何脱离传统的宣传导向语境,走上一条更为实用、更具传播效力的道路。 一、传媒应在两岸文化心理机制下建构台海政治互信 自近代西方选举制度与公关政治兴起,传媒便作为影响政治信任的工具广为运用。 在通常意义上,政治信任(political trust)是公民心理层面的某种信心状态,取决于政府或政治系统是否能够产生与公民期望相一致的结果。⑨“政治互信”则脱离出单一政治系统内部,指涉的是一种双边关系或多边关系,即国家、地区等政治主体之间的信任状况。就两岸政治互信而言,实际既包含了两岸执政当局之间在两岸基本的、原则性的政治立场的共同点、共同基础与共同的政治追求,又涉及两岸之间政党、意见领袖、政治社会团体、民众等主体之间的沟通。⑩但总体而言,政治互信与政治信任,皆指涉一种心理秩序。正是由于这种心理意志的复杂特质,两岸政治互信的表现形式可由口头、书面甚至于行为默契的方式呈现,(11)都难有统一尺度。 政治互信既然涉及“心理”状态,自然与个体的认知与理解行为息息相关。依据文化理论,信任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形式密不可分。自出生以后,个体就必须通过体验与他者如何在文化中相处、互动,学习信任或者不信任他人。(12)换言之,信任感的产生来自于社会学习过程。尽管按照惯例论(Institutional theories)的观点,政治信任或不信任乃是对制度行为的一种理性反应,(13)其将政治信任视为对客观存在的能动反馈,但亦无法否认,人们关于对象的政治信任可因公众关于制度“想象”的变化而改变。 Fukuyama指出,虽然人际交往是形塑社会信任的普遍形式,但由于更大范围内的非人际的、制度层面的信任,通常超越了文化范畴,这使得日常互动的“信任半径”(radius of trust)较为有限。(14)由是,在现代社会,传媒接过了人际传播的“接力棒”,在人们建构关于政治生活图景的社会认知之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对于政治互信对象交往双方而言,传媒所输出的话语不仅影响着对方关于自己的想象,同时也影响着自身系统内部对对方的评价。Gamson与Stuart便曾通过对冷战时期传媒内容中的政治卡通进行分析,认为在美苏政治互信关系之中,传媒话语承担着一定责任。大众媒体不仅作用于公众对政治意义的理解,同时反映出赞助人(sponsors)之间的符号对抗与场域竞争。(15) 作为一种特别的话语形式,媒介新闻乃是通过文本结构,来“实现意识形态在社会实践、新闻事件的解释”。(16)通过再现与“赋魅”,传媒影响着受众的认识结构与理解方式。如布尔迪厄所言,“符号系统不仅仅是知识的工具,还是支配的工具。作为认知整合的工作者,它们根据其自身的逻辑推动了那种对任意武断的秩序的社会整合。”(17)不过,在两岸关系中,整合两岸政治互信的传媒究竟是什么,仅仅是符号、文本、技术,还是其他?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关注的似乎仍是传媒在两岸空间中所传递的传播内容。或是类似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观点所声明,内容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技术的媒介本身。(18)麦氏的观点此处我们不作争论,但它至少证明,传媒本身拥有着较为复杂的属性。不同视角下的传媒,其功能认知亦大相径庭。在两岸关系中,虽已存在这样一种共识,即“传媒在促进两岸政党交流与沟通中,发挥着促进相互认知、培育情感认同、弥合政治分歧以及提供于舆论支持的作用”。(19)但两岸视域下的“传媒”概念为何,在政治互信进程中的传媒究竟是怎样的“传媒”,如果不能解构传媒在两岸文化心理机制下呈现的多重特征,我们也就无法得到一个“整体”的两岸传媒。 二、两岸传媒的功能变迁:从“政府”的传媒到“两岸”的传媒 自1949年祖国大陆与台湾相离,双方传媒交往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皆基于“政府”行为,即传媒完全受执政当局所主导,为对台或对陆方针所服务。这种“政府”的传媒又依据历史时段之不同,呈现出两种状态: 一是基本成为政治方针的“传布者”。这一阶段集中于1949年至20世纪80年代,强烈的政治意志浸淫其中,传媒的声明作用要远大于“沟通”功能。早在1949年3月15日,新华社便发表评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响应当时新中国成立前“解放台湾”的战略部署。此后,在新中国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战略转变以及两岸之间军事对抗与缓和中,传媒声音都扮演着先锋角色。同一时期的台湾岛内,自1949年实施全面戒严开始,政治体系内的言论思想便受严厉控制。通过建立“党国一体”的威权体制,国民党掌握着一批党营和军方媒体,同时通过政治拉拢与经济保护,将主流媒体作为政权侍从。(20)传媒亦成为国民党试图“反攻大陆”的重要动员工具。据1967年《联合报》报道,蒋介石便有“指定金、马、台、澎各电台与联络站,随时和大家保持联络,并命令敌后工作人员、秘密武装,尽一切可能,和反毛的军民力量,主动地保持联络接洽”。(21)可见,在这一时期,传媒乃双方政治军事对话的“传声筒”,传媒声音直接投影的便是政府双边的意图。追溯其缘由,固然与政治管控下的传媒体制密不可分,但核心仍在于,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祖国大陆与台湾存在迥异于当前的结构关系,即“本来在国家统一历史进程中,只有台湾问题,只有台湾问题的和平与非和平统一问题,不存在两岸关系发展问题”。(22)传媒于是亦与时代之社会意识一脉相承,受政府操控来解决内战遗留问题。 二是转向一种广泛意义而言的“宣传工作”。改革开放伊始,祖国大陆对台方针政策发生重大转变。1979年,《人民日报》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试图以“真诚的态度”赢取政治信任。(23)传媒虽依然附庸于政府意志,但内容与策略逐渐开始发生转型:即由之前反映政治、军事国家方针政策与态度为主,转向“通过各种渠道和多种形式,宣传我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和对内对外政策,全面介绍祖国大陆的形式和成就,以增进台湾同胞对祖国大陆的了解和对祖国的认同感、向心力,进而提高他们的爱国主义热情,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事业的发展”,(24)其内涵实际已经发生多元化转型。换言之,传媒由单一的政治主导话语进入到新的以“促统”为内在动机的符号话语生产过程。而在台湾岛内,随着国民党“反攻大陆”的破产以及民粹主义进入传媒领域视野,传媒业开始受政治与商业双重力量结合所牵制。(25)这亦决定了之前作为对陆反攻宣传机器的传媒,其社会基础不复存在。 伴随两岸政治对话“融冰”,双方在传媒领域亦开始拓展新的可能边界。1988—1989年后,台湾先后制定《沦陷区出版品、电影片、广播电视节目进入本国自由地区管理要点》《现阶段大众传播事业赴大陆地区采访、拍片、制作节目报备作业规定》,至2011年,新闻局废止《申请出版沦陷区出版品审查要点》,两岸传媒业交往已经逐渐步入新的格局。主要包括下述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由传统政治意志主导的传媒开始呈现商业转型。两岸传媒体制固然存在巨大差异,其中最大焦点是在经营管理者层面,台湾多以公司制出现,大陆媒体则多受政府管理。但自90年代以来,以集团化为先导的大陆传媒业改革依然急剧推动着两岸传媒业之间的业务实践,为双方求同存异提供了有利条件。以出版领域为例,祖国大陆向台湾地区图书版权输出已由2004年的655种升至2012年1781种,台湾对大陆图书版权输出则由2004年的1173种,增至2012年的1424种。(26)2009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公布《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鼓励大陆传媒进入台湾办刊办报,拓展境外市场。虽然宣传教化仍被作为大陆对台传媒的重要功能,但在日益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之下,传媒的话语输出实际已经脱离以往单纯的政治考量,而在某种意义上被纳入两岸经贸文化往来的一部分。 二是传媒超越各自独立系统,呈现合作合办趋势。如福建青年杂志社与台湾思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合作在台湾本岛创办《城市天下》杂志,首创大陆入岛落地办刊模式;台湾最大出版集团城邦媒体控股集团与福建海峡出版发行集团共同投资成立海峡书局股份有限公司。《两岸传媒》《海峡画报》等合办的产品已经以繁简两种版本形式在两岸流通。合办合作传媒形式的出现,有利于平衡处理两岸声音,营造更为和谐的意见气候。 三是传媒“民间化”色彩愈发浓重。民营资本开始进入两岸传媒业视线,如台湾诚品书店创始人之一廖美立与广州本土设计师合办概念书店,暗示传媒交流已在某种层面可由两岸民间自发架构。更为重要的是,传媒成为两岸民间社会议题与文化共鸣交流的重要载体。自21世纪之初,台湾电视剧、综艺节目便风靡大陆。而在近两年,大陆传媒文化呈现出“反哺”趋势,“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等一系列节目在台湾走红,一时创造了台湾社会的“大陆现象”。新媒体之浪潮更被视为有利于展望两岸“媒介共同体”的形成,两岸人民“可以在网络空间通过论坛、维基百科、博客、微博等各种平台,交流各种价值观念、情感经验、文化品位等各方面的交流,从而获得某种共同的族群认同或身份认同”。(27)甚至在电子商务领域,竟有“淘宝统一中国”(28)之议论。 由是,两岸之间的传媒交往经历了由政治话语对抗进到政治、经济、文化共同统合的过程。可以说,其早期交往是基于双方敌对情境,并无“信任”可言。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降,传媒才方得以摆脱对抗意识,成为两岸政治互信道路上的重要中介。在新时期两岸多层次、多主体的结构互动之下,政治互信进程中的传媒,亦呈现出相当复杂的面貌。 三、信息、资本、意识形态、交往环境四面向中的两岸传媒角色 政治双边主体的传媒交往,既不由市场力量自发组织,亦不大可能被政治权力所完全驯服。两岸传媒在受各自系统宣传方针统一指导的同时,又是“内视”两岸关系这一客观存在的结果。其不同于政治经济视角下,以“跨国传媒”为表征的全球化传媒互动,也非“华文传媒”可以一言以蔽之。在两岸政治互信背景、文化互动结构以及社会话语权力变迁过程中,“传媒”在两岸视域下呈现出多元的面向。 (一)两岸的传媒是作为“信息”的传媒 当前传媒在两岸关系中首先仍是作为“信息”而存在,即传媒的物质存在被淡化,而聚焦于传媒内容“建构真实”的力量。这一视角无疑带有香农与韦弗信息论的考量,往往从传播技术、传播策略、信息加工等多种角度考量话语产制问题,实际关注的乃是如何有效传递信息。作为信息的传媒,在两岸政治互信进程中又主要表现为三种功能: 其一是监测功能。从系统传播的角度来看,“什么是信息”固然重要,但同时亦需关注“什么不是信息”。因此,两岸之间的信息传播既意味着如实传递两岸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动态,反映两岸舆情民情,为增进两岸之间相互了解提供认知空间,又需认识到传媒的“把关人”作用,即通过选择与筛选信息,过滤不利意见,彼此建构有利于自身系统之“框架”。 其二是公关功能。“资讯操控”原本便在传统政治公关领域居主流地位。(29)而在现代传播革命的范式转型中,政治公关手段虽已朝向社会知识建构方向转型,围绕“信息”进行话语生产再现这一核心却并不会有所变化。通过信息图景的建构,传媒是两岸双边政治形象塑造、政治实力对话,以及政治意图表达的主要平台,甚至于在特定情况下能够强烈左右两岸之间政治敏感,使之缓和或加剧。 其三是仪式功能。依据传播仪式观,信息不仅意味着在空间上的传播,同时也造就了从时间上对社会的维系。(30)信息通过再现“景观”,将共同体内部的文化具象化。犹如德波(Debord,1968)所指出,作为文化的景观并非单纯的图像符号,更重要的在于作为社会关系的中介。(31)就此种意义而言,两岸之间正是通过信息分享,共识传媒所建构的“文化景观”,才使人们得以认识到两岸共同体的存在。 (二)两岸的传媒是作为“资本”的传媒 按照鲁曼的说法,资本是属于所谓的“普遍象征化传播媒介”,是系统为应对所处的互动机制,为确保传播互动成功发展而生的产物。(32)这或可说明为何两岸对话虽在国家历史、体制结构等层面存在诸多分歧,却能基于共通的经济文化利益和平发展。长期以来,传媒作为产业“资本”,已经并入两岸经贸往来体系的一部分。 经济资本为两岸政治互信之间提供的动力不言而喻。以祖国大陆为例,两岸“三通”以来所形塑的庞大台商群体已成为台湾“台、澎、金、马”25县之外的第“26县”。由于利益相关,被资本所聚合的台商正“日益成为对两岸政治走势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的新生力量”。(33) 在传媒领域,两岸资本流通不仅造就了作为产品的媒体与作为经营者的两岸媒体人,更在宏观层次上建构了一种两岸传媒共同市场。在广播电视产业,台湾与祖国大陆之间版权互通、电视剧和综艺节目制作与分销、艺人经营等领域的合作,已不再是新鲜话题。2010年,台湾《新新闻周刊》与大陆《中国新闻周刊》签署合作协议,合作创办名为《ILook》新闻文摘式杂志。2010年大陆博库书城网正式开通,为台湾受众提供简体版大陆书籍的通路。在传统的出版传媒领域,两岸之间资本投资可谓日益深入。在未来开放市场环境影响下,作为“资本”的传媒将会占据更为显重地位,深刻影响两岸传媒的整体生态环境。 (三)两岸的传媒是作为“意识形态”的传媒 传媒能够建构出公众的政治“想象”,同时,由于传媒系统及其审查机制往往与政党体系相互联结,传媒本身又存在某种政治依附(Political Clientelism)。(34)两岸关系中的传媒在此意义上也就成为“意识形态”的传媒,这不仅表现于传媒所折射的意识形态内容,更表现为传媒本身便作为意识形态结构产物的一部分而出现。 传播学界的实证研究表明,带有政治意识形态或政治偏见的新闻媒体,不容易得到人们的信任。(35)在两岸体制分歧现实之下,传媒的“意识形态”姿态显然是阻碍双方沟通能效的关键因素。在两岸关系中,谈及台湾传媒,台湾新闻自由及其民主制度备受瞩目,而谈及祖国大陆传媒,“政党喉舌”的形象亦往往不可回避。不过,作为”意识形态”的传媒远非这种二元对立那般简单。台湾媒体虽向来在两岸被视为岛内民主化的象征,但实际而言,自台湾两党政治雏形确定,新闻界便“已形成不同立场的报纸,为自己的政治偏向努力制造有利舆论的局面”。(36)在政党相互攻讦的两党选举制度下,传媒又受“行销政治”影响,染上恶质文化色彩。(37) 作为“意识形态”,传媒显现出两岸话语沟通难解的绳结。过去数十年来,两岸在“非政治文化”领域(non-political culture)亲密互动,颇有交流成果。但在特定情况下,“政治文化中存在的鸿沟,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抵消了经济互动的积极效果,把双方的亲密关系拉回原点。”(38)传媒的意识形态意义在于,传媒是社会结构的放大镜。在接受传媒话语的同时,也在接受所传媒所输出的观念影响。这或使我们思考,如何推动两岸对传媒所输出的意识形态产生信任共识,进而逐渐与两岸政治互信的追求相互一致化。 (四)两岸的传媒是作为“交往环境”的传媒 如波茨曼所指出,将传媒视为“环境”,这是跳脱出媒介本身,转向关注“媒介与赋予其文化特征的人之间的互动”。(39)传媒信息系统本身便是一种社会环境,其超越了“地点”创造的现场交往系统,在看似地域消失的同时,又存在一定的边界。(40)这种边界无法通过现实区隔可视化,而由共同体所进行的有意义的传播得以界定。 作为“交往环境”的传媒使得两岸在共同意义空间内所做出双向对话的可能性最大化。其一,执政当局可以通过传媒即时互动,“有来有往”,避免自说自话;其二,意见领袖可以就两岸议题公开讨论,引导两岸观点与舆情,央视的《海峡两岸》、深圳卫视的《直播港澳台》以及东南卫视的《海峡新干线》等节目通过广邀两岸嘉宾参与电视时评,便是其中范例;其三是就最广泛层面而言的,两岸民众可借助新媒体手段,实践公民对话与情感交流,进而在协商民主视角下建构相互间的政治认同。 四、文化、经济、政治多重博弈中的两岸传媒功能 两岸双边往来向来被认为基于三种原理:一是文化整合原理,即认为台湾与祖国大陆同源同宗的文化性,能够使旧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序列让位于以文化为决定性因素的新秩序;二是经济整合原理,认为能通过经济共赢推动政治互信上升到更高层次;三则是政治整合原理,认为可借由大陆政治实力的增强,将台湾自发吸纳进入国家运行轨道。两岸政治互信进程,亦基本沿袭上述三条线索,在彼此领域交互展开。 作为文化、经济、政治三者力量相互牵制的“中间地带”,两岸视域下的传媒被赋予了多种面向的角色。又正是因为这种多重复杂的互动的结构,造就了两岸传媒在功能实践上的困惑。 其一,可说而不可“解”的传媒。尽管通过提供政治生活中的信息与评论,媒体信任与政治信任常常呈现出某种统一面貌。但媒体本身的信任度也受到质疑:这一方面表现在不同国家与地区内部,公众对于媒体内容的信任感存在不一致的状态,(41)另一方面又取决于跨文化跨地域语境中对他域媒体的信任程度。(42)由是,作为信息的传媒并不能确保传播机制中的连续的安全性。在两岸往来中,信息的“传言游戏”时常呈现出某种不稳定的状态,尤其当面对同一事件之时,传媒话语不同面向的解读可能为交流附加别样的对抗危险涵义。如面对岛内反服贸协议的“太阳花学运”,祖国大陆传媒话语主要考量学生运动对两岸关系的不利影响,暗示其“暴力式撒娇”一面。(43)而台湾在承认学生行动“有不成熟之处”之同时,亦肯定“这些孩子毫无虚娇的纯真与热情,以及对台湾前途的关心守护,却是台湾从民主改革以来,一道最耀眼而强大的光”。(44)由于话语书写的框架差异,两岸之间的传媒表达与两岸双方各自的最终理解可能并不一致。恰似帕森斯所提出的“双重偶发性”(double contingency)概念,每个主体都有自由行动的能力,互动对象均不确定对方的选择会是什么,因而无法预期互动的后续发展。(45)两岸对各自传媒内容预判与后续猜测之间存在的分歧,实则降低了信息所可能达成的信任度。 其二,资本与政治耦合的传媒。两岸传媒市场并非建立在“资本”自由流通基础之上,其在相当程度上仍取决于当局政治意愿。传媒集团在两岸传媒交流中占据绝对主导,但集团化的传媒往往与政治当局“藕断丝连”。大陆入台的传媒资本,基本由承担政治导向的大型国有新闻出版集团所垄断,地方中小型企业难以得到政策扶持。而台湾方面,不仅对祖国大陆传媒业及其从业人员设置多重障碍,使得两岸新闻往来呈现严重不对称状态,而且其传媒政治敏感甚至波及岛内媒体行业。以2011年,台湾旺旺中时媒体集团提出并购岛内主要有线电视系统业者之一的中嘉网络(即“旺中案”)为例,旺旺中时集团正是因受“陆资”背景猜忌,备受岛内舆论攻击。 其三,参与与控制并存的传媒。在两岸传媒往来中,一方面,我们鼓励与推动参与式传播互动,但亦需认识到,参与本身并不一定意味着“有效”。因为话语即使被信息共享者接受与认同,其行为仍在较大程度上受制于客观社会结构的影响。以两岸经济互动为例,虽然大陆台商往往被赋予政治考量的关注,但有如Shu与Schubert指出,由于在大陆缺乏有组织的自治权力,在短期之内,台商不太可能以大陆代理人身份在台湾成为政治游说者;(46)另一方面,虽然开放与共识是两岸关系来往的主流,但这并不意味着解除对传媒的管制。因为传媒虽对形塑公众政治信任有着显著效果,但其功能尚存在正负的不确定性。(47)并且,这种效果的影响还随不同媒介形态而呈现出差异化现象。(48)可见,即使是出于理性交往需要,两岸仍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对各自传媒的可控,使之朝向预期的良性轨道行进。吊诡的是,这又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反向形成对两岸传媒自由的压制与约束。 五、两岸传媒建构政治互信路径的学理前瞻 在“信任”划分中,存在特指性信任(particularized trust)与普适性信任(generalized trust)两种情形。(49)前者仅对自身的内群体产生信任,并担心除此之外的人与其价值观产生冲突,后者则对与不同群体的联系抱有积极态度,信仰“共同体通过创造关于规范与诚实行为的期望,分享一系列道德价值”。(50)就此意义而言,两岸之间的政治互信架构在普适性信任之上,但在其建构过程中,又往往面临特指性信任的难题。反映在传媒领域,便是两岸的传媒虽是两岸共同体传播空间内的传媒,但又因不得不面对各自子系统内部的受众,常常导致传播互动过程出现某种背离与矛盾。考量新时期两岸传媒如何在建构两岸政治互信中发挥作用,需要在意识到此一现实局面基础之上,充分厘清传媒在两岸之中所扮演的角色,依据两岸交往的现实进展与未来空间,谨慎而又创造性地给予解答。本文认为,如下路径可供未来进一步思考: 其一,实现传媒作为“信息”在两岸的均等传播权利。“信息”意味着一种客观实在,但其本身又受制于人为“框架”的选择。两岸信息传播尚存在一些彼此限制:一方面,台湾对祖国大陆媒体入岛有着严格法律限制,岛内个别媒体甚至对大陆媒体怀有较强敌意;另一方面,大陆虽对台湾记者入陆驻点较为开放,但台湾媒体有时在报道祖国大陆某些新闻事件时又受“党的新闻事业”体制约束。如台湾《联合晚报》社长项国宁所呼吁,应当尽速协商开放媒体长驻和互设办事处,使双方彼此熟悉,促进更正确、客观报道两岸交流及情势。(51)但事实却远非仅仅开放采访空间那样简单。两岸传媒更需在“什么是有利于两岸关系发展的信息”这一问题上多做讨论,达成理念共识,方能真正保障双方的正当信息传播权利。在逐步清除信息流通的政策障碍之时,两岸当局也需针对传媒报道中的失真、夸张、歪曲现象制定共同的控制审查措施,进而推动两岸客观、真实、有效的信息传播。 其二,提升传媒作为“资本”在两岸传媒共同市场中的优化功能。自改革开放以来,基于两岸资讯交换的需求,作为商品的新闻实际早已在两岸孕育了一个颇具潜力的内容市场。而在海峡两岸密集互动,关系日益密切的今天,媒介联结资金流、物流、人才流的信息流作用更为明显。(52)大陆部分媒体在两岸传媒共同市场开发上已探索出一些经验,以具有地缘优势的厦门日报社为例,已与《金门日报》《旺报》等台湾岛内报纸建立了十余年稿件交换关系。由《厦门商报》与台湾传记工坊共同运作的杂志《两岸台商》于2010年创刊,开辟海峡两岸版权市场合作新模式。而台湾方面则早有学者估算,若大陆广告赴台,则每年可为台湾媒体创造1600亿元新台币的收益。(53)正是基于这种传媒经营收益考量,台湾已在2004年有限度地开放大陆媒体向台湾投入广告,2011年,又宣布进一步对已投资台湾的大陆企业以及已销往台湾的8000多项大陆农工商品进行广告“松绑”。虽然目前台湾传媒市场的开放力度尚为有限,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以两岸受众为核心的区域性的传媒共同市场依然颇具潜力。在遵循两岸共同利益最大化前提下,两岸可考量从两岸新闻共同市场入手,加强资本流通、技术交流、理念共享与产业合作,优化媒介资源开放竞争与自由配置格局,进而逐步向传媒产业共同市场过渡。 其三,探索传媒作为意识形态在两岸的对话空间。尝试考量“两岸传媒特区”这一概念,为两种社会意识形态提供“缓冲地带”,培育互信基础。两岸传媒特区,并非在国内现有特区生态下,开辟一个新的以传媒业为主导的特区,而是基于两岸之间存在的特殊地缘政治状态,开展以传媒为主要内容的两岸“特殊”合作模式。(54)自2009年,国务院颁发《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要求“发挥独特的对台优势,努力构筑两岸交流合作的前沿平台”,(55)两岸进一步奠定了传媒领域先行先试政策基础。2013年,国家批准5条先行先试、惠及台胞的新闻出版政策。同年,上海自贸区亦宣布开放部分外来传媒娱乐产业,从其负面清单来看,开放态度虽仍保守,但依旧为突破两岸现有传媒合作提供了理论可能。在ECFA框架逐步深入的背景下,以厦门、平潭等对台窗口为代表,亦可尝试进一步在媒体产品相互落地,媒体从业人员借调,共建传媒公司与数字基地等方面进行区域试点。 其四,深化传媒作为交往环境在两岸命运共同体中的内涵。两岸传媒交往不应当局限于一般意义的“大众传媒”,而应当强调为两岸民众的传媒。可引入“社区传播”之概念,跳脱从“两岸”谈“两岸”这一宏观交往环境,将视角回归到日常性的社区共同体。由于社区媒体通常呈现出与主流媒体不同的姿态,(56)因而又有利于消解两岸传媒中常常存在的意识形态偏见。目前,台湾社区媒体的运作相对祖国大陆较为成熟,以《中华社区报》《妈祖社区报》《金门社区报》等等为代表,其聚焦当地事务,目标受众较为明确,常常包含两岸交流话题,甚至不乏大陆读者投稿。未来两岸传媒一方面可结合政府出资与商业盈利两种模式,围绕以“两岸族”、在陆台胞或在台陆胞等两岸族群交集社区,推动民众通过社区报、社区有线电视等各种社区媒介形式在地发声,使两岸民众自主参与到内容资源创作过程;另一方面,由于在新媒体语境下,两岸“社区”概念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传统实体社区,因而更需注意到虚拟社区所发挥的作用。在以天涯社区台湾版,台湾政客邱毅、陈文茜等人的新浪微博,豆瓣等为代表的虚拟社区,两岸民众互动已经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现象”。随社会化媒体在两岸交往中的作用日趋重要,一些海峡两岸专业性协会与社团组织、台企亦先后开通运作微博、微信公共账号。但总体观之,许多两岸线上平台的运作多出于“一时兴起”,缺乏系统规划和长远维护。两岸传媒合作未来可多关注两岸在论坛、微博、微信、APP等虚拟社区的往来,加强两岸公共事务关联与环境参与度,进而推动两岸理性网络公共领域的成形。 六、结语 总而言之,既然两岸传媒能够在两岸政治互信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发挥沟通信息、疏通心结、凝聚共识的功能,那么,我们当更自觉地促进两岸传媒的交流与合作。因为两岸传媒有效的交流与合作能够为两岸政治互信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不断夯实民意基础。然而,传媒活动的效能又根本上极大地受制于两岸的政治气候。简而言之,当两岸政治互信状况较好时,传媒活动易于展现出活跃和友善的姿态,有时也会引发两岸社会众声喧哗;当两岸政治风起云涌时,传媒亦难免散播着猜疑和对抗情绪,有时却能帮助两岸关系拨云见日。正因如此,我们一方面应当加强对台湾传媒的舆情监测,深刻把握台湾媒体的话语产制策略,关注并巧妙运用话语修辞,透过两岸传媒对话,增进彼此的了解与理解,以期化解两岸民众的疑虑,增强彼此的亲切感和认同感;另一方面,通过合情合理的政治安排,建构具有强大舆论引导力的政治议题,推动两岸传媒通过交流合作来营造“两岸一家亲”的和谐氛围。只有如此,才能可能实现两岸政治与传媒的良性互动,不断增进政治互信,扎牢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 两岸传媒角色根植于两岸客观实在之社会结构,其在功能实践面向上,既反映着作为“我们”这一两岸共同体之认知,又存在“我”与“他”、“陆”与“台”之间的区分,此种纠葛造就了两岸传媒交往的复杂性。两岸传媒在实践过程中,既以两岸关系为中心彼此相互联结,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各自社会结构生态的宰制,因而常常摇摆在一种“在地化”与“两岸化”的矛盾之间。两岸政治互信牵涉到两岸民众关于两岸社会的基本定位。尽管两岸关系关于彼此的直观认知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传媒所筛选与拼贴的图景,但我们也需要认识到,此种认识是一个长期性的、渐进性的、双向性的过程,传媒对两岸关系改善的影响并非立竿见影。在当前两岸共同化传播系统尚不完善的背景下,两岸传媒的合作,应当脱离纯粹地“以传媒来反映两岸”的观念,而应更紧密地将传媒与两岸之间的社会生活与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发挥传媒在信息、市场、观念以及交往方式等领域中的融合效应,实现更制度化和常规化的互动。在两岸政治互信进程中,“传媒”既要回归到两岸多层次交往系统下多重属性意涵的传媒,又应当以两岸共同的未来利益为标准衡量传媒实践的有效性。在新时期两岸政治认同、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复杂话语权力博弈互动过程中,传媒必然成为两岸社会重新认识与反思的对象。 注释: ①《新中国重大决策纪实》编写组编:《新中国重大决策纪实》,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第259页。 ②葛星:《N·卢曼社会系统理论视野下的传播、媒介概念和大众媒体》,《新闻大学》2012年第3期。 ③樱井芳生:《卢曼社会系统论中的媒介观简介》,李卓钧译,《新闻与传播评论》,武汉:武汉出版社,2010年,第50页。 ④唐桦:《主观博弈论视角下的两岸政治互信初探》,《台湾研究集刊》2011年第6期。 ⑤Lippmann,W.Public opinion,New York,NY:Macmillan,1922. ⑥Luhmann,N.The reality of the mass media,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2. ⑦张文生:《两岸政治互信与台湾民众的政治认同》,《台湾研究集刊》2010年第6期。 ⑧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56页。 ⑨Bianco,W.T.Trust:representatives and constituents,Ann Arbor,MI: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4. ⑩严安林:《试论海峡两岸间的政治互信及政策建议》,见张文生主编:《两岸政治互信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2页。 (11)刘国深:《加强两岸政治互信ABC》,(香港)《中国评论》2009年第12期。 (12)Eckstein,H.Division and Cohesion in democracy:A study of Norwa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6. (13)Mishler,W.& Rose,R.“What are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trust? Testing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theories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2001,34(1):30-62. (14)Fukuyama,F.The Great Disruption:Human Nature and the Reconstitution of Social Order,New York,NY:The Free Press,1999. (15)Gamson,W.A.& Stuart,D.“Media discourse as a symbolic contest:The bomb in political cartoon”,Sociological Forum,1992,7(1):55-86. (16)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曾庆香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181页。 (17)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13-14页。 (18)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19)马汇莹、张晓峰、童兵:《传媒在两岸政党沟通中的角色审视》,《新闻大学》2006年第1期,第2-7页。 (20)佟文娟:《过程与分析:媒体与台湾政治民主化1949—2007》,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 (21)张宪文、方庆秋主编:《蒋介石全传》,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82页。 (22)王建民:《关于两岸和平发展框架建构问题的几点讨论》,见周志怀主编:《新时期对台政策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北京:华艺出版社,2008年,第218页。 (23)台轩:《中国政府的对台方针政策》,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2年,第41页。 (24)孙波:《对台宣传浅谈》,北京:华艺出版社,2002年,第21页。 (25)王天滨:《新闻自由——被打压的台湾媒体第四权》,台北:亚太图书出版社,2005年,第315-483页。 (26)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规划发展司:《中国新闻出版统计资料汇编2013》,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 (27)连水兴:《从“文化共同体”到“媒介共同体”:海峡两岸传媒业合作研究的视角转换》,《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第23页。 (28)新华网:《两岸网络热议“淘宝统一中国”:不选台湾省不发货》,2014年1月14日,http://news.xinhuanet.com/tw/2014-01/14/c_126002278.htm,2014年4月14日。 (29)张文强:《从资讯操控到社会知识建构:一种观看公共关系的新方式》,《广告学研究》,2001年第17期,第45-60页。 (30)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 (31)Debord,G.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Canberra,AUS:Hobgoblin Press,2002. (32)Luhmann,N.Social systems,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157-163. (33)孙展、陈晓:《两岸政局背后的台商势力》,《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第18期。 (34)Hallin,D.C.“Political clientelism and the media:south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Media Culture Society,2002,24(2):175-195. (35)Lee,Tien-Tsung.“Why they don't trust the media:An examination of factors predicting trust”,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2010,54(1):8-21. (36)洪丽完、张永桢、李力庸、王昭文编著,高明士主编:《台湾史》,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第322页。 (37)黄嘉树、程瑞:《台湾选举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02年,第63-82页。 (38)Chao,Chien-min.“Will economic integration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lead to a congenial political culture?”,Asian Survey,2003,43(2):284. (39)Postman,N.The humanism of media ecology,Proceedings of the Media Ecology Association,2000:11. (40)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4页。 (41)Connolly,S.& Heap,S.P.H.“Cross country differences in trust in television and the governance of public broadcasters”,Kyklos,60(1):3-14. (42)Chaffee,S.H.,Nass,C.I.& Yang,Seung-Mock.“Trust in government and news media among Korean Americans”,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68(1-2):111-119. (43)萧师言、张倍鑫、崔杰通:《台湾学生撤离“立法院”岛内担忧埋“台独”地雷》,2014年4月11日,http://china.huanqiu.com/article/2014-04/4966330.html,2014年4月16日。 (44)中国时报短评:《太阳花照黑暗》,《中国时报》,2014-04-12,第A22版。 (45)Parsons,T.& Shil,E.(Eds).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Cambridge,MA:Havard University Press,1951:105. (46)Shu Keng & Schubert,G.“Agents of Taiwan-China Unification? The political roles of Taiwanese business people in the process of cross-strait integration”,Asian Survey,2010,50(2):287-310. (47)Miller,A.H.,Goldenberg,E.,Erbring,L.“Type-set politics:impact of newspapers on public confidenc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1979,73(1):67-84. (48)Moy,P.& Scheufele,D.A.“Media effects on political and social trust”,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2000,77(4):744-759. (49)Uslander,E.M.& Conley,R.S.“Civic engagement and particularized trust:The ties that bind people to their ethnic communities”,American Political Research,2003,31(Ⅹ):1-30. (50)Fukuyama,F.Trust:the social virtues and creation of prosperity.London,UK:Hamish Hamilton,1995. (51)王连伟:《两岸新闻交流务实最重要》,《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年10月29日,第03版。 (52)谢清果:《海峡两岸传媒共同市场建构的现实需要与理性前瞻》,《现代传播》2010年第11期。 (53)任成琦:《大陆报道怎成“置入性行销”?》,《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年5月9日,第03版。 (54)谢清果、王昀:《平潭传媒特区建构的时代呼唤、现实困境与理性前瞻》,《发展研究》2013年第5期。 (5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2009年5月6日。 (56)Forde,S.“A descriptive look at the public role of Australian independent alternative press”,Asia Pacific Media Educator,1997(3):118-130.标签:政治论文; 两岸政治论文; 台湾媒体论文; 两岸经济论文; 台湾经济论文; 两岸关系论文; 传媒产业论文; 大陆文化论文; 意识形态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