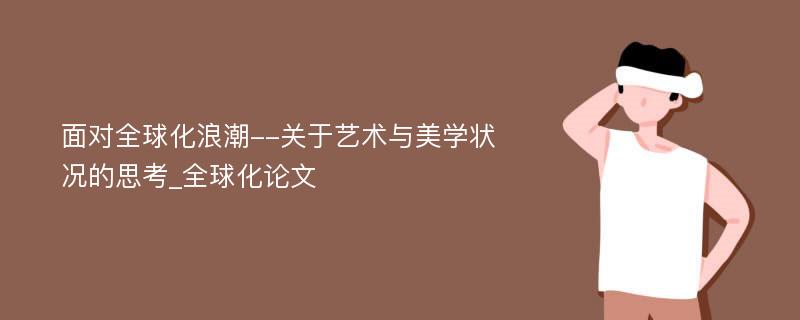
在全球化浪潮面前——关于艺术与美学处境的断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断想论文,美学论文,浪潮论文,处境论文,面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光耀转向和活佛拍电影
近些时候,有两件事给我触动颇大。
一件事是李光耀转向。
众所周知,李光耀被西方人称为“新儒学之父”,“亚洲价值最雄辩的发言人”。但是现在他宣布儒家价值观过时了。
且看李氏先前的观点。
在1994年3~4月号美国《外交》季刊刊登的李光耀同该刊编辑扎卡里亚长篇谈话录《文化是决定命运的》中,李光耀说:“西方人相信只要有一个好的政府制度,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东方人是不相信的。东方人相信个人离不开家庭,家庭属于家族,家族又延伸到朋友和社会。政府并不想给一个人以家庭所能给他的东西。在西方,特别是第二次大战后,政府被认为可以对个人完成过去由家庭完成的任务。这种情况鼓励了单亲家庭的出现,因为政府被认为可以代替父亲,这是我这个东亚人所厌恶的。家庭是久经考验的规范,是建立社会的砖瓦。”他还说:“中国的传统观念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齐家是基础,我们全民都对此深信不疑。”“我们感到幸运的是,我们有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人民相信做人要节俭、勤劳、孝敬父母、忠于家庭,尤其是要尊重学问。”(注:参见李慎之《亚洲价值与全球价值》,《太平洋学报》1995年第2期。)总之李光耀所崇奉的是建立在宗法家族基础上的长上崇拜和权威主义的亚洲价值,而且他似乎成功地组合了市场经济与亚洲价值相结合的发展模式,从而创造了经济腾飞的奇迹——至少以往几十年许多人这样认为。但是,几年前亚洲金融危机以及紧跟着而来的亚洲国家的内部动荡,给李光耀模式以重大冲击,以网络技术为基本标志的信息时代的伟大革命,给李光耀的儒家观念当头棒喝。
如今,李光耀终于改弦更张了。
2000年在北京举行的21世纪论坛上,他只字不提作为亚洲价值重要标志的权威主义而大讲西方价值观念所倡导的个人创造性。2001年1月底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他明确宣布儒家价值观已经过时。“尊重老人在信息时代似乎管不了什么用。父亲未必最有学问,孙子也许懂得更多。”“在信息技术时代,年轻和一副灵光的脑子是巨大的优势。在我们的国家里,做决定的是老人,他们行动迟缓,他们会错过机会。”在接受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采访时,他也说儒家文化不适应信息时代,会严重影响社会的经济发展,因此“要改变父母、叔叔大爷、表哥表姐和外甥侄子的精神状态和价值观念”(注:参见任剑涛《李光耀为何改弦更张》,《南风窗》2001年第4期。)。
一件事就是活佛拍电影。
据报载:“在喜马拉雅山窝窝里一向封闭的小国不丹,有一位名叫KHYENTSE NORBU的藏教转世活佛,成为该国首次投资拍摄的电影《高山上的世界杯》的导演。影片背景选在印度北部的一个寺院中。1998年,修行中的少年增人们因世界杯的开幕而欢欣雀跃。每天晚上,他们溜出专院到村民家中看黑白电视转播,醉心于比赛的进程。决赛前夕,虽然擅自外出被发现,而他们还是决心“即使借电视也要把决赛看完”。这个故事是根据这位41岁的导演年轻时的亲身经历改编而成。这位活佛说,之所以把它写成剧本,是因为“足球是现代化的象征,它甚至在远离世俗、戒律森严的寺院里也引起了变化。我想把这些告诉观众”。拍摄时,由于预算很低,无法雇用演员,剧组启用了两名真正的僧人做主角,连寺院住持也参加了演出,“真人演真事”。在不丹,1999年有线电视才开播。但现在,因特网在这里也开通了。这个远离世俗的国度正在被飞速的变化冲击着。据悉,这位活佛导演已在考虑拍摄下一部影片《美丽的故乡不丹》(注:见2001年3月25日《北京青年报》第12版。)。
上面两个例子,一个是一贯宣扬亚洲价值和儒家思想、对亚洲政治经济发生过重要作用、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政界“杠子头”的幡然转向,一个是在远离世俗的国度向来被人视为不食人间烟火、六根除净、“坐怀不乱”、同“现代化”不沾边儿的佛界圣人的“现代化”举措,可以说是两个“堡垒”的动摇。这不能不发人深思。
我不知道人们是否把它们看做是全球化问题中的例子。如果不是,那么它们属于什么范畴的问题?
我倾向于把它们看做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某种表现。
顺便说一句,我所理解的全球化,是指在地球上各种不同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通过各种形式、各种范围、各种程度、各种途径的交往、碰撞(甚至免不了厮杀),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融通,从而在某方面或某些部分达到统一,实现一体化,某些方面、某些部分难以一体化(或者说不可能一体化),但可以在保持个性化、多样化、多元化的情况下,互相理解、彼此尊重,达到某种价值共识和价值共享,促成全球性的人类文化繁荣。
以前,我只承认有限范围和有限程度的全球化,例如科学技术和经济等领域里的全球化,而拒绝艺术和美学领域里的全球化,认为在这些领域只能个性化、多样化、多元化,只能保持民族、地域、流派、个人的独特性,很难甚至不可能形成价值共识和价值共享,因而不存在全球化的问题。
而现在,由于越来越频繁的接触到类似于李光耀转向和活佛拍电影的现象(虽然给人的刺激并不都那么强烈),我发生了动摇。
人类文化的基本趋向
不言而喻,李光耀转向和活佛向“现代化”靠拢,绝不是简单的个人行为偶然现象,其中潜藏着深刻的人类文化动向。这里表现出两种或多种不同的文化在历史实践中经过碰撞和较量所发生的变化:思想观念变化了,价值取向变化了,道德规范变化了。也许在这种变化中,某种不太适应这个世界的过于狭隘的东西被淘汰了;某种仍然有价值的、仍然适宜于世界发展的东西保留下来了;某种对于这个世界的发展前景具有更大更广泛适应性的新的文化样态、新的文化因子产生了、滋长了——最后,某种新文化生成了。儒家文化同西方文化,佛家文化同世俗文化特别是同现代化的世俗文化,的确存在非常大的差异,两者距离十分遥远;但是,在这个世界上,距离再遥远、差异再大的文化现象,也很难避免发生联系、发生影响,尤其是在现代。而且随着交通、信息技术的发展,这种联系和影响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强烈。不同的文化碰在一起,有的可能会和睦相处,亲切交流,很容易取得价值共识,相通相融,合为一体,包括结合之后生出新的文化现象;有的则有矛盾、冲突,有时会格格不入,有时会打起来,会发生“战争”——当然这是特殊的战争,是精神上的战争,观念上的战争,价值取向上的战争,心理上的战争。这种战争同通常的战争并不相同。通常的战争,古代部族之间的战争,现代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其结果一般是以一方的毁灭告终。不是你吃了我、就是我吃了你。但是,文化上的“战争”却不是简单的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甚至也不是简单的谁占了上风、谁占了下风,谁败了,谁胜了,谁升值了、谁贬值了,谁吃亏了、谁占便宜了,谁向谁投降了……譬如在中国历史上,伴随着元灭宋、清灭明的民族之间真刀真枪的战争,也发生了两种文化上的“战争”、这种文化“战争”的结果,并没有像政治和军事集团那样一个被一个吃掉。汉文化败了吗?没有。蒙古族文化和女真族文化胜了吗?也没有。汉族文化并没有灭亡,蒙古族文化和女真族文化也没有独霸世界。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它们在温火慢炙、潜移默化中,逐渐互相理解、渗透、融合。通过这种融合,两种原有的文化都发生了微秒的变化,产生了既包含汉文化也包含蒙古族文化的元文化、既包含汉文化也包含女真族文化的清文化。这种变化的结果,其适应性(从地域和人口上说)更广、更大了——从窄狭走向广阔,长远地看,能不能广阔到全世界的范围呢?如果广阔到全世界的范围,那是不是可以称为“全球化”呢?当然,这会是一个非常细致、非常漫长的过程,而且文化中的某些方面、某些领域、某些部分,可能永远会保持其个性化、多样化、多元化的面貌,但是它们可以具有价值上的相互尊重、共识和共享,达到全球性的文化共存共荣。而且,按照事务发展的已有经验,单亲繁殖、近亲繁殖,不如远缘杂交来得好。不同文化甚至差异很大、相距遥远的文化的碰撞、交融,可能发展得更茁壮。
这是不是可以看做人类不同的文化互相接触、碰撞之后得以发展的一般规律呢?
面对不同文化的这种碰撞、融合以至产生新的文化因子或者最后干脆产生了新的文化,有的人站在原有文化的立场上,可以心理上感到不舒服、不光彩,好像失去了什么。具体到上面讲的两个例子,亚洲价值与西方价值、佛家文化与现代世俗文化之间的碰撞,李光耀和活佛对对方价值观念的认同,好像李光耀向西方价值投降了,丢了面子了。
我不这样看。我不认为有什么不光彩的地方。我认为不应当简单地看做是谁输了谁赢了、谁向谁投降了、未来是谁的天下了。倘有上述那种感觉,是不是某种民族主义的狭隘情绪在作祟?假如超越某种民族主义情绪而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超越“中”“西”派系观念而站在它们之上,我们也许会看到不同的甚至差别极大的两种文化由隔膜、对立、冲突走向对话、理解、融通,达到某种程度的价值共识和价值共享;或者觉察出两种文化在碰撞中,会产生文化的新因子甚至产生某种新文化的信息。譬如,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中有一种很重要的价值观念“信誉”——“商业信誉”或“企业信誉”。虽然这俩都沾了个“信”字,其实有根本区别。中国的“信义”与宗法家族社会的长上崇拜、士为知己者死联系在一起,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中的信誉则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自由竞争、公平、平等为基础。这两种东西,在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相遇了,两者相互碰撞,相互交融,产生了今天中国市场经济中的“信任感”、“信誉”。今天存在于中国的这种“信任感”、“信誉”,是不是有新的因子在其中呢?我认为有。它比起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中的“信誉”,可以多了点“义”的成分,多了点人情味;而比起中国传统文化中充满“士为知己者死”、“长上崇拜”的“信义”来,可能多了点“公平自由竞争”、“亲兄弟明算帐”的成分。这种新的文化因子,将来发展起来,是不是适应的范围和地域更广更大呢?
这将是全人类文化的前进。
这就是文化的全球化趋向。
在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各个领域里,全球化恐怕是难以避免的,也可以说是不以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无论从历史的方面说,还是从逻辑的方面说,都是如此。
其实人类的历史,宏观地说,就是不断全球化的历史。科学家们说,150亿年前宇宙诞生,50亿年前太阳系诞生,40亿年前生命诞生,5亿年前具有心脏和循环系统的“海口虫”诞生(注:不久前,科学家在云南澄江地区发现了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脊椎动物祖先的珍贵化石,命名为“海口虫”。它虽然只有3厘米长,但能清晰地辨认出它的心脏和循环系统,具有现代脊索动物成体和脊椎动物胚胎特有的神经索和脊索构造。“海口虫”代表了通向人类漫长演化历程的第一步,极有可能就是我们的祖先。——见《文摘报》2001年4年15日第6版。),500万年前人类诞生。地球是一个整体。地球上的人类,虽然是分散居住和生活的,但是彼此之间是可以相通、需要相通、必然相通的。普遍联系是宇宙的通则,人类作为有意识的族类更不例外。生活繁衍在同一个地球上的人类,有着趋向全球化的天然基础。起初,人类的文化是在不同的地域独立产生和发展的,后来不同文化逐渐联系、交流、碰撞、影响、融通,开始了漫长的全球化历程。人类文化具有某种天生的弥散性,是任何地域的、民族的、国家的边界所挡不住的,尤其在当今电子传播媒介越来越发达的时代,海关、国果对于互联网起不了拦截作用。上万年前秘鲁人发现的马铃薯和印第安人发现的番茄最终成为全球化的食品,中国人发明的火药传到西方又传遍世界供全球人使用,喝茶也不再是中国人的专有习俗而风靡全世界,莎士比亚、曹雪芹、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鲁迅的作品被翻译成各种文字激动着世界各大洲的读者……这不是全球化又是什么呢?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的传播,汉代张骞、班超等出使西域,汉唐通往大食、大秦丝绸之路的打通,罗马帝国的建立和分裂,阿拉伯世界在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形成,十字军东征,蒙古帝国的大面积扩张,郑和下西洋,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资本主义自近代以来在全球范围的推行,世界市场的形成,西学东渐,19世纪中叶之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及20世纪社会主义世界的发展,20世纪后期电视直播、电子文化、网络媒介创造的信息快速通道,信息时代的到来,等等,这些都是全球化过程中留下的脚印。不过在资本主义时代之前全球化是极其缓慢的,从资本主义时代起则变得十分迅速,而在信息时代,更有了电子传播的加速和全方位的广度。
重读《共产党宣言》
对全球化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老祖宗早就作了理论阐发。不信,你重新读一读《共产党宣言》肯定会有新体会。19世纪40年代,血气方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描述了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全球化现象,论证了它的价值和趋势。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家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化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论述了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全球化问题。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马恩首先阐明的是物质文化即居于基础地位的经济的全球化——市场的全球化、贸易的全球化、生产和消费的全球化;跟着他们也略微涉及这种经济全球化对政治全球化的影响——资产阶级迫使别人“推行所谓文明制度”。他们强调了在这个领域里全球化的步伐摧枯拉朽、势不可挡,是那样地无情和残酷。“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这不是蛮不讲理的霸道行为吗?然而,在这里道德和历史发展发生了冲突:它亵读了道德却促进了历史。
第二,全球化是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和必然结果,同时反过来它又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反过来,“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从而又使经济空前繁荣。“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这些都是符合历史前进的方向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彷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第三,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原理,马恩在论及经济领域、物质生产(物质文化)的全球化时,跟着必然也推及精神生产(精神文化)的全球化。他们明确指出:“物质生产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并且瞻望了未来将由各种地方的和多民族的文学形成一种“世界的文学”的前景。当然,他们在这里所说的“文学”包括了科学、艺术、哲学等书面文化的各个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精神文化的所有这些方面也是能够全球化和必然全球化的。
马恩当年关于全球化问题的论述不但得到了历史实践的证实,而且今天的世界全球化趋向又有了新的发展变化。费孝通教授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说:“跨地区和跨国界的经济关系,除了表现在市场经济的超地方特征之外,还表现在近年来跨国公司的大量发展上,跨国公司在产权方面与具有民族国家疆界的国有、私有企业不同,它们没有明显的地理界限。它们的最大特征就是‘无国界性’。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中,不仅外国人来中国设立他们的跨国公司的办事处、子公司,拓展业务,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海外办公司,开工厂,甚至开设大型专业市场。我家乡的震泽厂在美国开办了分公司,我访问过的青岛海尔集团在海外开了分公司,我所熟悉的温州人在巴西开设了‘温州城’。这样的经济交融,已经不是简单的‘西方到东方’、‘外国到中国’、‘中国到外国’的老问题,而是一种新型的国与国、区域之间交流和互动的新发展和新的组织形式。”(注:费孝通:《“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读书》2001年第4期。)费孝通如此这般总结了20世纪、展望了21世纪:“20世纪是世界性的‘战国时代’,意思是说,在20世纪里,国与国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有着明确的界限,这个界限是社会构成的关键。不同的政治、文化和区域实体依靠着这些界限来维持内部的秩序,并形成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共同经历过的历史事实。而在展望21世纪的时候,我们似乎看到了另外一种局面,20世纪那种‘战国群雄’的面貌已经受到一个新的世界格局的冲击。民族国家及其文化的分化格局面临着如何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纪里更新自身的使命。”(注:费孝通:《“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读书》2001年第4期。)
费先生的话对不对呢?我看很有道理。20世纪的情况既如先生所言;21世纪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歌德的启示
马恩对“世界的文学”(文学的全球化)前景的推想和瞻望,可能至今有的人并不赞同。但我现在认为马恩的说法既符合人类精神文化(包括文学艺术)已有的历史事实,也符合人类精神文化(包括文学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当然这个过程可能很长,可能十分十分遥远。而且即使全球化,也必须保持文学本性所要求的个性化、多样化、多元化。这是文学艺术全球化问题的特殊性。文学艺术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应该理解为文学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全人类共享;是价值共识,而不是排斥个性、多样性、多元性。总之,价值共识和价值共享是文学艺术全球化的基础和核心。
但是,不管文学艺术的这种全球化性质多么特殊、历程多么遥远,从长远的历史发展来看,其全球化的方向恐怕是难以改变的。
谈到文学全球化即“世界文学”的命题,也许(我还没有找到证据证明一定是)马恩受到歌德的影响,因为更早(大约比马恩早20年)提出这一命题的是歌德。1827年1月31日歌德同他的秘书爱克曼谈话时,由中国传奇《风月好逑传》引发出一大篇关于“世界文学”的问题议论。歌德肯定了中国人和他们的西方人在精神文化方面是相通的:“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歌德说:“我愈来愈深信,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不过说句实话,我们德国人如果不跳开周围环境的小圈子朝外看一看,我们就会陷入上面说的那种学究气的昏头昏脑。所以我喜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我也劝每个人都这么办。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注:《歌德谈话录》,第112页~1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歌德谈话中有两点给我们特深刻的启示。
一是他强调不同民族(譬如德国人和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是相通的,是“同类人”。我赞成歌德的观点。这就肯定了文学艺术之所以可以全球化在精神气质方面的内在基础。现在有的人之所以不赞成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精神文化的全球化,很重要的一条理由就是认为不同民族精神气质的不相通,认为艺术信息、审美信息不可能由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即不可传达。例如有人说:“文化原本只能以人心、民族或社会(区)之精神气质为生存和生长的居所,即是说,它天然就具有无法根除的‘地方性’(Locality)或“区域性’(Provinciality),这是其民族性(Nationality)的生存论意义所系。”“文化(我是说狭义的难以‘编辑知识化’或技术化的‘非科学知识’的‘隐意文化’,而不是广泛意义上的‘知识文化’)是人性化的产物,其生产方式只能靠传统的积累和地方性或民族性的‘精神气质’(Ethos)培育,而不可能像自然资源的加工和利用那样,借助技术的手段进行再生和模式化。”(注:万俊人《全球化与文化多元论》,《读书》2000年第12期。)文化诚然是人性化的产物,诚然具有地方性、区域性、民族性,诚然需要传统的积累和地方性、民族性的精神气质培育,诚然不同于自然资源的加工和利用。然而,这并没有否定人心是可以相通的,并没有否定西方人和东方人,黑人、白人、黄种人,在思想、行为、情感等等方面是可以互相交流、互相理解、互相融合的,是可以取得价值共识的。电影《刮痧》就写了中国和西方不同文化从冲突、厮杀到理解、认同的过程。起初中西两种价值取向、两种情感行为、两种思想观念是那样水火不容。中国人给孩子刮痧治病当然绝对是出于爱,但西方人却视为虐待、侵犯人权。这确实是由不同的“传统的积累和地方性、民族性的精神气质培育”出来的不同文化。但是这两者真的绝对不能相通吗?非也。经过激烈的痛苦的精神搏斗,最后中国人接受了油画,西方人接受了中国画。而且,即使是中国画家进行国画创作,也可以融合西方的绘画因素,徐悲鸿的画马,不是可以看到西画的某种味道吗?西方人理解中国画,恐怕不一定比具有传统观念的西方人理解西方自己的理代派抽象画更难。中国人理解西画,也不一定比中国人理解中国当代先锋派绘画更难。剪纸艺术是我们的国粹之一,纯属中国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但是西方人接受了,理解了,而且非常喜爱。最近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一个电视片,介绍东山泰安的民间剪纸艺术家卢雪女士几次到欧美和新加坡进行文化交流,深受欢迎。在新加坡受欢迎,并不令人奇怪。令人惊讶的是在欧美竟然那么轰动。她在瑞士苏黎世大学的讲坛上讲课、表演,不但学生认真学习,而且苏黎世大学的校长和教授也那么认真听讲(注:中央电视台2001年4月20日中午“灿烂星空”栏目播放。)。不同文化并没有绝对不可逾越的民族性、区域性鸿沟。
前面所引的那位先生还以宗教为例说明不同文化的不能融通。“真正的宗教是从民族和人们的心灵中生长出来并存在于民族和人们心灵之中,既不可能强行制造,也不可能强行消灭,更不可能人为地创造出某种形式的“世界宗教”,即使我们可以设想康德式的‘世界公民’,因为我们无法消除民族、肤色和地缘的差别。”(注:万俊人《全球化与文化多元论》,《读书》2000年第12期。)我不信仰任何宗教,更不赞成所谓“世界宗教”,但我并不反对别人信教。强行制造、强行推行或强行反对、强行消灭某种宗教,的确是愚蠢的,也是行不通的。某种宗教的确是从某个地方、某个民族产生、形成的,开始它们的确是地域性的、民族性的。但是,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自产生之日起,不是越出了它的产生地,传到世界上许多民族和国家吗?它们不是已经成为世界性的了吗?例如佛教,从印度起,传到中国、传到日本、传到亚洲和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基督教最早产生于小亚细亚犹太人散居的地区,传到欧洲和全世界各个地区和民族;伊斯兰教也早已不限于阿拉伯世界,前南地区的战争冲突,就有那个地区信仰伊斯兰教与信仰基督教的不同人群之间的矛盾作为一个重要原因。从宗教这种我并不赞成的文化现象的世界性传播,不是也可以看出文化的全球化趋向吗?除了宗教,哲学和美学也不是不能进行全球性传播即具有全球化趋向的。大家最不感到陌生的例子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这不用多说。至于美学,以中国百年以来的历史为例,可以说就是西方的许多美学思想在中国传播、同中国的美学思想和文艺现实相结合相融汇的历史,最近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印、我和我的同事合作编写的《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有相当篇幅涉及这个内容。说到文学,其世界性传播的广度、深度和速度,更是不比其他文化现象弱。前几年,一本《廊桥遗梦》(当然并不是多么伟大的或了不起的作品)竟然风靡世界,据说中国也印了多少多少万册。当然,说到精神文化特别是其中的文学艺术的全球化,大概谁也不会愚蠢到以为就是取消个性、多样性、多元性。关于文化,中国历史讲求“和”、“和而不同”。“和”,就是多样化的彼此不同的东西组合在一起。不同的东西可以共存共荣。“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注:《国语·郑语》。)即使是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民族之内,还会有不同流派存在,即使同一流派,不同的作家也须具有自己的风格特点。在统一性的“全俄罗斯化”的俄罗斯文学中,屠格涅夫不同于托尔斯泰,契诃夫不同于高尔基;在统一性的“全中国化”的中国文学中,鲁迅不同于郭沫若,巴金不同于老舍。假如世界上有一千个或一万个真正成熟的作家,那么就会有一千个、一万个不同的艺术个性。那么,为什么一说文学的全球化就一定是一体化、齐一化呢?假如真的一体了、齐一化了,失去个性、多元性、多样性了,那就连文学也没有了,还谈什么全球化?不存在的东西,去“化”什么呢?
歌德谈话中给我们第二个重要启示是“跳开周围环境的小圈子朝外看一看”,“喜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我认为这就是克服民族主义的狭隘性的问题。每个国家和民族的人,都有自己的爱国情感和民族自爱心。这极其正常,而且是十分美好的一种感情。但是爱国和民族自爱,绝不同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前者可以同时是开放的,好客的,喜欢同其他国家和民族交往的,善于学习和吸收他国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也慷慨把自己的好东西奉献给别人的。后者则常常采取闭关锁国和民族封闭主义,甚至奉行民族利己主义。我赞成前者而反对后者。我们曾经有过的闭关锁国和民族封闭主义,吃了大亏,给我们的国家、民族、人民造成了灾难,不论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方面,在经济、政治、哲学、美学、文学艺术等等方面都是如此。因此,必须坚决克服民族封闭主义、克服狭隘民族主义。不应惧怕别的国家和民族的好东西传进来,也不要舍不得把自己的好东西拿出去。英国诺丁汉大学聘请中国著名科学家、教育学家杨福家院士为校长,我听了很高兴,这倒不仅仅是因为杨福家教授给中华民族争了光,而是有感于英国人在这方面的胸怀和气派。在此同时,杨福家教授在2001年3月26日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中回答记者问题时提出一个主张:中国的著名大学应该用英语开几门课,以便于外国青年更多地来中国留学。这同样是值得高兴和钦佩的事。中国教育界应该有这样的全球化眼光和胸怀气派。全球性的文化交流、对话、融通有什么不好?如果通过交流、对话、融通,达到全球化的文化繁荣,对全世界人民不是都有好外吗?这样的全球化有百利而无一害。不应惧怕这种全球化,更没有理由拒绝这种全球化。我们应该奉行民族开放主义,以开放的心态欢迎这样的全球化,让我们的文学艺术、我们的美学在这样的全球化氛围中发展繁荣。
当然,当今世界上也有打着“全球化”旗号而实行经济沙文主义、政治霸权主义、文化霸权主义的。这是一种典型的狭隘民族主义、民族利己的表现,它损人利己,攫取别的国家和民族的脂膏来养肥自己。有人把这样的所谓“全球化”称为“陷阱”(政治陷讲、经济陷阱、文化陷讲)是有道理的。全世界善良的人们当然应该警惕这样的陷阱。但是要知道,这不是真正的全球化,而是损害全球化。我们不能因此就拒绝全球化、反对全球化。
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