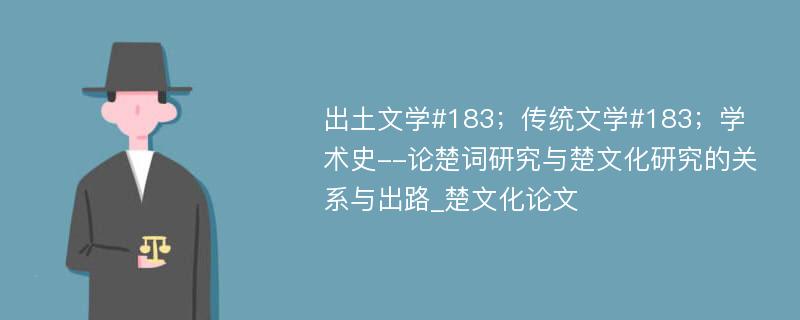
出土文献#183;传统文献#183;学术史——论楚辞研究与楚文化研究的关系与出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献论文,楚辞论文,出路论文,学术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中国考古学的史学特征:楚辞是上古史研究的重要文献
20世纪20年代李济主持的考古发掘,为中国现代考古学迈出了第一步;王国维的“古史新证”,则奠定理论基础。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周刊》发表《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指出四大发现:第一,1898-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古代,特别是商代的看法,使“东周以上无史”观不攻自破;第二,西域木简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汉晋历史的根本认识;第三,敦煌文书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经书和唐史的许多认识;第四,清代内阁大库三千多麻袋档案被罗振玉抢救,使人们对明清史研究的许多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同时,王国维又以四大发现为例证,在《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中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勾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①。
我们还可以通过商代先公先王的考证,尤其是王亥、王恒、上甲微的考证——这一典型的常常为后人称道的“案例”作些分析。
第一,在王国维之前,清代学者(主要是楚辞学者)已经作过理论研究,提出了比较准确的结,论。《楚辞·天问》“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四句之释,是一个历史疑案。清代徐文靖《竹书纪年统笺》、《管城硕记》指出,“该”,为冥子垓,是即该也②。刘梦鹏据《左传》、《竹书》、《山经》指出“该”即殷先公之“王亥”,“有扈”为“有易”之讹,“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即王亥败于有易,有易“困辱之,使为牧竖”③。
第二,一百多年后,王国维据甲骨卜辞进一步证成其说,断定卜辞中的王亥,亦即《山海经》之王亥、《竹书纪年》之殷侯子亥。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云:
季亦殷之先公,即冥是也。楚辞《天问》曰:“该秉季德,厥父是臧”,又曰:“恒秉季德”,则该与恒皆季之子,该即王亥,恒即王恒,皆见于卜辞。则卜辞之季,亦当是王亥之父冥也④。
余读《山海经》、《竹书纪年》,乃知王亥为殷之先公,并与《世本·作篇》之胲,《帝系篇》之核,《楚辞·天问》之该,《吕氏春秋》之王冰,《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之振,《汉书·古今人表》之垓,实系一人⑤。
王国维又说:
恒之一人,并为诸书所未载。卜辞之王恒与王亥,同以王称,其时代自当相接,而《天问》之该与恒,适与之相当。前后所陈,又皆商家故事,则中间十二韵自当述王亥王恒上甲微三世之事,然则王亥与上甲微之间,又当有王恒一世。以《世本》、《史记》所未载,《山经》、《竹书》所不详,而今于卜辞得之;《天问》之辞,千古不能通其解者,而今由卜辞通之,此治史学与文学所当同声称快也⑥。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指出,“商代的王位是‘兄终弟及’,这是在历史上有明文的”⑦。卜辞和楚辞所记殷先公,有亥、恒兄弟相继为王的事实,正是这一制度的反映。而《殷本纪》省去了恒,由亥的儿子上甲微直接继承王位,这正是周代父子嫡长继承制的反映。
第三,王国维的结论还不完备,楚辞学者张崇琛复据《楚辞·天问》圆通其说,恢复历史原貌。张崇琛《〈天问〉中所见之殷先王事迹》指出,《世本》、 《史记》既漏载恒一世,则不得不以微为亥子;王国维将恒补入,却又不知微即恒子。于是,张氏依据《天问》并结合甲骨卜辞及先秦有关典籍,将历来鲜为人知的殷代先王恒的事迹作了较为系统的勾勒,并考定上甲微为恒之子,而非传统所说的亥之子,可补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之不足⑧。
第四,关于殷代先公亥、恒、上甲微的系列考证,最有力的资料是卜辞与楚辞。所以,王国维进而推论,“由此观之,则《史记》所述商一代世系,以卜辞证之,虽不免小有舛驳,而大致不误,可知《史记》所据之《世本》全是实录。而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又虽谬悠缘饰之书如《山海经》、《楚辞·天问》,成于后世之书如《晏子春秋》、《墨子》、《吕氏春秋》,晚出之书如《竹书纪年》,其所言古事亦有一部分之确实性,然则经典所记上古之事,今日虽有未得二重证明者,固未可以完全抹杀也”⑨。这一典型“案例”说明,中国考古学的民族特征,决定了楚辞在考古学、古史学研究中的特殊地位;而楚辞之所以能够成为上古史研究的重要文献,则是与楚辞本身具有丰厚的上古史内涵分不开的。
作为一位失败的政治家、一位成功的政治型诗人,屈原他对楚国怀有“深固难徙”的钟爱,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深沉眷恋情绪;同时又具有浓烈得近乎狂热的从政热情,加之“自以为才能高超的贵族性、复杂政治生活的幻想性、企望权位官阶的高层性”,极其短暂的从政经历与始所未料的挫折,给屈原身心造成极大的创伤。他自以为“竭知尽忠,而蔽鄣於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卜居》),满腔的悲愤与委屈,上下求索与君王不寤的无奈,“定格”在一生的倾诉与追求之中。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曾分析屈原创作目的,“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返,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
基此,屈原的表白、倾诉、泄愤、舒愁、发问、追求,采用了常人难以理解的方式:从内心转向外物,从大地转向苍穹,从现实转向历史,通过时空转换,将视野投向遥远的神话、传说。因此,屈原作品从不涉及自己的家庭情况,从不直接涉及当时的国家大事,从来不涉及先秦诸子。反复出现的人物与事件,基本上集中于君王系列、忠贤系列,或“上陈尧、舜、禹、汤、文王之法,下言羿、浇、桀、纣之失”(班固《离骚赞序》),或“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纣、羿、浇之败”(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序》)。同时,屈原还提到了一些前贤,如挚(伊尹)、咎繇(皋陶)、傅说、吕望、宁戚、百里奚,往往吟唱他们生得其时,羡慕他们巧遇明君,向往他们有所作为;又提到不少‘前修”,如伯夷、比干、梅伯、箕子、彭咸、申徒、伍子胥、介子推,往往同情他们的不幸遭遇,佩服他们的忠而死节,追迹他们的以身殉节⑩——这就是屈原作品充盈历史要素,尤其是上古史信息的主观原因。
姜亮夫《屈原赋中的北学》曾列举十五例说明“屈赋所说到的许多史实(应当说传说),都与《诗经》《书经》《左氏传》相同或相似”,并说,“屈子所传殷的先公先王比北土所传翔实,孔子说夏殷之礼文献不足,而《天问》所传夏殷史实较儒家所传为多”(11)。郭沫若曾经这样评价《天问》:“这篇文字在研究中国的古代史上可以说是极重要的一项资料,它替我们保存下了无数古代的神话传说,可惜直到现在有好些都还不得其解”。“单就它替我们保存下来的真实的史料而言,也足抵得过五百篇《尚书》”(12)。孙作云通过十个例证说明,“作为史料的源泉,《天问》对于我们研究上古史,特别是氏族社会末期史,及从氏族发展到国家的历史,是有很大贡献的”。“根据《天问》中所保存的神话传说,可以恢复或部分地恢复我国氏族社会末期史,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甚至于一部分阶级社会史”(13)。林庚认为,《天问》是古代传说中的一部兴亡史诗,“以夏、商、周三代为中心”,从中可见“夏王朝的历史传说”、“上古各民族争霸中原的的面影”(14)。面对楚辞丰富的古史信息,郭沫若、孙作云等前辈学者均已自觉意识到:应该用考古材料与楚辞相印证,以再现古史原貌,纠正文献记载的讹错,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正如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新版引言》所述,“地下发掘出的材料每每是决定问题的关键”(15)。
要之,屈原特殊的身份、个性、遭遇、追求,决定了楚辞的政治学意义与丰富、生动的古史信息;而楚辞拥有的古史系统与“版本”价值,则使楚辞成为古史研究的重要文献。由于古史研究对考古学的过于依赖,也导致了楚辞在古史研究中的特殊地位:有时,仅仅是楚辞与考古发现互证,即能担当证史或补史之重任。
二 两千年楚辞研究史昭示:利用出土文献是学科深化的必然途径
楚辞研究肇源于贾谊与刘安,奠基于司马迁。1977年以来,这一专题研究似乎进入了饱和鼎盛期。据笔者统计,1985-1997年之间,出版楚辞研究著作132种,与楚辞有关或包括楚辞成果的著作105种;1900-1994年,发表楚辞研究论文4483篇,其中1977-1994年,发表3302篇(16)。另外,西汉至清代,有楚辞著作138种;1900-2005年之间,出版楚辞著作882种。因此,楚辞研究成果极为丰硕,累积至今,著作超过1000种,论文超过5000篇。而在选题上,正如张志岳所说,“楚辞和屈原的研究在学术领域内一直是热门,凡是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差不多都已经有人论证过,要前进一步很不容易”(17)。
但是,楚辞研究的效益,并不尽如人意:一代代的研究者都在反驳、纠正或补充前人的说法;而他们自己又受到后代或同时代人的反驳、纠正或补充。各家往往各言其是,虽然有一些证据,但合起来则相互龃龉。论文发表虽然很多,而能被广泛接受的结论甚少。每个个体总是虔诚地认为自己最了解屈原及其作品,而排斥甚至嘲弄他人成果,但同时代的人或后人对他的“独得之秘”往往不买账,目前研究中的这一困惑正是清代各逞臆说、言人人殊的延续,又可追溯到宋代义理探求在方法论上的不足(18)。对于这一特殊的学术现象,不少学者试图作过解释。崔富章指出:楚辞不是偶然发生的孤立的文学现象,而它本身几乎是楚国社会生活的缩影,涉及到许多学科,需要作综合考察,而研究者往往显得功力不足,认识不足(19)。对此,比如姜亮夫强调综合研究,其《楚辞通故·自叙》云:
欲证史、语两者之关涉,自本体本质,有不能说明,于是而必须借助于其他科学,乃能透达者,故往往一词一义之标举推阐,大体综合各社会诸科,乃觉昭晰,举凡:一、历史统计学,二、古史学,三、古社会学,四、民族学,五、民俗学,六、语言学,七、地理学,八、古器物学,九、古文字学,十、考古学,十一、汉语语音学,十二、哲学、逻辑学,乃至于浅近之自然科学,为余常识之所能及者,咸在征采之列,稍有发正,往往揉磨诸学于语言、历史中得结论,而求其当意(20)。
姜氏所述之“古史学”、“古器物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尤为学界所重,以考古新发现、以出土文献研究楚辞,愈来愈受到学者们的青睐,即王国维《古史新证》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地上之文献与地下之文物互相印证。陈直先生提出“使文献与考古合为一家”,1958年对其少作《楚辞拾遗》重加校补,其《自序》强调:
自1940年长沙战国时楚墓葬陆续被盗,后经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之正式发掘,所出铜、玉、漆、陶、竹、木各器,其花纹、绘画、雕刻,无不精致绝伦。加以前此寿春所出各铜器,去年信阳所出漆器、竹简等,楚国文物,灿然大备。知楚国由于经济之发展,反映出文化之高度成就,与屈原之作品,有互相联带不可分割之关系(21)。
于省吾在《泽螺居楚辞新证·序言》中指出:清代学者对于先秦典籍中文字、声韵、训诂的研究,基本上以《尔雅》、《说文》、《广雅》为主。由于近几十年来,有关商周时代的文字资料和物质资料的大量出土,我们就应该以清代和清代以前的考证成果为基础,进一步结合考古资料,以研究先秦典籍中的义训症结问题。换句话说,就是用同一时代或时代相近的地下所发现的文字和文物与典籍互证(22)。基此,于先生的《泽螺居楚辞新证》为了解释楚辞若干字句上的义训问题,“多半取证于周代尤其是晚周的文字或文物”。朱季海根据荆楚、淮楚之间的方言、风土、习俗等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物,从校勘、训诂、谣俗、名物、音韵等方面,对楚辞作研究,“务使楚事、楚言,一归诸楚。其有明文者,必征其始;其无明文者,亦以参伍而知之”(23)。汤炳正善于运用地下出土文物与楚辞文献相印证,为其治学之显著特征,比较突出的例子有:利用陕西临潼出土利簋铭文“岁鼎克”、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湖南长沙马王堆帛书《五星占》推算屈原的出生时间(24),利用安徽阜阳汉简《离骚》、《涉江》残句批驳淮南王刘安作《离骚》的怪论(25),利用包山楚简探讨《离骚》的艺术构思与意象表现(26),据曾侯乙墓竹简考证“左徒”与“登徒”之同异(27),据曾侯乙墓棺画研究《招魂》中的“土伯”(28),以及《天问》“顾菟在腹”别解(29),均新颖可喜,令人惊异。至于字义训诂之间,亦注重文物资料的佐证,也有不少创获(30),被有的学者称为“泰山不移”(31)。
此外,何剑熏《楚辞新诂》比较关注考古新材料,并及时采用来破释楚辞疑难,如《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畹,王逸注为“十二亩”,班固云“三十亩”,又有人说“二十亩”,莫衷一是。何氏引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孙子兵法》残简“八十步为畹,以百六十步为亩”等出土成果,证明“半亩为畹”。从而使千年争讼,一锤定音。赵逵夫有马王堆帛书《相马经》与屈赋比喻象征研究,唐勒赋残简校释与《远游》作者研究,以及泰安铜缶铭文、曾侯乙墓竹简与“左徒”研究,包山楚简、长沙铜量铭文等与战国屈氏世系研究等。汤漳平有楚墓竹简与《九歌》研究、唐勒赋残简与宋玉作品真伪研究、两周金文与楚文学渊源研究等,还出版了专著《出土文献与〈楚辞·九歌〉》。至于萧兵运用马王堆帛画研究楚辞神话、曲宗瑜利用出土文物研究《离骚》、《哀郢》的产生年代,郭在贻以马王堆汉墓漆棺画考释《招魂》之“土伯九约”,刘信芳运用秦简《日书》研究屈原生辰的宗教意义、利用包山楚简研究《九歌》等,亦值得重视。又,黄灵庚公开标举“二重证据法”,据楚汉简帛文字诠释屈宋辞赋,复取证于传世文献,著《楚辞简帛释证》,“发明前贤剩义”,在文字笺释方面,获得较大进展,对于学科建设亦具有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关于屈原生平、仕履的考述,本人也作了一系列考证,撰有专著《屈原考古新证》,发表《郭店一号楚墓墓主考论兼论屈原生平研究》、《屈原仕履考》、《屈原考古研究的时代内涵与实证基础》、《出土文献与屈原研究》、《三闾渊源考》等论文。
但从总体来看,尤其是与出土文献的丰富多彩相比,利用出土文献与考古成果研究楚辞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还处于探索、尝试阶段,了解与掌握考古信息还不够全面。据陈桐生《二十世纪楚辞考古文献著述表》,列出海内外学者著作论文,仅61种,其中还包括部分楚墓、楚简、汉墓、汉简、帛画的原始资料。但是,大量的出土文献(主要是简牍帛书)发现于20世纪70年代之后,而整理出版比较滞后,有的简帛资料出土之后,整理出版长达20年。马王堆汉墓帛书,1973年出土,至今才出版壹、叁、肆三册,专业研究成果的出版又在其后,比如《马王堆简帛文字编》,至2001年才出版。由于以上三个原因,老一辈学者未能看到及运用近30年来的数量巨大的出土文献,这是历史造成的学术遗憾。而大部分中青年学者往往理论上认为重要,而难以突破自身知识结构的局限,显得功力不足。因为出土文献涉及到多个学科,面广量大,涉及到多方面的专业知识,没有经过专门训练的学者,往往望而生畏,不敢问津。一些敢于尝试的楚辞学者,基本上是利用考古学界现成的结论,而缺乏评判鉴别的学科能力。当然,考古学、历史学、哲学等领域的专家,亦熟悉楚辞,他们也注意到出土文献与楚辞的关系、作用,但他们往往居高临下,点到为止,有时仅仅是一种怀疑与推测,比如,山东省临沂银雀山一号西汉墓出土竹简报告,涉及“唐勒赋”残简仅云:“唐勒宋玉论驭赋(疑为宋玉赋佚篇)”(32)。
三 楚文化研究的进展与困惑:楚辞与楚文化互证将获得突破
(一)“楚文化”概念研究的历史回顾与分析评判
我们期望考古发现能够解决“楚文化”研究中的疑难与困惑,从而在宏观上、背景上推进楚辞的研究。但“楚文化”研究领域同样问题成堆,可供直接采用的结论极其有限。即使“楚文化”概念的界定与解说,也颇难取得一致的意见。此仅以“楚文化”概念的研究为例,作一分析评判。
第一阶段:侧重于“精神文化”。长期以来,人们对楚的了解,是由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精神文化开始的,“精神文化”主要的载体就是楚国传统、民族精神、老庄思想与楚辞。第二阶段:侧重于“物质文化”。在20世纪20、30年代,安徽、湖南等地的楚墓陆续出土了艺术风格迥异于中原的铜器、漆器和丝织品,开始使人意识到先秦的南方,在物质文化形态上与中原有异。俞伟超认为,考古学中的楚文化,“就是一种主要由楚人创造的、有自身特征的、延续了一千年左右而分布范围不断有所变化的考古学文化”。苏秉琦指出,“楚文化就是‘楚’的文化。这个‘楚’有四个互相关联又互相区别的概念:第一,是地域概念;第二,是国家概念;第三,是民族概念;第四,是文化概念。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楚文化的内容和特征还是一个有待探索的课题。……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楚地、楚国、楚族的文化就是楚文化。因为前边三者是因时而异的”。第三阶段:探讨两种文化的关系。张正明认为,“是两个大小套合的概念。考古学上的楚文化,以体现在考古遗物上的为限,主要是物质文化。历史学上的楚文化,则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第四阶段:考古学上的楚文化研究高度繁荣,历史学上的楚文化研究相对沉寂。主要围绕考古发掘的新成就展开研究,建立了西周晚期以后的楚墓年代学。第五阶段:注意两种文化的沟通与融合,又比较侧重于“精神文化”研究。夏鼐先生提出,早期楚文化的探索应当遵循早期楚人活动的时间、空间范围,即“楚文化既属于历史时代,则一定要结合历史文献,将考古遗迹和遗物,与文献上的‘楚’联系起来”(33)。通过以上五个阶段的回顾与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楚文化的研究正处在动态发展之中,正处在学科的探讨与建设阶段。在惊人的考古发现面前,由于多学科的广泛参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逐步形成了改写历史、改写学术史的共识。学者们逐步冷静下来,理智地看待出土文物与传统文献的关系,清醒地把握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关系,这在考古学界、历史研究界是一个了不起的发展与进步。
(二)追寻楚文化渊源的效益评价
大约在春秋中期前后,以荆楚民族为主体、以楚国为中心的楚文化体系已经形成。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的楚文化,它的时代上限,一般定于春秋中期前后。楚文化的形成是以楚民族及其文化为主体的,所以,探讨楚文化的渊源,实际上是追溯楚民族文化的渊源。若追寻楚文化之源,必涉及到楚人的来源。而这一问题,无论在史学界,还是在考古学界,至今还是一个争论不休的疑案。就楚人来源来说,主要有四种不同的见解:东来说。郭沫若先生根据《令簋》、《禽簋》西周青铜器铭文,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提出, “楚本蛮夷,亦即淮夷”,是“殷之同盟国”。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中又说,“淮夷即楚人”,亦即《逸周书·作雒篇》中之“熊盈族”,“熊盈”就是楚先“鬻熊”。郭氏《金文所无考》云:楚之先实居淮水下游,与奄人、徐人等同属东国。《逸周书·作雒篇》……熊盈当为鬻熊,盈、鬻一声之转。熊盈族为周人所压迫,始南下至江,为江所阻,复西上至鄂。至鄂而与周人之沿汉水而东下者相冲突。《左氏传》(僖二十八年)“汉阳诸姬,楚实尽之”者,是也(34)。
西来说。岑仲勉《楚为东方民族辨》以楚姓之“芈”与西亚古国米地亚相附会,说楚之先祖颛顼、重黎、祝融皆为“西方人物”(35)。姜亮夫以为,《离骚》“忽临睨乎旧乡”之“乡”,应指昆仑山,即高阳氏的发祥地;“高阳氏来自西方,即今之新疆、甘肃、青海一带,也就是从昆仑山来的”(36)。
土著说。严文明提出,“长江中游……根据古史传说,那里曾是三苗部落活动的地区。该区较早有城背溪文化,其后发展为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到龙山时代则发展为石家河文化。往后的发展路程虽还有一些不甚清晰的地方,但无论如何,著名的楚文化应是从这里孕育起来的(37)。土著说认为,楚文化一直是在江汉地区土生土长起来的,其文化基础是以江汉地区各阶段民族文化为主体,同时也接受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这支文化的孕育、形成过程中,自始至终是以鄂西的沮漳河流域为中心,沮漳河一带发现的楚文化遗存属于典型楚文化(38)。土著说强调社会基本生活,重视以炊器(鬲)为核心的陶器文化。
北来说。楚文化不是本地区原始文化直接发展的结果,而是在中原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中周文化是楚文化因素形成的主体。楚文化的南下发展也吸收了江汉地区土著文化因素。楚文化的中心区域也经历了由北向南的迁移(39)。西周时期楚都丹阳在今河南淅川一带,湖北宜城楚皇城遗址是东周或春秋时期的楚郢都。北来说重视统治阶级文化,所总结的楚文化形成、楚文化基本特征都是以青铜文化为出发点,最重要的考古学证明是下寺等楚贵族墓属于归葬习俗。
相比较而言,“西来说”最不可取,既无文献依据,又无考古证明,所以大多数学者不予采纳。“东来说”有较早的文献依据,但与考古发现相悖。考古资料表明,东来说涉及的地区多属于东夷和早期吴文化范围,其文化面貌与楚文化完全没有关系,直到春秋中晚期,楚文化才真正东渐到达江淮地区,所以一般学者逐步摒弃此说。而“土著说”与“北来说”,均有文献依据与考古发掘支撑,具有一定的理由与根据。而且两说都承认楚文化是一个源流纷披、结构多元的文化系统,在其产生过程中江汉地区土著文化和中原周文化都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争论的焦点是:谁是楚文化的主要来源?两说分别有一些依据,但也有一些困惑,比如“土著说”的不足是:使用的是广义楚文化概念,而寻找楚人或楚民族之源,必须以芈姓贵族为主体;考古发现证明,长江中游地区大约从石家河文化的晚期开始,各区域、各类型文化均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土著文化发展线索基本中断;土著说以赵家湖墓地为楚文化典型墓地,并以此为基点寻找西周中期以前的楚文化遗存,一直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而“北来说”最重要的考古学证明是下寺等楚贵族墓,但不能确认丹淅或淅川一带的西周时期的楚文化遗存,仅仅侧重于传统文献与青铜文化。同时,两说也有一些相同的困难:比如寻找丹阳“城”的努力了无结局,楚都丹阳至今渺无踪迹,也没有确切的文献证明丹阳作为城或都城的性质;文献对春秋中期以前楚国的疆域范围记载不明或过于简略;考古发掘还缺乏比较系统或上下衔接的证据;还需要比较坚实的基础理论作指导。
(三)通过楚辞与楚文化互证,推进楚文化研究
在楚文化与楚辞两个密切相关、交叉叠合、又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它们各自的角色是不同的。在楚文化研究领域,楚辞作为精神文化的载体,首先是研究对象,罗运环从整体上探讨楚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影响:屈原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屈宋辞赋与中国文学;先秦楚国的巫文化和道家学说与中国的哲学与宗教;出土楚文化资料与现代学术文化(40)。四点之中,两点直接来自楚辞,一是“屈原精神”,一是“屈宋辞赋”,这都是楚辞的核心与精髓。但在更多的场合,楚辞只是一种材料,一个证据,作为论证的辅助之用。在楚辞研究领域,楚文化往往是研究的背景材料,迫寻民族特色的渊源,进一步推理、分析的前提,展开论说的主要根据。其次,两个领域的相互关注情况也有明显的差别。在楚文化领域,对于楚辞,他们直接发表意见,很少关注楚辞学者的意见与楚辞学界的研究动态;对楚辞学者的研究成果,很少采用。而在楚辞研究领域,整体上高度重视楚文化研究动态与成果,对楚文化的认识与把握基本上采用“拿来主义”,以现成的结论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前提或重要证据。我们提倡楚辞学者要充分利用楚文化研究成果,甚至批评楚辞学界在整体上对楚文化关注不够,但与楚文化领域对楚辞研究的关注相比,则显得相当主动、自觉、积极,而楚文化领域则比较轻视,乃至于漠视,还没有这样一种意识。
现在,我们应该转变观念,强调楚文化与楚辞双向互证,推进两个领域的同步发展。以往,我们比较多地分析了利用楚文化的成果推进楚辞研究的理由与方法,这里我们着重谈谈利用楚辞研究的成果,推进楚文化研究的话题。
其一,楚辞本身就是楚文化的重要内容。首先,楚辞是楚文化中“精神文化”的集中代表,从《离骚》、《九章》等自传性政治抒情诗中,可以抽象出屈原精神的内容与特征,比如屈原的忠君爱国、独立不迁、上下求索、好修为常等的追求。屈原力图将执著不舍的深切眷恋、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坚忍不拔的求索精神、好修不懈的崇高品质,“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种超越现实的理想模式、完人模式,是屈原的伟大、独特之处,亦是其痛苦、悲剧之源。其次,楚辞也是楚文化中“物质文化”研究的文献依据。其中《天问》、《九歌》、《招魂》等作品,可以与楚系青铜器及其铭文、楚简互证,还可以作为破译考古发掘成果的钥匙与内证。这对于从物质的、社会的、精神的角度研究楚文化,丰富楚文化的研究内容,破译楚文化的疑难,具有无法替代的学科意义与实践效果。其二,楚辞研究有助于楚文化渊源的探索。比如,从楚辞的角度看“土著说”与“北来说”的争议,则结论是明显的,因为《离骚》开头即云“帝高阳之苗裔兮”,而《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又云“楚之同姓”,与《史记·楚世家》、《大戴礼记》、《世本·帝系篇》记载吻合;包山二号楚墓竹简、望山一号楚墓竹简、葛陵楚墓竹简记载祭祀均有“楚先老僮、祝融”等,更能证明楚辞之可信。而且,楚国贵族屈、景、昭三家,均与楚王同姓,景氏源于楚平王,昭氏源于楚昭王(41)。这与王光镐唯有采用“有芈姓楚人所创造的、以楚国公族集团为代表的文化为典型楚文化”的结论(42),也是相得益彰的。其三,大量的简帛佚籍出土及整理研究,推进了楚辞与楚文化的互证与发展。随着大量的简牍帛书的不断出土,“学术史”探讨与估价的问题也就自然提出来了。李学勤提出,通过出土简帛的整理研究,竟使被认为最“物质”的考古学同最“精神”的学术史相沟通,这或许是有希望的研究方向。“把考古学的成果与学术史的研究沟通起来”,“把考古学、古文字学的研究方法,与文献学、历史学真正打成一片,一方面以学术史已有的成果去考察衡量新发现的佚籍,另一方面则以考古学的知识和方法来整理研究简帛,同传世文献对比参照,从而推进学术史研究的发展”(43)。据研究,与楚辞研究有关的出土文献有:长沙子弹库帛书帛画、包山楚简、望山楚简、郭店楚简、阜阳汉简《离骚》《涉江》残简、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简《唐勒》赋残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为吏之道》所附八首韵文、东周时期的楚国青铜器铭文等(44)。与楚辞属于同一系统的文献有:长沙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古本《易经》、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四时》、《天象》、《月忌》、长沙子弹库帛画、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山东临沂银雀山所出《尉缭子》(45)。与屈原、宋玉等作家生活大致同时的出土简帛(战国中期至白起拔郢,约前390—前278年)有:子弹库楚帛书、信阳楚简、九店楚简、慈利楚简、郭店楚简、上博楚简、香港中文大学购藏楚简等。
当然,考古发现虽多,真正与楚辞、屈原直接有关的材料极其有限,目前只有:1977年出土的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竹简,其中有《离骚》残文四字、《涉江》残文五字。1972年山东省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竹简,其中有《唐勒》篇残简。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竹简、1978年湖北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竹简,其中的有些祭祀对象与《楚辞·九歌》祀主相同。而大部分材料属于“背景”或“比较”,乃至“推断”、“猜测”性的。所以楚辞学者使用考古学成果,应从三个层面切入:第一,不再仅仅是“拿来”,而是将人家的结论“拿来”作“二度研究”,评判得失,甄别是非;第二,自己直接“开发”常人不注意但又颇有价值的资料;第三,参与考古学、古文字学、楚文化领域的论争与研讨,围绕楚辞而形成的出土文献、传统文献与学术史的学术圈,通过楚辞与楚文化的互证研究,破译楚辞的许多历史疑案,抽象出一种既相关又相对独立的古史系统,解决古史学、考古学、楚文化研究中的困难。
注释:
①⑥⑨王国维:《古史新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页、20页、52-53页。
②徐文靖:《管城硕记》,卷之十六,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85页。
③⑧张崇琛:《楚辞文化探微》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页、119-128页。
④⑤王国维:《观堂集林》,第二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98页。
⑦(15)见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郭沫若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页、4页、644页。
⑩周建忠:《屈原思想:有儒有法,然非儒非法》,《楚辞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7-50页。
(11)辽宁省文学学会屈原研究会、辽宁师范大学科研处、中文系:《楚辞研究》,1984铅印本,第6-7页。
(12)《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四卷,《历史人物·屈原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9-30页。
(13)孙作云:《天问研究》,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2-35页。
(14)林庚:《天问论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3页。
(16)周建忠:《关于楚辞研究的跨世纪思考》,《社会科学报》1997年3月20日。
(17)戴志钧:《读骚十论·序》,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18)周建忠:《关于楚辞研究的对象审视与历史回顾——楚辞研究一百年》,《贵州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
(19)崔富章:《楚辞研究史略》,《语文导报》1986年第10期。
(20)姜亮夫:《楚辞通故》,第一辑,齐鲁书社1985年版。
(21)陈直:《文史考古论丛》,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22)于省吾:《泽螺居诗经新证》,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34页、235页。
(23)朱季海:《楚辞解故》,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3年版,第4页。
(24)汤炳正:《历史文物的新出土与屈原生年月日的再探讨》,《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第4期。
(25)(26)(27)(28)汤炳正:《屈赋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426-428页、48-57页、271-280页、261-270页。
(29)汤炳正:《从包山楚简看〈离骚〉的艺术构思与意象表现》,《文学遗产》1994年第2期。
(30)汤炳正:《楚辞类稿》,巴蜀书社1988年版。
(31)黄灵庚:《〈楚辞〉文献学百年巡视》,《文献》1998年第1期。
(32)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33)夏鼐:《楚文化研究中的问题》,《江汉考古》1982年第1期。
(34)郭沫若:《金文丛考》,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4页。
(35)岑仲勉:《两周文史论丛》,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61页。
(36)姜亮夫:《楚辞今绎讲录》,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29、41页。
(37)严文明: 《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
(38)(39)陈振裕:《楚文化与漆器研究》,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4页、199页。
(40)罗运环:《楚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影响》,《光明日报》2000年6月2日。
(41)周建忠:《三闾渊源考》,《江汉论坛》2005年第2期。
(42)王光镐:《楚文化源流新证》,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2-182页。
(43)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400页。
(44)刘彬徽:《湖北出土两周金文国别年代考述》,《古文字研究》第十三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9-351页。李零:《楚国铜器铭文编年汇释》,《古文字研究》第十三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3-397页。李零:《论东周时期的楚国典型铜器群》,《古文字研究》第十九辑,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36-177页。
(45)江林昌:《楚辞与上古历史文化研究——中国古代太阳循环文化揭秘》,齐鲁书社1998年版,第314-315页。
标签:楚文化论文; 楚辞论文; 考古论文; 出土文献论文; 屈原的故事论文; 离骚论文; 屈原论文; 天问论文; 山海经论文; 招魂论文; 竹书纪年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