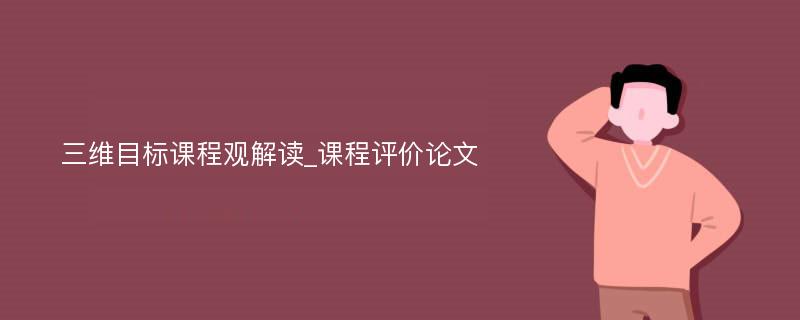
三维目标的课程观诠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目标论文,课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的教育界,自20世纪中期以来主要是受苏联凯洛夫(И.А.Каилов)教育学思想的影响,采取的是“中央集权课程行政”模式,以致长期缺乏“课程”的概念,对课程概念的理解片面。高师院校至今一直未开设课程理论的课,广大基础教育教师课程意识和课程理论缺失。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教育界经历了教育研究范式的转换,经历了“概念重建”的过程,课程观从“课程开发”走向“课程理解”,由此,课程观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在我国教育界,“课程”逐渐引起了注意,尤其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来,课程已成为广泛关注的热门话题。当代课程研究的丰富成果被大量地译介到国内,并且被吸纳到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之中。但是,由于课程定义的多样性,课程理解的多元化视角,反映了课程观的丰富。而不同的课程观,又支配着不同的课程设计、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因此,本文拟从课程观的维度,诠释课程三维目标,揭示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以进一步深入理解三维目标的课程观内涵。
一、课程观与课程观的范式转换
什么是课程观?课程观是人们对课程的基本看法,具体来说,课程观需要回答课程的本质、课程的价值、课程的要素与结构、课程中人的地位等基本问题。[1]
我国在一段时间里,把课程看作教学内容,认为“课程即学科”。例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定义课程为:“所有学科(教学科目)的总和,和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各种活动的总和,这通常被称为广义的课程,狭义的课程则是指一门学科和一类活动。”《教育大词典》界定课程是:“为实现学校教育目标而选择的教育内容的总和。包括学校所教各门学科和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课外活动;泛指课业的进程;学科的同义语,如语文课程、数学课程等。”这种课程观所导致的结果、就正如钟启泉先生所尖锐地指出的:突出了学科知识的封闭性、静止性和权威性,忽略了课程的开放性、生成性与主体性,这就必然导致课程实施中的“知识灌输”。[2] 教师是知识权威的代言人,严格地控制着课程的组织与开展;学生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学习的任务就是把作为结论和结果的现成的知识加以记忆,在考试时能尽量完整准确地复现出来,学生个人的体验和探究被抹杀了。然而,知识的形成、发展、创新才是更重要的价值所在。
观点是如何形成的?课程是什么?正如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课程观的代表人物多尔(William E.Doll,Jr.)所认为的,观点不是“在那儿的”,不是一下子就完全呈现出来的,也不是逻辑地统合在一个界定好的系统里。相反,它们是从缺少探索的联系之中、从半透露的可能性中逐渐创造出来或“发酵”出来的。课程实质上必须致力于促进这一“发酵”的过程,而不应强加一种预定的和没有意义的模式。多尔强调:我相信泰勒原理,奠定这一模式的泰罗科学效率运动,以及二者所引发的行为主义课程运动都“错误地认识了这一问题”。从关于教育作用以及对发展如何产生的错误观念出发,我们采用了一种不恰当的课程概念——一种深深根植于现代主义的概念。泰勒、泰罗和行为主义运动没有面对酶的问题,而是否定、越过或忽略它。但在酶之中,或舍恩的团块、普利高津的混沌(这里的混沌指混乱无序,而不是指混沌理论——作者)、杜威的问题、皮亚杰的不平衡,或库恩的异常之中不仅存在着发展和转变的种子,而且存在着生活自身的种子。视课程为转变的过程意味着利用酶来发展精确和概括化。[3]
派纳(William F.Pinar)是“存在现象学”课程观的主要代表,是概念重建主义课程范式的首席发言人。他提出的“存在经验课程”是“具体存在的个体”的“生活经验”的解释。莫尼尔(E.Mounier)生动地描绘:“一千张照片叠加在一起并不能得到一个行走、思维、有意志的人。”学习者是课程的中心,课程可以被合理地看作主体性的生成和个性的解放,这就彻底地摒弃了以学科内容为中心的传统课程观,认为个体与社会二者是内在统一的,个体是作为独立的主体而参入社会的,个体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是主体间的交往关系,即“交互主体关系”,所由以形成的是“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教学和课程是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对话”过程。“文本”是一种纯粹的手段和工具,绝对服从于主体的生成、自我的超越和个体的解放,它本身没有真正的独立性。因此,传统意义上的“课程”在“存在现象学”课程观的理智框架中被彻底地消除了。[4]
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批判课程论,阿普尔(M.W.Apple)等人认为,课程作为“反思性实践”,其内涵为:课程并不只是一套要实施的计划,而是由一个行动过程所构成的,在这个行动过程中,课程计划、实施和评价是相互联系并整合于一体的;课程必须在真实的而非虚假的学习情境中与实际的而非想象中的学生一起构建;学习必须被确认为一种社会性行为,教与学是师生间的一种对话关系,而不是一种权威关系;知识是一种社会性建构,通过学习行为,学生群体成为其自我知识建构过程中的积极参与者,对所有知识作出批判是“反思性课程实践”的题中应有之义;把课程看作是师生共同参与的意义创造的过程。[5]
布洛克(Alan Block)竭力反对现代课程的控制观。课程应该被理解成是一种机会,一种迷失的机会。布洛克认为,课程的功能在于带领学生离开机械、单调的、预先设定的、清晰可见的路线,而进入“迷途”,转向自己身份的创造。重视学生如何学习、如何提问;重视引导他们寻求自己的解答;重视让学生学会质询符号,发现其所表达的意义;重视鼓励学生学会提问,而反对学生无条件地死记硬背,做一个习惯于接受的“容器”。[6]
总之,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课程领域发生了课程观的范式转换,从“课程开发范式”走向“课程理解范式”,这种课程概念的重建突出地表现在:反对技术理性的价值取向;反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反对认识论上的“基础主义”。
二、课程观的范式转换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当前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力图实现三大转型:课程政策从“集权”到“放权”的转型;课程范式从“科学中心主义课程”到“社会建构中心课程”的转型;教学规范从“传递中心教学”到“探究中心教学”的转型。[7] 课程观的范式转换在新课改的多个方面得到了体现,尤其在课程标准的“三维目标”中得到了具体的落实。
1.在课程设计中实现体验课程
今天,我们试图重新理解儿童的主体性,着眼于儿童、自然、社会整体有机统一的人的“超越经验”。由此确立起来的体验课程,揭示了人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的根本规定,也因而揭示了个性的根本规定。它赋予“经验”以个性意义,以个性发展为依归,是一种“个性化课程”。体验课程也不与经验课程、既有的文化模式相对立,但只是在体验课程的个性追求中经验课程、既有的文化模式才找到了意义之源。[8] 这种课程是对传统的学科中心课程和儿童中心课程的超越。课程的设计也从泰勒(Ralph W.Tyler)的目标模式转向了过程模式,关注学生学习的“过程”与“方法”,课程设计的焦点集中在学生学习体验的获取上,是一种充分体现学生“如何学”的课程,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得到了全面的体现与真正的实现。任何科学知识的产生和发展是要受到社会的种种因素影响的,社会因素不仅影响着科学知识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而且也决定着人们对它的认识程度、接受的范围以及其所能发挥作用或功能的大小。因此,课程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具有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9] 不认识到这一点,就无法认清课程的本质,也会使学生在课程面前丧失自我,丧失其应有的主体性、自主性和能动性。
2.在课程实施中实践新型的学习方式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明确指出:“改变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在科学中心主义课程观中,科学知识被认为是“客观的”、“绝对正确的”、“价值中立的”,这样的知识当然不容置疑,因此可以被用来进行强制性的传递和接受,其结果,学生的质疑精神、探究意识、批判性思维和学习中的主体性、自主性被渐渐地抹杀了。而在“存在现象学”的课程观看来,学习者是课程的中心,课程可以被合理地看作主体性的生成和个性的解放,这就彻底地摒弃了以学科内容为中心的传统课程观。因此,新课改大力提倡学生学习方式的变革,即实施自主学习、探究学习和合作学习。这是对从洛克(John Locke)、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时代以来将学生看成是一张白纸、一个空的容器,教学就是教师单向的传递与灌输,对从赫尔巴特(J.F.Herbart)到凯洛夫课堂教学“五环节”的教学规范的一种彻底的否定。
3.在课程评价中实行发展性评价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强调:建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评价体系;建立促进教师不断提高的评价体系;建立促进课程不断发展的评价体系。要“改变课程评价过分强调甄别与选拔的功能,发挥评价促进学生发展、教师提高和改进教学实践的功能”。新课程提出在具体的课程评价中实行真实性评价,如表现性评价、学生成长记录袋评价等。真实性评价具有共同的特点:[10] ①评价既指向学生学习的结果,也指向学生学习的过程,凸显评价的诊断与服务功能,而不是选拔与区分功能。②强调在现实生活(或模拟现实生活)的真实情境中,给学生呈现复杂的、不确定的、开放的问题情境,以及需要整合知识、技能的活动任务来对学生进行评价;评价重在考查学生在各种真实的情境中使用知识、技能的能力,而不是重在考查学生对知识信息的积累与占有程度。③任何一个真实性评价都必须事先制订好用以评价学生的“量规”或“检核表”;学生应该提前知道评价的任务及具体标准,而不是象传统的测验那样需要保密。④真实性评价承认个体差异,主张对不同的学生提供不同的评价策略,以适应各种能力、各种学习风格以及各种文化背景的学生,为展示他们的潜能与强项提供机会,而不是忽视学生的个体差异而且是用以找出学生的弱点。⑤评价通常整合在师生日常的课堂活动中,成为教师教学、学生学习的一部分,学生是评价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是学习的一种形式,而不再是被动的测验接受者。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各个方面,都体现了当代课程观范式转换所带来的影响,当我们面对新课改的时候,不能不正视课程观的范式转换,因此,“实现课程观的转型,是贯彻新课改精神的内在要求与必然选择。”[11]
三、后现代课程观与三维目标的诠释
国际上课程理论的变革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概念重建,这种课程理论的概念重建与后现代状态的出现是吻合的,尤其与20世纪60年代末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导致人类的自然观、科学观的转变相一致,以重建后的课程理论与观点而构建起了一种新的课程范式。尽管这些课程范式是形形色色的,或许还是不成熟、不完美因而受到指责和批评,但它们都反映了后现代状况的要求和后现代的特征,这些特征表明了这些课程范式的清晰的后现代方向。作为一种世界性文化思潮的后现代主义,其理论建树和思维方式是不容忽视的。如何对待后现代课程观,钟启泉先生以宽容的态度和高屋建瓴的远见卓识指出:我们为什么不能从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资源中汲取“尊重他人、倾听他人”的“后现代意识”和“开放心态”呢?我想,后现代主义批判归根结底只能促进而不会阻碍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从后现代课程观的视角观照新课程三维目标,诠释三维目标所包涵的当代课程理论与观点的内在意蕴,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有利于我们认识新课改对待知识教育的态度,使我们能正确地看待三维目标的作用和地位,便于我们与传统的教育目标相比较而认清其内在的联系,同时又实现了一种超越或是在新的层面上的一种“返魅”。
1.知识与技能目标的理解
我国近代的学校教育滥觞于19世纪后期的西学东渐,到了20世纪中期,又实行全盘苏化。但至今一百多年以来,基本的课堂教学模式可谓陈陈相因,香火不断,尽管期间花样有所翻新,但课堂教学的本质并无根本的改变。其基本的教学规范就是传递、灌输,对学习者行为实施控制。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这种课堂教学的模式,并不是要“废止课堂教学”。而且要“提高科学知识教育的质量”,学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学习科学知识”也是毋庸置疑的。三维目标中把知识与技能目标放在首位,显然并没有把知识与技能的学习排斥于目标之外,也没有轻视它们在教育、教学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在于知识与技能的学习在教学中是如何完成的,学生在知识与技能学习的过程中处于什么地位。
后结构主义课程观认为:在课程学习中,知识不是被动灌输的,学习的过程就是主体原有的知识结构与客体相互作用、创建意义的过程。知识是建构的,学习是通过建构过程来完成的。这种知识的生成并不是单纯个人的事件,而是在学习共同体中通过与他人彼此之间心灵的交往作用建构的。因此,教育者应引导学生对其所认识的理论要具有自我意识,并以对话而不是以传输的方式学习理论,通过学生参与批判性的讨论、全班共同协作和后学科探询,而不是按部就班的单向讲授进行教学,整个教学过程中对课堂上使用的教材和教师的权威都始终提出质疑。
格林(M.Green)认为在传统的教学活动中,学生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他们只是旁观者,而不是洞察者;只是旁听者,而不是领悟者”。格林指出这种状况的形成归结于人类科学技术工具理性的膨胀。她提出运用现象学的方法,提升自我意识,教学的出发点不在于既定知识结构的传递,而在于师生互动中理解其世界,创造知识。学习者不是知识的接受者,而是意义的创造者,课程与教学旨在使学生以活生生的知识来解释其世界。认为学生在寻找意义的过程中,他们把外部世界移入到自己变化多端的经验世界之中,凭借自己的清醒意识重新诠释和创造学习题材。当然,这种自我意识觉醒需要与外界事物及他人有所关联。
2.过程与方法目标的解读
有人提出这样一种说法:“教学的本质和功能,就是把人类历史认识所获得的科学成果的精华,挑选出来,组成课程,让学生掌握,以发展和培养他们的素质。”“青少年学生个体的发展,主要是通过掌握人类长期积累的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已有的成果而实现的,也就是通过学习科学知识(而且主要是书本知识)而实现的。”我们需要继承人类所创造的优秀的文化遗产,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作为“成果”形态的知识,如何看待?如何呈现?学生如何获取这样的知识?
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有机哲学的核心观点之一是形成性、过程性,这在教育上的隐喻是很有意义的。知识是什么?知识不仅仅是对人类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吸收。知识并非静止不变,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形成的过程。而且,知识的形成、发展、创新才是更重要的价值所在。因此,我们对课程的认识,要更加重视过程而不是结果,这是智慧的第一步,也是迈向转变的重要一步。[12]
对于课程的本质,在派纳看来,传统的课程研究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错误地诠释了“课程”的意义。从词源学的角度看,currere是curriculum的拉丁文词根,是动词,原意是“在跑道上奔跑”,回归到currere,将使情况发生很大改变。Currere不再强调静态的“跑道”,而是强调在跑道上奔跑的动态过程和经验积累,它成为一种过程、一种活动,一种内心的旅行。这样的课程必须强调培养个人在重塑自己的人生经历方面的能力。因此,课程的作用不在于预定的经验而在于转变已有的经验。课程不是一种“包裹”(package),而是一种过程,是以局部情景中特定的相互作用或交互作用为基础的对话和转变的过程。课程的意义不是单方面呈现的或传输的,而是通过对话性交互作用所创造的。
伯恩斯坦(B.Bernstein)也认为:整合课程使各种不同知识之间的界限显得模糊,学校知识与社会日常知识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模糊,在教学中学生的权力增加而改变了原有的权威关系。这种课程“使人们对于知识是如何被获得的形成了另一个不同的概念”,并且“不太强调获得知识的状态,而更加关心建立知识的过程。”[13]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的阐释
有论者认为:“如果根本没有知识或轻视、削弱知识,那么学生的发展更无从谈起,主动学习态度、能力、情感、价值观等等,便无源无本。”但强调学习态度、能力、情感、价值观等等,并非就是否定或轻视知识教育,而时至今日,能力、态度、情感与价值观等等不能不引起教育的关注。
生态后现代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斯普瑞特奈克(Charlene Spretnak),其理论的科学基础是后现代科学,强调的是物质与意识,事实、意义与价值的联系而不是割裂。约翰·米勒(John P.Miller)的《整体课程》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研究体现了独特的生态关怀,认为在工业革命以后,人们开始片面强调分割和标准化,结果导致了生活的支离破碎。这种支离破碎性又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经济方面,经济的发展与环境分离,忽视对环境的影响,最终造成难以挽回的生态灾难;在社会生活上,工业化社会的人们集中居住在拥挤不堪的大城市,大家彼此隔绝,相互提防。暴力已上升为城市生活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人们抽烟、酗酒、吸毒。虐待自己,也遗弃、摧残、虐待老人、孩子。米勒认为,在很多情况下,正是教育的误导使人的身心发展相分离;在文化方面,缺少认同和共享,难以形成一致的价值观,人们无法在一些社会基本问题上达成共识。
人本主义课程观认为“除了纯粹的智力发展外,情绪、态度、理想、雄心、价值,对于教育过程来说也是应当关注的正当的领域,还要发展自尊和尊他的思想意识”。人本主义课程的核心是自我实现的人格理想。这种人格的中心课题是“情意发展”(情绪、感情、态度、价值)和“认知发展”(理智、知识、理解)的统一。惟有借助这种统一,整体的人格成长才有可能。麦克尼尔(J.D.McNeil)和辛普森(E.L.Simpson)认为:人的存在,就是认知与情意相统一的整体的人格,所以,认知学习与情意学习必须统一;学习是以内部动机为基础的,所以,课程内容必须同学生的要求、兴趣、爱好相适应,学习是一种探究活动,重点应从教材转移到每个学生的学习过程;学生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人而存在的,教育内容必须同社会合拍。尽管人本主义课程在20世纪70年代受到席卷美国的“恢复基础”的教育运动的批判,但人本主义课程观认为基础也应当包括能力感觉、价值阐述、积极的自我概念、改革的能量和开放的个性——形成“自我指导学习”的课程模式。
在新课程的背景下,我国的课程与教学也面临着“概念重建”,课程观相应地也必须有一个转向。本文试图从我国当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出发,从课程观转向的维度,对课程的“三维目标”作出诠释,希冀理解“三维目标”丰富的课程观转向的内涵;从课程观的视角,认识“三维目标”的整体性、全面性、统一性与时代感,而不是人为地加以割裂甚至相互对立起来。“三维目标”与传统教育目标之间既有内在联系,但在本质上又无疑地实现了一种超越。“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改革的步伐有时会放慢,改革的轨迹有时也会弯曲,但终究是要向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