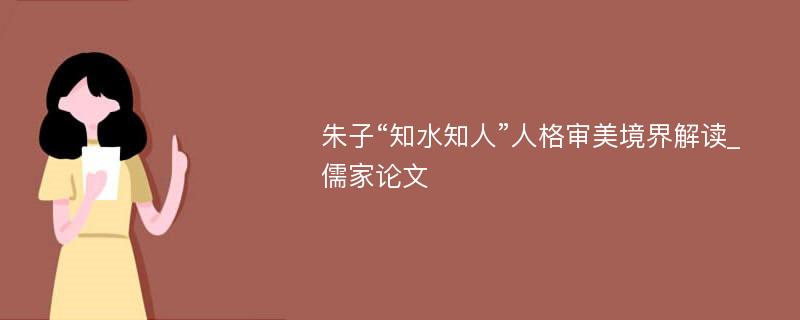
朱子“知者乐水”人格审美境界之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者论文,人格论文,境界论文,朱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非常悠久和深刻的人文内涵,而作为审美主体,中国传统文人对水的审视绝不仅仅是纯客观的、外在的,而融合在其自身对人格境界的理解之中。大体上,中国传统文人的“观水”是一种物我交融的移情观照,其“乐水”更是一种天人合一的人格境界和人格理想之投射。这一点在儒家审美文化中体现得最为突出。
一 “知者乐水”的“比德”传统
天人合一的元典文化心理与观念,使中国人在观照自然时总是将主体自觉不自觉地融于客体之中。中国人对自然的关注和审视,经过了由原始的顶礼膜拜、实用理性的功利观照和道德精神象征乃至对山水形态的视听愉悦和自由领悟几个阶段,而其基本审美取向是物我交融、情景合一、主客互渗的移情观照。中国人的自然审美观照从来就不曾满足于物我对峙、外在的纯形式描述和观赏,而总是从对自然景物外在形式的观照进入对其内在意蕴和意趣的探究,再进入物我交融的体验,乃至通过礼赞自然、怡神悦志而获得对宇宙人生的审美和伦理顿悟。于是,“比德”从一开始就成为中国人自然审美观照的基本视角和基本态度。
有学者认为,“比德”观最早见于《管子》,管仲曾认为禾“可比于君子之德”。更有学者认为,“比德”观首先见之于中国的玉文化,如《礼记·玉藻》提出“君子于玉比德焉”;《荀子·法行》曾借孔子之口说:“夫玉,君子比德焉。温润而泽,仁也;柔而理,知也;坚而不屈,义也;廉而不刿,行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远闻,其止辍然,辞也。”
其实,以水“比德”的观念更早于以玉比德或以禾比德,也使用得更为广泛。水是人类的生命源泉,人类生活一开始就与水紧紧连在一起。与其他各民族一样,中华民族在原生时期就有着种种与水相关的神话,其中最著名的是“大禹治水”。至中华元典文化形成的“轴心时代”,儒家和道家已经把对水的观照与人自身的生命、精神状态联系起来。儒家有“君子见大水必观焉”的说法,道家则有“上善若水”(老子)的哲言和“望洋兴叹”(庄子)的寓言。这几种说法有一个共同的内在基因和指归,即从对水的观照中体悟宇宙真谛和人生境界。老子为何说“上善若水”?因为“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注:《老子》第八章。)最充分地体现了道家所理解的宇宙真谛、所追求的人生境界。庄子“望洋兴叹”寓言则启悟水外有水、天外有天的宇宙人生哲理,引导人们崇尚更为广博无限的人生境界。儒家之所以强调“君子见大水必观焉”,也正有着这种强烈的人格伦理动机。
最典型地反映中华民族传统山水审美观照观念的,是孔子“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命题。语出《论语·雍也》:“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表面上看,孔子只是指出了自然审美观照中的一种现象,即不同道德审美主体对自然美的欣赏有各自的喜好。知者为何乐水,仁者为何乐山?孔子没有明确解释,但似已规范了这样一种对应的审照尺度,即:“知者”所以“乐水”,是因为水具有川流不息的“动”的特点,而“知者不惑”(《论语·子罕》),捷于应对,敏于事功,同样具有动的特点;“仁者”所以“乐山”,是因为长育万物的山具有博大宽厚、巍然不动的“静”的特点,而“仁者不忧”(《论语·子罕》),宽厚得众,庄重沉着,同样具有静的特点。按程伊川的说法,是“乐山乐水,气类相合”。(《朱子语类》卷三二引)这里的“乐”,不仅是对审美客体的被动感受,还包含着审美主体对自然审美对象的一种主动性选择;自然现象能否成为特定的审美对象,很大程度取决于它是否符合审美主体的道德品质和观念。从中可以给人们这样的启示:一定的自然对象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喜好,是因为它具有某种与人的精神品质相似的形式结构的缘故。因此,当代有学者以西方“格式塔”派同形同构说的完形理论来解释,认为这实际是在美学史上第一次揭示了人与自然在广泛的样态上有某种内在的同形同构、从而可以互相感应交流的关系。(注: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1卷,14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这是很有道理的。它使我们在这种看似较为简单的比附观照中,发现了远为深刻的审美文化心理和美学观念;它表达了中华民族传统审美文化对审美主客体关系的独特理解,具有相当深刻的民族文化心理基础。值得重视的是,这种山水比德观念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国古典美学史上具有相当广泛和深远的影响,以致成为中国传统文人自然审美观照的一种基本尺度。孔子以后,战国和汉代学者纷纷对“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这个命题进行解释和阐发,形成了所谓的“比德”理论。《管子·水地篇》、《孟子》、《荀子·宥坐》、《尚书大传》、《韩诗外传》、《说苑·杂言》均有相关的记载和论述。鉴于题旨,本文着重关注的是古人对“知者乐水”的闸释和理解。
据有关学者考察,《论语》中“知”字共出现111个;除作动词用的“知”以外,作名词使用的“知”都来源于求知、好学的品德。(注:敏泽:《中国美学思想史》第1卷,139页,济南:齐鲁书社,1987。)《论语》中多处记载孔子及其弟子对水的道德化礼赞,大体都与知者的道德品质和精神气象相关。如《论语·子罕》记云:“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表达了孔子通过对川流不息的观照所领悟到的宇宙永恒之原理。而所谓“君子见大水必观焉”,则成了中国儒家和其他传统文人修身养性的至真法门。且看古人如何论述水之品德:
《韩诗外传》卷三称:
夫水者,缘理而行,不遗小间,似有知者;动而下之,似有礼者;蹈深不疑,似有量者;障防而清,似知命者;历险致远,卒成不毁,似有德者。
西汉刘向《说苑·杂言》则有更为详尽的论述:
子贡问曰:“君子见大水必观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无私,似德;所及生者,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理,似义;浅者流行,深者不测,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绵弱而微达,似察;受恶不让,似包;蒙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万折必东,似意:是以君子见大水必观尔也。”
“夫知者何以乐水也?”曰:“泉源溃溃,不释昼夜,其似力者;循理而行,不遗小间,其似持平者;动而下之,其似有礼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其似勇者;障防而清,其似知命者;不清以入,鲜洁而出,其似善化者;众人取平,品类以正,万物得之则生,失之则死,其似有德者;淑淑渊渊,深不可测,其似圣者;通润天地之间,国家以成:是知者所以乐水也。《诗》云:‘思乐泮水,薄采其茆,鲁侯戾止,在泮饮酒。’乐水之谓也。”
这种论述已在孔子“知者乐水”说基础上所作了进一步发挥。君子所以见大水必观,是因为观水几乎可以启悟人们安身立命、处世行事的所有重要伦理品质;知者所以乐水,不但缘于知者本身有似于水,水与知者具有某种异质同构的品质,还在于水之品性和形态“通润天地之间”,涵盖着更为广泛的道德品质。借助对于自然现象——水的观赏和品味,获得对于宇宙真理和人生伦理的启悟,这又正是知者的特点。
以水“比德”的观念也见于《周易》,其“坎卦”有云:“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坎为重卦,故称习,有孚即有信。坎为水,水的性质是流,向下流,无论什么情况下,流的性质是不会变的,这就是有信。“维心亨”,水本无心,说水有心,只是说水的行动总是不停地流向底处,像有心在支配它的行动一样。水流向大海,经历千山万壑,形体常处在艰险之中,而心则是亨通的。也就是说,水的性质是不变的,永远奔腾,亨通而不为险阻所止。“行有尚”,程传释为行“能出险有可嘉尚谓有功也”,行能出险即是水之智慧。彖云:“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流与盈相反,流是说水就下而向前行,盈是说水满盈而不流。说水流而不盈,其实是水流而不止的意思。水按其本性永远是流的,纵然是在险难中也是不舍昼夜地流,“而不失其信”。(注:金景芳等:《周易全解》,223~224页,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君子学者正可以从水之品性中悟出知者立身处世的道德精神。
二 朱子对“知者乐水”说的哲理化、人格化阐释
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以其深刻而严密的哲理思辨,对孔子和儒家的“乐山乐水”说作了新的阐释。这一阐释在继承孔门山水比德说对自然审美对象作人格化观照这一理念基础上,达到了更高的哲理水平、更深的人格内涵。所谓更高的哲理水平,主要体现在朱熹对山水之象、仁知之体、动静之状、乐寿之效作了更具哲理性的逻辑层次之分,并且对仁知动静的体用分合关系作了更为辩证的阐释。所谓更深的人格内涵,指朱熹对山水品性的人格观照达到了更加深刻的程度。
《四书集注》是儒家经典的最权威阐释,表达了朱熹对儒家思想的最成熟理解。他对孔子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最精切解释,即见于《论语集注》:
乐,喜好也。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动静以体言,乐寿以效言也;动而不括故乐,静而有常故寿。
释“乐”为“喜好”,指的是一种心理趋向和情感反应;所喜好的对象是山和水即自然审美对象,这种喜好当然包含审美感受。不过,在儒家和朱熹眼里,这种喜好不是纯粹的自然审美感受,而是深刻地结合着对人格境界的融会与认同。朱熹在与门生讨论“知者乐水”章时指出:“圣人之言,有浅说底,有深说底,这处只是浅说。”(《朱子语类》卷三十二。以下所引朱子语均见该卷)所谓“浅说”,在这里可理解为形象地说;即通过对自然现象的观照和比拟来形象地表述圣贤道理,体会生命境界,这其实是一种自然美育的方法。所以,尽管孔子的立论和朱子的阐释重心都并不在美学,但确实具有美学的意义。知者为何乐水?是因为其“有似于水”。这种“有似”既包含着外在的人格状态,更潜在于内在的人格素质。“周流无滞”既有内在素质意味,又有外在形态形容,“达于事理”则主要是内在素质之透视。“仁者乐山”也当如是观。朱熹又引包咸注释“知”:“知者,乐运其才知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已”,“日进故动”;释“仁”;“仁者如山之安,固然不动,而万物生焉”,“无欲故静”。他又认为,“仁只似而今厚重底人,知似而今伶俐底人。”仁者似山一般稳重厚实、执着不移,不浮躁,不迎势,能安贫乐道,他表现出的德性主要是静的:知者似水一般灵活机动、周流无滞,不固执,不呆板,能随机应变,他表现出的德性主要是动的。
所谓“动静以体言”之体,既是本体,又是体状;“乐寿以效言”之效,既是效应,又是效能。这里不妨留意朱熹对山水、仁知、动静、乐寿逻辑层次关系的区分,体现了理学大师独特的哲理思辨。有学生问“知者乐水章”:“看这三截,却倒。似动静是本体,山水是说已发,乐寿是指其效。”朱熹的回答是:“然。”可见他肯定了这一理解。然而对“体”的理解,朱熹又有更精确的区分。语类卷三十二引学生问曰:
伊川第二说曰:“乐山乐水,与夫动静,皆言其体也。”第三说亦曰:“动静,仁知之体也。”“体”字只作形容仁知之体段则可,若作体用之体则不可。仁之体可谓之静,知之体也可谓之静。所谓体者,但其形容其德耳。吕氏乃以为“山水言其体,动静言其用”,此说显然以为体用之体。既谓之乐山乐山,则不专指体,用亦在其中。
朱熹的回答是:“所论体、用甚善”。他也强调“伊川‘乐山乐水’处,言‘动静皆其体也’。此只言体段,非对体用而言。”根据他的定义,体有体用之体和体段之体,体用之体是形而上的本体(“理”),体段之体则是形而下的形状(“体段模样”)。且看以下一段问答:
问:“知者动,仁者静,动是运动周流,静是安静不迁,以此成德之体而言也。若论仁知之本体,知则渊深不测,众理于是而敛处,所谓‘诚之复’,则未尝不静;仁者包藏发育,一心之中生理流行而不息,所谓‘诚之通’,则未尝不动。”曰:“知者动意思常多,故以动为主;仁者静意思常多,故以静为主。今夫水渊深不测,是静也;及滔滔而流,日夜不息,故主于动。山包藏发育之意,是动也;而安重不迁,故主于静。今以碗盛水在此,是静也,毕竟他是动物。故知动仁静,是体段模样意思如此也。”
在中国古代哲学里,体用范畴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指实体、形体与表现、作用,二指本体与现象、功能。吕氏所谓“山水言其体,动静言其用”,大体指的是第一层意思;山水为实体和形体,动静为表现和作用。而朱熹则兼顾两层且更侧重第二层意思。根据朱子理学的逻辑体系,仁知本身有体用之体和体段之体。仁知之“本体”是未发(形而上的天理),仁知之“体段”则是已发(形而下的体现)。所谓仁知之“本体”即仁知之理,知是指“渊深不测”的众理,仁是指“流行不息”的生理;因为是未发,故“知之体也可谓之静”,仁之体也“未尝不动”。所谓仁知的“体段模样”则是指其德性的形容,形容知的“成德之体”是“运动周流”,形容仁的“成德之体”是“安静不迁”;因为是已发,所以表现为形而下的动静状态,动与静正是知与仁的体段模样。这种体段模样又恰好与山水(已发之实体)的形态对应,“且看水之为体,运用不穷,或浅或深,或流或激;山之安静笃实,观之尽有余味。”本体之体是形而上的伦理,体段之体则是形而下的审美形态,通过形而下的自然审美形态观照领悟形而上的伦理本体,因此“观之尽有余味”。这样就通过山水比德把审美与伦理沟通了起来,而且这种沟通比之前人有了更深的哲理意味。
而且,在朱熹眼里,仁知动静体用关系也是辩证相对的:
然仁主于发生,其用未尝不动,而其体却静。知周流于事物,其体虽动,然其用深潜缜密,则其用未尝不静。其体用动静虽如此,却不须执一而论,须循环观之。概仁者一身混然,全是天理,故静而乐山,且寿,寿是悠久之意;知者周流事物之间,故动而乐水,且乐。乐是处得当理而不扰之意。
仁固有安静的意思,然施行却有运用之意。又云:知是伏藏、渊深底道理,至发出则又运用。然至于运用各当其理而不可易处,又不专于动。
因此朱熹又强调:“看圣人言,须知其味。如今只是看定‘乐山乐水’字,将仁知来必比类,凑合圣言而不知其味也。”对山水与仁知、仁知与动静的关系也应辨证地看待。
朱熹阐释“知者乐水”说的伦理动机,正在借“观水”“乐水”引人进入“知者”的伦理境界:
今且以知者乐水言之,须要仔细看这水到隈深处时如何,到峻处时如何,到浅处如何,到曲折处如何。地有不同,而水随之以为态度,必至于达而后已,此可见知者处事处。“仁者乐山”,亦以此推之。
他特别强调“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皆是就“成德”上说,“专去理会人道之所当行,而不惑于鬼神之不可知,便是见得日用之间流行运用,不容止息,胸中晓然无碍,这便是知者动处。心下专在此事,都无别念虑系绊,见得那是合当做底事,只恁地做将去,是‘先难厚获’,便是仁者静。”“‘知者动’,然其见得许多道理分明,只是行其所无事,其理甚简;以此见得虽曰动,而实未尝不静也。‘仁者静’,然其见得天下万事万理皆在吾心,无不相关,虽曰静,而未尝不动也。”这种对自然审美观照的人格化的强调,比之前人又更深了一层。
三 朱子的“乐水”情怀和“观水”境界
朱熹对“知者乐水”人格审美境界的阐释,是与他自己的人生情趣、人格境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一生对为官宦尘素无大的兴趣,除了讲学著述,很大一部分时间就去游山乐水。只要一有闲暇,便携友观光踏青、游山乐水,颇有曾点吟风弄月、浴沂以归之意。其观水兴致之高,乐水情怀之深,真可谓与生命相伴,成为其生命活动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按他自己的说法,就是他可以为此“足以乐而忘死”。(注:朱熹:《云谷记》,《朱文公文集》卷78,四部丛刊本。)《福建通志·列传》卷十二《朱熹传》这样记叙朱熹的山水情怀:
自号紫阳,箪瓢屡空。然天机活泼,常寄情于山水文字。南康志庐山,潭州志衡岳,建州志武夷、云谷,福州志石鼓、乌石,莫不流连题咏。相传每经行处,闻有佳深壑,虽迂途数里,必往游。携尊酒时饮一杯,竟日不倦。非徒泥塑人以为居敬者。
钱穆先生则如是述评朱熹之“乐水”情怀:
且不论其生平踪迹所至与吟咏所及。其主南康,游庐山,未及见三叠泉,常以为此后之恨。文别集卷6与黄商伯有云:“新泉之胜,闻之爽然自失。安得复理杖屦,扶此病躯,一至其下。仰观俯濯,如昔年时。或有善画者,得为使画以来,幸甚。”又曰:“五老新瀑,曾往观否,梦寐不忘也。”又曰:“瀑图韵谱,近方得之,图张屋壁,坐起对之,恨不身到其下。”又《与杨伯起》有云:“白鹿旧游,恍然梦寐。但闻五老峰下新泉三叠,颇为奇胜。计此生无由得至其下。尝托黄商伯、陈和成摹画以来,摩莎素墨,徒以慨叹。”此皆朱子晚年事也。(注:钱穆:《朱子新学案·朱子格物游艺之学》,台湾:三民书局,1972。)
此中记载朱熹因病老而不能去观水,竟到了请人描摹成画、对画感叹的程度。语类卷一0七也记曰:“梅雨溪流涨盛,先生扶病观曰:‘君子与大水必观焉。’”在病中尚且如此爱观大水,可见“乐水”情怀几已成为朱熹生命感受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朱熹更有诗句云:“知君便有刀头意,莫忘仙洲涧底泉”,这更是指乐水情怀,死而不己。
朱熹在观水过程中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散文和诗歌。朱熹的观水境界着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对水的审美描述来寄寓自身的人格境界,二是通过对水的哲理观照来表达对宇宙人生真理的体悟。我们可以从朱熹最成功的山水记景散文《百丈山记》(注:朱熹:《次清湍亭韵两首》,《朱文公文集》卷6,四部丛刊本。)中,看到朱熹在对水的审美描述中所寄寓的人格境界。其文中称所记之景中“最可观者,石蹬、小涧、山门、石台、西阁、瀑布也”,我们且对这些景点的特征作简要分析:石磴——“右俯绝壑,左控垂崖”,这是“山之胜”之始,其特点为险;小涧——“水自西谷循石滹奔射出阁下”,其特点为飞动;西阁——“据其上流,当水石峻激相搏处”,其特点亦为飞动,并伴有声响(“终夕潺潺”),西阁在小涧之上,两相照应,有动有声,故称“最为可玩”“可爱”处;山门、石台、瀑布——“下临峭岸,深昧险绝……瀑布自前岩穴瀵涌而出,投空下数十尺,其沫乃出、如散珠喷薄,日光烛之,璀灿夺目,不可正视”。“下视白云满川,如海波起伏,而远近诸山出其中,皆若飞浮往来,或涌或没,顷刻万变”。其险绝飞动之特点集中于此,故称“山之可观者,至是则亦穷矣”。朱熹在此突出描述和欣赏的山水情态大体属于险绝飞动的审美形态,“卑痹迫隘”的景物则称之无足观,从中体现了他对山水的审美取向;这种取向是与其人格境界一致的。中国古人有云:“山不在高,有水则灵”。显然,朱熹所激赏的自然景观的审美乐处,正是由于水的飞动和灵动造成的。
再看朱熹《卧龙庵记》云:
卧龙庵在庐山之阳五乳峰下,予自少读龟山先生杨公诗,……又得陈舜俞令举《庐山记》读之,其言曰:“凡庐山之所以著于天下,盖有开先之瀑布见于徐凝、李白之诗,康王之水帘见于陆羽之《茶经》。至于幽深险绝,皆有水石之美也。此庵之西,沧崖四立,怒瀑中泻,大壑渊深,凛然可畏。有黄石数丈,隐映连属,在激浪中,视者眩转,若欲蜿蜒飞舞,故名卧龙。此山水之特胜处也。”于是又知其泉石之胜乃如此……稍下,乃得巨石横出涧中,仰翳乔木,俯瞰清流,前对飞瀑,最为谷中胜处。(注:朱熹:《次清湍亭韵两首》,《朱文公文集》卷6,四部丛刊本。)
其审美取向、人格境界与《百丈山记》如出一辙。所称许的“山水之特胜处”,仍是“沧崖四立,怒瀑中泻,大壑渊深,凛然可畏”的“幽深险绝”处。另一出色的记景散文《云谷记》同样突出赞绘奇壮之水石,如“涧中巨石相倚,水行其间,奔迫澎湃,声震山谷,自外来者至此则已神观萧爽,觉与人异”;又如“时有支涧从两旁山谷横注其中,已皆喷薄溅洒可观”;“涧西危石侧立……水出其下,淙散激射于涧中,特为幽丽”。这里已把对险奇飞动之景的审美感受一并写了出来,突出了其震慑惊悸、令人哦叹的特殊效果。朱熹在文中也说此等处“非志完神王气盛而骨强者,不敢久居”,“非雅意林泉,不惮劳苦者,则亦不能至也”。同样揭示了欣赏险奇飞动的山水审美形态时,主体所需具备的伦理和审美的素质。这既是审美的观照,又是自我人格理想的投射。
同样脍炙人口、广为人知的是朱熹的《观书有感》: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
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乾道二年,朱熹在长时间冥思苦索中突然获得对《中庸》“已发未发”说的领悟,形成了“中和旧说”。这是朱熹首次在重大理论问题上获得突破,史称“丙戌之悟”。这两首诗记录了朱熹豁然开朗时的狂喜心态,被后人称为是“理语成诗”的突出典范。全诗运用形象比兴手法,表现了读书取得成效的高峰体验和乐趣;观水与观书相映成趣,审美观照与哲理顿悟互相生发,情景交融、水理相惬。虽是观书有感,却是观水有悟,正是朱熹“知者乐水”人格境界的绝妙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