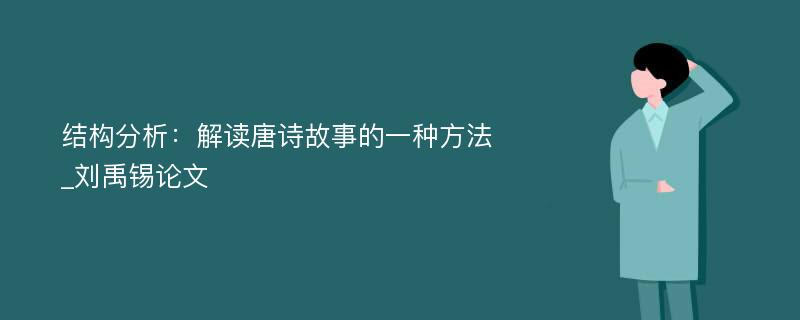
结构分析:解读唐诗本事故事的一种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诗论文,本事论文,结构论文,方法论文,故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晚唐的时候,人们对诗的创作情境、产生过程越来越有兴趣,于是,记载诗本事的故事特别流行,成书于晚唐的《本事诗》和《云溪友议》就收录了很多这样的故事。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通常把它们看作史料,以此了解诗人的性格和写作的具体情形。在《苕溪渔隐丛话》后集中,胡仔在引述韦应物宴会上写艳诗的故事之后,推论出诗人性格的“豪纵不羁”①。这种研究方法在我们今天也很常见。不过,把诗本事的故事当成史料,就必须考察这些故事的真实性,即辨伪。有的故事与其他历史记载有明显出入,须判定为有误,不宜作为可征引的史料;对那些与其他历史记载没有矛盾的故事,暂定它们是真实的,可以作为研究诗人创作或者一首诗的形成的史料来使用②。
举个例子。《本事诗》的“情感”篇里有关于刘禹锡以诗获伎的风流故事③。刘禹锡到李绅家做客,席间赋诗赞美一个歌伎。李绅闻诗,便将歌伎送给刘禹锡。除了《本事诗》,这个故事还有两个版本,一个保存在《云溪友议》④,一个保存在《类说》⑤。这三个版本引用的席间赋诗是同一首,但是每个版本的主人公却不完全一样。《云溪友议》中这个故事的诗人是刘禹锡,可是赠伎者不是李绅,而是杜鸿渐。《类说》中的赠伎者和《云溪友议》一样,是杜鸿渐,可诗人却是韦应物。一个故事出现了三个不同版本,从“辨伪”的角度,读者自然会问,哪个版本是真实的?
经学者考证,三个版本都存在问题,都包含了与历史材料不符的信息。岑仲勉指出,《本事诗》版本有两个细节失实,一个是时间问题⑥。故事里说,事情发生的时候,刘禹锡“罢和州,为主客郎中、集贤学士”,李绅“罢镇在京”,可是根据史料,刘禹锡“罢和州”与李绅“罢镇在京”的并不是同一时间。另一个问题是故事的引诗里称赠伎者为司空,可是在历史上,李绅从来没有作过司空。《云溪友议》版本的问题更严重,故事中的杜鸿渐和刘禹锡,根本不是生活在同一时代。刘禹锡出生的时候,杜鸿渐已经死了三年。《类说》版本也有和史料矛盾的地方。陈尚君指出,故事里韦应物担任苏州刺史倒是实有其事,可问题是韦应物任苏州刺史的时候,故事的另一个人物杜鸿渐已离开人世⑦。所以,三个版本的故事都不可信。
但是,设若这三个版本中的某一个不存在与历史记载矛盾的信息,是不是就可以确定它是真实的或最早出现的,而其他版本则是错谬的、较后出现的呢?实际上,我们也很难认定这一点,因为这些故事的传播途径是口头流传。《本事诗》编者孟棨和《云溪友议》编者范摅都曾提到,他们辑录的故事是听人讲起,然后记录下来,用范摅的话说是“因所闻记”⑧。孟棨也在《本事诗》里提到这个把口头流传的故事记录下来,变成文本的过程⑨。《本事诗》和《云溪友议》成书于晚唐,离故事描述的时代相隔几十年,故事在这期间口耳相传,必然会有种种变化,而《本事诗》、《云溪友议》和《类说》保存下来的版本只是若干版本中的三个。从这个角度看,不同版本故事之间的关系便很难说是真与假、真实与失实的关系,它们不过是某一故事类型的不同变体。在“口头文学”的世界里,无所谓最早的、真实的版本;或者说,即使有这样一个版本,我们也无从判断。
美国学者布鲁范德(Jan Harold Brunvand)在研究属于口头文学的都市传说的时候,曾归纳其形式特征。他认为,和其他的以口头形式流传的文学一样,都市传说是稳定因素和变动因素的结合。稳定因素包括故事类型、叙事结构和人物类型等结构性因素,它们在故事的流传过程中基本保持不变。变动因素则包括时间、地点、人物名字、故事的长短和详略等细节。随着故事的流传,这些因素会不断变化,以方便不同地区、背景的听众的需要。这些不断变化的因素造成一个故事与另一个故事的不同,也造成一个故事的有差异的不同版本。考察这些故事的模式,它们的共性和差异,分析共性和差异的意义结构,是理解这些故事的意义和重要性的基础⑩。
中晚唐诗本事故事和布鲁范德归纳的都市传奇的特点有不少相似之处。本文尝试用研究口头文学的方式,采用结构分析来处理中晚唐的诗本事故事。我会从许多故事中,选择一组同类型的故事作为分析的个案。这一类型的故事,都涉及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感情纠葛,暂且称之为“三角情”。选择这一故事类型,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三角情”故事在中晚唐特别流行,另一个是这个类型的故事保存下来的比较多。《本事诗》第一部分“情感”篇的十二个故事,七个与“三角情”有关。而且,在这七个故事里面,大多有多个版本,保存在《朝野佥载》、《隋唐嘉话》、《独异志》、《云溪友议》等唐代文献里。这些材料给我们分析唐诗本事故事的结构模式,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一、结构特征
“三角情”故事有两个稳定的结构性因素,一个是人物类型,另一个是叙述结构。故事通常有三个人物:一对夫妻(或者情人),加上一个有权势的男性(“第三者”)。在这三个人物的基础上,故事通常表现为这样的情节模式:开始是夫妻或情人分别,女方被有权势者占有;随后,夫妻或者恋人中的男方写一首诗,这首诗导致夫妻或恋人的重逢,或者是他们的永别。故事的叙述结构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分离、写诗、重逢或者永别。第二个环节(写诗),是故事关键的部分。有意思的是,这些故事关注的重心并不是夫妻或者情人之间的情爱关系,而是两个男人之间的冲突,以及他们各自所体现的价值。在故事里,女人通常既没有名字,也没有性格特征,她的功能是欲望对象和争夺目标。两个男性人物各体现一种价值,“第三者”体现权力,而丈夫(或者情人)体现婚姻关系或者男女之情。
如果说,人物类型和叙述结构是“三角情”故事中的稳定因素,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名姓、故事里引用的诗,则是故事中的可变因素。我们通常认为,唐代的诗本事故事记载的是诗人写诗的过程,由这个过程可以得知诗人的经历和性情。可是,如果把同一个类型的不同故事和同一个故事的不同版本放在一起考察,就会发现很多时候,这些故事并不能帮助我们实现这样的目标。因为从故事的构成看,某个诗人之所以成为故事的主人公,很有可能是他符合这一故事类型的需要。比如他活跃的时间和故事发生的时间相同,他做官的地点正好是故事发生的地点,他担任的官职和故事里某个人物的职位相符,或者是他的性格特征与故事里某一人物的类型特征相近,等等。下面试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本事诗》里七个“三角情”故事,有四个以中晚唐人物为主人公;在这四个故事里,又有三个由李绅或者李逢吉担任权势者这一角色。在历史上,李绅和李逢吉是政敌;在这三个故事里,他们的人格高下也构成鲜明对比。李绅慷慨风雅,李逢吉卑劣狡猾。在一个故事里,当李绅发现他的一个客人是歌伎的旧日情人,就让他们共度春宵;在另一个故事里,到他家赴宴的一个诗人作诗表达对一个歌伎的爱慕,李绅就把歌伎赠给诗人。和李绅的慷慨风雅相反,李逢吉在故事里心狠手辣,他把一个官员的爱姬骗到自己家里。李绅和李逢吉人品的优劣,在对待同一位诗人刘禹锡的态度上再明显不过:李绅把自己的歌伎让给刘禹锡,而李逢吉则把刘禹锡的歌伎占为己有。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把这些描述当成实事呢?笔者觉得更有可能的是,因为李绅和李逢吉是政治上的对头,所以被用来扮演故事中功能相反的人物角色:当故事需要一个正直慷慨的人物,就会考虑由李绅担任,故事里需要一个坏人,就会想到李逢吉的名字。可是,为什么好人的角色总是分配给李绅,而坏人的角色总让李逢吉担当?有可能是《本事诗》、《云溪友议》的编者同情李绅一党,所以采扬李绅抑李逢吉的态度。不过,有关《本事诗》和《云溪友议》编者的情况留下的材料不多,所以这一点很难论证。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故事里的李绅和李逢吉,一定程度反映了他们在中晚唐士人中间的“大众形象”。李绅的情况比较有意思。他不仅做到高官,而且年轻的时候,还是个爱写风流诗篇的诗人。我们知道,元稹写《莺莺传》的时候,李绅写了《莺莺歌》,流传很广。那时候说到李绅,除了想到他是成功高官之外,还会想到他是风流诗人:这使他特别适合“三角情”故事中助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权势者角色。同样道理,如果一个诗人的“大众形象”是风流才子,他也很可能被安排扮演男性情人的角色。刘禹锡可以看作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其风流诗人的名声,使他适合“三角情”故事中的这一角色;也正因为如此,才会有不止一个故事将他当作具有风流诗人类型特征的男主角。
刘禹锡风流诗人的名声,可以用两个例子说明。一个是他的乐府诗,尤其是他在夔州写的一些竹枝词,在中晚唐非常流行。白居易在《忆梦得》这首诗的序中,回忆他和刘禹锡一起度过的时光有云:“梦得能唱竹枝,听者愁绝。”(11)刘禹锡的知名度在敦煌讲经文里也可以看到。《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讲经文》里面有一段讲解人生的虚妄,说即使最美的女人、最风流的男人也会衰老(12)。说到最美的女人用的例子是西施,说到最风流的男人便举刘禹锡。可见刘禹锡在当时确立的“大众形象”是风流倜傥,这个形象自然契合“三角情”故事中的情人角色。
有时候,一个历史人物被选中充当某一角色,可能是他正好担任过故事里的人物担任的官职,韦应物在一个故事中出现就有可能属于这个情况。前面提到一个故事存在三个不同版本。在《本事诗》和《云溪友议》里面,诗人的名字都是刘禹锡,但是权势者名字不一样,《本事诗》里作李绅,《云溪友议》里作杜鸿渐。可奇怪的是,到了较晚成书的《类说》,权势者名字与《云溪友议》的一样,诗人却不是刘禹锡,而是韦应物。可以作这样的推测,韦应物的突然出现,可能是为了解决《云溪友议》里这个故事的一个矛盾,就是刘禹锡和杜鸿渐根本不生活在同一个时期,杜鸿渐死后三年刘禹锡才出生。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大致有两个,要么保留刘禹锡,然后找一个刘禹锡的同代人替换杜鸿渐;要么保留杜鸿渐,然后找一个杜鸿渐的同代人替换刘禹锡。《类说》采取的是第二种方案。韦应物比杜鸿渐年轻十九岁,符合故事对角色的年龄要求。此外,韦应物还符合故事对人物官职的要求。故事里的诗人赞美歌伎的诗有这样两句:“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肠”;诗人自称江南刺史。韦应物做过苏州刺史,让他在诗中自称江南刺史,也是恰当的。
就像历史人物被拿来充当故事里面的角色,某些诗作也常常为满足故事类型、叙事结构的需要而被拿来用在故事里面。虽然我们通常认为,唐诗本事故事是记录诗人写一首诗的过程,可实际上,故事和引诗之间的关系很复杂。有时候,一首诗早就存在,但是因为符合故事需要而被用在故事里面;有时候,一首诗被用在好几个故事里面;有时候,一个故事的不同版本会用不同的诗;也有时候,一个诗人的诗被用在另一个诗人的故事里面,但是因为故事流传得广,所以这首诗慢慢就被认为是另一个诗人的作品,甚至编入他的文集。《本事诗》有一个以戎昱为男主角的“三角情”故事,里面有这样一首诗:“好去春风湖上亭,柳条藤蔓系人情。黄莺久住浑相识,欲别频啼四五声。”(13)关于这首诗,《本事诗》讲述的是,与戎昱相好的一个官伎擅歌,为“镇浙西”的韩滉所召,戎昱被迫与歌伎分别。临别,戎昱写了这首诗,让歌伎带到韩滉的宴会上演唱。在这样的故事情境中,诗表达的是情人分别的痛苦,黄莺比喻的是擅歌的歌伎。不过,我们翻阅王安石的《唐百家诗选》,这首诗也署戎昱作,题目却是《移家别湖上亭》(14)。如果把诗放在这个题目下面读,我们体会的是诗人即将离开久居地方的伤感。那么,这首诗写作的过程、情境便成为疑问。还有更复杂的情况。《云溪友议》也收录了戎昱的故事,可是里面的诗和《本事诗》里的诗完全不同。即使我们相信戎昱为歌伎写诗,那么,哪一首“真的”是戎昱所写?这里存在多种可能:也许《本事诗》版本的诗是戎昱与歌伎分别的时候写的,后来这首诗和《移家别湖上亭》这个诗题不知怎么被安在一起;也不知怎么,《云溪友议》的故事用了一首完全不相关的诗。也有可能是,《云溪友议》版本的诗才是戎昱赠给歌伎的诗,那么,《本事诗》版本的诗就是讹传,有可能是戎昱为搬家而作,后来被用在这个故事里。还有一种可能性,也许这两首诗和戎昱的“三角情”故事本无关联,但是因为符合故事情节的需要,被引入而成为故事的一部分。不管是哪种情况,都说明故事里的诗是流动的因素,它与故事的关系变动不居,时而是故事的一部分,时而从故事中消失,时而被另一首诗替换。
有时候,一首诗用在一个故事里的时候,可能为适应故事的情节而改变。《云溪友议》里面元稹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例子(15)。故事赞美元稹和他的两任妻子之间的感情,说元稹的第一任妻子韦丛去世的时候,他“不胜其悲”。为证明,《云溪友议》引了两首据说是元稹丧妻之后写的诗。这里我要讨论的是这样的两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在《云溪友议》故事所提供的语境里,这两句诗表达了元稹对亡妻的感情,沧海之水和巫山之云比喻亡妻在他心中不可替代的位置。可是,如果把它们放在整首诗中,就会发现其实与元稹丧妻没有什么关系。诗的题目是《离思》。全诗如下:“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16)我们发现,诗人想念的对象不像是他的亡妻,倒像是风月场中的女子。元稹和白居易都写过很多怀念年少风流的诗,在那些诗里,“花丛”或“花”隐喻风月场的女子。在元稹带有自传性质的长诗《梦游春七十韵》里,他回忆若干年前与一女子的艳遇,后来幡然悔悟,告别风流生活,娶妻生子,步入仕途(17)。在诗里,他把这种转变比喻成大梦初醒和刹那间的顿悟,写自己醒悟之彻底,“觉来八九年,不向花回顾”,这里的“花”可以指某一花一般美貌的情人,也可以泛指风月场或风月场的女子。白居易在他的和诗里也写到元稹的这个转折,说他后来“京洛八九春,未曾花里宿”(18)。白居易意在赞美元稹告别风流生活的决心。告别风流生活的主题也出现在《离思》的第三句:“取次花丛懒回顾”,其修辞和《梦游春七十韵》中“不向花回顾”接近。两句诗里,“花”的意象都泛指风月场女子。这样看来,《离思》写的似乎是,一个女子在诗人心中留下不可替代的位置,所以他对风月场完全失去了兴趣。这里,诗人把她和风月场上的女子相提并论,放在一起比较,说明这个女子很可能也是风月场中的一员,而不太可能指诗人的亡妻。毕竟,把士人阶层的亡妻与风月场上的女子放在一起比较是不妥当的。
那么,如果《离思》这首诗和元稹怀念亡妻没有关系,它的头两句怎么会出现在《云溪友议》元稹怀念亡妻的故事里呢?也许,元稹怀念亡妻的故事在收进《云溪友议》之前,已经流传多时,流传中有人觉得这两句诗与故事的意思契合,就加了进去。把诗和故事粘结在一起的人,不管是范摅还是别人,可能是有意不用《离思》的后两句,觉得那有违怀念亡妻的情境;但是也有可能,故事只用《离思》的前两句,并不是有意的取舍。在中晚唐,诗中的一句或者两句作为“佳句”流传,是很普遍的事情(19)。也许,《离思》的头两句特别有名,早就作为“佳句”单独流传,再加上这两句所表达的情感和元稹的故事特别契合,所以就被套用在故事里。
把本来并不相关的诗放进诗本事故事里,作为故事里人物写的诗,这种做法在唐诗本事故事里很常见。黄璞的《闽川名士传》中收录的欧阳詹的故事就是这样的例子。欧阳詹是韩愈的同辈人,同一年的进士。欧阳詹去世的时候,韩愈写了哀辞,李翱写了传(已佚),孟简写了《述欧阳行周事》。其中,孟简的《述欧阳行周事》讲述了欧阳詹钟情于太原歌伎,分别后二人相思而死的故事。这个故事还有一个较晚的版本,收在晚唐黄璞的《闽川名士传》里(20)。孟简的版本和黄璞的版本情节基本一样,但是结构上有重要的区别,其中之一是黄璞版本里面有两首诗,是孟简的版本里面没有的,一首是欧阳詹写的与太原伎的离别诗,另一首是太原伎写自己等待欧阳詹的闺怨诗。这两首诗的加入使黄璞版本的叙事结构很像《本事诗》和《云溪友议》里面的诗本事故事,即围绕诗的产生展开的叙事模式。这两首诗在《闽川名士传》中出现,很可能是受到晚唐流行的诗文交杂叙事模式的影响,后来添加进故事里的。黄璞版本中的两首诗由送别诗和闺怨诗的典型意象构成。“自从别后减荣光,半是思郎半恨郎”很像《莺莺传》中莺莺写给张生诗的第一句和第四句:“自从消瘦减荣光”和“为郎憔悴却羞郎”。这是源于乐府诗的,已经高度模式化的用词和意象。从诗中我们看不出任何与欧阳詹故事相关的独特经验。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怀疑这首送别诗不是欧阳詹为太原伎所作,理由就是诗句的模式化。《欧阳行周集》里面收录的那首送别诗(《途中寄太原所思》),首句是“高城已不见”,陈振孙指出,“‘高城已不见’之句,乐府此类多矣”。他认为那首送别诗只是一般的乐府诗,不能看作是诗人情感的表现,“不得以为实也”(21)。陈振孙认为,欧阳詹与太原伎的爱情故事根本就是好事者杜撰出来的,而杜撰的根据就是欧阳詹那首乐府诗的诗题《途中寄太原所思》。陈振孙由此得出教训,给诗起题目要特别谨慎,不然会给好事者留下把柄,杜撰不相干的故事。
由诗题杜撰出故事,这是一种可能。不过陈振孙没有考虑到另一种可能,即从故事杜撰出诗题。在唐朝的手抄本文化里,诗题与作者不像在我们熟悉的印刷文化里那么稳定,一首诗在口头或者通过抄写流传的时候,它的题目、作者和字句,都常常改变。所以,保存在两个地方的同一首诗,题目作者不同,用字有出入,都很常见。还有,故事和故事里的诗的关系也不稳定。一个故事在流传的时候,可以插进一首诗,也可以省略原有的诗,也可以用一首诗代替另一首诗。欧阳詹故事里的那两首诗,可能本来与欧阳詹的爱情故事没有关系,它们后来进入黄璞版本的欧阳詹故事,为的是适应晚唐流行的诗文交杂的叙事模式。那首乐府风格的送别诗,因为故事里归在欧阳詹名下,所以加上一个与爱情故事有关的题目《途中寄太原所思》,进入了欧阳詹的文集。
有时候,一个故事的不同版本会插入不同的诗。前面讲到,戎昱故事在《本事诗》和《云溪友议》里就是这样。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通常会问,哪一首是戎昱在这个事件中写的诗?但是这个问题既不容易有答案,也不重要,因为在唐诗本事故事里面,故事与诗的关系经常是功能性的,而不是一一对应的。例如,在讲述朋友离别的故事框架里,只要是送别的诗,就都适用。在戎昱的故事里,诗的功能是让有权势者知道戎昱对歌伎的感情,迫使有权势者把歌伎归还戎昱。《本事诗》和《云溪友议》里的诗虽然不一样,但是它们都描写诗人与歌伎分别时的痛苦,符合故事的叙事需要。
诗与故事的这种功能性关系的另一种表现,是同一首诗用在不同的故事里。下面的例子就是一组诗出现在两个故事里。在第一个故事里,刘禹锡的歌伎被李逢吉骗走,于是刘禹锡写了四首诗给李逢吉。可是,这四首诗中的三首也出现在另一个“三角情”故事里,刘损的妻子被吕用之霸占,于是刘损写了这三首诗给吕用之(22)。这三首诗也收在《才调集》里,不过在那里,诗的作者既不是刘禹锡,也不是刘损,而是佚名。显然,《才调集》的编者不能确定它们的作者(23)。现在,我们已经不可能知道诗的真正作者,但是我们知道,这几首诗在中晚唐很流行。它们流传的时候,作者的名字也不稳定。
二、人物类型的变化
依照布鲁范德对美国都市传奇的分析,故事中的变化因素分成两大类(24)。第一类属于细节性的,为的是适合某个地方听众的需要。当一个故事流传到某地,时间、地点、人物名字这些细节就可能发生改变,以增加该地听众的认同感。这类变化一般不改变故事的意义。第二类变化是结构性的变化,比如叙述结构和人物类型的改变。这是大的,而非细节的变化,而且可能改变故事的意义。上文中讲到的变化,属于第一类细节性变化。下面要讨论的是第二类的变化,第一个例子涉及人物类型,第二个例子涉及故事里面的诗的功能。
《本事诗》“情感”篇第三个故事和王维有关(25)。宁王曼喜欢上饼师的妻子,把她占为己有。一年后,宁王召饼师入宫,让夫妻相见,并让在座的文士当场赋诗。王维第一个写完,诗是这样的:“莫以今时宠,宁忘旧时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在所有的“三角情”故事里面,这个故事与众不同,因为除了三个固定类型的人物(一对夫妻和一个有权势的男人),还多出一个角色,就是作为事件目击者的王维。在别的“三角情”故事里,诗人的角色通常由男性情人担任,在这个故事里,诗人却是与事件没有直接关系的目击者。这个故事的情节也有一些难以解释的地方。虽然王公大臣在宴会上展示家伎,令文士赋诗赞美,在唐朝是很普通的事,甚且被视为风流之举,可是宁王为一己私欲,拆散一对夫妻,又让夫妻相见,让文士为此赋诗,这是罕见、奇怪的事情。故事里说,在场的文士看到饼师与妻子见面时潸然泪下,都很难过,“无不悽异”。宁王也和在场的人一样,深深叹息,对饼师夫妻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故事讲到这里,读者不免感到奇怪,难道不正是宁王拆散了饼师夫妻并制造了这一悲惨境遇吗?宁王一边利用权势夺走饼师的妻子,一边同情被他剥夺、迫害的夫妻,于情于理,都实在是既纠结又分裂。
情节上的这种尴尬之处,与结构故事的方法有直接的关系。一方面,故事以“三角情”的类型作为框架,力求符合它的叙事结构;另一方面,故事又要以王维的一首诗为中心来结构故事,让情节契合诗的内容。可是,这两个目的在故事中并不容易调和。先说王维的那首诗,诗在《河岳英灵集》和《国秀集》中都有收录,一个题作《息夫人怨》(26),另一个题作《息妫怨》(27)。这里面包含一个来自《左传》的故事(28)。楚文王慕息夫人美貌,对息国发动战争,把息夫人占为己有。息夫人为楚文王生了两个孩子,但是从不和他说话。有人问她为什么,息夫人说:“吾一妇人,而事二夫,纵弗能死,其又何言。”所以,这首题为《息夫人怨》或者《息妫怨》的诗,是王维有感息夫人故事而发。这样,关于这首诗的产生,就有了两个不同的故事。《本事诗》说诗是为饼师夫妇的事情而写,而《河岳英灵集》和《国秀集》说是有感于息夫人的故事。清代的吴乔相信饼师故事的真实性,认为诗是王维为饼师夫妻的遭际而写(29)。他进而推论,说唐诗的题目有时候和诗的内容无关,甚至会误导读者,比如《息夫人怨》和《息妫怨》这两个题目,读者以为诗与息夫人故事有关,却不知道其实是关于饼师夫妻的故事。与吴乔相反,笔者认为王维的诗应该是为息夫人故事而写,后来被用在饼师的故事里面。《河岳英灵集》成书在前,《本事诗》成书在后,所以,《息夫人怨》和《息妫怨》的诗题的出现可能比饼师的故事早。当然,保存在《本事诗》里的故事,很多产生于中唐、盛唐,或者初唐。这些故事常会在晚唐以前的文献中留下痕迹。《本事诗》的“三角情”故事里面有涉及初唐人物乔知之的故事(30),就收录在《朝野佥载》和《隋唐嘉话》中,可见故事形成年代与乔知之生活的年代相距不远(31)。饼师的故事情况却不一样。这个故事在现存的盛唐和中唐的材料中都没有记载,到了《本事诗》才第一次出现。王维的知名度不比乔知之小,如果王维为饼师夫妻作诗的故事是王维在世或者去世不久形成,应该和乔知之的故事一样,在比较早期的文献中留下痕迹。王维的这个故事在早期文献中完全缺席,说明故事可能较晚才出现。也就是说,这首诗很可能是王维有感息夫人的故事而写,后来在“三角情”故事盛行的晚唐,被套进了这个故事里面。
饼师的故事对于历史人物的选择,也和别的“三角情”故事不一样。在别的故事里,有权势者通常由一个知名的人物充当;杨素、杜鸿渐、李绅、李逢吉在历史上有很多记载。可饼师故事里的宁王却是一个不大为人知的角色。选择他扮演有权势者,很可能是因为故事需要一个王维的同代人,而他符合这个条件。再说饼师这个角色。在别的“三角情”故事里,丈夫或者男性情人通常也是诗人,是推动情节发展的人。可是在这个故事里,因为故事里的诗人已经是王维,饼师这个角色变得很尴尬。他无事可做,既没有写诗给他的妻子或者权势者,也没有表达对妻子的思念,没有设法和他的妻子重逢,完全是一个没有动作的角色。在所有我看到的唐代“三角情”故事里,只有这个故事的丈夫没有名字。饼师与其说是一个人物,不如说是一个道具。饼师夫妇在宁王宫中重逢也有点牵强,好像是为配合王维的诗而设计的场景,整个故事也好像是从王维的诗句中发展出来的;一个意象生发出一个故事情节。诗的第三句是“看花满眼泪”,于是故事里面就有这样的场景:夫妻重逢的时候,“其妻注视,双泪垂颊,若不胜情”。诗的第四句是“不共楚王言”,于是故事中的妻子也拒绝说话:当宁
王问饼师妻子是否想念丈夫时,她“默然不对”。从作品的生成过程看,王维的诗和饼师的故事可能正好相反:王维把息夫人的故事凝缩为两个动人的意象,而饼师的故事则根据王维诗的中心意象来设计、展开故事。这里,诗和故事的创作过程,说明了那个时候诗与故事的关系:流行的故事可以是诗创作的依据,有名的诗也可以铺排出新的故事。
饼师夫妇重逢场景之尴尬,也因为宁王同时扮演着两个互相矛盾的角色。一方面,他是“三角情”中的权势者;另一方面,他和那些奉命赋诗的诗人一样,又是事件的“旁观者”。作为权势者,他夺走他人妻子,迫使夫妻分离。可是作为事件“旁观者”,他同情饼师夫妻的不幸遭遇,和在场的文士一起叹息。这就造成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情景:造成别人痛苦的人,又无比同情别人的痛苦,似乎对自己是痛苦的根源毫不知情。要把王维的诗放进故事中,要在故事中给王维安排一个角色,又不想改变“三角情”故事的基本模式,这样一来,叙事上、人物性格上的龃龉、冲突就不可避免。说到底,啼笑皆非的情景,还是由故事的结构方式所引起。
三、诗的功能的变化
《本事诗》里的“三角情”故事,可以按照人物生活的年代分成两类:生活在中唐以前的和生活在中晚唐的。前者有徐德言的故事和乔知之的故事,后者包括戎昱、刘禹锡、张又新、李逢吉等的故事。这两类故事有一个显著的差别,就是诗的接受对象的变化。在徐德言和乔知之的故事里,诗是由丈夫或男性情人写给他的妻子或者情人,可是在中晚唐为背景的故事里面,诗是男性情人写给有权势的男人的。在徐德言的故事里,发现战乱中失散的妻子被杨素占有之后,徐德言写诗给妻子:“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告知他的思念之情。在乔知之的故事里,乔知之的婢女被武承嗣霸占,他写诗示婢女,一面指责她见异思迁,言行不一(“昔日可怜君自许,此时歌舞得人情”),一面暗示她应该像绿珠那样,对主人忠贞不二,哪怕付出死的代价(32)。在这两个故事里面,诗的功能是夫妻或者情人之间的沟通手段,但都引发了诗人意料之外的后果。徐德言的妻子读了丈夫的诗后,不思饮食,日夜哭泣,杨素查明情况之后,决定将她归还给徐德言。所以,诗意外地促成夫妻的团聚。乔知之的诗引发的则是悲剧。乔知之的爱婢读诗之后投井自尽,武承嗣发现乔知之的诗,把他投进监狱,迫害乔知之的全家。在这些故事里,诗的功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诗落在预设读者(妻子、情人)之外的读者(权势者)手里,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在以中晚唐为背景的“三角情”故事里面,男性情人不是写诗给自己的情人,而是写诗给占有自己情人的权势者。诗的功能不再是向情人表达情感,而是给权势者传递信息。在戎昱的故事里,戎昱让歌伎在权势者的宴会上唱他的诗,“至彼令歌,必首唱是词”。当诗的读者(听者)从情人变成占有情人的权势者的时候,诗的功能和含义也会跟着改变。比较《云溪友议》版本戎昱的诗和《莺莺传》里莺莺的诗,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云溪友议》里故事的引诗是:“宝钿香蛾翡翠裙,妆成掩泣欲行云。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阳台梦使君。”诗中涉及“三角情”关系中的三个方面。戎昱叮嘱与自己相好的歌伎,要殷勤服侍新的主人韩滉,不要想念自己。这个姿态让我们想起《莺莺传》中莺莺的一首诗。张生和莺莺分手之后,两人别娶另嫁,张生想再见莺莺一面,但是只得到莺莺的一首诗,嘱咐他好生对待现在的妻子:“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虽然莺莺诗和戎昱诗的修辞有相似之处,都是嘱咐自己的情人善待新人,可是它们的预期读者不同,含义也就不同。莺莺诗的读者是张生,她的诗是向张生表达她此时的心情;戎昱诗的接受对象虽然也是他的情人,但诗将在戎昱的精心安排下,由歌伎在韩滉面前当众演唱,因而这首传达被迫分离者凄楚无奈情感的诗,就包含了批评韩滉利用权力拆散情侣的不道德的意味。诗的当众演唱,也使韩滉陷入两难境地。最后韩滉选择了不继续占有歌伎,而将她还给了戎昱,还特别强调自己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征召这个歌伎,不是有意拆散。这是个有关好人与坏人的道德选择的故事模式,在这里,韩滉选择了当一个有道德的“好人”。
戎昱和歌伎的关系,与徐德言和他的妻子,乔知之和他的爱婢的关系是很不一样的。在戎昱的故事里面,那个歌伎是官伎,在唐代,官伎归属于乐籍,不属于某个人。所以,戎昱和歌伎之间的惟一纽带是他们的感情。对一个官伎来说,被官员征召是很平常的事情。韩滉征召歌伎去他的乐籍,完全符合“程序”,没有任何不妥之处。只有当男女情爱被认为是一种价值的时候,韩滉征召歌伎而“拆散”一对情侣才会被视为是不道德的行为。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戎昱才能以他对歌伎的感情为理由,公开宣称对她的“所有权”。虽然戎昱成功地赢回他的情人,但是他所采取的方法——即在公众面前批评有权势者是有风险的。歌伎演唱了戎昱的诗以后,韩滉让歌伎更衣等待,在座的客人都很为歌伎的命运担心(“席上为之忧危”)。还有一个“三角情”的故事也描写了类似的忧虑。在那个故事里面,有权势者听到诗后,召见诗人,在场的人都不知道会发生事情,“左右莫之测也”(33)。这种忧虑的气氛,说明诗人对权势者的公开批评有可能招致灾祸。不过,在大多数的故事里,权势者都选择让情人团聚,然后受到舆论的褒扬。如果权势者不这样做,就会被塑造成一个依仗权势、胡作非为的坏人。前面提到的李逢吉的故事就是一个例子。所以,在这些故事里,情爱的价值和写诗的方式成为弱势者的有效工具。通过写诗宣告自己对一个女子的感情,可以和权势者在“情场”上一争高下。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这也说明诗歌创作在中晚唐被想象为一种力量,人们通过诗的写作、传播和表演,来处理各种人际关系。
笔者在本文中分析了“三角情”故事的结构特征,希望能够说明,这些故事不一定能告诉我们某一个诗人是如何写诗的,或某一首诗是在什么情境下创作的。那么,这些故事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信息呢?
第一,把同一类型的故事放在一起,我们可以了解这些故事的构成方式。稳定的叙事结构和人物类型是这些故事的基本框架,其他元素,像时间、地点、人物和引诗,则可以不断填充到这个基本框架中,形成同一模式的多种变体。故事与故事之间,一个故事的不同版本之间,会有差异变化。有的变化是细节性的,比如时间、地点、人物名字,这些变化不会改变故事的意义。另外一些变化是结构性的,比如人物类型的改变,或者一个元素在故事中的功能的改变;这些变化可能导致故事的模式和含义的改变。通过分析唐诗本事故事,我们也了解到,诗和故事之间的关系,诗和诗人之间的关系,不是稳定的,而是不断流动、不断变化的。这是因为,很多故事是在口头流传很长时间之后才记录下来,口头传播的过程中,故事总在不断变化。即使这些故事书面记录下来之后,文本也并不就具有高度稳定性。因为在文体的“等级”阶梯中,它们属于“低等级”文体(34)。文体的级别越低,文本的变动就越容易,越经常发生。
第二,把同类型的故事放在一起,把每一个单独的故事看成是某一结构模式的变体,我们才能看出哪些故事只是对模式的复制,哪些故事偏离了既有的模式,具有“独创性”。如果不是放在“三角情”故事模式中比较,我们可能不会注意到王维的故事的独特之处,也不会注意到在以中晚唐为背景的故事中,诗的读者(听众)和诗的功能,都和此前的故事不大一样。这些变化可能折射出社会中文化环境和价值观念的变动。诗的读者从情人变成“第三者”,诗的功能从表达和交流感情的媒介,变为也承担着解决人际矛盾的手段,从中可以见识诗的功能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拓展。在中晚唐,越来越多的故事讲述人们通过诗的写作、传递、演唱来处理各种人际关系。以中晚唐为背景的“三角情”故事还有另一个变化,故事里的男女主人公,可能不再是在社会和家庭制度中有从属关系的夫妻或主仆,而是士人和歌伎。联系后者的纽带是男女之情。这些故事所表达的对士人和歌伎之间感情的肯定,显示男女之情在那个时代拥有独立的价值。故事写到那些缺乏政治社会资本的士人,他们以文士和情人的身份,用诗,用情爱的修辞,与占有社会资源的官员在“情场”上一争高下,并且在竞争中取胜,这让我们看到,在中晚唐,“文化”有可能是或被想象是一种能够与政治权力对峙的资源。而这个“文化资本”,既包括写诗和运用诗的能力,也包括人的情感能力。这些都是我们通过结构分析所读出的“三角情”故事的社会文化涵义。
注释:
①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64页。
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包含了对《本事诗》、《云溪友议》的辨伪工作。
③⑨(13)(25)(30)王梦鸥:《本事诗校补考释》,台北艺文印书馆1974年版,第46页,第42页,第39页,第34页,第32—33页。
④⑧(15)(31)(33)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298页,第1259页,第1309页,第20、109页,第1265页。
⑤王汝涛:《类说校注》卷二七,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17页。
⑥岑仲勉:《司空见惯》,《唐史余渖》,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74页。
⑦陈尚君:《司空见惯真相之揣测》,载《新民晚报》2009年2月15日。
⑩(24)Jan Harold Brunvand,The Vanished Hitchhiker:American Urban Legends and Their Meanings,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81,p.13,p.14.
(11)(18)《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070页,第4857页。
(12)王重民编《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652—653页。
(14)王安石:《唐百家诗选》,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63页。
(16)(17)(23)(26)(27)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18页,第808—809页,第970页,第131页,第256页。
(19)唐代的秀句集很多,如元兢《古今诗人秀句》、王起《文场秀句》。张为的《诗人主客图》在评价诗人的时候,也经常摘句评点。
(20)《太平广记》卷二七四,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161—2162页。
(21)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451页。
(22)刘损的故事曾经收录在9世纪的两个集子《灯下闲谈》和《南楚新闻》中,这两个集子在《新唐书·艺文志》中列在“小说”这个类别下面。《灯下闲谈》版本的刘损故事,保存在《说郛》卷一一(台北“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885—886页)。《南楚新闻》版本的故事,笔者未找到。《唐代丛书》中收的《南楚新闻》没有这个故事,不过宋敏求(1019-1079)在《刘宾客文集》的序里提到在《南楚新闻》里,这三首有争议的诗被归在刘损名下。
(28)李学勤:《春秋左传正义》卷九,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3页。
(29)吴乔:《围炉诗话》卷一,台北广文书局1969年版,第32b—33a页。
(32)有关绿珠的故事,参见杨勇《世说新语校笺》卷三六,台北正文书局2000年版,第829页。
(34)对唐代的笔记和传奇故事的流动性,它们在通过口头和文本流传的过程中发生的变化,Sarah Allen有详尽讨论。(Cf.Sarah Allen,"Tang Stories:Tales and Texts"(Ph.D.Diss.,Harvard University,2003),"Tales Retold:Narrative Variation in a Tang Story",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6.1(June 2006):105-144)。
标签:刘禹锡论文; 唐诗论文; 河岳英灵集论文; 文化论文; 王维论文; 离思论文; 读书论文; 韦应物论文; 息夫人论文; 诗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