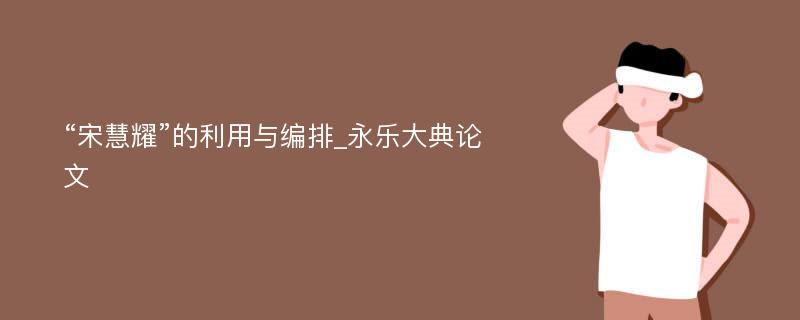
《宋会要》的利用与整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会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主要是供读者使用《宋会要》时参考的。
本文所说的《宋会要》,既包括《宋会要辑稿》(以下简称《辑稿》),也包括《宋会要辑稿补编》(以下简称《补编》)以及《永乐大典》残本中的《宋会要》辑文等,总之,是现存的所有《宋会要》的辑文。
关于《宋会要》的利用,包含两个方面。从消极方面说,是避免误用《宋会要》;从积极方面说,是充分利用《宋会要》。
一
先说避免误用《宋会要》。
就我所见到的情况而言,误用《宋会要》,有如下三种情况。
(一)误以他书为《宋会要》。
在《辑稿》(及《补编》)中,有些内容并非《宋会要》原文,而是其他文献。出现这种情况,同《永乐大典》编纂原则有关。按照《永乐大典》的凡例,同一事而有两种或两种以上文献记载时,事文均同即只选一种,事文稍有异,以一种为正文,他种作注文。在《辑稿》中,这种情况多见。在以他书为正文,《宋会要》作注文,如帝系1之4至6,正文为《十朝纲要》。也有以《宋会要》为正文,他书作注文,如乐1之1,以《玉海》作注文。注文用小字,开首并著录书名(有些是简称),本来是不会混淆的。但在徐松命《全唐文》馆书吏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宋会要》时,有些书吏误将注文也用大字抄录,有的连书名也没有抄下,因此极易与《宋会要》正文混淆。
据我所知,在《辑稿》第一本,可能引起或已经引起误用的,就有如下七段:1.帝系4之31至36,为杨仲良《长编纪事本末》卷4《裁定宗室授官》。2.乐5之27至39,为《宋史》卷142《乐志》。3.乐7之5至31,大字正文全为《宋史》卷138、139《乐志》。4.乐8之8 至10均为《宋史》卷140《乐志》。5.乐8之11“天书导引七首”以下至8之17均为《宋史》卷140《乐志》。6.乐8之20至28,大字正文为《宋史》卷141《乐志》。7.礼17之41第4行“淳熙十六年二月”以下,直至17之85共45页,全为《文献通考》卷98、99《祭祀时享》。
(二)引用时间错误。
《宋会要》的细胞(记事基本单位)为条。条有两种类型,一种以一人、一物为单位,另一种以一事为单位。前者较少,后者是基本的类型。《宋会要》分类的基本单位是门,如吏部门、边防门等等。同一门的条文一般按时间先后排列。条文记时的方法,每一朝的首条记事著该帝庙号(如编纂会要时该帝尚在世,退位为太上皇,则称其尊号,如高宗之称光尧皇帝,孝宗之称寿皇圣帝),每一年号的首条记事著年号,每一年的首条记事著年分,每一月的首条记事著月分,次条以下记事一般不再著庙号、年号、年分、月分。如兵27之1至29之30为备边门。兵27之1第一条为太宗朝第一条记事,记时为“太宗太平兴国三年二月”,既著庙号(太宗),又著年号(太平兴国),又著年分(三年),又著月分(二月)。次条为太平兴国四年九月五日记事,庙号及年号与上条相同,只是年分及月分不同,故记时为“四年九月五日”,不著庙号及年号。掌握了这个记时规律,引用《宋会要》时,如该条文没有庙号、年号、年分、月分,一定要往前追溯其庙号、年号、年分、月分,才不致造成时间上的错误。如兵29之48(属边防门),下半页第4行记时为“嘉定七年二月一日”,在这之前的两条,记时为“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和“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兵29之47)。三年、六年虽在七年之前,但这两条不是嘉定的三年、六年,因“七年”条冠以“嘉定”年号,按照《宋会要》的记时方法,该条应是边防门嘉定年号的第一条记事。要确定前面的“三年”、“六年”两条的年号,应往前追溯到有年号的条文。经查阅,为“庆元”年号记事(见兵29之45)。如将此“三年”、“六年”两条定为嘉定,将会造成13年的误差。
上面的例子,《宋会要》的辑稿本身记时没有问题,是在使用时可能发生的错误。下面说的是《辑稿》甚至《宋会要》本身在记时方面的问题。
先说因《宋会要》被收入《永乐大典》而在记时方面发生的问题。礼26之10属牲牢门,上半页第6行第1条记时为“十月十二日”,下半页第7行第1条记时为“九月十四日”,都没有庙号、年号与年分。如果按照常规,“十月十二日”前一条记时为“嘉祐七年八月一日”,此条应为同年的十月十二日,但文中提及“熙宁祀仪”,可见为熙宁以后的事;“九月十四日”前一条记时为“徽宗大观元年八月七日”,此条应为同年的九月十四日,但它的下一条“三年六月十三日”,据《长编》卷305,知为神宗元丰三年,可知此条非大观时事。经考证,据《长编》卷317,知“十月十二日”条系元丰四年;据《长编》卷292,知“九月十四日”条系元丰元年。为什么这两条条文不能照常规确定其时间?又如何识别类似的情况?读者请注意:《辑稿》牲牢门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文中多次另起“宋会要”(除开首外,礼26之10两处,26之13一处),对照《永乐大典》残本,可以推知在这一门(在《永乐大典》中为“事目”下的一个子目,是《大典》收录文献的基本单位),《大典》编者插花式地收录各种文献,即按所记内容的时间顺序,分别收录不同文献。在这种情况下,《宋会要》的牲牢门不但在《大典》中被分割,而且有些内容因与其他文献相似或较简而被舍弃了。所以在遇到同类情况时,引用《宋会要》要特别注意其时间。
还有一种是《宋会要》原书在记时方面的差错。如礼7之32属日历所门,第一条为(乾道二年)闰九月二十九日。乾道二年非闰年,此处“闰”字衍。象这一类错误需经考证才能发现。
(三)标目错误。
《辑稿》及《补编》有众多标目,有时同一内容有两种甚至两种以上标目。标目的位置也五花八门,有书于“宋会要”之下,如帝系1之24,“太子诸王”;有书于正文开首,如职官78之64,“罢免”;有书于“宋会要”之次行,如仪制11之1,“宰相追赠”;有书于栏上,如礼25之71,“郊祀神位议论”;有书于正文中间,如帝系1之3,“帝号杂录”;也有以上两种情况的综合;甚至有的辑文没有任何标目。这些标目,有些确为《宋会要》门名,有些为《永乐大典》的事目,也有为历次整理者误加的。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需要用许多篇幅才能说清楚。这里只能提醒读者,利用这些标目必须慎重。如职官44之42的“经制使”,就是整理者误加的,应为“经制司”。“司”指机构,“使”为官员,两者的重点是不同的。
二
除了避免误用《宋会要》之外,更重要的方面,是如何充分利用《宋会要》。下面也谈三点:
(一)多方面发掘《宋会要》的史料价值。
《辑稿》影印以来,使用者越来越多了。但对《宋会要》的利用,多集中于食货、职官、刑法、选举等几类,而对其他类则注意不够。其实它们中蕴藏着丰富而珍贵的史料。
现在举礼类中的祠庙为例。《辑稿》礼20共171页,辑自《永乐大典》卷1203至1239,为“祠”字韵,具体事目则有山川祠、天地月星风雨岳渎祠、帝王祠、名臣祠、忠孝节义祠、王公隐士祠、神祠等等,总之,包括了自然神及人物神。这是研究民俗史、社会史、宗教史等问题的宝库,凡善于利用者必有所获。
都江堰闻名世界,《宋会要》礼类中就有二郎神的宝贵材料。张政烺先生据礼20之141《郎君神祠》条,考定“灌口二郎神在后蜀号护国灵应王,显然还是个武夫。嘉祐八年,宋仁宗皇帝肯定他是李冰的第二个儿子”,分析了二郎神信仰在宋代发展变化的过程。(《<封神演义>漫谈》,《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4期)
笔者则根据礼20之142《陈元光祠》条,知陈元光母为吐万氏,是鲜卑族贵姓,因此判定陈元光这位至今在闽南、台湾有广泛影响,并被不少台湾同胞奉为祖先的唐初人物,具有鲜卑血统。(《从陈元光母妻的姓氏看他的籍贯》,《云霄文史资料》第11辑)
福建惠安青山宫奉祀青山王。随着惠安人的向外迁徙,如今青山王信仰已成为惠安联系台湾同胞及东南亚侨胞的一条纽带。过去所知有关青山王记载,最早的是嘉靖《惠安县志》,编成于1530年。笔者最近在《辑稿》礼20之107发现一条青山神祠的材料,从而把有关青山庙的记载提前了将近四百年。(《新发现的青山庙最早记载》,载《惠安青山考》,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出版)
当然,这并不是说,对食货、职官、刑法、选举等类的利用已经很充分了,在史料方面已经没有多少潜力可挖了。恰恰相反,即使这几类,对它们的利用也远远没有到头;而且随着宋史研究的深入,新的研究领域的不断开辟,其潜力是极大的。
在这里还要谈谈对复文的利用。出于多种原因,《宋会要》的辑文有不少复文,既存在于《辑稿》中,相当多的部分则收在《补编》中。(读者如希望对此问题有进一步的了解,可参考拙作《<宋会要>辑本的复文》,《文献》1988年第3、4期)虽然是复文,其价值不可低估。我在《补编》的《整理说明》中曾指出,《补编》有些复文可补今本《辑稿》之缺,并以食货类的商税门为例。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一位博士的论文《北宋市马之研究》,正是利用了这一门的复文,使北宋永兴军路、秦凤路与西夏接壤地区的商税额,得以有较完整的统计数字。(宋晞《宋史研究论丛》第4辑161页,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92年出版)
(二)辑佚的利用。
这方面的功能,过去似很少有人注意。它主要不是产生于《宋会要》本文,而在于《辑稿》和《补编》中的注文。
前面已经阐述了《辑稿》出现注文的原因。在《辑稿》和《补编》中,以《宋会要》作正文而以他书为注文的情况多见。这些作注文的文献,有些今天已无传本,有些传本也是辑本,有些虽非辑本但也非善本足本,可利用《辑稿》及《补编》辑佚。
例如李攸的《宋朝事实》,传本是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辑稿》注文所引《宋朝事实》,有些内容就是传本所没有的。
我相信,如对《辑稿》及《补编》注文作一次认真的清理,会在辑佚方面取得成果。
(三)校勘的功能。
《宋会要》可以说是宋代史料的渊薮。《宋史》在二十四史中卷帙最为庞大,食货志、礼志、职官志等各志,篇幅之长,超过各史;但若同《宋会要》的相应各类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无论是校勘宋代的各种文献,或者研究者使用这些文献,能否充分利用《宋会要》,效果大不一样。这方面既有成功的经验,也不乏应该汲取的教训。
三
上面简单地论述了如何避免误用《宋会要》和如何更好地利用《宋会要》。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问题,为什么《宋会要》容易被误用而又未能被充分利用?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现在通行的《宋会要辑稿》,是一部经两次转录、三次不得其法的整理、并且为整理者准备丢弃的底稿,与《宋会要》原本已有很大差别。
整理出一部能为广大读者正确而充分地利用的《宋会要》,是宋史研究者多年的愿望。现在可以说,经过多年的准备,条件已经成熟了。有志者,盍来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