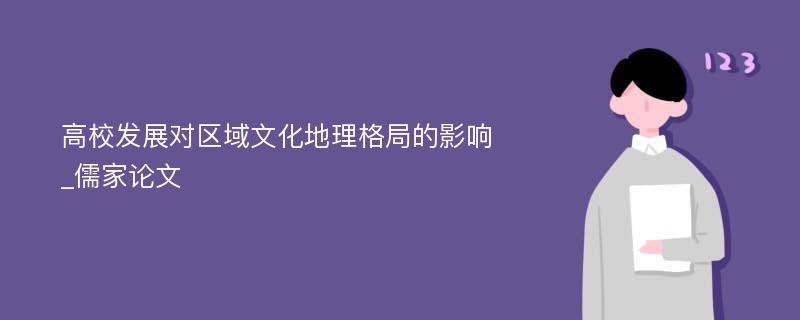
书院的发展对地区文化地理格局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书院论文,格局论文,地理论文,地区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08)05—0005—07
书院是儒学知识生产、创新、积累与传播的机 构,是儒家文化的重要象征。如果将书院置于社会文化的大系统中加以考察,我们会看到,书院在不同地域的发展会改变地方的文化生态,引起地区文化地理格局的变化。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书院的发展对地方文化地理格局的影响。
一 书院的发展与儒家文化的空间拓展
就整体情况而言,书院自唐代产生以后,就呈不断发展之势,其数量不断增加,分布空间也日益扩大。在其鼎盛时期的清代,数千所书院遍布城乡,除西藏、新疆等个别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外,全国各省书院林立,数不胜数,就不同地域而言,书院的创建数量在历代呈不断递增之势,到清代达到顶峰。书院的地域分布也日益广泛,清代大多数省份的书院已普及到县,许多偏远地区也有了书院,出现了所谓“穷乡僻壤,隔远都郡,亦就其地为书院”①[1]的情形。在此主要以湖南、江西两个地区历代书院分布情况为例加以说明。
湖南书院出现较早。据有关学者研究,湖南在唐代就已建立了7所初期形态的书院。②[2]北宋初期,在天下甫定、百废待兴之际,长沙岳麓书院就已开始创建并产生较大影响。宋元之际学者马端临所称的宋初四大书院石鼓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应天府书院中,就有两所位于湖南。③整个北宋时期,湖南地区创建书院达12所,主要分布于长沙、湘阴、衡山、临武、永州、兴宁等地。到南宋时期,湖南书院又有较快的发展,总数达44所以上。在当时湖南的15个州、郡、军,59个县中,有12个州、郡、军,27个县建有书院。元代时,由于政府对书院的保护政策,湖南共有书院41所,其中创建22所,恢复唐宋时期书院19所。从数量上看,元代湖南书院数量略少于南宋时期,但考虑到元代统治在湖南仅持续短暂的数十年,则可见当时书院仍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从地域分布上看,当时湖南的大部分州县已建有书院。明代,湖南书院数量达124所,其中修复25所,新建99所。从数量上看,已超过唐、宋、元三代的总和;而从地区分布上看,当时湖南全省56县,设置书院的已达53县,可谓分布广泛。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书院已推进到湘西、湘南的许多偏僻地区,如辰州(今辰溪)有书院5所,沅陵、溆浦、沅州(今芷江)各3所,黔阳、永顺各有1所。清中叶以后,湖南书院得到空前发展,总数达286所,全省各县均已建有书院,其中浏阳、衡山、攸县、茶陵、新田、溆浦、酃县(今炎陵)、兴宁(今资兴)、宜章等县均有书院10所以上。这些县大部分属相对偏远之地,由此可见,在清代湖南书院已经遍布三湘大地,真正达到了普及的程度。
江西书院始建于唐代。据李才栋先生的研究,唐代江西有高安桂岩书院、浔阳东佳书院、庐陵皇寮书院、南昌程氏飞麟学塾、庐陵登东书院、浔阳景星书院、李渤书堂共7所,其中江州3所,洪州2所、吉州2所。五代时期,江西又新建书院6所,其中洪州4所,吉州2所。北宋时期,江西书院发展迅速,约建书院40所,包括洪州8所,江州11所,南康军5所,抚州6所,建昌军6所,吉州5所,瑞州2所,袁州1所,临江军1所,饶州2所,信州1所,虔州1所,南安军1所,分布区域较唐、五代有明显扩大。南宋时期是中国书院发展的高峰期,江西地区表现尤为突出。始建于南宋的书院约170余所,分布地区包括当时12个军、州:隆兴府(原称洪州)21所,瑞州7所,临江军9所,袁州5所,抚州17所,建昌军2所,饶州37所,信州26所,吉州20所,赣州5所,南安军3所,南康军9所。元代江西始建的书院94所,分布地区包括龙兴路8所,临江路8所,吉安路19所,建昌路4所,南丰州1所,饶州路14所,信州路12所,南康路2所,江州路2所,南安路1所,抚州路14所,瑞州路4所,婺源6所。明代江西新建书院,有具体年代可考的达265所。清代江西新建书院达325所,修复前代书院74所,总数达399所,已经遍及全省各县。其中南昌一地清代新建书院就达19所,而地处湘赣边界较为偏僻的义宁州(今修水、铜鼓),在清代新建书院也达18所。万载一地,清代新建的书院就达25所,其中12所建于光绪年间。④如此数量之大,分布广泛的书院,反映了江西地区文化的兴盛发达及儒家文化的普及程度。
书院建立以后,就成为当地儒家文化的教育与传播中心。儒家士人以书院为基地,致力于儒家文化的传播工作。其具体的活动方式主要包括几个方面:第一,书院招收生徒,通过日常的书院教学活动,向生徒提供较为系统的儒学教育,传授儒学知识,灌输价值观念,培养儒家士人。这是书院儒学传播活动的基本形式。第二,书院举行面向社会大众的讲学、讲会活动,扩大儒学的影响。[3]讲学、讲会活动是书院文化活动的重要特色,也是书院实现其社会教化功能、实施文化垂直传播的重要途径。这种讲学、讲会活动往往实行“愿听者至”的原则,社会各个阶层的成员乃至田夫野老、贩夫走卒都可以参加,对象非常广泛。这些活动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明代嘉靖年间,江右王门学者邹守益等在江西、安徽等地建复古书院,组织惜阴会,“穷乡邃谷虽田夫野老皆知有会,莫不敬业而安之。”第三,书院还在书院内外设立祭祀场所,奉祀儒学道统传承中的代表人物和地方先贤,树立理想的人格典范,并经常举办有地方官员、士人、普通民众共同参加的各种祭祀活动,倡扬儒家的价值观念。[4]书院试图通过上述的各种活动,将儒家的思想观念、价值原则从书院辐射、渗透到社会的不同阶层,使之为不同阶层的人们所了解、熟悉,甚至体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他们尊崇信奉、身体力行的准则。
正因为如此,各地书院的建立与普及,对儒家文化在不同地区的扩展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一方面,在一些偏僻荒蛮的边远地区,尤其是南方的某些偏远山区,文化基本上处于主流文化的影响辐射范围之外,书院的建立就相当于文明的推进,美国学者琳达·沃尔顿(Linda Walton)在论及宋代书院时谈到,“坐落在‘不文明’的内陆地区如赣州的书院,起着‘文明’使者的作用”。[5]书院在这些地区的建立,就意味着“文”与“野”的分界线的改变。如湖湘地区重山叠岭、滩河湍急、舟车不便,所谓“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6]这种较为闭塞的地理环境对各种信息的交流传播都会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到宋元时期,湖南的一些边远地区仍处在一种荒蛮而与儒家文化相对隔绝的状态。如湖南靖州会同的广德书院在元代创建时,当地文化发展仍几乎是一片空白。“靖州居楚之极壤,洞庭渚其左,巴蜀据其右,狑獠与邻,猨鸟与游,而兵革之所狃藉也。”“土地偏陋,去上国遐远,士不典于学。”书院的建立才使得当地有了“弦歌之音”。⑤又如江西瑞州上高县蒙山,非常偏僻,多以采矿为业,儒家文化影响薄弱,出现了很多问题:“僻在万山之隈,近于宝货,则其民贪,远于都邑,则其俗陋,身不游于庠序,则耳目不濡染乎礼义。”到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蒙山银场提举建立正德书院以教山民子弟,授经书义理。延祐二年(1315)又重加修整增建,“延请师儒,招集徒众诵习其间”,⑥蒙山为此士习丕变,民德归厚。又如湖北郧县地处“楚西奥区,山高水险,俗尚朴醇”,到明代于莹中创建郧山书院才“渐知向化慕学”。⑦又如四川珙县,“僻处偏隅万山之中”“夷汉错处”,直到乾隆二十八年才有知县曾受创建南广书院,改变了“人自为学,家自为师”的状况。元代湖南慈利州天门书院创建之初,也是“傍邻獠峒”,而书院建立后,儒家文化得以迅速向当地渗透扩张,使当地成为儒家文化的覆盖区域,“士民怀道鼓箧而至,敬业乐群”,“欣欣顒顒,有如邹鲁”。⑧元代僻处湘西南崇山峻岭之中的武冈郡,天远地偏,众多少数民族聚居杂处,风俗民习基本游离于儒家文化圈之外,而元皇庆二年(1313)儒林书院建成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昔为要荒鳞辏之地,今为申夭燕居之堂。子衿子佩,游息藏修,冠带如云,弦歌盈耳。化其民为君子士夫,易其欲为礼义廉耻”。⑨可以说,书院的建立与普及使儒家文化空间的分布不断拓展,通过书院,儒家文化得以渗透传播到一些与原有的文化相对隔绝的偏远僻陋之地,儒家文化在地域文化地图中的比重大大提高。
从文化地理的角度来说,书院在一个地区的建立及其产生的影响,就意味着该地区被划入了儒家的文化版图。如宋咸平三年(1000)李允则重修岳麓书院之后,学者王禹偁说:“谁谓潇湘,兹为洙泗;谁谓荆蛮,兹为邹鲁”⑩。岳麓书院的发展,被视为湖湘地区从荆蛮之地到邹鲁之区的重要表征。
二书院的发展与区域文化中儒佛道势力的消长
书院的建立及其讲学与文化传播活动还可以营造出具有浓厚儒家文化气氛的人文环境,改变该区域内主流的儒家文化与其他非主流的文化形态之间的力量对比,使地域文化地图也随之改变。
一些书院的建造反映了儒家与道家之间力量的对比变化。江西奉新的华林山,早在晋代就是李八百与陶丘公修道炼丹之地,后来成为道教设坛的一个山头。(11)徐铉在《洪州华林胡氏书堂记》中谈到,“昔陶丘公、李八百皆修道于此。”但到北宋初,胡仲尧于此创办胡氏书堂“筑室百区,聚书五千卷,子弟及远方之士从学者数千人,常数十人。岁时讨论,讲习无绝。”(12)书院成为当时儒家知识传播的中心。这一点从当时人们题咏的诗句中可以看到:“南纪仙乡景最佳,林泉幽致有儒家。”“生徒似东鲁,书籍胜西斋。俎豆儒风盛,埙篪乐韵谐。”“义表衡茅外,儒官杳蔼间。家风类洙泗,世德有曾颜。……华林载图籍,从此是名山。”(13)华林山从道教仙乡、仙山变成了传播儒学的“名山”。显然,华林书院的创办,使当地文化格局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儒家文化在当地占据了主导地位。
实际上,不少书院就是直接取代道观而建的,如据同治《衡阳县志》记载,衡阳石鼓书院,旧为寻真观,至唐元和间,士人李宽“改道观为学舍,其后因之立学,祠先圣。”安徽徽州黟县碧山原有道观,嘉靖四十年(1563)知县谢适杰于碧山之阳建碧阳书院,“易观为院,锄道家之径,开正学之域”。(14)湖北蒲圻县金叠山原为唐县学故地,后来,“有老氏者流,募材建张忠烈祠于其上,借以家焉,而族日侈大。”明正德年间,当地官员“期崇正学”“遂迁其祠于南郊”,而在叠山上建凤山书院。(15)安徽广德的复初书院的建立也属于类似情况。广德原有玄妙观,明嘉靖四年(1525)王阳明弟子、著名的心学家邹守益谪判广德州时,将道观迁往东郊,在其旧址上建立了复初书院,讲学其中,传播阳明心学。
依托书院建立的复初讲会在当地产生很大影响。广州菊坡精舍也是在原来道观基础之上改建的。陈澧《菊坡精舍记》载,“初,粤秀山有道士祀神之庙,曰应元宫,其两偏有台榭树木,曰吟风阁,后改曰长春仙馆,遭夷乱废圮。蒋香泉中丞与方伯议改为书院,方伯葺而新之,题曰菊坡精舍。”(16)也有不少书院的修建所反映的是两个地区儒佛之间势力与影响的消长。如江西庐山,本为名闻天下的佛教圣地,早在东晋时,就有著名僧人慧远等在此建寺。到唐末,李渤隐居庐山读书,南唐升元中,庐山国学建立,宋初,庐山国学改称白鹿洞书院。这几个事件改变了庐山的文化格局,使庐山成为儒学传播的重要基地。其中白鹿洞书院在北宋初“尝聚生徒数百人”,(17)兴盛一时,是所谓的“宋初四大书院”之一。后书院在经历战乱兵燹之后废圮。到南宋淳熙六年(1179),时为南康知军的朱熹准备修复书院。朱熹此举目的相当明确,即以书院为基地振兴、阐扬儒学以对抗佛道之学,改变当地文化地理格局。在向朝廷陈述修复书院的理由时,朱熹反复以庐山佛老之学的兴盛来比对儒学之衰颓,阐明兴复书院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庐山一带,老佛之居以百十计,其废坏无不兴葺。至于儒生旧馆,只此一处,……而一废累年,不复振起,吾道之衰,既可悼惧,而太宗皇帝敦化育才之意亦不著于此邦,以传于后世。”(18)“此山老佛之祠盖以百数,兵乱之余,次第兴葺,鲜不复其旧者。独此儒馆,莽为荆榛。……况境内观寺钟鼓相闻,殄弃彝伦,谈空说幻,未有厌其多者。而先王礼义之宫,所以化民成俗之本者,及反寂寥希阔,合军与县,仅有三所而已。然则复修此洞,盖未足为烦。”(19)显然,朱熹的不满与焦虑,都与庐山佛老的兴盛有关。最终,朱熹在经过种种艰苦努力之后,成功地完成了修复白鹿洞书院的工作,并着手聚书、购置院田、聘请教师、招收学生、设立课程,后来还以知军兼任洞主,亲临讲学,训导诸生。其友人、弟子等也一同讲学于白鹿洞书院。淳熙八年二月,心学派大师陆九渊也率众弟子由金溪到白鹿洞访问并讲学书院。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白鹿洞书院一片兴盛景象。此前庐山“寺观钟鼓相闻”而书院学校“寂寥希阔”的情形得以改观。朱熹以儒家文化抗衡佛道之学的目的终于达到。
又如安徽九华山,自唐代以后,就成为与武夷山、庐山齐名的名胜之地,佛道势力颇为兴盛,但儒家文化在这里处于弱势地位,以至明弘治年间王阳明游历九华山时,就深感“诗人、隐士,仙释之流相与经营其间,而未有以圣贤之学倡而振之者”。正德年间,当王阳明再次携当地儒生游山时,试图改变当地儒学不振的状况,“慨然欲建书屋于化城寺之西,以资诸生藏修”。王阳明打算建书院于寺庙之侧,以儒家文化与佛道之学相抗衡的意图表现得非常明显。但这一规划当时因故未能如愿。到嘉靖七年(1528),当地官员祝增才完成阳明心愿,在九华山建立书院,命名为阳明书院。阳明弟子邹守益在《阳明书院记》中说:“书院之建,群多士而育之,固将使脱末学之支离,辟异端之空寂,而进之以圣贤之归也。”这就点明了建立阳明书院以倡扬儒学,排斥佛道的目的。阳明书院建立后,九华山儒家与佛道二教的力量对比就发生了变化,文化格局为之改变。
在书院发展史上,许多书院与佛教的寺院之间呈明显的互为进退之势,非常直观地反映着当地儒家文化与佛教文化之间的力量对比。许多书院的建立,都有倡扬儒学而排斥佛道的目的。宋嘉泰元年(1201),江西泰和县宰赵汝谟建龙洲书院,学者周必大为之作《记》,谈到当时儒家与佛老之学在该地区的力量对比情况说:“太和,子男邦也。略考图籍,浮屠之居百区,老子之宫亦十五区,而额存屋废者不预焉。……今也昔之庠序皆转而为寺观。”(20)由于儒者教化不行,在泰和的文化版图上,儒家文化已随佛老之学的扩张而失去自身地盘。基于此,建立龙洲书院以改变泰和文化版图的意图就非常明显了。又如祭祀理学家尹焞的和靖书院,旧在苏州虎丘,“元初为寺僧所据”。明嘉靖二年(1523),太守胡缵宗以龙兴寺废基改复书院。(21)这一举措,所透露的是当时儒家士大夫以书院捍卫儒家文化版图的意识。这种废寺而建书院的情形,在书院发展史上屡见不鲜。如四川郫县子云书院原建于明成化年间,后为水月寺所据,到清代,邑人李长馥等“议废寺仍为书院”,(22)以扶植名教,振起人文。明嘉靖年间,四川眉州为纪念魏了翁建鹤山书院,也是“撤城西南隅尼寺为之”。(23)嘉靖十二年,四川嘉定巡按熊爵倡建九峰书院,也同样是出于崇儒黜佛的目的。彭汝实《九峰书院记》称:“韦皋镇蜀之日,有黔僧因山凿象,绀殿十层,其徒日众,槃礴至今。……学宫负高幖山阳,为黄冠据久矣。先是,郏子刻我皇上《敬一箴》于其上。至是,熊子复创书院于此,两山皆归学宫,崇正黜邪之意不谋以合,其道可称也。”(24)乾隆十九年(1754),四川潼川府太守费元龙将城东草堂寺“割其半为文峰书院”(25)。
废寺庙、道观而建书院,除了利用原有地基、屋宇等物质方面的考虑外,通过儒家与佛老之间力量的消长以改善当地文化格局的目的也是相当明确的。实际上,在同一地域内,儒家与佛道之学往往彼此难以相容而明争暗斗,争夺地方文化的主导权。田产、院产等方面的争夺只是文化竞争的一种表现。在书院与寺庙、道观的争夺中,不仅有上述的废寺观而建书院的情形,也不乏书院房舍学田为寺观所侵夺者。如元代学者黄溍《明正书院田记》称,始建于宋代的明正书院在元代以后,“田之夺于浮屠老氏者什七八”(26)。这种情势,可以为我们对儒者废寺观而建书院的意义有进一步的理解。(27)
三 从书院看儒家与民间宗教对地方文化主导权的争夺
在中国古代社会,民间宗教有其深厚的文化土壤和民众基础,各地民间流传的一些祀神乃至异端邪说也常常产生很大影响,在地方文化格局中占据一定地位,甚至在短时期内还有可能成为特定地域内的主导文化。对于民间宗教,历代官方有加以利用的一面,但更多的是防范、打击。由于民间宗教的存在与发展有可能对处于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儒学造成威胁,对于以儒家原则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生活秩序和人伦关系产生冲击,甚至颠覆儒家的某些伦常原则和价值观念,所以儒学与民间宗教往往处于一种紧张状态之中,许多儒家士人对民间宗教的怀有敌意,试图通过倡扬儒学来弱化、消除民间宗教的影响。为此,他们往往将禁毁“淫祠”、兴建书院作为掌握地方文化的主导权、确立儒家文化主流地位的手段。这类情形,在书院发展史上屡见不鲜。
如明正德年间,四川邛州“有威显庙者亦曰土主,邛人以五月一日为神诞辰,而相率文身礼庙,至有试皮肤于刀剑、费田宅于牲牢、杂男女于玩戏者,耗财蠹俗,习为故事”。这类情形,虽然对社会秩序的维持并无大碍,但在国家祀典之外另有祀神,仍不能为正统的儒家士人所容忍,所以儒家士人往往凭借在国家权力网络中的绝对优势地位,对民间宗教予以打击。正德十三年(1518)九月,巡按御史卢雍与邛州知州吴祥“委去神像,改前殿为了翁祠”,建鹤山书院,“使邛人讲肆其中”。神庙被改造成为儒家文化的教育、传播中心,威胁儒家文化地位的隐患被消除。当时学者杨廷仪作《鹤山书院碑记》称:“淫祠者,二家之羽翼也。无淫祠则二家之羽翼息矣。……书院之设,经正之先务,诸君子可谓有功于圣门也。”(28)所谓有功于圣门,即确立了儒家文化在当地文化格局中的绝对主导地位。
又如广东一带,民间宗教颇为兴盛,在国家祀典之外有很多民间的祀神。明嘉靖元年,广东提学副使魏校曾经“大毁寺观淫祠,以为书院社学”。这一举措,反映的是儒家士人试图借助政府力量,通过打击民间宗教、兴建书院、社学以推行儒家教化,确立儒家文化的在当地的主导地位的努力。到清雍正年间,广东潮阳又有“林妙贵、胡阿秋之孽,以后天教流毒远近,历历多年,所招诱四方无赖,为徒数百人。驾言能事符治病,为人求嗣,又能使寡妇夜见其夫,以故城村风动,澄、揭、惠、丰之人无不笃信其术,重研而至”。一时间,民众如醉如痴,为后天教所吸引,地方文化似有脱离儒家文化轨道之势。这种情况,招致了官方势力的干涉。在取缔这一组织后,知县蓝鼎元反思此事,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根本原因在于儒家教化不兴,未能以儒家的先王之道去导引民众,在当地确立儒家文化的正确导向:“谓教化不兴,使吾民泯泯棼棼之以至于此,实官斯土者之咎。今群邪灭息,醉梦初醒,此风俗还淳、人心返正、君子道长之一大机,不可不明先王之道以道之也。”于是创棉阳书院,“以为阖邑人士读书讲学之所”。书院的建立,使当地文化重新回到了儒家文化的轨道上,潮阳恢复了在儒家文化版图中的地位:“自书院既建之后,邪说息,诐行消,人心正,风移俗易,礼乐可兴。”(29)
又如广西奉议(今田阳),“一边隅小州耳,唐为西原蛮”,“元明而后,屡遭兵燹,家室流离”。清光绪年间,“州之冻暮洲玉皇阁麕聚男妇百数十人,湔染邪教,日习经咒,蹈白莲之故智,甚有女子终身斋素,誓不适人者”。主流的儒家文化面临着“邪教”的挑战。到光绪十四年(1888),知州李霑春改冻暮洲玉皇阁为崇正书院。这一举措,捍卫儒家文化、防止邪教蔓延的意图十分明显:“今日异端之学支离怪诞,邪行诐辞,浸淫边鄙,若不力为挽回,将世衰俗弊,人心浇漓,日陷溺于狂澜而靡所底止,俾斯民仍不得安于畎亩衣食,以同被圣人之化。”(30)在李霑春看来,儒家正学与邪教此消彼长,互为进退,只有崇正学而息邪说,才能换回危局,消除影响。显然,正是崇正书院的设立,使当地邪说猖獗的状况得以改变,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得以确立。
值得一提的是,在儒家士人建立书院从而与佛道及民间宗教争夺对地方文化主导权的过程中,儒学虽然总是凭借其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取得了最终的胜利,确立了自身在地方文化中的主导地位,但在此过程中,许多佛教、道教及民间宗教的某些元素也往往会渗透到书院文化之中。这一点,从许多书院对文昌帝君与魁星、关帝、后土神的祭祀活动可以略见一斑。(31)
自宋代后期,就有一些书院建魁星楼、文昌阁等,祭祀号称能主宰文章兴衰的文昌帝君和“掌人间禄秩,司科甲权衡”的魁星。到书院发展后期,对文昌帝君与魁星的祭祀已成为各地不同类型书院中比较普遍的情况。一些影响较大的书院如岳麓书院、广东应元书院,都建有魁星楼、文昌阁。清人戴钧衡批判当时书院此类现象说:“世欲多崇祀文昌、魁星,建阁居像,岁时敬礼,以谓主文章科名之事。昔之通儒已辨其谬,昭昭然不可诬矣。”(32)可见当时书院祀文昌帝君、魁星的现象由来已久,且相当普遍。
关帝、后土神等也是一些书院的祭祀对象。如福建诗山书院在清光绪年间祠关帝与后土神。(33)白鹿洞书院在明代新辟石洞之时,祀后土神。(34)在康熙初年,则建关帝祠、庐岳祠分别祭祀关帝、庐岳神。(35)岳麓书院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一度改六君子堂为岳神庙。(36)
清代汉口紫阳书院曾祀后土神。(37)清代广东肇庆端溪书院也曾经修建福德祠以供祀土地神。(38)
上述情形,反映了同一地域中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相互融合与渗透。实际上,也正是由于这种相互融合与渗透,使得地域文化格局不是简单的此进彼推,互为消长,而是呈现出更为错综复杂的状态。
注释:
①刘宅俊《桐乡书院记》,佚名《桐乡书院志》卷六,赵所生、薛正兴《中国历代书院志》,第9册,第762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9月版.
②参见张楚廷、张传遂主编《湖南教育史》上册,第107-113页,岳麓书社2002年12月版,此段有关湖南历代书院的数量,均从此书之说.
③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六十三,《职官考·教授》,第571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11月版.
④参见李才栋《江西古代书院研究》各相关章节,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⑤揭傒斯《靖州广德书院记》,《文安集》卷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8册,第245页.
⑥吴澄《瑞州路正德书院记》,《吴文正集》卷三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393页.
⑦艾浚美《郧山书院记》,湖北《郧县志》卷十,清同治五年刊本,
⑧余阙《慈利州天门书院碑》,《青阳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4册,第400页.
⑨赵长翁《儒林书院记》,《湖广通志》卷一百零七.
⑩王禹偁《潭州岳麓山书院记》,《小畜集》卷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6册,第164页.
(11)徐冰云《奉新古代书院》,第73页,奉新县志编委会等1985年6月编印.
(12)徐铉《洪州华林胡氏书堂记》,《骑省集》卷二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5册,第215页.
(13)《华林书院题咏》,徐冰云《奉新古代书院》,第5-27页.
(14)汪尚宁《碧阳书院记》,安徽《徽州府志》卷七,清道光七年刊本.
(15)王俨《凤山书院记》,湖北《蒲圻县志》卷三,清道光十六年刊本.
(16)陈澧《菊坡精舍记》,《东塾集》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537册,第267页.
(17)洪迈《容斋三笔·州郡书院》,《容斋随笔》下册,第4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7月版.
(18)朱熹《白鹿洞牒》,毛德琦《白鹿书院志》卷二,《中国历代书院志》,第2册,第31页.
(19)朱熹《乞赐白鹿洞敕额》,毛德琦《白鹿洞书院志》卷二,《中国历代书院志》第2册,第33页.
(20)周必大《太和县龙洲书院记》、《文忠集》卷五十九,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7册,第627页.
(21)江苏《苏州府志》卷二十六,《和靖书院》,清光绪九年刊本.
(22)李长馥《修子云书院启》,《四川通志》卷八十,清嘉庆二十一年刊本.
(23)王元正《鹤山书院记》,《四川通志》卷八十,清嘉庆二十一年刊本.
(24)彭汝实《九峰书院记》,《四川通志》卷八十,清嘉庆二十一年刊本.
(25)吴省钦《潼川草堂书院碑记》,《白华前稿》卷八,《续修四库全书》,第1447册,第632页.
(26)黄溍《明正书院田记》,《文献集》卷七上,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9册,第406页.
(27)丁钢、刘琪在《书院与中国文化》中利用历代各地地方志、书院志、书院记等资料进行统计,对各代书院与寺观互为进退的情形作了一览表,涉及书院239所,或改寺观为书院,或废书院为寺观,不少书院与寺观之间还几经反复.参见该书《附录二·书院与寺观关系一览表》,第207—226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10月版.
(28)杨廷仪《鹤山书院碑记》,清嘉庆《邛州志》卷四十三,《艺文志》.
(29)《鹿洲初集》卷十,清光绪重刻《鹿洲全集》本.
(30)李霑春《创建崇正书院碑记》,广西《镇安府志》卷十五,清光绪十八年刊本.
(31)丁钢、刘琪《书院与中国文化》一著中指出,书院祭祀文昌帝君、魁星、关帝等,是儒、道文化的交融在书院中的表现参见该书第41—42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10月版.
(32)戴钧衡《书院杂议四首·祀乡贤》,佚名《桐乡书院志》卷六,《中国历代书院志》第9册,第766页.
(33)戴凤仪《诗山书院志》卷六,《祀典》118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34)王溱《新辟石洞告后土文》,李应升《白鹿书院志》卷十二,《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册,第819页.
(35)《知府廖文英申详减租文》,毛德琦《白鹿书院志》卷十,《中国历代书院志》,第2册,第142页.
(36)丁善庆《长沙岳麓书院续志》卷一,《庙祀》,《中国历代书院志》第4册,第414页.
(37)董桂敷《祀后土文》,《紫阳书院志略》卷八,《中国历代书院志》第3册,第627页.
(38)傅维森《端溪书院志》卷三,《祀典》,《中国历代书院志》第3册,第36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