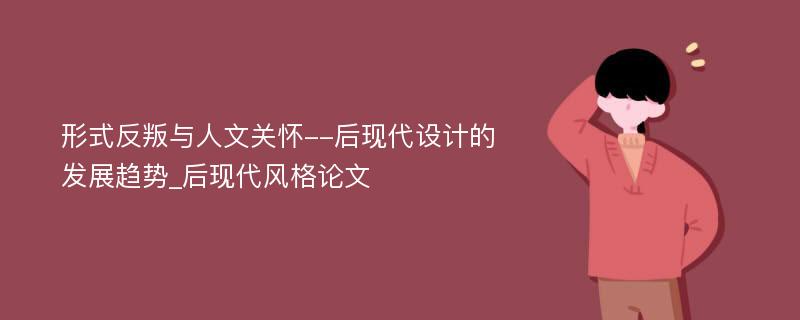
形式反叛与人文关怀——后现代时期的设计发展趋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论文,人文论文,时期论文,形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战后60年代的社会被称为“后现代社会”,是一个工业化的、多民族混合的、
消费主义的,
一切都建立在“有计划的废止制度”(planned obsolescence)上的、新闻媒介控制的“传播信息的狂喜”时代,变化最大特点是传媒、信息的大爆炸,一切都显得短暂、易变,后现代时期的设计不得不应付这个情况和环境。
70年代以后的各种各样的设计探索,主要是对发展到极端的现代主义、国际主义设计发起的挑战:求新求变的新生代对于一成不变的单调风格的抗议,造成装饰主义的萌芽;对于设计责任的重视而提出的调整要求,造成了现代主义基础上的各种新发展。
不可否认,现代主义设计曾经充满了民主的精神和革命的色彩,以它反叛、挑战的姿态,二战后在美国得到发展,成为独霸一方的设计风格,然而它的排他性,风格上的单调性,逐渐取消了原来的民主特点,意识形态上走向了自己的反面。60年代的美国,商业主义甚嚣尘上,现代主义的挑战性、民主性、激进性已被无孔不入的商业性所取代,成为一种非革命化的、单纯的商业特征。国际主义的垄断风格,抹煞了多元化,造成了一元化的设计形势,已经没有发展的余地,人们开始追求更加富于人情味的、装饰的、变化的、个人的、传统的表现形式,这就成为艺术和设计思想重要的催生剂。
另一方面,60年代的“丰裕社会”,消费主义刺激形成了巨大的消费市场,人们希望设计日新月异,而国际主义千篇一律的风格早已沦为厌烦的对象。人们不仅仅要求功能的完善,还喜欢装饰内容,对心理满足的要求日益强烈,企图利用新的装饰细节达到设计上的宽松和舒展,这是对过于理性化的倾向产生厌倦之后,希望设计上有更多非理性成分的自然结果。
所谓设计,就是创造一种把“价值转化为物态”,“物态上升为价值”,再从这一物态中进一步产生新的价值的一种反复轮回于价值与形态之间的良性循环系统。设计本身表达了技术的进步,传达了对科技和机械的积极态度;它以物质形态,构筑起生活文化的空间,予人广博的文化浸染。
后现代时期的设计者们孜孜不倦地在设计领域发动形式革命,通过对艺术语言、感觉和理解力的改造,将形式的冒险与批评态度相结合,反叛既有的艺术秩序,颠覆大众随顺世俗的惰性。但是,至关重要的是,后现代设计所体现的“革命精神”之真伪,取决了其艺术形式的变异是代表一种对既存现实的抵抗姿态,还是出于把玩、自娱亦或艺术投机之类的动机。因此,后现代设计对于设计责任的重视不能将人格因素排斥在外。
反叛惯常审美方式,破坏僵硬的标尺,强调艺术形式的陌生化和不可重复性,是后现代设计观念的主要特征。正是基于对既有的、垄断的、权威的国际主义发起的挑战,形式上的离经叛道才有积极含义,在“为艺术而艺术”的形式主义表象背后,有一种内在的人性本体的使命感的存在,不为标榜张显个人主义色彩,而要甘于俯首为群体,为人类生活服务,这才是世纪末设计师义不容辞的责任!
后现代设计之所以成为一种思潮,一种趋势,甚至一场运动,同人的自身意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愈加普遍的觉醒有关,也同现代工业文明下日趋加重的物质化现实与人的自由本性之间构成更为激烈的冲突有关。“反对”只是一个破坏的过程,“建立”才是设计的根本。反对什么,用什么去反对?建立什么,怎样建立?——我们在不断思考与反复追问中寻求答案,以使艺术的设计和设计的艺术重新关注人类情感取向和精神价值。
“后现代其实就是一个力场,在这个力场中,截然不同的文化冲动必须依照各自的方式去发展。”杰姆逊在他著名的《后现代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中这样阐述。新的文化冲突,使种族和文化混杂问题变得尖锐起来。
世界各国艺术家们所面临的问题焦点是一样的,即对现实的人文关怀。只是每个人因各自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的不同而采取的切入点有所不同。艺术以人的审美价值作为支点,而人首先是个人、地域、民族的人。以新国际主义观点为主旨的设计,主张多元文化和平共存的新型国际关系,十分鲜明地区别于现代主义的国际化倾向,而带有了地域和民族的特征。因此,这里的国际化并不意味着取消文化的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
比如日本的设计和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的设计,都是兼具民族特色和现代感的优秀典范。日本设计特点是它的传统与现代双轨并行体制,针对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两种设计体制也是双轨并行。在发展现代化时能完整地保持,甚至发扬了民族传统设计,并没有因为现代化而破坏或削弱了传统设计,两者的完美之境令人侧目。斯堪的纳维亚五国中最小的国家丹麦,其设计在风格上被喻为“不受时间限制的风格”,现代的结构特征与典雅细腻的民族手工艺相结合,精益求精,无懈可击,在国际上独树一帜。
必须承认,不是任何一种民族化都能标志人类感觉和表达方式的发展水平的,实际上国际化的真正含义是时间概念上的现代化与当代化,因此,可以用民族当代化来说明民族特征和国际尺度的关系。各国的艺术必须在与国际的对话或交流中产生,传统必须经历现代性的转换。
“越有民族性就越有世界性”的观点也应适应新时代的特点去辩证地考虑,否则就会发现原来似乎是正确和极具说服力的见解面临崩溃的危险,或者是将人的观念导入误区。我们不必讳言民族性的问题,因为民族的血液不断地在刺激艺术创作主体,并提供了深厚的土壤。把民族性看成是发展障碍,是一种很短视的看法。中国当代艺术设计的民族精神应在更高的审美层次上进行探索与追求,在与国际的交流中,发展设计艺术的新形态,使其具有国际水平,以其不可替代的当代价值成为国际当代文化的一支奇葩。
中国的设计不可能囿于本土,如今中国的设计师们在不断地实践探索中,突破了以往单一观念的束缚而获得了较大的空间,如果说,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对本土精神的追求,对外来技法的溶合吸收,是“现代设计”表层行为的集中表现,那么,更进一步,可以看出一个突出的举动,就是努力用饱含中国化的处理与改造的方式,以实现与世界的接轨。我们的传统在这个过程中吐故纳新,不停地演变,它将永远处在未完成阶段不会老化。当传统需要更新时,它难免会出现阵痛,而这阵痛正意味着现代的来临。“现代”、“后现代”根本不是传统的敌人,而是传统自我更新时的表达方式。
从现代到后现代,如何在不断地否定“已在”、否定自我的基础上再跨越一个台阶,真正的个性语言在哪里?正象过分重复以至不用辨认会造成一种相似(如国际主义风格),极度拆解以至难以识别同样也会造成一种相似(泛滥的解构主义潮流)。我们的设计应是观念和形式的双重设计,才会在由不认识到认识的过程中,由不成熟走向成熟。过分自卑和过分膨胀,都不能正确地看待和估计我们与国际的差距,都不利于中国设计的健康发展。我们应该站在一个客观的文化立场上,以我们所生存的这个国家,它的文化、政治、经济背景这一切构成的人文因素,来看待我们目前的落后和发展。
我们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并得到相当层次的国际参与的机会,这将使我们更清楚自己的文化进程在世界大文化进程中的位置和角色,以及这位置和角色的不断变化。真正的自信来自对当下社会意识的敏感和对本土文化及现实反思的自觉,这使我们有可能以一种新的形态及方式对待国际参与。
有一点始终应该坚持:设计只有在原创性得以充分显现的基础上,才有独创性的唯一和首创性的空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