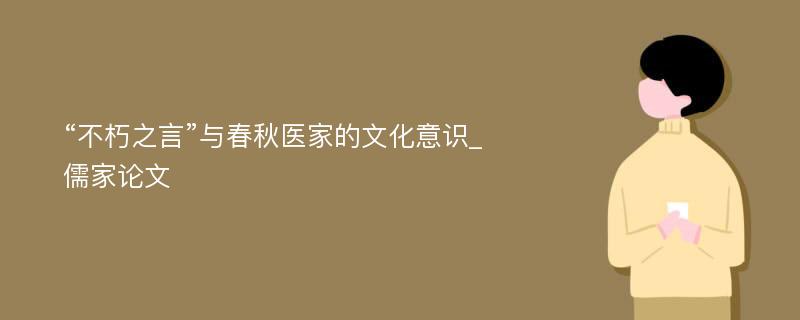
“立言不朽”和春秋大夫阶层的文化自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夫论文,阶层论文,春秋论文,自觉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4)04-0060-06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鲁大夫叔孙豹云: 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这就是所谓“三不朽”。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认为:立德即“创制垂法,博施济众,圣德立于上代,惠泽被于无穷”;立功指“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指“言得其要,理足以传”。惠泽无穷的“德”,价值要高于济于一时之“功”,而“立言”难见“博施济众”和“拯厄除难”的实效,故又等而下之。立德、立功、立言者分别为“上圣之人”、“大贤之人”和“又次大贤者”。而形成三种人格的原因是“人之才知浅深”①。“三不朽”显示了三个由高到低的等级,这已经被后世广泛接受。但由具有命定色彩的“才知”决定着成圣还是成贤,这与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相抵牾。今人则期望通过模糊“三不朽”之间的差异来解决这些困惑②,但这又与《左传》原文不符。叔孙豹曰:“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据《左传》所载,臧文仲为鲁卿,庄公二十八年曾“告籴于齐”,僖公二十一年谏焚巫尪使“饥而不害”,僖公二十六年“以楚师伐齐,取谷”,等等,颇有恤民之德和救败之功。那么,叔孙豹为何要舍“立德”、“立功”而独认等级较为低下的“立言”呢?显然,“三不朽”的成立一定受制于某种制度性因素,找出这个因素,才能真正理解“三不朽”的内涵及其意义。 一、“三不朽”本义 关于“三不朽”的主体身份,《左传·襄公十九年》所载臧武仲的一段话可以给我们以启发: 季武子以所得于齐之兵作林钟而铭鲁功焉。臧武仲谓季孙曰:“非礼也。夫铭,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今称伐,则下等也;计功,则借人也;言时,则妨民多矣,何以为铭?” 鲁襄公跟随晋平公围攻齐国,获胜。季武子用缴获来的兵械铸钟,并作铭颂扬鲁襄公的军功。臧武仲根据铭文礼制,认为攻伐之事不可用来称赞诸侯,而且败齐之功属于晋君,鲁君不得贪冒。从这段话来看,就铭文而言,天子称德,诸侯称功,大夫称伐,三者不可混淆。铸器作铭,为了上报祖先、下以传世,所以铭礼也一定体现了社会价值标准和表达规范。也就是说,春秋时代,各阶层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追求,不可错乱。将三等铭礼和“三不朽”进行比较,两者都是关于个体最高价值的表述,前两项都是“德”和“功”,只是第三项有“称伐”和“立言”的区别,可以推断,三等铭礼和“三不朽”其实是一回事,只是说法有异而已。那么,“三不朽”实际可表述为:天子立德,诸侯立功,大夫立言。所谓太上、其次云云,说的是天子、诸侯、大夫地位的差别。这就是叔孙豹为什么不敢称颂臧文仲的恤民之德和从政之功,而专言其“立言”的原因。 杜注“天子铭德不铭功”③,反之亦然,诸侯或大夫“铭德”就是僭越,“德”是天子专有的价值属性。晁福林说:“从甲骨卜辞的记载看,殷人所谓的‘德’更多的是‘得’之意。在殷人看来,有所‘得’则来源于神意,是神意指点迷津而获‘得’。”④殷王是甲骨占卜的主持者,所以他专有神意的“德”,故卜辞多见“王德”二字。西周文献中,“德”常被用来表示王权受诸天命的合法性。如《诗经·周颂·维天之命》云:“维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此处的“维天之命”,实即《大盂鼎》铭文所谓“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⑤,是“文王之德”昭示了周革殷命的合法性。这种用法在春秋时期仍然可见,如《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其中的“德”亦为受有天命之意。此后,“德”义有所演变,但往往与天子有关,如《国语·鲁语下》载孔子曰:“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远也,以示后人,使永监焉。”这里的“昭其令德以致远”,就是展示其天子之德性和德行,使方国服膺。又《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载富辰谏周王云:“大上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由于“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只有天子才有可能拥有“抚民”之德。也就是说,“德”是天子受命的合法性所在,是天子所能展示出的令人服膺的品质,所以才会有“天子令德”、“大上立德”的说法。 所谓“诸侯言时计功”,杜注“举得时,动有功,则可铭也”⑥。“时”在春秋时期是一种重要的价值标准,“得时”与否一般有两方面的参照:祭祀的时序和农时。臧武仲所云“妨民多矣”,指的就是使百姓错过农时,此为“不时”。显然,“言时”是对诸侯行政治民的考察。那么,“计功”是什么意思呢?《左传·庄公三十一年》载:“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从这句话来看,诸侯击败夷狄可以算是“功”,而战胜周朝之内的诸侯国,则不能算“功”。周初封建诸侯的目的是“藩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辰曰:“周之有懿德也,犹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怀柔天下也,犹惧有外侮;扞御侮者,莫如亲亲,故以亲屏周。”也就是说,封建的最重要功能是“屏周”,诸侯受王命而征伐夷狄,即是“屏周”之行为。《左传·成公二年》载:“晋侯使巩朔献齐捷于周。王弗见,使单襄公辞焉,曰:‘蛮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毁常,王命伐之,则有献捷。王亲受而劳之,所以惩不敬、劝有功也。兄弟甥舅,侵败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献其功,所以敬亲昵、禁淫慝也。’”诸侯征伐“兄弟甥舅”之国,即使出于王命,也不能献功,也就是不被周王认可。据此可知,在最初的含义上,诸侯的最高价值就在于尊王命以讨伐四夷。所谓“计功”,指的就是向周王献俘、献馘,如《虢季子白盘》云:“搏伐猃狁,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执讯五十,是以先行……献馘于王。”⑦铭文记载了虢国国君奉命讨伐猃狁获胜献俘之事,其中“折首五百,执讯五十”云云,就是“计功”。春秋时期,“功”的含义有所扩大,一般的“役王命”或尊王行为,都可以被称为立功。《周礼·夏官·司勋》将“功”分为六种:“王功曰勋,国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劳,治功曰力,战功曰多”,并说“凡有功者,铭书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勋诏之”。早先的“四夷之功”在这里只是被包括在“勋”之中,“功”被扩展到诸侯王的各项政治、军事行为当中,含义大大丰富了。但“功”主要作为诸侯的属性,这一点却仍然保留着。 “役王命”为“功”,从诸侯之命则为“伐”。孔颖达正义说:“若称伐,则从大夫之例,于三者为下等,不足为功美也。”⑧“大夫”作为贵族等级名称,约出现在西周后期⑨。西周和春秋前期,比较活跃的是周王朝的卿大夫,他们承担着治理王畿、出使诸侯和带兵出征的责任,其德性观念和标准早已形成⑩。到春秋中后期,诸侯国大夫的政治地位越来越重要,臧武仲所谓“大夫称伐”,指的就是诸侯国的大夫。诸侯大夫一般分为公族大夫和异姓大夫,前者是由国君的家族分裂出来的,后者则多为积累军功而被擢升为大夫的。大夫在经过数代沿袭后,形成世族,在诸侯国内拥有很大的权利和很高的地位。从现有文献来看,诸侯国的大夫以自己的私人武装为国君征伐,乃是其最基本的义务。张荫麟论曰:“一个大夫和他私家的僚属战士,每每构成一大家族:他出征的时候领着同族出征,他作乱的时候领着整族作乱,他和另一个大夫作对就是两族作对,他出走的时候,或者领着整族出走,他失败的时候或者累得整族被灭。”(11)《左传》中关于卿大夫为诸侯出征,并且拥有家族武装的记载很多。可以说,拥有私人武装,是诸侯世族最为显著的特征,而听从诸侯命令出征,并且通过战争积累功劳,壮大家族的声誉和势力,就成了大夫的主要目标。 春秋时期,人们认为人死后将成为神灵,并通过“世不绝祀”来维系其存在。一旦断绝了来自子孙的祭祀,则将成为孤魂野鬼,也就无法显示其存在。所以,个体生命是通过家族来延续的,这就是“保姓受氏”而“不朽”的意义,而“大夫称伐”则是“保姓受氏”的前提。 综上可知,“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三等铭礼,反映了天子、诸侯、大夫三类人群不同的社会责任和价值追求。那么,“大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三不朽”,也同样反映了天子、诸侯、大夫三个不同阶级的社会理想。两者的差别在于对大夫阶层理想的表述,是“称伐”还是“立言”?两者又有什么关系? 二、从“称伐”到“立言” 天子和诸侯的理想,早在西周初期就已经形成了。到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才逐渐兴起的大夫阶层,正处在一个快速变化着的社会,其价值观念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西周康王时器《大盂鼎》铭文记载康王对大臣盂说:“今余唯命汝盂绍荣,敬雍德劲敏,朝夕入谏,享奔走,畏天威……王曰:盂,乃绍夹尸司戎,敏敕罚讼,夙夕绍我一人烝四方。”(12)从这段话来看,盂的主要职责是进谏、奔走和司法,对他的德性要求除了一般的“畏天威”外,具有针对性的就是“敏”了。《诗经·大雅·烝民》所谓“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是对“敏”最周到而恰当的解释。“敏”兼有明智和勤勉的意思,它的对象是作为“一人”的天子,它的目的是“以保其身”,进而言之,就是“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求得家族的“不朽”。显然,西周时期的大夫之德社会价值较低,他们被严格限定在自己的职事和家族的范围之内。 这种观念对春秋诸侯国的大夫有着较大的影响。《左传·成公十七年》载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乱。失兹三者,其谁与我……君实有臣而杀之,其谓君何……受君之禄,是以聚党。有党而争命,罪孰大焉?”又《国语·晋语一》载晋大夫荀息曰:“吾闻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闻违命。君立臣从,何贰之有?”他们以“受君之禄”的“事君者”来界定大夫的社会属性,在此条件下所形成的“信、知、勇”等价值规范,对“敏”的突破是极其有限的,其核心还是无条件地服从、服务于诸侯。 另一方面,随着天子衰微,春秋时期诸侯国的各种政治活动、军事活动明显多于西周时期,诸侯国大夫在奉命征伐的同时,也有了更多的外交内政的工作,其政治和文化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诸侯国内政治动荡,大夫篡弑时有发生。大夫阶层开始有摆脱诸侯,追求独立的主体价值的意愿。以征伐邀功于诸侯,显贵于祖先,将自己的价值局限于家族的荣衰上,这种观念已经落伍,一种新的价值观开始形成。 西周和春秋时期,卿大夫除了带兵征伐外,还要参加祭祀、策命、结盟、朝聘、宴饮等仪式性活动。仪式性活动往往有巫史参与。《国语·楚语上》云:“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也就是说,君臣各类仪式性活动大多都离不开巫史人员的引导,他们才是政治和社会活动中的“专业人员”。而巫史的职业才能除了宗教和礼仪知识外,另一个重要的显现形式就是各类言辞或文辞。从《左传》中可知,早期为周王出使列国的主要是内史过、内史叔兴、内史叔服等史官。僖公十一年,内史过赐晋侯命,复命周王曰:“晋侯其无后乎!王赐之命,而惰于受瑞,先自弃也已,其何继之有?”由此可以看出,史官在西周和春秋早期的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不过,史官的政治地位在西周以后一直是呈下降的趋势,《左传》所记载的史官出使,往往是和卿大夫相伴而行,如内史过赐晋候命就是与邵武公同行,而到春秋中期之后,出使、朝聘、结盟等,则主要由卿大夫承担,有时会有“使者”或“行人”这类低级史官充当辅助性角色,主持者就很少见到史官的名字了。也就是说,在王室衰颓、礼崩乐坏的历史背景下,诸侯国卿大夫在各种政治场合越来越活跃,于是,言辞作为突出的政治外交才能,受到大夫阶层的高度重视。 言辞或文辞在春秋政治活动中十分重要,郑国子产的故事可为典型。郑“国小而逼,族大宠多”(《左传·襄公三十年》),可谓内忧外患,子产作丘赋、铸刑书、不毁乡校,并且以个人的才华赢得其他诸侯国的敬重,为郑国争得较为宽松的环境。在这个过程中,最为人所称道的是子产的言辞。《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子产乃问四国之为于子羽,且使多为辞令;与裨谌乘以适野,使谋可否;而告冯简子使断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应对宾客,是以鲜有败事。”又《论语·宪问》载孔子云:“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由此可见子产高度重视并十分擅长言辞。当郑人聚集乡校以议论执政的时候,他不毁乡校,而且要“闻而药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这其中就有容忍、鼓励言辞的意思。孔子论子产云:“《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左传·襄二十五年》)从子产的例子可以看到,大夫阶层已经主动学习史官的言辞才能,并逐渐取代了他们在政治活动中的地位。 此一阶段,出现了“辞顺”或“有辞”这类概念。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晋将鲍癸评论楚将“其左善射,其右有辞,君子也”。文公十四年,晋赵盾以诸侯之师八百乘纳捷菑于邾,邾人辞曰:“齐出玃且长。”宣子曰:“辞顺,而弗从,不祥。”乃还。襄公二十五年,面对晋人责问郑国为何攻陈,子产侃侃而辩,赵文子曰:“其辞顺,犯顺,不祥。”襄公三十一年,子产坏晋馆垣,并严辞责晋,使晋信服。叔向评论云“子产有辞,诸侯赖之”。在“辞顺”或“有辞”的评价中,对言辞有着神秘的、过度的推崇,这是言辞能力从巫史阶层转移到大夫阶层初期所形成的特殊状况。对于史官来说,“辞”是一种职业性的技能,而对于刚崛起的大夫阶层,“辞”既是一种值得学习的技能,也是一个值得膜拜的传统。《诗经·鄘风·定之方中》毛传有所谓“大夫九能”之说:“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为九德,可以为大夫。”这里所描述的可能是个理想状态,但至少可以说明,在此后的发展中,言辞已经成为卿大夫阶层最为重要的修养。 从“称伐”到“立言”,显示了大夫阶层社会理想的转变,这在《左传》中只间隔五年的时间,它反映了社会文化的急剧变革。“大夫称伐”所追求的乃是将个体价值融入到宗族“世禄”的链条中,通过永保“世禄”来实现自己生命的“不朽”;而“立言不朽”则有着根本的不同,“是直以人文成就于人类历史中的价值,代替宗教中永生之要求”(13),是将个体价值纳入到社会和历史中,从而超越了宗法文化的范畴。 三、“立言”的文化内涵 “三不朽”表达了三个阶层的不同价值追求:天子立德,诸侯立功,大夫立言,同时,也可以将其看做是三个前后相继的历史阶段的最高价值标准,它们显示了社会主流话语权力的传递过程。 西周前期,通过长达百年的礼乐文化建构,形成了从后稷“农德”到文王、武王的“文昭”、“武烈”等为代表的“王德”谱系。后嗣诸王无不以“嗣守文武大训”(《尚书·顾命》)、“扬文、武之烈,扬成、康、昭主之烈”(《清华简一·祭公之顾命》)(14)自勉,希望能效法先祖圣王,以“德”维系天命,泽及万世。对于天子而言,“立德不朽”的追求是其主体意识的体现:它既是为了保证天子“永言配命”(《诗经·大雅·文王》)的政治地位,也是为了展示其垂范天下的意识形态权威。西周后期及春秋时代,王室衰微,四方争霸,诸侯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主角,霸主打着“勤而抚之,以役王命”(《左传·成公二年》)的旗号,以“继文(晋文公)之业而信宣于诸侯”(《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甚至“求王者之功”(《国语·晋语六》)为理想,诸侯的“立功”中虽然也包含着“尊王攘夷”,但它越来越成为一个幌子,而成就霸业、号令天下,则成为一个时代的最高价值。“立功”这一观念,显示了诸侯期望在既往的宗法秩序之外,通过崭新的目标,站在价值至高点上,来实现并展示自己的主体意识。 春秋中后期,公权再次下移,大夫集团取代诸侯和及公室,成为政治主导力量。叔孙豹提出“立言不朽”的襄公二十四年,正处在大夫阶层政治活动高峰期的后段、而低潮期尚未到来之时(15)。大夫阶层正是通过“立言”建立起自己的价值观,并以此来取代“立德”和“立功”,彰示本阶层的社会地位。 那么,什么样的言辞才能算是“立言”呢?它首先必须是能够表现新的思想和观念,具有思想和教育的价值,如学者所说:“春秋时代只有那些富有教化意义,对时人以及后世子孙为政修德等各方面有普遍的指导价值的言论,才能长久流传,才能算是‘立言’。”(16)如隐公三年,卫大夫石碏针对公子州吁“有宠而好兵”发表议论云: 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为祸。夫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鲜矣。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君人者,将祸是务去,而速之,无乃不可乎?(《左传·隐公三年》)这一段话阐释了新的“教子之道”和六顺、六逆的伦理规范,它显示了大夫阶层试图对诸侯和公族进行制约,并期望用新的伦理观念逐渐代替旧的宗法观念,这是一个典型的“立言”。《左传》中所记载的“立言”,涉及到社会文化、政治、制度、伦理的各个方面,全方位展现了新的社会思想,这些“立言”承担着社会变迁中新的意识形态建设、为新社会立法的历史重任。它显示,大夫阶层已从狭隘的家族荣辱观中脱身而出,通过“立言”,成为垂范社会的“君子”(17),成为新时代的文化英雄。《左传》中“立言”载录非常多,而《国语》基本上就是从西周到春秋时期“立言”的汇编。春秋时期迎来了一个“立言”的高潮。 “立言”作为一个阶层地位的标志,必然具有某些形式上的规定性。《左传·昭公八年》载叔向评论师旷云:“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征,故怨远于其身。”这句话说出了“立言”的标准:“信”和“有征”。所谓“信”,也就是《易传·乾·文言》所谓“修辞立其诚”,“诚”和“信”指的都是“中正之心”、“敬畏之情”(18),能使人信服。它暗示了“立言”和早期神圣话语传统的联系。这种联系在形式上又表现为“有征”,就是有所征引。上引石碏所谓“臣闻”云云,就是一个征引。更为典型的“有征”是引《诗》、《书》、《易》等传统文献,其次是史事和礼仪制度,如襄公十四年师旷论“卫人出其君”云:“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其中就征引《书》以佐证自己限制君权的观点。前代典籍、史事、礼仪制度等此前都为巫史所职掌,是巫史传统有机构成部分。“征引”使得大夫“立言”和一个悠久的文化传统关联起来,从而具有了某种神圣合法性。 “有辞”和“立言”两者是有所区别的。“有辞”指的是熟悉巫史“经典”或其表述方式,并能自觉应用于当下的判断之中;而“立言”追求的则是使个体的“言”加入到“经典”的队伍中去,获得与“经典”同等的价值,为社会立法。如《左传·文公十八年》所载: 季文子使大史克对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礼,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队。曰:‘见有礼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贿为盗,盗器为奸。主藏之名,赖奸之用,为大凶德,有常,无赦,在九刑不忘。’”这段话将臧文仲之言和《周礼》、《誓命》之言相提并论,不仅意味着臧文仲“立言”的最终完成,同时还暗示臧文仲之言与前代“经典”前后相续,地位相当。这就是所谓“立言不朽”。因此,“大夫立言”这个观念,一方面认可“大夫称伐”中所包含的天子、诸侯、大夫政治身份的差异,互不取代;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各领风骚的方式,使得“立言”取代“立德”、“立功”,成为时代的主流和最高价值,并获得与“圣贤”同等的文化地位。它体现了大夫阶层对话语权力的追求和主体意识的觉醒。 上述现象说明,随着诸侯权柄渐渐旁落到强宗大族之手,价值取向也从诸侯“立功”转向大夫“立言”。到春秋晚期,随着士阶层取代大夫阶层成为政治和文化舞台上的主角,“立言”的接力棒也从卿大夫为主体的“君子”手里传递到士人手里。如果说后世以诸子百家为代表的士人阶层是以“文化知识和智慧”为资本、以“自我神圣化”为策略,“以‘立法者’的姿态出现在彼时的文化领域”(19)。那么,他们“立法”的追求、资本乃至策略,其源头都可以追溯到春秋大夫“立言不朽”的观念和行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