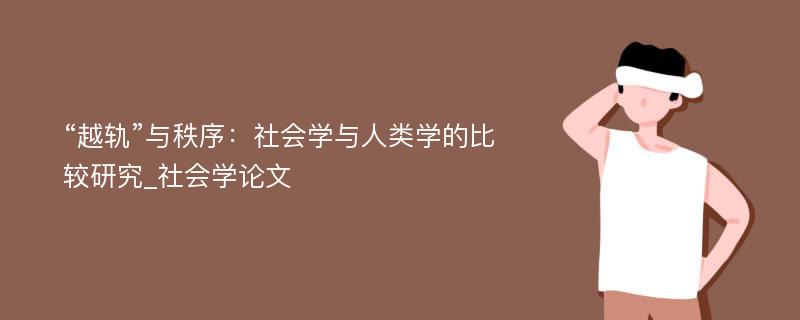
“越轨”与秩序——社会学与人类学相关研究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学论文,社会学论文,秩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秩序的破坏:社会学对“越轨”的研究
“越轨”(deviance)是指违反重要的社会规范的行为,亦称离轨行为或偏离行为。社会学由关注“社会问题”(social problem)而兴起,“越轨”(deviance)和最初社会学家们所认为的“社会问题”具有很大的关联和相似之处。所以,几乎每兴起一种新的社会学理论,都对“越轨”研究做出了或多或少的新贡献,其中早期和最近影响较大的理论有如下几种。
社会结构论主要以涂尔干和莫顿为代表。涂尔干比较关注社会病态和失范(anomie)问题,认为失范说明社会控制机制在两个维度上出现问题:集体意识丧失了社会规定性隐而不显;个体意识丧失了自我规定性而使欲望本身凸现出来。虽是从两个维度说明问题,但他没有区分失范(anomie)和越轨(deviance),因其更侧重于集体意识和社会事实。涂尔干《论自杀》便试图证明是社会解体引起了失序和越轨行为。莫顿则进一步把失序在集体和个体两个层面上进行研究,区分了anomie和anomia,使失范理论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上展现。Anomia使失范分析着眼于个体行为的筹划过程,试图在个体行动和社会结构之间建立关联。此处个体失范(anomia)和越轨(deviance)已无甚区别。莫顿认为越轨行为是制度化手段(Institutionalized Means)和文化取向目标(Cultural Goals)之间发生冲突的结果。他的模型显示了个体在此目标和手段之间的行为方式有遵从(Conformity)、 革新(Innovation)、仪式主义(Ritualism)、退隐主义(Retreatism)和反抗(Rebellion)五种,代表了个体行为者对于正当化的文化目标和社会化手段的不同态度和行为。革新与反抗行为的越轨者,其需求在现有的体制环境中无法满足或受到限制,不能以正常的途径达到目的,只有以非法的途径获得,或者干脆另谋出路。这一理论说明了越轨行为和其背景的关联,往往正是特定的制度和文化背景为其提供了动力和资源。对涂尔干和莫顿来说,秩序维持就是行为者行为的“合法化”,也就是行为者遵从制度及文化所认可的行为目标和手段,一方面,循轨行为和越轨行为(如“革新”)有时有着共同的学习过程、个体需求和价值取向;另一方面,越轨(如“反抗”)隐含在现有文化的价值多元和组织、制度的分类体系之中,规范变迁的动力多存于矛盾价值的冲突之间,而非主体价值的创造。
标志论(即标签论)与社会结构论不同的是,它强调的不是社会背景所决定的越轨者的动机和手段,而是越轨者的社会文化是如何认定这一行为越轨,强调了越轨行为的社会界定的主观一面,这等于认为没有任何行为是内在的(intrinsically)越轨或循轨,在人们变成越轨者的过程中,给其贴上标签是个关键因素。标签论不是把越轨存在的原因归于社会情境和促成其行为的“社会因素”,而是说,社会群体通过创建秩序,制定那些一经违反就会造成越轨的准则而创造了越轨行为。所以,越轨不是行为本身的特质,而是在越轨者同其反应者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种特质[1](P155)。虽然这一理论的局限对越轨行为本身有所忽略,但是我们既可以看出越轨行为的外在因素,也更容易理解贴标签对于秩序维持的重要性。舒兹的现象学派生出了本土方法论(也称常人方法学)。现象社会学企图通过行动者于具体情景中对社会的体验来理解社会现象和活动。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本土方法论(或常人方法学)感兴趣的是各种准则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当准则干预到实际活动时,准则不是被“废除”,而是被“重新解释”,是被“运用”而不是被遵守。并且可以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运用准则,不仅指导行为,还可以在行为发生之后以一种社会接受但未必真实的方式去解释行为。[2](P185)所以,本土方法论者感兴趣的是行为者自己的说明,即他们了解其行为的意义或对之加以解释的各种方式。这一理论视角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使我们看到了规范“后设”的意义,也就是说,看到了一个行为者如果应用规范使自己的行动“合法化”或“合理化”,规范在此成了一种策略。以往的越轨研究虽然给予了越轨行为本身的功能肯定和行为者本身的能动性说明,却剥夺了越轨的生存论意义。现象学的重要之处是:指出意义不是先验给予的,而是在行动构成的过程中呈现为思想和生活之间的张力状态。并提出具有限性的“意义域”概念,认为意义是多重的和不可通约的,行动筹划和意义解释有着存在论上的界限。也就说,行动者和评价者之间出于不同的目的,目的动机和原因动机并不能完全相互匹配,[2](P2)这就比莫顿的目的和手段论前进了一步。
象征互动论认为社会是其成员在其相互作用中建构起来的。社会内部的秩序是社会成员通过共同生活、共同学习而共同享有的各种象征(包括道德价值观念)的产物。象征论和结构论之间的区别在于,社会结构论认为社会遗传的价值观念是社会秩序直接的基本原因,个人的意图和动机是因为社会结构而引起的,共认的意义特别是共享的价值观念可以解释个人的行动。象征互动论则相反,认为共认意义虽是个重要变量,但无法完全决定人们如何对具体情境做出反应。结构论者认为人们所以越轨是被强迫或驱使的,而象征互动论者认为是人们选择了越轨行为。[1](P120)象征互动论认为,社会意义和行动是适应相互作用的实际情境而被建构起来的,这点和本土方法论比较相似,所以这两个理论往往结合在一起,难以区分。这里并没有否定共享的价值观对个体行为的作用,但却否定了这一价值观的跨时空的、恒定的、惟一或主要的作用。
标签理论的重要性在于关注社会群体对越轨者的定义和行为,以及越轨者的反应,故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一种互动理论。正如一些精神病人是在把其作为精神病人对待的过程中学会精神病的,标签起了很大作用。其实当代思想大师福柯也为此做出贡献,而且他是在更大的空间和更深的历史维度中来理解标签理论的。其卓越在于仔细探讨了标签过程中所包含的知识、技术和权力,特别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他把标签理论的应用时空扩大、加深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理论宣称犯罪和其他形式的越轨是由基因决定的,在此得到了最大的嘲讽,因为按照福柯的观点,正是这些学科,在对待越轨的过程中兴起,并在越轨的定义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总之,不同理论的关注点不同,有的强调外来的影响,注重越轨的外在社会定义及情境对越轨的塑造和作用,失范理论强调社会压力,标签理论强调外来定义。有的理论强调个体间的互动和个体对具体情境的利用,认为越轨是积极谋划和为获得特定利益的结果。从研究视角的侧重及研究规模而言,大致可以把诸多理论分为外因论、内因论和介于二者之间的综合因素论;宏观的社会结构层次,通过社会无序解释社会越轨,与此相对的是从微观心理学和生物学角度的研究(本文从略)。介于二者之间的是情境论和理性选择理论,肯定了主体在具体社会结构中能动的策略选择。随着研究层次的缩小,越轨者的能动性也越来越突出。其间不少理论都试图在社会结构和个体能动性之间进行综合,多数是在韦伯和涂尔干之间摇摆不定。
二、秩序的可能:人类学的相关研究
在人类学经典理论中,基本上不存在“越轨”这个概念(注:笔者也曾看到人类学关于“越轨”的专著,如《越轨——人类学的视角》(Morris Freilich,Douglas Raybeck,and Joel Savishinsky Deviance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1991.)。但此书所提出的三个模型给人的感觉是人类学向社会学已有越轨理论的靠拢,基本上是以社会学的越轨研究理论为原型进行加工,添加了一些人类学的调料而已,其真正具有人类学创意的地方并不多。)。社会学是在有国家的西方社会并以其本身为研究对象而发展起来的,而人类学家起始于关注通常认为是原始的、外在的、小规模的制度和社会。因为起始就是以“他者”为研究对象,所以对社会学来说极具反思性的新理论“本土方法论”在人类学来说却是“主位”(emic)观点理所当然的基本追求。人类学家如社会学家一样关注秩序及其维持,但不同的是,他们不是在自己的社会中去发现“异类”,而是干脆跑到本社会之外,去研究和本社会无关的似乎更加“异类”的部落和民族,并时刻提醒自己关注“当地人”的观点,关注“他者”的行动轨迹,“异类”被理解和同情为拥有其自身的内在合理性。所以人类学更多的是对特种“秩序”的关注,反而往往忽略了对此种秩序中“越轨”的研究。虽然同样研究“异类”,表面似社会学的“越轨”研究,但二者的研究取向却迥然不同。社会学研究往往以现存社会秩序的合理存在为前提,多研究这一秩序如何维持,这也是“越轨”理论得以产生的一大动力。而人类学从一开始就是以对现存秩序的怀疑至少是验证为出发点的,基于外在的比较,后者比前者更易探究、发现现存秩序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有无问题,也正因为如此,人类学倾向于研究某个社会或社区内整体的生活逻辑和思维方式,不少人类学家对此做出了贡献。
(一)秩序的进化与多元
梅因作为法律人类学的先驱,在《古代法》[3](P121)中对各式各样的法律传统进行分析比较后,提出了一个法律由简单到复杂的进化模型,认识到人与人之间关系上由社会身份到个体契约的转变。马林诺夫斯基在其对特罗布里恩岛详细考察之后所著的《蛮野社会的犯罪和法律》中对原始法也进行了阐述,他认为梅因误解了原始社会的法律和社会统治,通过实地田野调查观察当代人的风俗和习惯,他以民族志方式描述了一个复杂的民法和刑法体系以及惩罚强制系统。但他更关注法律的文化背景,以此来解释它的合理性,认为法律、规则、特权和完善的义务体系所产生的敬畏使秩序使然。霍贝尔在《初民的法律》中着重研究了七种原始民族,通过比较研究其法律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回到了梅因所运用的进化的方法,评述了它们各自复杂的程度,将法律进化分为四个时期。认为法律的发展是由于政府权威的加强和有组织的社会区域的扩大造成的,并受到经济规模发展条件的制约。他在评述梅因的著作时指出,在原始法的发展过程中,真正重大的转变并不是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上由实体法中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而是在程序法上的重心转移,即维护法律规范的责任和权力从个人及其亲属集团的手中转移到作为一个社会整体的政治机构的代表手中。[4](P316)企图说明不同的秩序,有不同的原则,更大空间秩序的维持需要更大、更强的权力。在此,以西方社会为归宿的进化论观念的影响还比较明显。
对于无国家社会秩序的关注,一度是人类学的热点,在这方面做的比较细致的是伊凡普理查。他通过对亚桑地人和努尔族人“追究责任”(tracing accountability)方式的研究,去发现一个社会基本的假设体系,寻找社会互动中影响注意力的选择性原则。努尔人的政治舞台上没有各种社会地位(social status),其生活却受到强烈的规范限制,每人都知道自己的权力、义务以及侮辱与伤害赔偿的标准。规则虽有,但权力分散于整个体系之中,每人都必须维护自己的权力,呈现一种“有秩序的无政府状态”(ordered anarchy),是一种结构距离在解决争端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法律的强制力随着纠纷者之间的结构距离的增大而减弱。所以,努尔人政治体系界限的建立不是源自部族间的协定或条约,而是源于逻辑的失败,政治意志和法律效力到体系的边缘就渐渐消失了。他们体系的界限也就是法律与秩序的界限,也是知识的界限。他们借助对本身社会体系界限的认识,对知识体系也设下了限制,然后再籍着无数的证据和实例,在整个体系中建立起真理和了解。[5](P169)他给我们的启示是,如何从日常生活入手去研究一个社区的制度以及制度背后的文化逻辑。一种秩序的背后不仅仅是权威或者权力,还包括一种认识方式,这和格尔兹的“地方性知识”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他的“归咎原则”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恰似越轨研究中的“贴标签的原则”,对于越轨行为进行贴标签的过程已经有不少社会学者做过研究,但对于这一“标签”背后所隐含的文化制度逻辑的研究却是很少,这也正是人类学整体论的优势所在。
(二)仪式与结构、象征与秩序
特纳(Victor Turner)在《仪式过程》[6](P57)一书中很好的体现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其早期的仪式象征论中,通过对非洲恩丹布人的田野调查,认为仪式夸大了社会统治的实际冲突并进而强调了一致性与联合的重要,最终实现了社会粘合剂的作用。在后期的研究中,特别是在《仪式过程》的后半部分,当作者关注于“阈限”(liminality)和“神会”(communitas)的时候,已不只是强调仪式的粘合剂作用,而是越来越关注“阈限”和“神会”的本体论意义。他把“社会结构”和“神会”看作相反的两种不同的社会存在形式。他并非如以往的功能主义者那样强调两种社会形式的共时性并列,而强调的是结构—反结构—结构的历时过程。这样,以往在空间上并置的文化和结构在时间上被展演开了。特纳特别关注仪式的反结构特性,在仪式中人性得以展现,并对社会结构进行反思,且仪式作为一个过程,其反结构特征不仅仅是对结构的强化,还有其自主的存在论意义。在特纳这里,社会内部结构—反结构—结构的“结构”模式使社会秩序成为可能,但这种结构是历时性的,类似于“越轨”行为的反结构对于结构是必需和必然的,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反结构已是结构的一部分。道格拉斯(Mary Douglas)也关注思想的结构(仪式)与社会的结构之间的关联。在《纯净与危险》中,她把“脏”界定为是一种系统安排和事物分类的副产品,违反了分类体系或者说在现有的分类体系无法给以定位或说明的时候,便是危险的和不洁净的。在《自然象征》一书中,道格拉斯寻找象征体系的特点与社会制度的特点之间的趋势和相互关系,提出在所有人类文化中存在着“一种要实现各层次体验中的和谐一致的动力”的假设[7](P224)。这点和特纳形成鲜明对照,如果说前者强调仪式—结构的“对立统一”,她便是“和谐一致”,重心放在象征类型与社会体验之间的一致性上。在《制度如何思考》中,道格拉斯告诉我们的是,一种观念和思维方式对秩序的维持最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制度是脆弱的,容易为私利动机基础上的行为所削弱,故制度须建在公义而非功利性或实用性的基础之上。而公义作为人们共享的基本理念,常隐含在自然或超自然的世界中。观念制度稳定性的渊源便是社会范畴分类的自然化,即通过类比(analogy)将关键的社会关系结构建筑在自然或超自然的世界中隐而不显。所以,认知、记忆和社会制度息息相关,因为这也正是类比的运作过程[8](P18-24),现代国家对意识形态的强调往往正是由此获得启示。
虽然一个关注一致,一个关注冲突,特纳和道格拉斯在关注社会与象征、制度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联上仍有相同的努力。尽管格尔兹的关注点也差不多,但他们的图式是有区别的,格尔兹认为文化结构和社会结构不仅互为镜像,而且也是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赖的变量。在《文化的解释——仪式与社会变迁:一个爪哇的例子》一文中,认为功能主义之所以难以解释变迁,在于它不能平等的对待社会过程和文化过程;二者之一往往不可避免的被放弃或仅成为对方的前缀和“镜像”。他强调区分人类生活的文化面和社会面,把他们看成独立变化且又彼此依赖的因素。他看到了两者之间的断裂,也由此看到了推动变迁的主要动力。在这里,仪式并不仅仅是个意义模式,也是一种社会互动形式,符号的政治意义与宗教意义之间可能发生冲突。[9](P176)另外,格尔兹在《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一文中指出法律事实非自然生成,乃社会之产物。故法律所关注的不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而是现在或将来会发生的事情,由此指出“任何一种企望可行的法律制度,都必须力图把具有地方性想象意义的条件的存在结构与具有地方性认识意义的因果的经验过程勾连起来,才能显示出似乎是对同一事物所作出的深浅不同的描述”[10](P83)。在他看来,法律和法律的实施都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只有在地方性的情境当中也才能理解它。
三、秩序的维持与变迁: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启示
(一)秩序的维持社会学学者从本土社会内部看社会秩序及其维持,容易预设规范的统一而忽略规范的多重性、冲突性和可替代规范的可能性。关于秩序维持中的规范性因素,早期的社会学家已认识到道德的重要性,后来又区分了道德和准则,认为道德先于准则,准则先于行动,并推理出越轨行为违反道德的绝对主义观点。有关“越轨”研究的新观点则说明道德受情境左右,无跨时空道德的存在,越轨与特定的价值和地位有关,这些研究反叛了秩序是铁板一块的绝对主义观点,使学者更加关注不同价值的冲突和替代规范的可能性。
在经典社会学家的思想中,文化和制度并非截然区分,随着社会学愈来愈经济学化,韦伯的理解社会学宗旨逐渐被忽略,秩序意味着“效率”还是“意义”成为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一个重要分野所在。而新的社会学越轨研究特别是本土方法论、互动论等是对这一理性主义取向的反叛,这既是对经典社会学的某种回归,也是借鉴或契合人类学和其他学科理论的一大表现。但人类学不仅关注“意义”,它对秩序的研究从两个层次上可以给社会学带来启示:一个是社会或社区内部秩序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和社会学研究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它认为秩序不仅和理性及效率相关,还和认知方式、仪式象征以至于整个生活相关;另一个是社会外部秩序的多元性,这不仅是指多种秩序方式在时间上的演化,更重要的是空间上多元秩序并存和交流的可能性。人类学使我们努力跳出自己的现存社会,从外部更广、更深的时空背景研究各类秩序的维持关系。
就社会秩序内部复杂性而言,人类学从整体上关注各种因素对于秩序维持的意义。其研究对象除国家政治制度外,还有民间非正式的组织制度,以及其背后所隐含的观念体系,并关注观念体系和行为之间在社会历史背景中的关系与变迁。社会行为包含着外在的规范性结构限定和特定的情境性策略选择,也包含着情感的非理性诉求。人类学者对秩序维持的方式最初有一个进化论的排列,如梅因认为其重要因素是社会身份也就是血缘和地缘关系到理性契约、国家强权的转变;其后是对进化论的反叛,结构主义的影响深远,特纳关注到了仪式以及“神会”等反结构因素对社会结构的重要作用;道格拉斯注意到社会知识分类体系以至于神话等对于制度的自然化,即强化;福柯也发现了权利产生的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权利运作的复杂性,通过知识考古,研究了“权力”、“知识”和“自我技术”在维持秩序中的关联。总之,秩序被理解为是一种道德,是习俗,是制度,是组织,是权力、是信仰、是知识、是逻辑,其间有一致也有冲突,以至于包含了生活的全部。
对于秩序的复杂性、层次性,社会学对于某个方面的专题研究突出,但整体研究比较薄弱,因为社会学研究务必关注现实社会,但随着社会的日趋复杂,社会学研究的分工也更趋细致化、精密化,关于秩序的研究,往往只能关注其中的某一个方面,如某一制度或组织等等。相比之下,人类学以研究部落或社区起家,空间的相对狭小,使人类学者更关注社会文化的一体性。所以,社会学往往把社会秩序化归结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主义的结果,而人类学关注的却不仅仅是这一种生活逻辑。对于社会学的“越轨”理论,人类学研究的贡献和启示在于,它不仅应关注行为者越轨后的社会反应或二者之间的互动,以及常人方法学意义上的越轨行为对越轨者的意义,还应试图理解这种不同的“意义域”或者不同的规范如何得以存在,更重要的是理解“意义域”或者“轨”的存在基础以及边界何在,在社区内,知识、价值和信仰是如何统一又是如果存在内部的冲突及其张力的,并把越轨和当地人的分类图示、经验图示及其个人的意义追求等联系起来。所以不适当行为、异常行为、自毁行为、不道德行为、反社会行为、犯罪行为等越轨行为并不是非要完全分离开来研究的。反之,社会学“越轨”研究的一大意义在于这一课题本身包含了鲜明的能动性和自觉性,这对于社会学特别是人类学结构主义带来诸多启示,因为他们过多关注秩序的维持,忽视了秩序的变迁。人类学这种社会内部秩序复杂性的认识往往和其对外部不同“他者”的研究相得益彰,比较的观点使人类学在研究不同的民族或社区时,根据不同的地理、生态环境来分析不同的秩序维持方法,去发现不同的思维,并通过研究“他者”增加了对自身社会内部秩序多样性、多元性的关注、宽容和反思。这种结合在中国的一个突出表现是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通过对中国复杂社会的研究所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并在方法论上注意到“模式”研究和类型学的比较。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真知灼见要求的还不仅仅是空间上对不同社会和社区的比较分析,对于文明社会而言,还需要结合长时段的历时性“考古学”分析,所以,对福柯等当代大师,我们已无法说清他们是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还是历史学家了。
(二)秩序的变迁
抽象社会的观点多以牺牲个体的能动性为代价,即使是充满活力的“越轨”研究,也往往被结构功能主义的解释所淹没。涂尔干认为犯罪是必然的,代表了社会结构的弹性。莫顿发挥了这种功能性解释,也深信是社会结构引起越轨行为,越轨行为在社会中具有积极的功能,并区分了其正功能和负功能。他们俩都认为一个对越轨行为容忍的社会不需要经历社会的分裂,这给秩序变迁留下了不多的余地。最近的研究越来越关注个体与结构、越轨和秩序的双向互动,认为社会结构不仅束缚个体行为,也能为行为带来新的或规范囿限之外的方向。吉登斯看到了结构的双面性(the dualty of structure),并作为他结构化(structuration)理论的核心。他认为社会结构不仅限制而且还促使了行为者生产和再生产社会生活。可以通过同时分析意义、规范和权力(meaning,norms and power)三个基本概念来理解此种生产和再生产,于是社会分析取向于“行为如何建构结构和行为如何结构性的建构”[11](P113),由此秩序变迁成为可能。
不同的是,福柯从权力运作角度认识到秩序的局限性,指出权力的绝对化之不可能,“自由”和不服从是权力运作的条件。越轨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社会中的个体对制度化的一种反抗和对个体意义的追求。但这种追求往往无法脱离社会制度所提供的情境,在某种程度上又恰恰强化了这一制度。他认为一种治理术,实际上是将权力技术与自我技术联系在一起。[12](P71)表面上看似单纯的程序化的治理术,往往以建立在伦理基础上的自我技术的合谋为成功要件,这点和道格拉斯所讲的“自然化”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也说明了社会和行为者个体、秩序和意义的必然关联。所以,规范对越轨实施着双重策略,一方面在分类图示中以禁忌或否定的手段,剥夺越轨在分类图示中的合法性,并以此反衬、强化已有的秩序;另一方面,秩序也通过各种稀释和溶解手段,来包容各种越轨,使其具有足够的韧性来应付各种意外。
越轨和秩序的变迁紧密相连,因社会学理论多源于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城市社会,而研究原始部落的人类学者也多出生于这一环境,故理论中的结构主义倾向都非常明显,人类学者尤甚,几乎包括了整个的地方性知识,假定了其各个部分的对应,强调“轨”的一致性和权威性,虽然这不仅是研究者的偏好,也是社会文化的外在性、自主性的反映,但易忽略即使是同一社会中也会有不同“轨”的存在和冲突。社会学越轨研究和人类学秩序研究的结合,应该是社会学者认为违背现存社会秩序、越轨的地方,人类学通过更深更广时空的比较研究去发现这一行为的“合理性”基础,在越轨中发现新的可替代性“轨”的可能性。而人类学在关注整体性的同时,不应只是关注不同因素之间的对应一致,或者即使是发现了冲突也只作功能性解释而忽略秩序变迁。社会学新的越轨理论已经关注到了“轨”和个体之间的互动,却没有认真研究个体在系统内部或者说社会制度、文化、认知等方面之间的冲突过程如何表现。近年来西方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等理论的兴起,是对原来绝对主义、理性主义、结构主义理论的一种反抗。格尔兹的“地方性知识”,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和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等的突破在于,他们既反对完全的结构主义也反对彻底的解构主义,而是在他们之间寻求一种张力的、变迁的秩序。
社会学与人类学理论的结合在研究中国这种历史悠久、地域辽阔,近代以来又历经巨大变迁的复杂社会时尤为重要。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开风气之先,随后关于中国乡村秩序的研究愈来愈多,如家族说、贸易圈说、信仰圈说、权威说、权力说、“关系”说、“面子”说等等,这些研究既有空间上的并存,也有时间上的错位。其背后隐藏的是“情”、“礼”、“利”、“理”、“法”等概念。韦伯关于“正当秩序”有效性的传统、信仰、章程说,具体提出了六个方面,也就是基于传统;基于感情(尤其是)情绪的信仰;基于价值理性的信仰;基于被相信是正当的成文的章程(又可分为基于协议和基于强制和服从),这是根据他关于社会行为的四个决定因素(目的理性、价值理性、传统和感情)的引申。可以看出,中国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也多多少少的体现了这几种情况,但具体的情况还要复杂,这几种解释难以反应中国复杂的社会实际。因为在乡土社会中,往往是多种因素重叠穿插,相互作用,以至于难以分辨。在中国社会有各种不同的“意义域”,也就存在不同的游戏规则,有时要讲法,有时要讲理,有时要讲情面,有时要讲“关系”。对这些规则的破坏,有的是“失礼”,有的是违法,有的是犯罪,有的是不合理,也有合情不合理、罪犯是英雄等现象存在,说明了中国秩序的复杂性,尤其是近代以来社会历经变迁,其间制度规范都几经更替,所以行为者能够能动地对待各种规范原则的选择和侧重,中国有“事在人为”的说法,看人看事重于看规范,正如闯红灯的人往往不是因为他没有看到红灯(象征规范)而是因为他看到没有警察(有权力的人),所以依法治国不只是学习西方制定法律条文那么简单,那么当前中国人的行为逻辑是什么?在理想层次上是否有各种规范之间行为取向的优先选择呢?多数行为者的实践行为和他们所期望的行为理想之间有什么差距呢?是什么影响了他们的实践选择和社会理想呢?这都有待于研究。前文所述理论对中国社会特别是乡土社会研究的启示在于,不仅要从国家的角度,而且从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角度,从多个层次上看待中国乡村的社会秩序,在此各个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很不够,因为即使是一普通的百姓也往往是生活在各个规范所编织的网络之中,这就需要做综合的研究。秩序和越轨都有其情境性和相对性,一个行为总是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才成为循轨或越轨行为,城市的秩序和乡村的秩序有差别,国家定义的越轨和乡土社区内的越轨也是不一样的。在中国这样复杂的社会中,乡土社会中的秩序和越轨就不仅仅是地方情境或国家背景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文化礼仪或社会经济变迁的问题,其间包含着特定的社区记忆、历史的文化图式和变迁的规范原则,它们的研究既需要不同学科学者的努力,也需要他们之间的借鉴与联合。
鸣谢:非常感谢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周星、蔡华、马戎、刘世定、麻国庆、王铭铭等老师,他们的课程和指导使本人受益非浅,对此文也多有助益。当然,文中的一切问题由本人自负。
标签:社会学论文; 人类学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社会互动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文化冲突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冲突规范论文; 法律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