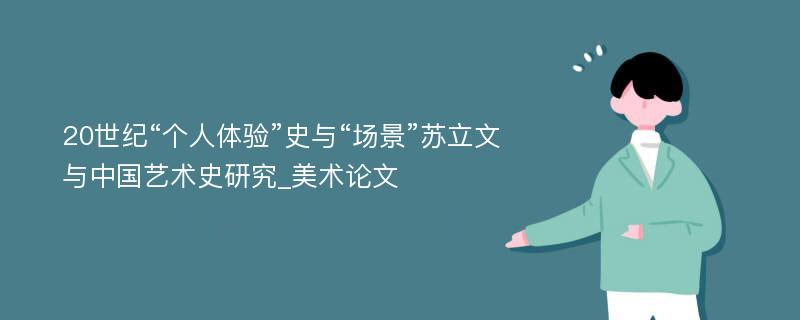
“亲历”的历史与“现场”的研究——苏立文与20世纪中国美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美术论文,现场论文,世纪论文,历史论文,苏立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21世纪以来,对20世纪中国美术的研究呈现出新的进展:一批综合性的通史著述,将美术发展置于社会背景之中,提出对20世纪中国美术文化属性的新见解,尤其重在阐述中国美术自身的发展规律;一些地方画派的研究相比以往挖掘出新的史料,对画派的历史渊源和传承走向作了深度探究;一批结合美术名家百年回顾展的研究,更是以作品和文献资料相结合的分析激发了新的学术认识与讨论。与此同时,中国美术史界也更加注重外国学者对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的成果,将其纳入中国的学术视野之中。这不仅彰显了新的文化条件下中国学界宽阔的学术胸襟,也构成了中外学术交流的延展。
对于20世纪中国美术的研究者来说,“苏立文”是个耳熟能详的名字。他从20世纪40年代来到中国,由此接触到20世纪中国美术和美术家,同时他也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发生的“现场”,见证和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美术变迁,并在“亲历”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开始20世纪中国美术的研究与书写。作为第一位将20世纪中国美术介绍给世界的西方学者,苏立文的研究特色不仅在于以西方学者的身份“远距离”地审视20世纪中国美术的发展,更在于他通过走进中国美术的现实,以“近距离”的目光深切观照中国美术家的创作与生活,考察各种“活态”,构成“远”与“近”相结合的研究视野。这种“远”与“近”交叉的视角历经70余载结出了丰硕成果,累累挂在《东西方美术的交流》《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艺术中国》等多部著作中。更为重要的是,在从事研究的过程中,苏立文还收藏了几百件20世纪中国美术珍品,使得他又以收藏者的身份介入了20世纪中国美术发展。因此,苏立文与20世纪中国美术是研究这段历史不能忽视的课题,更是20世纪中外美术交流史上的重要篇章。
要厘清苏立文与20世纪中国美术的关系,了解他从事研究的经过,不仅要梳理他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从事研究的不同特点,还要分析不同时期收藏的作品对他从事研究产生的影响,更要结合20世纪中国美术发展的实际总结他的评价标准和体系,由此才能走进苏立文的学术人生,走近他展开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的历程。
一、来到中国
源远流长的中国美术,在20世纪初期进入了一个风云激荡的历史时空,既遭遇到从传统到现代的巨大挑战,也遭遇到与西方文化碰撞的剧烈冲击,由此发生着深刻的变革。这场变革无论在艺术作品观念与文化内涵上,还是在艺术品种、技巧、样式与风格上,都使中国美术告别古典、走向现代。在建构中国美术现代形态的进程中,一代美术先贤怀抱新的文化理想,跨洋渡海、革新教育、传播新知,同时在艺术创作上反映现实、关切人生、重审传统、立足创新,涌现出轰轰烈烈的美术思潮和运动。
但是,中国美术进入新世纪的变革和变化,在很长时间里并没有进入国际学界的研究视野,此时的国际交流基本处在单向度向西方学习的状态。尽管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曾经有美术家努力在法国、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举办“现代中国美术”展览,但中国美术新的整体状态还未被西方学界所认识。西方对中国艺术的了解只能通过博物馆内少量的艺术品收藏来获得。1900年,当敦煌千佛洞的密封藏经被发现之时,西方的眼光开始关注中国艺术,但这种关注仅仅停留在对“他者”文化的兴趣上。到了20世纪20年代,一批西方汉学家开始转入对中国美术的关注,他们希望从美术的发展中寻求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但这一时期的研究还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美术史研究,主要原因是没有形成专门研究中国美术的队伍,特别是由于语言和现实条件等限制没有产生实际的成果。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尽管劳伦斯·希克曼、李雪曼等研究中国艺术的学者开始逐步刊布其研究成果,但研究范围仍局限于中国古代美术,“当下”的中国美术发展并没有进入西方研究的视野。40年代,在中国抗日战争如火如荼时期,苏立文作为国际红十字会的志愿者来到中国。他到达成都时,正值前蜀王建墓的发现,苏立文参与了前期发掘测绘工作,他在1945年《伦敦画报》上发表的专文就是关于发掘情况的介绍,这也是苏立文首次发表关于中国艺术的文章。历史就这样给苏立文提供了机遇,苏立文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进中国美术的研究,并在以后成为20世纪中西美术交流的桥梁。
二、结缘中国艺术家
如果说,来到中国是命运提供给苏立文的偶然机遇,那么走进中国美术则成为他毕生的选择与坚守。历史地看,苏立文是从走近中国美术家群体开始走进中国美术的。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中国处于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阶段,全国的艺术生态被战火分隔为不同地区,一部分美术家坚守在内地沦陷区,他们为宣传抗战奔走呼号;一部分美术家走向延安,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抗战美术,形成革命美术新的发展;还有一部分画家到了西南地区,在重庆和成都云集了一大批画家,特别是在重庆,会聚了大批名家坚持美术创作和教育。苏立文先后到达成都和重庆,在那里,他接触到了从临摹古代绘画而自出风格的张大千,这使他进一步了解到中国20世纪美术从传统走来的路径。通过与徐悲鸿等西学派代表画家的交往,他充分认识西方美术对现代中国美术的影响。而与傅抱石等行走于传统与现代间画家的结识,使他有机会理解中国画的笔墨语言特征,从艺术本体内部观察20世纪中国画的变革。更为重要的是,苏立文与庞薰琹等曾在上海发起现代艺术运动的决澜社画家保持密切联系,这使他及时了解到了中国美术中的现代意识和美术运动。丰富的交游使20世纪前半叶不同学派、不同风格的画家都进入到苏立文的视野,这些学派和画家在其研究中占有着同样重要的分量。通过多方面的接触,他一方面宏观把握了现代以来中国美术发展的文化特征,另一方面也认清了20世纪中国美术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等问题上的不同取向。这使得他尽可能地不带偏见,以宽阔的兴趣和眼光展开研究。
苏立文在艺术交往中结识了许多贴心好友,通过他们,他得以细致入微地了解20世纪中国美术发展的现实。在与庞薰琹的交往中,他看到庞薰琹作为决澜社代表画家的现代绘画风格,还看到他用工笔描绘西南少数民族形象的作品,由此认识到中国画家用传统方法讲述现代形式的创作语言,他这一时期收藏的庞薰琹的《家书》就具有这样的代表性。在和傅抱石的交往中,他注意到傅抱石运用中国传统笔墨的同时,吸收日本绘画经验和方法形成了自己的表现风格。苏立文的藏品中有一件《青海市集即景》,那是在他们夫妇成都家里的前廓上,画家吴作人创作完成的,在这件作品基础上吴作人创作的大型油画现藏于中国美术馆。这些身临其境的研究都被他记录在1959年出版的《20世纪中国美术》中。透过该书可以发现,苏立文在研究过程中尽可能把握当时艺术发展的动态,同时也根据交往的经历对代表性的艺术家进行重点描述。时间证明他的眼光和视角都是准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苏立文的研究既把握了中国美术走向现代的动态进程,也突出了艺术家个体的活动。这种动态与个案相结合的研究方式,是西方美术史学的传统,被苏立文恰切地运用到对中国美术的研究上。更为重要的是,他深入到中国20世纪美术发展的内部,既是历史的见证者,又是旁观者和记录者,由此激发起他持续的治学热情,产生了一系列“亲历历史”的研究成果。
三、走进中国美术史
抗日战争结束后,苏立文夫妇回到英国,他把对20世纪中国美术的了解内化为学术研究的兴趣和科学研究的方法。苏立文进入中国美术的专业研究是由“内”、“外”两种因素促成的。就外部学术环境而言,从20世纪中叶起,西方汉学研究进入革新阶段,其中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初露从古代向现代延伸的端倪,欧美一些重要博物馆开始陈列和收藏晚清以来的中国书画,西方艺术史学开始将中国美术问题的研究纳入严肃观照。就内部因素而言,苏立文在中国的经历使他对中国艺术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并转化为一种内在的力量推动他不断为之付出努力。越是在“海外”,就越是“遥想”中国,回到英国的苏立文立志成为研究中国艺术的美术史家,向世界介绍中国艺术的历史与发展。他先后进入哈佛大学学习汉学和中国艺术史,1951年还自驾车进行环美旅行,参观了沿途博物馆内的中国艺术品收藏。这一时期他的研究一方面聚焦于中国古代美术,力图从中国古代美术开始,建立通往20世纪中国美术的关联性结构;另一方面,他把对20世纪中国美术的研究纳入重点,在当时,这个领域在西方学界尚属空白。正当他开始着手这一课题时,他收集的许多研究资料在一次旅途中不慎丢失。庆幸的是,他在庞薰琹、傅雷等画家和朋友的帮助下,重新获得了许多珍贵的研究资料,其中包括画家们寄来的原作。黄宾虹的《松阴待渡》便是其中一件,这件作品一直被苏立文夫妇视为收藏中的珍宝。通过苏立文与当时画家的来往书信可以发现,隔海寄念,他关注着画家朋友们的安危,关注着中国艺术的发展,这些书信也成为今天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它们记录着一位西方美术史家在战乱的年代如何贴近了20世纪中国美术的情境,又以何种视野记录与分析他所亲历的历史。暂时别离中国的画家群体,苏立文因此能够将中国的现代美术置放在中西文化比照的视野中进行评述。在某种程度上,时空之隔与转换成为通观宏览、比照研究的催化剂,他成为既在西方也在中国第一个将现代美术置放在东西方交流的美术格局与坐标中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学者。这些成果在《东西方美术的交流》这本著作中得到体现。
四、南洋之旅
1954至1960年间,由于工作原因,苏立文前往东南亚,在那里从事艺术史教学与研究,教学之余也从事博物馆学研究和考古发掘工作。在东南亚工作期间,苏立文与当地的华人画家广泛交游。此时,苏立文进行的研究可视为20世纪中国美术的延伸研究,因为在新加坡的华人画家大部分都曾经在中国学习,他们的艺术既保留着中国艺术的风貌,也显示出进入南洋后的变革,这些也进入苏立文研究的视野,使得他的研究呈现出多维角度。在新加坡,他通过与画家钟泗滨、陈文希等的交往,充分认识了中国画现代发展的面貌和形态,这从他这一时期收藏的钟泗滨《甘榜日落》《吴环女士像》等作品,可见一斑。在南洋期间,他出版的第一本著作《二十世纪中国艺术》,是他多年来对20世纪中国艺术研究的成果,比较系统地梳理和介绍了20世纪中国美术展开的脉络。他对20世纪中国艺术进行的分时段叙述和由问题展开的分析,体现出实事求是的学风。在论述的体例上,则展现出现代学术的特质,而在内容上,毫无疑问,这本著作成为西方学界研究20世纪中国美术的开山之作。
五、跨越重洋的桥梁
苏立文从南洋回到英国以后的15年,是他对中国艺术、特别是现代中国美术综合研究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他的研究仍旧跨越古代美术和现代美术。一方面,他用心于中国古代史,其研究成果见于1961年出版的《中国艺术导论》、1962年出版的《中国山水画的起源》和1973年出版的《艺术中国》等,这些著作成为西方学界了解中国艺术的重要途径,成为许多所西方大学的美术史教材,多次修订、增补、再版,广受同行赞评。例如耶鲁大学艺术史系教授班宗华在评价《艺术中国》这本书时就提到:“三十年来,我一直选用该书作为我的课程教材。该书第四版经过全面修订,增加了反映今年(2006年)考古和艺术史研究的新内容,将继续成为最好的单卷本《中国艺术史》英文著述。除了苏立文外,没有任何中国艺术史家能有如此广泛的知识。”在这些著作中,他用一种超越西方艺术史叙述的语言描绘中国艺术,显示出国际性的多元文化史观。在这些著作中,1973年出版、1989年再版的《东西方艺术的交流》是最让中国和外国学者都注目和受到启益的研究成果。该书详细地将东西方艺术进行比较研究,论述了16世纪以来欧美与日本以及中国美术发展的交流,特别强调了艺术的差异性价值和艺术相互影响的作用,在史学观念上修正了以往艺术史书写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尤其是向西方学界打开了东方艺术研究的视野。他在书中论述的东西方艺术在相互交流中产生变革,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艺术对西方现代艺术产生的影响,别出新见。在本书中,最重要的是关于中国美术革命的叙述,涉及海派、岭南画派,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艺术争鸣,与新兴版画和现代运动等,同时还描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方针以及现实主义美术的发展,介绍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美术的变迁。有意义的是,该书还呈现出对当时活跃在国际画坛上的赵无极等画家的关注,显示了他多维的研究视野。
此外,苏立文还通过策划和组织展览推动20世纪中国美术在西方的传播。1967年,他在斯坦福大学策划的张大千个人作品展、1969年举办的他的个人收藏展等,都为西方学界直观了解20世纪中国美术提供了良好的契机。通过组织与策划这些展览,苏立文一方面得以更宏观地将20世纪中国美术置放于当时西方美术发展的情境中进行比较研究,另一方面在与画家的深入交游中他也多次获得新的收藏,由此使得这一时期的研究与收藏同时得到加强、相得益彰。例如,在策划张大千个人展览时,苏立文夫妇因此获得了《老梅新发》和《山岳雪》两件藏品,这两件作品基本概括了张大千用心传统而别具风格的创作特点。通过出版著作和策划展览等学术活动,苏立文为20世纪中国美术进入西方视野作出了积极贡献,也因此成为跨越重洋的文化桥梁。
六、研究常新
苏立文展开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的历程与中国社会变迁密切相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苏立文曾访问中国,但没有见到他的艺术家朋友。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他多次踏上中国国士,既与老朋友叙旧谈新,收集到大量新的研究资料,也仍然像当年一样,去结识更多新的艺术家,为中国艺术的新发展而欣喜,由此将向西方介绍美术的视野延伸到当代。这些成果见于1996年出版的《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该书全面论述了中国20世纪美术发展的历程,介绍了老一辈艺术家的创作,更以开放的视野介绍了许多中年的画家群体,也如同当年在中国西南的发现一样,书中还介绍了活跃的青年艺术生态。该书是他以“近距离”感受和“远距离”审视的方法,展开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的典型,特别是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艺术发展状态的描述,揭示了中国艺术与中国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时间到了20世纪的最后10年,百年中国美术正越来越多地进入国际学界的视野,中国当代艺术也成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热议之题,相比起西方对中国美术的一些单项(例如中国画)的研究和片段(例如中国当代艺术)的研究,苏立文为20世纪中国美术所作的通观性叙述,为百年中国美术的丰富史实编织了相互关联的网状结构,而且突出了中国社会变革的现实与中国文化对美术创作的支撑,从而建构起中国美术自身发展的文化逻辑。正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方闻评价该书时所说:“这是20世纪中国艺术的一本最系统和最有用的书,作为该领域的学术泰斗,苏立文教授通过丰富的结构呈现了20世纪中国艺术与审美、政治、文化与社会历史等方面的关系。”
纵观苏立文的研究可以发现,他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既注意将研究对象置于历史的语境中,突出20世纪中国文化整体中美术的文化价值,也运用比较的视野和比较的思维,对发生在中国内部的艺术价值和意义进行多维阐释;既注重艺术自身发展的形式风格分析,也从社会学角度探讨艺术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尽管他掌握的史料并不尽完整,但他对20世纪中国美术自身的“现代性”作出的阐释,他以“亲历”的方式书写20世纪中国美术发生的“现场”的经过,他为向西方和国际传播20世纪中国美术所作的贡献,是历史性的,也是独树一帜的,他的著作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苏立文与20世纪中国美术”也成为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学术命题。
